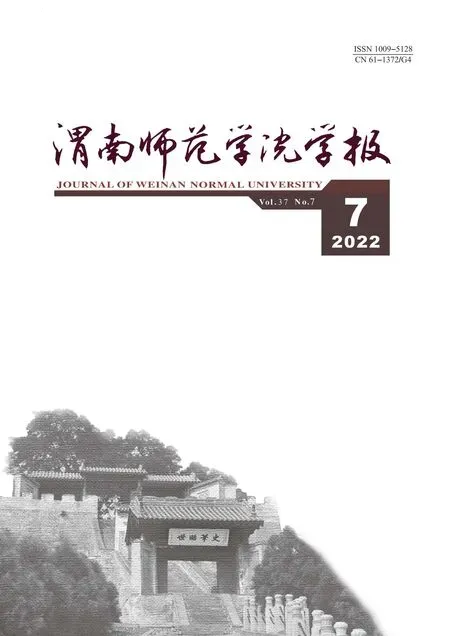吴起身世考论
刘 洪 生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关于吴起的身世或社会阶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极为简略:“其少时,家累千金。”[1]2165后世学者据此而认定吴起来自中下层的商贾或新富:“吴起出身于卫国一个商民家庭。”[2]78“从吴起家庭富有而政治上没有地位来看,他很可能是新兴商人之家。在奴隶社会里,富与贵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新兴的商人大量出现,他们拥有财富,但没有爵位和官职,是‘富而不贵’者。”[3]1“吴起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3]100历史小说《吴起传》,甚至描写吴起的父亲“是卫国有名富商”,“做买卖他是行家里手,可是却认不得几个字”,甚至说吴起的父亲是外出经商、路遇强盗、死于劫匪之手。[4]8-9
一、误判吴起出身商家的原因
对吴起的出身作如此判断,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史记》人物列传,一般都首先清楚地交代传主的宗族出身。“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1]2123而关于吴起的身世,只是说:“其少时,家累千金。”字面意思正是说其家靠累积打拼、艰难经营而致其富有。
第二,卫国本周武王之弟卫康叔的封国,也是前朝商都朝歌的京畿之地,大约在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之间。战国时期卫国东面与鲁国接壤,西北是赵国,南面是魏国,历史悠久,地理形胜,资源优厚,是中原水路交通枢纽和天下著名的商埠之地,商品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吴起出生的左氏中,即今山东定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吴起,卫左氏中人也。”[5]871这是一个“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地方。《史记·货殖列传》:“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1]3266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的第一个都城即定陶,由此可知此地的发达。今山东定陶,考古发现大量东周晚期金属冶炼、仓库、钱窖等旧址,也证明了当时繁盛的商业活动。因此,基于这样的商业环境,推论吴起的出身“可能是新兴商人之家”,似乎也合乎情理。
第三,春秋战国时期,以卫国左氏中(今定陶)为中心,产生一大批精通经营的商贾英才。孔子弟子子贡,即是卫国人,通达人情世故,擅长外交,尤善于贸易生财,《史记·货殖列传》:“子赣(即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1]3258还有号称天下“商圣”的陶朱公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1]3257裴骃《史记集解》:“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筭(算)”。’骃案:《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1]3256司马贞《史记索隐》:“计然,韦昭云范蠡师也。蔡谟云蠡所著书名‘计然’,盖非也。徐广亦以为范蠡之师,名研,所谓‘研、桑心计’也。《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其先晋之公子。南游越,范蠡事之’。《吴越春秋》谓之‘计倪’。《汉书·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则‘倪’之与‘研’是一人,声相近而相乱耳。”[1]3256-3257据此可知,计然作为范蠡的师宗,亦为卫国人,而且是一个特别精通经营算计的经济师。当然,卫国商人之大者,当是吴起稍后的吕不韦,亦是濮上人,曾经商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据称吕不韦其先乃姜尚,后“贾邯郸”,遇秦始皇之父——当时质于赵的秦公子子楚,以商人特有的灵敏,计算出“此奇货可居”,以赵姬作为特殊商品,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期货交易”。那么,在卫国左氏中(今定陶)昌盛的经商世风下,认为出生于此地的吴起乃商家子,似乎也理所当然。
第四,《史记》为子贡立传云:“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1]2201《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1]2505《孙子吴起列传》吴起传亦云:“其少时,家累千金。”三处均有“家累千金”之语,后世阅读极易受此心理定式的影响,将吴起之家也视为与子贡、吕不韦一样是与从商有关。但从诸多史料分析,吴起出身并非一般平民阶层或所谓的“新兴商人之家”,而是公孙贵族后裔。
二、吴起出身卫国公孙贵族的依据
第一,“家累千金”是食邑俸禄的“本富”。《史记》在交代吕不韦和吴起家庭背景时,同有一句“家累千金”,对吕不韦的“大贾人”身份及如何“家累千金”的“往来贩贱卖贵”商业经营活动,有非常清楚的描写。而关于吴起,是这样记述的:“鲁人或恶起曰:‘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仅仅是对手污名吴起是败家子,并没有具体指明其“家累千金”一定也是靠“往来贩贱卖贵”而获得。这里吴起的少时“家累千金”,应该是指《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谓“本富者”,即“封者食租税”“有爵邑俸禄”。当时列国贵族中,随着血缘关系的递减,有些虽已不在权力中心,却仍然享有丰厚的财富和特权。这样的公孙胄裔恰是后来吴起在楚国革新时废黜和清理的对象。
关于财富的问题,《史记·货殖列传》有所谓:“本富”“末富”“奸富”之说。“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1]3272田久川先生注云:“本富,指靠种田致富。”“末富,指靠经商做工致富。当时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奸富,指靠作奸犯科弄巧斗智致富。”[6]2727这里田久川先生对“本富”和“末富”的解释,是颇值得商榷的。“本富”,应是指《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爵邑俸禄”,即靠爵位封赏而致富;而所谓“末富”,是指无爵位封赏而致富,即传文中所说的“素封”,是“庶民农工商贾”靠正当劳动累积而致富,与之对应,那种“靠作奸犯科弄巧斗智致富”,被司马迁指为“奸富”。其实关于所谓“末富”,《货殖列传》的定义是非常清楚的:“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1]3272“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邪?”[1]3282-3283关于“素封”,司马贞《史记索隐》:“谓无爵邑之入,禄秩之奉,则曰‘素封’。素,空也。”[1]3272又云:“素封千户,卓郑齐名。”[1]3283张守节《史记正义》亦云:“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1]3272这些足以证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认为,最直接的致富就是靠爵邑俸禄而获得,所以称为“本富”;通过农、工、商业经营,积累而致,即“末富”,司马迁雅称其为“素封”,并认为其快乐和幸福可比于“王者”。然而又认为仅靠田间农业的劳作,确是最正当的生存之道,而致富却是不易的:“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1]3282“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1]3274因此,《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所谓“本富”“末富”,并非如田久川先生所云:“本富,指靠种田致富。”“末富,指靠经商做工致富。当时以农为本,以商为末。”按士、农、工、商——“四民”论的职业阶层分类,并以“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观念,来解释这里的“本富”“末富”是不当的。吴起少时的“家累千金”,并非一定是靠“往来贩贱卖贵”而获得,而更像是“有爵邑俸禄”“秩禄之奉,爵邑之入”之所致;吴起的身世,也并非一般商贾之家,而应是有拥有一定世袭特权的社会阶层。
第二,在卫国享有某种法律之上的特权。据《史记》吴起本传:“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1]2165细读史料,“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无论古今都是不小的犯罪,而吴起竟能从容“东出卫郭门与母诀”,如果是一般下层无地位的商家,无论如何难以做到,只能解释为,当时的吴起具有特殊的身份或地位。退一步论,即使吴起当时能潜逃,而其母并没有离开家乡,那些受害的三十余家,还能容许吴起的母亲安然家居,寿终正寝,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吴起的家庭一定具有特殊背景。此外,流寓鲁国的吴起,得到母亲死讯时,并没有依礼俗,千里奔丧,回乡葬母。有学者认为当时吴起“回到卫国,只怕还没有见到母亲墓就早已被人乱刃分尸了”[4]118。笔者认为,这恐怕不是吴起“母丧不归”的根本原因。真正使他做出这种反常之举的,是他“啮臂而盟”“不为卿相,不复入卫”的誓言。也就是说,是自己的誓言,阻止吴起停下了为母举丧的脚步。这不是“挟太山以超北海”一样的“诚不能”,而是不“为长者折枝”的“不为”[7]376;非客观不能,而是主观不愿。因此,才招致“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吴起虽曾“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仍可自由出入卫国的特殊身份。将誓言视作行动的准则,这是当时贵族的基本修养和身份的象征。《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进一步记载,郑庄公平定其弟共叔段叛乱后,又忌恨其母而誓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8]37后虽悔而不愿食言,就是将对诺言的恪守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姚鼐、钱穆、郭沫若、童书业等学者又认为,《左传》的作者正是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3]56-59
第三,在卫国的身份和地位远高于其妻族。《史记》将吴起与孙子、孙膑一起“合传”,意在突出描写作为兵家的吴起,在乱世之下辗转于鲁、魏、楚国之间,追求治国用兵之道,最后惨死的命运。正如清代史学家凌稚隆《史记评林》所说:“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9]476这样,司马迁在史料的选择上,必然是有所取舍的。也就是说,关于吴起的事迹,有些文献的记载,虽不见于《史记》中,但也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论,一定是不可信的。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之,其妻请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与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子毋几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于卫君,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吴子不听,遂去卫而入楚。”[5]871推敲这里韩非子的记载,分明可以看到一个身份独特的吴起。首先,他的妻族在卫国不是普通阶层,这可以通过其妻兄的言论及其识见为证,特别是其妻弟“重于卫君”的身份,绝非等闲之辈。如果我们不否认当时的等级制度,不否认婚姻方面门当户对的礼制,那么,吴起家族的地位也就可依此而知。其次,细读韩非子的记载,吴起决绝休妻一事,处处显示了他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对妻子、对妻族完全是高高在上的地位。其妻先是求助兄长以求再入吴门,后又拜托其“重于卫君”的弟弟,“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都没有能够让吴起收回成命。那么,就是说吴起连“卫君”的账也不买,更足以说明吴起非同一般的身份和阶层。正是这次冷酷无情的决绝休妻,得罪和结怨于其显赫的妻族,导致了吴起在卫国的“游仕不遂”[4]49-50。这种推断是合乎历史真实的,也进一步从其妻族之家的影响上反证了吴起特殊的身世背景。
第四,客居鲁国的联姻暴露了吴起的贵族身世。《史记》吴起传记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1]2165这就是吴起招致千古骂名的“杀妻求将”故事。对于事件的真伪,史学家郭沫若质疑:“这故事出于本传,然传文所据却只是一片蓄意中伤的谣言……除本传之外,别的书上没有看见过这同样的记载。司马迁自必有所本,但所本的恐怕也只是那位‘鲁人’的‘或恶’吧。但那位‘鲁人’的‘或恶’,从头至尾纯是中伤。我想,假如不是魏国的嫉妒吴起者如王错之流,便一定是后来楚国那些把吴起射杀了的反动贵族们所假造出来的。”[10]208-209但《史记》吴起传分别用史学家的叙述语言和历史人物对话两种形式言及其“杀妻求将”,应该确有其事。这里值得思考的是:其一,那位作为吴起妻子,又被吴起杀死的“齐女”是谁?或者说她是怎样的一个齐女,仅仅是一般的齐国民女吗?如果是的话,恐怕也不至于被鲁国权臣拿她和吴起的婚姻关系作为政治事件,来排挤和驱逐吴起。也就是说,这个“齐女”应该是一个颇有分量的人,足以引起鲁国各种势力敏感角逐。据此推论,作为齐国大夫的田氏,选择一个流亡鲁国的卫国人作为姻亲,这个卫国人,即吴起,除其好学和具有“源源不竭”之才外,也应与其具有相当的身份有关。其二,当时“事鲁君”的吴起,如何能在鲁国“娶齐女为妻”?这是《史记》和别的文献都没有交代清楚的事情,但也颇值得思考。根据当时列国争霸的形势,以及以“人质”处理“国际关系”的潜规则,这位齐女,应该是齐国“质于鲁”者之后。那么,够级别做人质客居敌国的人,其身份只能是齐国诸侯田氏。相应而言,吴起的身份也一定是能够被“齐女”之家所接受和认可的。
第五,拒婚魏公主再一次佐证了吴起的贵族阶层。《史记》吴起传:“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1]2167-2168吴起投魏后,因以尚贤著称的魏文侯的相知相遇,凭借自己杰出的才能,在魏国西部取得巨大战功,先后为西河守长达20余年。魏武侯继任后,娶魏公主的魏相公叔,忌惮于吴起的军功、威望,欲除吴起。依“仆者”之谋,利用魏武侯担心吴起难以驾驭的心理,设毒计让魏武侯以“延以公主”的方式联姻吴起,而从中作梗。最终,阴谋得逞,吴起拒绝魏武侯的联姻之约,而“惧得罪,遂去”。从事件发生的前后时间计算,至“田文死,公叔为相”时,吴起已年近五旬,即使这样,魏武侯仍愿以“延以公主”的方式相联姻,恐怕除吴起的功名和声威外,也与吴起虽是客卿,却具有与诸侯国君相当的贵族爵号或身价有关。当时虽然已是“礼崩乐坏”,但各诸侯国宗室之间的通婚仍相当看重门第爵位,这是他们没落前最后的荣耀。
第六,追求实现梦想但却“乱邦不入”。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卫国的设立是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武庚、管叔、蔡叔叛乱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周公同母少弟)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1]1589。故卫国可谓是周朝诸侯国中各种贵族最多、最具特权的一个侯国。周平王东迁时,卫国曾一度成为诸侯的首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三国分晋,田氏篡齐,卫国也逐渐衰败,甚至沦为魏、秦国的附属。这正是吴起少时“游仕不遂”的卫国现状。需要指出的是,吴起这里的“游仕不遂”,并非无任何仕位可居,而是他在卫国腐败不堪的政局下,深感理想不得施展,志不获遂。因此,吴起离开卫国是必然之事。关键是他出走的路线和选择的去向耐人寻味,先是流寓于鲁,再投奔至魏,最后止步于楚国,却终不至齐、秦二国。
当时的局势,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是列国中崛起势头最劲、最具发展空间的国家,自然也是游仕者实现自我价值和宏伟抱负最理想的地方。这对于吴起来说,应该是很清楚的,但他似乎是在刻意回避这两个国家。当然,吴起在鲁国时曾以少胜多,率军击败强齐;在魏国时又长期固守西河之地,强力阻止了秦国势力的东突。但在国家利益至上的角逐中,这一点恩怨,一定不是吴起不为这两国所用的主要原因。而是吴起对于篡逆的田氏齐国,对于一味崇尚攻伐的秦国,在观念中抱有拒斥感,坚持着某种操守和信仰所致,在吴起看来,国家的尊严和安危根本上说“在德不在险”[1]2166。
事实上,关于吴起离开鲁国,文献也有不同的记载。《韩非子·说林上》:“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无可为者矣。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吴起因去之晋(魏国在春秋时本属晋国,此用其旧称)。”[5]479这里韩非子从另一角度,解释了吴起离开鲁国而至魏国的原因。当时鲁国弱小,是齐国向西部扩张而首先要拔除的障碍。关键是鲁国内部,杀戮篡逆不断,毫无前景和希望。对此,吴起毅然主动离去。而不是如《史记》所记,吴起离开鲁国,是因为本土权臣的恶意排挤,被鲁君辞退和驱逐:“鲁君疑之,谢吴起。”那么,按韩非子这则史料,吴起正是在践行孔子所标榜的卿大夫的高贵品质:“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7]328
特别是吴起自魏国的出走,可谓是极其悲壮,毅然拒绝了最高统治者魏武侯的婚约,“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这是为尊严而争,绝不为利害而丧志,倒是有点孟子所谓的“大丈夫”气度,“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7]403。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唯利是图的商家子之所能为。
一切表明,吴起自卫国至鲁国,再至魏国,再至楚国的足迹,是行走在实现理想的人生道路上。而又固守某种高贵的、信仰性的东西,极似苏轼词中那只缥缈的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11]312。这只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环境下,训练有素而渐行渐远的贵族情怀。
三、结语
吴起少时即“游仕不遂”“曾学于曾子”,并著有《吴子兵法》,这些都说明吴起自幼受过良好而系统的文化教育。晚周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拥有知识文化,接受良好的系统教育,对于一般平民或普通商家并非易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作为中国最早的史志目录,系统叙论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余嘉锡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认为:“《汉志》所谓某家出于某官者,皆采自《七略》。盖古人之学,必有所受,故相传出于王官。刘歆考其学术渊源,亦似如此。”[12]在那个学在王官的时代,“百家争鸣”的诸子,无一不是贵族、没落贵族的后裔,或拥有隐秘而煊赫的身世,如: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商鞅、孙子等。具体如庄子,生活在当时的宋国,虽然一生“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13]1049,但却是“楚国贵族的后裔”[14]29等。
这样,综合诸因素看,吴起的身世和社会阶层不大可能是普通的“新兴商人之家”,而应是卫国没落的贵族或宗室之子。他不仅拥有不凡的理想和抱负,而且具有相当的操守和秉持,如“曾学于曾子”;拒绝魏武侯婚约;虽志在功名,却仅投身于鲁、魏、楚国,而终不践齐、秦国之境等,无不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贵族修养及其做事尺度。因此,在关于吴起评价问题上,似乎也就不宜绝对地认为他是一个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法术之士或冷酷的“赌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