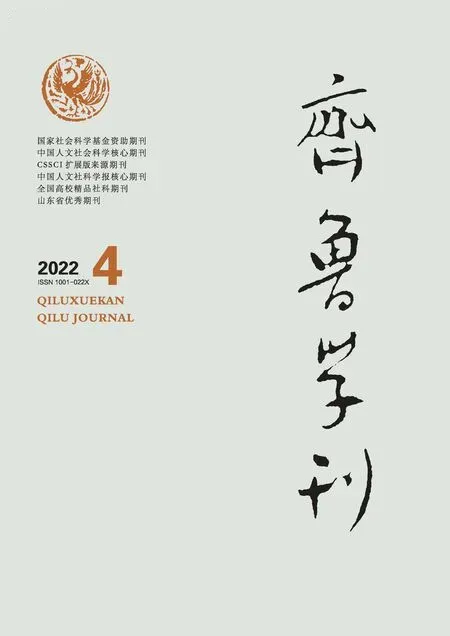由旧入新:梁启超对赵翼史学的认知转变
王云燕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湖北 武汉 430000)
晚清以降,随着社会变迁和西学东渐的加剧,传统史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诚然,西学的输入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史学近代化,但史学的近代转型绝非只受外来因素的单方面影响。中国自身的史学传统也会在激活后转入近代学术体系当中,成为创造近代史学的动力之一。换言之,近代史学除了受西学影响外,还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诸多学人已注意到,传统史学内部酝酿着变革的内在诉求(1)陈其泰认为:“外来影响只是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其内在根据还得从中国史学发展本身去寻找。传统史学中固然有大量糟粕,同时又蕴藏着许多精华,传统之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参见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第6 卷《近代时期(1840—1919):中国近代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1页。谢贵安也指出: “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也绝非只缘于西方史学东传的外部原因,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在中国传统史学内部求变求新的内在驱动下,受到不断输入的西方史学的影响,才转型成功的。”参见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6 页。,作为乾嘉学术精品的赵翼史学在近代的重新发现,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征。已有学人从现代史学的视野对赵翼史学的近代性加以阐释(2)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许苏民:《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第117 -122页;宋学勤:《赵翼史论的近代价值》,《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78 -82页;陈其泰:《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36 -144页。,饶有趣味的是,早在民国初年,梁启超在反思传统史学时就已意识到赵翼的治史方法与近代新史学有契合之处,并引起学界的强烈共鸣。截至目前,尚未有专文就此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致力于此。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对于赵翼史学的认知,清末民初的一代学人最具典型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自身的学术多出自清学,对清代学术的利弊得失有深切的体悟和感触。另一方面,生逢西学东渐,传统学术衰微之际,他们尤其想从传统学术中获取可以更新的资源,促使中国传统学术适应新的时代趋势,走上向近代学术转型的道路。最早以新思维、新方法对赵翼史学进行阐释的是“新史学”的开路先锋梁启超。梁氏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人物,被视为新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他一生以多变、善变著称,就治史而言,主要以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为基点,史学思想亦随时势变迁而不断变化。在新史学建构的过程中,梁启超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态度经历了由全面、彻底否定到理性分析、批判吸纳的转变,对赵翼史学的认知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呈现出由旧入新的特点。
综观梁启超对赵翼史学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初开创“新史学”时期,一是20年代回归传统学术之后。1902年,梁氏发表了讨伐旧史学的檄文《新史学》,文中有一处涉及赵翼史学,称: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7页。
此处并未对赵翼史学作直接评论,而是将其与司马迁、班固、毕沅等一同归为旧史家的代表。作为讨伐旧史学的檄文,《新史学》首先对“中国之旧史”展开系统批判,将旧史家的缺陷归结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弊和“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病,大有将传统史学全盘否定之势。在此语境下,被视作旧史家代表的赵翼自然也不能幸免。
细绎之,《新史学》发表之时正值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之际,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并非单纯针对史学本身,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诚如学人张越所言,批判旧史学的真正矛头指向的是当时的旧制度、旧政体,批判旧史学的实际意图,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保种保国,救亡图强(4)张越:《“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第94 -102页。。平心而论,梁氏之行文风格向来气势贯畅,不拘细节,若以客观的学术标准衡量他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显然是多有谬误和言过其实的。20世纪初年梁启超的思想较为激进,强烈呼吁破旧立新,尽管赵翼史学中蕴含着超越旧史学转向新史学的进步性因素,却未得到正视,而是将之一并归入旧史家之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梁氏既以赵翼与司马迁、班固等古代一流史家相提并论,一定程度上也表露出对其史学价值和学术地位的认可。
1904年,梁启超关于清学史研究的专文《近世之学术》问世,该文系统勾勒出清代学术的全貌,对赵翼史学也作了专门评论:
赵瓯北(翼)之《廿二史札记》,其考据之部分,与西庄、辛楣相类,顾其釆集论断,属辞比事,有足多者。其派宁近于浙东。或曰,其攘章实斋遗稿者过半云。无左证,不敢妄以私德蔑前辈也。其余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钱之流,不足道。(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614页。
与《新史学》不同,此文写作的初衷不涉及政治意图,单纯是为了学术研究。上段文字是梁启超首次正式从学术视角对赵翼史学进行的评析,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比较赵翼史著与钱大昕、王鸣盛著作的异同,二是对赵翼“抄袭”章学诚(字实斋)遗稿一说加以申辩,论述重点在于前者。自道光以降,学界逐渐接受了赵、钱、王三家史著齐名并称的说法,在此趋向下学人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三书的共性,梁启超则别开生面,致力于阐明其中差异。他发现,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虽在考史部分有相似之处却不可一概而论,并指明“釆集论断,属辞比事”是赵书区别于另外两书的独特之处。赵书如何“属辞比事”,此处未作说明,在梁氏后来的著述中有具体的阐发,且容下文再叙。梁启超早年在学海堂读书期间,接受过系统的考据学训练,对清学各派的治学特点十分熟悉。在他看来,钱大昕、王鸣盛属于吴派,即其所谓的“乾嘉学统之正派”(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614页。之一,赵翼的治学风格则与正派之外的浙东学派接近,有意凸显三人治学风格的差异。显然,梁氏已敏锐觉察到赵翼史学的独特性,但由于此时他的“新史学”构建尚处于破旧立新阶段,还未及用新史学的眼光重新加以诠释,只是从学术流派的归属上作简单辨析。
众所周知,学术流派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派和浙东学派虽是按地域做出的划分,但两派在学术师承、主张、治学特点等方面有显著区别。梁启超本人也有意对浙东学派和吴、皖两派的学术特色加以区分,尝谓:“浙东学派者,与吴派、皖派不相非,其精辟不逮,而致用过之。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614页。此处将浙东学派的学术特征归结为擅长史学、经世致用两点,或许赵翼史学正是因为符合这两点才被他归为浙东一派的“亲近者”。与之相对,吴派学人则专尚经学考据,钱大昕、王鸣盛二人皆以治经为主业,后将治经之法移以治史,遂有考史著作诞生。梁氏有言:“王、钱益推其术以治史学。西庄有《十七史商榷》,竹汀有《廿二史考异》,皆其支流也。”(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612页。他不但意识到赵翼史学与钱、王之学的差异,还尝试着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略加探讨,这是很大的进步,为后来从新史学的视角重新阐释赵翼史学奠定了基础。
就学术偏好而言,梁氏本人更倾向浙东一派,曾自言“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614页。。据此可推测赵、钱、王三家中,与浙东学派最为接近的赵翼似乎最受青睐。梁启超早年撰写的政论文中确有一些引述赵翼观点的例证。《烟士批里纯》一文中直接征引《廿二史札记》“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一条中有关刘备的评论(1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76页。;《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论及唐、宋以后奴婢种类增多的原因时称:“胡元盗国时,掠夺之祸极惨,汉人、南人率为俘虏以入奴籍(赵瓯北《陔余丛考》记之极详)。”(1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82页。据考证,《陔余丛考》一书并无相关说法,该观点实出自赵翼的另一史著《廿二史札记》的“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一条,可见梁氏在援引赵翼之说时未经审慎考辨;《新民说》中论及国家思想时也称:“吾国当胡元时代,士大夫皆习蒙古文(《廿二史札记》言之甚详)。”(1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6页。以上诸例皆梁启超明确标识引据赵说借以立言的明证,对赵翼史学的认同和接受程度可见一斑。借史言政是梁启超政论文写作的一大特色,他尤喜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素材,赵翼关于历代政治得失、社会风气变迁的史论与其写作风格不谋而合,故为其所欣赏。结合前面比较三家史著时所言“其考据之部分,与西庄、辛楣相类,顾其釆集论断,属辞比事,有足多者”之说,可推知20世纪初梁启超对赵翼史学已有所关注,不仅接受了他的史论,还注意到其“属辞比事”的独特著述风格,突破了传统视阈下的评判,朝着新史学的方向迈进。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他的新史学理论受西方史学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史学影响很大,对此学界已有专论(13)有关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渊源可参考: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5 -30页;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第5 -12页;李孝迁:《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第12 -18页。。他将历史重新定义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740页。还明确指出“近世史家”与此前旧史家在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上有明显区别:“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新史学》,第448页。梁氏将进化论引入史学研究,倡导近世史家用进化的观点研究历史,以社会风俗、民众心理等为研究重点,力求探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公理公例。尽管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赵翼史学中蕴含的某些进步性因素,如运用联系和变易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阐明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等(16)参见陈其泰:《乾嘉学术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论赵翼史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第59 -65页。,与新史学倡导的进化史观、因果律等颇为契合,却尚未引起梁启超的关注,这与此时他对待中西学术的态度有一定关联。20世纪初年,梁氏主要致力于宣传、介绍西学,鼓吹“史界革命”,破旧立新的强烈意识导致对西学的过度推崇与对中学的无视,此时他的新史学理论尚不成熟,还不足以从新史学的立场重新阐释赵翼史学。另一方面,深厚的旧学根基又在无意间影响着他的认知,尽管发掘出赵翼“属辞比事”的治史特点,却未能用新史学的理论加以解喻,直到他晚年回归传统学术之后才真正意识到赵翼史学的近代价值。
二
有关研究表明,梁启超的新史学之说本是在西学冲击下诞生,此后又一直在西学刺激与启发中成长,所以他的演变方向与辙迹,常因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而转移(17)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2页。。1920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后,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一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促使他从西方文明的迷梦中惊醒,在承认“欧洲文明破产”的同时,又积极宣扬东方文明救世的思想。此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复归”态度,在《欧游心影录》中甚至提出了关于重建中华文化的具体步骤: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1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4册,第2987页。
梁氏不但提出要尊重传统文化,还建议借鉴西方的治学方法来研究它,流露出“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1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4册,《新史学》,第3196页。的倾向,这对他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自欧洲归国后,梁启超逐渐淡出了政界,致力于学术史、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对待中西学术态度的转变,为梁启超重新认识赵翼史学提供了有利契机,当他参照西方的史学方法论准则去反思传统史学时,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赵翼史学。
20世纪20年代是梁启超学术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一生中几部重要的学术专著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均在这一时期问世,有关赵翼史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著述中。这一阶段,他对待赵翼史学的态度较之前更为明朗,关注重点也由史论转向史法,更从新史学的立场比较了赵翼史学与钱、王之学的差异。
1920年,梁启超全面总结清代学术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问世,论及乾嘉史学时重点突出了赵翼的史学成就:
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此处有关赵翼史学的评论与先前《近世之学术》中的说法明显不同,对比三家史著时,评判的重点已由史书内容转向治史方法。梁启超意识到,尽管《廿二史札记》中有关考证的部分与《商榷》和《考异》相似,但在史学方法的运用上却有独到之处。他明确指出,运用归纳和比较的方法胪列史实,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因,是赵翼史学区别于一般考史著作的关键所在。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评价视角由内容向方法转换,但这一变化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新、旧史学批评理念的分野。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归纳史学近代化的助力时,第一项便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2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页。。今人在对比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差异时,也指出“与传统史学相比,现代史学特别注重研究方法的运用”(22)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无疑,重视史学方法论是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传统史学中虽也有“史法”一词,但更多是侧重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领域的方法,系统研究史学方法的只有刘知幾和章学诚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无怪乎“新史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何炳松感慨:“唯吾国史籍,虽称宏富,而研究史法之著作,则寥若晨星。”(23)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页。清末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引起了国人对史学方法的重视,自20世纪初开始,史学方法就贯穿于历史的认识与研究之中。当梁启超以新史学的思维反思传统学术时,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赵翼史学与钱、王之学的差异,开辟了赵翼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学人许冠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自1920年起,梁启超的重要述作多爱以新眼光看旧学问,并图赋之以新生命(2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3页。。对赵翼史学的新阐释正是梁启超以新融旧治学倾向的极好例证,在他后来的学术著作中又对此反复加以申发,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1921年,梁启超的史学方法论专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问世,该书是著者结合自身多年治史经历和二十多年“所积丛残之稿”撰写而成,书中不止一次谈及赵翼史学。全书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将《廿二史札记》与《商榷》和《考异》一并归入考证之属,称:
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其他关于一书一篇一事之考证,往往析入毫芒,其作者不可偻指焉。(2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此处并未具体解释三书之差异,而是强调它们在考证方面的共性。稍后,在论述清代史学界之成绩时着重强调了《札记》的学术价值。梁启超宣称:“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2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6页。在他看来,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史学成果除《文史通义》外,只有《读史方舆纪要》《春秋大事表》《明儒学案》《廿二史札记》四家“卓然有所建树,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2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6页。。对赵翼史学的推重之意溢于言表,在具体介绍《札记》的成就时,又称:
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见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2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6页。
在梁氏看来,《札记》得以位居清代史学名著之列仍在于精湛的治史方法。只是,此处对赵翼之史法的诠释已与《清代学术概论》的说法不同。著者放弃了比较、归纳的新式说法,而是代之以“属辞比事”,以新融旧的意味更为浓厚。何谓“属辞比事”?“属辞比事”本是春秋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出自《礼记·经解》中“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一概念后来被用于史学研究,直接的含义是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按梁启超的解释,“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2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由此看来,“属辞比事”之法即排比事实、归纳史料,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实质为归纳、比较两种方法的综合并用(30)有观点认为,梁启超所谓的“属辞比事”只是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详参安尊华:《试论梁启超对比较研究法的运用》,《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2期,第62 -64页。笔者并不认同此观点,实际上,梁启超所说的“属辞比事”不仅仅包含比较的治史方法,比较中亦有归纳的成分。。梁启超不仅发掘赵翼善用“属辞比事”之法,还追溯其由来,指明自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已渐知使用此法,赵翼的典型性在于使用更广泛、技巧更精熟。赵翼是如何“属辞比事”的,梁氏在此并未说明,在后来问世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称:“《记》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书(指《廿二史札记》)深得‘比事’之诀。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31)梁启超:《读书指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页。梁启超形象地将赵翼治史的方法比作“采花成蜜”,这里重点突出了赵翼分类归纳史料,分专题作研究的治史特点,与清代一般考据学者的治学方法似乎并无二致。既如此,赵翼又何以成为“属辞比事”之法的标志性人物?直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问世,这一问题才得到较为详尽的解释。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又一著作,与《清代学术概论》堪称姊妹篇。两书虽研究对象一致,写作风格却不同。有学人形象的描绘说:《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少,言简意赅,是此期学术的鸟瞰图,重点侧重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多,内容充实,是此期学术的展览馆,重点侧重于“史”。前者高屋建瓴,气势非凡,论锋慑人;后者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学识服人(32)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344页。。与《清代学术概论》中言简意赅的归纳不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于铺叙、巨细兼顾的文风也反映在赵翼史学的评述上。该书汇集以往之说,在比较赵、钱、王三家著作的基础上,特别凸显了赵翼史学的特色,在篇幅和观点上都有所拓展。为方便比较研究,兹录全文于下:
三书形式绝相类,内容却不尽从同。(同者一部分)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比诸经部书,盖王氏《经义述闻》之流也。王书亦间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自序谓“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置旁参阅,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诚哉然也!书末“缀言”二卷,论史家义例,亦殊简当。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牴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自序语)但彼与三苏派之“帖括式史论”截然不同。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又有人谓赵书乃攘窃他人,非自作者。以赵本文士,且与其旧著之《陔余丛考》不类也。然人之学固有进步,此书为瓯北晚作,何以见其不能?况明有竹汀之序耶。并时人亦不见有谁能作此类书者。或谓出章逢之(宗源)。以吾观之,逢之善于辑佚耳,其识力尚不足以语此。)(3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7 -318页。
这段文字层次鲜明,观点独到,在综合先前诸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赵翼史学的认知。大致可归为以下四方面:首先,从内容上对赵、钱、王三家史著展开比较,突出各自的特色;其次,就赵翼擅长的“属辞比事”之法作具体解释,指明他运用此法的特点是不局限于狭义考据,而是多关注治乱兴衰和风气变迁,不执单词孤事以论史,多胪列相类史实比而论之,以得一代之特征;再次,以新史学的眼光重新衡定三家史著,推翻了考据学标准下“尊钱(大昕)抑赵(翼)”的排列次序,确立了“尊赵抑钱”的学术取向,肯定了赵翼史学的地位和价值;最后,在小字补注中重申赵翼确为《廿二史札记》作者,指明“攘窃他人”一说不足为据。综观整段文字,由浅入深,环环相扣,梁氏以史学发展的眼光,站在近代新史学的立场,重新审视赵翼史学与清学正统派的差异,突出他在史学方法上的进步性,构建出赵翼史学的新形象。
三
梁启超素以“流质易变”出名,他本人对此亦不讳言,曾坦陈:“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3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6页。这一特点也贯穿于对赵翼史学的理解中,纵观20世纪以来他对赵翼史学的认知, 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前后呈现出不同的认知特点。
20世纪初倡言《新史学》之际,梁启超将赵翼列为旧史学的代表,至20年代,态度为之一变,称赵翼能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一旧一新,形成强烈反差。转变之彻底一如他本人所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3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6页。。前一阶段,他的“新史学”构建尚处于破旧立新层面,尽管意识到赵翼史学的独特性却未及上升到新史学的高度,只是特别强调其史论。后一阶段,梁氏的知识结构得以更新后,则由破旧立新转向“以新融旧”,对赵翼史学的认知也从史论转向史法,突出其治史方法的优越性,完成了从新史学视角重新定位赵翼史学的尝试。单就对赵翼治史方法的诠释而言,在具体称谓上前后又有所调整,经历了由“归纳法比较研究”到“属辞比事”的转换,这一转变或许与他对归纳法的认识和态度有关。非但如此,每一次解释的重点和倾向亦有些许微妙的差别。概言之,梁启超对赵翼史学的理解由浅入深、由旧入新,充满一个“变”字。我们不禁好奇,不断变化的背后是否也有所坚守呢?
今细绎之,“变”中亦交织着“不变”的成分。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梁启超的赵翼史学研究总是伴随着与钱大昕、王鸣盛两人的比较,并表现出明显的“扬赵抑钱”倾向。运用比较法从事历史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学人杜维运考证,魏晋之际,比较方法已为史学界最为流行的治史方法之一(36)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23页。。梁启超对比较法十分推崇,无论是审时度势还是学术研究,都爱用比较的方法。他曾言:“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3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新史学》,第741页。又说:“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3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7页。他对赵翼史学的欣赏,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其擅长运用比较之法。比较研究的重点在于发现异同,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的过程中,梁启超对三人的相似度关注甚少,重在阐明赵翼史学优于钱、王两人的不同之处,并极力为之揄扬。这一举动是对清学视野下“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3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7页。学术格局的全盘颠覆,表现出明显的“尊赵抑钱”倾向,赵翼史学的优势得以凸显。
一般说来,清代考证家多擅长运用比较、归纳之法,为何梁启超推崇的对象不是清学正统派出身的钱大昕或王鸣盛,而是考据派的边缘人物赵翼?这个问题较为复杂,单从主观方面来看,三人之中,似乎赵翼的治史风格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念更为接近。尽管他与钱大昕、王鸣盛运用的治学方法相似,用途和目的却不尽相同。梁启超在考察治学方法的同时还兼顾到研究对象,他不止一次提及钱、王为狭义的考证,以“考证史迹,订讹正谬”为职志,赵书则“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为特长。据此可知,梁氏已深切体会到赵翼不同于钱、王之处在于,能透过此二法,发掘历史上富有深义的大问题。
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钱大昕和赵翼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治学风格,展示了不同的史学理念,王鸣盛则介于两者之间,不甚典型。三人虽同为考史,却同源不同流,就考证学内部而言,亦存在分野。杨树达先生曾将考证派分为两枝:“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洪筠轩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王西庄之所为是也。(西庄书至驳杂,兹据其一部分言之。)”(40)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55页。这一说法较为贴切地总结了钱大昕和赵翼两种治学风格的学术差异。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正统派以考证见长,主要借助归纳、比较之法订正史书的文本和典章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史料学的研究。赵翼则不拘泥于单个的字句与事实,多从宏观的大问题着手,并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归纳同类历史现象和事件,提炼出一个个独立的专题,展现了出色的综合概括和分析能力,已然突破史料学的范围。正如杜维运所言,“赵翼不是一位历史考据学家,而是一位长于历史解释的史学家”(41)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927页。。若从史学方法论的层面看,治史不外乎考证、解释两途。它们并非对立的关系,只是观察视角和思辨程度的不同,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均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史家由于学术背景和偏好的差异往往在取向上会有不同,赵翼史学中尽管也包含一些考证的成分,但较之钱大昕,他更偏重历史解释,钱大昕等正统派学人则略有“为考证而考证”的嫌疑。从梁启超的治史理念来看,虽然他认为考证是“史家求征信之要具”(4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页。,但又强调说明:
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是故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必也有说明焉,有推论焉……夫如是,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矣。(4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页。
他认为,考证只是史学研究的手段而非目的,单纯的考证研究并不能“尽史之神理”,还要对各类史料展开贯通的分析,注意历史事件横、纵两方面的联系,阐明历史之因果关系才能“语于今日之史”。他倡导的“新史学”从一开始即以追求历史规律为目标,因而《近世之学术》中评论清代考证学的成绩时不无感慨地说:“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4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609页。即使在20年代他的历史观发生很大变化之后,他仍然坚持治史的目的在于“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之活动之资鉴者也”(4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由此看来,以历史解释见长的赵翼比以考证见长的钱大昕更接近梁启超的“新史学”构想,故更受其喜爱。
结语
总体而言,梁启超对赵翼史学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旧入新的嬗变过程,随着学术理念的发展变化,他对赵翼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地更新与完善。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中国传统学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逐步接受和吸纳西方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调适原有的学术研究路向。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原本占据学术中心的经学急剧式微,史学成为既能弘扬民族精神又能与西方分科教育相对接的首要内容,渐由学术地理的边缘走向中心(46)罗志田撰有《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一文,收入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302 -341页。。这一转变为民国学人重新发现赵翼史学提供了历史机遇。“由经师弟子转变而为新史学家”(47)周予同:《经学和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6页。的梁启超最先摆脱经学的思维,适时地以新史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赵翼史学,发掘了其中蕴含的科学方法,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他的新阐释极大地丰富和升华了赵翼史学的特质,在民国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继梁氏之后,诸多学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赵翼史学,并遵循他开辟的路径,继续为之揄扬,他的新阐释也成为后继者们争相转引和参考的范本。在诸多学人的宣传和推动下,赵翼的史学地位空前提高,逐渐超越钱大昕、王鸣盛,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