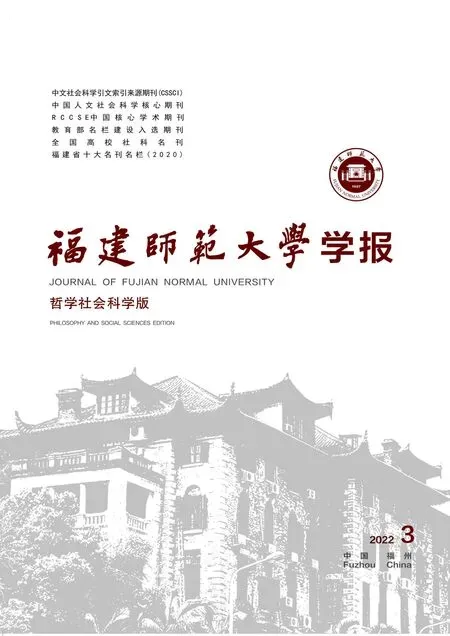网络平台、资本与主体境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
沈天乙,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随着网络平台逐渐崛起,对平台的理论思考日益成为社会生产、日常生活、数字空间中关注的焦点。在西方当代左翼语境中,网络平台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生存其间的主体境况往往是研究的重心所在。诚然,当资本作为“普照的光”(马克思语)已然散播到虚拟空间,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必要将对资本的研究延伸到网络平台等新的资本运作空间,“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进而“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第1版。
在平台资本问题上,部分西方学者指出:“随着制造业盈利能力的长期下滑,面对生产领域的低迷状况,资本主义已经转向数据,并将它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和活力的一种方式。”(2)[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页。另一些学者则基于这种状况将平台空间视为新的政治斗争场域,并认为其中包含新封建主义的消极要素。(3)参见:Benjamin H.Bratton,The Stack: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Cambridge & London:The MIT Press,2015,pp.3-17.按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 Nick Srnicek)的划分,网络平台包含: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精益平台等(4)⑤ [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7-97、7页。。本文将以承载了直播等文化内容的网络社交平台为切入点,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探寻网络平台资本与主体的关系,进而为当前应对平台资本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一点建设性意见。(5)伴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型经济模式的发展与普及,国内外学界近五年来逐渐将视角聚焦于平台与资本的关系研究。2016年,尼克·斯尔尼塞克( Nick Srnicek)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将互联网平台视为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产物,平台通过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垄断,进而成为维持经济增长和活力的方式。同年,国外学界就新兴平台经济所建构的平台-资本关系问题,从不同维度展开的回应,主要涉及平台对生产结构的改变、对劳资关系的重组以及平台的垄断化趋势(参见P.Langley和A.Leyshon,M.kenney和 J.Zysman以及A.Schwarz的相关文章)。在此基础上,国外左派学界自2016年起亦开启了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的思考,进而提出了构建“平台合作主义”的主张(参见 T.Scholz、R.L.Siftung、Evangelos Papadimitropoulos等学者的相关文章)。随着平台运营模式在日常生活中的蔓延,平台与资本的关系亦成为国内学界所遭遇的现实问题;2017年以来,国内学者不断推进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研究。尽管受到国外研究的一定影响,但国内学者在此问题上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将平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新形式展开研究与批判。对此,部分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角指认了平台资本主义所加剧的社会异化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参见夏莹、蓝江等学者的文章);部分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缺陷及发展趋势(参见谢富胜、王彬彬等学者的文章)。随着研究的深入,2020年以来,国内学者不断就平台传播及平台合作等问题回应了国外学界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相关探讨(参见姚建华、马云志等学者的文章)。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从纵向就平台资本主义兴起所引发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横向将平台资本所呈现的具体形态之一——平台文化产业资本作为着眼点,基于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探寻具体平台资本条件下的社会经济机制变迁及其主体效应。
一、网络平台:文化工业的延伸领域
当前,网络平台已然是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在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语境下,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道尔诺(Theodor Adorno)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融合视为文化工业的重要效应:“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6)④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8、111页。网络平台作为文化工业的延伸产品,加深了这种经济与社会的融合。在此前提下,网络平台借助文化,将经济权力的要求加之于主体之上。这既是一个社会机制的问题,又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正如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指出的:“康德的形式主义还依然期待个人的作用,在他看来,个人完全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然而,工业却掠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然而在今天,这种秘密已经被揭穿了。如果说这种机制所针对的是所有表象,那么这些表象却是由那些可以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或者说是文化工业计划好了的。”(7)④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8、111页。网络加深了文化工业对于主体认知的利用和影响。按照康德哲学所揭示的,主体的认知是“感性经验”和“基本概念”之间综合。文化工业所做的,是以工业化生产的方式来生产“基本概念”,后者在文化上表现为“图式”。由此,主体按照文化工业所设计好的图式来思考,即将文化工业设计的图式作为认识框架来接收感性经验。
这种状况在网络时代进一步加剧。今天,伴随着网络“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数据越来越成为企业及其与员工、客户和其他资本家关系的核心。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8)⑤ [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7-97、7页。。在消费者消费网络文化工业产品的过程中,文化消费的偏好以数据的方式被收集和分析。依靠对于文化消费行为的数据统计,网络平台可以以所谓“个性化”的方式来为不同消费者提供不同的节目。这一点无疑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言及的,文化工业对于主体认知的塑造的延伸和强化。
这其中网络平台所起到的作用正是“先验综合”,它作为吸收、释放认知信息的中介,实际上正在为每一个网络主体建构其独特的认知结构。但是,在这个认知结构中,起作用的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范畴。换言之,那些属于人的认知范畴,如时间性、空间性、因果性等,在网络平台中都以计算机语言重新排列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关联性替代了因果性,所谓的“休谟问题”在网络平台中变成了伪问题。因为因果性在平台中只是一种表面的效应,背后起作用的是数字化技术。在此条件下,网络平台用户的认知范围会被固定到某个特定的范围,从而使得主体的视域也被局限于某个狭小的领域。
与这种认知框架重建联系在一起的,是更为精确的广告投放。以网络购物网站为例,凭借数据统计的方式,网购平台会建立个性化的“物品认知框架”。商品生产者借助于网络平台,不断生产出个人消费者所喜好范围内的商品,但同时又要再造出些许差异。这种最低限度的差异不断建构了主体的消费欲望,同一与差异以庸俗的方式“辩证统一”。造就这种差异的,恰恰是作为文化工业的网络平台。即网络通过文化生产的方式,不断建构、固化网络主体的既有认知、文化结构。当这种固化与商品生产结合起来时,商品价值的实现无疑加速了。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客)与认知(主)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在平台网络中,经济结构直接制约着认知结构。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人的认知结构从属于资本逻辑。
不过,这种状况不同于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所分析的“现实的抽象”(9)[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页。。在网络平台认知中,起“现实的抽象”的作用的不是商品交换,而是大数据技术。在传统社会中,文化是社会经济与主体心理之间的桥梁。生产方式借助于生活方式的塑造,影响人的思维方式。今天,当文化变成了工业,当文化对象成了生产的对象,当文化对象成了网络中的虚拟对象,经济与心理将以更直接的方式相联系。有学者指出,在当代社会,“经济人”转型为了“心理人”,(10)[法]吉尔·利波维茨基:《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因为象征和符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网络所放大的文化工业中,我们可以看到,“心理人”之所以崛起,恰恰是因为个体心理已经被纳入到了经济的范畴,因为个体的心理结构在被文化工业不断地塑造。这一点,在网络文化中表现得更加强烈,却也更加隐蔽。在更深的层次上,网络使得文化的升华效果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的是人与社会压抑的关系的变化。人在网络社会中不再以升华来对抗压抑,因为压抑表现为快乐,而升华则发生了俗化。
二、主体需求的改造:网络平台的俗化效应
在大众的心理层面,网络的娱乐方式在效应上缓解了大众的心理压力。事实上,网络的文化机制,进一步改变了既有社会中压抑与升华的关系。按照精神分析的传统观点,文明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人类本能的压抑。(1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1页。当人类按照文明的方式,按照社会的方式来规训自身的欲望和行为时,人总是遭遇着一定程度上的压抑。对此,文化(比如艺术和文学等)以高尚的方式解决着人类的压抑问题,这个方式就是升华。在升华的过程中,人的需求改变了,由此相应变更的则是人与压抑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文化工业的影响下,压抑与升华的关系变化了。作为处理压抑的途径,“文化工业没有得到升华;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压抑。它通过不断揭示欲望的肉体、淌着汗的胸脯或运动健将们裸露着的躯干,刺激了那些从未得到升华的早期性快感”(12)[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在既有的形式下,艺术形式是通过提高需求的品位,来拉近需求与升华之间的距离,从而削弱压抑的程度。而在文化工业普及的时代,被工业生产出的艺术则是通过降低升华的门槛,来缩减需求与升华之间的距离,从而减缓压抑的影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将这种现象称为“压抑性的俗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在此,俗化即“去-升华”。在网络时代,伴随着网络游戏、视频网站、直播平台的发展,大众以更加俗化(去-升华)的方式来对抗压抑。马尔库塞指出,在这种过程的背后,真实地发生着商品化的过程:“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所以,重要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价值。从根源上看,现状的合理性和一切异己的合理性都服从于此。”(13)④⑤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7、60、59页。
换言之,伴随着艺术成为商品,升华过程则变成了可以购买的服务。这一点在网络直播平台的娱乐方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与艺术创作者的交流无需以复杂繁琐的方式来实现,观看者只需不断赠送虚拟的礼物,就可交换到“艺术”表演者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观众的需求亦在不断地缩小到欲望,甚至性欲的范围,所谓的解放,与其说是一种解放,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即性欲对爱欲的吞噬(1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77页。。对此,马尔库塞认为,“由于降低爱欲能力而加强性欲能力,技术社会限制着升华的领域。同时它也降低了对升华的需要”(15)④⑤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7、60、59页。。因此,“就像高层文化中的俗化趋势一样,性领域中的俗化趋势是对技术现实进行社会控制的副产品。这一趋势一面扩大着自由,一面又加强着统治”(16)④⑤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7、60、59页。。
在“压抑性俗化”的视角下,网络平台生活中的“解放”,实际上是现实矛盾的转移。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讲,这并非快乐原则克服现实原则,而是现实原则在进一步吞噬快乐原则。换句话说,快乐在网络平台中已然成了被规训和控制的对象。主体的快乐以网络平台给定的方式展开,这正是文化工业图式化发展过程的延伸。如同性解放一样,网络生活的自由意味着其他领域的自由被全面侵蚀。那么,自由究竟被什么侵蚀?答案是正在被生产侵蚀。准确地说,即自由被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生产侵蚀。
这个过程中,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经济人”,这实际上也是福柯探讨生命政治的背景。作为生产者,主体被压抑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意味着,在生产中,人的主体性不断地被磨灭,于是人只能在生产之外的领域寻求主体认同,这个领域就是消费。由此视角出发,网络社会亦是消费社会的延伸,只不过在网络中,人们消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商品,而是人的身份认同。在网络时代,文化工业与消费社会的结合更为紧密了,广大网民作为新的消费者,通过对网络文化的消费,满足了自身对于认同的欲望。其中,满足的方式包括一系列发表意见、抒发情感的平台,如中国网络中的微博、豆瓣、B站、贴吧等等。网络游戏也是相似的平台。一方面,网民可以在其中购买与身份认同相关的虚拟产品(如游戏装备);另一方面,以网络游戏的方式,主体无需花费精力思考和学习如何升华,只需要通过消费就可以反抗压抑。这正是马尔库塞所谓“压抑性俗化”现象的典型表现。
在回应文化工业的问题上,马尔库塞创造性地改造了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压抑”的关系链,使之成为更具历史性的“操作原则-额外压抑”关系链。这一理论创造,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作为文化工业的网络具有重大意义。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定义“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额外压抑:这是为社会统治所必不可少的约束。它与(基本)压抑的区别在于,它是为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作的必要‘变更’。操作原则:这是现实原则的现行历史形式。”(17)②③④⑤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25、26、26、27页。
由此出发,按照马尔库塞的视角,我们可以以一种接近于马克思的方式回应文化的问题。不可否认,文明和文化的产生不可避免地带来压抑,因为人不可能纯粹按照本能的方式行动,但如果由此就批判整个文明和文化本身,理论则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对于网络及其文化和生态问题而言,亦是如此。应该说,马尔库塞的视野为我们思考网络平台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即按照马尔库塞的思路,网络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必须被消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网络的负面效应所带来的压抑,而在于特定历史形式对于网络的利用,以及由此产生的额外压抑。在当代社会形式下,“力比多被转到对社会有用的操作上去,在这些操作中,个体从事着同自己的机能和需要根本不协调的活动”(18)②③④⑤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25、26、26、27页。。甚至,“爱欲操作也已被纳入社会操作的同一轨道”(19)②③④⑤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25、26、26、27页。。于是,“在操作原则统治下,人的身心都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20)②③④⑤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25、26、26、27页。。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是人的自由时间也被资本所收编:“在后期工业文明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很可能要冲破压抑性统治所规定的限度。直到这时,才由大规模的操纵技术产生了一个直接控制闲暇时间的娱乐社会。”(21)②③④⑤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25、26、26、27页。
在当代社会的状况下,社会形式将生产之外的所有空余时间也纳入价值增殖的过程,这是消费社会的问题。网络平台在实质上放大了这个问题,尽管这个过程不涉及直接剩余价值的剥削,但它却加速了剩余价值的实现。由于在网络平台互动生活中,网民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广义上的消费者,因此他们也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被吸纳到生产过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隶属于再生产环节,这是我们往往会忽略的一个维度。
三、网络平台与资本的再生产
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消费者,网络平台中的主体实际上从多个方面参与了资本的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再生产过程具有多个层次。
第一,网络平台与流通环节。以网络平台游戏为例,众多网络游戏在今天成了货币支配的空间,流行的游戏币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成了硬通货。于是,在网络游戏中,商品的二重性都以虚拟化的方式再现。游戏装备的虚拟使用价值和游戏币的虚拟价值在网络游戏运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网络游戏的普及,游戏币所起的作用甚至不仅是交换的中介。换句话说,游戏币不仅是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还是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与之相关,我们在游戏界中也广泛看到兜售稀有游戏装备的行为。当然,这些活动背后存在必要的技术基础。比如,手机游戏成了当下网络游戏的主流模式,游戏玩家可以在随时随地参与到虚拟的战争中,只要手中握有轻便的手机。游戏设备的灵活性,促使网游货币的流通性加强。而伴随着游戏币具有了贮藏的功能,它也不仅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作为资本的货币。于是,在一定范围内,游戏空间在以金融的方式运作。这是当代网络游戏的一个复杂之处。甚至,我们可以在反讽的意味上,将这种现象称为“网络资本”,因为游戏币所牵涉的已然是体系的再生产问题。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如果说网络游戏是文化工业的新型形态,那么它的复杂之处在于,它的内部甚至衍生出了次级的交换体系。这种发达的交换模式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工业产品的流通效率。由此,网络作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不但改变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还改变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借助于网络虚拟货币,网络吸纳了大量真实货币以实现自身体系的再生产。在此维度,网络游戏参与者实质上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参与者。
第二,网络平台与消费环节。在以文艺为导向的网络中,网络平台以美学包装的方式加速了购物者的消费节奏。例如,在以文艺风为主要风格的豆瓣网上,平台结合自身的风格打出了一系列以文艺为名义的购物导向。从网站发展的历史看,由豆瓣网所打造出的一个重大概念是“手工制作”,通过引导广大文艺青年发表自己手工制作的作品的图片、视频以及相关文章,豆瓣网塑造出一种独特的主体性氛围。这种氛围得以构建基于一点,即手工制作从概念上是对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反叛。换句话说,它用具有“手掌温度”的方式抵抗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意义上的冰冷的机械化复制(22)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李伟、郭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5页。。另一方面,区别于工业化生产的同一性,手工制作反映了手工制作的主体个人的主体性,从而满足了广大文艺青年的意识形态幻象。
对此,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第一,网络上宣传的手作物在价格上往往高于相似的工业品。第二,相比于工业制造的稳定性和精确性,手工制作品的质量具有不稳定性的特质,而且我们无法区分手工制作者的工艺水平。在此,我们无意于为工业制造献上赞歌,尽管马克思时常赞颂工业生产的生产力(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相反,我们必须指出手工制造这种有别于马克思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和趋势的对象在经济运行维度上的机制。
实际上,豆瓣网所打造的手工制作的概念,并非身处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异托邦”,它参与的是另一种工业生产,即文化工业生产。作为文化工业的延伸,网络平台所生产的不仅是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商品,而是一种虚拟的概念、能指。在网络平台中,生产已然不仅仅是物质形态商品的机械生产,而且是概念的机械生产。这使得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所提到的仿真原则,在网络社会中找到了实体。在文化工业的视域下,“仿真原则”是马尔库塞所发展的“操作原则”的延伸。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论推演,“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吸收了。以后,仿真原则将代替过去的现实原则来管理我们”(24)④ [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3页,第69页。。在此状况下,符号生产和交换变得可能,网络则将仿真原则在实体上呈现出来。于是,“新一代符号和物体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这是一些没有种姓传统的符号,它们从没经历地位限制,因此永远不需要被仿造,它们一下子就被大规模生产”(25)④ [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3页,第69页。。这构成了网络符号不断再生产的动力基础。当符号被纳入生产的体系,过往的象征立即被解构为符号,象征成为有一定秩序的符号的组合。如今,秩序被全面解构,符号可以以新的秩序被重新组合起来。网络平台文化恰恰起到了重新排列符号秩序的作用。在网络化的语境下,这种符号的重新排列组合被称为“恶搞”。网络以符号再生产的方式,拓宽了文化吸纳生产的能力,并加速了剩余价值的实现。
第三,网络与主体再生产环节。在广义上,主体的再生产是物质生活的再生产环节之一。网络社会还涉及主体的再生产。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广大工人亦可以方便地接触网络生活。重要的是,网络文化生活成了工人休闲时间的重要活动,甚至成了工人生活的基本文化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对于文化工业产品网络的消费,构成了其自身再生产的一部分。借助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考察网络文化在再生产方面的效应。在阿尔都塞的语境下,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有效地起到了再生产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意识形态将主体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下,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下的主体视为结构的代理人,即当事人主体(agent)。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26)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5、70页。。由此,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主体间的结构关系方面开启了讨论。他认为,意识形态在其运作中,会将个体质询为主体。(27)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5、70页。个体对于认同(identity)的追求,成了整个质询(interpellation)过程的关键推动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现代性社会权力中,权力的匿名性使得主体获得认同的过程变得崎岖。换言之,在现代性社会,个体难以找到绝对的权威及其人格化代表作为自己获得认同的见证人。然而,恰恰是这种困难性,成了个体不断追寻自身主体性的推动力。
网络平台无疑加深了这种权力的匿名性和分散性。这使得个体寻求认同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这种匿名性让个体产生了移情(transference)的效应,个体总是假定外部存在着一个“无所不知的大他者”。后者作为认同的允诺,是一个吸引主体的诱饵,这一点恰恰被意识形态所利用。网络平台,尤其是网络社交平台,放大了这种意识形态。
在网络社交媒体中,个体以追求认同为契机,以展现自身的个人生活为手段,追寻着社会大他者的认可。于是,在网络社交平台(微博、朋友圈等)上,我们看到了五光十色的生活掠影,这构成了新型的“景观社会”,网络平台成了“巨大的景观的积聚”。(28)[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对网民而言,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的关系发生了颠倒。摄影、上传并不再仅仅是对于美好生活的记录。相反,人们为了在网络上追求认同,而在现实过程中过所谓的“美好生活”。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在消费、享受美食之前,人们往往“忍饥挨饿”,先拍照上传网络平台。这样,在我享受美食之前,就有大他者“先替我享受”。由此,一系列不断涌现的“网红店”应运而生,它们又在现实社会中形成了新的景观。平台上的电商则通过数字化场景整合线下资源和线上交易,“建构起跨行业、跨地域、跨系统的交换空间”(29)国秋华、程夏:《移动互联时代品牌传播的场景革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33-137页。。这样,我们不但看到了主体的再生产,还看到了景观的再生产。
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网络从手段颠倒成了目的,大众为了网络认同而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被煽动的消费行为。而且,这种消费并不是一次性的。网络上,大众共同建构的意识形态“大他者”,以匿名权力的形式,不断地召唤着新的需求。在此召唤下,大众个体不断形成新的认同需求。有趣的是,恰恰是个体寻求认同的过程本身,回溯性地构架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离开个体对于认同的欲望,意识形态从来都无法实现,这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研究给出的教益。于是,这种现代性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得以在网络上继续强化。
不过,阿尔都塞所揭示的并非问题的全部。主体再生产所涉及的,不仅是抽象结构的再生产,而且是具体经济范畴的再生产。简单来说,主体的再生产实际上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当然,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前提。而在这个前提背后,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变迁,即劳动和劳动资料的分离。分离的发生并不仅仅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共时性的过程。换言之,原始积累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当下不断发生的事件。这一事件在网络时代中正在隐蔽地发生。比如,网约车机制。在一般观点看来,网络打车平台作为工具,促进了公共交通。从劳动过程看,事实确实如此。不过,正如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所指认的,与劳动过程同时发生的,是价值增殖的过程,这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在网约车的数字化经济中,平台所做的是将劳动和劳动资料进一步分离,这种分离具体表现为驾驶劳动和平台技术的分离。平台技术在此充当了工厂的角色,只不过这个工厂并非实体的血汗工厂,而是优雅的“云工厂”。司机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在形式上从属于平台“云工厂”,而且在实质上也从属于平台“云工厂”,受平台“云工厂”技术的调配。由此,网约车平台不但增进了资本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且增进了资本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也就是说,马克思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区分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9页。,在今天网络云经济中依然有效。
于是,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主体被吸纳到平台系统之中,因此主体的再生产不仅是抽象的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再生产,而且是作为经济范畴人格化的再生产。换言之,主体的再生产在此也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这个维度上,网络一方面通过文化工业的建构满足着劳动力再生产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平台将更多的主体吸纳为有效的劳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更多的剩余流动人口被吸纳到资本的体系之内。在这种语境下,所谓的后现代的灵活性和流动性,恰恰是资本积累方式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的展现。(3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8页。
四、网络平台中的资本及其主体效应
个性和风格是网络社会主体所追求的重要对象。建立在网络基础之上的文化工业,将风格的打造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标签,这一点是之前文化工业生产逻辑的延伸。在讨论文化工业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严肃探讨了当代文化背景下的风格问题。他们认为:“风格需要它能够吸收和消费的惊人的生产力。它会像恶魔一般,僭越人们以往从文化习俗的角度出发对真实风格与伪造风格之间的区分。一种风格之所以被称为是伪造的,是因为它没有依据形式的那种无法驾御的冲动而被强行制造出来。”(32)④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6、140页。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艺术风格不仅不断被创造,而且不断被制造出来。于是,主体在不同风格中寻找到的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由此,“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因为“个性不过是普遍性的权力为偶然发生的细节印上的标签,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接受这种权力”。(33)④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6、140页。在网络意识形态背景下,风格的问题变得更加普遍和轻盈。这是因为,网络文化所加深的文化后现代性,破坏了既有的象征体系。传统社会中既定的象征,意味着一种固定的符号排列秩序。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中,这种秩序被全面打破。当秩序链断裂,剩下的则是漂浮的符号,一如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所说的“漂浮的能指”(34)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这种文化状况为网络文化的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于是,不同符号之间的不同排列组合,致使网络文化中生成了前所未有的风格数量。因此,网络不仅促进着主体的生产,而且拉动了风格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这二者又是紧密相联的。因为风格恰恰为主体的建构提供了不同的位置空间,以供主体投射欲望。在这里,欲望不仅是需求,而且是被承认的欲望。通过对风格的生产,文化工业也在促生着欲望生产,并由此拉动了主体的生产。被网络平台的文化工业所带动的欲望生产,并不是原发性的实体。相反,网络平台所做的是提供欲望生成的现实条件,风格的生产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中介。
在当下网络平台中,更复杂的状况是,风格与知识产权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现实的联系。这种现实进一步暴露了,在文化工业生产中,风格逐渐转变为了一种不变资本。一方面,风格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风格创造者的劳动;另一方面,风格一旦形成,就又成了吸收更多劳动的工具和手段。这个过程中,既定的风格是“死劳动”,它不断吸收“活劳动”,进而促进网络文化体系的再生产。借助于知识产权的方式,虚拟的风格在现实中彻底成了不变资本。
伴随着风格生产的不断扩大,文化生产中的不变资本所占比例亦在提高。按照这个方式,文化资本生产的利润率将下降。网络平台文化的发展,恰恰在解决这个问题。网络平台文化的解构效应,使得象征秩序不断被加强,漂移的符号让重组、进而生成新的风格提供了条件。这构成了网络文化生产降低不变资本比例的有效方式。如果说,在过往的社会中,社会生产是“用商品生产商品”,当下的网络平台则是进一步发展为“用符号生产符号”,经济的问题仿佛变成了符号的结构问题。这是后现代主义思考的方式,他们把社会变革的机遇放在了符号结构的突围中。相比而言,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理论视野,对于我们更有参考价值,因为二者依然基于经济结构的分析,展开对于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这为我们反思网络平台文化背后的经济基础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路。
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逻辑下,作为消费主体的个人被捕获在平台经济中,即作为需求侧的消费环节成为资本所首先关注的对象,这在资本逻辑下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资本追求逐利的方式永远是剩余价值“短平快”的实现。于是,当网络平台作为资本实现渠道逐渐趋于垄断,不断被打造的消费理念借助于对主体欲望的建构,成了西方消费社会扩大内需的扭曲方式。之所以说这是扭曲的,是因为内需的扩大并非源自分配结构的优化与人民收入的提高,而是不断催生消费的欲望。比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的“扩大内需”往往是假借消费者需求升级之名,不断创造融资题材,吸收剩余资本以进一步加固垄断;垄断往往是网络平台数据加工的核心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不是要对网络平台进行“一刀切”?彻底将其禁止或者取缔?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出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这就需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防止资本野蛮生长”。(3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第1版。对于平台资本而言,亦是如此。要“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36)④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第7页。,要改变网络平台“以资为本”的逻辑(37)相关研究可参见徐康宁:《数字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及其全球治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83-92页。。在新发展阶段,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实体经济上,因为人民财富的增长与共享离不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财富生产过程。对此,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发展,都需要紧紧围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④的重要理念,将建设的焦点从消费数据平台的完善延伸至生产数据平台的构建,将平台建设打造为推进产业数字化的有效抓手,使之成为开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渠道和扩大人民收入的有效渠道。发挥平台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防止平台资本野蛮生长,才是网络平台真正的健康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