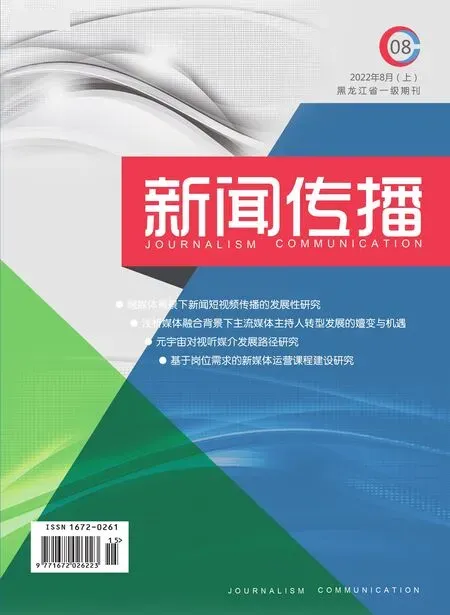以框架理论视角看地区形象符号的形成
——以“阜阳毒奶粉”事件报道为例
任荣荣
(安徽广播电视台 合肥 230071)
一、事件回放
在2003年初阜阳就发现“空壳奶粉”,2003年4月至10月是伪劣奶粉在阜阳销售最猖獗的时期,但并没有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注意。不久,阜阳市各级医院出现了因食用劣质奶粉发病的婴儿,这些婴儿明显的特征就是头大身体小,后来在媒体的报道中被称为“大头娃娃”。阜阳市民高政未满周岁的儿子是“伊鹿”牌空壳奶粉的受害婴儿,在2003年3月上旬,高政向当地新闻媒体求助,阜阳电视台、《阜阳日报》都做了相关报道,在当地引起一时轰动,但“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受害婴儿天价索赔’,劣质奶粉毒害婴儿问题没得到根本的解决”。[1]在2003年12月,央视七套《聚焦三农》的记者首次得到阜阳劣质奶粉毒害婴儿的新闻线索,并赶赴阜阳当地采访,在2003年12月25日,该记者制作的新闻片《流入农村的劣质奶粉调查》在央视七套《聚焦三农》首次播出。阜阳市工商、质监等部门从2003年12月底至2004年1月,对伪劣奶粉展开了一次专项整治活动,公布了33种劣质奶粉的“黑名单”。但在这之后,医院仍然不时出现受害的“大头娃娃”。2004年3月29日,新华社发布电讯,揭露了劣质奶粉导致婴儿死亡的沉痛事件。直到此时,阜阳劣质奶粉案仍没有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2004年4月16日,上海《东方早报》作出重点报道,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引起一定社会反响。从2004年4月18日起,央视二套经济频道《经济半小时》连续用七期节目做了专题报道,引起强烈社会反响。2004年4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立即对此进行调查。当天下午,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组成的专项调查组,从北京奔赴阜阳,拉开查“毒”大幕。这成为事件标志性的转折点,至此,安徽省内媒体,国内各大知名媒体,包括国外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如《国际先驱导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都开始出现“阜阳劣质奶粉毒害婴儿”的报道,这一事件进入了国际视野。从2004年4月20日开始,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反思延续了数年。
二、样本选择及分析方法
笔者用不同的关键词如“阜阳奶粉”“阜阳毒奶粉”“大头娃娃”在百度和Googel进行搜索,以单篇新闻文本被三家或三家以上的不同媒体转载为选择标准,得到可供分析的文本58篇。这些文本涵括了全国性官方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地方性媒体:成都日报、广州日报、都市报类以及舆论监督类报纸。
新闻标题是新闻内容形象化的高度概括,是信息传播者对所传递信息内容的重点突出,[2]也可以说是文本框架主要内容的体现。所以笔者选择新闻报道的标题作为文本分析对象,通过对不同时期新闻报道典型标题的分析,来分析媒体的报道是否框限了新闻事实,哪些内容被媒体摒弃在报道框架外,以及在事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媒体所采取报道框架背后又隐含了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另外,笔者通过对不同时期媒体报道重点的列表整理,来显示在阜阳奶粉事件中,媒体报道的取材范围,分析媒体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进行放大和凸显,什么样的信息被忽略和删节。在此基础上,分析媒体对框限的内容如何架构,也就是分析媒体采用的不同诠释框架,这些不同的诠释框架隐含了什么样的道德观和价值判断,对事件归因起到了什么样的导向作用。
从有利于危机解决的角度出发,媒体担任着从突发事件爆发前的预警和监测,危机处理中的状态评估、信息传递、利益相关者的调节,到危机恢复期的形象塑造中的主导角色。[3]我们不妨将上述突发事件中媒体理想意义上的功能划分作为我们文本分析的一个理想背景。
三、研究结论
(一)框架之外——沉寂的两端
笔者通过分析整理,将媒体在各个阶段的报道重点的典型文本列表如下: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发展,媒体的报道角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地变化,这体现在他们对这一事件不同阶段所框限的报道内容上。
根据商品的流通过程,阜阳奶粉事件所牵涉的主体应包括:伪劣奶粉生产商、奶粉生产地监管部门、销售商及所在地监管部门以及伪劣奶粉消费者及家人。
在突发事件的潜伏期和爆发期,从有利于危机解决的角度出发,媒体最大的职能应当是预警、监测以及信息传递。伪劣奶粉的相关信息应当是媒体报道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从笔者的统计来看,媒体对劣质奶粉毒害婴儿事件的报道内容中,出现了“沉寂的两端”,也就是处于毒奶粉源头的生产地和流通终端的受害婴儿,他们的声音在媒体的报道中是微弱的,在某些文本中甚至是缺失的。在伪劣奶粉流通的整个环节中,毫无疑问,奶粉生产商应承担最大的责任,但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对奶粉生产源头的报道量与这一点很不相称。很多媒体在报道后期直接将这些伪劣奶粉称为“阜阳毒奶粉”,给受众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伪劣奶粉是阜阳生产的。
对伪劣奶粉的受害婴儿,众多报道主要停留在对个别受害婴儿惨状的描述和渲染,对这一群体的总体形象比如群体成分构成没有在媒体上得到呈现。这使受众无法了解毒奶粉的整个流通过程,也难以引起“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流通路径”的反思。由于媒体报道中对受害者“人文关怀”框架的弱势,使得受害者的利益没有成为媒体关注和维护的焦点。
从表一我们可以看到,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媒体主要着力于调查阜阳政府在该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并在报道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报道高潮点。第一个高潮是得出“阜阳政府不作为导致‘大头娃娃’惨案发生的根本原因”的结论,并直接呼吁中央政府对阜阳官员进行问责。典型文本如“追踪采访杀婴奶粉阜阳副市长:我不想引咎辞职”。第二个高潮是该事件的相关官员被处理后,记者发现被撤职的某工商所管理人员仍在上班,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阜阳一些官员“阳奉阴违”的行为再次成为媒体的矛头所向。
(二)框架之内——符号的形成
恩特曼(1993)曾经从媒介框架的不同功能来进行解释和论述不同媒体采取的不同报道框架的原因。恩特曼认为,媒介框架有四大功能,即:界定问题,就是决定社会问题的影响及社会情况,反映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确认问题:确认问题产生的原因;定出道德判断:评估社会问题的影响与结果;给予解决方案或改善方法:提供问题的补救方法,并预测补救方法的可能效果[3]。虽然媒体所选取的报道框架,在某一个文本中不一定同时具有这四种功能,可能只包含一种或几种,但框架可以影响人们对事件的认知,并且对事件归因和道德判断起导向作用,并进一步依此作为采取行动的依据。所以,在笔者的框架分析中,将某一框架所凸显的功能也列入分析的范围。
在事件发展的初期,媒体报道的主题框架主要是受害婴儿信息框架,这一框架的主要功能是界定问题,告诉受众发生了什么。通过这一框架,媒体向受众呈现的是阜阳市场监管部门形同虚设,伪劣奶粉肆虐阜阳市场,造成大批婴儿营养不良甚至死亡的事实。在“受害婴儿信息框架”将伪劣奶粉问题界定清楚以后,该框架很快就从媒体报道中淡出了,于此同时,与“受害婴儿信息”框架同时并存的“阜阳市政府不作为”框架逐渐成为报纸版面上的强势话语内容,并贯穿事件发展的始终。阜阳政府玩忽职守以及滥用职权,直接导致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阜阳政府官员在媒体的报道中以阜阳人民的对立面的形象出现。同时,“官员腐败”关联框架的启用,也使得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对阜阳官员的问责”顺理成章地成为媒体报道中的响亮呼声。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对阜阳渎职官员的惩处,都成为顺乎民意、响应舆论的行为,引来媒体的一片赞扬声。中央政府“整顿吏治”的报道框架,树立了中央政府权威,契合了“党和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这一社会主流话语模式,体现了媒体在当下整治环境下自觉引导舆论,维护主流价值观的角色认同。至此,奶粉事件似乎以中央政府重拳整顿吏治,维护人民利益圆满收尾。但是,在6月初,媒体爆出阜阳被查处人员仍在正常上班,并向媒体解释“查处相关人员是迫不得已,为了给上级一个交代”的言论,引起媒体报道的又一轮高潮。阜阳市政府对中央政府决定的“阳奉阴违”成为媒体讨论和谴责的焦点,在媒体的报道中,形成了中央政府是好的,阜阳政府是坏的,体制是好的,阜阳官员是坏的这样的价值判断。
纵观整个事件的报道过程,对伪劣奶粉何以生产,如何流通,媒体没有深入调查也没有重点关注,食品的安全问题,反而成为了报道中的边缘问题。一起伪劣奶粉毒害婴儿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在这种报道框架的格局下,演变成对阜阳当地政治生态环境的考量和整顿。“阜阳毒奶粉”不再是食品安全问题,而成为“阜阳整治生态环境恶劣”的代名词。政治经济地位并不显著的阜阳,因为毒奶粉案“一举成名”。但是在这一事件过后,阜阳在很长的一段事件内又在公众的视野内销声匿迹,使公众对阜阳的认知,还是停留在“阜阳毒奶粉”的层面上,“阜阳毒奶粉”在很长时间内成为阜阳的认知符号。2004年之后,媒体在报道阜阳发生的一些事情中,“阜阳毒奶粉”多出现在新闻的背景介绍中,这一认知符号背后隐含的是:阜阳市政府的腐败以及混乱的政治经济秩序,造成的民不聊生的局面。
单一的报道框架必然带来单一的问题解决途径[4]。在阜阳奶粉事件的媒体报道中,媒体将这一事件的原因归结为阜阳官员的失职和渎职,对事件展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公共食品安全,比如三农问题视而不见,这样即使是阜阳的腐败官员受到了查处,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在阜阳奶粉事件中,媒体的作用只是再一次把原有的社会权利结构和刻板成见生产了出来,并近一步固化,受众在其中受益很少,甚至会得到更多的思想束缚。在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媒体的社会整合及环境监测的功能没有得到应有体现。■
——阜阳师范大学产学研服务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