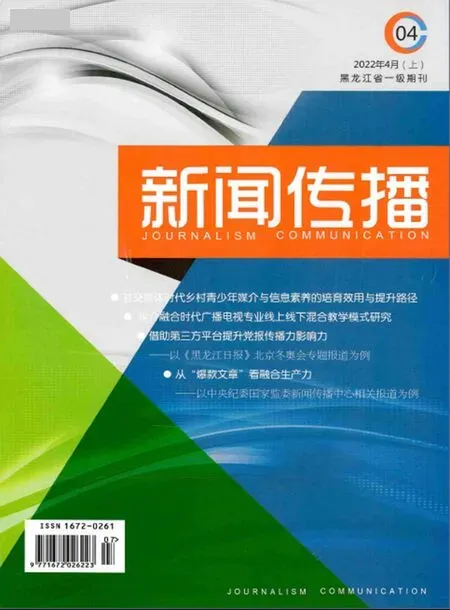网络维权行动中女性的自我呈现与传播策略
王玉英
(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庆 400044)
“女性维权”行为是关乎我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关键问题,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权益保障特别受到重视的今天,特殊群体如农村女性、女性农民工群体等仍然需要得到重点关注。不仅如此,在当前社会,隐形的性别歧视广泛存在,性骚扰、家庭暴力等均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女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地位已经有所提升,女性维权形式是否发生转变?一般采取何种传播策略?这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一、女性自主维权形式的演变
我国“女性维权”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对某类特殊女性群体的研究,二为对某个地域女性群体的研究。传统的维权方式主要包括信访、上访、热线维权、社区机构维权等,《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就是改革开放后女性维权的缩影,秋菊维权的方式是逐级走访,个人口头陈述和信访文字材料相结合,反映情况并提出投诉请求,是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容易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与支配,也是传统维权中最常见的非官方形式。
大众传播时代,“维权报道”作为一种常见的报道类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关研究大都结合具体维权案例,分析女性在其中的媒介形象或总结媒体的报道策略。由此可见,当前阶段以传播者的传播内容、作用、策略等研究较多,对女性维权者的主观能动性关照不足。
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发展促使民众参与到各种社会事务中来,可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与围观者、新闻发布者、政府等官方声音进行交流互动,女性维权形式逐渐从传统的线下维权、大众媒体维权报道向互联网多元维权递进。《穹顶之下》就是互联网多元维权的一个缩影,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通过网络、视频平台等多种渠道发布,采用音视频和信息图表相结合的方式,将自身经历、社会困境与数据支撑、专家观点联系起来。
本研究所探讨的“网络维权”就是这样一种自主维权行为,指的是行为主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主动发布或依托他人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吸引受众关注,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期望达到对自身有益结果的行为。
二、女性网络维权中自我呈现与传播策略
在网络维权事件中,女性对自己的形象呈现有了更多的掌控力,需要“精心包装”来获得他人的支持、扩散,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何通过叙事框架激发网民共情,如何发挥情感表达的传递性、社会性,如何建构和维护形象是考察女性网络维权中自我呈现与传播模式的关键。
(一)悲情叙事逻辑下叙事框架的多元拓展
在弱势群体维权行动中,不管是媒介维权报道还是维权者的自我呈现,大都借助悲情叙事框架,将自身的弱势地位、不公平的遭遇、对侵权方的声讨控诉等展示出来,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网民的共情与认同,将其转化为事件的“围观者”。若网民有类似的遭遇,则自身情绪会受到该事件的强化,从单纯的看客变为与维权者目标一致、紧密团结的行动者;若之前已经发生过类似的热点事件,则会形成网络舆情“联想叠加”[1]现象,能够催生新的舆情热点,延长事件的兴奋周期。网络维权时代,维权者的主动性增强,悲情叙事逻辑下叙事内容、策略均有了更加多元的拓展,在描述事件时可同时使用多种框架,主要包括生命安全框架、财产职业框架、蒙冤受辱框架、声讨问责框架。其中,生命安全框架更强调维权者的人身安全受到他人威胁,如受到家暴、殴打、性侵等;财产职业框架则更强调维权者的金钱、财物、工作、学业等受到损失,如被抢劫、欺诈、无故开除、冒名顶替上学等;蒙冤受辱框架更强调维权者的精神、心理状况,指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被侮辱,如性别歧视、辱骂、猥亵等;声讨问责框架则更注重维权者与政府相关部门、与媒体甚至与事件责任方的互动,主要形式为罗列出侵权方的侵权证据,进行归责与批评。
(二)情感表达中模因的复制扩散
情感是人类独特的心理表征,对网络维权来说,情感的传递性可以很好地动员大众,形成控诉不公、伸张正义的舆论,而不同的情感表达便于维权者有针对性地进行“精细包装”。模因论者认为文化的进化和生物的进化类似,可以通过非遗传方式(模仿和复制)在人的大脑之间相互传染而传播,只要可以进行模仿和复制的都可以被称为模因,如信息、观念、语言、行为等,而情感并不携带信息,它们不是模因,是对模因的潜在反应。[2]也就是说,真正可以被称为“模因”的是网络维权事件中的情感表达方式,并非情感本身。
根据海拉恩(Francis Heylighen)的观点,一个模因必须经历闭合的循环传播过程。首先,个体需要同化模因并成为模因的宿主,模因就保留在了个体的记忆中,个体会通过语言、行为等形式对模因进行表达,并将如此创建的信息或模因载体传输给一个或多个个体;[3]随后,再进行第一阶段形成模因宿主,从而不断复制循环,可以总结概括为同化阶段、记忆阶段、表达阶段、传播阶段。
在网络维权事件中,女性的维权策略一般体现在模因复制的表达阶段和传播阶段。在表达阶段,维权者往往以发生过的类似事件为背景,采取第一人称的视角,依托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将主观性的个人信息转化为容易被他人感知的物理形态,充分利用女性的弱势地位来获得受众的同情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并不断发布相关内容,对维权信息进行强化。内容一般是理性的申诉与感性的声讨相结合,主要包括:事件叙述,讲清自己和责任方的身份,一般按照时间逻辑描述发生的具体事件;证据罗列,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形式;权利申诉,明确表达自己的维权目标,如要求道歉、归还财产、精神损失等。
(三)女性维权者的弱势身份与刚强形象
中国人所说的“脸面”与“拟剧”理论相似,且更能体现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翟学伟认为脸面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和行为”[4]。换句话说,与“拟剧”理论相比,“脸面”具有更深层次的成因,它的存在是为了符合某些圈层的人的心理和行为,带有“众望所归”的隐喻色彩。以往艺术作品、影视作品或媒介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大都以“被侵犯”“被伤害”的弱势身份出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网络维权事件中的女性大都进行自我呈现,实现了“弱势身份”与维护社会正义、替女性群体发声的“刚强形象”的双重建构,既得益于社交媒体、短视频媒体等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媒介环境,又依赖女性维权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自主性和表演性。
三、女性网络维权中的迷失与管控
网络维权的公开性、传播快、成本低等优势,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维权者队伍,加大了维权力度,大大缩短了维权周期和成本,为女性维权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话语权。但利用弱势身份和悲情叙事“颠倒黑白”的维权者,不断渲染、制造话题、吸引眼球的社会化媒介,盲目跟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受众,让网络维权逐渐背离初衷,迷失在各方的利益交汇之中,引发诸多乱象。2020年爆发的“鲍某明事件”“罗冠军事件”等,都是由女性维权者首先发声,在生命安全、蒙冤受辱、声讨问责等叙事框架和一些敏感词汇共同作用下,引发社会关注和对男性的强烈谴责,网民们纷纷为女性维权者打抱不平,向侵权者问责,追求社会公平正义。随着时间的推进,新的网络热点事件吸引了网民的注意力,对该事件的热情消退,背后的细节和真实情形逐渐浮出水面,部分理性的人才发现民意与真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许多事件是被他人蓄意操纵的作品,甚至原本的维权者就是谣言的传播者,网民的舆论发生反转,但对另一方造成的伤害已无法挽回。
网络传播的特质赋予了民众较大的话语权和情绪表达空间,促生了非理性传播,然而,技术是中立的,数据和算法也不带有任何偏向性,甚至可以被用来监测和管理舆论,因此,真正客观的反思应该是重新审视人本身,如何提升维权者的媒介素养,如何重塑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力量,如何使民众的言论表达回归理性,才是引导网络维权事件积极发展和保障维权者合法利益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