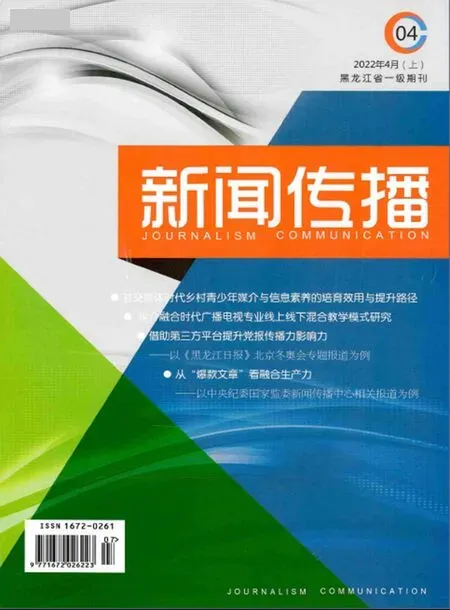舆论为何“失焦”:网络媒体平台的谣言传播治理
韩雪迪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450001)
一、传播技术发展后的舆论浪潮
在技术发展还不够先进的前信息时代,人们或依靠面对面,或通过书信纸张等介质传递信息,但随着网络等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意见表达更为直接和迅速,舆论的形成周期被大幅缩短。
(一)网络发展更新舆论传播进程
现代汉语词典中将舆情一词解释为“群情、民情”,简而言之就是公众意见表达的集合。而舆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公众的言论”,是不同意见、信念、态度等的总和。不同于舆情一般针对特定话题,舆论的形成更为复杂,往往是公众针对一类话题发表的总括性意见,是针对某些现象形成的较稳定看法。公众可能在某些因素刺激下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舆情现象,舆情消散后,针对该刺激因素隐含的更深层次问题而沉淀下来的看法态度等则被保留,附着于舆论场中。不同于舆情的短时性,舆论往往持续较长时间。
(二)被网络强化的舆论传播力
我国网络舆论研究关注开始于2005年,在发展的十余年里,网络舆论发展一直与社交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1]口头传播时代,人们往往通过面对面交流沟通意见;随着文字、印刷品的出现,沟通的空间界限慢慢减弱,人们无需面对面也可了解彼此心中所想;再往后的广播电视等的发展更是打破沟通的时间界限,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有形媒介交流。直到互联网时代,这种时空界限进一步消失。口头、文字、广播、再到互联网时代,公众发布与接受信息的无所限制使得本身充斥各种情绪化的舆论场经由网络的即时、互动、开放性等将自身特点放大,公众情绪的流动更加频繁且激烈,网络舆论场中的各方博弈更为复杂、对主动权的争夺更为急迫,这也使得各类新闻反转事件的发生频率不断提高。
(三)谣言伴随舆论阵地变化转移
对谣言的认识中总包含一定程度的虚假认定,即谣言是假的并且有绵延不绝的极强生命力。但谣言的虚假与否与公众信任程度上却不成正比,即公众似乎并不因某个信息真实性存疑而选择不相信。这也是谣言从古至今均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任何时期谣言都不缺少听众。
有学者提出网络谣言是在互联网这一特定的环境中,运用网络平台进行广泛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2]无论经由何种介质,谣言均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不断变换形态,网络时代的谣言则集中表现为各类电子产品上显示的代码。相对其他传播媒介,网络给了谣言很好的生存环境,网络的匿名性使得信息发送主体放松对信息准确程度的监控,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经由网络发送,形成网络谣言;为了满足公众日益急切的信息需求,网络的即时性使得信息在几秒钟之内到达数以千万计的用户,单个用户又能在几秒钟之内收到数以千万计的信息,信息的堆叠加大了信息审查的难度,谣言便肆无忌惮地滋生扩散。
二、多方合力推动下的舆论怪相
在公民发声成本越来越低的当下,争议性新闻事件频繁发生,而对于争议性新闻事件的讨论也呈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舆论生态。
(一)各类谣言主导受众的真相建构
信息越是不全,人们就越是不知不觉地去斟酌其含义。[3]争议性新闻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之初,事实信息披露不全面、事实本就不充分的情况极易引发人们对于事件真相的猜测,盛行的“阴谋论”背景下,公众不具备辨别信源可信性程度的能力,只愿意相信首先爆出的夹杂大量情绪的刺激性言论,对后期的辟谣内容不闻不问。或者受众囿于信息茧房的禁锢,接触不到相关辟谣信息,或者对相关信息不加思考一带而过。另外还有部分受众只是为了情绪的抒发,尽管其能接触到辟谣信息,并且认同其真实性,但仍在持续发布与辟谣内容完全背道而驰的情绪化表达,对这部分受众来说,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发泄口,此类受众最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喷子”。
事实不足时谣言以补充事实的形式存在;相关事实已经充分公布时,谣言又以既定事实出现的原因存在,使可能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细节开口说话。总之,谣言贯穿新闻事件真相建构的动态过程之中。
(二)专家成为谣言生产者而非辟谣者
埃诺尔曾说:专家是谣言的一个古老来源[4],一定程度上,专家能够基于其研究领域对事件做出相对专业的判断与解读,对于笃信其判断的民众以及以报道其言论为主要内容的记者来说,专家的专业性是理解事件的“救命稻草”,但若专家获得的事件信息是未经证实的二手或N手信息,则专家很可能成为错误信息的担保者,此时专家的专业化就给各执一词的旁观者提供了选择性的专家话语,造成舆论的分化甚至对立。
另外,由于专业壁垒的限制,一些专家分析被媒体公众歪曲解读后成为新的谣言内容。专家或因不熟悉新闻的生产运作方式,在面对媒体及公众关注时的手足无措导致其无法发挥自己的专业性,并可能因无法适应大众话语传播模式而做出不合适的决定,成为新的谣言发酵容器。一些争议性新闻事件中引入专家解读,是对公众理解事件真相的很好手段,但两方知识转换做不到位的情况下专家则更容易成为民众发泄情绪的靶子。
(三)传播各环节媒介素养的普遍缺失
之前我们区分大众传播系统与新闻传播系统,但现在二者已很难分开,网络的即时性使信息的传播能力大大增强,大众媒体及其记者不再是大众信赖的唯一权威信息源。
1.传统权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不足
在“媒体见证”向“公民见证”转移的情况下,传统模式的公信力与合法性都遇到强有力的挑战。[5]人人都能发声带来的是不确定性,权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减弱,他们设置关注热点的能力逐渐被公民记者消解。遗憾的是权威媒体的事实检验速度比不上舆论的发酵速度,辟谣速度赶不上谣言的传播速度,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此次新型冠状肺炎中体现出的舆情混乱。这其实要求权威部门面对质疑时尽可能快地发声。但纵观众多争议性新闻事件,媒体对受众的整体舆论把握与导向以及主流媒体对舆论痛点的敏感程度有待提高。
2.部分新闻媒体无节制炒作模糊焦点
当下新闻是大量“对表征进行表征”的产物,是对新闻中已经报道事件的报道,很多新闻媒体在二次或多次转述时并不进行新闻核查,并且在未经核实的信息基础上添油加醋。计算机、互联网以及其他新的通信技术正在改变信息形态,对于新闻工作者和公众而言,过去常常用来识别值得信任的消息来源和有效信息的标准正在消解。谣言在互联网上能获得如同新闻一样的关注,甚至很有经验的记者也会被迷惑。[6]对于不确定性的内容,做出与标签所含刻板印象相同感情倾向的模棱两可的解读总是最有效的。
此外,虽然媒体将公众注意力吸引至一处,但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得到极大提升的当下,舆论过度聚焦事件一方而忽视其他方面时,舆论就会出现失焦。[7]此处的舆论失焦不同于受众在信息洪流的冲击下抓不住重点的迷茫,而是媒体集中报道事件某些侧面,却忽视主要矛盾造成的本末倒置。媒体专注于道德谴责的渲染,却更应重视对真相的寻找、问题的解决,这需要引起所有人对媒体舆论引导失范行为的注意。
3.受众发声的情绪化与匿名性愈发突出
社交网络上人之所以会拥抱愤怒,被情绪所左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交网络上的表达本质上不是一种沟通和对话,而是一种类公众演讲。表达愤怒、道德批判、公开羞辱驳斥异见者、只讲情绪不讲真相,这些“道德作秀”策略在公共演讲中很有用,不断出现在网络舆论当中。此外,现有的网络媒体的匿名性使其比传统媒体更具私密性,人们往往处在自己天地中的狭小一隅在网络上浏览消息发表评论,他们需要一种感情交流以填补个人的空虚,需要一定的表达平台,而一些道德上的评论极易引发感情上的反应,找到相同意见者,所以,发表或接收大量情绪化的言论都有利于网民快速找到同盟。舆论之所以能被称为爆发,是因为之后对其的讨论量都在走下坡路,受众对事件失去了讨论的欲望,他们已经发泄想要表达的情绪,事件后续发展,甚至事件真相已经提不起他们的兴趣。
三、各方行动构建良性舆论生态
在争议性新闻事件频繁发生的当下,各方急于进行情绪表达的现状无助于事件的理解与真相的探寻,对舆论场的净化已势在必行。
(一)强制性法律措施保证底线
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仅有短短二十年时间,并不像早期的传播媒介一般易于控制,可以说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将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介都处在探索阶段,需要各方根据互联网的新特点不断摸索出合适的传播形式,而法律则是对互联网传播进行任何创造性开发的基础。对于一个新兴事物,法律的制定实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近年来各项针对互联网管理办法的通知也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已经在针对互联网管理进行一系列行动,例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多项法律条规均为针对互联网管理的专门条目,并且均包含针对谣言的处理,另外《宪法》《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综合法中也有关于互联网的法律内容。
综合近年来的互联网违法处罚案例来看,对于互联网的管理呈日益收紧状态,网络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但能够发现严厉程度仍稍有欠缺。与此同时互联网执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便捷,网络监管需要完善的技术支持和充足的人才储备,在监管体系未得到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很多互联网上的灰色地带得不到管制。另有部分声音反馈互联网管理方向“使错了劲儿”,不良信息大行其道,一些有效信息却因某些规定不予显示,不利于公众的理性交流。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在法律制定方面多做权衡,尽量细化法律法规,确保法律能够作为互联网舆论场的底层保障发挥最优效果。
(二)各平台完善信息审核机制
现今出现很多新兴互联网公司参与瓜分互联网用户市场,一个互联网公司个体产品的用户数据已达海量,可以说公众想要接触信息必须借助平台。虽然有国家法律约束措施兜底,但各平台在信息审核方面仍占主要地位,很多时候监管部门只履行抽检职责,实时监测任务仍需各平台方运作。针对海量的信息处理,各平台都开发了自己的算法工具,借助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各平台间也会进行交流沟通经验。但算法等程序设计即使再灵敏也是机器控制,人工智能再智能也无法完全与人脑等同,所以人工筛查目前来看仍是不能被替代的一环。针对信息管理方面问题,各平台间还可以沟通确立良好的信息公开系统,相互交换信息管治经验,变对手为盟友达到多赢。
此外,各平台还可以加速推进网络实名制进程,把好用户关也是确保信息质量的重要一环。目前来看国家相关立法已在推进过程中,各平台可以积极合作,推进其用户的实名认证进程,必要时可以合作推出全平台实名认证,既便利了用户也减轻了各平台的数据压力。
(三)各传播环节强化媒介素养
不同于之前点对面的单一传播模式,参与网络传播的个体均成为一个个的节点,网络传播是一种点对点的传播,任何人都能成为信息发出者,成为传播中心。从网络舆论场中谣言泛滥可窥见传播链条的不同节点的信息发布者媒介素养的缺失,有研究者针对网民的网络谣言识别能力和谣言辟除能力进行测试后指出网民对网络谣言的重视度以及危害度认识远远不够。[8]
公众对于网络谣言的轻视态度使得网络中谣言与事实齐飞,大量真假难辨的信息在舆论场上大肆传播,部分媒体从业者也未能坚守职业准则做好“把关人”,很多事实信息未经核实就急于发出,反而成为虚假信息传播者中的一员甚至是领导者。而传统媒体则扮演尴尬角色,传统媒体要求的真实性、权威性、代表性、严肃性、主导性,与网络的瞬时性、当下性、流动性、互动性等特性不相适应,[9]于是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进军的过程中,传统媒体从业者或无法适应新媒体速度,或无法保证其发布信息准确度,其话语主导性被大大削弱,这些问题都要求网络时代下的媒体从业人员积极主动变换思维模式,寻求将网络与信息融合,平衡准确性与时效性等信息传播要求的新范式。
结语
面对部分公众宣扬的“技术有罪论”,我们应该清楚技术发展不是原罪,社会进步必定依靠技术的不断提升,我们不能在技术浪潮下迷失自我并将一切错误归咎于技术不断发展下海量信息的裹挟,我们应该看到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放在传播场域中则是对信息搜索、归纳、整理等的工具实用性。我们需要找到技术与个人、技术与传播间的平衡,进而为涤清舆论环境做出改变,努力建立属于公众的公共领域。在矫正对待新媒介技术的态度之后,面对技术发展下日益突出的诸如谣言等问题才不会因噎废食,须知共同行动,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网络生态模式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