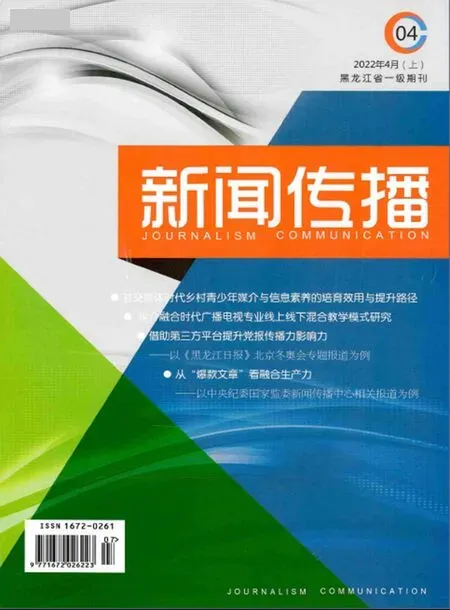“在农广播”:应急广播的媒介化乡村治理
刘王平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210023)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原本“消音”的农村广播重回大众视线,只不过其身份由扮演组织与教育的高音喇叭变为服务与宣传的应急广播。我国广播从1940年发轫,80多年来,农村有线广播将党和国家声音传遍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乡村治理中最重要的媒介。
媒介依靠其特有的技术特征,沟通各个主体达成集体协商,实现治理效果,这种媒介实践被理解为媒介治理。肖恩认为媒介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与完善、政府的监管与共治、跨国家机构和组织的跨文化治理。[1]但不同于西方世界,中国的媒介无疑是一种“治理技术”。“媒介在权力结构中运作,从而构成了权力的组成部分”。[2]媒介发展会受到政治逻辑的支配,媒介发展的过程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媒体不断被纳入治理体制的过程[3]。因此乡村媒介治理便是国家依靠政治逻辑策略性选用媒体、并使之成为服务于乡村治理改革的过程。媒介治理超脱于前述肖恩的三个层次,而是伴随权力运作散布在乡村生活的各个层面。
当前在乡村振兴的全面推动与基层治理改革之际,应急广播建设和疫情高音喇叭的“硬核式喊话”使得乡村广播呈现回归的趋势。复归广播的角色与功能出现很多新的转变,并给乡村治理带来很多创新亮点。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有线广播建国后的政治功用,以及考察其衰落动因。少数研究分析农村有线广播回归对乡村治理的作用及复归动因。因此,本文试图吸纳“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从媒介化治理视角出发,考察农村应急广播的回归,探讨当前农村应急广播发挥的治理效用,对优化乡村治理乃至推动乡村振兴具有建设性价值。
一、农村有线广播的复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行乡村治理改革,新的乡村治理框架更强调社会自治、公共服务、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4]因此,为实施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乡村振兴,建设平等开放、多元共治的乡村媒介工程被提上了日程。当前,我国除了继续推进“村村通”基础工程、电影放映工程、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造以外,应急广播建设同样是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
2013年《推进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出台,应急广播建设的目标任务、工作分工和进度安排被明确。农村有线广播“改头换新面”,经再组织、再整合成为应急广播,陆续在田间地头重新奏响。同年12月3日,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揭牌,应急广播中心网站上线,标志着我国应急广播体系进入全面建设阶段。[5]2014年陆续在四川、广西进行试点实验工作。随后广东、浙江、江苏等着手建设应急广播。到了2020年底,全国已有23个省及自治区开展了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程。农村有线广播不仅全面复归,而且其功能与角色发生了重要转变。
二、“在农广播”与乡村服务治理
2013年后新一轮乡村治理改革向“服务治理”转变,提出了两大要求,一是更好地供给多元公共服务,二是更好地协调乡村主体参与共治。应急广播的技术特征为满足“公共服务”与“公共商议”、实现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提供了可供性。
首先,应急广播可作为乡村公共服务媒介,发挥灾害预警与抗灾指导作用。在四川雅安、云南鲁甸地区地震灾害发生时,应急广播发挥发布灾情信息、稳定灾区舆情、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等重要作用。其次,应急广播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2017年湖南建设的“村村响”应急广播成为农村地区宣传政策、传播知识、服务日常的重要平台。此外,满足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主流舆论宣传,为建设平安乡村、推进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最后,应急广播实现了“公共话语的可沟通”。地方政府及时公开民生信息,有利于乡村公共话语的形成与表达,达成公共协商。不少村庄通过应急广播硬核喊话,让村民知晓“抗疫”政策,及时汇聚民意,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又或在脱贫攻坚中,基层干部借助广播同乡村组织、村民的共同协商,实现产业发展。
具体在媒介化治理实践中,应急广播又体现了“双重在场”的特征:
其一是应急广播成为乡村治理的在场参与主体。应急广播提供了24小时预警、精准信息的传达,以及乡土味的信息娱乐服务,成为了协同乡村组织、个体之间的中介。具体来说,应急广播“用本地方言播出区、镇新闻、解读政策”,在乡村服务中广播媒介成了联系干群关系的“连心桥”。此外,乡村自制的文化节目,不仅唤起了老人的“集体回忆”,而且成为村民自觉的文化实践。有线广播通过富于地域性的文化节目,可以形成较强的文化场域力量,聚合乡村社会共同体[6]。
其二是应急广播突出了乡村主体地位。农村中电视和手机等媒介的盛行,将农民束缚在封闭的自我空间中,使得个体对村庄事务等缺乏必要的敏感。应急广播作为“挂在天空的耳朵”的公共媒介,在突发事件中制造附近的声音景观,将村民集中在同时空的公共事务的知晓与表达上。由应急广播搭建的公共场域较微信、微博更具地域的开放与包容,可以容纳村庄的各层次群体,能够让乡村社会主体同心协力,实现多元共治。总的来看,应急广播的建设是基层治理模式转变与乡村自组织能力提升的彰显。
三、应急广播媒介化治理的未来之路
当前,农村有线广播的确在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交织中得到复兴,但广播作为声音媒介,单纯依靠其自身的技术革新,无法实现听众的互动与表达的需求,无法独立助力乡村振兴。“应急广播”的多措并举,最终仍有可能滑入精神宣传与信息传达无效的窠臼,例如疫情期间农村有线广播的压力型动员存在“硬核式无力”的问题[7]。而且已有不少研究发现当前乡村文化凋敝,原因在于其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民主体性依然难以发挥。此外,农村有线广播因为声音瞬时、范围固定的限制,需要特定的场域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乡村治理与文化振兴的效用。
因此,为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乡村媒介治理需要开拓创新,更好地促进媒介融合,赋予农民表达权,唤起农民主体性,激发农民参与公众生活的积极性。具体而言,应该努力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促进媒介融合,善用乡村媒介生态。为更大可能地释放农村有线广播的媒介治理优势,需要将农村有线广播与乡村在地媒介以及社会化媒介加以深度融合。例如将农村有线广播与乡村在地媒介包括电视、布告、宣传单、口头传播等,以及社会化媒介QQ、微信和直播等资源整合,更好地推动农村媒介治理格局建设,实现媒介善治。
其二,赋予农民表达权,释放农民主体性。除了思考治理媒介的行动之外,也应该从乡村治理的内部、从国家与社会对话的视角出发,思考农村治理中“参与式传播”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开拓创新乡村传播媒介形式与内容,在发挥主流舆论引导的同时激发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传播形式与内容不仅要让村民听得懂,还要让村民喜闻乐见,更是要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参与乡村共同体事务的能力与信心,推动乡村“三治格局”的建立。
总之,在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逻辑中,农村有线广播被赋予了应急服务、日常服务以及主流舆论引导的多重功能。但未来如何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农村有线广播仍亟须探索一条适宜的媒介深度融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