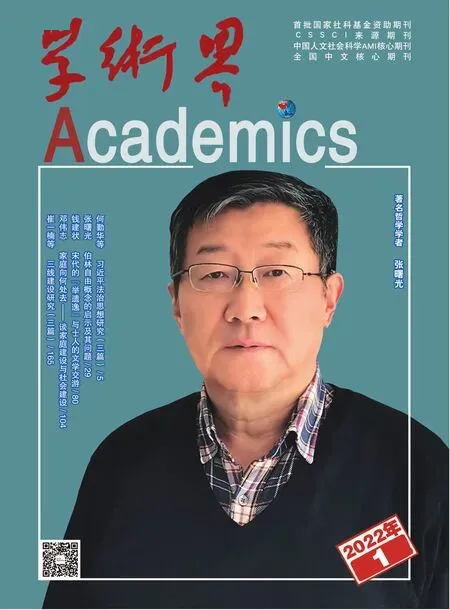自然与环境〔*〕
〔美〕布里安·特里诺 (何卫平 译)
(1.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 哲学系, 美国 洛杉矶 90045;2.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引 言
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对环境解释学(environmental hermeneutics)领域有一个清晰的看法。首先,“解释学”(hermeneutics)和“环境”(environment)是有争议的术语,它们本身就是研究这些主题的思想家们分析的主题(在许多例子中,可参见Nash 1976和Vogel 1996);其次,环境解释学,至少作为一个独特和自觉的研究领域,是一个相对近期的现象。这意味着“解释学”和“环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融合成一个受到特别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之前,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历史,这也意味着学者们仍在积极致力于发展和描述这一领域,它进展很快,以致任何精确的定义都有可能在印刷品的油墨还未干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然而,如果我们今天要掌握环境解释学的本质,我们就必须从涵盖它产生的某种历史开始。
尽管环境解释学是一个动态和不断发展的学术活动领域,我们仍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准确地描述它的历史发展、告知它的某些共同的知识传统,以及一些重叠的关注范围,它们一起让我们来界定这个领域。自觉的解释方法(hermeneutic approaches),如那些在哲学、神学或宗教研究以及文学中可以发现的解释方法,占据了这个领域的中心。然而,包括回忆录、诗歌、设计理论和历史在内的其他体裁,都是该领域逐渐过渡的场所,就像它曾经回到其他学科的森林中一样。
很难确定解释学的起源,因为哲学解释学是相对近期的现象,但它的血统可以追踪至书写传统和文化的黎明的解释活动,这使它有一个漫长的思想传统。的确可以说,解释学和语言一样古老,它一直对解释(interpretation)开放,甚至需要解释(interpretation),随着字母系统的发展和文字在文本中的保存,我们也许可以为解释学找到一个更加准确的起源,这项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的特性,正如柏拉图所指出的那样,当文字固定在文本中,而不是活生生的对话中时,它们就摆脱了作者的控制,可以对各种各样的解释敞开,包括可能与作者意图背道而驰的解释。因此,柏拉图对书写文本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书写确实不如对话中“活生生的言说”(living speech),因为前者对理解者和不理解者的解释敞开(Plato 1961)。然而,相比之下,也有一些传统高度重视书写文本和它所要求的开放的(openended)解释过程,也许这样一种解释学文化最著名的例子可以从起源于Tanakh(希伯来圣经)的塔木德学术的丰富传统中找到。
塔木德学术的解释传统在深层次上影响了解释学的轨迹,而解释的早期传统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对神学的关注。然而,哲学的解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1〕是一个比较近期的现象,它——始于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998)和威廉·狄尔泰(1996),并发展到马丁·海德格尔(1962)、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1984,1985,1988)那里——遵循解释的逐步扩张:从神圣文本到广泛的书面文本,最终,“文本”被隐喻地设想为包括身份、社会群体、世界以及类似的现象。哲学的解释学的范围不断扩大,又导致了另一种模糊不清,有些人认为解释学是一门主要或专门关注实际书写文本的事业,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更普遍地适用于语言,还有些人将文本设想得更为宽泛,包括生命的“故事”或自然之“书”,等等,在这一趋势的极限,我们发现一些人认为解释学不仅是一个解释的事情(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有意或无意,它还具有意识和具身性(embodiment)这类特征(Keamey 2001)。
环境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在定义“自然”(nature)或“荒野”(wilderness)的尝试中最为明显(Nash 1976,Cronon 1996,Vogel 1996,Cameron 2013)。当然,虽然有无数的方法试图理解人类对不止于人属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2〕的关系——从神秘教派到犹太教—基督教神学,再到笛卡尔的二元论、泛神论——当代绝大多数环境思想都始于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人类是众多动物中的一种,其发展方式与其他动物相似,也受到同样的进化制约。然而,如果人类和其他生物(植物、动物、真菌等)有相同的起源,并遵循相同的进化过程,那么很难说人类和他们的筹划在哪里以及如何变得不自然。如果海狸是一种自然生物,当它在建造它的水坝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环境,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人类改变环境所形成的现代城市称为“非自然的”(unnatural)呢?
“荒野”(Wilderness)同样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尤其是在北美的环境保护主义那里(Callicot和Nelson 1998;Rolston 1991;Guha 1989),罗德里克·纳希(Roderick Nash)表达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他认为,“荒野”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现实,一种存在于世界上的事物,还不如说是在不同时间和地方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state of mind)(Nash 1976)。在北美,与荒野的关系对人的影响尤其大,人们(即欧洲的定居者)已经不再将这个不止于人属世界看作是一个险恶的、陌生的、不祥的无序状态,必须被征服、被驯养,被带到犁下,用来重建地球上的伊甸园,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神圣的、未受破坏的、可治愈的,值得严格保护的环境。我们已经从把荒野看作魔鬼的住所变成把它看作由人类虐待恶化之前的纯粹神圣的杰作。
所以“解释学”与“环境”或“自然”都是复杂的概念,而且作为一个动态和发展的领域,环境解释学则通过它的持续演变加剧了其复杂性和模糊性。当代环境解释学是一个大帐篷,在它的下面,许多哲学家回归到对“自然”和“环境”的宽广且具包容性的观点。总的来说,环境哲学的路径与环境主义的路径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轴上,环境哲学由(a)对“周围”(environs)的普遍关注演变而来,在20世纪之前的研究中,它甚至不可能被认为是“环境的”(environmental);(b)在20世纪中后期对非—人类的自然更有具体的兴趣,(c)对各种环境(野生的和人化的、自然的和文化的、全球的、地方的以及身体的生态系统)的非常广泛的关注。这意味着当代环境解释学占据了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各种不同的旨趣交织在一起。
由于这种多样性,我认为了解丰富和多样化的环境解释学的景观最准确的方式是从广义上看待这样两个构件:包括文本(涵盖书籍、身份、社会团体、风景等等)解释的“解释学”;和包括从旷野到建筑环境、到我们肉体熟悉的地方环境在内的一切“环境”。事实上,这种对解释学与环境的广泛叙述与最近的学术方法是一致的(Clingerman et al.2013),而且我敢打赌,这里大多数学者都自视为环境解释学家。因此,环境解释学包含这样一种筹划:从对梭罗的《瓦尔登湖》的解释到对风景重写本的阅读,从对建筑与设计的美学描述到对与自然界有关的个人身份的描述。
二、探讨领域
环境解释学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个领域开始探讨的任何一点都是武断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只希望粗略地概括一下该领域历史发展中的一些路标,并对一些主要趋势和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总的综述。任何这样的综述必然是不完整的,但考虑到单个章节的限制,一个有代表性的综述要比试图建构某种严格的起源层级或详尽地编目分类更恰当。
(一)文学
虽然它并非通常当代意义上自觉的解释学,但我们或许可以在环境文学中找到一个培育环境解释学的主要支流。在环境哲学发展之前、期间和之后,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和其他思想家都在创作作品,探索自然的各种含义、自然界中其他存在者的道德或伦理意义、人类在不止于人属世界中的地位和关系,以及类似的主题。这些文学贡献在环境解释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可能包括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971)、约翰·缪尔(John Muir)(1997)、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75)、阿尔多·列奥波尔德(Aldo Leopold)(1985)、华莱士·希坦格讷(Wallance Stegner)(2002)、加里·希里德(Gary Snyder)(1990)、雷谢尔·卡森(Rachel Carson)(2007)和爱德华·阿贝(Edward Abbey)(1990)。这些思想家以及其他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通常不会提供一个深思熟虑或自觉的解释学叙述,但他们仍然对不止于人属世界提供了一些观点,认为它具有丰富的意义,这需要培养我们的敏感,一种开放或“倾听的意愿”(willingness to listen)以及对保罗·利科所谓的“意义剩余”(surplus of meaning)的欣赏。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将其还原为仅仅是语言的游戏——因此,许多作家以及环境解释学家对生态学怀有深深的敬意,或者至少对观察和科学有一种普遍的认同。
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Thoreau 1971)也许是这类作品中最典型的例子,它是描写人类与不止于人属世界之间关系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在整部作品中,梭罗自由地使用了与解读文本、风景和人性有关的解释学的类比。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鼓励他的读者以一种新的方式看世界,即改变他们的解释视角(hermeneutic perspective)。但梭罗对自然界的爱,他对自然所能教给我们的东西的开放态度以及他那诗人的敏感,远非独一无二。许多作者——从诗人到科学家,都肯定自然界无穷无尽的丰饶,以及悉心“倾听”其教诲的必要。因此,小说家和散文家华莱士·希坦格讷(Wallance Stegner)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他曾将美国西部称为“希望之地”(geography of hope),那里的景观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直到今天”,它既影响我们的文学,也被我们的文学所影响。生物学家雷谢尔·卡森(Rachel Carson)也在她的第一本书《海风下》(Under the Sea Wind)(Carson 2007)中使用了解释学的技艺(hermeneutic techniques),在这本书里,她从一条梭鱼、一条鲭鱼和一条鳗鱼的视角讲述了三个故事。在创作这本书时,她“决定,作者,作为一个人或人类,不应进入这个故事,它应该以简单的方式讲述海洋中某些动物的生活。我想尽可能地让我的读者感觉到,他们曾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过着海洋生物的生活”(Carson 1998)。
(二)宗教
如上所述,解释学与许多宗教传统相关的解经方法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另一个重要支流——其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从事什么样的解释学——可以在各种宗教传统的环境世界观(environmental worldview)里找到。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传统给它们的信徒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世界观,这包括一个创造的叙述,关于不止于人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教义,而且,常常是世界的目的(telos)或目标和在其中存在的一个叙述。
例如《创世纪》中,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创造性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如何形成、它有何价值以及它的各种居民之间的关系的故事。上帝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被创造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very good);它充满了植物和动物,上帝叮嘱它们繁殖,遍布大地和海洋。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生物有所不同,其任务是“征服”(subdue)或“看护”(watch over)地球,这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理解希伯来语的“radah”(统治)和“kavash”(奴役)。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叙述召唤广泛的解释,而每一个解释对读者理解人和不止于人属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方式都有意义,我们发现神学家们既主张“创造关怀”(creation care)的伦理,即人类看护或守护地球(Delio et al.2008),也主张“支配”(dominion)神学,即非—人类的自然存在仅仅作为人类福祉的资源而存在(Hendricks 2005)。今天,人们发现各种各样的当代运动针对“绿色”神学,所有这些运动都利用解释学的资源和技艺来重新阅读、重新解释或重新理解《圣经》和传统,它颠覆了传统的各种支配的本体论(ontologies of domination),支持一种不那么专横傲慢、甚至是非人类中心论的观点。
这些宗教解释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信徒读者。因为大量环境问题都与某个“共同的”问题相关(Hardin 1968),神学解释学在一个宗教信徒占绝大多数的世界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宗教的环境解释学的重要性不仅在学术传统中得到证实,也存在于批评家的作品中,他们认为,传统上与环境有关,宗教对人类和不止于人属世界之间关系的解释不够开明,甚至是完全贪婪的。这些批评中最著名的是林恩·怀特(Lynn White)常被引用和批评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White 1967),它认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解释学观点崇拜人类中心主义,将世界看作不过是一口可以满足人类需求的资源之井。
(三)哲学解释学
环境文学和环境神学的传统在遇到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解释学〔3〕后得到了显著的修正,这种转变在20世纪后半叶急剧加速,受到埃德蒙·胡塞尔(1970)、马丁·海德格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2003)、保罗·利科(1984,1985,1988)以及其他人的影响。
虽然解释的工作一直是一个哲学问题,例如,在亚里士多德(1938、1997)、奥古斯丁(2008)、维柯(2000)以及其他人那里——但严格地讲,哲学解释学始于思想家们开始“试图从每次涉及不同文本的解释活动中提取出一个普遍的问题”(Ricoeur,1991),也就是说,始于哲学家们开始思考的不是解释,例如,神秘的文本,而是解释本身的性质。从特殊解释到一般解释这一转变引发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它将解释学的领域打开了,超越了语文学或圣经注释,包括文化和历史的分析。
然而,正是海德格尔的工作标志着当代哲学解释学真正决定性的转向(Heidegger 1962)。海德格尔对应用于文本解释,甚至对我们可以将解释概念扩大到类“文本”,如文化、历史或自然之“书”这样的事情不感兴趣。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解释学是人(此在)的本体论条件。因此,解释学不再是我们做的某事(something),如游泳,有时我在游泳,其他时间我不在游泳。相比之下,在海德格尔之后,我们必须把解释学当作一种本体论的条件或人类自身的特征来讨论。它不是我做的某事(It is not something I do),而是我所是的某事(but something that I am);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中的构成方式。伽达默尔(2003)继承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洞见,认为我们生来就是语言的存在者,语言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我们是由我们的传统和文化的地平线或世界形成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们当作单纯的客体。超越我们偏见的唯一途径是理解我们的传统如何对待他人,这最终可以导致一种“视域融合”,通过这种融合,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传统和他人。
环境解释学的早期探索倾向于间接地处理环境问题,倾向于追随一个或多个解释学经典巨匠的工作,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努力有些只是在回顾时被欣赏,或者更明确地说,他们的思想被环境哲学家所承认、恢复和发展。这意味着很难准确地将环境解释学的起源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尽管有一些重要的早期文献,但人们总能在更早的著作中找到类似原始环境解释学或原始解释学的环境保护主义的东西。然而,随着现代环境主义生根和成长,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思想家一样,或多或少直接地去处理环境问题,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解释学也如此。
随着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这样的哲学家出现,哲学解释学的领域扩大到这样的程度:它不再可能识别或辨别其边缘,不再清楚现象学会在哪里停止,解释学在哪里开始,或者哲学解释学会在哪里停止,文学批评、解构主义,或某个其他领域在哪里开始。哲学解释学与环境主义相遇就显示出这种模糊性,而它的发展也遵循着类似的路径。
(四)环境解释学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不可能对环境解释学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一个完整的叙述,它始于20世纪后期欧洲和北美各种学术著作中的一些较小的排放(emissions)〔4〕和21世纪初火山式的大爆发之前。我们离任何假定的“原始的”环境解释学越远,由于所考虑问题的范围和多样性就越难明确地界定该领域;而当我们对当代作品进行考察时,在如此简单的一章里,除了提供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的粗略清单外,很难做更多的事情。因此,很不幸,如果有必要的话,简要的概述是不完整的,无法引用所有相关的著作,而这些著作表达了对环境解释学的关注。本章以适中的解释学方式,只提供该领域发展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来讲述。
亨利·布格比(Henry Bugbee)在1958年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回忆录兼反思的日记《内心的早晨》(The Inward Morning)(Bugbee 1958),这是最早将大陆哲学与广泛的环境伦理学相结合的尝试之一。《内心的早晨》以伽布瑞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形而上学日记》(Metaphysical Journal)的风格写作,但同梭罗《瓦尔登湖》的风格交织在一起,它是一部单一的著作,一部完全不同于主流学术的哲学;然而,它确实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个人的、诗意的和哲学的反思,这种反思,与其他事情相比,类似某种荒野和地方(place)的解释学现象学。但是,尽管《内心的早晨》是一部重要的文本,然而,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相对来说,布格比的工作一直鲜为人知,甚至在环境哲学家的圈子里也如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一下艾拉辛姆·克哈克(Erazim Kohák)的《余烬与星星》(The Embers and the Stars)(Kohák 1984)可能是一部更好的“突破性”著作的候选者。克哈克的作品是现象学的——受到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利科的影响;同时也是关于环境的,探讨地方的意义和自然的道德感。在该书中,他主张对自然、上帝和伦理/道德(ethics/morality)的个人主义理解,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存在之善(goodness of being)。然而,整本书是对地方、自然和荒野的无穷无尽的神秘和意义的细致思考。
但是,如果说布格比和克哈克一开始是荒野中的孤独之声,那么不久之后,其他人也表达了对不止于人属世界的类似解释学的关注。修恩赫(Schonherr)(1987和1989)、克劳伦(Cronon)(1992)、特莱培尔(Trepl)(1992)、杜朴莱(Dupré)(1993)等人对环境解释学的早期研究作出了贡献。很快,其他人开始以一种更专注、更坚定的方式将解释学与环境问题加以联姻。早期大部分活动来自基于地方和基于空间分析的学者,其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爱德华·凯西(Edward Casey)和罗伯特·穆格劳尔(Robert Mugerauer)。追随克哈克基于地方的研究,凯西和穆格劳尔在地方方面研究的优势确保了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是环境解释学中一个活跃的学术领域,甚至作为新领域得到探索和发展。
凯西开创性的《回到原位》(Getting Back into Place)于1993年问世,它现在仍是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地方(place)的原始性质,并将其发展为存在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Casey 1993),并给出令人吃惊的大量插图和例子,涉及安置、迁移、具身性(embodiment)、建筑场所、荒野、无家可归、返乡或回到原位。此后不久,穆格劳尔发表了《代表地方的解释》(Interpretations on Behalf of Place)(Mugerauer 1994)和《解释环境》(Interpreting Environments)(Mugerauer 1995),巩固了基于地方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称之为环境解释学的重要性。穆格劳尔的工作与设计和建筑——还有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有很深的联系,并导致了“建筑环境的”现象学和解释学,或建筑环境的解释学这类独特和健康的分支领域的建立。穆格劳尔开发了许多理论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与规划、建筑和设计的不同概念的基础有关,探索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交替融合与排斥的特征,以及在文化史上展开的划时代的披露和隐瞒”。
环境解释学早期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可以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中找到。生态女性主义在环境解释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指出了对环境的霸道和剥削的观点与对女性的剥削和支配之间的联系,认为两者都是相同世界观和立场的延续。生态女性主义有不同的关注焦点,这是一个广泛的话题,就其本身而言,值得详尽地论述;这一传统的几个主要思想家包括瓦尔·普拉姆德(Val Plumwood)(1994)、瓦达拉·希娃(Vandana Shiva)和玛里亚·米丝(Maria Mies)(1993)、罗舍马里·拉德弗特·吕特(Rosemary Radford Ruether)(1994)和凯瑟琳·凯勒(Katherine Keller)(2003)。
(五)当代景观
环境解释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世纪之交,仍是一个相对较小并未受到广泛关注的领域。然而,在新千禧年开始后不久,类似一场大爆炸发生了,而且相对来讲很突然,许多人研究起各种不同的可被合理地称为环境解释学的问题。
虽然很难指出哪一部作品是整个领域转折的关键,但布朗(Brown)和托阿德维内(Toadvine)的《生态现象学》(Eco-Phenomenology)(2003)在环境解释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占有重要地位,它包括了像艾拉辛姆·克哈克(Erazim Kohák)、爱德·凯西(Ed Casey)、大卫·伍德(David Wood)等先锋哲学家的工作,它为通过大陆哲学的视角来处理环境问题定了基调。《生态现象学》有助于证明,对经验细致的哲学关注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传统的、将自然作为资源的观点。此后不久,布鲁斯·富尔兹(Bruce Foltz)和罗伯特·弗罗德曼(Robert Frodeman)发表了《重新思考自然》(Rethinking Nature)(2004),其中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论文,这些论文属于广义的环境解释学。
在布朗(Brown)和托阿德维内(Toadvine)宣布生态现象学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十年后,而且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他们有影响的著作〔5〕发表后的工作,一部更特别的解释学文集——《解释自然》(Interpreting Nature)(Clingerman 2013)出版了,它直接论证了解释学在环境哲学中的重要性。这本书认为,环境解释学现在足够活跃、足够庞大,可以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独特领域或子领域,而不是20世纪相对较少(有远见的)学者特殊的专题研究。这部文集汇集了资深学者〔穆格劳尔(Mugerauer)、范·布伦(Van Buren)、伍德(Wood)〕和新学者〔德伦腾(Drenthen)、卡梅隆(Cameron)、格斯万特纳(Gerschwandtner)〕的观点,继《生态现象学》之后,它宣布并将环境解释学确立为一个独特的、自觉的和适时的环境哲学领域。这部文集的贡献只反映了环境解释学多样性的一部分,但仍涉及到神学解释学、伦理解释学、应用于身份叙述、应用于理解不止于人属世界、景观恢复的解释学、建造场所的解释、荒野的保护、环境正义等的叙述。
这部文集的文章——和其他类似来源——包含各种各样的方法、问题、主题和焦点。任何综合性的尝试都必然会被发现是有欠缺的,所提供的任何有代表性的学者或文本都会在更长的处理中也可以被命名的其他人的语境下被提及。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解释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用较小的、单独的努力来恢复或扩展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列维纳斯等权威哲学家的思想——是弥合从早期对环境解释学的关注到我们今天发现的这个更活跃和更多样化的当代领域之间差距的逻辑方式。
神学和宗教研究在形成它们的贡献中借鉴了解释学的悠久传统和新生态学的敏感。在这里,我们会提到凯瑟琳·凯勒(Katherine Keller)的生态过程神学(ecological process theology)(Keller 2003)、布鲁斯·福尔茨(Bruce Foltz)对东正教传统的解释与发展(Foltz和Chryssavgis 2013)以及福里斯特·克林格曼(Forrest Clingerman)关于地方(place)的作品(Clingerman 2011),作为这类作品的代表,凯勒也表达了当代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声音,以及其他已经提到过的人物,还有葛瑞塔·伽德(Greta Gaard)(Gaard 1993,1998)和许多年轻的学者(参见Gaard 2013)。
地方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lace)——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建造的——仍然是环境解释学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关注点之一。像凯西和穆格劳尔这样的先驱仍是很活跃的学者,他们的工作集中在空间、地方、边缘、转变以及类似的现象。这些地方哲学对城市设计、生物保护、身份理解等都有影响,其他学者扩展了这项工作(例如,Seamon 1993、Stefanovic和Scharper 2012)。
宗教哲学和特别是地方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lace)“变迁的”焦点,为我们指出了环境解释学的其他当代关注,例如,地方解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place)与许多同区分自然与文化以及景观修复本质相联的问题有关。我们能条理清楚地区分“自然”和(所谓“非自然的”)文化吗?当我们试图恢复景观、生态系统或自然本身时,我们会做出什么呢?环境解释学为我们澄清这些问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回应或解决它们,提供了资源。举个例子,有些说法表明,恢复至少部分是通过对叙事的解释学敏感来调解的,在这种敏感中,一个物体或地方的“自然性”(naturalness)与它的起源及其故事有关(Elliot 1982)。
关于景观恢复提供的叙事解决方案指向了对叙事更广泛的关注,叙事是某些解释学方法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Ricoeur 1992年;Kearney 2001)。环境解释学的工作追问了叙事在我们对不止于人属世界的感知、经验和理解(Treanor 2013;Drenthen和Keulartz 2014)以及在环境美德培养(Treanor 2014)方面的作用。乌特斯勒(Utsler)(2009)更广泛地指出了这种方法对环境哲学的意义。
三、结 论
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找出无争议,或不需要一些限定条件或详细阐述的环境解释学的定义特征,这使该领域不太可能欣赏沿着现象学路线提出的一个简洁有力的战斗口号——“回到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然而,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广泛的、交集的认同,它们标志着“环境解释学”。这一多层面运动的不同成分的特点是:(1)相信利科所谓的现象中的“意义剩余”(surplus of meaning);(2)对有关不止于人属世界的现象,生态系统、景观、荒野、建筑环境、元素、天气、肉身以及其他任何可能会考虑到的“环境的”因素的特殊兴趣;(3)利用从哲学、神学、文学批评、心理学和类似领域所获取的解释学资源来揭示其中的一些意义。因此,“环境解释学”吸纳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努力,这些努力通常以引入哲学解释学的资源为特征来应对与环境有关的问题,这种环境既包括狭义的非—人类的自然世界或野生世界,也包括相对广义的任何环境,自然的或人化的。
注释:
〔1〕这里指的是广义或宽泛意义上的“哲学解释学”,不是狭义的、在现象学运动背景下产生的“哲学解释学”。为示区别,这里译成“哲学的解释学”。
〔2〕“不止于人属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指一个包含人类在内、不限于人类的大千世界。
〔3〕这里指相对前面讲的宽泛意义上的“哲学的解释学”而言的,它是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产物。
〔4〕这是一种比喻性的修辞表达,相对于后面的“火山式的大爆发”。
〔5〕指上面提到的《生态现象学》(Eco-Phenomenology)。
——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