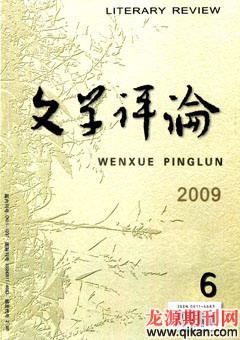创建“中国文学解释学”的若干前提性问题
邓新华
内容提要:对近三十年中国文学解释学研究所走过的基本历程进行反思,可以发现学界对有关中国文学解释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前提性问题还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达成共识,对这些前提性问题进行追问并提出初步的解答策略,对于我们更好地实现创建“中国文学解释学”的目标应该不无裨益。
对西方现代解释学进行引进和介绍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尝试创建“中国的文学解释学”,可以说是近三十年中国文学解释学研究所走过的基本历程,对这一段历程进行反思可以发现,我们的中国文学解释学研究尽管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若干关乎中国文学解释学理论建构的前提性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并形成共识,因此有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
一
首先是中国文学解释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学界对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经学与中国文学解释学的关系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学解释学起源并生成于中国传统的经学解释学,因此研究中国的文学解释学就是研究中国传统的经学解释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的经学解释学大多并不是围绕文学性问题展开的,因此它理应被排除在中国文学解释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其实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未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经学解释学与中国文学解释学的辩证关系,因此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学界通常所说的“经学”,按照最一般的理解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因此它的确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献解释学。经学的起源,晚清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断定为“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这里所说的“六经”即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典籍。但儒家的这六部典籍真正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最高经典,则是从西汉中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上述几部儒家典籍法定为“经”并设立《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五经博士开始的。自此,对“六经”的训诂、考据、理解和解释便成为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一门学问——“经学”,并由此而形成一整套对中国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发生重要影响的注经释义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再加上作为文学文本的《诗经》本属于“六经”之一,经学家在对《诗经》进行训诂、考据和解释的过程中同样提出了不少富有解释学意味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命题。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学解释学就和经学解释学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从中国的文学解释学与经学解释学的联系来看,由于中国的文学解释学是从经学解释学的母体里孕育出来的,因此经学解释学的一整套理论原则方法作为遗传基因必然要存留下来并对文学解释学产生若干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举其大者,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经学解释学的解释目的对文学解释学的影响。尽管经学家们经常标榜他们注经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把握所谓“圣人之道”,但从根本上看,他们注经的真实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代以儒教治国的统治者们大力提倡“经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经学解释学的这种以维护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为本位的解释目的也就内在地决定了,经学解释学必然要把儒家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作为解释的根本尺度,而这种由解释目的裹挟而来的解释标准对文学解释学的影响不仅巨大,而且有时候还是灾难性的”。二是经学解释学提出的一些基本的解释原则对文学解释学的影响。如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原则,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原则等等,由于这些原则大多是在讨论如何理解和解释文学性文本《诗经》的时候提出来的,再加上后世无数注经者的踵事增华,这些原则遂衍化为文学解释学的根本解释原则,从而对文学解释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三是经学解释学所创立的一些基本的解释文体或解释形式对文学解释学的影响,如“传”、“笺”、“诂”、“注”、“解故”、“故训”、“义疏”、“正义”、“集解”等等。对经学解释学自身而言,这些基本的解释文体或解释形式的创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有了这些解释经典的固定的体裁和格式,经学家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解释才有可能被定型化并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而得以流传下来,同时这也是经学解释学走向成熟的一个外在的标志。然而对于文学解释学研究来说,内容则比形式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些解释文体或解释形式里所承载的无比丰富深刻的解释学理论和思想,才给文学解释学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例如经学家焦循对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解释原则的理解和解释,就是借“正义”的解释文体或解释形式传达出来的,而焦循的上述思想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解释学之根本解释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中国的文学解释学由于是从经学解释学的母体里孕育出来的从而与经学解释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但由于它同时又是中国古代理论家和批评家紧密结合文学解释活动的具体实际提出来的,其中凝聚着中国古代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解释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因此它与经学解释学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在于:解释者究竟是把解释对象当作文学来理解,还是当作政治道德的教科书来研究。在《诗经》阐释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诗》为经”与“以《诗》为诗”这两种阐释取向的对峙,实质上就是经学解释学与文学解释学的区别所在。所谓“以《诗》为经”,就是把《诗》看成是儒家的经典,一味在作品中寻找政治教化的讽谕托义,从而将优美动人的文学形象歪曲为僵化的政治道德教条。汉代的儒家经生对Ⅸ诗》的解说就是典型的“以Ⅸ诗》为经”。在汉代经学家那里,明明是表现周代先民之生存景况和情绪心态且形象优美、意蕴深厚、韵味无穷的《诗三百》,却统统被套上“温柔敦厚”和“思无邪”的光圈,成为政治教化和辅成王道的“谏书”。这种置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特征于不顾而竭力把文学性文本纳入经学的企图,无疑取消了文学,也取消了对文学的文学性解释。因此经学解释学的这种“以《诗》为经”的解释态度和解释取向受到历代不少理论家的尖锐批评。如宋代的文学解释学家朱熹就对时人以汉儒的迂腐陈见来肢解文学的做法深致不满:“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清人方玉润也指出:“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两家性情,与《诗》绝不相近。故往往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又安能望其能得诗人言外意哉?”而“以《诗》为诗”则完全不同,它是把《诗》当作文学作品来理解,它注重的是对《诗》的情感性、形象性和审美性特征的考察。例如朱熹就明确指出:作为解释对象的《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他看重的是《诗》中各种自然情感的诗意的表现,而不是经学家硬性比附和强加的美刺讽喻之义。
他还基于对《诗》的审美抒情本性的认识,对Ⅸ毛诗序》单方面从政治教化角度解说“风”的含义提出批评,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而与“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所谓政事善恶无关,这同样是在强调解释者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作为解释对象的《诗》的审美性和抒情性特征上,而不是外在于文学文本的那些政治教化的东西。
在弄清楚文学解释学与经学解释学的联系与区别之后,现在就可以比较方便地回答中国文学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了。在我看来结论很明确,创建中国的文学解释学就应该从中国文学解释学与传统经学解释学的联系与区别处着手: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文学解释学是从经学解释学的母体里孕育出来的,所以创建中国的文学解释学首先必须注重考察文学解释学与经学解释学的内在联系,必须从解释目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方法等根本性方面来深入考察经学解释学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原则、理论命题和方式方法如何衍化为文学解释学的重要理论原则、理论命题和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文学解释学与经学解释学又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它关注的是文本对象的审美特征,注重的是对文本对象的诗性阐发,所以创建中国的文学解释学绝不应该把眼光局限在经学解释学所限定的所谓“五经”或“十三经”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实际上中国历代众多的诗歌总集、选本、注释本和诗话、词话、曲话乃至小说戏剧评点等一切有关文学文本的文学性理解和解释的著述,以及中国古代理论家批评家对文学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特点、规律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都应该作为文学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梳理和总结出具有理论涵盖性和理论穿透力的中国文学解释学。
二
由于创建“中国的文学解释学”是在西方解释学理论输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就自然引申出创建中国文学解释学的第二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处理好“中”与“西”的关系问题。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有两种思想倾向不容忽视:这就是狭隘的“中国化”与片面的“西方化”这两种“单一性”的思想倾向。所谓狭隘的“中国化”,是指一种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解释学思想盲目自信而拒斥西方解释学理论的思想倾向,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典型表现就是以为与西方思想文化即将从世界的中心退到边缘而中国的思想文化则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大趋势相匹配,中西方文学解释学的地位和影响也将产生相应的错位。而所谓片面的“西方化”则是指一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与文化,无视我们民族自身的理论遗产,以西方解释学的概念、逻辑、观点和理论为标准和尺度来分析和评判中国的文学解释学的思想倾向。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认为解释学是西方的专利,它产生在西方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土壤之中,因此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学,这显然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虽然也主张以西方的解释学理论为参照来解释中国的文学解释学思想,但实际上是削中国传统文论之“足”来适西方文论之“履”,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印证西方解释学思想的正确性,这同样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
很显然,狭隘的“中国化”与片面的“西方化”这两种“单一性”思想倾向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学解释学研究都是极为不利的。我认为中国文学解释学理论重建要处理好“中”与“西”的关系问题,就必须坚持“对话”的根本立场和原则。按照加达默尔的解释,所谓“对话”就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之间寻找契合点,从而形成“视域融合”,“对话”的目的是达到相互沟通和理解,“对话”因此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种主导精神。就创建“中国的文学解释学”这一理论命题而言,坚持“对话”特别是“中西对话”的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中、西方文学解释学理论拥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构架,因而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二者之间也并非存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中西方文学解释学理论作为人类解释实践经验的结晶,必然蕴含着为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共通性。所以中、西方文学解释学理论应该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坚持“中西对话”的原则,就有可能在共性与个性的联系与区别中揭示出中国文学解释学深刻而独特的理论蕴涵。
例如中、西方解释学理论都对解释学的基本问题——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十分重视,但是通过“中西对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中、西方解释理论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在西方,对理解和解释问题的重视主要体现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探讨和形而上的分析,例如在西方传统解释学那里,理解(understanding)、解释(interpretation)和运用(appplication)被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西方当代哲学解释学则更重视理解、解释和运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更把解释看成是理解的发展和展开。而在中国,对理解和解释的重视主要以实践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中国文学解释学很早就开始了对于文学阐释活动中理解、解释和运用这三种方式的探讨,先秦时期盛行的“观《诗》”、“说《诗》”和“用《诗》”就是理解、解释和运用的三种典型范式”。在这里,中西方解释理论都对解释学的基本问题理解、解释和运用十分重视,这是“异中之同”但各自重视的方式又不一样,这又是“同中之异”。如果在此基础上将“中西对话”再继续推进一步,我们就会有更重要的发现,这就是:当西方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理论家把西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上述思想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的时候,西方长于理性分析的逻辑思辨传统的弊端就完全显露出来:他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具体化”的理解和解释的时候,往往热衷于对解释者的审美感知觉经验、作品的意义乃至整个文本理解过程作纯理性的解析,结果反把原本包孕着无限审美愉悦和审美心理奥秘的文学理解和解释活动变成了一个由语言和逻辑分析所笼罩的世界,从而最终使文学理解和解释活动失却其活泼泼的生命而成为一种僵死的存在。与西方文学解释学对理解与解释问题作形而上的理论分析不同,中国文学解释学始终把作品意味的品鉴看得高于作品意义的阐释,它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品味”、“涵泳”、“自得”的文本理解方式和“象喻”、“摘句”和。论诗诗”的诗性阐释方式,与作为解释对象的诗性文本有着更为内在的契合,它从直观感悟角度对作品整体风神韵味的玩赏和把捉,在内容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精微性上,都远胜于西方解释学那种细密繁琐的纯理性解说。显然,这种中、西方文学解释学的深层差异,中国文学解释学富有东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理论蕴涵,惟有通过“中西对话”,才有可能被洞察。
三
学界提出创建“中国的文学解释学”这一命题本身还包含有第三个前提性问题,这就是如何处理好“古”与“今”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在个问题上,学界也存在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复古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主张中国的文学解释学研究应该回到乾嘉学派的老路
上去,另一种则是“现代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用现代的理论来简单比附中国传统的解释学思想资料,或者对中国传统的解释学思想资料作过度诠释。
很显然,“复古主义”和“现代化”这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对中国文学解释学的理论重建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我看来,要处理好中国文学解释学研究中的“古”与“今”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必须并行不悖地坚持“历史还原”和“现代阐释”这两个原则。
这里所说的“历史还原”的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像“复古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要求解释者完全消除已有的文化历史“前见”或“前理解”去重返过去,因为绝对意义上的“重返过去”和“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解释者所能“还原”的只能是他所“理解的”历史。所以我们强调的是研究者应该首先将中国古代理论家批评家对文学理解和解释活动的规律性认识和经验总结,以及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文学理解和解释的概念、命题和方式方法放回到其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其原初的文化思想蕴涵和理论蕴涵。例如中国的文学解释学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文学理解和解释的规律的探究,并由此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命题和方式方法。对这些重要的解释学概念,命题和方式方法的清理和探讨无疑是中国文学解释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概念、命题和方式方法往往并不是首先从文学解释活动中总结出来,而是首先从哲学或经学领域内产生的,这就需要我们去仔细地加以辨析。例如“涵泳”最早只是一个纯道学的概念,在宋代理学家张载和二程的心目中,“涵泳”具体是指一种优游不迫的体道方式和人格修炼方式,后来朱熹将其运用于《诗经》的理解和解释,“涵泳”才逐步衍化为中国文学解释学的一种重要的文本理解方式。尽管“涵泳”的理论内涵发生了由哲学(理学)向文学的转换,但“涵泳”本身固有的重内省尚体验的心性之学的理论意蕴却并没有消解,而是继续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了“涵泳”这种内倾式的文本理解方式的形成。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学解释学提出的诸多有关文学理解和解释的概念、命题和方式方法放到其赖以生长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还原性的考辨和分析,其原初的理论蕴涵及其由哲学向文学解释学演变的历史过程和逻辑发展过程就有可能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其实不仅仅是“涵泳”,中国文学解释学提出的有关文学理解和解释的概念、命题和方式方法还有很多,如作为文本理解方式的“自得”、“品味”、作为诗性阐释方式的“象喻”、“摘句”和作为文本解释策略的“妙悟”、“活参”、“忘言”等等,都需要运用“历史还原”的方法来加以考辨和分析,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原初的思想蕴涵和理论蕴涵。
但是,对中国文学解释学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历史还原”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坚持“现代阐释”的原则。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古代的文论家、批评家在千百年来的文学理解和解释的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一些概念、命题和方式方法作为一种历史遗留物,它本身的确蕴含有许多合理的因素和真理的颗粒,但它还不是真理本身,它还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局限性。因此,只有研究主体立足于当下的人文现实环境并根据现实的需要,在现代理论思维、美学观念和方法论的统摄下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相关材料进行新的理解和新的阐释,中国古代的解释学思想资料中潜藏的极为深刻极有价值的文学解释学思想才有可能被激活,其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才能最终被开掘出来。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现代阐释”与当前文学解释学研究中存在的“现代化”倾向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后者缺少“历史还原”这个环节,它从根本上是反历史主义的。
从中国文学解释学研究的实际来看,坚持“现代阐释”的原则的确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增添许多亮色,可以发现许多我们以往难以发现的东西。例如由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的文学解释学原则,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似乎很难再有什么新的突破。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确蕴涵有完全可以与现代解释学理论相沟通的理论因子:“以意逆志”表面上看是以“志”为指归,即强调解释者必须恢复作者的“原意”,这与西方传统解释学的解释取向似乎十分一致。但由于其间加了一个“意”字,因此这实际上是对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的肯定,这又与西方传统阐释学竭力消除由时间间距和历史间距所造成的解释者对于作者的误解的理论相悖,而与西方现代解释学家加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观点不谋而合。而且还有,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由于包含着一个“逆”字,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初始视域”下的作者之“志”和“现实视域”下的解释者之“意”不是自行会合,它需要一个“逆”的过程,而两个不同视域下的“意”和“志”正是通过解释者的主动的“逆”的过程才最终产生了契合,这不正和加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观点相通吗?由此可见,中国文学解释学研究只有坚持“现代阐释”的原则,那些潜藏在传统文论思想材料中的极为深刻极有价值的文学解释学思想才有可能被激活,也才能真正进入到当代形态的“中国文学解释学”的理论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