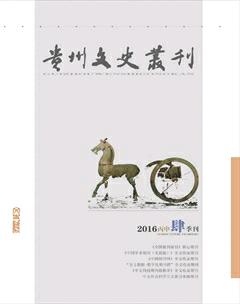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张承宗
摘 要: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经学 学风 演变 更新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4-41-56
我国近代著名经学家皮锡瑞(1850-1908)在《经学历史》中认为:两汉为“经学极盛时代”。1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中衰的原因,一是政治变迁,“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2二是学术走向,“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3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其原因是国家分裂,“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为南北朝分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4
周予同在1928年为《经学历史》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皮氏是经今文学者。”5又说:“不要忘记皮锡瑞究竟只是一个经学家而不是史学家。因为他不是史学家,所以史料的搜集不完备,史料的排比不妥善,而且每每不能客观地记述事实,而好加以主观的议论。”6周予同对《经学历史》的评价是中肯的。所以皮氏所说的魏晋“经学中衰”,并不能代表魏晋经学的全貌。皮氏所说南北朝“经学分立”有一定道理,但对“南学”“北学”之分的意义缺乏足够的分析。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历史学的立场与视角来研究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一是要去除派别成见,对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给予平等的地位。二是要考察经学传播的地域范围是否扩大,学者及受众的人数、性别及民族成分是否增加。三是考察经学与玄学、佛学的互动关系,对经学的演变与更新起了什么作用。四是考察教育内容与格局的变化是否促进了经学的进步。
一、两汉经今古学之争是政治问题也是学术问题
两汉经学的成立,在政治上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西汉所立十四博士都是今文学家。其中:《易》有施、孟、梁丘、京房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有公羊春秋颜、严二家。
武帝好大喜功,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的恶果。到元、成、哀、平之世,各种矛盾激化。王莽以刘歆为国师,利用古文经的《周礼》《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推动托古改制。王莽虽尊古文,但不废今文。他以周公自居,但很多改革不切实际。王莽失败,光武中兴,又废古文,提倡今文经。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流传。
章帝建初四年(79)十一月,大会诸生、诸儒于白虎观辩论,“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2建初八年(83)十二月,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榖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3章帝的诏书,一锤定音,古文经取得了与今文经同等的待遇。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问题基本解决,东汉今古文并行已成常态。但政治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学术问题的解决,经今古文之争在学术领域依然进行。
东汉的今文学大师,除何休外几无名人。古文学大师,则有贾逵、郑众、马融、许慎。何休作《公羊解诂》,为《公羊》辩护,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郑玄毫不客气,“乃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4
郑学的代表人物郑玄,字康成,北海(今山东潍坊)高密人。东汉末年,他在太学受业,先通今文,后通古文,曾“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通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5郑玄博学多师,兼通今古文。他以古学为宗,兼录今学以附益其义,并下功夫遍注群经,自成一家之言。史称:“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议》《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6
郑玄并非专主古文。他博习古文,今文、谶纬之学,采取今文的长处,又混合谶纬,融入古文,多有创新,使古文学获得极大胜利。皮锡瑞说:“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7东汉末年郑玄的出现,标志着魏晋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由于郑玄弟子众多,影响很大。其门人山阳郗虑、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还有乐安国渊、任嘏都出仕曹魏,著名于世。所以,郑学在曹魏一代,仍有一定影响。
二、汉末至三国经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影响
两汉时期经学传播的地域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汉末至三国随着人口的流动迁徙,经学在长江流域传播,甚至影响到南方的交州;并反馈回北方黄河流域,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
(一)汉末荆州学者对经学的传播与影响
汉末董卓之乱,黄河流域的大批难民涌入荆州地区,其中“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8刘表对这些北方来的知识分子安慰赈赡,并加以录用,发挥其文化优势,致力于保境安民,恢复经济与文化。
刘表本人是汉末名士,著有《周易章句》九卷、《丧服后定》一卷、《荆州占》二卷、集一卷。他在荆州“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1宋忠(一作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刘表治理荆州时,他为五等从事,著作有《周易注》《世本注》《太玄经注》《法言注》及《易纬注》《春秋纬注》《孝经纬注》等。他对汉代学者扬雄的《太玄》深有研究。《太玄》融合《易》《老》,最早开以玄释经的风气。宋忠为《太玄》作注,影响很大。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占领荆州,赤壁之战后退回北方,荆州名士除诸葛亮、庞统等随刘备入蜀外,大部分士人如宋忠、王粲、傅巽、刘廙等都随曹操回到北方,又将这种新风气带到了黄河流域。魏晋时期的儒学大师王肃“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2其学术带有明显的儒道兼综的倾向,就是受宋忠的影响。
避乱荆州的的学者,也有精通《左传》的,如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3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4
(二)蜀汉境内的经学传播与学术文化
东汉末年,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最早为刘焉出谋划策的是今文学者董扶。史载:“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难。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5随刘焉返回蜀地。陈寿《益部耆旧传》曰:“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6
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祖父真,有清节高名”。《三辅决录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经》,兼通谶纬,学无常师,名有高才。”7法正是引刘备入蜀的谋主。
蜀汉境内的治经学者,既有外来人士,也有当地人士;既有今文学者,也有古文学者。学者之间因持论不同而时有争议,但这种争论并非出于地域之见。长江上游地区不仅与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地区有学术文化交往,而且与北方地区也有一定学术联系。
南阳人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刘备平定蜀地后,以许慈、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孟光是河南洛阳人,“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8常与来敏发生争论。来敏是义阳新野人,“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9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10汉末汝南的月旦评,就是由许劭主持。士人为了提高名气,往往请他们品题。许靖为了避董卓之害,移居江南。孙策取江东,许靖又远走交州避难,受到交阯太守士燮的厚待。他以书信婉拒曹操邀请,后应刘璋之招入蜀。荆州学者宋忠得知后,曾致书蜀郡太守王商,称赞许靖的才具。王商亦因此而对刘璋说:“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后来,刘备任命许靖为太傅,“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11他与曹操的公辅大臣华歆、王朗及陈群等都有书信往来。
蜀地比较流行的是今文经学。汉末广汉人杨厚曾以孟氏《易》及图谶之学教授,生徒甚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董扶、任安。董扶善于言谈,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后丞相诸葛亮问秦宓以扶所长,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1任安“究极图籍,游览京师,还家讲授,与董扶俱以学行齐声。”他去世后,“门人慕仰,为立碑铭。后丞相亮问秦宓以安所长,宓曰:‘记人之善,忘人之过。”2褒贬时事,臧否人物、品题高下,是东汉末年的一股清议之风。这股清议之风,后来成为清谈的先导,它在长江上游的蜀地亦有所发展。
杨厚的弟子,还有巴西阆中人周舒,“名亚董扶、任安”,而喜图谶。“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3其子周群从小受学于父,善望气。周群死后,其子周巨“颇传其术”。4周氏三代,可谓谶纬世家。
任安的弟子,有梓潼人杜微、成都人杜琼,都精于谶纬之学。杜琼“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巴西人谯周,年轻时向杜琼请教图谶之术,有所领悟,编了“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后来,宦官黄皓弄权于宫廷之内,蜀汉景耀五年(262),“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周曰:‘此虽己所推寻,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5谯周是劝说刘禅降魏的主要人物之一。
蜀地治今文经学而不言图谶的,有成都人张裔。他“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诸葛亮出驻汉中,裔以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吏,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6此人处事机敏,深得诸葛亮信任。
蜀地治古文经学者,有梓潼人尹默、李譔,他们深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见闻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受古文学。尹默“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他担任过蜀汉的劝学从事,后来又“以《左氏传》授后主”。李譔于“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他的著作有“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7李譔与王肃虽分仕蜀魏,但都是宋忠的弟子,共同的师承关系,使他们学术观点多同。可见三国时期,政治上虽然鼎立,但南北学术文化上的联系却并未割断。以古观今,怎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东吴境内的经学传播与学术文化
东汉末年大量士人避乱江东,也有一部分人越过荆、扬二州,远至交州。交州太守士燮,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时就南迁交州。其父士赐,东汉桓帝时为日南太守。士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又兼通今古文《尚书》。在他治理下,交州社会秩序安定,“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8汝南人许靖、南阳人许慈,避居交州,建安中一起自交州入蜀。沛郡人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9后来出仕孙吴。汝南人程秉,是郑玄的弟子,“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10后来成为孙权的太子太傅,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刘熙字成国,北海人,诸史无传。他“博览多识,名重一时,荐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谓之征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中州士人避难交州者,多从游焉。生徒多至数百人,建安末卒。作《释名》八卷”。11他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考见古音,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遗。著作仅《释名》流传至今,还有《谥法考》《孝经注》《孟子注》《列女传》等,均已亡佚。
长江以北来到江南的士人中,有不少是知名学者。如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张昭“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1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严畯也是彭城人,“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2琅邪(今山东诸城)阳都人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3
江南的学者治学方法上与北来的士人有所不同,如会稽余姚人虞翻著《易注》,开以玄释经之风,他认为:“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4虞翻是江东《易》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江东士族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经师。史载“翻性疏直”,因失言得罪了孙权,被徙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5他对交州学术文化的发展有所贡献。
吴郡吴人陆绩“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孙权时“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加偏将军,给兵二千人。绩既有躄疾,又意存儒雅,非其志也。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豫自知亡日,乃为辞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逼厄,遭命不永,呜呼悲隔。又曰:‘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年三十二卒”。6当时的郁林辖境,在今广西玉林西北、贵县东南间。陆绩以太守的身份,扩大了儒学及玄学的传播范围与影响。他自称“有汉志士”,不忘故里“吴郡”,预见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可谓远见。
三、魏晋经学的演变与玄学的兴起
魏晋时期被皮锡瑞称作“经学中衰时代”,其实也仅仅是今文经学的中衰。这一时期经学的传统地位在中原地区仍得以继续,但这种继续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演变中的继续,更确切地说,是黄河流域的儒家经学发生了演变。大致说来,汉魏之际是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则是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王学亦好景不长,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北方继续传承。
(一)曹魏时期的“儒宗”
曹魏时期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鱼豢在《 魏略·儒宗传》中记载了他们的事迹,在当时黄河流域文化发展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董遇,字季直,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人,性质讷好学,家贫,靠采稆负贩为生,常挟持经书,抽空习读。建安二十二年(217)被录诣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从曹操于左右。黄初中,出为郡守。明帝时,入为侍中、大司农。撰有《周易章句》《老子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义,遇言‘冬者岁之余,夜乃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7可见他要求学生扎实读书,重视基本功。
贾洪,字叔业,京兆新丰人。“好学有才,而特精于《春秋左传》。马超兵败投蜀后,贾洪为曹操所召,署为军谋掾,“晚乃出为阴泉长。延康中,转为白马王相。善能谈戏”。白马王曹彪“亦雅好文学,常师宗之”。8
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学,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他本是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投依刘表。建安十三年(208)归属曹操后,与曹植相交甚欢。魏黄初年间,“为博士给事中”,“作《投壶赋》千余言”,9甚为工整,著作有《笑林》。
薛夏,字宣声,天水人。“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均为世家大族,“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东诣京师”。曹操“宿闻其名,甚礼遇之”。魏文帝曹丕“又嘉其才,黄初中为秘书丞,帝每与夏推论书传,未尝不终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谓之薛君。……后数岁病亡,敕其子无还天水”。1薛夏出身寒门而颇有骨气,虽受曹魏政权重用,仍担心其子受天水地方大姓迫害,反映了当时世家大族把持地方政治的根深蒂固。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曾避乱荆州,后出仕曹魏。曹操“召署军谋掾。黄初中,为谯王郎中。……年八十余,以老处家,就之学者甚多。禧既明经,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叹息谓鱼豢曰:‘天下兵戎尚犹未息,如之何?豢又常从问《左氏传》,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之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豢因从问《诗》,禧说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作诸经解数十万言”。2
苏林,字孝友,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建安中,为五官将文学,甚见礼待。黄初中,为博士给事中”。3曹丕作《典论》中曾提到他。魏明帝景初年间,高堂隆、苏林、秦静都已年老,曹叡下诏:“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 4意在传绍其业。
乐详,字文载,河东人。少好学。建安初步行至许(今河南许昌),从谢该学《左氏传》,撰有《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所问既了而归乡里,时杜畿为太守,亦甚好学,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至黄初中,征拜博士。……至正始中,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5乐详与杜畿对河东地区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很有影响,史称:“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6除上述七人为“儒宗”外,曹魏时期黄河流域的儒学之士还有:周生烈,治《春秋左氏》学,作《论语》义说;杜宽,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糜信,著《春秋榖梁传注》《榖梁音》《春秋说要》。
(二)魏石经的刊刻
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国最早的石经,是东汉的《熹平石经》,又称《一字石经》《今字石经》《鸿都石经》,是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刻写的。熹平四年(175),蔡邕等人“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7董卓之乱后,洛阳残破,汉石经亦受到破坏。汉魏之际,今文经学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古文经学地位上升,并出现了治经学者必须兼通今古的趋势。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以古文为主,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要,并反映了今古文地位的变化。
魏石经刊刻于正始年间,位于汉石经的西面。后人或据其刊立之时代,称《正始石经》;或据其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称《三字石经》或《三体石经》。关于魏石经的记载,见《晋书·卫瓘传》附《卫恒传》、戴延之《西征记》、郦道元《水经·谷水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关于魏石经的经数与石数,因上述史料歧异,故后人多有考证之作。
(三)王肃及西晋儒学
魏晋之际,反对郑学最力的是王肃。其父王朗,汉末为会稽太守,被孙策所虏,复归曹操,为魏三公,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王肃,字子雍,生于会稽,“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8颇受荆州学派之影响。黄初中,为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229)拜散骑常侍。青龙中,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正始、嘉平年间,是魏晋交替的关键时期。王肃坚决支持司马氏集团,其女适司马昭,生晋武帝司马炎与齐王司马攸,政治上炙手可热。他遍注群经,极力攻击郑学。史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异同,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经》,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1晋初郊庙之礼,皆依王说,而不用郑义。当时,治郑学的孙炎、王基、马昭都驳王申郑。
孙炎,字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王肃作《圣证论》以讥玄,孙炎“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2
王基,字伯舆,官至征南将军,封东武侯。魏晋之际,“王肃著诸经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3还曾作《毛诗驳》,以申郑难王。
王肃为了与实力深厚、门徒众多的郑学相对抗,故意标新立异,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明显带有儒道兼综的倾向。他极力渲染孔子拜老子为师,把孔子的“天道”与老子的“道”沟通起来。王肃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又以道家思想补充儒学,为经学的玄化起了先导作用。王学随着司马氏政权的垮台,也就失去了市场,但其中一些合理的内涵也不应全盘否定。
西晋时期,活跃于黄河流域的儒学之士,据《晋书》卷九一《儒林传》记载,还有:陈邵,撰《周礼评》;刘兆,作《春秋调人》,又为《春秋左氏》解,撰《周易训注》;氾毓,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徐苗,作《五经同异评》,又著《玄微论》;崔游,撰《丧服图》;范隆,著《春秋三传》,撰《三礼吉凶宗纪》;董景道,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著《礼通论》;续咸,师事杜预,专《春秋》《郑氏易》。这些散布于各地的儒学之士,使儒家经学深入于士庶之中,从而为永嘉之乱后儒学传统得以在中原继续传承奠定了基础。
(四)玄学兴起与儒玄双崇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研究老庄学说,并以老庄学说解释儒家经典,祖尚玄虚,别树义理,开始对汉儒的经训进行玄学的改造。他们抛弃了两汉的正统外衣,重新解释天道自然,提出了“贵无”的思想体系,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4何晏写过一篇《无名论》,保存在《列子·仲尼篇》张湛注中,他提出无名为道,圣人体道,故圣人无名。唯其无名,才可以遍天下之名名之;唯其无所有,才能用有所有。其实何晏心目中的圣人,仍然是尧舜与孔子。
何晏作《论语集解》,援道入儒,而儒道双崇。在《学而》注中,他说:“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5在《述而》注中,他说:“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6在《卫灵公》注中,他说:“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7可见他并不反对儒家的名教,只是认为名教应复本于自然,主张无为而治。这部《论语集解》是以他为主,与孙邕、郑冲、曹羲、荀顗四人合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可见这部《集解》是时代的产物与集体的结晶,“虽采郑注而实不尽主郑”,8反映了魏晋的时代变化与经学更新的趋势。
王弼注《老子》《周易》,主张道本儒用,他善辩能言,但不善事功。他在传统观念的框架中,把孔子凌驾于老子之上,成功地调解了儒道之间孰高孰低的矛盾。何晏曾经为《老子》作注,后来看到王弼的《老子注》精奇高明,自己便不再作注,而改作《道》《德》二论。
王弼重视言意之辩。他以老庄解释《周易》,把言、象作为得意的工具,强调“得意忘言”,主张“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着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1这样就把《庄子·外物》篇中的“得意而忘言”与《周易·系辞》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说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2玄学的发展,使老庄之学兴起,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已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
(五)“名教”与“自然”之争
正始十年(249),发生了高平陵事件。这场政变,是司马氏取代曹氏的关键一搏。曹爽软弱无能,束手就擒,被司马懿一网打尽。何晏被杀,王弼夭亡。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氏之手,儒学世家成为司马氏政权的支柱。这个集团重又提倡名教,标榜“以孝治天下”,3而行篡夺之实,其名教的虚伪性为一些正直的士人所不齿。于是,出现了一批政治上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的人物,其典型代表就是嵇康与阮籍。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魏晋之际,他“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4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5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6在《管蔡论》中,他为管叔、蔡叔辩诬,说他们反对周公是“恩在王室”、“欲除国患”、“翼存天子”。7其实两人都是忠贤之臣,只是因不了解情况,才怀疑周公。嵇康为管蔡翻案,乃是针对“淮南三叛”,讥刺司马氏也。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赞嵇康“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8就曾以此篇作为例证。
嵇康在玄学理论上最有影响的是《养生论》与《声无哀乐论》。他受道家思想影响,清心寡欲、淡泊人生、注重内功的养生方法,与那种放荡形骸、沉湎酒色的旷诞不羁之风有天壤之别。他音乐造诣很高,当遭受迫害临终就刑时,十分淡定。向秀在《思旧赋》序中说:“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绝代古曲《广陵散》于今绝矣!传世的只有其探讨音乐理论的《声无哀乐论》。嵇康认为人是有哀乐的,而音乐的声音是没有哀乐的。声音是客观的存在,感情是人们主观的东西。感情与音乐,本来是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人的哀乐,只是内心感情的宣泄。音乐的表演形式,艺术手法和美感,只能使欣赏音乐的人精神集中或分散,感到兴奋或恬静,并不能左右人的喜怒哀乐。在这种情况下,音乐才起诱导的作用,使它表现出来。从哲学的角度看,《声无哀乐论 》所阐述的道理,在考辩“名”“实”方面确有独到见解。所以,直到南北朝时,仍是清谈的重要内容,正如王僧虔《戒子书》所云“《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9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崇尚老庄、不拘礼法,喜怒不形于色,而性至慎,口不论人过。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10正是这种佯醉及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的处世方法与态度,使他得以避祸。
阮籍崇尚自然,最讨厌礼法之士。在《大人先生传》中,他诅咒礼法之士如虱处裤中,“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档”,11若遇火烤便难逃一死。他向往庄子,在《达庄篇》中论天地万物自然一体,发挥庄子的相对主义,推论六经与老庄之道的关系,显示出企图构通“名教”与“自然”的趋势,其言论行为并未违背儒学传统及西晋玄学的主流。如果我们再看看他的《通易论》与《乐论》,更可看出他内心并不是反对名教的。他赞同礼乐,承认上下、君臣、贵贱之别,推崇圣王制礼作乐之功。不过他认为当时的“君子”是虚伪的,应该受到谴责。
魏晋交替,司马氏滥杀名士,“自然”与“名教”发生激烈冲突,竹林七贤分化。嵇康龙性难驯被杀,阮籍有疾为颦沉醉。山涛、王戎为时羁绁而左右逢源,身居高位。刘伶啸歌《酒德》,阮咸妙解丝竹。向秀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使“读之者超然心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1在《逍遥游》注中,他提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在山林之中”。从而将儒家礼教与老庄思想统一起来,使玄学适合门阀士族的现实需要,变为一种与儒道互补的官方哲学。
中朝清谈派的领袖,琅邪大族王衍,身踞高位,不理政事,“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在其影响下“矜高浮诞,遂成风俗”。2永嘉之乱,王衍被石勒所俘,居然厚颜无耻,“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石勒怒而“使人夜排墙填杀之”。王衍临死,才懊悔地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石勒怒斥王衍:“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 ,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3可谓一针见血,点出了问题的要害。西晋时期,高门士族凭借权势把持政权所造成的制度腐败,让许多本来不称职的人身居要津,这才是西晋亡国的症结所在。即使有个别出类拔萃的人物,也无法挽救腐朽的西晋王朝。
四、十六国北朝的儒学传承与经学特点
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尽管黄河流域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但为了得到中原士族的合作与支持,稳定其在中原的统治,就必须“变夷从夏”,4吸收汉文化而缩小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所以始终把儒学作为其统治思想。同时,汉族知识分子在外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下,也希望通过提倡儒学,将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纳入汉文化的轨道,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于是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其统治地位在北朝时期重新得到确立。
(一)十六国境内的儒学传承
从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刘渊建立汉国到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灭北凉统一北方这一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黄河流域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中纷纷建立政权,出现了群雄割据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历史被称为十六国时期。
刘渊长期生活在与汉族杂处的环境之中,汉化程度较深。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5刘渊的从祖刘宣,师事乐安名儒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6刘渊的后代也都熟知汉文化。其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7第四子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8刘曜字永明,是刘渊的族子。他提倡经学、崇尚文治,“立太学于长安宫中,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9
后赵石勒统治时期,国力强盛。石勒虽不识字,但对文化十分重视。石勒取得司州、冀州后,社会秩序逐渐安宁。他就在襄国“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10
前燕慕容皝统治时期,境内比较安定。他注意提倡文化教育,“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馀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1
前秦苻坚与王猛治理关中,大力提倡儒学。他“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2当时的著名学者习凿齿、苏通、刘祥、郭瑀、公孙永、王欢和胡辩等人,均受到礼遇。苏通和刘祥精于《礼记》和《仪礼》,被分别任命为《礼记》祭酒与《仪礼》祭酒。
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参与经学教学,充当学术的传承人。如韦逞母宋氏,“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韦逞在母亲宋氏的教诲下“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壸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缀撰,正经粗集,唯《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行于世”。3
当时私家的讲学活动,女儿也可旁听。如刘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昞。遂别设一席于坐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昞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4博士郭瑀公开在讲学时别设一席,招刘昞为女婿,满足了女儿的要求。女儿能旁听父亲讲经,从中挑选佳偶。刘昞后来出仕北凉,成为河西走廊的知名学者。
北凉沮渠蒙逊重视文教,对学者很器重。如河西硕儒刘昞,字延明,敦煌人,“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5
敦煌人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6
此外,还有敦煌人张湛、宋繇,金城人宗钦、赵桑,也都受到北凉政权的重视。北凉灭亡后,河西学者的东迁和河西学风的东传,对北魏的学术文化有很大影响。
(二)北朝的儒学与经学特点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7天兴二年(399)春,又“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8
明元帝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9即位后“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10并首次“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11
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又在城东另立太学,并广征北方名流如范阳卢玄、勃海高允等人为博士,并令各州郡举荐才学之士,使儒学在久经战乱的北方重新兴盛起来。为了进一步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太武帝下诏毁佛,并于次日下诏“今制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12这两条诏书的颁布和执行,把儒学推广到了整个鲜卑贵族。后来,又下令在平城西边立石刻写崔浩所注《五经》,用儒经的经义裁断疑狱。
冯太后执政之后,听从高允的建议,下诏在各地设立乡学,“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1以复兴百多年来衰微的儒学。为了促进鲜卑贵族的汉化,冯太后专门设立了皇宗学,为皇子皇孙选择忠信博闻的大儒任教。
北魏儒学的发展在孝文帝时期达到了高潮。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2他在位时,继续大力推广儒学。他亲自在清徽堂、苑堂给群臣讲经,又亲临皇宗学问博士经义。太和十三年(489),在平城建孔子庙。太和十九年(494)南下鲁城时,还亲祀孔庙。迁都洛阳后,下诏立国子太学和四门小学。刘芳、李彪等儒生因精通经义而受到重用。同时,在孝文帝的诏书中,不时地引用儒家经典,大力提倡儒家的忠孝等观念。
宣武帝元恪即位后,对重建国子学和四门学也相当重视,下诏修建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小学,“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3孝明帝元诩于正光中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在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下,北魏的儒学出现了一片兴旺的景象。
北魏的儒学大师有:平恒精通经籍,撰有《略注》;陈奇精于《易经》,注《孝经》《论语》;常爽撰《六经略注》;刘献之善《春秋》《毛诗》,著有《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章句疏》三卷;孙惠蔚以通经为中书博士,转皇宗博士,参与制定雅乐和丧礼;徐遵明善《服氏春秋》,撰《春秋义草》三十卷,精通《三礼》;卢景裕精通《五经》,曾为《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礼记》《老子》作注;李兴业博涉百家,尤善算历,宣曾撰《戊子元历》,入东魏时后又撰《甲子元历》和《九宫行棋历》。
东魏高欢也相当重视用儒家思想教育子弟。他先后聘请北魏博士卢景裕、李同轨到府中教授诸子。李同轨死后,又聘请名儒李铉、刁柔教授诸王经术。李铉著有《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共三十卷。高洋建立北齐政权后,随即下诏恢复中央和地方的官学,“广延髦俊,敦述儒风”。4还下令将高澄从洛阳运到邺城的蔡邕所书熹平石经五十二枚移置学馆。
西魏、北周的儒学比东魏、北齐兴盛。宇文泰“雅好经术”,5执掌西魏朝政时,不仅设立了太学,而且“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6又于诸生中挑选侍读,陪他读书。平定河东以后,他又置学东馆,引名儒为师,教授诸将子弟。
北周武帝宇文邕颇擅儒学,常亲自讲经,并且讨论儒、佛、道三教的异同。天和二年(567)七月,“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7他对儒学大师十分尊崇,将原萧梁的五经博士沈重礼聘到京师长安,封为露门学博士,让他参与讨论《五经》,请他讲授经义。沈重博览群书,擅长《诗》《礼》《左氏春秋》,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主要著作有:《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
周武帝灭北齐入邺城后,亲自到北齐国子博士熊安生家,“亲执其手,引与同坐”,厚加赏赐,拜为露门学博士。8在他的倡导下,“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9熊安生精通《五经》,著有《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四十卷、《孝经义疏》一卷。时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儒学人士皆出其门。
又有樊深精通汉、魏以来各家学说,博览诸史及《苍》《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撰有《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七经异同说》三卷、《义纲略论》并《目录》三十一卷。乐逊师从徐遵明,习《五经》《论语》《孝经》《丧服》,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又著《春秋序义》,精通贾逵、服虔之说,发杜预之微,辞理可观。黄河流域出现了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的第二次儒学高潮,涌现出许多精通儒学的大师。
在研究风气上,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研究《五经》主要依据汉代的旧注,而不善于创新。南朝经学所依据的,基本上是魏晋以来的新注,出现了玄化的倾向。“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1形成了南北不同的两种学风。
五、东晋南朝的清谈与经学的玄化
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批士族南迁,玄学清谈之风也带到了江南。东晋王导善清言,“为政务在清静”。2庾亮“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3他玄儒兼综,“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4殷浩、桓温,行事不同,但都通玄学。谢安镇之以静,因淝水大捷而名垂千古,被誉为“江左风流宰相”。5魏晋士人们苦心孤诣,几代人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终于出现在现实政治文化生活之中。东晋南朝时期清谈的盛行,教育内容的丰富及格局的多样化,对于经学的玄化起了促进的作用。传统儒学经过玄化的更新,也终于适应时代的需要,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
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是侨姓士族的冠冕,也是清谈的领袖。《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记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6可见王导清谈时,只谈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欧阳坚石的《言尽意论》三篇的义理,而词锋无所不至。王导以善谈“清言”而在士族中享有威望,即使像桓温那样有野心的人物也为之折服。这对于他推行镇之以静的政策,稳定东晋政权有着一定的作用。
王导的从兄王敦,也喜欢清谈,他与谢鲲、庾敳、阮脩,“号为四友”。7卫玠好言玄理,为王澄所推服,渡江后到达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8王敦认为,卫玠玄谈胜过王弼、何晏。王导支持清淡,镇之以静。庾亮也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他们的施政,均以宽容为特点。这对笼络士族,维系人心有重要作用。
名士殷浩清谈时,最擅长的内容是谈钟会的《四本论》。“《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9这是一部开六朝清谈先河的著作。殷浩“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10殷浩以善于玄谈著称,但统兵北伐,却损兵折将,大败而还。他“被废,徒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籖,便释然。”11由清谈而皈依释氏,殷浩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六朝时称佛教僧人为“道人”,道教人物为“道士”。
东晋另一名相谢安,是淝水之战中运筹帷幄的决策人物。他年少时,清谈不佳,曾“请阮光禄道《白马论》”,12遭到阮的讥笑。后来,谢安与僧人支道林、玄言诗人许询共集于士族王濛家,谈《庄子·渔父》,已能“作万余语,才峰秀逸……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道林对谢安说:“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1可见清谈是当时上层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清谈是文化修养高低的标志。谢安为了在士族中建立威信,必须“一往奔诣”,努力学会清谈的本领。但谢安与殷浩这类清谈家不同,他有治国的能耐。他不仅能谈玄,还以玄理来释儒经,开辟了学术发展的新途径。像谢安这样既善清淡,又能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当时是不多的。谢安把清谈作为应世的手段,而以治理天下为己任。这正是他比其他清谈家的高明之处。
东晋后期的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也是一位能以玄理来释经的人物。有一次,他与释慧远清谈,问:“《易》以何为体 ”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 ”释慧远“笑而不答”。2殷仲堪最喜欢老子的《道德经》,曾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3从殷仲堪与慧远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当时玄、儒、佛的交往与合流的趋势。
僧人参加清谈,在东晋时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之所以参加玄谈,是为了接近士族,取得士族对佛教的支持,同时又援佛入玄,给玄谈增添了新的内容。其时,长于清谈的名僧竺道潜、支道林、慧远等人,尤为世人所重。
竺道潜,字法深,俗姓王,出身士族。永嘉初渡江,为元、明二帝及丞相王导、太尉庾亮所尊重,后来隐居剡山三十余年,在宣讲佛经的同时,也述及《老》《庄》。他尝在琅邪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座上,名士刘惔问他:“何以游朱门?”他回答说:“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4东晋玄言诗人郭璞《游仙诗》中有“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之句。竺道潜虽是僧侣,而对道家思想的了解却是很深的,所以能以巧妙的谈锋来对付清谈的名士。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永嘉中随家人渡江,后出家为僧。他在玄学清谈方面所达到的精微程度,不亚于王弼,士族王濛曾称赞他“造微之功,不减辅嗣”。5他撰有《庄子内篇注》《即色即玄论》,特别善于玄谈,据《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记载:“《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6有一次,支道林与许询、谢安共集王濛家,言及《庄子·渔父篇》,“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7他写《即色论》,阐发“色即为空,色复异空”8的理论,促进了佛学与玄学的交融。
慧远,本姓贾氏,是中原地区佛教首领道安的大弟子。他受师命派遣南下后,长期隐居庐山东林寺,成为东晋后期南方的佛教大师。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9对儒、道、佛三家理论均有研究。慧远借玄学宣传佛教,影响是很大的。清谈之风客观上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
(二)教育格局的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
晋室南渡,王导镇之以静,儒玄兼综。建武元年(317),他看到“军旅不息,学校未修”,就向晋元帝建议立太学。他说:“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10当年十一月,晋元帝下令立太学。大兴二年(319),在贺循的建议下,开始立经学博士。咸康三年(337),国子祭酒袁瓌上书,请求重立国子学,得到朝廷批准。东晋时期,“公卿子弟,并入国学”。11当时南方社会风气,士人仍崇尚老庄。孝武帝时,谢安运筹帷幄,取得淝水大捷,江南政局比较稳定。太元九年(384),朝廷增置太学生百人,命车胤领国子博士。次年“正月,立国子学”。1
东晋庾亮,于咸康元年(335)在武昌开置学官,起立讲舍,建儒林祭酒。范宁曾在豫章立学,大设庠序,“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官员用自己的俸禄办学,已带有私学的性质。范宁被免官后,“家于丹阳,犹勤经学,终年不辍。……以《春秋榖梁氏》未有善释,遂沉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2。范宁勤于经学,但未完全遵守汉儒章句。他对《春秋》三传皆有所不满,在《榖梁集解》序中,他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榖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范宁的《榖梁集解》,虽存旧说,但不专主一家,多断以己意,力求公允。东晋司徒蔡谟,“既被废,杜门不出,终日讲诵,教授子弟”,3也属于私学的性质。
南朝刘宋政权建立后,因势利导。永初三年(422),刘裕下诏兴学,说:“古之建国,教学为先。”4他任命范泰为国子祭酒,征裴松之为国子博士。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刘义隆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讲授,置生百余人”,对教学内容作了调整。“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又以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5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6
萧道成建立齐朝后,于建元四年(482)立国学,置学生一百五十人,聘张绪领国子祭酒,设博士、助教。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又立国学,“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7王俭是高门士族,被获准在家开馆讲学。这是私学被官方承认、官学与私学合流的重要标志。
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重视文教,曾“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8他还亲自前往当时著名学者刘瓛家中“修謁”,并于永明七年(489)上表文给齐武帝萧赜,为瓛立馆 。刘瓛,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以“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性谦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游诣故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9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少孤贫,曾就学于刘瓛。司马筠也“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强力专精,深为瓛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10儒学人士吴苞,“善《三礼》及《老》《庄》,……与刘瓛俱于褚彦回宅讲授。瓛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瓛,晚听苞也”。可见私学教育中,学生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同时,老师也有选择在何处执教的自由。
南齐的经学家中,不少人精于《易》经,如虞通之善言《易》。张充明《易》。宗测善《易》《老》。玄学家中,喜欢谈《周易》《老》《庄》,如“周颙,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徐嗣伯善清言。柳世隆专以谈义自业,自云清谈第二。王玄载夷雅好玄言。张充尤明《老》《易》,能清言。张绪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诸卦中所有时义,是其一也”。11张充与张绪既是经学家,又是玄学家,是集经学与玄学于一身的人物。
梁朝堪称是六朝官学最发达的时期。天监四年(505),梁武帝“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生徒数百人,官供膳宿,还建立了定期考试的制度,“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梁武帝本人博学多通,对民间州郡及其本身宗族的教育也很重视。他“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508),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1天监八年(509)五月,梁武帝下诏:“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2这种选才用人的方法,开了科举制的先河。
梁朝时“《庄》《老》《周易》,总谓《三玄》”。3当时父兄师友之间,讲究《老》《庄》,以为谈助。五经之中,唯推崇《易》理。梁武帝“洞达玄儒,著有《周易讲疏》《老子讲疏》,“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由于他精通三教,尤善清谈。大同七年(541)十二月,他又“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4把士林馆办成了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晚年,他虽然沉迷于佛教,但主张三教同源,推动了儒学的玄化与佛化,促进了各种不同文化习俗的融合。
梁朝的伏曼容,宅在建康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5崔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是会稽山阴人,“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当时还有一名助教虞僧诞,是会稽余姚人,“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虞僧诞“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该通义例,当世莫及”。6可见在南朝的《左传》学中,晋人杜预的《集解》,比汉代服虔的《解谊》更受人推崇。原因是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指出孔子作《春秋》有五种笔法,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这样的笔法,更合乎封建统治的需要。
陈朝的徐孝克,“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后东游,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省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7说明南朝的私学,讲授内容已不限于经史之学,还包括佛学。
家庭教育与家学传承,在儒学传家的同时,也沾染玄风的特色。儒学是士族的立家之本,对子弟的教育必须以儒学为先,如琅邪王准之,其曾祖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8吴郡盐官人顾越,“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9儒学传家对士族保持崇高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以玄学立名,也是弘扬家声的一种手段,如琅邪王氏本以儒学传家,王祥以孝闻名天下;王衍为中朝名士,唯以玄谈为务;王导善清言,为江左名相。陈郡谢氏,从谢鲲起由儒入玄,成为名士;而谢安更有“风流宰相”10之称。庐江何氏,本崇尚孝道、精通儒学,何尚之“立宅南郭外,立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风不坠。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风尚在。”11其子何偃“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时”12
六朝士族以儒学入仕,以玄谈立名,以儒家学说严格教育子女并兼传道家之言,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南朝人伏曼容,“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其子伏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13梁武帝时兼《五经》博士。伏暅子伏挺,“幼敏悟,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博学有才思,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天监初年,“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1
南朝会稽山阴人贺瑒,“晋司空贺循之玄孙也。世以儒术显。……祖道力善《三礼》,有盛名,……父损亦传家业”。2贺瑒继承家学,“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数百,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贺瑒子贺革,“年二十,始辍耒就父受业”,“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3贺瑒的侄子贺琛,“幼孤,伯父瑒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尤精《三礼》……瑒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4可见贺氏家传儒学对子女的影响是如何深厚,其在乡里所办私学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六朝时期教育格局的多样化,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儒、玄、史、文“四学并建”,有利于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学,在吸收玄学、佛学及各种文化的精华后得到了更新。南学与北学分立,并逐步形成“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5的不同趋势。
陈朝至德元年(583),吴人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他善言玄理,推重南学。陆德明由陈入隋入唐,南学传入北方。《经典释文》三十卷,采辑汉魏南北朝诸家读音诂训及文字异同,考证详尽。第一卷为序录,余为《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老》《庄》《尔雅》。书中列《老子》《庄子》为经典,而不列《孟子》,反映了六朝时期竞尚《老》《庄》的时代特色。《孟子》在当时还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唐朝贞观年间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北朝时期在长江流域重建的玄化的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The Changing and Renovation on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Wei Jin NanBei Dynasty
Zhang Cheng Zong
(Shuzhou University Social College, Jiangshu,Shuzhou)
Abstract:Pi xisui told in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Weijin is a degrading time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Nan Bei Dynasty is a divided time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which can not stand the whole survey of this study.The end of Donghan represented and embodied the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time changing study. During San Guo period,the study spreaded in the north, which appears the new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ei jing study continued to spread in the north. And it developed in the changing study. !6th countries in the north ,the rulers of various minority groups“Changing Yi to Xia”,it decreas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u and Hans cultures. Zhongyuan Confucianism became to exist inspite of war and other reasons. 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women joined the groups of Confucian study and tranditional keeping. It is traditional way of two Hans,focusing on the envidence,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reation.Dong Jin Nan Dynasty paid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The simple way improved the spreading and interac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The various educational styles improved the metaphysical school of Confucianism.So called “Nan school simple,getting its key point,Bei school has deep studying even to its tiny parts. ”It appears the differences tendency of Nan and Bei schooling. Ludemings Excellent Explanation of the studyspreaded from Chen to Shui and then to Tang Dynasty. It spreads from the sourth to the north. Yan shigu,Gongyingda gave Wujing Justicesaccording to Nan school,which at last became the main stream of the study of confuian.And it also became the main curr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Weijing Nan Bei Dynasty,the study of Confucian,changing,renovation
1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页。
2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页。
3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5页。
4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0页。
5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页。
6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页。
1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3页。
2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页。
3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5页。
4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8页。
5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7页。
6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2页。
7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页。
8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21页。
1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2页。
2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4页。
3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84页。
4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84页。
8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65页。
6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66页。
7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57页。
8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2~1023页。9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5页。
10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63页。
11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67页。
1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66页。
2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72页。
3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0页。
4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1页。
5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2页。
6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12页。
7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6~1027页。
8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1页。
9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50页。
10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48页。
11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19页。
2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47页。
3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31页。
4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2页。
5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1~1322页。
6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8~1329页。
7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0页。
8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1页。
9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03页。
1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1~422页。
2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2页。
3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21页。
4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18页。
5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7页。
6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96页。
7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00页。
8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4页。
1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9页。
2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0页。
3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51页。
4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6页。
5 阮元《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57页。
6 阮元《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81页。
7 阮元《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17页。
8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5页。
1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9页。
2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页。
3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5页。
4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06页。
5 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87页。
6 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7页。
7 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92页。
8 鲁迅《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92页。
9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98页。
10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0页。
11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2页。
1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74页。
2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6页。
3 同上。
4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56页。
5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54页。
6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53页。
7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52页。
8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57页。
9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88页。
10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20页。
1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6页。
2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88页。
3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21~2522页。
4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0页。
5 同上。
6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59页。
7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1页。
8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5页。
9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4页。
10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2页。
11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8页。
12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7页。
1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2页。
2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页。
3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1页。
4 李百药《北齐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3页。
5 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06页。
6 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24~625页。
7 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4页。
8 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13页。
9 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06页。
1 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09页。
2 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1页。
3 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4页。
4 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5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36页。
6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4页。
7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9页。
8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67页。
9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页。
10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0页。
11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1页。
12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7页。
1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0页。
2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2页。
3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3页。
4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0页。
5 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9页。
6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120页。
7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0页。
8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1页。
9 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1页。
10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7页。
11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5页。
1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35页。
2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8~1889页。
3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0页。
4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页。
5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3~2294页。
6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15页。
7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36页。
8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98页。
9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79页。
10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4页。
11 朱铭盘《南朝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82~183页。
1 李延寿《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30页。
2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9页。
3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9页。
4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7页。
5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3页。
6 李延寿《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39页。
7 姚思廉《陈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37页。
8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23~1624页。
9 姚思廉《陈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45页。
10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36页。
11 李延寿《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82页。
12 李延寿《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86页。
13 李延寿《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31页。
1李延寿《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33页。
2李延寿《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07页。
3李延寿《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08页。
4李延寿《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09页。
5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