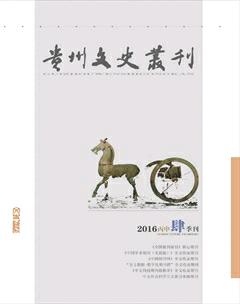论阳明心学与散文载道传统的进境
常威
摘 要:明中叶后,华而无实的文风渐滋日盛,以故时人每有文佞之议。在这样的情形下,同样以复兴儒道为职志的阳明心学承担起救弊之责,而阳明心学“心即理”主张下的“正心”所倡言的“师古人之心”的具体内涵也本质上暗合了散文载道传统。因此,若推本溯源的话,“师古人之心”比师古人之文无疑在学道的取资上更加勘进一步。而其对“文以载道”的影响自然不再像前代那样单纯地附道于文,实际上更要求道熔铸于心而自然流露。这样,具道于心而自然发抒之文,不论诉诸于何种内容,以何种形式表现,则文章必然充溢着道的气息而“莫非道之用也”。
关键词:阳明心学 散文 文以载道 复兴儒道 师古人之心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4-23-31
自儒学定于一尊之后,文章载道传统亦随之而兴。古文自不待言,即使两汉铺采摛文的赋体创作亦不免打着劝百讽一的旗号。此后,一旦形式主义文风占据文坛的主流地位之后,文以载道的大纛就顺理成章地被高自标榜,成为反驳形式文风的有利锐器。时至明代,程朱理学定于一尊,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独一无二的言说话语,那么一般而言,在此情况下,文以载道可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沃土基壤。不过究其实,或未尽然。因此,在阳明心学熠熠生辉之际,阳明心学与文以载道的关系有必要加以寻绎。
一、文佞论的提出与明代“文以载道”观的审视与批判
有明之际,寻绎文章与载道关系者颇多,综核其言,其要无怪乎在于揭示唐虞三代,“人未有以文名者,六经所作文也,”1莫非中于道,而王慎中的解读更为具体,其曰:“极盛之世,学术明于人人,风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于其间。自铭器、赋物、聘好、赠处、答问、辩说之所撰述,与夫陈谟、矢训、作命、敷诰施于君臣政事之际,自闺咏、巷谣、托兴、虫鸟、极命、草木之诗,与夫作为雅颂奏之郊庙、朝廷、荐告、盛美、讽谕、鉴戒以为右神明、动民物之用,其小大虽殊,其本于学术而足以发挥乎道徳,其意未尝异也。”2屠隆的论述则更加注重考镜文道关系的源流,将文道关系的递嬗表述的更为清晰,其曰:“黄虞以后,周孔之前,文与道合为一。秦汉而下,文与道分为二。六经理道既深,文辞亦伟。秦汉六朝工于文而道则舛戾,宋儒合乎道而文则浅庸,我朝道学知宗宋儒而践履多疏。”3这里屠氏述及文道离合关系甚详,撮其旨要,盖谓周孔之前,无非六经之文,故而文道合一。而秦汉而下,六经之外,词章繁兴,是以文与道遂趋向于离分。萧纲所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1者,庶几可作为词章兴起后文道分离倾向的反映。而三代以还,文士多以才胜,非以理胜,是故“文与道离,行与言戾,而行道有得之文,盖亦有之,”2但实难多见。自韩柳以来,复倡道统,文以载道便成为高歌猛进的散文发展历程的主旋律,至宋为极,是以李春芳曰:“夫道在人心,弗言弗彰。古今正言者,即人人殊,要以明道而已。自孔孟既没,微言遂绝。迨汉晋诸儒,溺意词章,言愈繁而道愈离。有宋嗣兴,濂洛辈出,周云纯心,程云定性,其旨归于揭斯道之真诠,觉斯民之朦膭,非有二也。”3虽然宋儒间有文以害道之论,但是多在具体语境中就具体事实言之,并非蔚然风行之说。有明之后,亦有“道学之谈者,曰必去而文,然后可以入道”之语(参见《明文衡》序),然而多非公允持正之论,业已为时人所驳,诚如程敏政所云:“夫文,载道之器也。惟作者有精粗,故论道有纯驳。使于其精纯者取之,粗驳者去之,则文固不害于道矣。而必以焚楮绝笔为道,岂非恶稗而并剪其禾,恶莠而并揠其苗者哉。”4因此,尽管间或有学人对文以载道略有微词,然而文道合一在更大范围内成为时人文章写作期冀达到的理想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宋及明初因理学兴起,虽然重视理道,不过文反而多流于华而无实的境地。是以薛甲曰:“古之作者,皆非有意为文,盖事之所触,意之所感,而理自形,非如后世摹拟篆刻之文也,故能信今传后。若韩欧之文,非不脍炙人口,然细玩之,则意味终浅。”5尽管唐宋以后对儒道的重视日益加强,但是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兼之伪道学的层出不穷,文、道、人分离的情形大有每况愈下之势,故而唐顺之曰:“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6唐氏此语无疑道出了自程朱以来儒学强化之后文、道、人关系的紧张对立,是以文道虽然满纸炫然,但是却鲜有真道,亦鲜有真人,是故黄侃曰:“韩退之满口仁义,而受人谀墓之金;方望溪貌为道德,居母丧见妻子而动心。故因为论人,不可语于唐宋以后。”7究其因,从根本上来说,程朱理学对“天下莫尊于理”的强调容易造成文、道、人的隔礙。申而言之,盖若理先于心,那么理、心难免歧分为二,因此,外在之理与内在之心便有了随时抵牾的可能。那么反映在文学上,道、文、人自然由于理、心的冲突而趋向于崩离。荒木见悟云:“对于理学来说,为了给予心的无约束活动以一定基准,强调了理(天理)的先验性权威。从而在那里,心本身的机能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管是心学还是理学,心作为一身之主宰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被心学所赋予无条件信赖之心与理学的由理控制之心有着明显差异。”8因此,基于程朱理学强调理对心的绝对控制,而不是像心学那样注重于理与心的统一,那么一旦内心被物欲充塞就会滋长背离理道的趋向。事实上,这种物欲影响下的真我丧失以及理道之背离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或如钱穆所云:“这世界中,到处见有一个个的人,其实都是以外形肉体为主,在其生活中,却觅不到一个真吾。……作为我之真吾之心,实际上早堕落而为奴,为物质生活之奴。更可悲的,连此奴之存在这一层,也已为人们所遗忘。人之生活,都只见了物质,却不见有心。”9诚然,真吾之心即不存,道将焉附,因而心、理不一致情形的产生便不足为怪了,而道、文、人的离析亦可以从中想见。万历进士张恒便指出了时人为文华实不符的弊病,而有文佞之论。其曰:
易传曰:有华无实,佞人也。有实无华,道人也。……近世以古诗文名家,若秉华轮策。……近代之人几越之矣。第读其文而究其意,失之诡而遏焉者,或亦不少。……茕古人之精华以自藻饰,而又以其藻饰为声利之筌。竭夙夜之心思以谐世纳交而又以其谐世纳交之词为千秋擅场之金距。……惟意之雕琢,则燕石为珪璋。惟口所吹嘘,则枯荑为兰芷。文愈多而质愈漓,言愈工而道愈远。……文溺心,华胜实,酬应夺志,此近世文人之通患也。1
这是有关近世学人文章有华无实的评述,“通患”之谓表明其并非一时之现象,而诚一世之风气。张氏谓之“文佞”,盖谓时人为文重形式而轻内涵,故而有“读其文而究其意,失之诡而遏”之失,而此类作者所瞩目者,不在于道与质,而在于酬应、名利而已,其所专擅者,亦不过雕琢而已,吹嘘而已,加之殚精竭虑,以诗文为追逐声利之筌。因此,文章华实不符之病渐滋日盛,乃至于“文愈多而质愈漓,言愈工而道愈远”。平心而论,文章形式上之“文”与“质”并不必然与道相合或相离,虽然自唐宋之后,文质常常与道联系在一起,文“文”则往往饱受诟病。但是应当指出,有“文”之文亦能载道而施之于用,如刘熙载评骘屈辞曰:“‘文丽用寡,扬雄以之称相如,然不可以称屈原。盖屈之辞能使读者兴起尽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2只是若过分地注重于“文”乃至于无实,则载道不免有失,是以王樵曰:“窃谓今日文固盛,然文盛而不已,则实将不继,实苟不继,则文日工而道日漓,非所谓文也。窃谓莫若救之以质,质者非谓不文也,惇本尚实之谓也。”3而张恒“文佞”之论盖本于此。
因此,如何使文、道乃至与人不再有割裂失实之感,主动地融渗儒道但已为罪魁的程朱理学显然难以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而前七子复古又自固于古人文章法度,字雕句琢,自然有损于文道的抒发而至于文与身心绝不相类。诚如彭黯所在评价刘玉时所指出的那样,“先生(案:指刘玉)之文章如先生之政事与其仪貌也。先生其不可及也已矣。嗟乎,世之号称文章家者,不过于一句一字较体裁求形似耳,其与心身绝不相类。”4至此,在明代文章与身心绝不相类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同样以儒道践履为职志的阳明心学或许能够担荷文、道、人浑融为一的重任,而其“师古人之心”的思想旨归则是其有效途辙。可以说,作为阳明心学本体论的“心即理”提高了主体心性的地位而使得心、理融汇为一。这样一来,只要心体复归于正,则终极追求的理自然不期而至。而王阳明取资古人之心的做法实际上要求的是以古人之心为己心(这里的古人显然称指的是古之圣人),以求得古人的真精神,而古人之心与精神无不是与道浑融为一的。换言之,在阳明看来,圣人之心即是“理”,因此,取法古圣人之心,求得古圣人之精神,自然在古人之心与己心相契中最终使得己心与理统一起来。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阳明心学既然以复兴儒道为初心,并且在师古人之心中找到了达成“心即理”的有效途径,那么其对于文学与道、人关系的影响,自然一方面使文道合一成为践行方向,另一方面其注重主体道德蓄养的反身归诚之论更易使其落到实处而不至于有文、道、人悖离之患。
二、殊途同归:阳明心学复兴儒道的终极诉求
这里略带提及的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虽然在本体论及修养功夫论上存在分歧5,兼之阳明心学肯定自然情欲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明显差异,以致国内外的学者每有阳明心学是程朱理学的反动之论,例如,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曰:“朱熹一派的儒家思想支配了元明清三代,他支配的力量在他后来枯僵的状态里并没有消谢。但是在明代中叶,对于这儒家的正统起了一种反动,也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新生机:这反动是王阳明和他的学派。”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于儒道复兴而言,二者盖殊途而同归。虽然阳明心学注重主体心性的建构带来的精神解放看似要与注重道统的程朱理学划出界限,其实殊不其然。应该说,在践履儒道的路向上,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并无二致,只是在实现途径上有所差异而已。对此,施邦曜阐述曰:
先生之学,因讥议与朱子有异,遂开人疑信之端,愚以为实无异同也。二先生之言虽殊,卫道觉世之心则一。……晦庵当五季之后,虚无寂灭之教,盈于天下,患在不知穷理也。故宗程氏之学,揭主敬穷理之教,使人知所持循。文成当晦庵之后,词章训诂之习,没溺人心,患在徒事见闻也。故明陆氏之学,揭知行合一之旨,使人知所返本。……非文成知内而不知外也,晦庵知外而不知内也,尚安得有异同哉?2
可见施氏所论瞩目于阳明与朱子之学卫道觉世之大本而倡言其实无异同,而就其兴起之由,各就前世之弊,故其理论主张不能不略有差异,但是不过内外之别罢了,二者实非根本抵牾。万斯大亦曰:“有明一代儒者,后先踵起,或尚躬行,或崇解悟,皆因时为救,故其发明圣道,排黜佛老,其功直与宋儒等。”3而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引述朱子之言以自证其晚年倾向于心学,虽然阳明本意出于维护自身主张的需要,但是亦未尝不是向程朱理学的依归,其对朱子之学,曾言“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4,从中可略见阳明本不欲背离朱子,而之所以有所抵牾者,因笃守道之所在,不得已而为之,是阳明诚不愿以小人文过之心事朱子之反映也。盖学以求道,二者所共趋,而其之差异,惟在取道“直”与“不直”之别,是故亦可窥二者在精神血脉上的关联。即以为学而论,阳明心学提倡由心体认以自得,而程朱为学治经又何尝不是以其心得之。是以明经学家王樵曰:“宋程二子以其心得说经,朱子承之而道学大明于宋世,非以其说也,以其心得之也,夫何门人末流推衍不已,此则门人之失欤。”5观王氏之论,盖谓程朱之学皆由心体认,所谓“其心得之”,至于其后推衍不已,则是其门人之失,非程朱之过。由此而言,二者的差异可谓微乎其微,是故胡泉曰:“以阳明之学准诸朱子,确有依凭。盖阳明讲学,删不尽格物传义在外,而朱子注经,包得尽良知宗旨在内。惟朱子精微之语,自阳明体察之以成其良知之学;惟朱子广博之语,自阳明会通之以归于致良知之效。”6钱穆则认为“讲理学最忌的是搬弄几个性理上的字面,作训诂条理的功夫,却全不得其人精神之所在”(《王守仁》序),从而将心学归于理学,其曰:
宋明六百年理学,大体说来,宋代是创始,而明代则是结束。王守仁尤其是明代学者里的重镇。到他手里,理学才达顶点,以后便渐渐地衰落了。7
李泽厚亦有相似的论述,只是与钱穆不同的是,其认为阳明心学不是理学的顶点,而是理学的末端。其曰:“王阳明是继张载、朱熹之后的宋明理学的关键人物。张载立(理学),朱熹集大成,王使之瓦解。……如果说,张的哲学中心范畴(气)标志着由宇宙论转向伦理学的逻辑程序和理学起始,朱的中心范畴(理)标志着这个理学体系的成熟和精巧构造,那么王的中心范畴(心)则是潜藏着某种近代趋向的理学末端。”1
综上可见,阳明心学与理学尽管有所差异,但是血脉相连,可谓理学发展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诚如孙毓修所说:“阳明之学出于陆氏,与朱子异道而同归。乃反对之者,辄斥之为异端,目之为空谈,朱王之间,成为水火。盖两家门户之见,非定论也。”2诚如其论,阳明与朱子异辙而同归于儒道殆无可疑,吕思勉所谓“(理学)诸家之说,各有不同,非好为异也。补偏救弊,立言固各以其时;殊途同归,辙迹原无须强合”3者。即以推崇本色的唐宋派而论,其本色说看似有背道的倾向,但实际上也体现出了重视儒道的色彩,这恰好表明深受心学濡染的唐宋派在价值取向上与程朱理学并无二致。所以左东岭曰:“荆川的本色说实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必须有自我的特性,二是在本色之中又有高低之别。这意味着他可以承认其他各家各皆有其见解,亦即各有其本色,但他不可能承认其本色与儒家具有同等的位置。因此荆川的本色严格说来仍停留在道德论的层面而未进入审美论的境界。”4即便对于素来被谓为异端左道的阳明学派的极端人物李贽来说,顾炎武所谓“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背圣人”5者,尽管其受到儒佛道思想的三重浸淫,但是若究其实,其思想的主流依然归于儒道,故李贽自言:“夫卓吾子落发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6由上皆可见然阳明及其后学在绍继儒道上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之处,尽管如此,但是亦应看到后来阳明心学“及其末流,许多人滥唱高调,自欺欺人,而行检之间,反荡然无忌惮。晚明政治混浊,满人入关,从风而靡,皆由于此”7,于是顾炎武倡“行己有耻”以救之。然则心学余波沉沦至此,所谓“其以良知本来无可修证,才欲修证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悬空守寂,截然不着事物工夫;其一以知即是行,一切应迹皆可放过,其弊使人见这光景,自以为是,不复修行,干没于伪欲而不自以为非,是看格物为不要紧工夫”8之弊,是阳明所始料未及的,也断非阳明心学本意。陆树声曰:“阳明致良知之说,病世儒为程朱之学者支离语言,故直截指出本体。而传其说者往往详于讲良知,而于致处则略坐入虚谈名理界中。如禅家以无言遣言,正欲扫除前人窠臼,而后来学人复向无言中作窠臼也。”9诚如其论,阳明心学虽讲良知,但于“致”尤其侧重,自然非后来重良知而略于致者可同日而语。易言之,“阳明之学,以致良知三字为宗旨,而以事上磨炼为入学之门。学者苟循序着实用功,庶几可入其门而进窥其堂奥。如徒事口耳讲说,而欲明阳明之学,是所谓南辕而北其辙也。” 10
综上可知,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虽辙迹殊分,但本归实一,且二者后学皆有其无可讳言之弊,是故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有异同则可,但实不可言其优劣。平心而言,或如王源所论:“论其所见之偏,不能无过不及,而论其得则皆圣人之一体,乌得是此非彼,立门户于其间,若水火之不可以并立者。且夫对君父而无惭,置其身于货利之场,死生祸福之际,而不乱其内行,质之幽独而不愧,播其文章议论于天下,而人人信其无欺,则其立说,程朱可也,陆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陆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则尊程朱即程朱之贼,尊陆王即陆王之贼,伪耳。”1
三、“师古人之心”与散文载道传统的进境
可以说,有明一代,复古运动渐滋日盛而俨然成为一种风尚。而从文学形式与内容的角度而言,此期学人的学古又可大致分为“师古人之文(词章)”与“师古人之心”两途。而就“文以载道”而言,台阁体古文雍容典雅、善于颂扬,因此易受意识形态影响,难免造成文道失真,而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取貌遗神倾向业已将道、文歧分为二,故薛应旂曰:“(李梦阳)一涉于六经诸儒之言,辄斥为头巾酸馅,目不一瞬也。……而六经诸儒之言,则文之至者。舍六经诸儒不学,而唯学马迁、班固文,类《史》、《汉》亦末技焉耳,何关于理道,何益于政教哉!”2因此,散文载道传统的复归未能在前后七子身上得以实现,从而不得不另辟蹊径,而阳明心学“师古人之心”的提出恰逢其时。需要说明的是,自觉而普遍的“师古人之心”显然是受到横空出世的心学濡染后的产物。(虽然韩愈《答刘正夫书》有“师意”的表述,但毕竟没有更近一步,而明前期如宋濂等人虽有“师心”的论述,但是应该看到,其还未流衍为一时的风尚。)而这一倾向不仅使散文载道传统得以复归,而且在更大意义上使得散文的载道不再似前代那样外显为儒道强行介入后“道”、“文”乃至与人(创作主体)的割裂分离,而实呈现出一种道、文、人浑融合一的自然面貌。诚如孙奇逢所云:“理学,节义,事功,文章,总是一椿事,其人为理学之人,遇事必能殉节,当事必能建功,操笔必能成章,触而应,迫而起,安有所谓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学,则节义亦属气魄,事功未免杂霸,文章只成空谈。”3观孙氏所论,可见其对理学(这里指阳明心学)本根的强调,只要人为理学之人,则理学、节义、事功、文章自然能够兼而有之,依此,则道、文、人亦自然契合无间而可以融贯为一。
“师古人之心”的思想倾向在王阳明的论说中多有呈现。如《答顾东桥书》曰:“‘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4又,《远俗亭记》曰:“是故诵其诗,读其书,求古圣贤之心,以蓄其德而达诸用,则不远于举业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学,是远俗也已。”5以上可见王阳明对“求古圣贤之心”的强调,而在心即理的理论旗帜下,“好古敏求”也被赋予更为具体与确切的内涵,所谓“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除此之外,在涉及个人的评价时,王阳明也时常以“求古人之意”作为评判的标准,如《重修浙江贡院记》曰:“若诸君者,诚可谓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后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6当然,作为与“师古人之心”相为表里的一个表达,“师古人之意或精神”(“师意”之论,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已有论述,但是其理论内涵尚停留于学道的宽泛称指,而阳明及其后学因其有心学理论的支撑而显然指出了如何学道的向上一路)在此期学人的论述中也多被提及。例如,王慎中有“当其覃精于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载之远,若古人之在而与之为酬酢客之”(《聚乐堂记》)、“居今时而有尚友千载之心”(《陈沅潮小像赞》)以及“祖述其精神,血脉贯通联属,若传气界质而生”(《赠别董容山先生序》)的论说7。而袁宗道亦倡言发古人之精神,其《刻文章辨体序》曰:“兹集所编,言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堙灭之精神在,岂徒具体者。后之人有能绍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体,而务自发其精神,勿离勿合,亦近亦远,庶几哉深于文体,而亦雅不悖辑者
本旨,是在来者矣,是在来者矣!”1而在具体的文章写作中,袁宗道亦认为应该学古人之意,而不必拘泥于古人字句2。此外,钟惺《隐秀轩集自序》亦曰:“务求古人精神所在……近时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拟之古,皆与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之精神别有在焉。”3 综上可知,此期诸多学人显然已经窥见文坛拟古不化的流弊,而至于文与行歧分为二,交相背离。要其因由,盖时人徒钩棘修饰文辞,而不务修本实,故而辞藻虽工,然忠信渐薄。诚如傅镇所曰:“今学士大夫相与谈艺文之事,准汉则唐,所谓美也,舍是则无所庸其好。已学者逐时好,刻意错比其文,乃荒纰其德,视其行,往往与文畔,不可信如此者岂少哉!余甚惑焉,岂文与行固二也。孔子之论文也,谓文莫犹人而以躬行,君子为未得夫文言之华而行其实也。本实不存,枝华焉丽,是故辞藻之工,忠信之薄。”4屠隆亦表达了对文行不一的深深忧虑,其曰:“文人言语妙天下,谈天人、析性命、陈功德、称古今,布诸通都,悬于日月,亦既洋洋洒洒矣。苟按之身心,毫不相涉。言高于青天,行卑于黄泉,此与能言之鹦鹉何异?务华绝根,则无为贵文章矣。”5因此,随着词章之繁兴所带来的“务华绝根”之趋向,兼之理学背景下文人无行的突显,明人不得不另寻文、道、人契合无间的出路,而阳明学旨归返本以求诸心性的探本思识,庶几是解决难题的肯綮所在。可以说,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之下,注重于词章句法的复古倾向得以纠正,复古人之心的价值导向几成共识,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绾文以载道转移之纽者。虽然唐宋诸儒已倡言文以载道,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主体道德的重视,因此不乏代圣人立言的真儒家,但是这毕竟取决于个人的修养努力为多,是一种偶然而非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外在于心的道与人、文的分离为更多假道学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是以方东美曰:
有很多宋儒,‘经是废经不读,‘子是废子不读,虽号称代圣人立言,也只是根据他肤浅的体验,来装点门面,冒充圣贤而空说大话。像这类宋儒的话,不仅不是‘有德之言,而是‘缺德之言、‘废学之言。在《宋史·道学传》里,此类人比比皆是。6
尤在科举取士后,虽然士子学人称述六经,援引先王,从表面看来,似乎与古人古道合若符契,但究其实,则甚似而已,而其实则非,是故王慎中曰:“今称述必在乎经,援引必则古先王,如书生科举之文者,岂不为正,而岂可以为文,而亦岂可以谓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实非,有太反而正合,非独文然,凡人之事业功行皆若此矣。”7诚然,学法为易,载道为难,故包世臣曰:“文之盛者,言有物。文之能者,言有序。无序而勉为有序之言,其既也可以至有序。无物而貌为有物之言,其弊有不可胜言者。”8而古人言道者“附于事而统于礼”,是以“子思叹圣道之大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至于后来“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而“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9诚然,韩柳古文运动有“虚言道以张其军”的倾向,而有宋一代亦多“门面言道之语”。换言之,在程朱理学向外索求的功夫论下,其实更大程度上“作者的心灵与道德规范,事实上是隔断而为二,写作的动机,并非出于道德心灵的感发,而只从文字上把道德规范套用上去,甚至是伪装上去,此时的道德便成为生硬的教条”1。在这样的情形下,阳明心学因注重主体道德的建构而透显的“文”与“道”的合一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决难题的方案。具而言之,“心”与“道”的浑融在极大程度上消解了道与文的二元对立,因为“由道德而来的仁心与勇气,加深扩大了感发的对象与动机,能见人所不能见,感人所不能感,言人所不敢言,这便只有提高、开拓文学作品的素质与疆域,有何束缚可言?”2因此,应该说,阳明心学所秉持的“复古人之心”真正将文学的载道品质内化于心,而非在文学创作上强加上道德的说教,这显然比简单地“复古人之道”来得更为彻底和纯粹。袁宏道《叙竹林集》曰:“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3斯言诚是。这样,儒道看似被古人之心所取代,然而由于其先验地存在于每个个体的心中,所以“师古人之心”不仅不会带来儒道的沦丧,反而使其有了更为自由和广阔的舒展天地。徐阶曰:
古昔圣人具是道于心而以时出之,或为文章,或为勋业。至其所谓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国,或形诸家庭,或见诸师弟子之问答,与其日用应酬之常,虽制以事殊,语因人异,然莫非道之用也。4
王慎中亦曰:
知者观之,固知其为道德之言而亦有道德之能言者也。诚有德矣,亦何事于言,未有有德而不能言者。近世乃有诡于知道而不能为文,顾谓不足为也。其弊将使道与文为二物,亦可患也。5
观二人所论,前者重在强调古圣人具道于心,故而其为文章自然能够为道之用;后者旨在一方面表明文、道不可偏废,另一方面则又强调了道德对能言的重要价值。诚然,圣人是具道于心而发而为文的,而“未有有德而不能言者”。因此,若推本溯源的话,师古人之心比师古人之文无疑在学道的取资上更加勘进一步。而其对“文以载道”的影响自然不再像前代那样单纯地附道于文,实际上则要求道熔铸于心而自然流露。这样,具道于心而自然发抒之文,不论诉诸于何种内容,以何种形式表现,则文章必然充溢着道的气息而“莫非道之用也”。刘熙载曰:“扬子云说道理,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求。然从来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气尽力竭耶!”6诚然,文自然流出者,道才能淋漓尽致地得以表达,而若有意附道于文,即便气尽力竭,道不免依然滞碍难以寻求。因此,师古人之心对“文以载道”的影响,一方面在使道蓄存充塞于心性之中的同时,另一方面师心的直觉内涵又使得其能够得以自然发抒。兼之阳明“师古人之心”植根于其“知行合一”的理论中,因此自然确保其不流于形式。
当然,这仅是就理论上而言,若究其实,或未尽如人意,诸如阳明后学袁宏道等人执着于“良知”一端而宣扬主体自适,而不务阳明“致”之精义,以致追求快意自适人生,而反映于文学,则要求快意于语言文字,这又难免造成文以载道的陨落。是以孙奇逢曰:“大凡语言文字到极快意时,便有背道伤教之弊。”7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心学派师古人之心(精神)理论虽高,且无七子派拘于法度之弊,但是很多情况下又难免因法度的缺失乃至于过于漫衍无的,因此或最终流于空虚,而对于这一情况的扭转,或至于秉持以音节体悟古人之精神主张的桐城派那里,方才提供一种较为圆融的方案。是以郭绍虞曰:“盖后世文人既以古文相号召,则势不能不取则于古作。然而取则古作,学其字句则嫌太似,学其法度又怕太拘,若欲学其精神则理论虽高,奈苦无下手之处。论文到此,真入穷途。所以桐城文人在音节字句上以体会古人之神气,则学古有途径可循;同时再在音节字句以体验已作之是否合古,于是作文也有方法可说。”1尽管如此,虽然师古人之心亦有弊端,这并不能否定心学派诸人对文以载道的实现所做出的努力。
综上所述,明中叶后,文风渐趋华而无实,以致时人每有文佞之议。在此情形下,同样以复兴儒道为职志的阳明心学面对程朱理学的没落不得不承担起救弊之责,而阳明心学“心即理”主张下的“正心”所倡言的“师古人之心”的具体内涵也本质上暗合了散文载道传统。因此,若推本溯源的话,“师古人之心”比“师古人之文”无疑在学道的取资上更加勘进一步,而其对“文以载道”的影响自然不再像前代那样单纯地附道于文,实际上更要求道熔铸于心而自然流露。这样,具道于心而自然发抒之文,不论诉诸于何种内容,以何种形式表现,则文章必然充溢着道的气息而“莫非道之用也”。
The relations between Wang Yang-mings Aesthetics of Xinxue with moral deeds carried by articles
Chang W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the articles appeared to be superficial,so people often had a comment called“WenNing”.In such circumstances,Wang Yang-mings Aesthetics of Xinxue deserved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to save the disadvantages as its duties. And Wang Yang-mings Aesthetics of Xinxue guided by the idea“heart is the universe”Advocated the concrete connotation of“Learning from Heart of the ancients”,which was essentially consistent with moral carried by articles.
Keywords: Wang Yang-mings Aesthetics,moral carried by articles,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Learning from Heart of the ancients
1黄楷《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二《重刻甘泉先生文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十六册,第512页。
2 王慎中《遵岩集》卷九《曾南丰文粹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二百七十四册,第191页。
3屠隆《鸿苞四十八卷》卷十七《文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九册,第231页。
1 萧纲《梁简文帝集》《戒当阳公大心书》,扫叶山房发行重校精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2 马理《方山薛先生全集》《方山先生文录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三百四十三册,第1页。
3 李春芳《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二《甘泉湛先生文集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十六册,第516页。
4 程敏政编《明文衡》《明文衡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页。
5 薛甲《畏斎薛先生艺文类稿》卷二《与何吉阳太仆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三百四十册,第104页。
6 唐顺之《荆川集》卷四《与茅鹿门知事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千二百七十六册,第274页。
7 转引自段凌辰《中国文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8 荒木见悟《心学与理学》,复旦学报,1998年第五期。
9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59页。
1 张恒《明文海》《文佞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49页。
2 刘熙载撰、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文概》,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9页。
3 王樵《方麓集》卷四《送胡学训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二百八十五册,第184~185页。
4 彭黯《执斋先生文集》《执斋先生文集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三百三十四册,第269页。
5 对于心学与理学之差异,可详参冯友兰《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清华学报,1933年年第八卷第一期。
1 转引自冯君培《评福兰阁教授的李贽研究》,图书季刊,1940年第二卷第一期。
2 王阳明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3~144页。
3 万斯大《明儒言行录》《明儒言行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四百五十八册,第594页。
4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5 王樵《方麓集》卷三《今述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二百八十五册,第168页。
6 胡泉《王阳明全集》《王阳明先生书疏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4页。
7 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第一页。
1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
2 孙毓修《王阳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页。
3 吕思勉《理学纲要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 左东岭《明代文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5页。
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0页。
6 李贽《李温陵集》卷十《初谭集又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一百二十六册,第289页。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8 王畿引吴悟宅语,参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之十《答吴悟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九十八册,第438页。
9 陆树声《陆学士杂著十种》《清暑笔记》,吴门马凌云刻本。
10 王禹卿编著《王阳明之生平及其学说》,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80页。
1 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朱字绿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四百一十八册,第153页。
2 薛应旂《明文海》《遵岩文粹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82页。
3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8页。
4 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5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3页。
6 同上,第904页。
7 以上分别参引王慎中《遵岩集》卷八、卷二十、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二百七十四册,第148页、503页、269页。
1 袁宗道撰《白苏斋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2 袁宗道《论文》曰:“今之圆领方袍,所以学古人之缀叶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学古人之茹毛饮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饱口腹、蔽形体,今人之意,亦期于饱口腹、蔽形体,未尝异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肴核之内也。大抵古人之文专期于达,而今人之文专期于不达。以不达学达,是可谓学古者乎?”(袁宗道撰,白苏斋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3 钟惺《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4 傅镇《执斋先生文集》《执斋先生文集叙》,《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三百三十四册,第271~272页。
5 屠隆《鸿苞四十八卷》卷十七《文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九册,第231页。
6 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页。
7 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三《与项欧东》,《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二百七十四册,第542页。
8 包世臣《艺舟双楫》《雩都宋月台古文钞序》,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51页。
9 以上参引包世臣《艺舟双楫》《与杨季子论文书》,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8~9页。
1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篇》,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2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3 袁宏道《袁中郎文钞》,世界书局1935年初版,第9页。
4 徐阶《王阳明全集》《王文成公全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5页。
5 王慎中《遵岩集》卷九《薛文清公全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千二百七十四册,第193页。6 刘熙载撰、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文概》,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7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