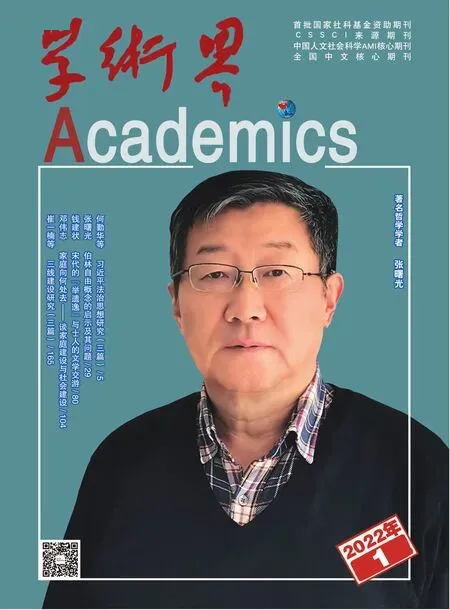反思与群己之辨〔*〕
沈顺福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人的生存通常有三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作为生物体的自然性,第二个向度是群居生物的社会性或道德性,第三个向度便是理性存在者的个体性。作为自然生物的人,自然生存是第一使命。生物者不仅自然生存,而且必然生存,否则便一无所有。由于这是一个自明且自足的主题,因此,我们通常不需要过多地讨论此话题。于是,人的生存便只剩下社会和个体两个向度,人也因此至少具备上述两种身份,即人不仅是一名社会成员,而且还是一个独立个体。那么,个体人与群体社会之间如何相处呢?这便是卢梭提出的问题:个人意愿与公共意志如何协调而统一?传统思想家如卢梭、费希特、黑格尔等通常将群体实体化,从而形成一个公共意志。为了协调二者的关系,他们通常厚此薄彼,强调个人意志服从或从属于公共意志,从而实现了所谓的“统一”。如费希特将普遍的“公共目的”〔1〕当作个人的目的,认为“我应该遵循那个设想的普遍意志而行为”。〔2〕个人意志消失于普遍意志中。准确地说,“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什么,因为全部人的意志想的是一样的。”〔3〕这样,在个人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张力中,费希特等选择了公共意志,即以公共意志为个人意志的内容或标准。
个人与群体关系理论,中国人称之为群己之辨。从中国传统儒家来看,它的策略也和德国古典思想家们的策略相似,即以整体或全体来代替个体,从而让个体服从于整体。这便是无我。其最高观念便是天人一体。“天与内在之心或内在之德具有隐秘的通道,以至于天人在特定个体那里合二为一,并且通过这些特定的个别人,天也成为了所有人(尽管他们并不能与天合一)的本质或决定者。”〔4〕在天人一体视域下,个人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整体之分子,我不是我,而仅仅是全体之分子。作为整体之分子,我自然或必然地服从整体。这便是牺牲自我来成全大我或整体的观念。以牺牲个人的方式来成全群体意愿的方案,虽然顾及到了全体,却忽略了个人或自我。在此种方案中,只有群而无己。这显然也不是一种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完美方案。本文将以反思为策略,试图通过反思行为来统一自由的个体与现实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以为具备反思能力的理性人的生存是个体性之自我对普遍存在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中,个体自我融入了群体,成为群体之一员。在自我的反思指导下的行为中,个体不仅因为身为群体一员而与群体保持和谐,而且因为自我的在场而实现了自由。自由个体与现实群体之间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一、意志与自主的自我
我们通常承认:人是理性存在者,常常在自己的理性指导下生存或行为。如康德说:“在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依法运行。只有理性存在者有依据法则观念行事的能力,即依据意志原理而行为。由于依据原理的行为需要理性,因此,意志正是实践理性。”〔5〕实践理性具体于人的身上便是意志。理性人总是在自己的意志指导下活动。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观性意志的主要职能是驱动人的行为或实践: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即“意志则是通过规则范畴来决定自己的因果关系的动力”。〔6〕意志是人类行为的动力,这个动力产生于对相应物体的追逐,这便是行为的目的。理性人,经过自己的理性认识和判断之后,确定一个行为目标,从而将其当作行为的最终指向,即“为了什么”。这个目标便是善的东西。我们因为某物是善的(good),因而将其转换为意志追求的对象(goods)。善良与否的标准便是人的意志,符合我们意志的东西便是善的,否则便是不善或恶的。“另一种人类专属并由此而区别于野兽的官能便是意志。借助于这种内在动力的意志,人类放弃那些最不适合于自己的、转而选择那些最喜欢的东西。”〔7〕意志是人类理性活动的判断者、主动性行为的驱动者。
作为理性行为的发动者的意志,不仅直接驱动了某种行为,而且在此行为中体现了行为者的自我自主性或个体性,即这是我的行为,体现了我的个体意志或自主性。个体意志是一个特殊整体或枢纽。作为一个整体,它可以被抽象出两个部分,即作为行为主体的意志和作为意志对象的意志。我的意志不仅包含我想、我意愿,而且包含意愿的对象或内容。因此,意志包含两项内容,即我的意愿主体与意愿内容。二者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意志。在这个整体意志中,自主的我始终在场。这种自我在场的行为表现为我意愿什么。作为行为主体的我是主体,是主观形态,行为对象或意志的内容则来源于客观。它因此形成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整体。这是自我和他者的结合体。这个客观之他在其进入我的主观意志之后便由客观存在转化为主观意志的内容,从而与原始的主观我形成一个整体。这大约便是胡塞尔所说的由“意向观念”(noesis)与“意向对象”(noema)所组成的“意向性”。〔8〕胡塞尔的意向行为近似于意志的早期活动。
行为主体与意愿内容合作而形成意志整体。其中的行为主体(我想、我意愿)又可以被继续分析,形成思辨的二重性存在,即形而上的个体性或自主性与形而下的气质我。其中形而下的气质我提供动力,表现为行为者的主动性。而形而上者便是我的个体性。所谓个体性,即这个意欲活动不仅具有主观性,而且具有个体性、是我主导的行为、体现了不同于别人的、自我的行为。我因为我的个体性而成为我。个体性具有两个特点或性质,即确定性和超越经验(transcendent)。
其一,个体性是我作为一个特殊个体的真正基础,是特殊自我的依据。这便是个体性的确定性。费希特称之为“自我”,他说,“我的个体性尽管由这些因素所决定,可是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从物质存在的角度来说,我成为我。”〔9〕我,作为一个行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具体的、特殊的自我,其根据便是个体性。个体性是特殊个体的终极性根据。费希特说:“我们在别处(即我的《自然权利》一书)已经阐明:我只能在个体中安身。这意味着:个体性意识是自我的一项条件。因此,伦理学比其他具体的哲学学科要高级,它甚至比权利学说也要高级。因此,对个体性是我的存在条件的证明必须在更高级的原理上进行。”〔10〕个体性是个体自我的根据,即个体性是具体的特殊个人的终极性依据。个体因此而成为独特的自己。故,个体性是个体存在的“基础”。〔11〕这便是个体性的确定性:个体性让个体成为特殊的个体,并因此区别于别物。我是自我。海德格尔说:“人是一个自我。”〔12〕个人一定是自我(Ich)。这个自我便是个体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我,因为它都是一个我。自我的本质建立在我的本质之上,自我在于‘我’。”〔13〕这个作为基础的“我”或个体性是具体的、特殊的自我的终极性依据。个体性让个体的人成为自我,从而将自我区别于他者。
其二,个体性是一个超越的实体。作为终极性依据的个体性不仅是最终极的,而且还是不可识别的形而上存在:终极性的个体性超越于我们的经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放弃理性的思辨,它常常隐身于我们的经验意识或意志活动中,表现为我意愿做什么。黑格尔曰:“具体个体反思自身,并由此回到普遍性。”〔14〕黑格尔将普遍性视为个体性,其实不是。在这个反思活动中,那种能够促使反思者将普遍性收回自身、成为自己的基础便是个体性。它隐身于这个反思活动中。它是一种理念性存在,是一种“可能性”。〔15〕作为可能性,我们无法在现实中直接发现它的身形,但是,我们可以从自由中发现它的踪迹或身影,因为它存身于此。个体性隐身于人的自由活动中。个体性是经验视域下的超越实体。我们只能借助于主体观念与行为并对其进行深度反思,才能发现它的存在。当我们反思自己的意愿、想法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确定而隐蔽的自我。这个自我便是个体性或曰自主性。个体在反思中觉悟到的自主性便是个体性主导的行为。没有反思便无个体性。这也是人类个体区别于自然界个体的原因之一。只有在自我反思中我们才能发现个体性。自然界的动物等并无此本领。这些自然动物可以是具体的个体,却没有自我,也没有反思能力,找不到自己的个体性。个体性是理性人通过反思而呈现的超验实体。
二、从个体到成员
自我也是个体。既然是个体,自我便一定从属于某个群体或种类即属。因此,自由个体的行为不仅产生于个体自我,体现了自我的主观性和个体性,而且与维护群体秩序的规则如伦理等密不可分。从自我观念的确立,到自我行为的确定,我不仅是自主的个体,而且依赖于群体的现实、依赖于群体的秩序以及规则。
列维纳斯说:“所有的思想,哪怕是模糊的思想也总是一个关于某个事物的倾向。”〔16〕作为思想的意志不仅是主体的“我想”,而且一定包含着关于某个东西或事情的“想法”。“我想”一定是关于什么的“我想”。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我想”即意志活动。作为意志活动主体的自我,如前文所说,也分为两个部分,即形而上的个体性和形而下的气质我。其中形而上的个体性确保了我的在场、确保此行为是我的行为。这是一个不变的确定性实体。它最终通过气质我而落实于具体的行为中。或者说,个体性只能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假设脱离了个体性的)气质我的行为而呈现。气质我让我的个体性存在。那么,自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自我观念的产生来源于自我对我的存在现实的反思与理解。胡塞尔说:“人类的生活经过了自我反思和自我责任的阶段之后,从孤独的、偶然行为转向普遍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责任的阶段,最终到达一个终点。在这个终点,它在意识中抓住了自主观念,这个观念能够通过意志让自己的全部人生转变到一个普遍的自我责任的生活整体中,并因此而相应地形成一个真正的我,一个自由的、自主的我。这个我能够实现自己的内在理性,努力成为真实的自己,能够和理性的自我保持一致。”〔17〕自我观念不是天生固有的观念,而是理性者通过现实的观察和抽象而形成的观念。具体地说,我通过设想将自己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如我将自己理解为人类整体中的一员,或者将自己理解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等。总之,我从普遍存在的角度理解自己、定义自己,并最终形成一个独立的自主的自我。这意味着,在现实中,作为起点的自我观念又来源于现实:自我依据现实,通过反思而虚构一个整体性存在,并将自己视为此整体中的一员。
在这个虚构的整体性现实或逻辑现实里,我仅仅是其中一员。因此,当我以虚构出的现实为焦点思考问题时,我不再是具备个体性的我,而是转换为虚构现实中的整体性存在的一分子。此时,在这个虚构的逻辑现实中,我和外部存在融为一体、我和现实中的他者形成一个整体。胡塞尔说:“我们还可以借助于反思得出一个合法而自足的命题,即作为真正的经验,没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可以完全独立地存在。所有的存在皆置身于完成的需要之中、成为整体之一员。无论是形式还是种类来看,它都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对象,而是我们注定接受的东西,”〔18〕我们身处现实,与现实形成一个整体。“当一个指向某个具体‘朝向此’的指称被唤醒后,我们抓住了‘朝向此’自身,以及与之相伴的东西。它们组成一项工作,形成一个整体的工作坊。正是这个工作坊才是我们的关切安身之处。器具的背景被照亮了。它不是以从未见过的身份出现,而是在事先的谨慎中被不断地觉察到的整体。正是借助于这个整体,世界宣告了自己。”〔19〕我们在整体中获得了新解释或新定义。我是整体中的一员,如我是人、我是生命体、我是哲学家等。“同样必须的是,在自我组成的团体中,我和我们的相关存在总是在这个世界中。这种存在被设想为公共经验性存在而面对,即我们言说它、命名它,依此建立我们的认识,组成现实。只有在意识生活的团体中才是合法的。这种意识生活不是完全孤独的,而是内在公共化。”〔20〕我将群体意识内化于自己观念中,将自己转化为群体成员。通过反思、抽象与理解,我将自身置身于现实整体中、成为整体的一员。我和群体中的他者共为一个整体并因此而协调。
整体性存在有两种形式,一个是有机整体如某个生命体便是一个整体,另一个是观念整体如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传统甚至是整个人类等。这些,至少在理论上,都可以被定义为整体性存在。整个人类、整个国家、整个社团等都属于一个整体。有机体的生存,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有机的,而且有其自身的法则。这个法则便是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其实是否真实存在依然值得质疑)的功能便是确保生命体的生命持续。为了维护生命、延续生命,这个整体会调动其中的各个部分,使其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如一棵树,果实提供贡献,展现自己的成就,树叶接收阳光而进行光合作用,树根确定位置、掌握方向以及吸收营养等。总之,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职位、作用和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职位、作用和功能等是自然的,也可以说是被安排的。自然的存在一定不是故意的、积极的行为。在这个整体中,各部分不仅是自然司职能,而且也是被动的。它们仅仅是整体中的一分子,如同一部机器中的不同零件。这应该不是人类社会所体现的整体存在。
人类视域中的整体性存在主要落实于后者,即观念性整体,如国家、民族和人类等。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些所谓的整体性存在其实产生于人类的抽象思维,因而属于逻辑存在。我们运用抽象思维,最终形成一个整体性观念,如我们将所有人概括起来形成一个人类观念等。这便是观念性整体。这些观念性整体乃是人类由多向一进行抽象活动的结果。比如人性便是人们依据众多的人的性质而抽象出的、共同的、唯一的人性定义。人性是所有人的根本性质,因此也是唯一的属性。当我们想到自己是人时,便是对此唯一人性的想象,即我们必然用普遍的人性来理解作为人的我。这便是方以智所说的“大我”:“又有决几焉,动心以知不动,忍性以知不忍,无我以知大我,大我摄于小我。”〔21〕人性之“大我”涵摄于小我中。所谓大我即由普遍人性转化而来的我。我们依据于普遍人性等普遍观念形成我的观念。或者说,我们通过设想自己属于某种存在物如人之属、从而确定自己的、作为成员的职责或义务等。
在自我观念形成时,自我向观念性整体开放,从而将普遍性吸收进来,共同构成完整的自我。从定义的角度来说,这个观念性整体便是种类所归的属。这个属便是普遍存在。因此个体自我向普遍实体开放。开放的途径便是反思,即我们通过反思,进而知晓自身的归属(群体或种类等),最终将这个普遍存在纳入自我观念中。黑格尔说:“自然物不可能将自己的灵魂带入意识中。只有人类才能首次让自己变成双份,即成为一个普遍存在者而言的普遍存在。这首次出现于人知道自己是‘我’。通过‘我’这个词,我意味着自己是一个单个同时也被决定的人。”〔22〕我是某时某地的人,这意味着个体的我是人。我属于人,人是我的属,我的任何行为必须符合人的标准。自我因此获得了新内涵,即人性因此被注入了我的观念中。一旦自我视自己为整体中的一员时,自我便隐身成为整体中的一分子。此时不再有个体的我,而是只有整体性存在。在这个整体中,我仅仅是群体成员。作为成员的我与其余成员自然协调而融洽,即我和别人一样都属于这个属。这种融洽或和谐依赖于理性人对自身角色的反思与设想:我是整体的一员。在这个设想过程中,我不再是自我、我忘却了我。
三、成员与规则
整体中的分子或者自然地遵从自然法则,比如自然物;或者自觉地遵从社会规则,如理性人。只有遵循法则,我们才能确保整体的秩序,进而确保整体的存在。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秩序是整体性存在的标志或基础。一个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国度不是一个国家。只有秩序才能确保整体,而维护秩序的主要手段便是广义的法则,如社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法律制度等,我们统称之为法则。法则是秩序的必然性的理性形式,即它的存在能够确保稳定的、整体性秩序。法则是维系秩序的纲领,如同一个建筑物的大纲或框架一般。没有了这些大纲,建筑物便会坍塌。这些大纲,本质上来说,是对现实中诸存在者之间关系的整体性安排。
这种秩序性安排常常表现为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权利和义务其实是一个整体性存在的两个不同的视角定义。我们常常把我们想做的、也能够做某事的规定叫做权利。我的这些权利,对于他人而言便是义务。二者其实是一种行为或现象。权利与义务仅仅是对同一个行为的不同角度的理解。黑格尔说:“在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的同一性中,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在伦理生活中,一个人只要有义务,便有权利,反之依然。我有抽象的权利,另一个人便有相应的义务。”〔23〕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一致的。这样,对某个行为的定义便形成双向,即从我出发的理解,以及从他人或整体出发的理解。从我而言便是权利,从他人而言便是义务。通过权利和义务,我与他者不仅形成一个联系,而且构成一个整体。黑格尔说:“一个奴隶没有义务。只有自由人才有义务。”〔24〕单向的权利或义务都是不成立的,因为单向的权利或义务无法与他人形成关联,因此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社会行为的秩序性本身体现于如下的事实,即个体成员只能在其行为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从其伙伴那里得到预期的反应,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够完成一个行为的完整计划。”〔25〕权利行为与义务行为不仅形成相互感应或互动,而且因此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其中,义务便是一种受到法则约束的行为。康德说:“义务是一种行为。该行为具备实践的、无条件的必然性。它普遍有效于所有的、完全适应于命令的理性者。因此,它对于所有人的意志来说是法则。”〔26〕义务具备必然性。其必然性表现为与法则的符合或对法则的遵循。从形式上来看,它符合法则,因而接受法则的约束。这便是必然义务的表现即约束。义务的必然性表现为对意志的约束。康德说:“由这种对这种约束的意识而产生的情感不是慈善性情感,因为后者可能是出于感性对象而产生。它是实践的,即它只能通过对意志的客观决定以及理性的因果性而可能产生。对法则的臣服,也就是命令,不包含快乐,而是相反,它只有行为的痛苦。”〔27〕对主观意志的约束甚至可能会带来痛苦。它不是出自于我们的喜好等情感,而是出自于理性的必然。在理性指导下,我们必须遵循这一法则。这便是该法则的必然性。必然性法则规范了主观而任意的意志。“为了完成此事,我们选取了义务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善良意志,即某些主观性约束或妨碍。”〔28〕义务是出于被约束的意志的活动。
康德将人的存在分为两个世界,即自然王国和目的王国。自然王国即现实世界,目的王国即超越的自由世界。前者是经验的存在,后者是超越的存在。人同时身处这两个世界。康德说:“义务和约束是我们称呼我们和道德律的关系仅有的名称。的确,我们不仅以自由的身份而可能成为(由理性呈现于我们面前而成为尊重对象的)道德王国里的立法成员,而且我们在其中,不是主宰者,而是臣民。”〔29〕在道德王国或目的王国中,人是目的。而在自然的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便是现实的、有限的存在。它必须接受制度的安排和约束。作为其中的成员,我们只是服从的臣民,接受制度的约束。也正是这种必然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确保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即法律不仅保障我的权利,而且规定了我的义务,从而利用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整合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出于对规则的敬畏或遵循而产生的义务不仅约束了自己,而且将行为者转变为符合整体秩序的存在。黑格尔说:“义务的束缚,作为一种限制,可以表现于对不确定的主体性或抽象自由的约束上,以及对自然意志或道德意志的冲动上。”〔30〕主观而任意的人必须接受规范来约束。这些约束所产生的行为之一便是义务。这些义务能够规范或约束独立个体。在现实中,独立个体常常自行其是。因此,黑格尔指出:“作为性格中的实质物体,这些法则和制度便是约束个体意志的义务,因为作为主观的,同时也是不确定的,抑或是确定为具体的存在,他将自己区别于他们,从而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与他们相关却对立的存在者。”〔31〕在规则的约束之下,独立个体不仅约束了自己的、不确定的、任意的、主观的观念,而且意志在接受各种规则的同时,不仅将自己潜在地视为整体成员之一,还将自己的行为或存在方式安置于这个整体中。也就是说,一旦人们接受了某个公共规则,我们便将自己转化为某个整体性存在之中。这样,我的行为不再仅仅是自我的、自由的行为,同时也是一个符合整体秩序的公共行为。
客观规则,作为一个现实存在,一旦其被自由人选定之后,便可以转变为内在于意志的行为准则(maxim)。康德说:“准则是意志的主观基础。其客观基础便是实践法则。假如理性具备完全的力量来掌控欲望的话,这个客观基础,作为实践基础或原理,便可以主观地服务于所有的理性者。”〔32〕准则是主观的。人的一切行为,从主观的角度来说,直接服从于人的主观准则。也就是说,在主观意志中,准则是最重要的内容。客观法则对意志的影响最终形成准则。康德说:“有必要说明一下,这种道德必然性是主观的,即它是一种要求,而不是客观的义务。义务不会去假设某个东西的存在。”〔33〕因此,产生于普遍法则或法则形式的义务仅仅以主观必然性的形式而存在,即它是一种主观必然。
以主观的准则为内容的意志不仅是主观的,而且还是任意的。我可以这样想,也可以那样想。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认识作决定便是我的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任意的,即我说了算。在自然状态下,意志的自然行为常常会受到人的自然禀赋等的影响,即“在主观原理上,我们还有偏好等情感因素。这些自然的禀赋等常常会与那些指导我们行为的客观原理产生冲突”。〔34〕自然的主观意志常常是靠不住的。它需要某种东西来规范或制约它,使之成为可靠的基础。康德说:“最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主观准则判断中,必须加入准确的东西,即所有行为的道德可以被放入来自于义务、出自于对法则的尊重的行为必然性,而不是让我们的行为出自于爱和偏好等。”〔35〕只有具备客观必然性的法则的出现才能纠正主观偏好等的影响。这种来源于客观的、具备必然性的主观准则,将普遍存在与个体紧紧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意志整体。这个整体包括了作为行为者或意愿者的自我,以及作为意愿内容的普遍法则。其中,前者是个体,后者则是普遍存在。至此,个体与普遍存在如社会获得了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由于普遍道德规则的参与,自然而任意的个体行为获得了普遍性超越,人由自然生命转身成为社会人或道德人。
四、个体自由与普遍伦理
普遍法则的接受和遵循让人摆脱了自身的自然性。对规则的接受和遵循通常有三种情形,即自然接受、自觉接受和自愿接受。第一种情形主要指自然界。自然界的生物自然而然地遵循各项自然法则。对于人类来说,我们通常通过反思形式来选择后两种,即自觉接受,或自觉且自愿。那么,自觉接受法则与自觉且自愿接受法则有哪些不同呢?二者存在着本质差异。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别,但是二者皆有一个共同性,即依赖于反思:自觉或自愿行为皆产生于反思。
法则是公共规则,是维护整体秩序的原理。对规则的自觉接受的直接后果便是秩序与整体性,即按照规则行为,行为人便可以自觉地融入整体秩序中成为整体一分子。这和自然界的有机体的整体性十分相似。唯一不同的是,自然界是自然的,而人类则是自觉的,即我们经过反思与筹划,然后接受某种规则,最终的结果依然是遵循规则或符合规则。在这种形式中,行为人如同自然物一般仅仅成为整体的一员。在这个形式中,规则仅仅被视为工具,即我们自觉地遵循规则,不是因为这个规则本身有什么价值,自己喜欢这个规则,而是因为它有用。所谓的反思与筹划也仅仅是出于利益最大化或伤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与伤害最小化都是秩序的体现。利益最大化是权利,伤害或付出最小化便是义务。总之,我们仅仅将这些法则当作谋取利益的手段或工具。
尽管如此,反思性行为让人类摆脱了自身的自然性,即我们不再盲目地顺从于自身的自然本性、服从自然法则。我们能够主动地、有意识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这种主动安排与筹划便产生于理性者的反思。自然界的动物并无此类本领,便无自觉行为。可是,人类仅仅依赖于自觉而产生的行为常常仅仅将自己视为这个规则效力范围内的整体之分子,如同自然生命体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个体对规则的遵循仅仅体现了行为人是整体之一,谈不上行为人自己。在这个符合规则的活动中,只有行为人,没有自我或自由的个体。因此,符合规则、符合伦理的自觉行为未必是个体的自由行为如奴隶行为。奴隶的行为符合规则、符合伦理,但不是自由人的行为。没有自由的行为可以符合道德或伦理。在这种伦理行为中,行为人的活动虽然符合规则,却无法体现自身的个体性,行为人是不自由的。
自由人的行为不仅遵循自觉原理,更依赖于自愿原理。事实上,自愿原理本身便包含自觉原理。我们意愿遵循某个规则乃是“出自于对法则的尊重”。〔36〕敬重规则不仅体现了我们对规则的自觉认知,而且还反映了我们对规则的认可与接受,即这是我们意志选定的、自己愿意遵循的规则。这个规则最终产生于自我的选择。康德说:“遵循一种由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可以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的准则去行动。”〔37〕能够成为我的行为准则的普遍法则乃是出于我的意愿与选择。这段经典表述体现了行为人的双重反思或超越:经过反思道德规则而寻找到其终极性依据、其表现形式便是普遍法则。普遍法则产生于人类的存在论追问(ontological argument)。这种追问形式便是反思。在反思中,人们通过追问普遍观念背后的普遍实体而让其获得存在论的证明。由此人们对此法则产生“尊重”:“尊重,不是出于快乐和享受快乐的尊重,是某种在其之前,理性便已经具备了某种先在的情感为基础的东西,因为那样的话便是感性的、慈善的情感了。法则对意志的直接约束所产生的意识绝不同于愉悦的情感,虽然它在和欲望官能产生联系时难免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但是二者的来源不同。只有这种类型的观念,即我们能够在追寻行动中获得快乐,它不仅符合义务,而且出自于义务。这才是道德行为的真正目的。”〔38〕所谓尊重,即意志服从或接受普遍法则。意志在服从普遍法则时不仅接受了普遍法则为内容,而且产生相应的情感。前者体现了行为人对普遍存在如真理的反思与认识,从而能够完成道德行为,后者则表现了行为人的个体性与情感。尊重与选择分别从两个向度揭示了意志与普遍法则的关系。尊重体现了意志对普遍法则的臣服与接受,而我意愿则是自我的自主性的体现。这种体现最终经由反思而获得证成或认可,即这是我确定的普遍法则。在我确定遵循某种普遍法则、遵循社会伦理的同时,我也成为自由人。它是自我的自主性与社会的普遍性的完美统一。
康德把自由分为两个向度,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康德说:“事实上,道德的唯一原理由那些完全摆脱了法则的质料(即欲望对象)的东西组成。在对任意意志决定中,只有普遍立法形式所产生的准则才是可行的。这种摆脱便是消极意义中的自由。而纯粹的、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便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39〕积极自由即自主立法、我的行为我做主。在争做主宰进程中,理性和欲望都可能发挥主导作用,即有时候人们出于欲望而做主,有时候则不是出于欲望与利益等经验因素而决定。这种排除感性与经验因素而自作主张的自由便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不仅去除欲望的干扰,而且排除利益与情感等考量,它是纯粹自我的决定,这便是个体性超越,主导这个超越的因素是人的个体性。超验的个体性确保了该行为属于我的行为,个体性的在场乃是对自我反思的结果。
真正自由的行为不仅体现了自我的个体性,而且同时关联着规则,即独立而自由的个体的意志仅仅以普遍规则为自己的意志对象,我们只意愿这个规则以及这个规则所表征的普遍实体(universal)。普遍实体产生于人们对普遍观念的反思。由普遍实体所支持的普遍道德规则成为自我追求的最终目的:我仅仅追求规则的实现,而不关心效果或后果,这种追求,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说便是义务。黑格尔说:“义务是一种对主体性的自我意志的限制。它仅仅阻碍了主体性所归属的抽象善。……义务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仅仅是将自由抽象化,即不去的自由。义务是我们的本质的实现,是积极自由的胜利。”〔40〕义务便是自由。反过来说,自由不仅有积极的主动行为,而且伴随着约束与限制,这便是自由的消极维度。消极自由其实不消极:它协助人们超越了自身的感性限度与经验限度,将人转变为社会人或道德人。“自由只能通过超越得以存在。”〔41〕这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不仅体现了个体人的个体性与自由即个体性超越,而且也一定符合伦理规则,实现了普遍性超越。自由行为是个体性超越与普遍性超越相结合的行为,或者说,自由是一个超越性行为。这个超越性行为体现为两个向度,即个体性向度和普遍性向度。前者便是个体性超越,后者便是普遍性超越。经过超越而形成的个体自由必然符合普遍伦理。自由者一定是讲道德的人。反过来则未必,即遵循伦理者未必是自由者。奴隶遵循伦理,却不是自由者。这种超越性行为的基础便是理性者的反思。通过反思,人类不仅可以成为社会人,而且能够成为自由人。也只有反思才能确保人类能够实现个体存在与群体相居的和谐共处。
注释:
〔1〕〔2〕〔3〕〔9〕Johann Gottlieb Fichte,The System of Ethics: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Wissenschaftslehre,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niel Breazeale and Guenter Zoell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p.224,228,242,211.
〔4〕郭美华、陈昱哲:《个体道德与普遍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及其缺失——〈大学〉的政治哲学解读》,《周易研究》2021年第1期。
〔5〕〔26〕〔28〕〔32〕〔34〕〔37〕Immanuel Kant,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c der Sitten, Kant’s Werke Ⅳ,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1, pp.412,425,397,400,425,421.
〔6〕〔27〕〔29〕〔33〕〔35〕〔36〕〔38〕〔39〕Immanuel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Kants Werke,Band Ⅴ,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pp.32,80,82,125,81,81,117,33.
〔7〕Samuel Pufendorf,The Whole Duty of Man: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ature,translated by Andrew Tooke, 1691,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Ian Hunter and David Saunders,Liberty Fund, Inc. 2003,p.31.
〔8〕〔18〕〔19〕Edmund Husserl,Ideen zu einer reinen Phānomenologie und phā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1976,pp.235,186,74-75.
〔10〕Johann Gottlieb Fichte,Zur Rechts und Sittenlehre, Johann Gottlieb Fichte’s Sämmtliche Werke. Zwcit Band, Berlin, Verlag von Veil und Comp, 1845, p.218.
〔11〕 〔22〕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 Suhrkamp Verlag Franckfurt am Main, 1986, pp.314,82.
〔12〕〔13〕 Martin Heidegger,Logic a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Wanda Torres Gregory and Yvonne Un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p.32,34.
〔14〕〔15〕〔23〕〔24〕〔30〕〔31〕〔40〕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ft im Grundrisse,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7,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0, pp.54,54,304,305,297,296-297,298.
〔16〕 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9,p.122.
〔17〕〔20〕Edmund Husserl,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translated by David Carr,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0, p.336.
〔21〕《方以智全书》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2018年,第267页。
〔25〕F. C. Von Savigny,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0, pp.159-160.
〔41〕Karl Jaspers,Philosophy of Existence,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F. Grabau,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