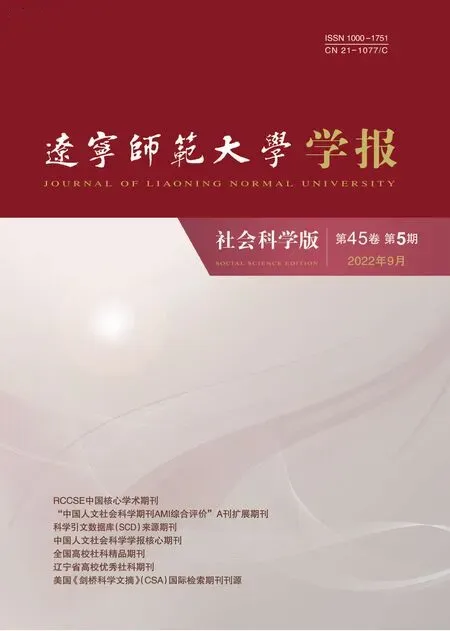清代八旗子弟的历史教育初探
李 立 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旗人是清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清入关后,随着与汉人交往的日渐频繁,旗人对汉文化的认同也日益加深。其中,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学习被越来越多的旗人所接受。历史教育促进了旗人社会的发展、进步。然而,学术界以往关于清代历史教育的研究却忽略了旗人群体(1)目前关于清代历史教育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李良玉《清代书院与历史教育》(《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70-78页)及其专著《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安昊《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历史教育初探》(《文化学刊》,2016年第3期,第218-223页);宋艳秋《晚清历史教育思想变革研究(1902—1912)》(河南师范大学,2016年)等。然而,这些成果几乎都忽略了清代旗人群体的历史教育。严格意义上说,清代的帝王及皇子也属旗人。学术界在对清代帝王及皇子教育的研究中也涉及了历史教育,如杜家骥《清代的皇族教育》(《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第88-92页);吴吉远《清代的皇子教育与上书房》(《紫禁城》,1995年第2期,第11-13页);陈东《清代经筵制度》(《孔子研究》,2009年第3期,第96-104页)等。然而,对皇家之外大部分旗人群体的历史教育状况,学术界目前尚无专门论著。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八旗”重点指代皇室之外的满、蒙、汉旗人群体。。本文试从官方、私家和家族三个角度考察清代旗人的历史教育及其意义。
一、官方开展的旗人历史教育
清开国之初,统治者就重视学习汉人的历史文化。他们为了打破满汉语言隔阂,将翻译汉文史籍作为旗人历史教育的重要形式。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成立文馆后,皇太极“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史》《金史》《元史》《性理大全》诸书,以教国人”[1]1。一些满洲大臣还因翻译汉文史籍、传播历史知识受到褒奖。满洲正红旗大臣希福于顺治初年“译《辽》《金》《元》三史成,奏进,世祖恩赉有加”[2]9348。满洲正白旗大臣苏纳海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以翻译《三国志》告成,赉鞍马、银币”[3]346。翻译史籍等形式的官方历史教育还体现了清朝统治者鲜明的政治需求。皇太极曾命翻印辽、宋、金、元四史,除学习求治方略外,“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4]。在此尤其强调了四史中的“忠良”“奸佞”行为,体现了统治者欲借助历史教育在旗人中灌输忠君的主流价值观。
清入关后,逐渐形成了以官学为主导的旗人教育体系。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清政府设立八旗官学,由国子监负责稽查考课,此后八旗官学在教育设施、教育制度等方面不断完善。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朝廷又为宗室子弟建立了宗学。至康、雍年间,还相继设立觉罗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世职幼学、八旗义学等多种教育形式对旗人子弟加以督导,官学“严其章程,明其劝惩,所以造就而成全之”[5]1530。此外,还有少部分八旗子弟以“荫生”或“贡监”的身份在国子监肄业。在官学中均设有满、汉文的教学,其中也涉及了对历史知识的学习。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朝廷为宗学中的亲王、世子、郡王“选用满、汉官各一员,讲论经史”[6]5436。国子监祭酒、司业及六堂学官还为八旗诸生主讲《四书》《性理大全》及《资治通鉴》。八旗官学中聪颖者可选拔为国子监生,“与汉贡生一体肄业,讲求明经治事之学”[7]204。可见,官学亦有教导学生习史的职责。
朝廷还通过“赐书”的形式为八旗各类官学提供多种历史书籍。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朝廷分别赐八旗官学《大学衍义》《古文渊鉴》各一部。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朝廷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二十三部正史类图书以及《三通》《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御制评鉴阐要》《御制萨尔浒战书事》《御定子史精华》等史书颁发于盛京八旗官学[8]8596。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朝廷又颁发吉林各处旗学《开国方略》《八旗民俗通考》《盛京通志》等书籍,以供士子参阅[8]8597。
此外,朝廷十分注重营造良好的历史教育环境。自康熙年间,“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9]。这些小说多数以历史为题材,有些情节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使人阅看,诱以为恶”[8]8547。为净化旗人学习环境,康熙帝“通行中外,严禁所在书坊,仍卖小说淫辞者,从重治罪”[10]197。乾隆朝通行各地方官“凡民间淫辞小说,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10]198。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朝廷针对旗人社会中流行的满文《水浒传》《西厢记》等历史小说,饬令各地自行烧毁。咸丰年间,官学中流行的满文《资治通鉴》等书籍使用的多是无圈点的旧满文,“引用经史,皆系旧语,对音切字,有未经翻译成文者;又止清文单行,未及增注汉字”[8]8550,故咸丰帝令以完备的新清语重新翻译,并以满汉对照的形式付梓,“俾在京八旗及各省驻防同资讲肄”[8]8550,方便了旗人的阅读需求。
八旗官学的历史教育常常被纳入日常的考课制度中。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朝廷令满汉祭酒、司业率助教等官每日亲临官学,勤课八旗官学生《古文渊鉴》《大学衍义》等书,并每月将八旗官学生传至国子监“考试一次,分别优劣。优者奖赏,劣者戒惩”[6]5464。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朝廷要求八旗汉文官学生“当使讲求经史,为有用之学”,并规定“每三年一次,奏请钦点大臣考试。优者拔作监生,与汉贡监等一体肄业”[10]160。进入国子监的八旗诸生遇考课之时“其考试题目,应用四书制艺一篇、经史策问一道,恭请钦命”[11]。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朝廷又令教官引导学生在八股文中融入经史之学:“窃思八股非经史精义不能佳,教习等果能发明经义,学生各以经史为时文,则获益自多。”[8]8544旗人官学倡导的历史教育实际上已经流变成一种“应试教育”。
二、旗人私家历史教育的多元呈现
清中叶以降,随着社会环境由战乱转向承平,众多八旗子弟远离了战场,开始重视学习汉文化,“今见八旗人等专尚读书,有子弟几人,俱令读书,不肯习武”[5]1539。一些有能力的八旗之家“莫不延师接友,则文学固宜其骎骎然盛也”[1]25。历史教育也成为旗人私家教化子弟的一种形式。
旗人子弟最初接触的历史知识往往来自家中长辈。佟世思曾祖“教子弟以正,事无巨细,必取法古人”[12]408;玉麟早岁父亲病故,其祖父“授麟以古人之书,勖麟以古人之行”[12]208;法式善五六岁时,其祖母教其识字“每举古人乡里官爵、表字相问难”[12]112;博明“自髫年侍先人,即获闻绪论于辨证考订之事,每心志之”[12]125。一些旗人家族甚至专门为子弟编写了历史教材。清初正白旗汉军名臣蔡士英便将《通鉴纪事本末》节取精要,重新更定为《通鉴纪事本末纪要》八十一卷,“盖观往而知来,信无逾于斯矣。仲儿自愧吴蒙,将于是乎?求所以淑身而应世者”[12]188。从以上介绍可知,一些旗人家族中长辈充当了子弟历史教育的“蒙师”角色。但对大多数旗人子弟而言,由于年岁尚幼,而中国史书浩博,“骤难责其研究”[7]204,故此阶段他们通常接受的是一些浅显的历史典故和常识。
旗人子弟年纪稍长便进入家塾读书。家塾教育以八股时文教育为主,如完颜麟庆十二岁始读经,学作文;崇实十一岁学吟两韵诗,此后又习作起讲,读四子书,授试帖之法;英和十二岁即学举业;文祥八岁读《孟子·天时章》,十一岁读《四书》、学韵诗、作八股;金梁九岁读《孟子》,十四岁学作制艺,十八岁始精研经史[13]。从中可以看出,历史教育并不是家塾教授的重点。康、雍以降,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旗人子弟重要的进身之阶。自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八旗科举考试在几经废止后最终复科,并形成定例[14]。八旗子弟竞相应举,“今见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详究其原,皆由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6]5442,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得免从军之役,“无不乐于部用”[6]5442,甚至还形成了“八旗科举家族”[15]。在这一背景下,旗人家塾教育在教授内容上自然以科考为重心,汉军镶红旗人刘廷玑曾说:“余少习举子业,键户咿唔,其于五车二酉,未能寓目。”[12]121在以参加科举考试为主旨的教育背景下,大部分人没有精力再博涉掌故之学。
一些旗人是在成年以后才养成读史习惯的。汉军正红旗都统吴兴祚便言:“余束发就学时,辄喜读古人书传。每纵观大意,于源流得失之故,亦尝探其要领”[16],“束发”表明其至少在十五岁以上;袭封康亲王永恩则“年始及冠,雅志经史”[12]155;汉军正黄旗人李锴辞官后退居盘山,“当壮盛,得离跂佁拟肆厥志,盘阴虚无人,樵爨之隙,览古高,时读旧史,有蕴而隐,精凿而佚,疏而互紊而乖迕者,则杂群书研几之”[12]98。从中可窥见旗人读史多是出于自身兴趣,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官学“应试”的窠臼。从学习的内容上看,除正史外旗人还热衷于传统的文化艺术。宗室敦成、敦敏兄弟齐名,“诗宗晚唐,颇多逸趣”[1]25;永忠为恂恪郡王嫡孙,“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1]25;允禄则精通古乐,“仿《周礼》磬氏遗法,制特磬十二”[1]9050;甘道渊屡试不第,遂专注于书画,“画学宋人,楚楚有致。篆隶八分,俱有古法”[12]425。他们在历史中汲取艺术的养料。
此外,在旗人的社会交往中通过友朋间的“谈古论今”同样可以受到历史教益。满洲正黄旗人铁保与汉军旗人甘道渊相交甚厚,两人于聚会间分别以汉代张良和唐代狄仁杰为例谈论“谋事”与“成事”的关联,“两论默合,相视狂笑”[12]425;李锴寄居潞河时,“遇秣陵钟生,以为学者宜读《左》《国》《史》《汉》,以厚其基”,李锴得到启发,对此前所学“幡然有悔心”[12]156,自此多留意于史学;满洲正黄旗人恒裕(字益亭)与友人相聚,“迨酒酣耳熟,益亭则吐气如虹,发言成轨,一部二十一史,供其谈笑”,同游之客“俱为倾倒不止”[12]427。走出书斋的历史教育展现了更为丰富的魅力。
与官学相比,旗人私家教育的受众更为广泛。由于八旗官学设有固定的学额,八旗每佐领下最多可选两人入学,“额外私自读书者,部院不准选用考试”[5]1539,因而大部分旗人子弟都受益于私家教育。私家教育也成为旗人历史教育的主要途径。旗人私家历史教育内容更丰富、形式更灵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官学中“应试教育”的束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对旗人整体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不无裨益。
三、谱牒编修与家族史教育
在官方及私家历史教育之外,家族历史教育也成为旗人历史教育的一种形式。这里的“家族”主要是指清开国之初因立有显赫军功而享有世职世爵的旗人世家群体。家族历史教育是指旗人世家对其子弟进行的家族史教育,它以纂修家族谱牒为载体,是旗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清中叶以后,旗人世家记载家族历史的文献多残缺不全,造成了家族史教育的严重缺失:“溯自我皇开国以来,归马放牛,而万民悦服。虽属先皇之仁德所致,实赖满蒙之英勇辅弼而成就之也。……然满蒙既有如斯根基,如斯名爵,何竟忘本图末?考诸世系由来,罔不茫然,无所推尊也。”[17]667嘉庆初年,辅政多年的宗室相国禄康,竟将褚英贝勒身遭刑戮之事误归于其祖诚毅公穆尔哈齐,“诚所谓数典忘其祖矣”[1]182。旗人对家族史的茫然无知,时人不禁有所隐忧:“代序日远,族姓日繁,不为之明章统系,俾知世德所自,将罔克念先人之勤,无以光昭前列。”[18]八旗世家开始重视对子弟的家族史教育,口口相传便成为权宜之计。吴俄尔格氏五世孙吴宗阿曾记载其祖父为其讲述家族史的经历:“祖每执余手,抚余首,呼余名而训之曰:‘女父与女伯父及今累受宠眷,历登仕籍,然仅以武功显。……每思祖功宗德,世系族姓,未尝一日忘之。余即不言,女父自能为尔言。然姑言之,子试听之。’某为始,某为曾,某祖几子,所居何官,所职何业,发于何地,迁于何境,言之不厌其详。”[17]699而更多的旗人世家则希望通过重新整理家族谱牒以考世系而明人伦。族谱中详细排列了先祖的世系,并记载先祖远近姓氏讳字名号,“始而父子、兄弟,久而分派,则为宗族。至情所系,大义攸关”[17]644。有些族谱更是图文并茂,作有谱系、坟茔等图,图外详载祖宗名号、婚配,“俾支系了然,妇孺可晓”[17]1057。通过考论世系,辨别亲疏,以实现“正人伦之大经”的旨归。
清中叶以降,旗人社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许多旗人失于教化,安于游惰,“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19]。甚至,一些子弟“但求目前之利,频更祖宗善教,另生妄念。惟是视祖先遗泽,茫然不晓”[17]352。由此,一些旗人世家希望通过编修族谱阐明家族的创业发展史,教育子弟继承先德,摒弃陋俗。佟氏始祖达礼,自明初以勋伐起家,历二百余年,文武并进,以“忠贞世家”享誉辽左。然自万历年间,遭党人构祸而全族被难。《佟氏宗谱》中即载有《先世被难述略》,详载其祖之功业与遭难始末,“尤在阐扬先德,昭示子孙,俾思所以缵承遗绪而光大之也”[17]1094。《乌喇纳拉氏谱书》记载了其先祖事迹,以及其祖拜达礼、图尔格、阿穆尔图的敕纂碑文,“示后世用传不朽,所以益忠励”[17]391。《宁古塔那穆都鲁氏家谱》中附载了《那氏先祖列传》,详载其先祖康果礼随努尔哈赤平定中原事迹,“子孙均当效法,以文教武才为事”[17]352。《吉林成氏家谱》中还保留了其先祖的诸多诗文、墓志、行状等内容,“藏之族长家,每岁清明俱集于此,循循执子弟礼,听老辈道古今忠孝、可泣可歌事,以为法则”[17]1057。这些旗人谱牒书籍阐述了家族发展源流,记载了祖先的发展创业史,使同族子弟“爱慕之心明于先,敬惕之意存于内,不仅无渝薄之风,将孝弟之性油然以生”[17]13。谱牒的教化意义凸显了家族史教育对旗人子弟的社会文化功用。
需要强调的是,旗人家族史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了满汉民族的畛域:“若专专以谱寻族,以族合谱,则凡满汉不同、旗分不同者,皆曰非我族类,岂不缪哉!”[17]1176他们更多展现的是旗人家、国、天下的经世情怀。从家族的创业史中延伸出对清开国基业的颂扬:“念我圣朝发祥长白以来,应天顺人,享一统无疆之业,推恩施德,基万年有道之隆。诚媲美唐虞,远过商周矣!”[17]181又进而以族谱为媒介,形成了对“天下”秩序的理想主义建构:“盖谱书者,一则可使后人考察世系而生报本之念,一则可使后人知同一先祖而生爱类之思。报本之念,爱类之思,苟能引而申之,扩而充之,触类而傍通之,则天地间一切万类,何往而非一本乎?天地间一切万类,何往而不宜相亲相爱乎?举万类而视为一本,举万类而相亲相爱,世界有不以之大同乎?”[17]283历史的教化功能在家族史教育中得到了宣扬与升华。
四、历史教育对清代旗人社会的意义
有清一代,自顺治朝开始施行“文教是先”的政策:“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20]康、雍以降,逐渐形成了以崇尚朱子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崇文重道”方针[21]。清朝在入主中原后,经学一直被统治者所推崇。在这一背景下,无论在官方教育还是私家教育中,经学教育始终是旗人学习汉文化的重要部分,加之旗人自幼接受较系统的举业训练,因此历史教育在整个八旗文教体系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由此也导致了旗人历史教育整体水平有限,一些旗人对历史典故未能深悉其意便任意征引。如满洲正蓝旗副都统文庆在总理孝慎成皇后丧仪的奏疏中误引《尚书》专指皇帝丧仪的“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之说,“文庆系翰林出身,《虞书》二语,深切著明。若竟不知,则学问亦太浅薄”[3]3132,因而被降革。旗人中虽不乏如满洲镶白旗人盛昱这样的博识者,“然系好古之徒,于经史各种学问,未闻有何著作”[22]。旗人群体中也并未出现具有深厚史学造诣的学者。尽管如此,旗人的历史教育却依然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历史教育成为涵养旗人道德观念的重要源泉。中国史书有“惩恶而劝善”的优良传统,一些道德模范及其事迹被各代史家载入史册,通过学习历史,古人先贤的言行会对八旗子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宗室恒斌自幼读史,其父萨喇善官吉林将军,因事被遣戍伊犁时卧病不起。恒斌奋然曰:“古人有身代父役者,吾何不为?”于是上奏陈请,乾隆帝命从父行,“公竟行,昼夜侍父疾,至废寝食”[1]175。包衣王弼公“以父母老,尝疾苦,乃研精岐伯书,通其术,葆摄缜密”[12]390,孝心成为其学习、阐扬传统医药之学的动力。奎林为乾隆帝孝贤纯皇后之侄,他在学习《元史》时对王保保赞赏有加,“耶律文正公非余所及,得及王保保之忠贞足矣”[1]42。奎林在此后乾隆朝出征两金川的战役中英勇奋战,凯旋回师,“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2]10945,同样赢得了“忠贞”的美誉。成哲亲王永瑆,读《史记·孝文帝本纪》《三国志·诸葛亮传》后,对文帝、诸葛亮的俭朴品质十分颂扬,“夫文帝则三代以后之贤君,莫或逾也;武侯则三代以后之贤相,莫能过也”[12]43。他认为俭是可与孝、悌、忠、信并而行之的道德修养。历史教育滋养了旗人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历史教育深化了旗人对史学的理解,培养了旗人治国理政的历史观。汉军镶黄旗人郎廷极便云:“夫史,非徒记事而已。将以明一王之制,政治之得失,礼教之盛衰,鲜不于是乎取征,使后之读者了然如指诸掌。”[12]96因此,史学可以起到“顺天心,合民志,措天下于太平”[12]218的政治功用。正是基于此种共识,史学在旗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旗人官员从历史中汲取了执政的经验。满洲镶白旗人胜保引《尚书》“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强调执政要以民为本,“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3744。为政之要,莫大于选贤与能。满洲正白旗人官文力主甄拔人才引入“优贡”制度,“选举古法寓于优贡,请特加擢用,以收实效而广登进”[3]3585。山东道监察御史穆缉香阿,疏请同治帝慎择宦寺,“溯自汉末及前明,朝政之失,半由宦寺”[2]12207。执政还要有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精神,觉罗桂芳便认为即使如尧、舜这样的古代贤君,在政事方面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昔孔子论仁至于济众,论敬至于安百姓,皆曰:‘尧、舜其犹病诸。’岂真以尧、舜之圣为未至哉?夫天下之大,万民之众,而决其无一夫之梗者,盖自古其难之。”[2]11284旗人官员通过学习历史积淀政治素养,从而为他们入仕参政提供历史智慧。
最后,历史教育促进了传统文化在旗人中的传播。一些带有鲜明传统文化特征的历史人物通过历史教育进入旗人的视野。满洲镶蓝旗人鄂尔泰依据《礼记·郊特牲》《汉书·食货志》所载,考察了代表中华文明先祖的“先农神”,指出炎帝即有“神农氏”之号,并对其祭祀源流进行了考证[12]51;满洲镶黄旗人达礼以汉代董仲舒有功于圣学,随其父入陕,“每过车而必式兮,磨短碑之碧藓。撮瓣香以致敬兮,伸仰止于高山”[12]447;满洲正白旗人继昌任陕西按察使时,在公余之暇,取《抱朴子》读之,指出“《外篇》驳难通释,稽古正今,于持身接物之宜,言富而理济,又颇通达治体,为政者当置座右”[12]126;汉军镶红旗人赵宏恩,重修婺源朱子阙里,将朱子视为与孔、孟并举的圣贤,“公之教列于千秋,孔子之道愈光昌于万古”[12]319;满洲镶红旗人常安赞赏北宋贤相韩琦的应变能力,“当天下之大任、居天下之令名而无愧也”[12]64。以先贤为纽带,旗人的历史教育增强了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为满汉社会的深入融合奠定了情感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接受过历史教育的旗人继承了传统史学中的经世史观,在清末时局变迁中引领了时代新风。汉军正白旗进士延茂认识到了晚清以降中国面临的新形势,“开古今未有之奇局,合地球万国为战场”[3]4689,而欲“控驭外人”就要了解外洋各国的发展历史,“于各国之贫富强弱,利弊兴衰以及山川夷险,随时随地,密为考证”[3]4689;宗室寿富,在清末政治的改良思潮中,“尤谙《周官》《礼》《太史公书》,旁逮外国史”[2]12779,光绪年间,他受命赴日本考察,归国后撰《日本风土志》四卷,于日本政务及变法维新的历史多所留心,被光绪帝召见时,他“痛陈中国积弊及所宜兴、宜革者,漏三下始退,上器之”[2]12779。中外历史的融会贯通开拓了部分旗人视野,彰显了旗人历史教育所具有的时代内涵。
五、结 语
清代旗人接受历史教育的途径主要有官方教育、私家教育和家族史教育。旗人主要通过私家教育获取历史知识,私家历史教育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官学教育的应试束缚;而家族史教育是旗人社会内部演化的必然要求,成为官方历史教育和私家历史教育的有益补充。由于朝廷推行崇尚经术的文教政策,历史教育在旗人教育体系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旗人历史教育的整体水平有限。尽管如此,历史教育提升了旗人的素质与能力,促进了以历史文化为纽带的满汉融合,彰显了积极的政治文化内涵。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科举考试头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历史教育的地位至此有所提升。嗣后,科举被罢黜,历史教育被引入各类新式学堂,史学在教育史的层面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旗人的历史教育也随之开始走向制度化、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