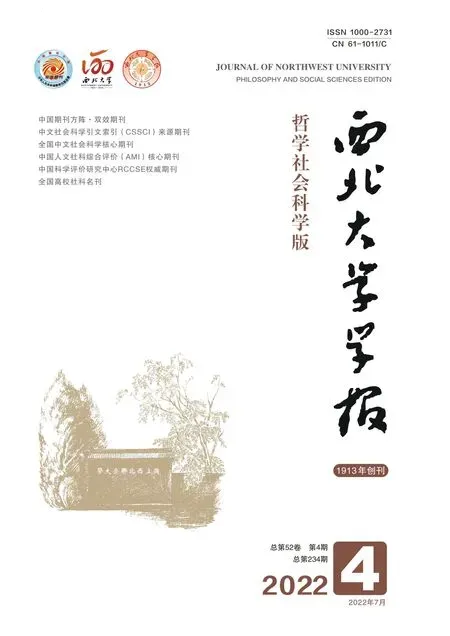论医学考古学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赵丛苍,张 朝,曾 丽, 祁 翔
(1.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医学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27;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图书馆,陕西 西安 710126)
“医学考古学是以考古学和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古代人类医学遗存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医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1]医学考古学学科的构建,一方面是基于古代医学遗存被越来越多地揭露,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则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充实和完善使然,也为考古学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医学考古学的本质属性仍是考古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考古学田野工作得来的实物资料。脱离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医学考古学的研究便无从做起,也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我们据此逐步建立古代医学遗存的时空框架,梳理与整合其基本文化内涵,为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奠定基础。并通过借用和转化其他理论与方法,也为考古材料的深入探研创造新视角,从而实现医学考古学的学科目标。
一、医学考古学的理论基础
医学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医学与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互相借鉴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促进了医学考古学理论的构建。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医学考古学本身具备考古学基本理论的支撑,又得到其他学科理论的补充,从而形成其不断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进化论
进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是医学考古学最根本的理论基础。自达尔文(Charles Darwin)通过对生物界的观察,提出进化论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生物学、医学、病理学等学科的创立和发展皆以进化论为重要基础。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之前7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这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也是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源泉之一。医学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同样遵循着进化论的法则。
生物进化论是医学考古学解释疾病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生命最大的敌人便是疾病,疾病是随着人类进化不断发生和演变的,时至今日,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依旧受到生物进化的影响。古病理学的研究表明,对病原体和人类协同进化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当前对患病模式的理解[2]。近些年提出的达尔文医学表明,“一切生物功能的设计都可用查理士·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3],生物进化离不开疾病,疾病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畸变衰变病理过程的系统化。以进化论的思想看待疾病的发展,认为疾病是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形成并演变的,对于认识疾病和人类体质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利于医学考古学对于某种疾病在古代发展情况的准确认识。
人类对疾病的认知以及应对疾病的方式同样是不断进化的。了解古人对于疾病认知的变化,是医学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史前时期,对于疾病的治疗多依赖巫术,这主要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处于蒙昧阶段,认为疾病的产生是鬼神作祟。《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刺法论》:“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真?”[4]816在这种鬼神观念下,人们往往寄托于巫卜之术,以借助神灵的力量驱邪祛病,《管子·权修》就有“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聚祟”[5]14的记载。而随着对疾病认知的提高,人们逐渐觉察到医药对治疗疾病有重要的效果。至西周时期,还设立了医师这一官职,以掌握医疗事务。《周礼》记载:“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6]10,102-103但需要注意的是,占卜治疾并没有因此消亡,甚至至今也有遗留,这表明鬼神医疾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古人对于疾病的认知情形决定着当时的治疗方式,运用进化的理论对探究古人关于疾病的认识以及医疗方式的转变等有关古代医学发展情况,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作为医学发展的表征和重要载体,医学物质遗存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进化论的法则。进化论是考古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柱石。韦代尔·西蒙森(Vedel-Simonsen)和克里斯蒂安·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提出了“三段论(或称三期说)”学说,即人类发展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此后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H.Steward)等学者,不断拓展进化论在古史研究中的应用领域,形成了文化进化论对古代社会的解释范式。此同样适用于医学考古学。考古实物资料反映出古代所使用的医用器具总体的变化是从形式简单到复杂、种类单一到多样。考古所见的先秦时期医用器具,种类相对单调,不外乎砭镰(藁城台西出土)[7]197-202、青铜针(广西武鸣马头西周墓出土)[8]、用作热熨的砭石(长沙下麻战国墓出土)[9]诸种。而至汉代及以后,医疗用具种类明显增加,且形制丰富多彩,如河北满城汉墓一座墓葬就出土了“医工”盆、“九针”、铜药匙、铜滤药器、银罐药器、银漏斗、双耳铜镬、铜手术刀等多种医疗用具[10][11]117,还如江西南昌海昏侯汉墓中出土了带有“医工五禁汤”的漆盘和盛放药品的精美木质漆盒[12-13];徐州狮子山汉墓的铜杵臼和铜量[14]239,等等。这些汉代医用器具无论是类型、工艺、材质以及适用性等都较先秦时期有了巨大进步,亦可谓发展进化的结果。
(二)系统论
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之于医学考古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系统论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L.V Bertalanffy)创立[15]。系统论认为,万物皆成系统,系统无处不在、无物不包。世界可以划分为无数个系统,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此外,系统是各要素之间和要素与整体间相互作用、联系的矛盾体。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系统的关联性。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有序性、最优化都是事物的客观规律。系统论对于医学考古学研究的指导是显而易见的。以中医为例,宏观而言中医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的系统之中, 那么医学考古学对其遗存的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中, 透过医学文物揭示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医学考古学亦是一个系统, 其中包括了古代医学理念、 古代医药管理体系、 对疾病的认知以及医药救治方法、 健康养生、 医学人文等多个方面内容, 这些方面构成了医学考古学的子系统, 而这些子系统中又包括各要素, 例如医药管理体系这一子系统中包含有医药管理机构、 医药管理制度、 官医与民医等方面;医学人文子系统中包括有医患关系、 医患心理、 社会价值取向等内容。 这些子系统之间和子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与联系的, 任何子系统或要素的变化势必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
鉴于此,医学考古学所获得的大量医学物质遗存,需要以系统论的思维加以解析,从而获得对古代医药遗存功用、古人的医药实践活动、古代医学发展情况、医学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等深层次的认识。同时,构建医学物质遗存之间或与其他遗存之间的关系,以建立起较完整的医学考古学体系。实际上,系统论的观点在新考古学中已经得到重视。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中指出:必须把考古材料放到一个系统的参照系中去考虑,……认为考古学家用来描述事实的方法必须由寻求互不相干的特征的组合或结构转变为探索功能上互相依赖的系统[16]43-55。虽然医学与古人生命健康具有重大关联,但是古代医学遗存相比其他日常生活用物来说却发现相对较少,因此医学考古学更需注重系统论的运用,以充分揭示医学遗存的丰富内涵。藁城台西商代遗址M14中出土的一件漆盒,里面放置有一枚砭镰,其应是用于切割肿疡和泻血的医疗器具[7]197-202。商代医药用具砭镰发现的重要意义毋需多言,但如果只注重遗物本身而不重视更多信息的获取,则会给进一步的讨论造成缺憾。从系统论的理念出发,至商代并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医学体系,而处于巫医并行阶段。联系该墓葬中出土的其他遗物,如三件卜骨的存在,推断该墓主很可能是“巫医”。从墓葬的规模、殉人、出土遗物看,埋葬等级不算低,表明巫医在当时的身份地位是较高的,其服务对象也多为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从出土的砭镰到巫医身份的确认,再到巫医的地位等一系列信息的获取与认知,如若不是从商代医疗系统中去看待砭镰,就不易认识到其与卜骨等遗存之间的关系,也难以透过小小的砭镰识别出其作为巫医墓葬的性质以及对医患关系等问题的引申思考。
其实, 古代医学的发展, 尤其是中国传统医学已具备有一定的“系统”思维。 “从系统的角度认识生命过程不是系统生物学所特有的, 我国的传统医学很早就认识到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 通过经络和精、 气、 血、 津液把全身组织器官联系在一起, 成为统一的整体来维持生命活动。 ……中医理论中这些朴素的系统观与整体论的思想, 与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思路有一致性。”[17]了解中国古代医学的系统思想, 能更好地认识医学物质遗存。 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 导引法强调“调身、 调息、 调心”三调合一, 若不了解导引“形神合一”的整体观, 则难以领会《导引图》中的养生智慧。
总之,在医学考古学中,系统论的运用能够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医学物质遗存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利于透过相应要素反映系统的内涵。
(三)中程理论
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属社会学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倡导。路易斯·宾福德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开创了考古学的中程理论。中程理论为分析实物遗存和古代人们行为间的联系架起一座桥梁。一般而言,基于反复的观察,考古材料中的各种形态得以发现,包括器物类型学分析、特定考古学文化的描述、相对年代的判断、某一文化中特定的葬俗等,但是其基本不涉及人类行为,对于经验、观察也难以提供解释。而抽象法则通常被用来解释各论点之间的关系,这些论点与了解某一重要领域密切相关,包括自然选择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等。 这些法则欲将人类行为的概念彼此联系起来, 而非说明特定的观察, 因此它们一般无法被直接肯定或否定。 中程理论试图解释案例中两个或更多变量之间的规律, 这种通则要么通过改善抽象法则, 使得它们能应用于特定材料, 要么为某些存在于许多案例中的基础通则提供一种解释来构建。 路易斯·宾福德发展了的中程理论就是试图利用民族志材料在考古学可观察的现象与考古学无法观察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一种可靠的相伴关系[18]28-31。中程理论核心思想是联系古代物质文化与人类某种行为方式, 注重对考古材料中某种现象的解释, 减少研究中的主观因素影响。中程理论不仅采用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也应包括其他方面如实验考古学、 微痕分析法、 埋藏学、 实地调查、 分辨人类行为的方式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
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医学考古学,建立医学物质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理所当然,实验考古学则于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对于考古发掘出土的医药遗存,运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测定成分,调制药材,推测是针对哪种疾病的药方并测试药性,这也为现代中医制剂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参考。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H85中以组合的形式出土有夏至草、秃疮花、泥糊菜。结合它们的具体医药用途,应为当时的“妇科草药”[19]。当然,还可尝试对该遗址墓葬中的女性人骨及相关遗存进行检测,推测发病人数及其大致所占的比例。
医学物质遗存与人类行为关系的构建,离不开对人骨遗骸的检测分析。疾病是依附于人体而存在的,在考古遗存中一般无法发现“疾病”的直接物象,如何由遗尸获知其生前的患病情况、死亡原因等,离不开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的介入。根据其所患疾病的类型,可留意墓葬中是否有相关医疗用具、药材等,并分析导致这一疾病发生的原因,或许与其生前的饮食、生活环境、职业性质、基因等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构建起患者生前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职业、医药治疗等行为关系链。如通过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进行检测,发现其患有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心脏病、多发性胆石症、胆囊先天畸型、肺结核钙化病灶、血吸虫病、蛲虫及鞭虫感染等疾病,墓中还发现有辛夷、茅香、花椒、干姜、高良姜等治疗心痹的中草药,综合判断,墓主很可能是死于冠心病[20]。
中程理论于医学考古学的运用,最终体现在揭示医学物质遗存中蕴含的人类行为。这使得医学考古学不仅仅停留于医药遗存的发现与识别、医药器具的年代判断、古代疾病的发展历程等观察性的信息,而是希望建立医学物质遗存与人类行为、人群活动间的关系。此涉及药材的种植、采集与流通、中医药剂的配制、患者的医疗救治活动、医者的施医方式、医者医术的传承与培训、官方的医药管理措施、古人的日常养生活动等一系列人类医疗与康养行为,内容丰富而含义深刻。中程理论为医学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广博的视角。但需要注意的是,其目标的实现仅仅运用单一的方式是不够的,因为医学考古学本身即为多学科理念与方法的结合,其研究需经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而进行。例如:C(碳)、N(氮)同位素对古人食谱的分析之于营养及健康;植物考古学对药用植物的鉴定分析之于药材的种植或流通;实验考古学对药物药性的检测之于中医药剂的分析与配制,等等。在具体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或许还会有许多新的方法萌发,但此类尝试在某种程度上均离不开中程理论的有效指导。
(四)辩证法
辩证法于中医体现得亦是经典。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其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医的医学理论主要来自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核心是矛盾对立统一观念,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21]235这种对立统一的观念在中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皆是遵从这一理论。中医将阴阳二元对立统一的关系贯彻于生理病理之中,与人体寒热、气血、脏腑、表里、经络等相联系,指导针灸、诊脉、方剂等医学的具体实践。《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4]57-68扁鹊行医“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阳气盛,则损之而调阴,寒气盛,则损之而调阳,是以气脉调和,而邪气无所留矣”[22]142。五行学说认为天地万物由木、火、土、金、水构成,而人体以五脏为主,与五行相对应,如同五行的相生相克,五脏间的生克平衡被打破,人便会生病。但古代医学难以直观地观察人体器官的情况,通常以对人体外在的色脉来体察五脏的问题。中医对药物与食物特性的认识也是遵从辩证法的思维,将其划分为热性食物和凉性食物。众多药理调养等法则,亦是据辩证思想发展而来。
中医的精髓即为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 了解中医的基本医学理论则可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医学考古学中的医学遗存。 对于考古发现的药物遗存,运用中医辩证法的思维能较好地理解药材、 方剂。 在中医药剂中发现, 补阴之剂并非一味地滋腻, 补阳之剂也并不是一派辛热, 而是“阳中求阴、 阴中求阳”, 即在大部分或寒或热的药物中辅之以少量或热或寒的药物组成方剂, 这也是对立统一辩证思想的体现。 在山东巨野县西汉墓铜鼎中发现丸药一百五十余粒,呈颗粒状, 朱红色, 丸状物主要含有硅、 铁、 铝, 以铁、 铝为主的硅酸盐物质, 推测为五石散[23]。 根据文献记载, 五石散又称寒石散, 用于治疗伤寒病者, 因该药性子燥热, 故在服用此药后, 必须食用冷食来散热, 五石散的发明和使用充分体现了医学辩证法原理。
中医针灸疗法也是遵循辩证统一的思想。针刺需掌握气的往来顺逆盛衰之机,正气去叫作“逆”,正气来复叫作“顺”。正气已虚,则用补法,邪气盛,则用泻法,明白补泻之法,能用心体察,便是针灸之道。正如“其来不逢,其往不可追。……知其往来,要与之期。……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4]850-851。如在满城汉墓便发现有“九针”[24]116-118,九针形制不一,就是针对不同的病症以实现补泻之法。
二、医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哲学抽象,而方法则是理论的具体落实,是实践过程中可以直接使用的守则。医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其理论框架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体系组成。
(一)考古学基本方法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而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化因素分析日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李伯谦曾说过:“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一样,是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25]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医学考古学研究应主要遵循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相较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言,利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医学考古学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可直观反映古代医学发展情况的考古出土医用器具、药物遗存、医学文献等;二是与疾病相关的直接载体,如人类遗骸等;三是作为弘扬医药文化重要载体的医药名家遗迹。这三方面的内容,多是通过考古手段所获得的材料,其发现与研究首先离不开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具体而言,对医药物质文化遗存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发掘,此类医学遗存的考古学解读需要建立在科学的田野发掘基础之上,故而需要发挥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获取遗迹、遗物历史信息的综合作用。考古地层学一般指的是“地层堆积的层位上下、堆积时代的相对迟早关系研究”[26]。在考古地层学理论的指导下,对相关医学遗存的科学发掘,可以有效地获取医药遗存的出土地层、遗物放置位置、组合情况以及其与周边遗存的关系等信息,为构建医药遗存所存在的历史情境提供基础性材料。而考古类型学得以对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科学地展现医学遗存的形态变化过程、年代特征及演变规律等。如对于医用器具,通过考古类型学的分析,能够判断其年代早晚关系及形态的演化。透过这一外在的演进关系,可进一步揭示古代医学的变化发展过程。再如古代药物遗存,同样可运用类型学的方法,以分析古人对于药材药性、药剂配比的认识情况。同时,可运用区系类型学,确定在同一时间内、具有共同特征的医药遗存的分布范围,并在更大范围内划分不同中医医理、药理的分布地域,乃至中医疗法的地方类型。
在此基础上,“对跨时代、跨民族、跨区域、跨国家的考古遗存的研究,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可以较为清晰地解读同一考古文化事象中不同因素在时间上的传承与创新关系、不同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传播关系、文化互动关系以及文化融合关系”[27]。对所获得的资料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作梳理研究,有望揭示古代医学文化的传播、互动、融合关系,分析不同文化或不同地区之间的医药文化影响,进而推动医学起源及发展情况的探究和阐释,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医学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在中国范围内,除了传统汉医外,还包括藏医、蒙医、苗医、维医、壮医等民族医学。这些民族医学受当地自然、文化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医学理念和医技,对于它们的研究可运用文化因素分析并结合区系类型学的方法,揭示民族医学的文化特征、相互间的交流与传播。
医学考古学需要运用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科学地发掘医学遗存,确定医学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演变规律及区域特征,也离不开文化因素分析法以及区系类型学方法对不同医学文化间的交流互动进行分析。这些共同构成了医学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相互补充,为医学遗存更高层次内涵的揭示奠定基础。
(二)情境分析法
情境分析法由凯斯(Case)提出,伊恩·霍德(Ian Hodder)在凯斯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发展而来。情境是指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各种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围绕任何客体的变量的相关纬度的总和”[28]196。该分析方法主要强调的是“充分考虑遗存所在的特定历史情境,以及与情境内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使碎片化的遗存得以整合”[29]。考古学家可通过确定不同类型的相似和差异,建立不同类型的情境关联,然后从情境、关联和差异中扼要总结,以便获取功能和内容的意义[28]182。考古发掘出的遗物有其所处的单位、层位关系、遗物位置、摆放情况、共出器物、周边遗迹等情境,如果脱离了这些情境,就会丧失大量的信息,对遗物的解释将变得苍白。将物质遗存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其所反映的内在信息才可被认识。情境的理念应贯穿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阐释的全过程。在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应注重资料收集的全面性、科学性,同时,在资料的研究过程中也应树立情境意识,揭示其象征意义和深层内涵。通过借助物质遗存所有可利用的证据和信息,尽可能复原重构其存在和发生的背景,从而实现对物质遗存较为可靠的分析。
医学考古学研究过程中,注重情境分析法的运用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医学遗存的识别上。由于部分医学遗存其实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存在形制、用途及功能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为识别医学遗物带来了较大困难,需要通过确定遗存的时空关系、出土背景及其与周边遗迹的关系等判断其性质。如《素问·异法方宜论篇》中记载:“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4]115受自然环境及生活条件的影响,东方地区的先民相对多生痈疡一类的病,适合用砭石来治疗。而通过对时空背景、器物形制、墓葬规模、随葬品位置、墓主人性别、器物组合等方面情境的综合分析,推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东方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及其邻近地区,随葬的内盛有骨针或骨锥的穿孔龟甲很可能即是当时具有广泛标识作用的砭刺医用套具[29]。
对于医学遗存更多信息的揭示也需要运用情境分析法。通过对遗存的时间、空间、埋藏环境、类型、功能等信息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分析,从而获取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要素。如有些医药遗物多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墓葬中,这些遗物或为墓主生前所使用,或寄托着一种对健康的期许,或是墓主医者身份的体现……而这些情况的确认则需要分析其所处情境。在海昏侯墓葬中发现有“医工五禁汤”漆盘、中药材地黄等,这样的情境显示出该墓中大量的医药遗存应为其生前所使用的,而史料中关于该墓主生前疾病缠身的记载则印证了这一点[12]。上述藁城台西M14中出土有医药用具砭镰,还发现有卜骨三件,结合情境研判墓主应为“巫医”。对于不同的墓葬,由于医药遗物出土的情境不同,其所获得的与医学相关的信息也不一样。
因此,对遗迹、遗物进行情境分析,建立起遗存与各客体间的关系,对识别、揭示医药遗存的深层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三)现代科学技术方法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逐渐运用到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较完善的交叉学科体系——科技考古学[30],[31]10。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蕴含的信息十分丰富,仅凭借人的感官观察而获得相关信息是不充分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则有望实现最大化提取其中的潜在信息,且经过科技检测所获得的科学数据,信息通常更为客观、有效。
医学考古学涉及药物遗存的判定、古病理的诊断包括遗传性疾病的探研、古人食谱、寄生虫等内容的研究,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对相关信息的提取、检测。比如,在海昏侯M1所出木质漆盒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中药地黄炮制品实物,而这一信息的获取是通过核磁、三维重建、显微分析等科技手段而完成的[13]。又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哈民忙哈遗址发现大量人类遗骸,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利用古DNA技术对该遗址人骨及骸骨胸腔内土壤等进行宏基因组测序实验,可以定位当时遗址中细菌和真菌的种类,从而确定某些致病微生物,为揭开哈民忙哈遗址人群非正常死亡原因提供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证据[32]。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哈民忙哈遗址的先民可能经历过一次瘟疫的袭击,其聚落的消亡也应与此有关[33]。再如通过对郑州东赵遗址M50出土人骨的古病理分析,发现其患有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DISH),可能是中国目前最早的DISH病理之一,深化了对这一疾病的认识[34]。
另一方面,信息化时代的科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运用适应信息化发展要求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当下任何学科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医学领域,信息化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医学人文的信息化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数字健康人文”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数字健康人文是指“健康人文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即应用数字技术和计算工具来研究健康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也可以说是数字人文与健康人文的结合”[35]。数字健康人文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资料累积,而将大量有用的医学信息和数据进行系统整合,能够为医学考古学研究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资料整理和分析手段。医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结合,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对于定量分析较为欠缺,在医学考古学的框架下,需要以更加精准的数据和信息探讨医学话题,因此应注重对古代医学信息的搜集、整理,形成具有图谱化和可视化的数据系统,为医学考古学研究储备丰富的数据资源。
国外诸多学术机构已建立起了相关数据库,如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霍乱在线:文字和图像中的世界大流行》(Cholera online:A Modern Pandemic in Text and Images)、哈佛大学的《疫:历史视域下的疾病与流行病》(Contagion:Historical Views of Diseases and Epidemics)。目前,我国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信息化手段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如2018年开始加入“全球健康史项目”,该项目旨在探讨新石器时期以来人类的疾病史,以前所未有的大数据研究方式回顾近代人类的历史,来衡量人类的生活质量和人类在充满挑战的生活条件下的适应能力[36]。总之,随着医学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所获得的信息势必会更加丰富,能够有效推动建立医学考古学数据库,在数据库形成规模之后,也必然会实现信息化对于医学考古学研究的反哺,从而实现对古代医学更加系统和精准的认识。
由此可见,医学考古学需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医学遗存进行检测,如微痕分析、材质成分检测、同位素分析等,以获得科学的数据。并适时建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医学考古学数据库,来分析人类历史上的健康问题。
(四)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
医学考古学是考古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旨在通过医学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揭示古代医学发展情况、解读古代人类生命的延续。而这一目的的实现,除了有大量的考古实物资料外,还需要众多的医学文献资料。医学考古材料和医学文献资料均是古代医学活动的产物,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医学考古材料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实物,具有可信性和具象的特点。但医学考古材料多数较零碎,要通过碎片化的考古材料揭示其所蕴含的医学信息是较为困难的。而古代医学文献资料丰富,并且多为系统的描述与解释,两者可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共同推进医学考古学的深入研究。
考古实物资料与文献的结合利于医学信息的揭示。考古发掘的医学遗存是古代人类活动的物化载体,但是仅凭直观的体察只能获知如年代、材质、工艺、形制等表层的信息,而其内在的功能及所包含的医学活动、社会关系、思想意识等隐性内容,在运用历史想象方法的同时,利用文献资料加以研究必不可少。我国医学文献资料丰富,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千金方》《脉经》《肘后备急方》《本草纲目》等,所包含的医学内容相当丰富。一些古代史籍中也涉及有医学内容。这些文献资料均可作为医学考古学研究的文献依托。前述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九针”,有四枚金针、五枚银针,形制不一[24]116-118。而据《黄帝内经·灵枢·九针》知,九针即为鑱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且关于其形制、尺寸、用法也有详细说明[4]1430。便完全明白了此“九针”所对应的名称与具体用途。
医学考古学实物资料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中, 出土医学文献应予以足够重视。 长期以来的考古发掘已使得出土医学文献有了相当的积累。 殷墟甲骨文中就发现了较丰富的医学内容。 又如睡虎地秦墓竹简、 周家台秦墓“医方”简、 马王堆汉墓医学帛书、 武威汉代医简、 张家山汉代医简、 老官山汉墓医简、 阜阳双古堆汉墓医简等。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出土医学文献会愈益增多。这些出土医学文献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有对疾病的认识、药方、针灸、经络、养生、行气、导引等内容,是了解中国古代医学的直观资料。其一方面可与史籍文献相对应,具有证经补史的作用;一方面也可与医学遗存相印证,以获得更丰富的医学认知。历史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实物三者的有机结合,方能更好地实施医学考古学的研究。在成都老官山汉墓发现的经络髹漆人像,其上标有经络线,包括22条红色粗线、29条白色细阴线、119个穴位点,并有多处刻文[37]。 这些经络、 穴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与该遗址出土的简牍《经脉书》《五色脉诊》《脉数》、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 以及医书文献《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相对应,使我们充分理解经络、穴位的位置、功能、针灸疗法等医学信息。
三、余 言
考古学研究不仅仅是与古人对话,更是要启迪当下。从古至今,人类经历了无数次严重疾病的冲击,能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健康对于古往今来的人类皆无比重要。每一个学科都负有对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探索的使命。考古学研究也需要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把我国医学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出来。
考古学和医学的交叉研究,进化论、系统论等理论和考古学基本方法、现代科学技术等方法的综合应用,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积极对话和有机融合。在此意义上,医学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人类生命的致敬。通过学科的交叉融合,进一步客观、真实地揭示古代医药的起源与发展情况,深入认识古代医药文化,推进传统医药与现代科学的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38]。著名药学家屠呦呦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一定启发,从中国医药学宝库中发掘出惠及人类的抗疟疾新药青蒿素,即为科学研究面向现实、服务现实的具体实践[39];对中国古代的防疫抗灾进行伦理学思考,则有助于了解古代灾疫疾病防控的发展历程,同时为当前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40]。我们希望通过医学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和研究领域,以其所有可以获得的研究理论、方法和成果对人类生命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理解,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考古学的力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