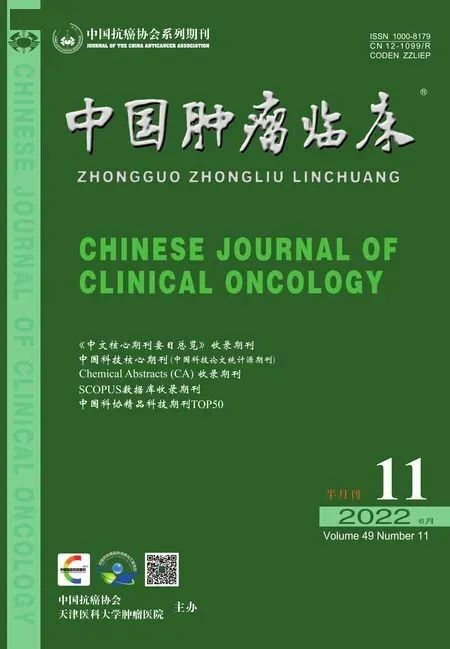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与IDH1及1p/19q对脑胶质瘤患者假性进展的诊断价值*
张宝双 周欢娣② 王国辉② 综述 薛晓英 审校
脑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原发肿瘤,约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27%[1]。自术后联合放化疗作为胶质瘤治疗的必要手段以来,其预后得到了改善,这也使得治疗相关的影像学表现有所增加。MRI的假性进展(pseudoprogression,PSP)影像学特征表现对比增强、范围扩大等现象,类似早期进展(early progression,EP)的影像学改变,但本质是治疗后反应[2]。临床上将这种在肿瘤非EP情况下MRI表现出的短暂对比增强或范围增大,伴或不伴T2WI和FLAIR像的异常改变定义为PSP。病理学及影像学随访可诊断PSP,但两者或因颅内标本的可获得性差,或因影像学随访的不及时,均不能满足临床及时诊断的需求,成为影响疗效的难题,亟需无创且及时的PSP诊断方法。PSP的发生除与治疗有关外,也与肿瘤自身的分子特征,如与MGMT启动子甲基化、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以及1p/19q等有关。本研究将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MGMT启动子、IDH1及1p/19q分子标记物在区分脑胶质瘤PSP与EP中的价值,为精准医疗提供参考。
1 PSP概述
1.1 PSP的发生机制及时间
PSP的发生机制较为复杂,一些假说认为PSP是多种治疗因素对肿瘤区域及其附近的血脑屏障功能造成的破坏,从而会在MRI增强扫描时出现强化影像[3-4]。脑胶质瘤患者放疗后PSP发生的时间尚未形成共识,近期一项研究发现,PSP发生的中位时间为放疗后1个月[4]。一项纳入941例脑胶质瘤患者的研究发现, PSP发生的中位时间为放疗后6~12个月[5]。由于PSP通常无症状,导致影像学随访不及时,可能是造成PSP发生时间报道差异的原因之一。
1.2 PSP的发生率
关于PSP发生率的报道相差较大。Chaskis等[6]研究发现,PSP在脑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GBM)患者中的发生率为6%。而Brandsma等[7]的报道中PSP在GBM中的发生率高达64%。关于低级别脑胶质瘤患者PSP发生率也有报道,在van West等[8]的研究中71例低级别胶质瘤患者PSP的发生率为18.3%。不同研究PSP的发生率相差较大,Abbasi等[9]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统一的PSP评判标准。
1.3 鉴别诊断
PSP现象主要与放射性坏死间的鉴别存在困难,常规的影像学检查并不能区分,只能通过病理学鉴别。放射性坏死与PSP同样影响着对于EP的诊断,区分三者的“金标准”仍然是病理学。有研究认为,放射性坏死与PSP的主要区别在于放射性坏死为不可逆的放射性损伤,而PSP为可逆的放射性损伤[4]。此外PSP与放射性坏死还存在以下的区别:1)PSP的出现时间较早,多数发生在放疗后6个月内;放射性坏死发生的时间较晚,多数发生在放疗后12~18个月[10]。2)PSP患者多数无症状,无需处理;放射性坏死患者症状通常较重,需要更多的类固醇激素干预且必要时需手术[10]。3)在影像学检查中,放射性坏死通常出现在脑室周围并且呈多中心结节状表现;相比之下,PSP主要在肿瘤术腔周围形成环形强化结构[4]。由于PSP与放射性坏死均影响着对于EP的判断,因此提高对三者的认识,可避免不必要的治疗。
2 影像学新技术诊断脑胶质瘤PSP的研究进展
MRI是诊断PSP最常用的方法,常规的MRI序列很难准确诊断PSP。近年来,更多的研究使用多模态MRI来提高PSP的诊断。
2.1 扩散加权磁共振成像
扩散加权磁共振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可检测组织内的水分子运动,在DWI中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与水分子弥散速度呈正比,而与细胞密度呈反比[11]。脑胶质瘤EP表现为细胞增多,而PSP表现为组织的坏死和炎性水肿,因此EP的ADC值低于PSP的ADC值。一项纳入26项研究共900例GBM患者的Meta分析[12]提示,DWI在诊断PSP方面具有较高的性能,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8%和85%。
2.2 磁共振波谱
磁共振波谱(MR spectrum,MRS)可无创探测细胞代谢产物,如胆碱(Cho)、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及肌酸(Cr)等。脑胶质瘤EP时Cho峰增高,而PSP时Cho峰降低。申小明等[13]研究发现,脑胶质瘤EP组异常强化区Cho/Cr值明显高于PSP组异常强化区的Cho/Cr值,鉴别EP与PSP的准确性为82.5%。
2.3 MR灌注成像
肿瘤复发伴随着血管形成,而脑胶质瘤PSP时仅引起血管通透性改变,故可采用MR灌注成像诊断PSP。PSP时PWI表现为低相对血容量(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rCBV)和低相对血流量(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rCBF),而在EP中表现为高rCBV和高rCBF。一项纳入26项研究共900例GBM患者的Meta分析[12]提示,PWI诊断PSP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和79%。
2.4 PET
脑胶质瘤EP时18F-FDG的摄取量高于PSP,据此诊断PSP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14]。肿瘤细胞生长除需要葡萄糖外,还消耗大量氨基酸。氨基酸代谢PET显像,如11C-蛋氨酸[15]、18F-氟酪氨酸乙酯[16]等对诊断胶质瘤PSP同样具有价值。有研究发现,氨基酸示踪剂诊断胶质瘤PSP的准确性高于MRI[17]。PET虽敏感度高,但费用较昂贵,未能广泛用于临床。
2.5 影像组学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影像组学可以从医学图像中提取大量数据。Elshafeey等[18]通过研究MR灌注的放射学特征诊断PSP,发现该模型在诊断PSP方面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为诊断脑胶质瘤PSP提供了新方法。影像基因组学还能对肿瘤mRNA表达情况、肿瘤分子亚型等进行分析。影像组学有望为精准医疗提供新途径。
3 分子标记物在诊断脑胶质瘤患者PSP中的价值
由于PSP重要的临床价值,研究者们不断探索其他诊断途径,发现脑胶质瘤的分子特征,尤其是MGMT启动子、IDH1、1p/19q等分子状态与PSP明显相关。
3.1 MGMT启动子诊断PSP的价值
3.1.1 相关性 MGMT启动子是脑胶质瘤备受关注的分子之一,可为胶质瘤患者预后提供参考[19]。MGMT是一种DNA修复酶,可将O6-甲基鸟嘌呤的甲基转移至自身半胱氨酸残基上,以去除DNA链中被异常甲基化的鸟嘌呤的氧六位甲基,使DNA损伤得以修复。替莫唑胺(TMZ)抗肿瘤的机制是通过烷基化DNA分子上鸟嘌呤第6位O原子和第7位N原子,发挥细胞毒性作用[20]。MGMT可修复被TMZ烷基化的肿瘤DNA,从而导致治疗失败。MGMT启动子甲基化可导致MGMT转录的沉默,从而使烷化剂更好地发挥抗肿瘤作用。因此MGMT启动子甲基化的脑胶质瘤患者比MGMT启动子非甲基化者经过TMZ治疗后会更有效[21]。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MGMT启动子甲基化的脑胶质瘤患者比MGMT启动子非甲基化者放化疗后更易发生PSP[22-23],这可能是由于MGMT启动子甲基化的患者对放化疗更敏感,加重了放疗介导的放射性损伤。Park等[24]研究发现,PSP的发生率在MGMT启动子甲基化的脑胶质瘤中为61.5%,高于MGMT启动子未甲基化者的33.9%(P=0.006)。为进一步证明MGMT启动子与PSP的关系,Zhou等[23]进行了Meta分析,纳入13项研究共536例高级别脑胶质瘤患者,提示MGMT启动子甲基化在区分PSP与EP之间具有显著性相关(OR=4.02,95%CI=2.76~5.87,P<0.001)。
3.1.2 MGMT启动子在诊断PSP中的应用 如上所述,MGMT启动子的甲基化状态与PSP相关,但仅靠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尚不足以对PSP进行诊断。有研究将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与影像学技术相结合,在区分PSP与EP方面进行深入探索。Bani-Sadr等[25]回顾性分析了33例治疗后出现早期影像学进展(EP或PSP)的GBM患者,研究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和患者在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MRI成像中(MSC-MRI)的rCBV和相对渗透率rK2(relative vessel permeability on K2 maps)的相关特点,发现PSP与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rCBV及rK2具有显著性相关。基于rCBV、rK2及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与EP和PSP的关系,建立以rCBV、rK2及MGMT启动子甲基化为基础的联合诊断模型,将出现影像学进展的33例GBM患者中满足MGMT启动子甲基化且rCBV<1.75的4例患者归为PSP,将满足MGMT启动子未甲基化且rCBV≥1.75的16例患者归为EP,而在其他13例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与rCBV值相矛盾的患者中(即患者的MGMT启动子甲基化但rCBV≥1.75,或MGMT启动子未甲基化但rCBV<1.75),将rK2≥27的8例患者中的7例及rK2<27的5例患者中的3例归为EP,其余3例归为PSP。按照上述联合诊断模型区分EP与PSP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得分为0.94,明显优于单独利用rCBV≥1.75(AUC=0.82)、rK2≥27(AUC=0.74)和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AUC=0.77)单一标准的AUC值。将脑胶质瘤患者的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与影像学技术相结合,在区分PSP与EP中有广阔的前景,但现有的研究均为回顾性研究,仍需要前瞻性研究进行验证,同时探索其相应的内在机制,构建更加合理的联合诊断模型。
3.2 IDH-1基因对PSP的诊断价值
IDH-1基因为三羧酸循环的限速酶,参与人体的产能过程,其同工酶有3种形式,即IDH-1、IDH-2和IDH-3。IDH基因突变是脑胶质瘤发生过程中的早期事件,主要发生在低级别胶质瘤和继发性GBM中,其中IDH1突变最为常见(80%~90%),IDH2突变较为少见(约3%),而IDH3突变尚未在胶质瘤中发现[26]。IDH突变与脑胶质瘤的预后有着密切的关系,IDH突变的胶质瘤患者有更好的总生存期[27]。因此,在2021版世界卫生组织(WHO)星形胶质细胞瘤分类中将具有微血管增生、坏死和(或)特定的分子特征,如TERT启动子突变、EGFR基因扩增和(或)7号染色体扩增/10号染色体缺失的成人IDH野生型弥漫星形胶质细胞瘤诊断为GBM伴IDH野生型;IDH突变的GBM被称为IDH突变的星形细胞瘤WHO Ⅳ级;所有IDH突变型弥漫性星形细胞肿瘤被认为是同一类型,分为CNS WHO 2、3或4级。
IDH1基因突变与胶质瘤患者PSP的发生相关,但不同的研究显示两者的关联度差别较大。Li等[28]分析了145例GBM患者,发现IDH1基因突变的GBM更易发生PSP(P<0.001),IDH1诊断PSP的敏感度为34.2%,特异度为97.3%。Zhou等[23]研究的一项Meta分析提示IDH1基因突变在区分PSP与EP时具有显著相关性(OR=12.78,95%CI=3.86~42.35,P<0.001),与Li等[28]研究结果一致。
IDH1突变与PSP的关系同样存在相反的结果。Mohammadi等[3]对来自4个医疗机构的多中心研究发现,IDH1突变的患者发生PSP的概率更低(P=0.008)。进一步分析发现9例患者(1例IDH1突变型和8例IDH1野生型)诊断为EP,17例(3例IDH1突变型和14例IDH1野生型)诊断为PSP(P=0.004);在出现影像学进展的26例患者中,IDH1突变的患者中PSP占影像学进展的75%(3/4),IDH1野生型患者中PSP占影像学进展的63.6%(14/22),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96)。上述结果表明,无论GBM的何种亚型,在完成放疗后的90 d内,PSP的发生比EP更有可能性,尽管PSP的发生率在IDH1突变患者中绝对值更低,但相似的相对PSP发生率被证明继续当前的辅助治疗是有意义的,尤其是IDH1突变的患者;因此在放疗结束后的90 d内若怀疑IDH1突变的脑胶质瘤患者出现影像学进展,应当继续当前的辅助治疗。Lin等[29]的研究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关于IDH1突变与PSP发生之间的关系尚不确定,但较为肯定的是IDH1基因状态对PSP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影响,仍需更多的研究探索其内在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中对PSP的诊断。
3.3 1p/19q基因对PSP的诊断价值
1p/19q联合性缺失主要发生在低级别和间变性的脑胶质瘤中,是少突胶质细胞瘤(oligodendrogliomas,OG)与星形细胞瘤(oligoastrocytomas,OA)鉴别的主要依据。研究显示,伴有1p/19q联合性缺失的脑胶质瘤患者对放疗及化疗较敏感,因此1p/19q联合性缺失可作为提前判断脑胶质瘤疗效的标准之一[30]。
脑胶质瘤患者PSP的发生与其1p/19q联合性缺失与否相关。Lin等[29]的一项纳入143例OG和混合少突星形细胞瘤(mixed oligoastrocytomas,MOA)患者的研究发现,PSP的发生率在1p/19q非缺失的患者中比1p/19q联合性缺失患者更高(27% vs. 8%),其诊断PSP的敏感度为60%,特异度为67%。该研究认为1p/19q非缺失的OG和MOA患者在放疗后的6个月内出现影像学进展时主要为PSP。目前关于1p/19q基因与PSP发生关系的研究有限,为了更好地发挥1p/19q基因在诊断PSP中的作用,仍需更多的研究。
4 结语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IDHl基因类型、1p/19q基因缺失情况对鉴别PSP与EP有潜在的价值,多种分子特征与PSP和EP等影像学改变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成为关注的热点。随着对脑胶质瘤分子特征认识的逐渐深入,以及临床医师对脑胶质瘤患者PSP现象的不断了解,将分子标记物与影像组学技术结合,建立联合的预测和鉴别模型有望成为区别PSP与EP的有效手段,但要真正应用于临床仍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