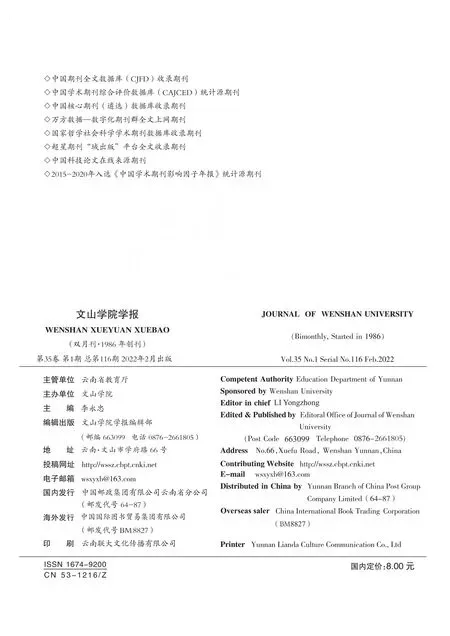论《赎罪》的后现代创伤叙事
黄伟龙
(内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内江 641100)
《赎罪》是英国作家伊因·麦克尤恩中后期创作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讲述了叙述者布里奥妮年少铸成大错而终其余生进行自我救赎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创伤主题作品。赎罪本义为抵消所犯的罪恶,是对创伤事件的匡正与弥补,传达了创伤治愈的意图,是创伤积极应对的题中之义。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赎罪》进行了创伤主题的研究,不少研究者从创伤理论出发,分析《赎罪》等作品中创伤表现形式(个体创伤、家庭创伤、社会创伤、文化创伤)及创伤演化,分析创伤体验对个体或群体造成的困境,并关注作品中创伤救赎的可能性和创伤治愈的范式。[1]108-111也有许多学者运用叙事理论,研究《赎罪》中的元小说、非线性叙事、互文等特征,分析这些叙事策略下的叙事意图和文本效果。但后现代叙事策略和创伤主题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待澄清。本文拟分析后现代叙事与小说《赎罪》的创伤主题之间的关系,从文本指涉、叙述视觉拼贴、多种全知视角的切换等方面剖析小说中个体创伤、家庭创伤与社会创伤,梳理后现代创伤叙事策略参与到现代社会多元创作主题表达的叙事方式。
一、扉页引语文本指涉:误读创伤的期待视野
扉页引语是读者进入小说正文本的门槛,预示了小说中人物的误读创伤。误读导致布里奥妮指控罗比,在此有必要了解布里奥妮的误读性话语。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有多种人物视角的全知叙述,人物与人物的心理活动差异、他们对事物的认知悬殊与当时的环境、人物性格和教育背景有很大的关联。罗比和赛西莉娅的叙述视角叙述中,展现的是一对年轻人罗比·特纳和赛西莉娅冲破世俗阶级观念,追求爱情幸福的行为。在未成年的布里奥妮的视角中,她在窗前看到了姐姐塞西莉娅当众脱下衣服跳入水池中的情景,颠覆了她以往对跨越门第爱情的童话故事的认知。布里奥妮在潜意识中希冀罗比对塞西莉娅求爱,正如贫民王子和公主的爱情一般,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她所理解的罗比对塞西莉娅的摆布和欺侮。正如她所述,“这般跨越门第的爱情,每天都该有不少吧。”[2]43但喷水前的一幕却是另外一幅场景。“罗比高傲地抬起一只手,仿佛正向塞西莉娅发号施令”,而姐姐却屈从于他“飞快地脱去自己的衣服”。[2]43这一幕,布里奥妮为罗比羞辱姐姐的行为所震惊。
误读在布里奥妮无意中偷看罗比写给姐姐的带有色情内容的情书后又一次加深。从信件中获得确凿证据后,布里奥妮又机缘巧合瞥见到书房中的罗比与赛西莉娅性爱的一幕,使得布里奥妮对罗比的偏见越来越深。最后,布里奥妮在个体认知的偏差下,将具有“色情狂”特征的罗比理所当然认定为一宗强奸案的施暴者。因此,误读在创伤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误读给受创主体所造成的个体创伤也可以称之为误读话语创伤。
误读不仅仅是解读《赎罪》中赎罪主题的重要线索,也是作品中创伤故事框架中必要元素。《赎罪》标题无法为读者揭示这一线索或元素,但麦克尤恩在扉页中有意插入一段具有“误读”话语的引语,既是对正文中误读话语的一种呼应,也是刻意在创设一种关于误读的期待视野。让我们来看看扉页中简·奥斯丁《诺桑觉寺》的一段文字是如何与“误读”相关的。“亲爱的莫兰小姐,你好好想想,你这样疑神疑鬼有多么的可怕。你凭什么下此断论?……倘若犯下了暴行能不为人所知吗?亲爱的莫兰小姐,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2]1麦克尤恩的这些做法契合了热奈特的说法,一本小说也可以成为另一部小说的副文本,成为进入正文本的“门槛”。扉页引语在功能上类似于自序之副文本,具有阐释正文本的功能,刻意帮助读者更好地接近文本意义或者作者意图。扉页引语作为麦克尤恩的特殊提示,无疑为读者进入小说正文本打开了一条通道。阅读扉页引语会使读者产生对正文本的“期待视野”。接受理论代表人物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这一概念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秘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升一种特殊的感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点的情感态度中”。[3]扉页引语为“理想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审美经验性质的”文学期待视域。在《赎罪》中,扉页引语通过亨利在小说中的直接引语陈述了他对莫兰小姐那丰富的哥特式想象的评价。在《诺桑觉寺》中,莫兰小姐对哥特式小说的喜爱让她嵌入到哥特式想象世界中,将人性美好一面的亨利无端地想象为谋害妻子的凶手。相比之下,布里奥妮把罗比误读为“色情狂”,亲手将罗比送进监狱,这似乎比莫兰小姐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两位女性人物的惊人相似性在于文学的酷爱所带来的哥特式想象。这两位人物都将好人误认为恶人,与她们耽溺于文学想象不无关系,因为那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并可能引发危险后果文学想象力。构建扉页引语的互文特征,麦克尤恩为读者开启了性格缺陷所导致误读话语的期待视野,为书写人物的创伤拉开了序幕。一言以蔽之,扉页引语让读者对布里奥妮的误读产生一种期待视野,因而引语作为一种副文本兼互文手段,对叙事主题中误读创伤的“呈示”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二、叙述视角的拼贴
如上所述,扉页引语可以在读者心中激起误读创伤的期待视野。而小说中叙述视角的拼贴则深入地参与到创伤故事的书写与创伤主题的表达上。叙述视角的拼贴指的是叙述视角的反复切换、以布里奥妮为主导的叙述视角在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分离和重合,其使得文本叙述出现故事重述、文本空隙与填补、叙述干预和预叙。叙述视角的拼贴导致叙事文本碎片的拼贴,使得创伤故事的言说出现延宕、延迟特征,是创伤言说、后现代文本的典型特征。
在小说的第一叙事单元,以经验自我为主导的叙事视角实质上夹杂着叙述自我的叙述干预,使得创伤言说出现延宕、创伤故事悲剧化等特征:经验自我以少年的布里奥妮为视角,回忆往昔的创伤事件来进行创伤言说,但经验自我叙述中时常夹杂着以成年布里奥妮为视角的评论性话语,使得小说文本出现叙述干预、预叙等后现代文本特征,展现布里奥妮创伤言说欲言又止、往事难以平复的复杂创伤心理,增加了创伤故事的张力和悲剧性。其次,多种全知叙述视角在第一叙事单元内部的切换解构了传统的、单一的宏大创伤叙事结构,不同叙事单元中叙事背景的离散、叙事视角的多元使得个体创伤去中心化,创伤意义在家庭、社会、战争维度下变得多元,使得个体创伤与家庭创伤、战争创伤、社会创伤巧妙融合,后现代创伤叙事策略深入地参与到现代社会多元创伤主题的表达之中。
(一)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分离和重合
小说《赎罪》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方式,可以分为四个叙事部分。第一部分可以窥见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多元化,以不同人物的全知视角对同一事件进行故事片段的叙述,这些叙述因为人物视角和人物认知能力受限等因素,使得重叠的故事情节出现差异。而恰好是故事内容的重叠与差异,给读者留下了文本意义建构的悬念空间。小说的第一叙事单元包含14章,涵盖布里奥妮、赛西莉娅、罗比母亲艾米丽、表妹罗拉等人物的叙述视角,对当时人物的见闻、感受进行大量心理活动的描写。其中布里奥妮的叙述视角高居5次,是最为重要的叙述视角,也从侧面揭示了人物布里奥妮的隐含作者身份和对叙述人物的操控。不过,第一叙事单元中,布里奥妮尚未成年,只能以未成年的视角来回顾整个事件,采取了经验自我的叙述形式。在这一叙事单元中,未成年布里奥妮的叙述视角还原了她年幼时的复杂、孤僻的心理活动。通过经验自我的叙述视角,读者直抵少年布里奥妮的内心世界,对人物的性格缺陷和文学想象力有着直观的体验。这种叙事方式是对创伤事件的忠实描述,增加了创伤事件的亲历性和逼真性,是叙述者努力通过创伤言说走出创伤阴霾的重要手段。
除了经验自我,叙述自我视角也在小说中出现过。以布里奥妮为视角的叙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未成年的布里奥妮的眼光来追忆往事,展开叙述的,可称之为经验自我,另一类是以成年的布里奥妮的视角来观察往事,可称之为叙述自我。第二类叙述视角“叙述自我视角”主要在第三叙事单元、第四叙事单元中出现,讲述了布里奥妮如何通过参与医护工作与通过写作来救赎的故事。可以说,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在不同叙事单元中的作用有所不同:经验自我主要是完成创伤言说,而叙述自我主要是讲述如何通过后续的努力来进行创伤修复的,体现了叙述视角分离在创伤主题上不同的叙事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在第一叙事单元中也出现重合,即叙述自我视角突然插入经验自我视角,使得正常的叙事进程出现打断。它主要体现为预叙和叙述干预,对于创伤主题的表达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叙述干预对于人物的创伤性性格与情节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她那时本可以走进屋子,依偎在妈妈身边,把这一天发生的事都给妈妈听。如果这样做了,后来也就不会铸下大错。很多事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发生。”[2]180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后来也就不会铸下大错”道出了布里奥妮对错误决定导致严重创伤行为充满懊恼和后悔,间接表达了创伤施行后的不安与悔恨;其二,它明确指出布里奥妮性格上的缺陷和认知偏差是她走向歧途的原因。从布里奥妮的心理活动中,可以得知布里奥妮认定“童话故事已不再属于她”,“此时她所要做的是找到事实真相,不仅仅是动机缘由,还有解开谜团的办法。这就对得起她的新的认识了”。[2]177布里奥妮宁愿将自己固封在哥特式想象中,生成对罗比的误读心理;在现实层面,布里奥妮在关键事件上亦没有与母亲进行交流,使得悲剧最终发生。
其次,有关故事情节的预叙直接交代了人物命运,增添了小说的悲剧意蕴。在悲剧性事件发生之前,成年的布里奥妮视角再次穿越,对未来半个小时的故事结局进行了预叙。“再过半个小时,布里奥妮就将犯下罪行了。”[2]这一句话揭示了人物悲剧即将到来。在文本结构方面,叙述干预与其他叙事要素之间存在潜在的联系,这或者是一种互动关系。如果说扉页引语是激活误读创伤的期待视野,那么这句话便是直接交代误读创伤,道出了误读罪行的必然性。
此外,采用成年的布里奥妮的视角,也实现了当下的她对过往错误抉择的灵魂拷问。这种拷问虽然是自省式的,似乎是对过去行为方式的缘由进行澄清,也似乎在回答一个问题。实际上这是急迫与读者互动交流的一种表现。“她永远也不能安慰自己说,这么做是迫于压力,是被威逼的。现在也不能这么讲。她跳进的是自己挖的陷阱,她走入的是亲手搭建的迷宫。她太年轻了,太畏惧了,太想讨好人了,所以没能坚持到底,撤回诉讼。”[2]190这体现了叙述自我视角强行介入经验自我视角,急迫希望通过与读者进行交流沟通来表达叙述自我视角对事件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叙述干预是叙述自我借此澄清当初错误抉择、年纪幼稚、性格弱点的之间的关联,从而强化读者对年轻的布里奥妮的认知,进一步赢得读者对主人公创伤心结的同情,希望通过赢得读者的同情来进行创伤修复。因此,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重合体现了叙述干预,这种干预也是创伤修复的手段。
(二)全知叙述视角的切换:传统宏大叙事解构效应下个体创伤的去中心化
多种全知叙述视角在第一叙事单元内部的切换,解构了传统的、单一的宏大创伤叙事结构,不同叙事单元中叙事背景的离散、叙事视角的多元使得个体创伤去中心化,创伤意义在家庭、社会、战争维度下变得多元,使得个体创伤与家庭创伤、战争创伤、社会创伤巧妙融合,后现代创伤叙事策略深入地参与到现代社会多元创伤主题的表达之中。
不同叙事单元中叙事背景的离散是小说后现代创伤叙事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一叙事单元以英国二战前夕没落的庄园为背景,从不同人物的叙述视角展现了普通人物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创伤。第二叙事单元以二战战场为叙事背景,通过罗比的视角描述了二战战争的死亡和战争本身的残酷与恐怖。第三叙事单元的背景设定在医院,通过布里奥妮的视角描述了二战期间的护士工作的艰辛无畏和士兵生命临终前的心灵脆弱无助,从另一层面间接回应了人类战争的残酷与无情。这些叙事背景彼此独立分散,使得个体创伤意义延伸到战争创伤和政治创伤,呈现了后现代社会无序、混乱的生存状态。
在小说的第一部,除了有叙述自我的视角,不同人物视角的转化也是小说的叙事特点之一。通过布里奥妮、塞西莉娅的视角,塔利斯太太、罗比等多人的视角,读者在对同一事件的重复叙述中不仅了解了创伤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清晰地把握了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性格与价值观念。这些视角相互交织,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件进行差异化的叙述,从而引导读者对个体创伤进行重读。
事实上,叙述视角的转化不仅揭示了布里奥妮性格缺陷所导致的个体性创伤,而且有效地隐射了战前、战后英国社会的家庭创伤。布里奥妮所处时代的家庭创伤与社会创伤无形之中影响了未成年布里奥妮的认知,而且这种深层次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流逝非但没有消逝,反而愈演愈烈,成为整个创伤社会的缩影,使得多元创伤的主题极为明显。
叙述视角的转化可以清晰地展现塔利斯太太一家家庭秩序的瓦解。从布里奥妮的叙述中,可以得知父亲缺场对她的认知判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姐姐塞西莉娅的视角中,可以了解到塞西莉娅与母亲在价值观上的对立。塞西莉娅是追求自由、知性的新女性代表人物,而母亲却急于为塞西莉娅择选门当户对的女婿。从小说中,可以得知母亲对塞西莉娅与罗比的恋情一无所知。同时,母亲困囿病床,竭力靠声音来“看”这个家。然而,整个家庭秩序时而混乱不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塞西莉娅视角下,母亲与家庭仆人的冲突显示出家庭秩序瓦解下的紧张人际关系。可以看出,家庭秩序趋于瓦解的背景下,无论是母亲还是塞西莉娅,都无法有效承担监管未成年布里奥妮的职责,这导致了布里奥妮最终徘徊于现实和文学想象力之中,无法洞悉现实社会与童话世界之间的细微差别。
三、结语
麦克尤恩的中后期作品中的创伤叙事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创伤叙事在宏大的政治、社会、历史框架中融合个体创伤、社会创伤、历史创作、政治创伤、战争创伤等多元创伤元素,并采用了元小说,非线性叙事、互文、不可靠叙述等后现代叙事技艺。《赎罪》这部小说具有互文、叙述视觉拼贴,预叙等后现代文本特征,某后现代叙事策略使得文本意义变得不稳定,与后现代社会的破碎、混乱和多元化遥相呼应,大大增强了创伤故事的悲剧性,深化了现代社会多元创伤主题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