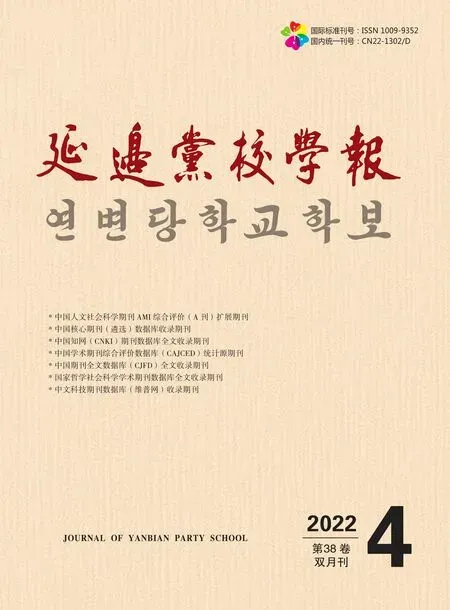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内蕴联系
张晓琴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习近平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革命先驱不畏艰险、筚路蓝缕,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1]。伟大建党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思想结晶,它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底蕴厚重、根基扎实,这表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巨大的涵养功效。因此,探析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蕴联系,对于解读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建党精神以及奋力实现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根植于“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基石,自“红船精神”起,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目标,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更传承于古代“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成为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的关键所在,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唐虞盛世的美好夙愿而不懈努力。
“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古已有之,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华民族就有了以禅让制为代表的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理想社会雏形。在《礼记·礼远》篇中,儒家先贤孔子首次为大同做了定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到了近代,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表达了不同的“天下大同”的夙愿。康有为的《大同书》便是极具乌托邦元素的理想社会书籍,在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暴力机构,取代国家的将是“全地大同公政府”。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则认为,要把儒家思想的“仁”作为基础,将其中的同类意识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实现“大同社会”的根本动力。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认为,谋求民族独立实则是为了更好地讲世界主义,“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并最终实现大同社会。
古代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相容相通的共性,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与理念内容。因此,在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建党复兴之路。李大钊最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并将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社会大同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并提出了“新亚细主义”的设想,他指出,凡亚细亚的民族都应当联合起来,与欧美三足鼎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合,实现人民的幸福。同时,他还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2]这就是说,大同社会的世界形式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它需要一步一步地实现,并且应当有科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书信中提到“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3]在《人民民主专政》中,他还用大同一词来指代共产主义,这就说明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可以说,大同理想是共产主义理想之源,共产主义理想是大同理想之魂。
古往今来,大同社会的时代内涵尽管不断发生改变,但其中心主旨一直都是致力于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所不同的是,古代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在地域上只限于中国,在实质上只是一种知识分子或者圣人对于美好社会的憧憬,并没有可行性以及现实性。到近代,知识分子在怀揣最初“天下为公”的理想时,吸收了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仍然带有很大的空想性质。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产主义理想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相结合,并且具有革命精神与实践导向,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承袭于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
以红船精神为发轫,中国共产党人涵养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可以说,一部有血有肉的党史正是一部践行初心与使命的共产党人奋斗史,无论是早期的建党创始人,如:南陈北李、毛泽东、蔡和森等,还是走在抗疫一线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扎根贫困地区四十载将其终身奉献给人民教育事业的张桂梅,他们的事迹无不彰显出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而这种初心与使命正是源自于我国古代的“家国情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国”与“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一点可从“国”与“家”的文字渊源中得到说明。“国”最早在甲骨文中写作“國”。在《说文·囗部》: “國”是一个会意字,有通过武力守卫领土之意。因此,“國”最初表示疆域之义,后来被引申为邦国或者诸侯国。“家”在《说文·宀部》中的含义就是居住的地方。在甲骨文中,家表示豢养生猪的居所,此外也有家族之义,在古代,大夫治理之地也称为家。因此,“国”与“家”不仅渊源流长,关系可谓十分紧密。“家国情怀”包含有“爱国如家”和“治国如家”的文化内涵。首先,“爱国如家”就是要以自身贡献国家,这样就可以使父母享有君子的美誉[5]。由此可见,对父母的孝顺,要通过对国家的忠心来实现。其次,“治国如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家国情怀”,就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像治理自己的家一样。因此,从古代起,家庭与国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家国情怀”要求个人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理想之中。
“家国情怀”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追求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初心与使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对于无产阶级者来说,其历史使命就在于实现自身的解放,也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正是在无产阶级使命意识与爱国情怀的双重影响下,共产党人艰难地为国家寻找出路。革命先辈李大钊自1907年中学毕业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发表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中表明他已经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方向。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便暗暗下定决心要救亡图存,并意识到要打破独断思想,重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他在湖南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建党建团等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1920年远赴欧洲求学,在他的三封家书中,明确表达了追求信仰,要为中国寻找适合道路的决心[6]。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主义”的较量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个致力于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主义”,而革命先驱能够以大家为小家,于风雨如晦、兵燹不断的年代勇担时代赋予的伟大建党使命,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基因中所赋予我们的“家国情怀”,正是这种“爱国情怀”的基因在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碰撞中转化为建党精神之源,也成为支撑百年大党从弱到强的精神支柱。
可以看出,伟大建党精神正是源于对古代“家国情怀”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所不同的是,古代统治者强调家国情怀主要是基于维护统治者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段时期,强调“爱国情怀”,其实也就是强调个人对于统治者无条件的服从。但不同的是,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初心与使命精神是发自于内心的真实情感,并无外力制约或者思想的钳制,相反,最初的共产党人甚至还面临着当时政府的围追堵截,他们能够在这种条件下肩负起建党任务,表明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已经实现了从他为到自为的转变。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传承于舍利取义的奉献精神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这就是说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而所谓奉献精神,是一种不计较利益得失、勇于牺牲的精神,它是为了实现目标与理想,甘愿付出一切直至生命的精神。这种精神追根溯源,其核心与要旨便是古往今来各家争论不休的义利之争。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中华民族的奉献精神体现在年湮世远、无可考证的传说中,诸如开创中华农业文明的炎帝、尝尽百草的神农氏以及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这些传说无不闪耀着奉献自我的光辉形象。春秋战国时期,奉献精神的伦理旨归就体现在儒家的利义之辩,孔子主张“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荀子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 先利而后义者辱”,这便是要求人们将义放在首要位置,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得到更大的发挥,屈原投江殉国、诸葛亮鞠躬尽瘁、岳飞精忠报国等,他们舍弃个人之利而追求国家之义,正是文化基因沉淀于民族血液之中,镌刻在每一个国人的心中,传承下来,成就了一代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奉献精神。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古代传统的义利观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中华民族传统的为统治者自我牺牲的义利取舍就升华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懈奋斗,勇于奉献的奉献精神,“就是把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不畏艰险、敢于牺牲,苦干实干、不屈不挠”[8]。正是这样的奉献精神,推动着早期共产党人充满艰险的建党历程。早在建党之前,共产党员就将个人安危置于身后,无论是李大钊、毛泽东等深入到工人阶级中进行秘密工作,还是陈望道等私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亦或是建党前突破重重封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陈独秀的《新青年》、李大钊的《晨钟报》、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在面临查抄、封禁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种于困境之中以国家大义为先的品质都彰显出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气节,正是这种奉献精神,才催生出百年大党的诞生。也正是如此,一大会址、小小红船才承载了一代革命先烈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奉献精神,正如习总书记所言,这里“是我们党梦想启航的地方”[9]。另外,这种奉献精神,还体现在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视死如归的坚毅品格,据统计,仅在中共一大前入党并为革命奉献生命的党员就有23名,包括李大钊、何书衡等党的重要领导人物,正是这样视死如归的奉献精神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沧桑。
古代社会的利义之争毕竟有其局限性,其实质就是要求个人牺牲自身之利为集体无偿奉献,此后“存天理,灭人欲”更将这种义利观发挥到极致,强调个人为统治者奉献一切,由此可见,这种利义观就要求个人完全舍弃自身的利益而为统治者奉献所有,这种奉献精神到封建王朝后期已经完全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这种奉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得到了升华,这里的义绝非为某一个阶层无偿奉献自身的狭隘之“义”,这里的“义”是建立在“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美好愿景。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流淌于“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一种深厚的为民情怀,它是我们党不竭的动力源泉,也是百年大党的力量支撑,更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宗旨与发展理念的政治底色。这种为民情怀承袭于我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
“民本”一词,最初见于《尚书》之中,这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成为了其后几千年中华民族民本思想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民本思想下,有“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的畏民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民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得民思想、“不知民而欺民者,不当为政”的知民思想以及“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的宽民思想等。由此可见,古代君王和统治者将重民思想放在治国理政的核心,“民”是黎民百姓,也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这里的“民”颇有理性为自然立法的意味,显示了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宗教缺席带给人们更多的理性觉醒,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带给“民”更多的自由空间。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人是“感性的、现实的人”,人只有真正成为自然界自觉的主人,才真正摆脱了动物界。这样的主张在与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融合中,逐渐生成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比如,在面对国外记者“中国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的问题中,毛泽东就明确表达了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的特性,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承诺以及江山人民论正是对这一精神的生动诠释。除此之外,从建党伊始,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10],这就是说,在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与不负人民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党的事业需要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人民的自由与发展需要对党忠诚,捍卫党的权威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社会,“民”这一思想中其实带有深刻的阶级性与不平等性,“民”与“君”更多地还是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来出现的,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之下,这种民本思想更多地将“民”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抽象存在,这种“人”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现实的人”“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也就不具有马克思主义中追求“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夙愿。建党精神中所体现的“民本”思想,实质上已超越了这样整体性的抽象存在,这里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人,已经对于这种思想革命性地扬弃,此处的党与人民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融合统一,也就是说党的事业就是民本,民本就是党的根基。
——理直气壮地回击抹黑、诋毁、妖魔化共产主义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