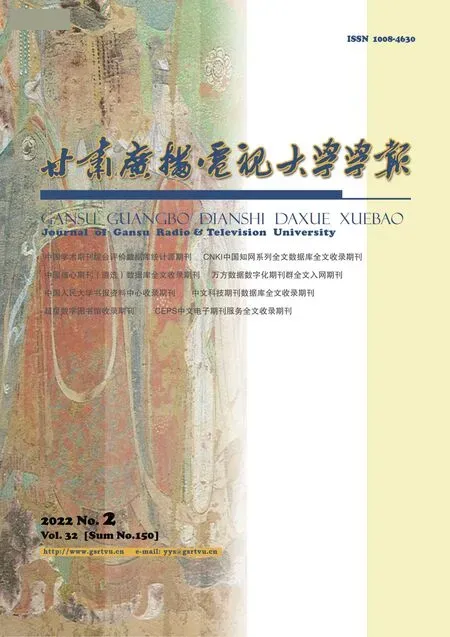试论中国古代官方音乐机关的设立与诗体的演进
王小恒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涪陵 408100)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礼乐治国的思想源远流长,底蕴厚重,影响深远。“礼乐”就其“乐”之一端而论,当然与音乐密不可分,也与文学尤其是诗体的演进很有渊源。“乐府”,顾名思义,是中国历代官方音乐机关之总称,其正式设立之确切时间,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然而一般认为始于汉武帝刘彻。实际上,在刘彻之前与其后,我国官方音乐机关有径以“乐府”相称的,也有行乐府之实而不以乐府相称的,凡此种种,以官方音乐事务,担负治国理政的宏大功能,却与诗体发展演变结下不解之缘,有力地推动诗体发展,使之成为一种创作范式,进而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不能不令人驻足思索,实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西周的社会调查制度——乐府设立之滥觞
中国历代统治者凡是致力于国政者,莫不关注其社会治理效果,同时关注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沟通互动。这一点也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之际,而两周乃其集大成者。西周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光辉的事件,足以启发后世,彪炳万代。文学上的成绩只是其副产品而已。西周大规模社会调查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采集民间里巷歌谣,从中“以观风俗,知薄厚云”[1]128。当时采诗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又长期施行,所采民间歌谣一定数量众多,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诗经》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故而有孔子“删诗”之说。虽说孔子“删诗”尚有争论,但所谓的“诗三百”当时幸得有一个相对定型的版本才得以传世,却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西周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制度,所调查者想必涉及诸多方面,诸如人民、田赋、人口等,对民心诉求的调查也是重要方面,这方面主要依靠所谓的“采诗”这一渠道。既有“采诗”之事,必有“采诗”之官,也就是“采诗”的官方机构,这一官方机构是不是在当时亦称作“乐府”,不得而知,所知者,其功能与“乐府”无实质性的不同,当无疑义。《汉书·艺文志》有段著名的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213可见,以汉代人的口吻称“古有”,当属先秦事。但是,单凭这条还不能说明“采诗”之事与当时官方音乐机关有什么直接联系。再考之《汉书·食货志》,其云: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询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墉户而知天下。[2]
此段文字将“采诗”的全过程做了详细的记录:冬春季节,民人或作或息,集于一处,这是“采诗”的时机选择;男女不得其所,心有所伤,口有所诉,可尽情申说,这是“采诗”的对象。以上是“采诗”的民间阶段。所需之诗既得,即进入官方层次,由基层采诗者——行人将所采之诗献于“太师”,想必有一番选择和甄别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将所采之诗“比其音律”,才上达天子,完成最后一步。“比其音律”是将“采诗”与音乐机关联系的十分重要的步骤,通晓音律属于专业艺术活动,不是人人都可胜任之事。故此两周采诗制度,要顺利完成“采诗”流程,上达天庭,官方音乐机关之设立从情理上讲乃是必然之事。不但如此,由于“采诗”涉及地域广泛,数量庞大,加之两周乃是礼乐之邦,官方音乐机构应该规模不小,否则的话就难以完成对所采之诗意义加以甄别、汰选并加以润色赋音的工作。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诗经》305首,常被称作诗歌总集。殊不知,这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较为通行的“采诗”选集版本。既为通行版本,则肯定经过官方音乐机关加工润色赋音的精选本。这也解释了作为两周基本制度的“采诗”活动为什么与官方音乐机构产生联系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久远,材料匮乏,对于两周采诗活动与音乐机构的关系问题,多是汉代人的记述。这就导致有一种声音出现,认为现存先秦文献中并没有关于“采诗”制度的确凿记载,所以现在汉人的记载是根据汉代乐府之设立和活动而做出的推测甚至虚构。笔者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我们对于一项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有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即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其萌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它不可能突然从天上掉下来,而掉下来之后即非常成熟。汉代官方音乐机关——乐府亦是同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两周的“采诗”制度作为其社会调查制度整体之组成部分,卓有成效,对于后世具有启发性,成为后世乐府设立的滥觞。其次,先秦文献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关于“采诗”制度的确凿记载。1994年面世的上博竹简《孔子诗论》中关于对于“采诗”“观俗”等论述,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学者论述亦详明[3]
由以上论述可见,周代“采诗”活动,使得诗歌文体在礼乐治国的大背景之下,与音乐这一艺术门类首次产生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此后的汉代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不单是音乐史要考察的课题,也是诗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代乐府对现实主义诗风的光大
在中国诗史上,汉武帝设立乐府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原因之一在于,汉代乐府承接两周的“采诗”的做法,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关于两周诗经和汉代乐府的关系,余冠英先生之论甚为精辟,其云:
《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菁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的部分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4]
由于所采之诗多为“里巷歌谣”,即民歌。民歌是唱出来的,有歌词,又发而为声,故而属于诗与乐的联合体,只不过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只存歌词,声已不存,无从知晓了。
关于武帝设立乐府之事,有两段记述为学者所熟知,均出自于《汉书》,这里很有称引的必要。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1]151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章之歌,昏祠至明。[5]
可见,武帝设立乐府是出于考察前代治政得失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明主,汉武帝文治武功皆有可圈可点之处,一方面利用武力开疆拓土,一方面尤重“文治”。“文治”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是大手笔。立乐府,采谣谚,致上下,观得失,作为清明政治的产物,确立承续两周采诗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诗风并将其发扬光大,或许不是他的主观动机,然而就诗体的成长来说,汉代乐府的确立,不但使得乐府成为官方音乐机关的称谓,更使得“乐府”成为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为基本吟唱精神的诗歌体裁,到唐代杜甫、元白,更集成此种精神,把入乐与否视为末流,而把是否具有乐府精神视为标准,确立了所谓新乐府诗,则诗体又是一变,这是后话。
我们讨论汉乐府在诗体发展演变中的地位,要明确的是它的承前启后的独特作用。
其一,汉代乐府之设立,继承两周“采诗”的传统,明确地把考察治政效果作为首要目标。这一点对后世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及功能具有实质性“轨正”效果,即历代统治者把诗歌等文学体式置于其政治教化的框架之内,极力使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所谓“文以载道”“诗言志”之类就是这种动机和努力的重要结果。汉代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都起到一种奠基的作用。武帝将本来在先秦为百家之一的儒家变成了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学,其他文化思想、文学思想等都在儒家思想的统率下行事,这是不言而喻的。就乐府之设置而言,武帝将两周以来行之有效的做法发扬光大,并进行了强化,可以说既总结了前代,也影响到后世,如南北朝乐府,也是汉以后乐府发展的重镇。
其二,汉代乐府的设立,对于文学精神和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两周以政府意志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采诗”活动,其动机在于了解民风民情、考察治政效果。而到了汉代,除了上述目的之外,恐怕还带有反向指引的动机。即所采之诗,乐府机关通过专业润色赋乐,使之用这种“过滤”过的思想情绪反过来影响民心民情,以帮助官方“润色鸿业”,政治化和帮闲化的立场大大增强。但是,这些都在现实定位的大方向之下展看。民歌的重要特点是现实定位,若无此特点,历代统治者的“采诗”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毫无意义了。因此,由周代民歌开启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定位的诗风,虽由官方主导,实是一条优良传统,到了汉代,经汉乐府采集润色和整理,蔚为大观,并在中国诗史上延续下去。所以汉代乐府的承前启后作用也甚明显。
其三,音乐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强化。两周政府的官方音乐人具体做了哪些,没有系统文献流传下来,但有一点可以知道,即润色、相对雅化,使之得以登“大雅之堂”,这是可以肯定的。汉代乐府对于所采之诗的音乐工作更加专业化,分工精细化。如上引所谓“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之类,即审音度曲、填词造赋者各具其长,更加专业化。对所采之民间歌谣,不但润色其词采,而且调整其音律,可见这种“再处理”,不但要使之雅化,更要“纯化”其思想倾向,这与后世清代之修《四库全书》大肆消灭反清思想言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需要指出的是,汉魏乐府之后,六朝乐府仍然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而题材领域有所扩展。周、汉民歌题材基本指向的是农村,而南北朝民歌中的南朝民歌有不少反映的已经是城市生活和情调,而乐府诗的精神未变。这些都是乐府诗发展进程中的新因素。
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乐府诗对乐府诗体发展的启新和嬗变
乐府诗作为一种在中国诗史上别具一格的诗歌体式,究其实,乃是在民间的土壤之上发芽、生长并成长为一棵大树的。这说明文学的真正创造力和生命力在民间,周民歌和汉魏六朝乐府都是采自于民间的里巷歌谣,历代乐府机关虽对于他们有润色加工之功,但本质上还保留了这些歌谣淳朴的原貌,实是原汁原味的民歌。乐府诗经过历代连续不断的采集、整理和发展,俨然成为我国诗史上独具特色的一大宗。乐府诗发展到唐代中期,元白新乐府出,倏然为一巨变,乐府诗体发展出现了重要的变化。
“新乐府”一词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将白居易的创造。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列诗十二类,最后一类标名“新乐府辞”,这种说法即本于白居易。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的自创的题目写的面向时事的乐府式的诗歌。相对于此前的传统的乐府诗,有以下几点需要申明。
一是新乐府都严格地采用新的题目。从汉末建安之时起,文人创作乐府诗,若写的是时事,一般不立新的题目,而是借用古题,这虽然显得古气盎然,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古题与时事有时候会不协调,影响内容的表达。白居易的新乐府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做法,全部采用新题,切实地为反映新的时事服务,是乐府诗发展历程中的新变和进步。
二是新乐府写的都是当代之事,有的抨击当时的各种弊政。回顾历史上的一些做法,我们注意到,建安之后也有自创新题的,但内容多与时事无关。这中间杜甫有其贡献,杜甫既用新题,又写时事,然而取法不严,尚有新题无涉时事之篇。白居易的《新乐府》50首则全部是立新题写时事,这是一个进步。
三是在新乐府的创作中,音乐不是衡量的标准。新乐府这些“未尝被于声”的诗篇,从音乐角度看,只有乐府之名,与音乐毫无关系;但从诗体发展的角度看,继承了前代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乃是真正的乐府诗。
从诗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文人创作乐府诗也有一个改造的过程,这种改造可以说在汉魏时期就已开始了。经过建安以来到唐代杜甫,这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实际上是乐府诗体摆脱音乐局限、采用古题等束缚,走向独立化的过程,由“旧”乐府到新乐府,音乐的影响减小甚或消失了,诗体独立了,更加便于创作的需要了,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白居易的“新乐府”是其标志,也是集大成者。
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乐府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之一体,从其出现之初,就与音乐这一艺术门类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诗歌”虽并称,但“诗”本于“歌”,似是没有问题的。“诗”既本于“歌”,那么,“诗”与“歌”也就是诗与乐结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从周代民歌到中唐白居易“新乐府”出现之前,乐府诗密切地与音乐联系在一起,亦吟亦唱,成就了乐府诗这一十分独特的诗歌体式。只到白居易“新乐府”出来,乐府诗与乐分道异趋,乐府诗走向独立的阶段,这实在也是诗体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