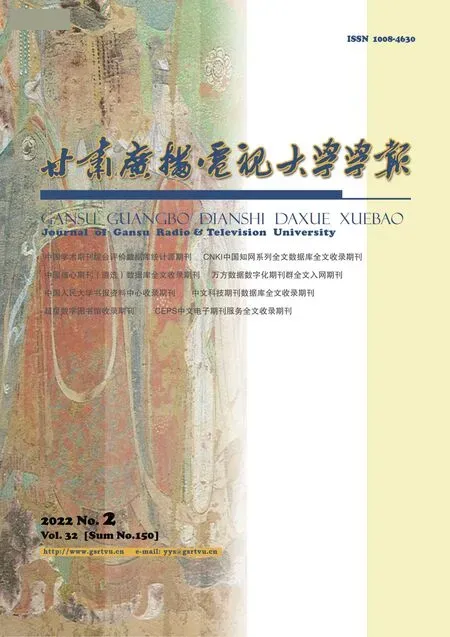大卫·哈维对“退步乌托邦”迪士尼乐园的文化反思
李 茜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迪士尼乐园创造了一种高品质的品牌形象,主要体现为金融、消费和娱乐中心,而经济差异的真实基础被文化多元和趣味性所掩盖。迪士尼乐园看起来赋予了动画形象以“真实”的存在,其实是用这些形象将政治权力的话语和时空关系内在化了。目前对迪士尼乐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商业模式、管理策略方面,如张明(Ming Cheung)和威廉·麦卡锡(William McCarthy)以上海迪士尼乐园为例,对“迪士尼乐园的中国化”进行深入分析[1]。褚劲风的《美国迪士尼公司创意产业化的全球网络与战略管理》从迪士尼的管理战略出发,旨在探求企业内部创意产业治理的规律性[2]。除此之外,高度的“迪士尼化”也吸引了众多理论家的目光。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从“拟像与真实”的角度对迪士尼乐园进行批判,指出迪士尼乐园作为对美国社会的超真实复制,看似是为了凸显外部世界的真实,其实批量制造了“虚假”。可是,当美国本身都成为超真实的存在时,迪士尼乐园作为拟像本身就成为了绝对的真实,它成为了虚拟的实在[3]。瓦伦蒂娜·芙尔吉尼蒂(Valentina Fulginiti)考察了三部意大利小说中迪士尼乐园作为反乌托邦的形象[4]。达科·苏文(Darko Suvin)认为迪士尼乐园是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存在,并且建立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5]162-190。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作为代表性理论家之一,对迪士尼乐园也有着独特的思考。
在哈维看来,迪士尼乐园并不是文化共同体的理想存在之域,而是货币共同体生长空间,资本、权威、身份、权力等因素混杂其中。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它类似于“乌有之乡”,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难以付诸实践,但是“退步乌托邦”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对现实的不作为。乌托邦与生俱来的反抗张力被抹平了,而乌托邦的幽灵依旧存在,它需要一种新的、适合现代的形态。
一、大卫·哈维的乌托邦理论
“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托马斯·莫尔爵士(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中,试图在英国混乱的背景下寻求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在这种幻想中,“永恒回归”的时间、周期性仪式的时间就被保存了。为了使一种快乐稳定的状态永恒存在,“时间之箭”,伟大的历史原则,就被排斥了[6]155。当代的乌托邦理论早已脱离了原始的乌托邦领域,将乌托邦从衰退的境况中拯救出来,其内涵被进一步拓宽。
(一)大卫·哈维乌托邦理论的提出
大卫·哈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理论的代表人物,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间问题,立足于全球化的大背景,确立“政治人”和“身体”的地位,从空间的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以顽强的乌托邦姿态推动着地理想象的进展。地理学被置于时空之中,并把自己视为时空的历史地理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地理学想象融入到了宏大的社会理论中[6]11。“空间生产理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大卫·哈维一方面对《共产党宣言》中的地理学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并将其与“全球化”“劳动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等问题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仍然充满着活力,仍旧适合当代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他对乌托邦问题进行单独讨论。传统的乌托邦被分为“空间的乌托邦”和“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在大卫·哈维看来,二者都是十分片面的。所有那些只是集中于空间或时间一方面的研究,注定要失败[7]248。只存在空间维度的乌托邦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孤岛,看似有条理,实际上是孤立的,空间被用来控制着世界,其内部严格遵守着不变的社会秩序,时间被封存。在这里,想象力自由驰骋,但不可避免受到权威的存在和限制性管理形式,必须正视其中的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6]158。而时间性的乌托邦更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一个乌托邦不被束缚于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性的乌托邦都会被空间化的方式所破坏。迪士尼乐园属于“空间性的乌托邦”,并进一步属于“退步乌托邦”。迪士尼乐园是在地理空间中实现的一种想象关系的表现,这种关系是美国社会主要群体及其真实生存条件与美国的真实历史及与美国边界之外的空间所保持的关系。
(二)“退步乌托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者建立的乌托邦是自身对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空间定位”,在这个空间内,人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政治热情。那么大卫·哈维是否放弃了现实的阶级斗争而躲避到幻想的国度中去?大卫·哈维对乌托邦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不是从形而上学的理论出发去探讨宏观层面对人类起永恒作用的乌托邦,他的理论之路是通向现实世界的,理论矛头直指不合理的现实制度。
路易斯·马林(Louis Marin)在其论著《乌托邦学:空间的游戏》(Utopics:Spatial Play)中最早将迪士尼乐园看作“退步乌托邦”:“我想展示一个乌托邦式的结构和功能是如何退化的,乌托邦式的表现是如何完全陷入一个主导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中,从而变成一个神话或一个集体幻想。”[8]239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沿用了马林的观点,迪士尼乐园的退步之处在于没有对现实世界有任何的批判与启发,一味地让人们沉溺在编织好的幻梦中。全部的空间化乌托邦,从托马斯·莫尔经过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再到迪士尼乐园表现出来的乌托邦堕落(它已经体现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设计中),都不可能抹去历史和过程。解放政治提倡一种生动的过程乌托邦理想,反对僵死的空间化城市形式的乌托邦理想[7]489。虽然乌托邦的出现是为了逃避现实,但这也是我们渴望去干预重塑自己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创造着乌托邦,一方面又要批判性地反思乌托邦理想。不论是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还是在《后现代的状况》中,大卫·哈维对以迪士尼乐园为代表的“退步乌托邦”都持批判的态度。
迪士尼乐园的不断扩张作为问题的一种辩证表达,激起了我们对“退步乌托邦”的反思。大卫·哈维的解决方案是要建立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理想,在避免陷入时间乌托邦和空间乌托邦的同时,也要避开空想主义的陷阱。现实中的“退步乌托邦”不会消失,但它会成为变革社会的强大力量。
二、作为“退步乌托邦”的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乐园是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乌托邦空间之一,近年来的“迪士尼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理论家的目光。除了新自由主义对其持正面的态度外,大多数理论流派和代表理论家们对迪士尼乐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更是透过迪士尼乐园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实质。
(一)技术化的迪士尼乐园
大卫·哈维认为技术与迪士尼乐园的实现与运作紧密相关。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7]273。乌托邦形式的实现离不开资本积累的力量,更离不开对技术的依赖。即除了由科技幻想、商品文化和无尽的资本积累纠合在一起提供的东西,“我们别无选择”[6]163。在游客以为自己拥有快乐的背后,是一套根深蒂固的操纵流程,这套高科技的操纵流程从踏入迪士尼的大门就开始实施。迪士尼乐园本身就是工具理性崇拜的结果,它的选址、建设、动画角色的选取、游乐项目、餐厅都是早已计划好的操作结果,乐园本身就以一个被全面控制的模型姿态存在。游客在这里只能感受到正面情绪,因为其他多余的东西早已被严格控制在乐园之外,所享受到的是高科技带来的结果。迪士尼乐园必须凭借技术的触角为我们呈现未来生活,这实际上是用精密的技术去展现另一种技术。
初入迪士尼,游客会被它的梦幻所吸引。舒适的环境、隐藏在树丛后动听的音乐、真的从动画中“活”过来的人物,让游客日常的感觉完全消失。但是,不论是动听的音乐、舒适的环境,还是充满未来感的游玩项目,甚至人群的流动都是有序可循的,其背后皆为高科技手段的控制。所有的东西都被揉烂、重组,虚假性反而成了最真实的东西,一切因素都试图完成一种不可能的呈现。正如马林建议将迪士尼乐园转变为技术进步的神话,迪士尼乐园越真实存在,它越是空虚。隐藏在这所有背后的是高科技的操纵,是对工具理性的盲目推崇。技术万能一再被强调,没有其他东西能够来玷污这里的快乐,控制网络规划着所有的一切。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迪士尼乐园具有细腻的穿透力。在其光辉的表面背后,它的艾略特式的“意象的荒原”遮蔽着令人恐慌的气息。乐园既展现了、也浓缩了我们时代工商业文化的种种思想和实践。人们会感到好奇,到底有多少参观者注意到这种普遍流行的特征:用技术来展览和赞美技术以及技术所可能带来的生活?[9]
迪士尼乐园游离于真实世界之外,商品拜物教在这里永久化,稳定性则通过监视和控制得以确保。这种极致的“快乐”与稳定性规定了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冲突的空间,而这些特征都是退步的,并没有对外部事物和社会提供任何批判。迪士尼作为“退步乌托邦”的样本,把将来的可能性吸收进非冲突性舞台,批判和反抗力量对统治秩序顺从。社区也是如此,一般来说社区是排他性的,它在人与人之间划定了明确的边界,这样看来,社区常常是社会变革的阻碍[6]165。当人们进入迪士尼乐园,好像进入了一个没有烦恼的世界,这种不可呈现之物的呈现都是通过人工打造出来的。游客在迪士尼乐园中度过了没有烦恼的一天后,回归正常生活便觉得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也变得不那么可憎,批判的初衷慢慢消退,最终完全寄托于迪士尼乐园编织的美好幻梦中。
(二)资本化的迪士尼乐园
在哈维看来,西方社会中许多现实存在的空间形态,如“公共建筑”“大型购物中心”“迪士尼乐园”“持续蔓生的商业化郊区”等之所以堕落为一种彻头彻尾“对资本秩序顺从”且带有一定保守色彩的“退步乌托邦”,根本原因不仅在于“空间形态乌托邦”一贯保持的封闭隔绝性,而且更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资本势力强大的介入与监控力量[10]。类似的“退步乌托邦”建筑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如巴黎的林荫大道等。迪士尼乐园除了提供表面上的幻想与快乐之外,乐园内的事物及其乐园本身都在资本的指引下指向了消费,它是“软消费”的乐园。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取得商业成功之后迅速在全球各地成功“落户”,现已拥有其他5个世界顶级的家庭度假目的地,分别为奥兰多华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区,日本的东京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法国的巴黎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中国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它的商业成功让空间消费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于是它就成了空间消费的成功例证。
如果仅仅将迪士尼乐园当作好莱坞梦工厂的真实重现,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运作下,迪士尼世界从荧幕走向现实并大获成功之后,迪士尼周边商品的开发一直没有停过。杂志、书本、孩子们的日用品、影音产品、衣服、发饰、餐饮等领域都有迪士尼的一席之地。调动大众(与精英相对)市场的时尚,提供了加快消费速度的一种手段,不仅在服装、装饰品和装潢方面,而且也在整个生活风格和娱乐消遣活动的广泛领域中(休闲和运动习惯,流行音乐风格,录像和儿童游戏以及类似的东西)[7]256。给观众所带来快乐的艺术形象转身就成为了可以进行售卖的商品,艺术被彻头彻尾的商业化利益价值所笼罩,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全球化的后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思考。迪士尼的乌托邦应该遵守一般的表现法则。这种代表性的调解清楚地表明,在乌托邦的地方,商品就是意义,意义就是商品。迪士尼的乌托邦以19世纪的街头为背景,在成人的现实和孩子般的幻想之间,销售最新的消费品,将商品转化为意义。反过来,买的东西也有迹象,但这些迹象都是商品[8]253。就像大卫·哈维所思考的一样,我们作为劳动者用劳动力和资本家进行交换,劳动力作为商品早已卷入了资本循环的漩涡。在消费环节中,劳动者拥有有限的选择自由,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劳动者成为循环的一部分,通过资本家支付工资这种方式才能购买资本家的产品,资本家轻易地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了顺从,并为自己的销售活动开辟了独特的市场环境。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并且不断地展开劳动者的身体欲望、需要、社会关系[6]110。
新自由主义强调,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性尊严与个人的价值,所以要提倡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名实行暴力性压榨,最终获胜的只能是雄厚的资本,而迪士尼乐园就是资本的代表。新自由主义鼓吹的乌托邦以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前景来为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开辟空间,不仅大卫·哈维对新自由主义提倡的“退步乌托邦”进行批判,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也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是城里唯一的游戏”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游客自发地去迪士尼乐园寻找快乐,也只是看上去拥有主动权罢了,实际上每一个个体都被随意抛入了大众传媒所营销的幻化世界中。权力不在你我手中,它被资本牢牢掌握,同时权力也被穿上了一层足以迷惑人心的糖衣。用技术去呈现不可呈现之物本身就是对金钱赤裸裸的崇拜。而资本主义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地理,足可说明,资本主义与空间生产是紧密相关的。
(三)意识形态化的迪士尼乐园
大卫·哈维致力于将深层的“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化揭示出来。当迪士尼乐园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落户在世界各地,空间障碍的消除一方面激起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意识,另一方面又激起对文化和个人政治认同的异质性和多孔性的欢呼[7]247。但是这种欢呼是对多元化与异质性的欢呼吗?这种多元化与异质性又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文化多元化本质上就是美国主义,是美国多元文化的缩影,如后现代通俗艺术的体现。虽然迪士尼乐园也鼓吹平等,但是它自己也成为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制造者。这种极端的“多元”就像极端的“民主”一样,极端的“民主”一转身就踏入了僭主制的泥沼,极端的“多元”最终体现的只能是控制与被接受,表面上看着民主,没有负面情绪存在,实际上早已在更深层次被规训。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存就是建基于对一种日显包容性、工具性和从社会角度加以神秘化的空间性的建立,这种空间性隐匿于幻想和意识形态厚厚的面纱中,借以逃避批判视线[11]。迪士尼乐园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代表,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舞台和投射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和检验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意识形态。
迪士尼乐园作为由幻想和想象构成的世界,本身就隐藏着复杂的现实,不可否认它是美国的一个微型缩影,但是却伪装成了不同于现实的一面。马林认为迪士尼乐园再现了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不允许任何批判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现实是被遗忘、中和、虚化的,因为迪士尼乐园已经是现实的全部。让·鲍德里亚在马林的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的后现代模拟理论。在《拟像与仿真》中,迪士尼乐园为后现代“超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这种现象以绝对的自我指称为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图像不再具有与现实的任何相似之处,也不再指的是对现实的扭曲,已然是他们自己的模拟了。之后,苏文认为迪士尼乐园是资本主义如何将“一切可能来自乌托邦”[5]162-190的完美典范,有效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根据他的观点,这种转变是通过“转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发生的。
乌托邦除了被意识形态吞噬外,还适应了不同的文化,抹去了它们最具威胁性的特征。迪士尼乐园要承载成千上万的游客,对文化多元的包容成为其一大特点。但是,文化多元主义混淆了文化与政治的界限,政治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特殊空间被抚平了[12]。因此,文化多元化容易被当作在这里没有意识形态的存在,而这种“去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乐园构思者沃尔特·迪士尼所设想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的壮大,文化与政治的沟壑被抹平的同时,这种“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化也更加稳固了。
因此,我们很难片面地相信迪士尼乐园是一个纯粹的幻想世界,人们在此可以无忧无虑地观光玩乐,它对所有人种、文化、习俗都包容的态度不过是想用多元主义拥抱所有,这种“去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大卫·哈维对迪士尼乐园的批评是基于对传统乌托邦的批评,传统的乌托邦是非辩证的,将时间、空间、历史、地理等因素对立起来,这种乌托邦是封闭性的和绝对化的。同时,大卫·哈维看到了迪士尼乐园的“退步”之处,作为社会替代前景的乌托邦,不是针对形而上学的人类的永恒作用,而是针对现实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带有一定的实践意图,迪士尼乐园只会让人沉溺于此,慢慢消磨掉改造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雄心壮志,它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骗局。
三、“退步乌托邦”理论的现实意义及困境
大卫·哈维从不同的角度对迪士尼乐园进行了深度批判,指出建造乌托邦的冲动应该是良性的,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建设。但当乌托邦陷入自身的泥沼中时,我们不能完全抛弃它,更需要通过对乌托邦的设想对未来提供指导。
(一)理论的建构与合理性
从理论上来说,大卫·哈维开辟了自己研究领域的新高度。相比列斐伏尔强调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将历史的建构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结合在一起,大卫·哈维以理论为武器向现实突进,致力于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要想超越新自由主义倡导的“退步乌托邦”,只能赋予乌托邦新的意义。将时空进行叠合,也是一种希望与实践的重建。“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都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作为我们欲望的隐蔽能指而无处不在。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变革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欲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但也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思想(以及给那些给予可能性如此不良压力的所有利益集团),胜过生活在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的欲望。”[6]196这不仅对我们研究迪士尼乐园有理论性的指导,也不断转换着我们研究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化的综合空间的视角。
大卫·哈维所倡导的“辩证乌托邦”立足于人生活的空间,不在于对现有社会的革命性超越,而是提醒我们存在于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世界中,也许还有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我们可以作为真正的自由人拥抱这个世界,对未来作出更好的规划与期盼。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中间,都会发现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这意味着,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不会发现对资本主义不满和愤怒的示威运动,通过找到正确的空间形式,社会生态变迁之混乱的并经常成问题的形式能够被校正和控制[7]492。大卫·哈维最终还是将希望寄托于人身上,让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与建筑师、蜜蜂相比,更加注重了与世界的互动,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建造这个世界。“我们是有感觉的存在物,与周围世界是新陈代谢的关系,我们改变世界,并且这样做的时候也在改变着自己。我们不可能摆脱作为感官和自然生命、作为生物和历史地理演化过程的产物而存在的普遍特征,是政治的、符号的动物,此外,更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破坏者,自然法则的客体和活跃的主体。”[6]203我们首先要成为自己,才能将人类的潜力发挥到极限。我们不应在资本的控制下认识这个世界,也不应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制造的幻象中乐此不疲。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商品经济指向的是消解真理的场域,作为大众的我们在这里几乎是无力的。对这个世界进行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有世界的反叛,而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先改变自己。我们既是主体,也是“向无数过程开放”的实体,拥有能将人类潜能推向极限的意识。
(二)理论的困境与软弱
大卫·哈维理论上的建构具有深度和合理性。“迪士尼化”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从地理学的、后现代的角度出发,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些对迪士尼乐园空间的美好设想在实际的操作方面却有着很多障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巨大,在此背景下实现一个“辩证乌托邦”可以说是希望渺茫,如果不持续性地对此进行思考与探索,理论也只能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与小打小闹,根本不能触及制度层面上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辩证的乌托邦还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被建构出来的,这不过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烈的反对声音,并不能真正做到撼动资本主义的体系。在理论的宏观层面上,简单地“告别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的终结”之论都是其称为“退步乌托邦”的致命的理论征兆,在逻辑上与“没有选择”同出一辙,基本的矛盾是“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空间物化和人们幸福生活的追求之间冲突”[13]。可以看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女性政治问题、生态问题、移民问题等都是不平等的地域事实,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与这些特殊的地理转型相适应。从个人、工厂、国家联盟到全球,这些不同空间形态上的问题与冲突越发尖锐,这就需要在微观和宏观上都对资本的地理策略问题作出回应。从个体的角度,我们的身份是“类存在物”,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作用于世界,我们对自身抱有期待,对自然生态负责。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空间早已成为意识形态、资本、权力等因素的交汇之地。迪士尼乐园、博物馆、纽约时代广场、购物商厦等都是“退步乌托邦”的代表形式,人们处于被资本建造的万物商品化的城市文化空间中,这是一种虚幻的手段,在构建空间的同时也构建了群体本身。迪士尼乐园作为研究空间的一个微小的切入点,我们得以窥探资本打造世界的真相,始终对现代的乌托邦形式进行思考。
大卫·哈维用理论开拓出一条以现实生活为指向的理论路径,即个体在被型塑与构建的同时,也拥有与世界交流、改变世界的潜力。理论虽有局限性,但在被资本主义笼罩的大氛围下,这不失为找到自身以及改造社会价值意义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