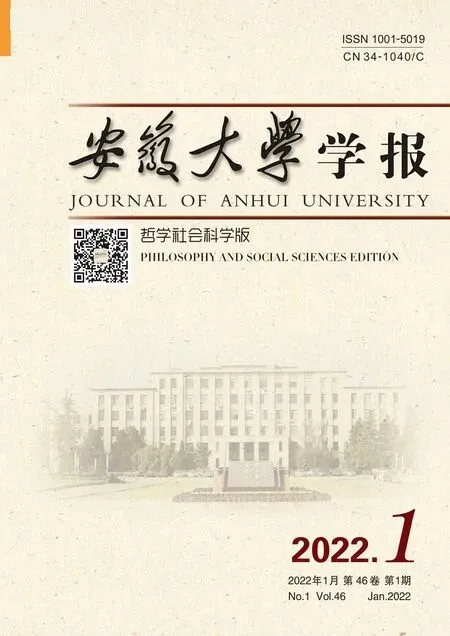给予者,抑或受予者?
——论马里翁对自我的激进化理解
朱 刚
由笛卡尔开启端绪的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至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达到其高峰:在这一超越论现象学中,作为超越论主体的本我或自我被视为世界的构造者、意义的给予者,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本原。不过胡塞尔之后,自我的这种主体乃至本原地位便遭到各种颠覆与消解。且不说现象学运动之外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即便在现象学内部,从海德格尔的“此在”开始,到列维纳斯的“奠基在无限之中的主体”和始终受到他人“纠缠”的自我,再到马里翁的作为“受予者”(l’adonné)的自我,各种对自我本原性的消解也是此起彼伏、不绝如缕。本文要探讨的就是马里翁把“自我”理解为“受予者”这一晚近的激进方案。在这一方案中,自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或本原:既不是现象之显现的可能性条件,也不是世界之构造者或意义之给予者,而是使其所接受者显现出来的舞台、棱镜或屏幕。在这里,自我由主格自我被逆转为宾格自我或与格自我,由给予者被逆转为接受者和受予者,而且甚至,它也正是在接受被给予它的事物之际才接受和发现它自己。这是马里翁对自我的激进化理解。
不过马里翁对自我的这种激进化理解与他对现象学还原的激进化理解密切相关,甚至正是后者的必然结果。所以,若要深入理解马里翁对自我的这种激进化理解,首先要对他所理解的现象学还原作一讨论。
一、从显现到给予:马里翁对现象学还原的激进化理解
马里翁认为:“所有的现象学都或明(胡塞尔)或暗(海德格尔、列维纳斯、亨利、德里达)地把还原作为其不容谈判的试金石来用”(1)Jean-Luc Marion, De surcrot, études sur les phénomènes saturés, Paris: PUF, 2010, p. 56. 下引该书仅随文夹注页码。,甚至,现象学还原“这一操作构成全部现象学事业的条件,它的缺失也将不可挽回地毁灭现象学”(p. 20)。的确,保证现象学不重新堕回形而上学或经验论的,恰恰就是还原这一预先的警戒:它既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学的预设,也阻止了任何未经纯化的素朴经验的僭越。它唯一赋予现象学上合法性的,就是纯粹的显现者(现象)。但是众所周知,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两位经典现象学家那里,还原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其对“显现”的纯化和保证也体现为两种不同途径。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还原被称为超越论还原,而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还原则是生存论还原。两种还原都力图回到纯粹现象,回到现象学的实事本身,但它们所理解的纯粹现象或实事本身又显然不同。而在马里翁看来,无论是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还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都不够彻底,他进一步把它们激进化为第三种还原:“对呼声和向呼声的还原”(2)马里翁:《还原与给予》,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或“从显现向被给出者的还原”(p. 57),最终是向被给予性的还原。当然,马里翁对第三种还原的提出也并非一蹴而就,无论是其名称,还是其内涵,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下面我们首先分别考察马里翁对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的分析,然后再考察马里翁自己提出的第三种还原,以为下文讨论马里翁对自我的激进化理解作一准备。
首先看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严格意义上的超越论还原标志着通向超越论主体性的方法通道(3)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增补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34页。。为什么要通向“超越论主体性”?因为经过现象学悬搁(它构成了超越论还原的第一步)后,唯有被理解为超越论主体性的纯粹意识才是超越论现象学的唯一合法领地,当然这里的纯粹意识不再是传统哲学所理解的那种首先封闭在主体性内部然后才与对象发生关联的意识,而是原本就处于意向性结构之中并带有其意向相关项的意识。正是作为这样一种纯粹意识的超越论主体性被揭示为世界的构造性起源(4)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增补版),第434页。。需注意的是,这种还原的动机是为了揭示对象世界的构造性起源,所以马里翁说:“它等同于对象的构造”,但也因此,“它便从被给予性中排除了所有无法被回溯到对象性之上的东西”(5)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48页。。而对象,在超越论还原之后,又总是被理解为超越论主体性或纯粹意识的构造成就。因此这种还原有两个决定性的后果:一方面,它把“自我”还原为一个构造性自我意义上的主体;另一方面,它把“对象”还原为“意向相关项”,即意识活动的构造成就,后者在此意义上已经不再是从其“自身”显现出来的“现象”。正是这两方面的问题促使马里翁提出第三种现象学还原。
至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实际上,海德格尔本人似乎并没有提出过“生存论还原”或“生存论上的还原”这样的说法,这是马里翁对海德格尔的还原方法的命名。他在《还原与给予》中说道:“第二种还原表现为生存论的还原,它是由生存着的存在者推动的;也可以说是表现为存在论的还原,它打开了存在问题。”(6)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48~349页。译文根据法语原文有改动。所谓“生存着的存在者”,显然指“此在”。因此这种还原是由此在推动的,实质是从存在者还原到其存在性,进而打开存在问题。海德格尔曾把他自己对现象学还原的理解与胡塞尔的理解进行对比,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海德格尔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说道:“对于胡塞尔而言,现象学还原……是这样一种方法:将现象学目光从沉溺于事物以及人格世界的人之自然态度引回超越论的意识生活及其行思—所思体验(noetisch-noematische Erlebnisse),在这种体验中客体被构成为意识相关项。”(7)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修订译本),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7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深刻地领会到了胡塞尔超越论还原的精义,即把人从自然态度支配的生活引回到超越论的意识生活,并在这种意识生活的意向性构造活动中理解客体的构成。正是在这种对胡塞尔超越论还原精准把握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凸显了他自己对现象学还原的不同理解。他接着说道:“对我们来说,现象学还原的意思是,把现象学的目光从对存在者的……把握引回对该存在者之存在的领会(就存在被揭示的方式进行筹划)。”(8)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修订译本),第27页。显然,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或超越论还原并不彻底,因为它只是把对象还原为意识的构造成就,而没有达到对象的存在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马里翁看到了二人的区别或海德格尔的推进之处,他说:“自此之后,还原不再把(存在者的)世界这一主题引向在现象的静止在场意义上的内在性之中,而是把作为存在者之解蔽的现象引向着眼于其存在的深度理解之上”,所以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现象学沉思所关心的仅仅是对存在者本身的存在进行规定”。总之,这种生存论的或存在论的还原“给出了(或声称给出了)不同的存在方式,因而也给出了存在论差异本身,简言之,给出了‘存在的现象’”。这是其所得,但在马里翁看来,这同时也是其所失。因为,“它排除了那些不必存在的东西,特别是排除了‘存在的现象’的先决条件”(9)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107~108页、108页、349页、349页。。就是说,马里翁认为,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虽然回到了存在现象,回到了显现,但仍不够。因为,存在之外,还有不存在者或无须存在者;显现之外,还有给出自身但尚未进入显现者。
上述问题其实是前两种还原的共同局限,因为它们都是向“显现”的还原:无论是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所还原到的超越论主体的意向性意识,还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所还原到的此在的生存活动,都是事物的显现方式,因而向它们的还原就都是向事物的显现的还原。但无论是通过超越论主体的意向性意识而显现,还是通过此在的生存活动而显现,事物严格说来都不是通过“自身”而显现。就前者而言,正如马里翁所追问的:“实际上,如果一个超越论的我把一个现象构造为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为了完全统治它的思想并由这一思想置于支配之下,那么这一现象如何能够要求由其自身并就其自身而展开自身?”(p. 37)所以在胡塞尔这里,一个现象其实是无法就其自身展开自身、显示自身的。也因此,超越论还原实际上并没有像它允诺的那样达至事物“自身”。就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而言也同样如此:虽然海德格尔将现象规定为那就其自身且由其自身而来显示自身者(10)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追溯“现象”一词的希腊词源而给“现象”下了这样的定义:“‘现象’一词的意义就可以确定为: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7页。,但是,正如马里翁所指出的: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任由在自身显示中起作用的那一自身能够被思考的方式处于不确定之中”(p. 37)。相反,在海德格尔那里,事物的显现其实是需要通过此在的生存的,是在此在的解蔽着的操劳活动中实现出来的。没有此在的存在,事物就无法被揭蔽,无法进入显现。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也没有到达事物的“自身”。
这两种还原之“得”在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回溯至事物的显现、现象,但它们之“失”则在于它们没有达至事物之“自身”。而它们之所以有此失,归根到底是在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没有看到显现与自身给出之间的间距:他们把显现等同于自身给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诚然,事物的显现离不开超越论主体的意识活动或此在的生存活动,但事物的自身给出却未必如此。显现并不等于自身给出,二者之间有着不可抹除的间距,而且,一者(显现)还以另一者(自身给出)为可能性前提。
揭示出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以及依赖关系的正是马里翁,他在其现象学三部曲的第二部《既予:一种被给予性现象学研究》中甚至将此问题视为该书的“唯一的主题”:“凡自身显示者,必首先自身给出——这是我们唯一的主题。”(11)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aris: PUF, 2013, p. 8.在其现象学三部曲的第三部《论溢出》中他也明言:“仅就其自身给出(sedonne)而言,一个现象才自身显示——为了达到这一点,任何自身显示者首先必须自身给出。”(p. 37-38)就是说,现象如果要成为现象,即自身显示或表现出来,首先要自己把自己给予出来,自身给出是自身显示(表现)的前提:“如果表现可能是由给出产生的,那么给出就必定先行于表现;因此给出相对于表现而言就是在先的”(p. 38)。然而反之却不然:“一切自身给出者并不必然都自身显示——给出或给予(la donation)并不总是现象化。”(p. 38)同时,马里翁又认为,唯有现象化者、自身显示者或被显示者才能被看到,而“自身给出(la donation de soi)实际上并不能被直接地看到”——既如此,那我们该“如何辨认出自身给出者?”(p. 38)
如何辨认?通过进一步的还原,或把原来向显现的还原进一步激进化为向被给出者并最终激进化为向被给予性的还原。这就是马里翁提出的第三种还原。他毫不怀疑第三种还原超出了前两种还原,因为它更为彻底或激进:“我们要求实现的从显现向被给出者的这一还原充满危险地区别于它要求超出的两种主要的还原形象……因为它不再只是把现象引导到现象之被构造的对象性上(胡塞尔)或现象之在存在中的存在性上(海德格尔),而是把现象最终引导到被给出者上,后者在其给出自身的程度上显示自身——因此它用最终的、不可用任何其他还原加以还原的术语确定了被给出者。”(p. 57)(12)必须要说明的是,马里翁早在现象学三部曲的第一部即1989年的《还原与给予》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第三种还原,但是在那里,他把这种还原称为“对呼声和向呼声的还原”(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38页),因为那时他是从对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呼声”、基督徒听到的“天父的呼声”和列维纳斯所凸显的“他人的呼声”的现象学分析中引出这种还原的:所谓“对呼声的还原”是指他对这三种呼声的起源(存在、天父或他人)进行悬置,而“向呼声的还原”则是指向呼声的纯粹结构本身进行还原(详见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36~339页)。不过,在那里,马里翁已经是在“自身给出的东西”的意义上理解“呼声”(参见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38页,中译本将“自身给出的东西”译为“自身给予的东西”),因此《还原与给予》中用来命名第三种还原的“向呼声的还原”可以被视为后来马里翁更明确地提出的“向被给出者的还原”“向被给予性的还原”的预先表达。显然,这种还原与前两种还原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两种还原只是还原到了现象的显现上,而这种显现又要么是通过主观的意识要么是通过此在的存在,因而这两种还原实际上并没有还原到现象自身上;而马里翁的这一还原则是要还原到就其自身给出自身的现象自身上。在腾格义(Tengelyi)看来,这一点正是以马里翁为主要代表的法国新现象学与经典现象学的一个区别性特征。他指出:“‘就其自身’这一表达在这里并不是偶然被强调的。对显现的自发性给予注意,这是法国新现象学的一个区别性特征……马里翁致力于证明,现象一般是经由自己本身而被给出的,因此可以说:现象不单是自身显示,而且还是自身给出的……现象本身毕竟始终是不可还原为任何一种通过主体的意义给予。对一种自发的意义涌现的描述……是法国新现象学的一项根本成就。”(13)Hans-Dieter Gondek László Tengelyi, Neue Phänomenologie in Frankreich, Berlin: Shurkamp Verlag, 2011, S. 217.腾格义指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列维纳斯还只是强调他人的面容作为卓越的现象是无须凭借主观的被给予方式而自身给出的,但马里翁则将这种自身给出拓展到现象一般。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向被给出者的还原还远非还原之终点。因为被给出者,是被给予出来的,因此这种“(被)给予(性)”或“(被)给出(性)”(la donation)才是最终的现象学实事,才是现象学——或哲学本身——的首要者、第一者或开端:“凭借该[给予]行为,自身显示者给出自身,而给出自身者总是从显现之不可还原的和首要的自身(lesoi)出发显示自身。”(p. 31)于是,这一还原势必要从向被给出者的还原进一步激进化为向“(被)给予(性)”的还原。由此,“(被)给予(性)的现象学”就成了马里翁现象学的最终形态。同时,由于这种(被)给予(性)被视为哲学的真正的首要者或最终者,所以这种被给予性现象学也就成了第一哲学(14)参见Jean-Luc Marion, De surcrot, études sur les phénomènes saturés, p. 16-32,以及朱刚《作为第一哲学的被给予性现象学——马里翁对经典现象学的激进化》,《哲学动态》2019年第6期。。
现在——经过这一激进的现象学还原——既然被给出者不再是通过我的意识这一主观的给予方式被给予出来或被构造出来,而是作为自身显示者由其自身给出自身并凭其自身而来到我这里,那么,在这一激进的还原中,“我”的地位也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再也不是构造对象、给出意义的给予者,而是接受自身给出者的接受者。
二、从给予者到接受者(l’attributaire):自我在被给予性还原中的转变
自笛卡尔以来,自我就被确定为主体,被确立为哲学上的首要者和开端。如沙恩·麦金利(Shane Mackinlay)所指出的,作为主体性的自我成为现象的可能性界限(15)Shane Mackinlay, Interpreting Excess, Jean-Luc Marion, Saturated Phenomena, and Hermeneutic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如此一来,所有其他存在者都被置于与自我我思的关系中,被还原为自我我思的对象。而且,因为它们的实存依赖于自我的在先存在,自我就变成了一切其他存在者的基础与根据,变成了卓越的存在者(16)Shane Mackinlay, Interpreting Excess, Jean-Luc Marion, Saturated Phenomena, and Hermeneutics, p. 3.:“自我在先存在,并且比所有其他存在者更为确定,因为,而且只是因为,每一个存在者都只是作为对象(objectum),因此作为所思者(cogitatum)。反之,自我卓越地、带有优先性地存在,因为而且只是因为,所有其他存在者都只是作为所思的对象。”(17)Jean-Luc Marion, Sur le prisme métaphysique de Descartes, Paris: PUF, 2004, p. 102.所以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还原为自我的思想对象,自我为对象的存在奠基。自我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奠基性角色(18)Shane Mackinlay, Interpreting Excess, Jean-Luc Marion, Saturated Phenomena, and Hermeneutics, p. 3.。笛卡尔赋予自我的这一主体性地位,经康德的过渡,到胡塞尔那里变得更为彻底:经过现象学的还原,自我我思不仅是最先得到保证的、无可怀疑的哲学沉思的起点,而且被揭示为构造一切对象的起源,成为一切意义的赋予者、给予者,从而成为双重意义上的开端(19)参见朱刚《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的双重开端与双重还原》,《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
就此而言,胡塞尔的现象学虽然以回到实事本身为使命,但这一使命由于胡塞尔之思以超越论的主体性为最终本原而先天受阻:当他以超越论的主体性为最终的实事本身的时候,当他把现象还原为由超越论主体所构造且为了超越论主体而被构造的对象的时候,从而当他以超越论主体及其意识生活为现象的条件、界限乃至起源的时候,他就已经先行阻断了回到那并非由主体性构造的事物自身的可能性,当然也从根本上排除了这种事物自身。所以马里翁有理由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并没有彻底摆脱形而上学,因为它仍保留了起构造性作用的主体性的观念:“我们常常以为现象学摆脱了形而上学,可是我们无法彻底坚持这个断言,因为我们强调的是,胡塞尔保留了康德的判定(现象性的可能性条件,视域,自我的构造性功能)。”不仅胡塞尔现象学如此,在马里翁看来,海德格尔现象学同样难逃形而上学的窠臼,因为:“海德格尔既保留了存在问题的特殊地位,也维持了此在中的主体性。”(20)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6.就是说,在马里翁看来,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中,主体或其相当者(此在)仍保留了构造性作用,并因此仍承担了构造者、开端者、给予者的角色。
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自我或此在的这种理解——将我或此在理解为构造者、给予者——真的揭示或回到了自我的“本来面目”吗?未必。因为在马里翁看来,对自我的这种理解乃是这样一种先见的结果,即现象只能经由主观的显现方式显现,只能以主体(哪怕此主体被激进化为此在)提供的方式作为其显现的条件和界限。但如上文所说,这一先见本身是以一种误解或盲目为前提的,即认为现象的显现和现象的自身给予或自身给出是一回事。然而正如马里翁所揭示的,现象的显现和现象的自身给出并非一回事,二者之间有一种不可还原的间距或差异:事物若要显现或现象化,必先已经自身给出;但自身给出却并不必然进入显现。而一旦我们把还原由显现进一步推进到自身给出,把现象首先理解为自身给出者,而非在一个主权性的主体或笛卡尔式形而上学主体所确立的界限内显现(21)Shane Mackinlay, Interpreting Excess, Jean-Luc Marion, Saturated Phenomena, and Hermeneutics, p. 4.,那么自我必然也要经受进一步的还原:这时就将暴露出,“我”首先并不是对象的构造者或给予者,而毋宁是接受自身给出者的接受者(22)参见欧阳谦《“充溢现象”与主体换位——论马里翁的“新现象学”》,《哲学动态》2017年第10期。。
这才是自我的本来面目。以现象学的方式系统揭示出这一点的正是马里翁。他早在现象学三部曲的第一部《还原与给予》中就已经区分了超越论的自我、经验之我和自身给出者所要求、呼唤的宾我之间的不同,并强调“我”首先是被自身给出者的呼唤与要求创造出来的,从而我首先是被呼唤的宾我而非创造性、给予性的主我:“要求呼向我(moi)。如果不是要求已经在召唤我,因而已经抓住了我并把握了我,我还不能说出我(je)呢,因为这个要求已经在告诫我并把我命名为我(me)。”在这里马里翁与列维纳斯一样,也认为是“要求本身首先说话……从而在我(me)中把我创设出来”(23)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39页、340页。。在分析了现象学的超越论自我、经验之我和要求、呼声所寻唤的宾我之不同(24)详见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40~341页。后,马里翁得出结论:“由于我(me)被寻唤到宾格之上,而这个宾格通过针对它所提出的呼声被剥夺了主格的性质,因此,宾我从现象上表明了任何一种[超越论的]自我的缺席。在这个意义上的要求的绝对范围内,这个要求所激发的宾我(me)证明了一切超越论的自我或构造性的自我的退位。”(25)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41页。从何处退位?从其自笛卡尔以来到胡塞尔乃至海德格尔(以此在的名义)一直被赋予的开端、本原、给予者的地位上退位。自我首先不再是这样的超越论自我或构造性自我,不再是构造者、给予者,因而也不再是这个意义上的开端、本原。自我首先是宾我,是被呼唤且在这呼唤中才被创设出来的我。在这个意义上,“我”首先是接受者或见证者:接受和见证由其自身出发将其自身给予我者。这一点马里翁后来在《既予》中给出了更为详尽的分析。
马里翁在《既予》中指出,现象就其给出自身而言才表现出自身。“然而”,马里翁说:现象“为了能像给出自身那样表现自身,现象由之得以展开的那个‘自身’(soi)首先必须要如此这般地证实自身(s’atteste)。而现象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又唯有通过居有现象性的重心,亦即承担起它本己事件的起源”。这就是说,“现象”要显现自身,必先给出自身;而要能给出“自身”,又要先得“证实自身”;而“自身”要得到“证实”,现象就必须承担起其本己事件的起源,居有其现象性的重心:这就意味着,现象必须是完全由其自身给出自身,将其自身给予我,而非由“我”作为主体将其给予出来乃至构造出来。而“唯有这样,现象才能从客体的被异化的地位中摆脱出来”。于是,现象不再是被构造、被呈现的客体,而成了自身给出的主体。而要做到这一点,现象之“自身”又必须要反抗自我的超越论的要求,即自我的那种将现象客体化、赋予其限制和条件的要求:“现象只有把自己确认为一个‘自身’,才能给出自身和显示自身;而这一‘自身’又只有通过反对自我的任何一个……超越论的要求才能得到证实。”于是最终,“现象本身的‘自身’就恢复了在其现象性中的创始性”,而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就是:“迫使我们根据自我之形变(anamorphose)的引导性线索重新定义自我,就像现象的单纯见证一样”(26)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05.。从而,“我”就从构造性的超越论自我的王位上退下,成为一个作为接受者和见证者的“我”:
现象之“自身”——既然它是在与客体性相对立的情况下建立起自身——决定性地把自我转变为一个见证者……因为它首先把主格……颠倒为一个更为原初的与格(un datif),后者指示着……现象之接受者(attributaire)所具有的被予向者(l’ à qu[o]i)[这一身份]。当然,这样一种接受者是形而上学用“主体”所意指的那种东西的接替者,因为它与之正相对立。不过,这一对立并不只是源自这一事实,即接受者是在现象之后到来,而“主体”则预见到或引发现象;而尤其是源自这一事实,即接受者不再能够声称拥有或产生现象。它不再处于与现象的拥有关系中,而是处于一种单纯的接受性关系中……因此接受者是在双重的意义上在“主体”之后到来:它是继主体的形而上学形象而来,但尤其是,它来自现象,而非在现象之前到来或产生现象。(27)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06.
可见,“我”现在就被给予“我”的现象自身转变为它的“接受者”与“见证者”。“我”的这一形象从哲学史上看是“继主体的形而上学形象而来”,但从思想的实事本身来看,乃是“来自现象”,来自现象的呼唤与要求,因此是随着现象而来,而非在现象之前到来或产生现象——后者正是笛卡尔、康德、胡塞尔所赋予“我”的“主体的形而上学形象”。在马里翁看来,这一作为“接受者”和“见证者”的形象,才是自我的本源形象或本来面目。
这个从事哲学或现象学沉思的“我”,首先是被给予了现象,而非构造和给出现象;首先是被给予一个世界,而非构造和给出一个世界。所以,马里翁说:“作为现象之被给予这一实事的严格的结果,接受者就作为‘主体’的相反者被确立起来了,并取‘主体’而代之。”(28)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11.于是,这样一种“取‘主体’而代之”的“接受者”,就不再是现象的“作者”或“生产者”,而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或被给予我的现象的“记录员、接受者或被动者”。由此马里翁认为,“关于超越论性的形而上学的和主观的形态在此就首次经受一种决定性的倒转”,因为这里也发生了一种“价值重估”:对自我的价值重估(p. 31)。所以正如沙恩·麦金利评论的那样:“马里翁毫不妥协地坚持从现象的被给予性开始,而非从一个主体的视域或界限出发。……这种坚持常常导致主体的角色被还原为纯粹被动的接受者。”(29)Shane Mackinlay, Interpreting Excess, Jean-Luc Marion, Saturated Phenomena, and Hermeneutics, p. 2.
三、从接受者到受予者:自我的激进化
但是,自我在被还原为纯粹被动的接受者之后,它在这一还原中的“形变”就到头了吗?它的原本含义在“接受者”这一形象中穷尽了吗?不,没有!因为,在马里翁看来:“如果接受者是从作为被给出者的现象之浮现本身中诞生的,就是说,是从一种这样的被给出者——它实施着其作为事件所带来的单纯冲击——中诞生的,那么,当一个被给出的现象作为饱溢现象(le phénomène saturé)而浮现出来时……冲击就会激进化为呼声,而接受者(l’attributaire)就会激进化为受予者(l’adonné)。”(30)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2-433.这里,马里翁把他的被给予性现象学进一步激进化:将被给出者激进化为“饱溢现象”,作为饱溢现象的被给出者所带来的冲击随之激进化为“呼声”,与之相应,原本接受被给出者的“接受者”在受到这种呼声的召唤时,就激进化为“受予者”。所以,在马里翁的被给予性现象学中,自我的最终形象还不是接受者,而是受予者。然而,自我如何由接受者激进化为受予者?接受者与受予者又有何区别?这要从作为饱溢现象的被给出者如何激进化为呼声以及呼声具有哪些现象学特征谈起,因为正是由于被给出者对我的呼唤,“我”才进一步形变为受予者。
(一)饱溢现象作为呼声
在《还原与给予》中,虽然“饱溢现象”的问题还只是隐含着(31)马里翁后来在《论溢出》的“告读者”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说:“这一问题[即饱溢现象的问题——引者按],自从我们尝试着从被给予性(la donation)在现象学计划中的首要性出发彻底地重新把握整个现象学计划以来——尽管那时它还是隐含着的——就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其轮廓了。”(p. vii),但后来被马里翁用来刻画饱溢现象的“呼声”(32)对“呼声”的专题现象学讨论可参见Jean-Louis Chrétien, The Call and the Response, trans. by Anne Davenpor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4。却已经成为该书的一个重要概念,他甚至将其提出的第三种还原先行命名为“对呼声和向呼声的还原”。“呼声”在那里已被马里翁理解为“自身给出”的现象,它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突袭”(surprise)(33)也有译为“意外”,见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43页。——已经预示着后来成为其现象学主题的“饱溢现象”。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中如此描述呼声的“突袭”性:“突袭从绝对陌生的场所和事件出发攫取被吁请者,以至于最终取消了主体的任何打算构造、重构或确定这种突袭它的事物的意图;这种突袭以下述方式抓住了被吁请者:它使被吁请者摆脱了任何一种主体性,它挑战被吁请者之中任何自行构造的极性,最后,它从被吁请者自己无论如何也不理解的事件出发并在这个事件中理解被吁请者……从字面意思上来说,突袭禁止被吁请者理解其所接收到的召唤。”(34)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43~344页,译文根据法语原文稍有改动。Cf. Jean-Luc Marion, Réduction et donation, Recherches sur Husserl, Heidegger et la phénoménologie, Paris: PUF, 2015, p. 347-348.从这种对“突袭”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突袭”就是指呼声作为自身给出者超出了被吁请者的意向性把握能力,溢出了被吁请者的任何的含义意向或概念,从而体现为不可理解或禁止理解之物。而这,实际上也正是马里翁后来在《既予》中所刻画的“饱溢现象”的基本特征,即“直观在现象中的过剩……直观在饱溢现象中颠覆并因此先行于它所溢出……的任何意向”(35)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5.。后来在《论溢出》中马里翁对饱溢现象的这种“溢出”特征给出了类似的描述:“在此,关键在于溢出(surcrot),在于直观相对于概念的剩余(l’excès)……直观相对于概念以及……概念的所有含义而言所具有的不可还原的溢出。”(p. vii)总之,所谓“饱溢现象”就是这样一些现象:它们从其自身而来给向我,并溢出了我关于它可能有的任何概念与含义。
可以看出,饱溢现象实际上也正是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中作为主题予以讨论的自身给出者的激进化。在《既予》中,马里翁根据康德的范畴表,从量、质、关系和模态四个方面把饱溢现象分为四类:事件(l’événement)、偶像(l’idole)、肉身(la chair)和圣像(l’icne),此外马里翁又把“启示”(la Révélation)作为同时具有前四种饱溢现象之特征的最卓越的饱溢现象加以单独讨论。不过,在分析饱溢现象的呼声特征时马里翁只分析了前四种。他认为,事件是量这一维度上的饱溢现象,偶像是质这一维度上的饱溢现象,肉身是关系这一维度上的饱溢现象,而圣像则是模态这一维度上的饱溢现象,它们“都逆转了意向性,并因此使呼声得以可能,甚至成为不可避免的”。所以,“呼声实际上刻画出了任何一种如此这般的饱溢现象的特征”(36)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6, p. 435.。
然而呼声何以就能刻画饱溢现象的特征呢?因为呼声之所以为呼声,就在于它溢出我的意向性,就在于它逆着我的意向性而召唤我、激发我。所以当饱溢现象由自身给出自身,不再听命于、服从于主体,而是溢出主体的意向性,逆转主体的意向性时,它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表现为或激进化为向“主体”发出的呼声。马里翁认为,这样一种呼声不仅剥夺了我的构造性的、给予性的超越论地位,而且也正是这一呼声才把“我”呼唤出来或激发起来(37)马里翁:“如此这般的呼声就足以——无须其他对本原的认同——激发起窘迫的被呼者(l’interloqué),因此激发起受予者。”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3-434.:我是在接受这一呼声之际,才发现并同时接受我自己。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我”,被马里翁称为或激进化为“受予者”(l’adonné)。所以马里翁说:“受予者就是这样诞生的:呼声使它作为完全从它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其自身者继‘主体’而来。”(38)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6.在这个意义上,l’adonné也不同于“接受者”(l’attributaire),因为后者仅仅接受自身给出者,而前者不仅接受给予它的自身给出者,还“从它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其自身”。这也是我们把l’adonné不译为“接受者”而译为“受予者”的原因:“受予”这里隐含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接受给予的意思,另一方面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接受我”。换言之,“受予者”中的“予”,既可以理解为“给予”,也可以理解为“我”。
但问题是,呼声究竟如何激发起、建立起作为受予者的“我”呢?
(二)呼声对作为受予者的“我”的建立
马里翁说:“呼声根据其本己显示的四重特征以现象学的方式建立起受予者,这四重特征即:召唤(la convocation)、突袭(la surprise)、会话(l’interlocution)、实际性(la facticité)(个体化,individuation)。”(39)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6. 值得注意的是,马里翁早在《还原与给予》中就已经提出呼声的“要求”(la revendication)具有四个特征:“召唤(convocation)、突袭(surprise,也译为‘意外’)、认同(identification)和实际性(facticité,也译为‘事实性’)”,而且也已经提出呼声凭借这四个特征“在除了呼声的纯粹形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的情况下把被呼者本身建立起来了”(参见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45页,译文有改动)。显然可以看出,我们前面刚刚引用的《既予》中的相关思想与《还原与给予》这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表述上稍有变化:首先,在《还原与给予》所列的四个特征中的“认同”被后来《既予》中所列的“会话”取代;其次,在《还原与给予》中,呼声凭此四个特征所建立起来的是“被呼者”(l’interloqué,中译本译为“被吁请者”),而在后来的《既予》中,“被吁请者”已经被“受予者”(l’adonné)所取代。显然,这两个变化体现了马里翁思想到后期更趋明确乃至成熟,也找到了更准确的表达。正是通过其本己显示的这四重特征,呼声使受召者或被呼者转化为或激进化为受予者。
首先来看呼声的“召唤”特征及其对“我”的影响与对受予者的创建。马里翁说:“召唤:被呼者经验到一种足够强烈的和强制性的呼声,以至于它必定在‘被移向’和‘屈从于’这双重的意义上转向呼声。于是它必定放弃自行设定(une auto-position)和自行实现(auto-effectuation)所具有的那种自满自足。”(40)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6.这即是说,我被呼声所召唤,我被转移向呼声并听从于呼声,在这个意义上我就不再是自我设定、自我实现的,也不再是自足的。我从主格转变为宾格或与格:“召唤的完全的冲击只是通过把[主格的]自我(leje)即刻转变为一个‘受呼的’我(me)才对我进行同一化;从主格向补语格(le cas régime)(41)le cas régime一般也译为“宾格”,但马里翁在该词后面括号里又补充了“宾格(accusatif)、与格(datif)”,而régime在语法上就是指“后置成分或补语”,所以我们这里把le cas régime译为“补语格”。(宾格,与格)……的这种转换因此颠倒了形而上学范畴之间的等级秩序:个体化的本质不再先行于关系……相反,关系先行于个体性。”所以,并不是先有一个自身同一的我,由这个我出发去建立关系。毋宁相反,正是在受到呼唤和接受呼唤之际,“我”才得到同一化或认同。所以马里翁接着说道:“由此产生一种原初的悖论:通过召唤,受予者自我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却一下子又从受予者那里逃逸出来,因为它接受这种认同而并不必然认识这种认同;因此它[受予者]是从它并没有加以清楚明白地思考的东西那里接受它自己的……[所以]主体性或臣属性(la subjecti[vi]té)服从于一种被本源地变异了的、被呼唤的同一性。”(42)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6-437, p. 437.可见,正是由于召唤或通过召唤,受予者才自我认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受予者是由呼声的召唤创建起来的。也因此,它的同一性就是一种本源地变异了的同一性,一种受到召唤且在召唤中才被创建起来的同一性,而非事先已存在的、在那里等待着召唤的同一性。
其次来看呼声的“突袭”特征。关于这一点,马里翁写道:“突袭:被呼者,作为一种召唤的结果,它承认自己被一种掌控(emprise)所支配和悬临(突—袭)。……呼声抓住受予者,借此突袭它,然而又并没有教给它这种呼声究竟是什么;呼声把受予者还原为仅仅窥伺在侧,让它原地不动……它与超越论的自我在其中……构造对象的任何知识的绽出都背道而驰。”(43)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7-438.可见呼声的突袭特征就在于呼声突然抓住被呼唤者,使其僵立不动,不再有任何主动的意向,不再有任何知识的绽出,从而也不再能构造对象。换言之,呼声的突袭使我的那种客体化意向性发生逆转,不再发挥作用。在呼声突袭我之际,我不是构造呼声,而是任由其抓住我、掌控我;我完全地接受而不再给予,并只在这种完全的受袭、受控中才发现、接受和认同我自己。
再次来看呼声的“会话”特征。需注意,这里所说的“会话”“根本不涉及这样一种对话处境,即两个对话者会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展开对谈;而是涉及一种不平等的处境:我处于被呼召状态,就是说被呼唤,甚至被冒犯”。因此在马里翁看来,呼声作为“会话”根本不是指他人与我的一种平等对话,而是指呼声呼召我、呼唤我甚至冒犯我。所以,“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人之被理解不再是根据主格(瞄向客体——胡塞尔),也不再是根据属格(存在的——海德格尔),甚至也不再是根据宾格(被他人控诉——列维纳斯),而是根据与格:我从呼声那里接受我,呼声把我给予我自己,在把它自己之所是给予我之前”(44)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8-439, p. 439.。换言之,受予者从召唤它的呼声那里接受它自己。这里可以看到马里翁关于作为“受予者”的“我”的一个崭新观点:我作为受予者,不仅不再是主格(从而与笛卡尔—康德—胡塞尔一系对自我的超越论理解相区别),也不再是属格(从而与海德格尔把自我归属于存在的做法相区别),甚至也不再是宾格(从而与列维纳斯把自我首先理解为被他人所控诉者区分开来),而是“与格”:在“我从呼声那里接受我,呼声把我给予我自己”这一意义上的与格(45)前文提及,马里翁在讨论呼声的“召唤”特征时把“我”同时理解为“宾格”和“与格”意义上的“补语格”,而在这里,马里翁则连“宾格”身份也从“我”中排除了,仅仅将其视为“与格”。。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成了受予者。由此可见,在语法上,“我”从否定的意义上说不再是主格与属格,从肯定的意义上说则是与格。而语法上的格的情况反映的其实是深层的实事状况,即我不再是给予者、构造者,不再是主体,而是受予者、受召唤者和被给予者。
最后来看“实际性”特征。马里翁说:“实际性:被呼者承受呼声,承受呼声的作为总已被给予的事实的要求;呼声的这一被给予的事实引入了被呼者的无可否认的实际性。”这里的“实际性”指的就是“个体性”,因为呼声这一事实使我个体化,使我作为这个我而独立出来:“呼声把我作为我自己给予我自己,简言之,把我个体化,因为呼声把我从任何的所有物或对所有物的占有中分离出来”,“是呼声……在我之先对[与格或宾格]我起作用;[主格]我唯有在这种情形下才存在:呼声总已经要求我自己并把某种类似我的东西给予我自己”。所以,并不是先有一个“我”在那里等待着呼唤。不,是呼声先呼唤,我才被唤起,才获得实际性,才被个体化为这个“我”。由此,受予者才得以“完全从它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其自己”,才“由被给出者给出”,才得以诞生(46)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39, p. 440, p. 411.。
至此,我们分别考察了呼声的四种特征及其对受予者的创建。而马里翁对呼声的这四重特征如何共同创建受予者做了如下刻画:“实际上,在认识一个对象之先(突袭),在观看他人之先(会话),[主格]我总已经在呼声的冲击(召唤)下被转变为一个[宾格]我;结果就是,我的独一无二的个体化或自身性就仅仅系于这一实际性,即被那从呼声处原初听到的而非我所发出的话语强加于我的那一实际性。”(47)Jean-Luc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 441.总之,是在呼声的突袭、会话、召唤及其强加于“我”的这一实际性的共同作用下,“我”才首先作为宾格或与格之我浮现出来,作为受予者被创建出来。
综上所述,马里翁正是通过如下步骤将自我一步步激进化为受予者:首先,确认现象是从其自身——而非从主体性(或其相当者,如此在)的给予方式——出发给出自身,这一自身给出着的现象自身是第一性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其次进一步确认,既然现象是由其自身给出的,所以它的这一自身给出就“拒绝任何自我对超越论功能的要求,或者——这是一回事——拒绝一个可能的超越论自我对其作为现象经验之最终基础的要求”,换言之,“自我就被剥夺了它的超越论的王位”(p. 56)。最后由此得出,“我”就从超越论自我——一个构造着的、给予着的主体——还原为一个受予者,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受予者,即既在接受自身给出者的意义上,又在它从其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它自己的意义上。所以,正是“从现象向被给出者的还原”,导致超越论的自我必然被还原为受予者。
但是,当超越论的自我被还原为受予者时,当它的构造、给予的作用被剥夺时,它是否就仅仅成了一个纯粹被动的接受者,因而仅仅起到被动接受的作用呢?这正是一些研究者对马里翁的质疑,比如麦金利就曾认为,马里翁忽视了接受者在接受中的解释作用或主动作用(48)Shane Mackinlay, Interpreting Excess, Jean-Luc Marion, Saturated Phenomena, and Hermeneutics, p. 2.。但事实上,马里翁并没有忽视。当马里翁不只是把我还原为“接受者”,更把我还原为“受予者”时,他正是想借助这个新术语来表达我的那种在超越论自我和经验性自我之外的新角色及其功能。对此他说道:“受予者(L’adonné)在失去了超越论的地位及其所含有的自发性或主动性的同时,并没有被归结为被动性或经验的自我。事实上,受予者就像超出了主动性那样超出了被动性,因为,在它从位高权重的超越论身份中解放出来之际,它就取消了超越论的自我与经验性的我之间的区分本身。”(p. 59)所以,虽然“受予者是由接受刻画其特征的”,虽然“接受当然暗含着被动的接受性”,但是,马里翁话锋一转,“[接受]也要求主动的姿态;因为为了提高到与被给出者相称的程度,为了保持住已到达者,[主动的]能力(capacitas)必须劳作起来——对被给出者加以劳作,以便接受它”(p. 60)。可见,马里翁之所以苦心孤诣地要用受予者这“第三个术语”来指称这新的“我”,就是因为这个作为受予者的我超出了主动性与被动性之分,同时又兼具这二重性。它不仅在接受,而且在接受的同时还在进行加工、劳作,而且这种劳作又是双重的:“既对被给出者加以劳作,以便接受它;又对自身本身加以劳作以便进行接受。被给出者每一次都要求受予者进行劳作,且只要它给出自身它就这样要求。”(p. 60)
给出不止,劳作不息;给出愈多,劳作愈多。为了让被给出者保持住进而显现出来,需要不断对被给出者进行劳作,这种生生不息的劳作就是受予者的现象学功能。
四、受予者的现象学功能
对于受予者的现象学功能的问题,马里翁曾如此刻画:“如果受予者不再构造现象,如果它仅限于接受纯粹的被给出者,甚至限于从被给出者那里接受自身,那么,它在现象性本身中还承担何种行为,进行何种操作以及扮演何种角色?”(p. 60)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马里翁先标出了在被给出者与现象性之间的本质性的间距,这一间距意味着“被给出者给出自身还不足以使它显示自身,因为被给予性往往几乎遮蔽了表现”。在马里翁看来,正是这一“在被给出者与现象性之间的本质性间距”使得“受予者”有了用武之地:“受予者的功能恰恰在于在其自身中衡量被给出者与现象性之间的间距:被给出者从未停止将其自身强加给受予者,并由其自身而来强加给受予者;而现象性则唯有在接受活动终于把被给出者现象化或毋宁说让其现象化的程度上且仅就此而言才能实现出来。”(p. 60)然而又是何者实现这一操作,即“把被给出者现象化”?正是“受予者”:“这一操作——把被给出者现象化——为受予者所固有,因为它具有这样一种艰难的特权,即构造出唯一的被给出者——在其中才会有所有其他被给出者的可见性。这样,受予者就把被给出者揭示为现象。”(p. 60)所以,“构造出唯一的被给出者——在其中才会有所有其他被给出者的可见性”,这一“艰难的特权”,就是受予者的现象学功能。借此功能,“受予者就把被给出者揭示为现象”,同时“被给出者与现象性之间的本质性的间距”也才得以弥合。
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受予者如何揭示被给出者?在何种程度上它可以这样做?换言之,这种被给出者如何能够从未见过渡为已见?马里翁“冒险”用了一个比喻来回答:“在这一方面,人们会冒险说:未被见到然而被接受的被给出者将自身投射到受予者(意识,如果人们宁愿这样说的话)上就像投射到一块屏幕上一样;这一被给出者的全部能力就像都重压到这一屏幕上一样,一下子激发起双重的可见性。”(p. 61)哪双重可见性?
首先是被给出者的可见性。马里翁说:“第一,当然是被给出者的可见性,它的直到那时仍不可见的冲击波爆裂、爆炸开来,四分五裂,这些四分五裂的轮廓是最初的可见者。”(p. 61)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受予者在被给出者从不可见到可见这一过程中的作用,马里翁又将受予者比作“棱镜”,而把被给出者比作原本不可见的“白光”:棱镜阻止不可见的白光,将它分解为基本的彩色光谱,它们才变得可见。与此类似,受予者接受并分解被给向它的东西,赋予其形式,从而才使其可见。所以,“受予者之所以能在接受被给出者之际将其现象化,恰恰是因为它构成了被给出者的障碍,通过成为被给出者的屏幕而把它拦截下来,并且通过对它加以调整取景而将它确定下来”(p. 61-62)。总之,受予者的作用或现象学功能,就在于它“作为屏幕、棱镜、背景,把纯粹的、未被见到的被给予者的冲击兑现出来,把它的冲力扣留住,以便把它的纵向力量转化为一种平铺开来的平坦敞开的表面”(p. 62)。
其次,受予者自身的可见性也是在被给出者对它的冲击中才被激发起来的。马里翁认为,从被给出者那里浮现出来的可见性也同等地激发起受予者的可见性。就是说,在接受被给出者的冲击之先,受予者本身并没有被看见。前文已说过,受予者作为受予者,已经被剥夺了原本赋予超越论主体的“皇家般的超越论地位”,就此而言,它已不再先行于现象,甚至不再作为已经在此的思想“伴随”着现象:它是从它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它自己的。既如此,它就并不先行于它所接受者,也不在接受之先可见。所以,正如前面棱镜模型所表明的那样,不仅白光在被棱镜阻拦、分解之前是不可见的,而且棱镜本身在阻拦、分解白光之前,就是说,在发挥其现象学功能之前,也是不可见的。因此,正是被给出者对受予者的冲击,才把受予者的屏幕照亮,从而使其从不可见变为可见。或者说,受予者正是凭借它使被给出者现象化这样一种操作本身而使自身现象化。简言之,被给出者的现象化或由不可见变为可见,与受予者的现象化或由不可见变为可见,实乃同一事件的正反两面,二者同时发生。
因此在马里翁看来,受予者与被给出者互为对方的“显影剂”:“被给出者把自己向受予者揭示出来,而这乃是通过把受予者向其本身揭示出来实现的。二者都是以被揭示者这样的模式现象化……受予者像被给出者的显影剂那样运作,而被给出者也像受予者的显影剂那样运作。”(p. 62)所以,被给出者与受予者互相成就,互相使对方可见。这也就意味着,被给出者与受予者在何种程度上由不可见变为可见,取决于受予者对被给出者带来的冲击的抵抗:“对被给出者……所带来的冲击的抵抗越大,现象学的光就越多地显示自身。抵抗——受予者的本己功能——变成了在显示自身者中给出自身的事物之转变的索引。”(p. 63)所以对于受予者来说,其功能既不在于主动的构造、给予,也不在于被动地逆来顺受,而在于逆来迎受:迎受给向它的冲击,抵抗这种冲击。正是在这种迎受与抵抗中,给向它的被给出者变得可见,受予者自身也一道变得可见。
五、结 语
如上所说,从笛卡尔开始,西方哲学即进入了以自我为开端和本原的主体性哲学时代。这一哲学到胡塞尔的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现象学臻至顶峰。在这一主体性哲学传统中,自我首先被理解为哲学沉思的出发点或开端,进而被理解为一切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和限制,最终被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构造性起源和一切对象的给予者。作为研究笛卡尔哲学的专家和晚近现象学的最重要代表,马里翁却对笛卡尔—胡塞尔这一主体性哲学传统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激进化阐释甚至解构:不再将自我理解为主体、开端、本原,而是将其理解为迎受、抵抗被给出者的受予者。而这一激进化理解之所以可能,又有赖于他对现象学还原的激进化理解:这种还原既不是胡塞尔式的向作为构造性起源的超越论主体的还原,也不再是海德格尔式的向此在之存在的生存论还原,而是向被给出者的还原,最终是向被给予性本身的还原。经过这一还原,现象自身就不再是由作为构造性起源的超越论主体或生存着的此在给出,而是由现象自身并从其自身出发给出。由此,自我就既不是超越论的构造性自我,也不再是生存论的此在,而是被还原为“受予者”,双重意义上的受予者:既在接受被给出者的意义上,也在从其所接收者那里接受其自身的意义上。而这一受予者的现象学功能,恰恰就在于凭其自身对被给出者所带来的冲击的抵抗或阻拦,使得被给出者从被给予进入显现,获得现象性,进而现象化。而且也正是在这过程中,受予者自身才显现出来,由不可见变得可见。由此,我们可以把被给出者带来的冲击、受予者对这种冲击的抵抗以及被给出者与受予者的显现这几方面的比例关系概括为:冲击越大,抵抗越强;抵抗越强,显现越多。
无疑,马里翁对自我的这一激进化理解(作为受予者)走出了传统对自我理解的双重模式及其困境,即要么把自我理解为作为本原的超越论主体,要么把自我理解为纯粹被动的接受者。他将自我理解为受予者,本质上是试图在作为起源的创造性自我和纯然接受性的被动自我之间给自我定位,以化解对自我的两种传统理解之间的张力。就此而言,马里翁对自我的这一理解的确更为巧妙甚至精妙,也更为切近自我之实事本身。
但另一方面,在马里翁的这一理解中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
首先,马里翁对自我在受予之前或倾听呼声之前的状态缺乏分析,亦即对自我何以“能受予”或“能受予”的条件缺乏必要的分析。这一缺乏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我们无法解释这样的情况:同样的被给出者作为呼声在给向不同的自我时,有的人能听到、受予并予以回应,有的人则根本听不到,对呼声完全麻木不仁,还有的人虽然听到了但却将其理解为完全不同的呼声,并因此予以不同的回应。所有这些不同显然需要对“自我”之“何以能受予”的条件作超越论的分析才能予以解答,但这一工作在马里翁这里还付诸阙如,就此而言,马里翁对自我作为受予者的分析更多的是形式化的。
其次,马里翁对受予者的现象学功能的强调有夸大受予者的作用而抹消外在性本身的危险,这尤其体现在他在回答我们如何辨认呼声的源头这一问题上。我所听到的呼声来自哪里?由何者发出?我听到的究竟是存在的呼唤(如在海德格尔那里)、他人的呼唤(如在列维纳斯那里)、上帝的呼唤(如在犹太教徒或基督徒那里),还是道的呼唤、良知的呼唤?马里翁对此的回答是:这取决于我的回应、我的决定、我的解释。他说:“这里总是存在着解释的结构……如果我们读海德格尔,我决定这是存在的呼唤;如果我们读列维纳斯,我决定这是他人的呼唤……总是我对回应做出决定。在回应中,我决定呼唤的来源本身。”(49)马里翁:《笛卡尔与现象学:马里翁访华演讲集》,方向红、黄作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65~266页。显然,马里翁的这一回应过于夸大了我的作用,因为如果呼声的源头究竟为何竟取决于我的解释、我的决定,那么这必然会导致呼声源头所具有的绝对外在性重新被还原、被抹消。而这不就又回到了超越论主体性哲学的老路了吗?这似乎是马里翁在把自我激进化为受予者时所未曾料到的结局。马里翁是否可能走出这一困境?对此,我们只能留待其他地方再予以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