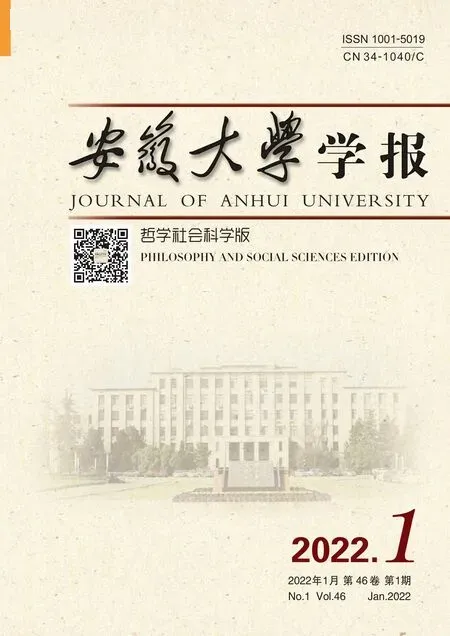诗律自由平衡说
孙立尧
一、诗的自由与限制
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有一句话常被引用,他说:“如果你取走维吉尔的语言和格律(language and metre),还能给他留下什么?”他还批评维吉尔缺乏“深厚的情感”(deep feeling),在柯尔律治看来,似乎“语言和格律”已经是维吉尔最大的成就了(1)James J. O’Hara, “Virgil’s styl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1.。事实上,维吉尔作为“全欧洲的经典”(“the classic of all Europe”,T. S. Eliot语),并且在近两千年之中都是西方经典的核心之一,其成就当然不止于此;然而退一步说,仅就其“语言与格律”而论,维吉尔也已经足够伟大,他对于“六音步长短格”(hexameter)之下种种句法的自如运用,同样是造就其伟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语言”与“格律”所代表的,其实正是诗歌艺术的两个层面:自由与限制。在诗歌的“格律”与“语言”两个方面,各有不同的自由与限制。同时,二者又交相为用,一个层面的“限制”,必然导致另一层面的“自由”,反之亦然。“诗歌语言”之所以异于普通语言,正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一切语言之下的诗歌,概莫能外。
在中国古典的范围内,杜甫之诗“集古今之大成”,独为诗家所推;尤其是其夔州以后诗,黄庭坚认为已达“不烦绳削而自合”(《与王观复书》)之境界,而陈善则谓其“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扪虱新话》卷1)。杜甫精擅各类诗体,而五排、七律之开拓,拗律之尝试,更兼收精密、萧散之长,其于诗律之纯熟,可谓毫发无遗了;细味老杜的夫子自道,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律细”和“浑漫与”,前者代表的是格律因素,后者代表的则是语言因素,二者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并行而不悖。
维吉尔、杜甫俱为百代诗宗,他们在“语言”及“诗律”两者之间,都已极尽了诗律的精细,同时又发挥了语言的自由。返观古今中外的大诗人,莫不皆然。诗歌以语言为载体,这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只是这种限制,读者往往习矣不察,而更多地强调其格律因素罢了。一切诗律,都给诗人以限制;而一切语言,诗人都拥有最大的自由。限制越多,自由也必越多;自由越多,而限制亦随之而至。就诗人而言,他们既在“语言”的自由中创造限制,也在“诗律”的限制中创造自由。无论是“诗律”还是“语言”,“自由”还是“限制”,它们在诗歌之中毋宁都是“守恒”的。
任何语言下的“格律诗”都具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性,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限制来源于节奏、音节数、韵式等等,其限制多寡不一,但总体趋向是使诗歌成为一种均衡的独特语言形态,而这种语言形态既与人的心跳、呼吸等生理韵律相呼应,也顺遂了读者的心理预期,从而产生均衡的美感。然而,语言传统的不同,却足以造成格律的千差万别,一种语言下诗歌语言的长处,却未必不是另一种语言之下的短处。
拿“用韵”这一特征来说,“尾韵”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代表性特征之一,即使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是“韵的艺术”也不为过。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之中的韵式,便已具备了多种复杂的形态。到唐宋时期,押韵更有严格的规定,一旦“落韵”,诗歌的创作便告失败;而“次韵诗”占据宋人的诗集的大量篇幅,成为诗人之间互相竞胜的重要载体,“窄韵”“险韵”的运用,更是诗人技艺的极端表现之一。而反观古希腊、罗马的诗人,他们却尽量避免使用“尾韵”,罗念生《格律诗谈》中曾举例说:
在古希腊文里,押韵是很方便的事,因为几乎每个动词都可以用来押韵,这是由于动词的词尾变化大致相同。有韵脚的诗行只偶尔见于古希腊剧的滑稽场面中。(2)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
由此可见,押韵若过于浅易,也为诗人所不取。然而与中国古典诗歌同样具有“尾韵”传统的英语、法语诗歌,它们运用“尾韵”的情形,与中国古典诗歌也有很大差异。英诗中的“尾韵”常被看作是通俗化的象征,尤其是在十六、十七世纪崇古风气盛行的时候。莎士比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莎剧中韵语的逐步减少,从《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爱的徒劳》之中韵语随处可见,到《李尔王》《奥瑟罗》《冬天的故事》之中几乎不用韵语,或者只是在一幕、一场之中作为“下场诗”之类的“更端之辞”(Speech-End Rhyme),是一个显著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据此为莎剧系年。当然,这里既有戏剧表达的因素,也有诗体本身的因素。素体(blank verse)长于叙事,韵语却偏于抒情,这正代表了莎剧抒情性的减弱以及戏剧的成熟。但由此也可见“尾韵”在英诗之中并不占据核心地位,因为莎剧的“素体诗”正是英诗中的主要形式之一(3)Frederic W. Ness, The Use of Rhyme in Shakespeare’s Pl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又如,“头韵”(alliteration)在西方诗歌之中司空见惯,古英语史诗如《贝奥武甫》等均以“头韵”的传统著称,“这种连续重拍产生一种粗粝声音,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经形象地说,这节奏犹如古日耳曼武士‘在酣战中一下一下的刀砍’”(4)王佐良:《英国诗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年,第3~4页。。现代英语诗歌之中,也不乏“头韵”的名句,如叶芝晚年名诗Long-leggedFly中有句云:
Move most gently if move you must
In this lonely place.
其句声韵极美(Move,most,move,must用头韵),令人击节。但在中国古典诗歌之中,除了双声词之外,如果多用头韵,便已等同于文字游戏。不妨举苏轼的《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为例,其序文中说:“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题一句云:‘玄鸿横号黄槲岘。’九曲亭即吴王岘山,一山皆槲叶,其旁即元结陂湖也,荷花极盛。因为对云:‘皓鹤下浴红荷湖。’坐客皆笑,同请赋此诗。”其诗云:
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角挂经。
篙竿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
解襟顾景各箕踞,击剑赓歌几举觥。
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
诗序中的对联及这首诗歌之中,每字皆用头韵,读起来既十分拗口,也不能增加诗歌本身的美感。正是由于这种游戏性质,这一对联才能够引起“坐客皆笑”,诗歌也成为“戏题”之作。所以,很难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之中具备一种“头韵”的传统。
因此,讨论不同语言之下的诗歌格律,不能不考虑语言传统本身。诗歌的自由与限制往往不在于“诗律”的形态,而在于“语言”的传统。从原理上说,二者应该取得相应的平衡。若诗律过于严苛,便极易发展成为纯粹的文字游戏;但诗律过于简单,诗人又必须为其增加更多的句法规则,以适应诗人的诗艺及才华的表现。同样,如果一切必须遵循语言的规则,则诗歌语言便会显得太过平凡;但如果诗歌的语言极端自由,过多地突破语法规则,便会造成诗歌之中的大量歧义,从而增加更多的解读难度。
二、诗律的“反语法性”
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曾说过:“令人愉悦的必要变化属于诗的艺术,而不属于语法的规则。”美国“新批评”派的主将之一维姆塞特(W· K· Wimsatt)在其所编《诗律学:主要语言类型》的前言中,特别征引了约翰生这一句话,作为该书前言中的题词(5)W.K. Wimsatt, Versification: Major Language Typ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2.。尽管诗歌的“反语法性”在不同的语言传统之下有不同的成因和特征,其程度也各不相同,但诗艺与语法本身,其矛盾却是天然存在的,而且早就被人所认识,并且几乎在所有的语言之中都是如此。
“反语法性”是语言趋于自由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往往是在“诗律”的限制之下产生的。就其浅近者而论,诗句之中音节的脱落或增加、词语的省略、词类的特殊用法以及灵活运用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反语法性”,这种情形在所有语言之中都有。例如,“音节变体”(syllabic variants)是莎翁诗句中的显著现象,如将“against”简化为“gainst”,“becomes”简化为“comes”等等,这在莎士比亚的诗作、剧作之中,其实是极其体系化的一个问题,已有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6)Dorothy L. Sipe, Shakespeare’s Metr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又如拉丁诗中常常省略必要的介词、系词,同时也出现很多的语言变体,如其过去完成时(perfect active indicative)中第三人称复数的词尾“-ērunt”常被“-ēre”所取代,而“esse”的将来时不定式“futūrus esse”又常被“fore”所取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大诗人在这方面似乎都拥有某些特权,荷马、维吉尔乃至但丁、莎士比亚,莫不如此。
西方诗歌中的这些形式,基本上是由于音节的因素,但同时也是风格化的象征;这样,每一位诗人的不同风格,都可以通过他的具有特征化的“诗律”来得到体现;因此,每一个重要诗人,都应该有属于他自己的“格律体系”。西方的大部分重要诗人,都有学者对其诗律进行专门研究;但在中国的古典诗人之中,连杜甫这样极其重视句律、集“句法诗学”之大成的诗人,也无专书研究他的诗律,更遑论其他诗人了。
然而,作为诗律中“反语法”的一般情形,中国古典诗歌之中当然也很多,自《诗经》《楚辞》以来的重要诗作之中,就已经体现出很多不同于散文句法的地方,但唐代以前的诗歌都属于“古诗”,如果要说诗歌的“反语法性”,其实还是律诗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王力《汉语诗律学》中有一段简要的概括:
古诗的语法,本来和散文的语法大致相同;直至近体诗,才渐渐和散文歧异。其所以渐趋歧异的原因,大概有三种:第一,在区区五字或七字之中,要舒展相当丰富的想象,不能不力求简洁,凡可以省去而不至于影响语义的字,往往都从省略;第二,因为有韵脚的拘束,有时不能不把词的位置移动;第三,因为有对仗的关系,词性至相衬托,极便于运用变性的词,所以有些诗人就借这种关系来制造“警句”(7)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
这里的“省略”,可以说是格律诗之中的通则。至于其效果,虽说不一定影响诗的语义,但如果诗句之中省略了一些重要成分,或者是省略过多的语言成分,其影响还是显然的。
一般而言,诗句中的省略法,如果将其省略语补上,其语句就会很完整,逻辑也很清楚;省略用语也不能过多,因为省略越多,诗句之中的语意断裂就越明显,词语之间的距离也就越大,它们的关系也就越不能精确地判断;但这种省略却可以造成特殊的诗歌效果,让诗歌的句法更显精警。其实,很多诗人正是利用这种省略,来构筑诗句的独特风味。王力在谈律诗“省略法”的时候,列有“略谓语”一类,但这类诗已经很难用“省略”来概括,比如他所举的杜律之例:
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江上》)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五首》之一)
这两联,王力将其分别补足为“勋业尚赊,频看镜以自惕;行藏未定,独倚楼而深思”和“时序迁流,百年之心已碎;乾坤浩荡,万里之眼徒劳”,这里补充的成分显然已经过多,而且王力也承认:“这些并不一定都是省去谓语;译为散文的话未必都很确切。但至少也该认为句子的某一重要部分已被省略了。这如果是在散文里出现,简直不成话;但它们在诗句里是被容许的,甚至显得是诗的特殊格调。”(8)王力:《汉语诗律学》,第271页。事实上,在此类诗句之中,诗人想要构建“特殊格调”的意图早已经超越了省略的需要,诗人在句中有不少意味故意隐而不发,从而制造符合“诗”的特性的“模糊语言”。
至于“词的变性”,在汉语的律诗之中固然司空见惯,但其实也可以视为各类格律诗的通则,只不过在不同语言之中,其用法略有不同而已;但它们所具备的艺术效果,却是相近的。如莎翁《麦克白》中的一句:
Father’d he is, and yet he’s fatherless.
(Act 4, Scene 2)
此处“fathered”是由名词转变而来的,但它与句尾“fatherless”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诗人刻意将其用在一行诗的首尾(因为首、尾都具有强调意义),既顺应了五音步的需要,同时麦克德夫夫人对丈夫的怨怼、对儿子的怜悯之情也彻露无遗,诗句极精警有力。
现代诗歌之中,如果运用此类手法,那么其风格也是“古典的”,这里不妨略举两例。事实上,凡是对于古典比较熟谙的诗人,对此都是比较注意的,如:
夏季随台风飘去,秋季随雨
惟遗恨皑皑屹立
——余光中《诀》
据说回国以后,这人不酒不烟
甚至也不太诗了
——杨牧《酒壶二题》
第一例之中加点字相当于“秋季随雨飘去”,属于省略的用法;而第二例之中,“不烟”“不酒”“不诗”则是词类活用,通过这些手法的运用,可以比较充分地展现诗中的古典风味,这可以是继承古典诗歌传统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多数现代诗人不大注意罢了。
然而,古典律诗中“反语法性”最强的表现,却是在“语序”方面。“语序”的解放,标志着“语言”的规则在古典诗歌之中的彻底破坏,它将汉语表达中最依赖的“语序”完全放弃,这正是在诗律绝对限制之下的绝对自由。
三、论语序:以杜甫与维吉尔为例
“语序”(word order)在西方诗歌,尤其是古希腊、罗马诗歌的研究之中,已经成为专门问题,但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之中,仍缺乏系统的论述。事实上,“语序”恰恰体现了“限制”与“自由”在不同诗律之中的不同表现。本节试以杜甫、维吉尔为核心,讨论汉语与拉丁语传统下的这一问题。
语言表达对于“语序”的依赖程度,汉语与拉丁语恰好处于两端:汉语的表达极端地依赖语序,而拉丁语的语序却极端自由。拉丁语是屈折语,句法以“格”(cases)的变化为中心,每个格在句中有不同的功用,词语的格一旦确定,它可以放在句中的任何位置,对于全句的意义都没有影响;而汉语之中,如主格必在动词之前,宾格必在动词之后,其位置不容随意调整。二者的差异体现在许多方面,又如,拉丁语中名词和修饰形容词的性(gender)、数(number)、格必须一致,因此它们虽然在句中的位置相隔极远,却并不妨碍其修饰关系;而汉语中名词与修饰它的形容词却必须连在一起。
在中国的古典律诗以及“六音步”的诗律之下,这两种语言的“自由”与“限制”也体现出相反的趋势。如果从诗律的限制角度来说,中国古典律诗的限制,在所有语言之中,也许是最为严格的;每句诗有固定的字数,声调上有平仄的限制,又有押韵的规定,还要讲求一联中的对仗、联与联之间的“粘”,等等。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格律”上的限制,必然导致“语言”上的自由,而以“语序”的自由最为突出。试看杜甫的几联诗:
1.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江汉》)
2.饭抄云子白,瓜嚼水精寒。(《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
3.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
4.细草留连侵坐软,残花怅望近人开。(《又送辛员外》)
5. 隐居欲就庐山远,丽藻初逢休上人。(《留别公安大易沙门》)
6.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秋兴八首》之二)
7.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滕王亭子》)
8.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九日》)
这里的诗句,诗律精丽而对仗工稳,音调极其和谐;但从语言上来说,正常语序中的种种限制大多已被打破,如介词可以放在名词之后(第1句;“共天远”、“同月孤”),宾语可以放在动词之前(第2、4、5句;“抄饭、嚼瓜”,“留连细草、怅望残花”,“初逢休上人之丽藻”),修饰形容词与名词也可以隔开(第3、7句;“青峰峦、黄橘柚”,“清江锦石丽”),不是修饰语的也可以放在修饰词的位置(第6、8句;“三声泪”、“无数新”),等等。这种情形的成因,往往是由于平仄、对仗、押韵等诗律的规定性而造成的。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本身的特性,说诗者便会对这些诗句有不同的理解,“歧义”或者“多义性”(ambiguity)固然可以给诗歌的解读添加一些内涵和色彩,比如将“三声泪”“伤心丽”“细草留连、残花怅望”等语句,按其字面意义来理解(9)这几句诗的解读,“三声泪”,如高友工、梅祖麟在《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尝试》中说:“在杜诗中,‘三声’似乎是在修饰‘泪’,使悲伤的情绪得到加强。”见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页。“伤心丽”,如毛西河说:“江石有伤心之丽,花蕊成满目之斑,此深于艳情之言。”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100页。“细草留连、残花怅望”,如赵大纲说:“‘留连’,就草言;‘怅望’,就花言。欧公诗:‘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亦同此意。”边连宝:《杜律启蒙》,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402页。;但从其本质上来说,却是由于语言的传统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杜甫是在“诗律”的限制之中,创造了“语言”的自由。
反观拉丁语的格律诗,它们在语序上极为自由,一个词与它的修饰语可以相隔很远,甚至也不在同一行诗中,如古罗马诗人Martial的讽刺诗(Epig.11.59):
Sēnōs Charīnus omnibus digitīs gerit
Nec nocte pōnit ānulōs.
句意是说Charīnus的每一根手指上都戴着六枚戒指,而“每六枚”(Sēnōs)和“戒指”(ānulōs)却分别放在此句的首尾,且又分置于两行,其跨度极大;诗句本身是用夸张之辞讽刺那些好炫耀财富的浅薄之徒——句首仿佛设置了一个悬念,到第二行的句末才揭开谜底,其强调意味和新奇之趣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只要稍稍研究就可以发现,拉丁诗中的语序其实已经形成了很多特殊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散文之中是罕见的。试以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为例,这是“六音步长短格”代表作品之一,如其卷1中的部分诗句(括号中为行数):
1.omnīsut tēcum meritīs prō tālibusannōs(74)
2.taurīnōquantum possent circumdaretergō(368)
3.Quassātamventīs liceat subdūcereclassem(551)
这三行诗的共同特征是一个词与它的修饰语分置于一行诗的首尾,为方便起见,不妨称之为“首尾句”,尽管在拉丁诗中很常见,但仍被视为是极具特色的一种句法(characteristic line-pattern),“将表示其性质特征的形容词与其所修饰的名词置于首尾,它们通常是一个紧密的句法组合”(10)R.G.Austin, Aeneid Ⅰ,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9.,其长处是诗句的首尾都得到了很突出的强调作用。句中分别以omnīs修饰annōs,以taurīnō修饰tergō,而以Quassātam修饰classem,虽然它们的“格”各不相同,但语意清晰,俱能得其妙用。这种句法在杜律中其实也有不少,但它们却是杜诗中最有歧义的一些诗句,如: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之八)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稍。(《堂成》)
林花著雨燕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酒》)
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立春》)
简单地说,这里的几句诗,都需要将其首尾之词合起来理解,前三句中题咏的是“绿笋、红梅”“香稻粒、碧梧枝”“桤林叶、笼竹稍”,而后两句虽稍有不同,但一样要理解为“林花湿、水荇长”“白玉盘、青丝菜”。有些诗句,自古以来就聚讼不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语序变化而引起的歧义,因为汉语之中并没有类似于拉丁语中“格”的规定,歧义是语言“自由”的必然结果。拉丁诗中还有两类句法值得注意:
4.vī superum,saevaememoremIūnōnisobīram(4)
5.NāscēturpulchrāTroiānusorīgineCaesar(285)
6.Asperatumpositīsmītēscentsaeculabellīs(291)
这几句都是所谓的“连锁语序”(interlocked order),第4句中以saevae修饰Iūnōnis(残忍的朱诺,二者皆为属格),以memorem修饰īram(未忘的愤怒,二者皆为宾格);第5句以pulchrā修饰orīgine,两者皆为夺格,以Troiānus修饰Caesar,两者皆为主格;第6句以Aspera修饰saecula,而positīs与bellīs合在一起构成“独立夺格”(ablative absolute),以表达一句的含义(战争平息了)。另一类是所谓的“丫叉句”(钱钟书译语,chiasmus),也很值得注意:
7.spemvultūsimulat,premitaltumcordedolōrem(209)
这里出现的是用语的对应平衡关系,第7句意为“希望强现在脸上,心底深埋着痛苦”,而在结构上,spem与dolōrem相应,都是宾格;vultū与corde相应,都是夺格;而 simulat与premit相应,都是句中的动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对称结构。第8句以lionēa与Serestum相对应,而以dextrā与laevā相对应,其原理相同。这种对称结构是内含式的,趋于静态;与连锁句环环相扣的动态颇有差异。如果拿杜诗与之相较,这两类句法很难在一句诗中出现,因为它所引起的歧义更大,试举两例:
云石荧荧高叶曙,风江飒飒乱帆秋。(《简吴郎司法》)
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郑附马宅宴洞中》)
“风江飒飒乱帆秋”一句,既可以理解为“江风飒飒秋帆乱”,也可以理解为“秋风飒飒江帆乱”,因为诗句在语序自由之后,其理解也随之自由化,如果是后一种理解,其结构类似于“丫叉句”。第二联也是奇格,诗句本是要表示主家之豪贵,故上句的“春酒”不可言“薄”,所谓“薄”,自当指琥珀杯,以见其制作精巧;下句的“寒”“碧”则意义相通,如果依照上句之逻辑,此联可理解为“琥珀杯薄春酒浓,玛瑙碗寒冰浆碧”,这样则差可拟为“连锁句”;然而边连宝认为:“琥珀薄,以杯言,而兼酒之色;玛瑙寒,以椀言,而兼浆之味。”(11)边连宝:《杜律启蒙》,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413页。这种含混理解的出现,自然也是因为语言自身的因素。事实上,这两种句法,中国古典诗歌之中,多在较大的结构之中出现(12)胡震亨说:律诗如老杜“待尔鸣乌鹊,抛书示鹡鴒;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排律如老杜“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之类。一顺续,一倒续。又如赠张山人:“草书应甚苦,诗兴不无神。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续至三联。白乐天以为诗有连环文藻,隔句相解者,起于鲍照之“扰扰游宦子,营营市井人,怀金近从利,负剑远慈亲”。其来有自云。见胡震亨《唐音癸签》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页。按:胡氏这里所说的“顺续”,即连锁结构;倒续,即丫叉结构。。
要之,以杜甫与维吉尔相比较,杜甫是在“格律”的限制下创造自由;而维吉尔则是在“语言”的自由下创造限制,两者的取向虽然不同,但对于诗歌特定风格的追求,以形成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却是毫无二致的。
四、论“自由诗”
通常所说的“自由诗”,即是现代的白话诗,或称新诗,有时亦可统称为现代诗。其基本的形式特征是与“格律诗”是相对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王力在《中国格律诗的传统与现代格律诗的问题》一文中,曾明确指出:
自由诗的反面就是格律诗。只要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写出来的诗,不管是什么诗体,都是格律诗。(13)《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
“格律诗”所具备的一切特征:押韵、平仄、粘对、字数及句数的限定等等,“自由诗”都能够从中解放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现代诗中的“现代格律诗”,却不能够算作“自由诗”。“现代格律诗”是一个争论纷纷而没有结果的问题,从闻一多、卞之琳、林庚、何其芳到余光中等人,都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试验。现代诗的格律是无法最终确定的,但毫无疑问,“现代格律诗”只能算是古典诗歌的延续,不管它是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部分形式,还是借用西方格律诗的形式。因为它的基本要素仍然是“尾韵”“音尺”或“音步”(甚至是字数)、诗的行数,还包括“吟调”“诵调”,只要这些要素还在,它就必定是“古典”风格的。古典风格的存在,并非不可以;每位诗人都可以具备自己的“格律”,但不必自我作古,为所有的诗人制定统一的形式。
另一方面,也是被更多诗人忽视的,就是诗的语言。依王力的判断,“按照一定规则写出来的诗”都算是“格律诗”,这里的“规则”肯定不能包括“语法规则”,否则再自由的诗也都是“格律诗”了。然而,“语言”本身却又是极其重要的,从前文论证可知,它与“格律”从来都是密切相关的。林以亮在《论新诗的形式》中认为:
有很多勇于尝试的人,做过不少把西洋诗移植到中国来的试验,把西方某一种形式,某一种体裁,或某一个作家的诗介绍到中国来。他们的工作,和提倡中国文化应“全盘西化”的主张一样,早已注定了非失败不可。因为他们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根本忽略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性质,构造和音乐性,而新诗无论怎样新,还是不能不用中国文字作工具。写新诗非用中国固有的文字和语言不可,正好像我们生下来就是中国人一样:这是一个不可避免,无可否认的事实。(14)《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第363页。
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中国现代诗而言,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和“传统的诗歌语言”并不相同;而对现代诗人而言,就存在如何兼顾的问题。
从“诗律”的角度来说,由于限制的减少,现代诗的“自由”已经达到了极致,它的唯一限制就是“分行书写”(15)这也是很多诗人和学者的共识,如林庚认为,自由诗在成功地构成自己的新格律之前,“除了分行之外更别无任何阵地”。见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9页。;但是另一方面,现代诗的“语言”限制却大大地增强了,它通常应该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在汉语诗歌之中,“格律”原本是突破语言限制的基本理由,但自由诗放弃了“格律”的限制之后,其语言的自由也就同时失去了。
因此,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现代诗又是“最不自由”的诗体,现代诗的语言与口语没有太大区别,所以现代诗给人的整体感觉,必然也是通俗的、口语化的。事实上,“格律”原本是诗人的利器之一,只需比较一下俞平伯等深谙于古典诗词的诗人们所创作的“格律诗”是如何的老到,而他们的“白话诗”又是如何的稚嫩,便不难明白:“格律”,作为古典诗歌艺术的核心之一,已经最大程度地失落了。反观大部分现代诗人,或执着于对西方“现代感觉”的借用,以增加所谓的“深度”;或者滥用“分行”的技巧,写成一堆似诗非诗的分行材料,就可以明白现代诗的困境。何其芳曾提出一个设想:
先受过一个时期写格律诗的训练,再写自由诗,总不至于把一些冗长无味的散文的语言分行排列起来就自以为是诗吧。(16)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见《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第371页。
但若想以此来提高现代诗的语言水准,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从根本上说是处于诗歌“自由与限制”的两端:“格律诗”有格律的限制和语言的自由,而“自由诗”却有格律的自由和语言的限制。“格律诗”的艺术早已完熟,却未必完全适用于“自由诗”;“自由诗”的发展不及百年,事实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艺术技巧,却已经早早地趋向衰落。
当然,现代诗唯一的限制既然是“分行”,“行”的技巧本身也应该是值得用心经营的,尽管有一些诗人进行过积极的试验,比如说充分利用“跨行”的技艺,以及“行”与“行”之间的诗性空间等等(17)孙立尧:《“行”的艺术:现代诗形式新探》,《学术月刊》2011年第1期。,但显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自由诗”自然不必在“诗律”上继承古典诗歌,却可以在“语言”“句法”的传统上继承古典诗歌,这不失为现代诗发展的一种途径。这不仅可以将现代诗纳入中国诗歌的“大传统”之中,也能够让现代诗在“语言”上获得一定的“自由”,如郑愁予《错误》中的名句: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这里“向晚”及“紧掩”两词的后置,可视作古典诗歌的传统,它在构造特定音响效果的同时,也改变意象的秩序(18)杨牧评论说:一句无可回换的“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使愁予赫然站在中国诗传统的高处。“青石的街道向晚”绝不是“向晚的青石街道”,前者以饱和的音响收煞,后者文法完整,但失去了诗的渐进性和暗示性。诗人的观察往往是平凡的,合乎自然的运行,文法家以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诗人以时间的嬗递秩序为基准,见青石街道渐渐“向晚”,揭起一幅寂寞小城的暮景,意象转变: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见杨牧《传统的与现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1977年,第61页。。当然,如果诗人能够同时运用“行”的技巧,其效果会更加突出,如郑愁予的《残堡》:
趁夜色,我传下悲戚的《将军令》
自琴弦……
此处既强调了“自琴弦”这一古典意象,同时,“行”与“行”的诗意空间,也得到了展现(19)杨牧说:“倒装句法的使用,造成悬疑落合的效果。愁予继承了古典中国诗的美德,以清楚干净的白话,又为我们传达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悲剧情调。”见杨牧《传统的与现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1977年,第69页。。
古典诗歌的句法如“关系语”“名词句”等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省略”“词的变性”往往也是构成此类句法的技巧,如果受到现代语法的限制,这些句法在一行诗内便难以完成,诗人便常用“跨行”来表达,如杨牧《林冲夜奔》中所用的句法:
……
且吃我一刀
宛然是童年
大朵牡丹花
在你园子里开放
是浮沉的水莲仲夏
开满山池塘,是你
读书的朱砂
这段诗属于“博喻”,也是所谓的“荷马式比喻”(20)其用喻手法,在“荷马史诗”的传统上,可以参考《伊利亚特》第4卷第140~147行中一段典型的比喻场景,即潘达罗斯用箭射伤墨涅拉奥斯后的一段描写,用法很相似。亦即所谓“不切题的明喻”(irrelevant simile),即比喻经过展衍,已经脱离原诗的主题,比喻本身也形成了艺术上的自足。,其中糅合了中西诗法的传统。而在这里,“童年”及“仲夏”都指示时间,是将名词用作状语,其意为“在童年时代”“在仲夏时节”,这显然是古典句法的运用;同时,“夏”字也与“花”“砂”相韵。表示地点的状语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如同一首诗中的:
我是风,卷起沧州
一场黄昏雪
“沧州”即“在沧州”,可以视作省略用法。这种句法,继承了古典诗歌句法的精神,但在一行之内是不能成立的,经过现代诗“跨行”的技巧,则不但显得俭省有力,而且还可以构成一种特殊的效果。如这句诗在初读之下,本以为风烈,可以将“沧州”卷起,及读至下行,方才知道“卷起”的对象是“黄昏雪”,实际上便构成了一种“多义性”(ambiguity),而“多义性”也恰恰是现代诗人的艺术追求之一。但这些正是由于对古典句法的继承才能达到的。可以说,这样的诗句结合了古典诗与现代诗的共同特色,可以作为现代诗在句律发展上的借鉴。
要之,从现代诗的发展方向来说,继承古典传统的必要是不言自明的。但如何能够让自由诗的语言获得真正的“自由”,也有待于有心的诗人创造特定的“限制”,融入并修正中国诗歌的“大传统”。
五、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格律”和“语言”构成诗歌不同层面的“限制”与“自由”,前者显而易见,后者易被忽略,但诗律的平衡离不开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诗律的“自由”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守恒”。
第二,诗人在“格律”的限制下可以更多地创造“语言”的自由,中国古典律诗是突出的例证;同样,在语言、格律相对自由的情形之下,诗人也会积极地创造限制,古希腊、罗马“六音步”诗律中的“首尾句”“连锁句”“丫叉句”等即是有力的例证。
第三,诗歌“格律”的限制愈严,则“语言”的自由也越充分;相反,“格律”的限制愈小,“语言”的限制反而愈强,比较汉语“律诗”与“自由诗”的不同,其两极关系是显然的,它们也可以代表不同层面的自由与限制。
第四,就现代诗的发展来说,它所要继承的古典诗歌传统,更多地不在“格律”层面,而应在“句法”层面将其与现代诗“行的艺术”相结合,现代诗人不在于滥用“自由”,而要更多地学会创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