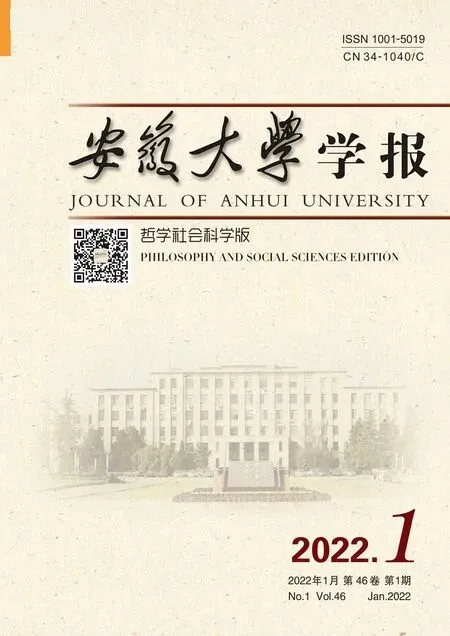论跨文化研究的殖民无意识
顾明栋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席卷全球的反帝反殖运动风起云涌,前殖民地纷纷独立,殖民主义的历史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由于殖民主义500年的扩张历史,殖民主义的后果在全球无处不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深受其影响,只是表现方式大不相同而已。由于殖民主义500年的历史和深刻影响,全球的文化意识虽然在政治层面与过去的殖民主义已无多少直接的关联,但其核心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以新殖民主义的面貌而呈现,特别是在精神领域和文化领域产生作用,因此,精神领域的去殖民化仍然是任重道远。新殖民主义的精神内核就是汉学主义理论所探讨的文化无意识。我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世界范围的文化无意识会表现为殖民无意识及其变体,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隐藏在人们无意识深层的殖民意识常常会露出地表,以有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久前香港一些人在游行示威中打出英美的国旗,恳求英美干涉香港事务,就是殖民无意识因为没有经历去殖民化的过程而抬头的鲜活表现。新殖民主义的种种表现促使我们去反思去殖民化的最终结果——去殖民性,这一议题已在跨文化研究领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后殖民研究的新课题。去殖民性绕不开全球文化无意识的去殖民化问题,因为彻底的去殖民化的标志就是文化无意识中无殖民性。本文拟通过考察跨文化研究领域几个涉及现代性、后殖民研究和汉学主义的学术问题,分析文化无意识的殖民属性及其在不同社会和不同身份的人群中的表现,一方面批判性反思前殖民宗主国家的人们的文化无意识,另一方面使第三世界的人们认识到有意无意的自我殖民和精神殖民的危害,从而为跨文化研究领域文化意识的双向去殖民化做出贡献。
一、西方文化无意识的殖民性
我们首先来分析西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如何成为殖民无意识的历史条件和心理机制。自工业革命以来数百年,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世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把广大的亚非拉地区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其在各方面的全面领先地位,表现在地缘政治领域就是“只要在东方一个国家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征服那个国家”,在思想精神领域则灌输欧美人肩负着给野蛮民族带去启蒙理性和文明进步的“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的理论,导致白人优越的自大意识,这种意识统治了西方思想达数百年之久。但随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席卷全球的反殖民运动和其后的去殖民化,西方的白人优越情结被压制到无意识层面。当前,除了少数新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外,很少有西方人会公开支持西方文化优越、非西方文化低劣的论调,即使有西方人宣扬白人至上,不仅没有多少市场,还会遭到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尽管如此,西方优越论并没有因为殖民主义在全球的崩溃而随之消失,这就好像一棵大树被砍到了,但如果树根没有被刨掉,还会不断冒出小树来。殖民主义的物质之根是强大的工业化带来的船坚炮利,其精神之根则是以启蒙理性、文明进步为标识的现代性。现代性在中国学界通常被视为一个积极正面的概念,不少中国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甚至有着宗教式的迷恋,但在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德里达、拉康、福柯等西方思想家眼中,现代性却有着阴暗肮脏的另一面,在其论著中,他们致力于揭露现代性是如何与殖民主义共谋,统治、奴役、压迫、剥削非西方的人民。当前在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兴起的“去殖民性”运动也把现代性视为殖民主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根本原因,因而把给现代性祛魅列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本文希望指出的是,正是殖民地宗主国和被殖民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缺乏足够的清醒认识,使得白人优越论在精神思想领域难以被彻底根除,至少是在无意识层面难以消失,而且常常以主体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方式表现出来,包括在学术研究领域。在政治外交领域,特朗普鼓吹的“美国优先”其实就是白人至上的情结以改头换面的形式从无意识层面突入有意识层面的生动表现。在文化生活方面,欧美社会经常出现的侮辱、谩骂、殴打,甚至枪杀有色人种的事件更是殖民无意识付诸行动的极端表现。涉及中国人和文化,西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常常表现为在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下对华裔和中国人的轻蔑和公开侮辱,甚至是恶言谩骂和拳脚相向。而且这些举动不只是出现在西方国家,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言行有时竟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公然表现出来,比如前几年德国奔驰高管因停车纠纷谩骂、动用辣椒喷雾喷洒中国居民的事件(1)见《奔驰高管辱骂中国居民后续》,“人民政协网”2016年11月24日报道,http://www.rmzxb.com.cn/c/2016-11-24/1168308.shtml.。笔者仔细分析过最近几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些案例,认为只有以西方人自大情结为核心的文化无意识才能解释这些辱华现象。笔者注意到,在中国发生的辱华现象基本上是西方人在与中国人发生口角和冲突时爆发出来的,也就是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一时的激愤之举,无论是破口大骂中国人,或者动手殴打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激愤的情况使人丧失理智,辱华行动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鬼使神差”的勾当,而“鬼使神差”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受无意识的力量所驱使,肇事者在事后冷静下来恢复理智以后往往感到后悔、羞愧,进而诚恳地赔礼道歉。这时,非理性的意识被压制到无意识层面,而理性的文化意识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和西方人的文化无意识的相遇会产生林林总总十分怪异的现象。比如,一些西方汉学家,只因在中国研究某一领域小有成就,一到中国就成了汉学大师;连不少学术极为平庸的西方学者到了中国也被尊为“知名”学者,在各大学招摇过市,开讲授课,中国学界虽然有人私下颇有微词,但由于种种原因极少提出公开质疑,相反有些学校还以能请到这样的“知名”洋学者为荣。笔者曾经问过一些大学的学者为何要把这样平庸的学者奉为上宾,顶礼膜拜,得到的回答是:请几个西方学者至少可以充充门面,提高学校的国际化程度。甚至有国学研究者也渴望得到国外汉学家的认可,并以此认为要高于国内同行一等。李零先生曾经对这种心态有辛辣的嘲讽:有些学者“死乞白赖想让人家引用和承认,以为只有得到他们的重视,才算为国家挣了脸,也比国内同行高了一大截儿”(2)李零:《学术科索沃: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3页。。这些都是典型的文化无意识的殖民性的鲜活表现。
在多数情况下,文化无意识催生的是无意识文化,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对西方文化表现出不自觉的崇拜,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不自觉的轻蔑。无意识文化也刺激了本来正在逐渐消退的西方文化无意识,一些西方学者在国内被尊为上宾,顶礼膜拜,国内学者有意无意的抬举使得一些西方学者的自大情结常常从被压抑的文化无意识层面回归到有意识层面。结果,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旧的殖民主义让位于新殖民主义,欧美的他者殖民也被非西方国家的自我殖民和精神殖民所代替。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西方的汉学在中国甚至得到了无由头的追捧,西方汉学家的一些观点,常常在没有被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被奉为圭臬,出现了为一些有识之士所批评的“仿汉学”和“汉学心态”(3)见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在此用文化无意识分析一个例子。有一位在中国名声很大的西方汉学家,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耸人听闻之语(4)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发了一则消息,题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该文经过 “新华网”转载之后,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谁知在国内竟然赢得一片喝彩,全国那么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竟然只有微弱的反对声音。中国文学有没有垃圾?平心而论,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哪个国家都是一样,既有垃圾,也有美文,但断言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那就得有所根据。本人与那位汉学家有过接触,对于他的垃圾说,笔者一直感到不解,很想知道他说出此话时的心理状态,甚至想写信问他,中国当代有那么多作家,发表了那么多作品,不知您看了多少?您的断言又有什么根据?后来,我从北大一位教授那儿得知,他曾当面向那位汉学家提了我想要问的问题,而那位汉学家的回答竟然是:没有看过多少当代作品。北大的教授进一步追问:您既然没有看过多少当代作品,怎么能得出当代文学几乎都是垃圾的结论呢?他的回答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我知道当代作品质量不好,质量不好的作品我为什么要看?”学术的规范和常识告诉我们,一位评论家没有看过作品,怎么知道作品的质量不佳?又有何资格对作品发表评论?我们如果深入分析这一回答,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他的言下之意是,我不要看就知道没有什么好作品。如果进一步追问,您不看怎么知道没有好作品呢?进一步分析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在内心早就知道,至少是当代的中国作家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如此一来,这种对中国当代作品的成见其实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在产生作用。
自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一直怀有一种无意识的自大情结,在温文尔雅的表面常常掩盖着连西方人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无意识轻视。笔者在国外生活多年,屡屡见到自信满满的西方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他们有些人在自己那一个小小的领域做出了一点成果,就以为自己的一亩二分自留地可以囊括中国学问的广阔天地,对中国学术领域指点江山了。笔者曾在拙文《中西研究的政治无意识》中批评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判,指出他们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将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我曾提到斯坦福大学某著名汉学家在西方媒体上对工程的严厉指责,他声称西方学界会对两百多位中国学者几年研究的结果不屑一顾。在质疑中国两百多位学者耗时数年的研究的同时,他却声称独自一人澄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所有的问题,并认为他的研究比浩大的中国专家团队的研究更为可靠、更为优秀。他甚至自信地宣称自己单枪匹马攻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要解决的所有的年代定位问题(5)Cf. D. S. Nivison,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West Branch meeting, October 1997, Boulder Colorado.。“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没有错误?肯定会有!可以不可以批评?当然可以!但批评必须建立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之上,不应被政治立场影响判断。但有些西方学者的批评走的正是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不过这次不是批判殖民主义的学术,而是对第三世界学术的口诛笔伐。即使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也没有多少道理。笔者亲身参加了美国亚洲研究年会“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讨会”,在会上,面对一些西方学者咄咄逼人的批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代表李学勤先生从容不迫地回答了提问和批评,令人信服,十分有力地否定了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指责。那次年会围绕“断代工程”一共有两场讨论,由于某些原因,笔者没有旁听第二次会议,但我事后曾向一位在某一名校当教授的西方汉学家询问他的看法。他和我有完全一致的评价,即李学勤等人的答辩十分有力地否定了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指责,他甚至对我说,他真为那些吹毛求疵的西方汉学家同仁感到羞愧。看了以上的案例分析,人们不禁要问,西方学者的无比自信来自何方?500年殖民扩张的无往不胜、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丰富等等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西方人的文化自信的底气来自其500年殖民扩张所积累的文化无意识。文化无意识不仅是殖民主义的隐性逻辑,也是西方民众“白人优越感”的精神支柱,在后殖民的全球化时代,也是东方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各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层逻辑。
二、中国文化无意识的殖民性
中国曾是个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帝国主义从没有完全征服过中国,有人可能要问:中国的文化无意识怎么会有殖民性呢?对此问题,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文化无意识不仅有殖民性,而且,正如笔者在以前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分析的那样,其程度丝毫不亚于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化无意识(6)涉及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南京大学学报》 2010年第1期;《汉学主义: 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方法论之批判》,《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汉学主义的历史批判》,《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西方的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走出语音中心主义——对汉民族文字性质的哲学思考》, 《复旦学报》 2015年第 3期。。在此,笔者想分析一篇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7)邓伟:《从“东方主义”和“汉学主义”看跨文化研究中“强制阐释”的出路》,《江汉学刊》2017年第11期。本段出自本文的引文不另注。,该文涉及后殖民研究、东方主义、汉学主义、现代性和强制阐释等重要理论问题,通过分析文中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看法,旨在揭示学界存在的一些文化无意识现象,说明殖民无意识如何在不知不觉之中演变成清晰的文化意识。该文通过批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和汉学主义理论的所谓“强制阐释”,号召“克服以‘东方主义’和‘汉学主义’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思想和理论,才能走出‘强制阐释’的迷途”。笔者不打算对其全部内容、观点、论证、学术规范等问题展开分析,只想通过一些文本分析、揭示该文在中国当下语境下不自觉流露出的殖民无意识心态。
开篇不久,作者就批评现当代中国学者在世界文论领域没有提出原创性的理论、做出思想的贡献。的确,在现代,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提出许多原创性的理论、做出多少思想贡献,但我们不应置这样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即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强迫中国支付天文数字的赔款,导致中国陷入上百年积贫积弱的苦难境地。像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那样,当中华民族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偌大的中国都没有一张可以坐下来读书做科研的桌子,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谁还能指望中国知识分子能像西方列强的知识分子那样,吃着奶油面包,悠哉游哉地喝着咖啡,全神贯注地思考着科技和文化的问题,提出“独创性”“突破性”的理论?我们也不应无视这样的情况:在全盘西化、骨子里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低一等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支配之下,中国学界唯西方马首是瞻,导致中国人原创力的萎缩(在此应该强调的是,这一情况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有较大的改观)。可以这样讲,中国上百年积贫积弱,在现代没有像古代那样对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奴役、精神殖民和文化殖民。对此,那篇文章表面上也不否认:“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代表的文化霸权,批判是必须的、紧迫的任务”,可是话锋一转却告诫读者说:“但一定要超越民族义愤、苦大仇深才能克服之前许多批评流于表面的问题。”作者真的能容许对西方霸权的批判吗?我们在此不妨以文本证据说话。笔者在有关汉学主义的文章中对西方思想家和学者从西方的立场出发曲解、误读甚至贬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文化霸权做了相当多的批评,那篇文章作者的反应是:“这一点令笔者印象非常深刻:顾教授用很长篇幅列举了大量西方学者在汉学研究中把持方法论、认识论霸权的案例,以及一些中国和华裔学者的‘自我汉学化’现象,其表达充满苦大仇深的民族义愤。”又是一句“苦大仇深的民族义愤”!文中还不止这两处,紧接着下一段,作者又说:“对西方霸权和‘自我东方化’现象展开批评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定要避免苦大仇深、流于表面。在批判西方霸权的同时一定要结合对本土霸权的批判……本土霸权是一种包裹着‘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的外衣,占领了道德高地而不易被察觉的‘自我东方化’。”这里作者错误理解了“自我东方化”的含义。笔者很难想象,会有学者对从事后殖民研究和批判殖民主义的人发出“避免苦大仇深”之类的劝告,这样的劝告在西方学界是只有极端保守主义学者才会说出的言论,而且会受到主流学界的批评。遗憾的是,作者竟然没有意识到一个东方学者、第三世界的学者发表这样的言论才是真正的“自我东方化”。三个“苦大仇深”不仅贬低了中国学者对西方霸权的反思性批判的思想意义,而且混淆了批判西方霸权与批判本土霸权的逻辑理路,将两个学术问题裹挟在一起,实际上是对西方霸权这一客观事实的间接否定。
该文还有一些证据不仅暴露了无意识的殖民性,而且使人觉得作者不知不觉地成了西方价值的辩护士和中国价值的抨击者。作者一方面把萨义德等后殖民学者描绘成靠出卖前殖民地人民的痛苦而在西方学界谋求个人地位的投机者,另一方面把中国的后殖民研究批评为“主观预设”的“强制阐释”:“中国后殖民批评所鼓吹的 ‘第三世界文化理论’ 在这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 从这种理论的 ‘强制阐释’ 视角出发, 当今世界文化的主要矛盾是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间的文化冲突与矛盾。”作者曾对中国学者没有提出原创性理论表示出不满,但是当第三世界学者试图通过质疑西方学术、提出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时,他却又不以为然。然而在当下的国外文化研究领域,这正代表了一种新趋势,即“去殖民性”运动,提出“去殖民性”的西方学者不仅提倡要与西方认识论和知识体系脱钩,还要从殖民主义到来之前的原生态传统汲取资源,完成第三世界的认知重构和知识重组(8)Nelson Maldonado-Torres, Thinking through the Decolonial Turn: Post-continental Interventions in Theory, Philosophy, and Critique—An Introduction, Transmodernity, Fall 2011, pp. 1-15.。但中国学者在这个方向刚要迈步,就被那篇文章作者当头棒喝:“为了取代这些支撑我们现代化进程的西方核心人文价值,中国后殖民批评炮制并抛出了‘中华性’理论,与西方文化展开对抗。‘中华性’理论炮制的所谓‘中华文化圈’,以中国大陆为核心层,第二层是港澳台,第三层为海外华人,第四层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我们应注意作者的用词:提到西方文化时用的全是褒义词,而提到中国思想则使用了“炮制” 等贬义词。作者对张颐武等提出的“中华性”(9)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主张大加挞伐:“这种打着后殖民主义的旗号,将民族文化本质主义化,拒斥、对抗西方文化,否定中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的文化认同中心,其力图重返世界文化权力中心,谋求新的文化霸权的意图非常明显,已经完全与后殖民主义关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论断背道而驰。”这样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后殖民批评理论和最新进展缺乏深入了解,才会将中国学者重振中国文化的努力视为“谋求新的文化霸权”。中国人提不出新的思想、概念、理论,他们冷嘲热讽,中国人提出了新的观念、理论,又被其抨击为有“重大理论缺陷”的“文化民族主义”。对于海内外华人学者提出的汉学主义理论,该文在连“强制阐释”都不做的情况下就给出了这样的价值判断:“‘汉学主义’总体上弊大于利。 在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话语长期占据主流,现代性进程尚在路上的中国,如果将 ‘汉学主义’运用于学术研究,极易引发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导致新一轮的思想混乱和思想封闭。”这种罔顾事实、不经论证的断言处处透漏出殖民无意识倾向。试问: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思想界是民族主义还是全盘西化占据的时间更长?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是民族主义排外情绪还是崇洋媚外和拿来主义?
颇具嘲讽意味的是,与作者讴歌西方现代性相反,西方的思想家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早已开始质疑西方的现代性,认为其并没有完成其设想的乌托邦式的启蒙主张,其实是一个大规模骗局(mass deception)(10)Cf.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in Vincent Leitch, et al, eds.,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2008, pp. 1120-1127.,而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现代性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11)Jurgen Habermas, 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 in Vincent Leitch, et al, eds.,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pp. 1577-1590.,更有西方思想家们重点探讨现代性在历史上的毁灭作用,如世界著名的社会理论家、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杰弗利·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其深受好评的社会学名著《现代性的阴暗面》的主旨介绍中指出:“现代性的观点体现了启蒙主义进步和理性的崇高愿望,但是现代性的现实是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暴露了其仍然在激发人类走向毁灭的动机。”他进而告诫人们:“认为现代性可以消除邪恶的想法是危险的妄想。”(12)Jeffrey Alexander, The Dark Sid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3.引自该书主旨介绍。在西方跨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领域,当前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批判现代性的阴暗面,众多后殖民研究学者以充足的历史资料证明现代性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征服、殖民压迫和剥削、奴隶贸易、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成为掩盖殖民主义罪恶的一块理论遮羞布。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论去殖民性》一书,该书是杜克大学出版社“去殖民性”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在该书的导论中,创造了一个与福柯的“权力—知识”类似的新词,“现代性—殖民性”(modernity/coloniality),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明的:“现代性当然不是一个去殖民性的概念,但是殖民性是的。殖民性不是衍生自现代性,而是由现代性构成的,这就是说,没有殖民性就没有现代性,因此才有‘现代性—殖民性’这一复合词。”该书甚至做出连笔者都有点难以接受的激进断言:“现代性的终结就意味着殖民性的终结,去殖民性因此也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13)Walter Mignolo and Catherin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Concepts, Analytics, Praxis, pp. 4-5.这样的论述几乎将现代性与殖民性等而视之。西方学者对现代性与殖民主义共谋的强烈批判反衬出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殖民无意识是何等深厚。
笔者不必分析该文更多的其他观点了,已有的文本分析足以证明这样的论断:这是一篇含有殖民无意识而丝毫不觉的文章,由于不知不觉的殖民无意识,文章在没有搞懂后殖民理论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就对第三世界学者提出主观性批评,而对西方文化和学者,包括日本的汉学家则表现出高山仰止尊敬有加的态度。该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以殖民无意识为核心的文化无意识。由于其文化无意识的作用,该文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状态。该文开宗明义声称后殖民批评和汉学主义是“强制阐述”的理论,但其论争的方法恰恰是一种前后矛盾的“强制阐述”。在文章后面作者又对汉学主义表示了支持的看法:“笔者认为, 顾明栋教授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缺陷辨析得比较到位, 认为二者解释中国文化会出现 ‘强制阐释’ 现象, 对一些中国学者将西方视角内化为自己的研究范式的批评一针见血。”此处的前后矛盾一目了然。读者可能会问:怎么会出现这样前后矛盾的看法呢?笔者认为,一方面,该文作者口头上反对“强制阐释”,但实际上走的正是强制阐释的路径,预设主观立场,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造成这种自相矛盾不能不说是殖民无意识导致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结果吧。
三、文化无意识的去殖民化
上文对文化无意识性质的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全球语境中的文化无意识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就是一种殖民无意识。殖民无意识的内容多种多样,在跨文化研究中,前殖民宗主国的人民和前被殖民国家的人民的文化无意识内容是不一样的,但它们的形成和运作方式却一样,都是500年殖民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差别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14)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拙文《论文化无意识的双向去殖民化》,《学术界》2020年第4期。。无论是以文化优越感和自大情结为中心的西方人的文化无意识,还是以崇洋媚外、自认文化不如西方的自卑情结为中心的东方人的文化无意识,都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殖民权力通过工业化带来的硬实力和标榜文明进步的现代性所带来的软实力的协同作用,并经过较长时间积淀而生成的心理和精神结果,其运作方式都是文化无意识通过前意识对意识产生作用,以常常不为人们觉察的方式影响、左右人们的行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传统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和学界青睐拿来主义,中国文化不太容易产生强大的对精神殖民和自我殖民自觉抵制的心理防护机制。相比之下,中国人很容易认同西方文化的价值,贬低自己文化的价值,在思想领域和精神层面以自我殖民去迎合西方的他者殖民,有意识无意识地认为自己人种低劣、文化落后,比不上优越的西方文化。这种文化无意识常常以有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思想界就是“黄土文明”的落后, “三百年殖民地”的必要性,“中国在现代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凌辱、压榨是因为中国人拒绝现代文明”;在普通民众中就是追捧西方的生活方式,极端的案例就是“带路党”欢迎西方带来“解放”,并表示愿意为这种“解放事业”甘效犬马之力,还引以为豪;在学界就是唯西方学术马首是瞻,实行绝对的“拿来主义”,导致认识论的惰性和原创性的萎靡不振,对于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和实践,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就给批判者扣上一顶“文化民族主义”的帽子。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对于一些殖民无意识已深入骨髓的学者而言,后殖民理论和汉学主义理论是弊大于利,甚至是无价值的理论。这种对后殖民研究的贬低证实了笔者以前的一个直觉:与西方学界后殖民研究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繁荣现象相比,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没有像其他西方理论那样得到持续的关注,呈现出后殖民研究专家赵稀方先生所说的“从未到来,却已过去”的昙花一现的状况(15)赵稀方:《从未到来,却已过去》,《读书》2016年第5期。。后殖民研究在中国学界所受的冷遇与无意识层面的殖民心态恐怕不无关联吧。后殖民理论主要是由在西方的第三世界学者提出的,汉学主义也是海内外中国学者提出的,都对西方文化持尖锐的批判态度,显然不合那些有意无意地唯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味。
当下的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所谓的“去殖民性转向”,拉美著名思想家奎加诺(Aníbal Quijano)将殖民主义的逻辑概念性构思为“权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16)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of Power, Eurocentrism, and Latin America, 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Vol. 1, No. 3, 2000, pp. 533-580.,美国去殖民性研究理论家米格诺洛(Walter Mignolo)进一步将“殖民性”构思为“权力的殖民母体”(colonial matrix of power),并以足够的论证说明,这一概念“可以发现西方文明的根本逻辑,及其自16世纪以来在全球的形成和扩张”(17)Walter D. Mignolo and Catherine Walsh, On Decoloniality: Concepts, Analytics, Praxis, p. 225.。笔者认为,这一深层逻辑就是现代历史演进过程中在认识论和知识生产方面发挥作用的殖民无意识。时至今日,政治的殖民化已走到尽头,其影响和后果主要存在于殖民遗产和人们的大脑之中,以文化无意识的形式出现并产生作用。根据殖民主义对全球意识的影响,世界的文化无意识也许应该被叫作“殖民无意识”,在文化殖民和精神殖民方面,“殖民无意识”构成了实现彻底的去殖民化和去殖民性的终极障碍。文化无意识是汉学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使知识和学术生产以及生活异化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前殖民地国家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原创性和创造力的一大杀手,也是阻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健康交流的无形障碍。文化无意识的去殖民化任重而道远,如果从佛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在20世纪50年代应用精神分析理论解释黑人的自卑情结和白人的优越情结(18)Cf.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lated by Richard Philcox, revised edition,New York: Grove Press,1994.算起,至今已有近70年时间,但全球文化无意识的核心——殖民无意识仍然鲜活地栖身于人们的无意识深层。要消除殖民无意识导致的异化现象,我们需要采用文化领域的精神分析对策。精神分析的指导原则就是古希腊雋克在泰尔菲神庙上的箴言——“了解你自己”(Know Thyself)——在精神分析医疗过程中,通过特殊的治疗程序,造成神经症的无意识心理机制被转化为对自己的有意识了解,从而导致神经症的痊愈。由于全球文化无意识的内在逻辑是殖民无意识,因此解决这一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一种类似于精神分析的策略,对无意识层面的知识异化、认识异化、生产异化和生活异化进行自觉反思和分析,使文化无意识通过去殖民化而转化为文化意识,从而使无意识的殖民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藻海无边》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