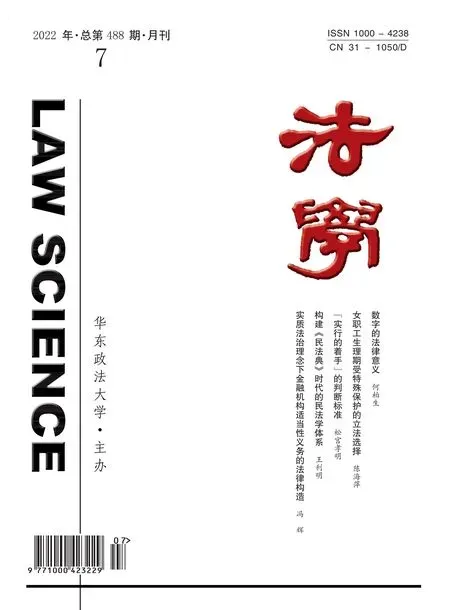Incoterms 何以在国际贸易中适用
——从 CISG 第9 条切入
●贺 辉
一、问题的缘起
为了减少进出口贸易商之间的买卖纠纷,将国际买卖契约之各式贸易条件定型化,明确规定双方之义务(obligations)、风险(risks)、费用(costs),使进出口业者得以在相同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交易,国际商会于1936 年制定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旨在规避贸易争议,保障国际贸易的顺畅运行,明确厘清贸易纠纷之基准。〔1〕参见黄培真:《Incoterms 2010®之研究》,载《台湾海洋学报》2011 年第2 期,第1-28 页。但是,国际商会属于民间组织,并不具有立法者的法律地位及相应的立法权限,制定出的Incoterms 并无直接的法律效力,〔2〕参见张锦源:《贸易条件详论》,三民书局2003 年版,第2 页。而且该规则已随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及需要更新了若干版本。〔3〕2020 版本是其最新版本,标志着国际贸易合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典型之商业惯例,Incoterms 对买卖双方的责任、交付以及风险等内容相对确定,但未能解决合同当事人在未约定适用Incoterms 或者何种版本的Incoterms 时该如何适用的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介入可优化Incoterms 的适用,使其契约性效力更加彰显。从某种程度上说,CISG 第9 条是赋予Incoterms 法律适用地位的重要依据。〔4〕该条源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组织并经多国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a Uniform Law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第一海牙公约》第9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a Uniform Law on the Formation of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第二海牙公约》第13 条)。参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正式记录》,联合国出版物1981 年,第21 页。A/CONF.97/19.第9 条分为两款,第1 款规定:“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明示同意某个国际商事惯例,那么这个国际商事惯例就明示地被并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依据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对当事人直接发生法律约束力。第2 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从功能上看,这一规定将特定贸易同类合同当事人“广泛知道”“通常遵守”的惯例直接视为对涉案当事人有约束力的规则。〔5〕参见宋阳:《“一带一路”商事仲裁中国际商事惯例适用问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20 年第2 期,第183-196 页。基于该规定,国内学者提出Incoterms 作为一种国际商事惯例是当然的国际商事的法律渊源,对当事人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6〕参见陈晶莹:《论CISG 项下国际惯例的效力——兼论我国〈民法通则〉第142 条的改良》,载《国际贸易问题》2011 年第4 期,第157-165 页。而且由于这种任意性的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更贴近当事人的意思,规则内容更为具体,更能体现商人的合理期待,所以理当优先于任意性国际商事条约和国内法任意性规定进行适用。〔7〕参见左海聪:《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特点及相互关系》,载《法学》2007 年第4 期,第97-100 页;左海聪主编:《国际商法》,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18-19 页。此种认知虽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但忽视了Incoterms 作为国际商事惯例最为核心的属性,且已对司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货物贸易国,从相关的司法裁判入手考察两国法院适用Incoterms 的实况,能够发现裁判者存在依据CISG 第9 条将Incoterms 直接归属于CISG 一部分的误区,借助条约解释法对CISG 第9 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Incoterms 何以能在国际贸易中适用、Incoterms 与成文法之间的适用顺位关系及优先适用条件等问题。
二、中美法院适用Incoterms 中存在的问题
梳理中美相关案例可以发现,不论是中国法院还是美国法院,在对Incoterms 认知和适用上均存在诸多值得怀疑之处。
(一)中国法院适用Incoterms 存在的问题
与国际惯例接轨是中国司法审判的基本理念,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甚至考虑不再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指向国际海商事惯例。〔8〕参见李健男:《论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6 期,第17-22 页。在此思路的指引下,司法机构在裁审过程中对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往往不加甄别,尤其是对于Incoterms 这种非常著名的国际商事惯例,法院更多的是以尊重为根本原则。
比如,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引用某个贸易术语作为价格条件时,法院往往会将贸易术语的功能范围人为地扩大,将其作为解释合同的基本规则来进行运用。在“Landmann(Macao Commercial Oあshore)Limited 与江苏惠宝翔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当事人选择了FOB 贸易术语为由,直接适用了Incoterms2000 的规定,将货物越过船舷的时间认定为双方约定的交货时间,既未考虑双方约定的FOB 术语只是出现在成交价格条款中,与交货时间没有必然联系,也未考虑Incoterms 的版本问题。〔9〕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35 号民事判决书。在“福州闽胜砂石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营业管理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在货物发票中注明的货物价格条件——“CIF 鹿岛”——这一信息作出认定:“在CIF 价格条件下,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因货物交至承运人之后发生意外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则应由买方承担。因此,自货物装上‘PIA FRONTIER’号轮后,案涉货物的所有权和风险已经全部转移给了买方。所以,只有买方才有权依据保险合同就货物的灭失向答辩人索赔,被答辩人无权向答辩人提起诉讼。”〔10〕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闽经终字第232 号民事判决书。法院不但直接根据Incoterms 的规定确定了货物保险利益的转移时间,甚至连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也根据Incoterms 对CIF 术语的字面规定一并确定了。
上述司法实践完全没有顾及当事人选择贸易术语时的真实意思,而且超越了贸易术语的功能范围和调整范围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分配,是完全错误的做法。同时,在适用Incoterms 时,法院几未对适用Incoterms 的理由作出说理和论证,而是将这种民间组织制定的规则认作是“理所应当”的裁判依据。〔11〕这样的例子太多,此处仅挑选几个典型性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02 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最高法民四终字第37 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民终205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甬商外初字第75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734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商外终字第0031 号民事判决书等。与之相较,在适用相关国内法和国际公约时,法院的态度则表现得比较谨慎,通常会仔细审查这些法律和条约的适用范围,但基于CISG 的法律体系定位及缺乏统一适用的机制等原因排除CISG 的适用转而错误援引中国国内法。〔12〕参见贺辉:《我国法院适用CISG 的问题、成因及改进》,载《法学》2019 年第4 期,第181-192 页。
(二)美国法院适用Incoterms 存在的问题
美国的司法实践情况与中国类似。在“St. Paul Guardian Insurance Co. v. Neuromed Medical Systems & Support, GmbH 案”〔13〕See No.00 CIV. 9344(SHS), 2002 WL 465312, at *1 (S.D.N.Y. Mar. 26, 2002).的判决中,法院犯了较为严重的推理错误,对该案的论证和分析亦不够充分且存疑。详言之,一家德国的医疗器械公司将一套昂贵的医疗设备出售给买方(案外人),并向原告保险公司投保。交货后由于不可归因于卖方的原因而致货物毁损灭失,于是原告在向买方理赔后代位向被告提起诉讼。审理此案的美国纽约南区法院认为,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CIF 纽约港”作为交易条件,那么根据本案准据法CISG 第9.2 条,Incoterms1990 的规定应视为被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国际商事惯例,即便书面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其作为解释CIF 的规则,也应认为Incoterms可以被整合(incorporated)成CISG 的一部分,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根据Incoterms1990 对CIF术语的规定,在货物自装运港越过船舷后,卖方将不再承担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因此原告在向买卖合同的买方理赔后无权向被告代位求取保险金。笔者认为,据此作出的判决至少忽略了以下三个重要事实:一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能够认定Incoterms 可整合成CISG 的一部分。本案原告并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虽然继承了买方的权利义务,但并没有完全参与买卖合同的谈判,那么让原告直接受Incoterms 约束的结论就值得重新考虑。二是CISG 本身也有关于货物风险转移之具体规定(如第30~34 条、第60 条、第66~69 条),但法院完全没有考虑这些规定就直接适用了Incoterms1990 的规定。虽然根据CISG 第6 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不适用CISG 或变更减损CISG 的规定,但其有一个“当事人需要有明确排除或改变CISG 规定的意思表示”的前提。〔14〕参见“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判例第107 号,2019 年2 月25 日公布。若将Incoterms1990 的规定作为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引入合同之中,则根据CISG 第9.1 条的要求,也需要当事人在合同中作出明示同意并明确引用Incoterms1990 才可以改变CISG 的默认规则。然而本案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中根本未以任何方式提及Incoterms1990。三是退一步说,即便根据CISG 第9.2 条的规定,将Incoterms 视为当事人默示同意的条款来约束当事人,仍然无法解决原告并非买卖合同当事人这一重要障碍。除此之外,法院也未根据CISG 第9.2 条的要求对Incoterms 进行“三步法检验”,即当事人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Incoterms1990 作为一种商事惯例存在;与当事人从事同样贸易活动的商人是否广泛知道Incoterms 1990 作为一种商事惯例存在;与当事人从事同样商业活动的商人是否通常遵守Incoterms1990 的要求。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案件当事人任何权利义务的增减都应该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进行,而不应当仅以法官的主观经验为依据。〔15〕该案件的影响较大,也被写入我国教育部推荐各大高校使用的马工程教材中并成为典型教学案例。参见余劲松、左海聪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第78 页;左海聪主编:《国际商法》,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 页。
在“BP Oil International, Ltd. v. Empresa Estatal Petroleos de Ecuador 案”中,营业地在美国的英国BP 石油公司将140 000 桶无铅汽油出售给厄瓜多尔的一家公司,合同约定了汽油中橡胶的最高含量,并约定了贸易条件为“CFR 拉利贝塔德港”。货物在出货港的检验中没有发现问题,但在到达港检验时发现了橡胶的含量明显超标,买方遂拒绝接受货物。法院在最终的上诉程序中同样适用了CISG 作为买卖合同的准据法,但犯了与前述纽约南区法院同样的错误,即根据公约第9.2 条将Incoterms1990直接整合到CISG 中,使Incoterms 被整合成为CISG 的一部分发挥法律效力。在本案中,值得肯定的是,第五巡回法院对Incoterms 的著名性以及被广泛熟知性进行了调查和论证,〔16〕See 332 F.3d 333 (5th Cir. 2003).但遗憾的是,法院同样得出了视Incoterms 为CISG 一部分的错误结论。作为纽约南区法院的上诉法院,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本不必受到纽约南区法院的约束,但其还是基本原封不动地援引了纽约南区法院的结论。
在“Cedar Petrochemicals, Inc. v. Dongbu Hannong Chemical Co., Ltd 案”中,美国纽约南区法院更是作出了一个让人迷惑的裁决。在该案中,营业地位于美国的雪松石化公司和韩国的东部韩农化学株式会社签订了一份提供苯酚的书面合同,双方选择的贸易条件是“FOB 蔚山港”。与前述两个案件相同的是,本案的争议也是源自到达时的货物与装运时相比出现了质量严重劣化的情况;与前述两个案件不同的是,本案的涉诉双方明确选择了Incoterms2000 作为FOB 贸易条件的解释依据。法院认为,当事人东部株式会社未能解释为何Incoterms 在整合进CISG 后还可以减损CISG 的规定。因为根据GISG 第6 条的规定,当事人若想减损公约规定必须要采取明示的方法,但该案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双方有意减损CISG 第36 条的规定,所以不能认为当事人有意排除了CISG 的默认规则。基于此,法院直接根据CISG 第36 条等公约中默认的交货责任规则作出了裁决,而完全没有顾及双方在合同中已经明示选择Incoterms2000 的约定。〔17〕See No. 06 Civ. 3972(LTS)(JCF), 2011 WL 4494602 (S.D.N.Y. Sept. 28, 2011).
(三)评论
从两国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裁判机构存在超越Incoterms 功能和调整范围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进行错配的情况,不论是中国法院还是美国法院,似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将Incoterms 与成文法视为性质相同的法律规则,从而将Incoterms 直接整合到CISG 或国内法的条文中加以适用,完全没有虑及Incoterms 不同于成文法的属性。正是由于缺乏对上述事实清晰的认知,才导致法院出现了裁判理由和结果相互矛盾的情况,显然有逻辑不能自洽之嫌。〔18〕参见陈晓庆、张斌峰:《试论法律价值逻辑》,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 年第5 期,第85-91 页。那么,Incoterms 作为国际商事惯例,其法律属性究竟该如何确定有必要通过对CISG 第9 条的条约法解读来进一步释明。
三、Incoterms 法律属性判断:基于CISG 的条约解释
前文述及案例之所以出现裁判者对Incoterms 适用错误和混乱的情形,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CISG 第9 条的解释与理解错误造成的。前文提及的法官和学者大多对CISG 第9 条中“同意”的字眼视而不见,甚至认为第9 条中的当事人同意要求是一种“法律拟制”。〔19〕参见左海聪、孙莉:《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商事惯例的规范性效力——基于公约第9 条第2 款的分析》,载《法学评论》2017 年第2 期,第114-125 页。要破除上述令人迷惑的法律认知,有必要回到CISG 文本中使用公认的条约解释方法对第9 条的真正含义作一解释。
目前最为权威的条约解释法律文件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各种条约文件。该公约第31 条第1 款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第32 条规定:“依第31 条作解释而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根据该两条规定并结合CISG 第9 条解释之客观需求,笔者析取并通过四类解释方法来对之加以法律解释。
(一)文义解释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在对条约解释时必须根据条约文字通常的含义进行解释。很显然,根据CISG 第9 条不论是第1 款还是第2 款都有“同意”这一明确的限定语。不同之处仅在于第1 款的同意是基于缔约双方当事人的明示同意,而第2 款则是在符合前置的事实状态要求的情况下将Incoterms 作为合同的默示条款来对当事人发生法律约束力。作为缔约国代表签署并经过缔约国立法机关批准的正式国际法律文件,CISG 第9 条的规定事实上是一种程序与实体规则相结合的二元规则结合体。不论是法官还是学者都不能将其中的任何字眼和词汇予以无视或删除,司法机关亦无权改变条约文本的字面含义。
从程序层面看,该条首先要求当事人证明双方同意受到惯例的约束。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双方当事人明示选择受Incoterms 的约束。根据Incoterms2010 的要求:“如果要使合同适用Incoterms®规则2010,应在合同中明确表明,例如,所选择的Incoterms 规则(含指定地点)适用Incoerms®规则2010。”那么,此种情况下根据CISG 第6 条的规定,基于当事人明确约定适用Incoterms 的规定,在术语所能涵盖的射程范围内当然可以减损或改变CISG 的默认规则。在此意义上说,前述美国雪松石化公司案中法院的裁决显然存在不小的问题,因为其无视了当事人对Incoterms2000 的明示选择。第二种是当事人虽未明示选择Incoterms,但当事人有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已然同意了Incoterms 作为一种商事惯例而对双方产生合同约束力。在美国,要想证明上述事实,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会受到言词证据原则(parole evidence principle)的约束,〔20〕See Christopher R. Drahozal, Usages and Implied Te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abien Gélinas ed., Trade Usages and Implied Terms in the Age of Arbi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18-120.正式合同文本以外的相关证据线索往往无法被法院采信,或许正是上述原因使美国法官倾向于将商事惯例视为一种法律而予以适用。在我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任何查证属实的证据都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所以不会出现美国法院的上述问题。〔21〕参见李娟:《习近平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就、规律及实践意义》,载《探索》2018 年第1 期,第13-20 页。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能够证明在履约过程中对方当事人已然同意Incoterms 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约束力,那么根据公约第9.1 条的规定就可以直接判定Incoterms 对其产生约束力。第三种情况则较为复杂,但最为重要,即在没有证据证明合同当事人已然同意Incoterms 对交易具有约束力时,必须按照CISG 第9.2 条的要求进行“三步法检验”〔22〕关于“三步法检验”的内容,参见前述对“St. Paul Guardian Insurance Co. v. Neuromed Medical Systems & Support, GmbH案”评论时所作的论述。以验证Incoterms 是否已被从事相关贸易的当事人普遍知道并遵守进而成为合同的默示条款。〔23〕需特别说明的是,在进行“三步法检验”的过程中应当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根据专家证言来客观判断上述事实。See Orsolya Toth, Lex Mercatoria: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57-58.
从实体层面看,CISG 第9 条的含义反倒变得非常简单。如前所述,一旦当事人能够证明前述事实的存在,那么Incoterms 就会自动被整合到当事人的合同之中,成为合同条款的一部分,从而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并且,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之法则, Incoterms 的实体内容规则会在其调整范围内优先于CISG 以及国内合同法的默认规则,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
(二)整体解释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的规定,在解释条约时应该参照条约的上下文进行解释。换言之,在解释CISG 第9 条时我们可以参考条约的其他条文来解释该条文的真实含义。那么,在CISG 的规定中究竟哪些条文可以为理解第9 条提供依据呢?经过梳理和研究,笔者发现以下几个条款可以作为理解第9 条含义之依据。
1. 第8.3 条:该条对国际商事惯例提供了目的论依据。该条规定在确定当事人的行为意旨时,要合理考虑“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惯例”。很明显,该条将惯例和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紧密衔接,将惯例设定为理解当事人意图的一种客观根据。因此,我们在解释第9 条时完全没有理由人为割裂惯例的内容和当事人的意图,这有可能导致对公约中不同条款的解释发生冲突。
2. 第4 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公约的适用范围明确排除了“惯例的效力”的认定问题,因为“惯例的效力”认定问题被视为缔约国国内法才能处理的“保留事项”。既然公约不能赋予惯例以“法律效力”,那么对于第9 条最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商事惯例的约束力来源是当事人对协议的同意,是“同意”使作为合同一部分的商事惯例对当事人产生了法律约束力。
3. 第18.3 条:该条款强调了当事人主观意思与惯例的相关性特征,即当事人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习惯做法和惯例……来表示对要约的同意”,再一次将惯例和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也再次印证了惯例与主观意图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综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商事惯例从来没有和当事人的同意这种主观意思区别开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CISG 第9 条不可能也无理由单独在这个层面抛弃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这一相关要素。
(三)目的宗旨解释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要求对条约解释时考虑条约的宗旨和目的,也就是必须考虑条约意图实现的根本目标。针对CISG 目的和宗旨解释,应根据第7.2 条的规定,首先考虑根据其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释公约。
1. 缔约自由
缔约自由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可谓是CISG 的一项基本原则,〔24〕See Laura Lassila, General Principles and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Uniformity Under an Interpretation Umbrella?, 5 Russian Law Journal 115 (2017).根据其第6 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任意改变和减损本公约的规定,而这种改变和减损仅受公约第12 条的限制。第12 条仅仅是当事人所在国对合同的形式做出保留的情况下,才不得对这种保留进行变更。可以看出这种禁止改变的范围事实上非常狭窄,几乎允许当事人对合同的任何方面进行改变,由此得出CISG 中的缔约自由能够被视为该条约一项根本目标和一般原则的结论。〔25〕See William P. Johnson, The Hierarchy That Wasn’t There: Elevating “Usage” to its Rightful Position For Contracts Governed by the CISG, 32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281, 283(2012).
在此语境下,将Incoterms 作为一种优先适用的法律直接纳入CISG 中的做法显然会阻却上述目标的实现。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可能不会想到,会有合同条款以及准据法之外的规则在未经他们同意的前提下直接对他们产生法律约束力,更不会想到,对价格术语的选择会对他们的保险义务以及买卖合同本身产生根本的影响,〔26〕See Leonardo Graき, Remarks on Trade Usages and Business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Sales Law, 29 Belgrade Law Review 102-123(2011).这些问题的出现显然有损于缔约自由这一根本价值和目标的实现。
2. 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
CISG 第8.1 条“为本公约的目的,一方当事人所作的声明和其他行为,应依照他的意旨解释”的规定,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上升为“实现公约目的”的层次高度。第8.3 条对如何确定当事人的意志进行了路径规定——“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应有的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到与事实有关的一切情况,包括谈判情形、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这其中虽然提及了惯例可作为一种证据来应用和参考,但最终目的却是发现当事人的真实意志。为了实现此目的,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在解释CISG 第9 条的时候完全不去考虑当事人的意志,而是直接把一个民间组织制定的规则凌驾于当事人的意志之上,很显然不合乎常理。
3. 促进公约的统一适用
根据CISG 第7.1 条的规定,促进公约的统一适用也是公约所追求的根本价值之一。〔27〕参见[奥]恩斯特•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272-274 页。目前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贸易术语是全球普遍认同的国际商事惯例,但实际情况远比前述理论来得复杂。以CIF 术语为例,就存在国际商会的Incoterms 解释、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解释以及国际法学会的华沙—牛津规则的解释。即便承认国际商会Incoterms 的解释影响力更大,但也应注意其自身存在的版本冲突问题,尤其是在版本更替时期该问题更加突出;即便是能够统一版本,Incoterms 规则内部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冲突。〔28〕See Leonardo Graき, Remarks on Trade Usages and Business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Sales Law, 29 Belgrade Law Review 102-123(2011).
(四)条约筹备历史材料解释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32 条的规定,在文本解释之下,应考虑条约的辅助材料或起草历史。具体来说,确认条约的起草历史与条约的文本、背景、目标和目的,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歧义,防止解释“明显荒谬或不合理”。在条约解释方法上这被称为历史筹备材料解释方法(travaux préparatoires)。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在CISG 第9 条的评注中述及了该条之蓝本《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第一海牙公约》)第9 条第2 款曾规定,可适用的惯例与统一法冲突时,除非各当事人另有协议,应适用惯例。这项规定被认为与某些国家的宪法原则相冲突,且违反一些国家的政府政策,实无必要,所以不再保留。〔29〕参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正式记录》,联合国出版物1981 年,第22 页。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优先性,对于商事惯例与商事统一实体法相冲突,原则上应优先适用惯例,但Incoterms 规则并未列入成文法的CISG 文本中,因此还需要裁判机构依据具体案情进行识别和判断。
考察审议CISG 草案的过程,曾经有国家代表提出应明确贸易术语在CISG 中的适用地位,但是该版本的条约草案最终未获通过。瑞典代表对于CISG 第9 条提出的修改方案是:在“惯例”和“当事人应当知道”之间增加一个短语——“或者对贸易术语的解释”或者是重新采用《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第9 条第3 款的内容也即采用商业惯例中常用的合同表达方式、条款或者合同形式的,应按照与贸易有关的通常赋予的含义进行解释。那么,根据瑞典代表的建议CISG 第9 条的规定就可能是:“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或对贸易术语的解释,而这种惯例和对贸易术语的解释,在国际贸易上,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30〕同上注,第104 页。
埃及代表提出的修改草案是在第9 条下增加一款,即“在商业实践中经常采用的合同含义、条款以及形式应当按照具体贸易中有关行业的习惯用法予以解释。”〔31〕各国和国际组织对于CISG 草案的评论和建议,同上注,第84 页。很明显,两国的动议都有将Incoterms 直接引入CISG 的想法。瑞典代表明确指出,他提起这项修改提案的目的是“涵盖贸易术语解释的问题,如‘FOB’‘CIF’‘CIF 卸至岸上’(CIF Landed)和‘净重’等术语的解释问题”。埃及代表持完全相同的看法。这两条修改意见虽然得到了比利时代表的支持,但是也受到苏联、美国和日本代表的强烈反对。其中苏联代表和日本代表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提案“过分含糊”而不可取,美国代表则认为广泛熟知的贸易术语解释会产生歧义,《美国统一商法典》同样有对贸易术语的解释。最终,瑞典、埃及代表针对草案修改的动议没能通过,而是美国针对草案的修改建议稿获得通过,形成了现今CISG 第9 条第2 款。〔32〕See William P. Johnson, Analysis of Incoterms as Usage Under Article 9 of the CISG, 35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6,429(2013).所以,对CISG 进行解读和适用时必须将上述条约的起草背景以及准备资料纳入考虑范围,通过考察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历次会议记录,针对是否明确CISG 第9 条第2 款就是Incoterms,各国争议很大,笔者认为最终的讨论结果应该是Incoterms 不宜直接被视为法律,也不能直接作为CISG 的一部分适用,商事惯例的优先适用性根本上还是因为其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适表达。
(五)结论
由上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国际商事惯例不能被视为CISG 规则的一部分,也不直接具有法律的约束功能,其对于合同当事人的效力来源主要因为它明示或者默示地并入合同。其次,国际商事惯例之所以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CISG 的规定将国际商事惯例和当事人的交易意旨和交易意图联系起来,因为国际商事惯例更能体现商人的实践及合理期待,所以其适用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只是裁判机构在合同当事人同为CISG 缔约国或者合同当事方国内法与Incoterms产生冲突或出现不同解释时,遵循条约法解释的方法分析CISG 第9 条的立法原意以及其与国际商事惯例的互动关系,CISG 第9 条架设了CISG、国内法与Incoterms 合乎逻辑适用的桥梁,尤其是通过前文述及的CISG 官方记录资料更能予以佐证。因此,国际商事惯例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在于其是一种可以被整合到具体合同中的“标准条款”。〔33〕这与2021 年1 月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496 条所规定的单方提供未与相对方协商的格式合同不同,这种标准条款是由第三方提供,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来说是相对公平公正的。
不管是CISG 还是部分国家的国内法均明确了国际商事惯例的补缺地位,在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同意Incoterms 的内容后,Incoterms 的相应规定就会视为被合同双方当事人整合到已经生效的合同之中,进而发挥约束当事人的法律功能。在此思路的指引下,若想确认Incoterms 的法律约束力,就必须从客观证据出发推断当事人在交易时的真实意图。裁判机构必须结合合同的条款、合同的上下文语境以及合同的具体履行过程来判断当事人是否真正接受了国际商事惯例中所包含的规则。作为国际商事惯例的Incoterms 也应当如此,合同当事人选择了某个贸易术语并不意味完全接受Incoterms中所规定的当事人的所有权利义务,必须结合合同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事人的意思乃至合同的缔约目的来综合判断Incoterms 是否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四、Incoterms 作为国际商事法律渊源的优先适用
根据《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法律渊源通常指法官从何处获得裁决案件的规则……通过对法律来源的讨论可以确定在处理争议时的不同种类法律的适用条件和范围。”〔34〕Byan Garner ed., Black Law Dictionary (10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2014, p. 1892.此外,其还有一个功能——“通过了解和分析各类法源适用的效力等级和范围,可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达到各种法律规则的和谐统一。”〔3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53-54 页。基于此,Incoterms 作为国际商事惯例在具体裁判时发挥法律效力的等级是什么?进一步说,同样作为国际商法的法律渊源,当Incoterms 的内容与相关成文法发生冲突时,司法机关应当秉承何种思路进行处理?这些问题将成为本文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Incoterms 与成文法内容的潜在冲突
作为一种自治性的法律渊源,Incoterms 与成文法虽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发生交叉,但这不意味两者在所有领域不会发生任何的潜在冲突,笔者通过梳理发现,它们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会发生冲突。
其一,交货义务冲突。以Incoterms 中的D 组术语为例,该组术语要求卖方将货物运送到买方所在地才算完成交货。这就与CISG 第31 条和我国《合同法》(已废止)第62 条〔36〕该条相关内容被2021 年1 月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11 条吸收。的规定发生了冲突。
其二,风险转移规则冲突。Incoterms 不同组别的术语都有各自不同的风险转移界限,以最为常用的CIF 术语为例,根据Incoterms 下CIF 术语A5 条款和B5 条款的规定,在卖方自装运港船上完成交货时,风险就归买方承担。然而根据CISG 第67 条的规定,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时风险发生转移。设想一下,如果卖方将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后,由于不可抗力导致货物在运往港口的途中毁损,那么买方很可能会依据CIF 术语条件主张由卖方承担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而卖方则会依据CISG 第67条的规定主张免责,进而引发争议。
此外,根据CISG 第30 条的规定,卖方有义务转移货物的所有权,在卖方保留所有权的情况下,法院可能据此判断卖方也同时保留货物的风险。在前述“St. Paul Guardian Insurance Co. v. Neuromed Medical Systems & Support, GmbH 案”中,原告正是以被告明示保留所有权为由,主张风险也应由被告承担,而被告则以买卖合同中选择的CIF 价格术语为抗辩,主张货物风险应该由案外的投保人也就是买方承担,由此引发争议。
其三,投保义务规则冲突。根据CIF 术语的规定,卖方有义务按照最低保险险别进行投保,但同时要求“最低投保金额为所定价款中加一成(即 110%)”,这就在客观上让卖方承担了“超额保险”的义务。然而,根据大多数国家的合同法及保险法,卖方完全没有如此投保的义务,甚至根据我国《保险法》第55 条的规定这种投保亦属于无效的投保。那么,在双方约定CIF 术语的情况下,关于卖方是否有义务进行超额投保以及超额投保后的法律后果很可能成为争议的一个潜在诱因。〔37〕See Tribu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ward 406/1998.
可见,Incoterms 作为一种法律渊源很可能会与同样作为法律渊源的成文法冲突。在此情形下,裁判机构须结合合同当事人的履行情况及缔约意图,通过法律推理分析相互冲突的两类规则优先适用哪种法律渊源的问题。
(二)Incoterms 优先于成文法适用的法律空间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成文法未作规定时,才可以适用相关的国际商事惯例,我国《民法典》第10 条也规定了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但该条更多是基于国内民事法律纠纷解决的视角,未来《民法典》涉外编抑或是可能的国际私法法典是否沿袭原《民法通则》第142 条之规定还不可知。可见,从既往我国国内立法来看,国际商事惯例起到的仅仅是一种补充成文法不足的功能。〔38〕参见已失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0 条,以及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 条。但是,在国际商事交易的语境下,上述规则将不再有效。根据CISG 第9.2 条的规定,当某种国际商事惯例被法院查明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且“该惯例为从事同类贸易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和通常遵守”时,该惯例就被认为“默示地为当事人所同意”。换言之,符合前述条件的话,惯例就直接被纳入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中,成为合同的一项“默示条款”(implied terms)。此际,根据当事人约定优于法律一般规定之原则,该惯例就应该优先于CISG 和相关国家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作为典型的国际商事惯例,Incoterms 亦概莫能外。
此外,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斯德哥尔摩仲裁院仲裁规则》《英国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等国际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规定,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员可以直接适用其认为合适的法律规则作为解决争议的实体依据,而且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考虑国际商事惯例的要求。〔39〕参见《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第21 条、《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第22 条、《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4.2 条等。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仲裁规则中所说的是“法律规则”(rule of law),这与法律的概念完全不同,国际商事惯例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其虽不能归入法律的范畴,但完全可以归入法律规则的范畴。此种准据法适用方法被称为实体法直接选择方法(Voie directe)。〔40〕See Loukas Mistelis, Unidroit Principles Applied as “Most Appropriate Rules of Law” in a Swedish Arbitral Award, 8 Uniform Law Review 631,637(2003).也就是说,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员在确认Incoterms对当事人有约束力且更有利于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情况下,可能会越过相关成文法之规定,直接根据Incoterms 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分配。
(三)Incoterms 优先适用的条件
前文论证了Incoterms 作为一种国际商事惯例与相关成文法存在冲突的客观事实以及优先适用Incoterms 的可能性。但是,优先适用Incoterms 还需要有严格的前置条件。根据CISG 的规定以及相关仲裁机构的裁决,笔者归纳了以下三个优先适用的前提条件。
1. 确认交易当事人属于相同的商业群体
与成文法相同,国际商事惯例也有严格的属人适用范围。根据CISG 第9.2 条的规定,商事惯例发生法律约束力的前提是“该惯例被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当事人广泛知道且通常遵守”。由此可知,当事人属于相同的商业群体(relevant business community)是优先适用国际商事惯例的根本前提。法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盖拉德将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范围界定为国际商业社会(de commerce internationale)。〔41〕See Emmanuel Gaillard, La distinction des principes generaux du droit et des usages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in Etudes oあertes à Pierre Bellet, Litech, 1991, p. 206-211.但实际上,国际商事惯例的作用范围会因地域和行业被划分为更细致的子区间。例如,泰赛根法(Tegernseer Gebräuche)作为一种商事惯例就只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木材商之间。〔42〕See Oberster Gerichtsh of Austria, 21 March 2000, http://www.cisg.law.pace.edu/cases/000321a3.html, last visit on March 25,2022.在“西屋公司仲裁案”中,国际商会仲裁员指出,双方当事人都是长期从事军事装备交易的企业,这也是他们熟知相应的军事装备交易的商事惯例的根本前提。同样基于该理由,适用军事装备交易领域的国际商事惯例显然比适用伊朗或美国的国内法更具中立性,更能够保护美伊双方的合理期待利益。〔43〕See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Paris 7375, 1996, http://www.unilex.info/case.cfm?pid=2%20&do=case&id=625&step=FullText, last visit on July 7, 2021.同理,在适用Incoterms 时,要注意双方当事人的贸易背景和是否来自相同的贸易区域,这决定了他们对Incoterms 的内容是否存在共同的认知。假如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来自美国,就需要特别注意合同中所选择的贸易术语是否有可能特指《美国统一商法典》中的贸易术语,因为该术语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与Incoterms 的几乎完全不同。〔44〕参见U.C.C § 2-319..§ 2-320. § 2-321 的相关规定。
2. 尊重Incoterms 规则的射程范围限制
即便明确了Incoterms 对当事人的约束力,从调整范围的角度看,国际商会对Incoterms 的调整范围作了非常明确之限定,即该规则的射程范围仅限于解释被缩写后的某些贸易合同条款,如从卖方到买方的运输条件条款、进出口清关事宜的安排条款以及双方约定的风险转移时间的条款。该术语解释明确排除了物权转移、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造成的免责及违约责任等。该官方文件还特别明确指出:“商人们通常认为Incoterms 规则可以解决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大多数问题。实际上,向国际商会专家组提交的关于Incoterms 规则的大多数的解释要求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Incoterms 的调整范围。这些问题通常涉及销售合同关系本身的问题,如各方在文件信用证、运输和储存合同下的义务。许多问题涉及合同当事方的实体义务,这超出了与货物交付条件有关的事项。因此,有必要强调的是,Incoterms 只能处理有关货物交付的问题,并不涉及货物买卖合同本身以及与货物交付有关的其他合同。”〔45〕Jan Ramberg, ICC Guide to Incoterms 2010, ICC Services Publication, 2011, p. 16-18.
对于超出Incoterms 调整范围的诸事项,只能依据合同的准据法来进行调整。例如,在某仲裁案件中,希腊的买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并指责法国的卖方没有尽到妥善交付货物的义务。但是,法国的卖方抗辩说,双方的合同选择了CIF 贸易术语,货物是在买方承担风险的区间内发生毁损灭失的。仲裁庭承认合同中的CIF 条件受Incoterms 的调整,但同时指出,卖方在签订合同后的附随性义务并不在Incoterms 的调整范围内。卖方没能保证承运人船舶的适航性,因此必须承担违约责任。〔46〕See Buyer (Greece) v. Seller (France), Final Award, CAP Award No. 3174, in Albert Jan van den Berg (ed),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13,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Vol. 38 , 2013, p. 53.
3. 认定Incoterms 优先适用的路径方法
承前所述,Incoterms 乃是基于当事人的同意进而成为国际商事交易合同的“默示条款”从而发挥法律约束力的。那么,确认当事人对Incoterms 内容的同意范围就成为Incoterms 得以优先适用的根本条件。为达此目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明示选择了具体版本的Incoterms,就特别需要注意合同条款中对Incoterms 的使用是基于何种目的。如果当事人使用Incoterms 仅仅是为了进行报价或者价格评估,此时就不应该用Incoterms 关于运输和风险承担的规则去约束买卖双方当事人。〔47〕例如,在“韩国栗村化学、天津高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民终21 号民事判决书]中,双方当事人选择“FOB 釜山”的贸易术语价格条件。根据任何版本的Incoterms 的规定,此种贸易条件下都应由买方安排运输,然而在本案中,双方却均认可双方已然合意由卖方韩国栗村化学来安排运输完成交货,且交货地点最后法院认定为中国新港。只有当术语的使用明确是为了安排交货事宜时,才可以直接按照Incoterms 的规定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相应权利义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示约定选择Incoterms 作为解释合同的依据,那么就要依据CISG 第9.2 条规定所要求的“三步法检验”来审查当事人是否可被视为已然默示地同意了Incoterms,进而有义务遵守Incoterms 中的规定。对此的举证责任由主张适用Incoterms 的当事人来承担。
五、结语
必须承认的是,Incoterms 与CISG 始终处于一种共生和互动的关系中。〔48〕See Juana Coetzee,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coterms and the CISG, 32 Journal of Law & Commerce 20, 21 (2013).经过对CISG 第9 条的分析不难发现,Incoterms 作为典型的国际商事惯例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效力,之所以对国际货物贸易的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并不是因为其是正式意义上的法律,而是由于其作为一种标准合同模块可被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地整合进国际贸易合同中,进而被裁判者推定为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其法律效力应当优先于CISG 和相关国内法默认的任意性规定。但因Incoterms 并不天然是CISG 的一部分,CISG 第9 条对于Incoterms 为代表的国际商事惯例的契约性效力作了进一步补强,故在国内法未赋予Incoterms 强制性效力或授权替补性效力的情况下,法院不考虑当事人的意图和对解释标准的选择态度就直接对Incoterms 进行适用的做法显然值得商榷。
此外,在当事人只是选择了某个贸易术语作为价格条件的情况下,未明确Incoterms 具体版本或者是否是Incoterms 术语的情况下,裁判机构应依据当事人举证以及缔约意图等综合因素予以确定,不应直接将Incoterms 认定为合同的默示条款。裁判者同时应尊重该贸易术语的射程范围,涉及CISG 的相关条款、国内法有关规定与Incoterms 产生冲突理解的情况下,可以根据CISG 第9 条的规定并结合合同的约定及履约过程依次判断Incoterms 相关条款是否优先适用。首先,应当调查当事人有无明示选择Incoterms 作为解释贸易术语的依据,并根据当事人选择的版本在贸易术语的限定范围内对合同进行解释。其次,若当事人没有明示选择Incoterms 作为解释规则,那么就应该根据当事人的履约过程和先前的习惯性做法判断当事人是否已然同意将某个版本的贸易术语解释规则作为合同术语的解释规则。最后,如果上述情况都不存在,则裁判机构应通过咨询专家证人的证言,通过“三步法检验”来调查、确认在合同涉及的贸易领域内哪个版本的贸易术语解释规则属于“为交易当事人广泛熟知并经常遵守的商事惯例”。
总之,相较于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国际及国内立法,Incoterms 的适用地位和适用方法与成文法完全不同。在没有确认当事人对其内容同意之前,该规则对当事人无任何法律约束力。一旦确定当事人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接受了Incoterms,那么Incoterms 的规定便转化为当事人合同中的“默示条款”,进而优先于CISG 以及其他准据法中的规则发挥约束力。诚然,在CISG 生效之前,不同版本的Incoterms 已在司法和仲裁实践中被适用,〔49〕在CISG 生效之前,ICC 颁布了1923 年版、1936 年版、1953 版、1967 版、1974 版共计5 个版本的Incoterms。但作为当今世界上有巨大影响力且深刻影响许多国家国内合同法的商事实体法公约,其体现的不仅仅是商事规范的契约性效力,还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规范性效力。即便对当事人是否接受Incoterms 难以识别,CISG 缔约国的司法和仲裁裁判者亦可以依据具体案情,运用条约法解释等方法对CISG 第9 条作善良合理解释,能够将Incoterms 解释为合同当事人之间达成的“默示”合同条款,进而进一步促进和扩大Incoterms 在国际贸易纠纷中的适用,打破商事惯例与商事统一实体法之间的藩篱,基于CISG 第9 条的规范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对于Incoterms 的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