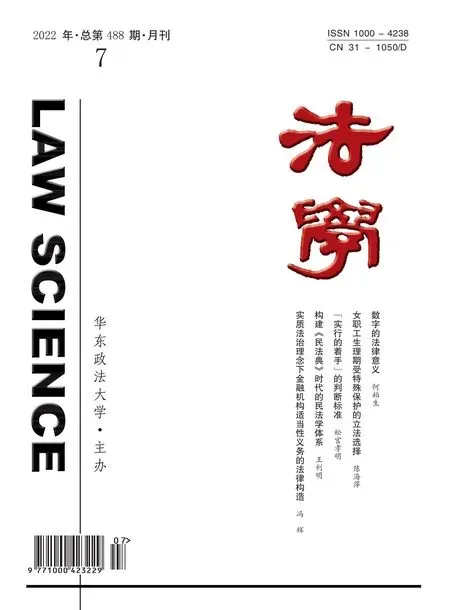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司法应用逻辑
●吴冬兴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迅速推进,“统一法律适用”无疑已经成为新时代司法审判的关键主线。近年来,除了持续推进并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还相继出台了系列性的司法文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法〔2021〕289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 号)。等,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推行“统一法律适用”要求。然而,“统一法律适用”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一个方法问题。单纯通过压实司法责任等途径显然难以达成这一目标。质言之,欲落实“统一法律适用”这一制度性要求,必然以正确理解“统一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机理为前提。在法理上,“统一法律适用”实际上主要依靠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实践应用,使繁芜的法秩序要素在每一个案件中,被有序转化为不包含矛盾的统一体,以尽可能纾解司法评价的尺度多元难题。〔4〕正如雷磊教授所言:“同案同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依法裁判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是其更为具象化的表达。”详见雷磊:《如何理解“同案同判”:误解及其澄清》,载《政法论丛》2020 年第5 期,第34 页。因此,能否实现“统一法律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裁判落实。从国内目前的学理研讨及实践操作来看,虽说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作为裁判论证的必要考量,已或明或暗地贯穿于裁判说理的各项环节,但是究其司法应用而言,仍存在诸多尚待勘定之处:第一,在规范定位层面,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能否拘束裁判活动仍然存在争议;〔5〕例如,有学者就提出,“同位法秩序之间的一致是立法者的追求,而非司法者的义务,法秩序统一原理原本强调的整体法秩序的统一应当被否定。”详见郭研:《部门法交叉视域下刑事违法性独立判断之提倡——兼论整体法秩序统一之否定》,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 年第5 期,第76 页。第二,在具体要求层面,因深陷“存在论统一”与“目的论统一”之争,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司法裁判的规范要求始终晦暗不明;〔6〕“法秩序统一”到底系“存在论统一”还是“目的论统一”,涉及将法规范视为行为规范还是裁判规范的理论分歧,将“法秩序统一”视为“存在论统一”的观点在德国法上享有通说地位,将“法秩序统一”理解为“目的论统一”的观点则为日本法上的通说,这两种观点在我国法学界均有其拥趸。详见陈金钊、吴冬兴:《论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违法判断的法域协调》,载《东岳论丛》2021 年第8 期,第162-165 页。第三,在落实方案层面,由于脱离司法评价的基本结构,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存在着沦为裁判修辞的风险,在很多情形下,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反倒是法官个人的价值立场。〔7〕例如,就民事违法和刑法违法的关系而言,同样以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为说理前提,但不同判例却得出不同结论:在“彭某某、临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浙江省高院认为,“同一事实已因刑法评价而为生效刑事裁判所实质性否定,基于法秩序统一性而言民事法律规范亦应维持对同一事实的否定性评价”;在“王国栋等合同诈骗案”中,北京市三中院主张,“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并不是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竞合、包容关系”;在“李某等敲诈勒索案”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出,“从权利基础上来讲,在财产犯罪中,刑事违法性判断是在法秩序统一原则下的违法相对性判断”。详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01 民终3171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 刑初23 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 刑初3339 号刑事判决书。归根结底,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司法应用逻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问题,而是一个集合了观念与技术的复杂问题。法律方法理论的任务,肯定不是单纯地将基于体系哲学的论点,转化为以法律为对象的抽象命题,其还必须依托司法评价的一般结构,科学建构法律获取的方法论规则。进言之,欲厘清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司法应用逻辑,除了必须证立该原则应当拘束司法裁判活动,还必须明确内含于该原则的具体规范要求,并通过将之嵌入司法裁判的一般评价结构,理性设计该原则的裁判应用方案。
一、作为裁判辅助的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具有司法拘束力
法秩序统一性原则(das Prinzip der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也被称为法秩序一致性原则、法秩序无矛盾性原则或法秩序免于矛盾原则(das Prinzip der Widerspruchsfreiheit der Rechtsordnung)。“当我们谈及‘法秩序统一性’时,我们总是意指,在调和整体法秩序的目标下法秩序各部分间的相互关联。在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背后——例如,不同的法域——系法秩序各部分间不会无关联存在的理念。”〔8〕Dagmar Felix, Das Ehegattensplitting und die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Barbara Seel (Hrsg.), Ehegattensplitting und Familienpolitik,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08, S. 76-77.论证的逻辑无矛盾本就是任何实践论证的必要准则,裁判论证自然概莫能外。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制定法数量的急剧膨胀、法律渊源的日趋多元、审判权专业分工的细化和法学内诸学科壁垒的强化,基于法律体系的思维方式(体系思维)持续遭遇现实挑战。愈严格地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显然就意味着司法裁判必将承受愈繁重的论证负担。〔9〕Vgl. Klaus Friedrich Röhl, Hans Christian Röhl, Allgemeine Rechtslehre: Ein Lehrbuch., 3.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2008,S.430-431.基于司法裁判的“效益”取向,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可欲性不断面临理论危机;基于现实法秩序矛盾重生的状况,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可能性似乎愈加难以维系。然而,司法裁判必须受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之拘束的理念,因此就该被放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假如司法裁判不必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那么其在面临“不讲逻辑”之指摘的同时,还会招致整个社会对法律系统难以估量的信任危机,法律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一)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具有裁判辅助性
在法律适用中,当我们强调司法裁判必须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时,这里的“法秩序统一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直接关联着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在司法裁判中的规范定位。基于理论上的认知分歧,有必要首先就此给出理论说明。
一方面,“法秩序统一性”不能被理解为对现实法秩序的客观描述。德国学者卡纳里斯曾将法学上的“体系”区分为“认知的体系”和“对象的体系”,并且主张认知的体系须紧密贴合对象的体系。〔10〕Vgl. Clause-Wilhelm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あ in der Jrisprudenz, 2. Aufl., Duncker & Humblot, 1982, S. 13.法秩序的统一,亦只有在“认知的体系”中才能局部且暂时地被实现。因为“对象的体系”,即现实中存在的法秩序,作为立法者有限理性和利益妥协的产物,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内在矛盾。法律的发展史已然揭示:“迄今为止被研拟出来的法体系均因后续的发展而被超越;实则,依吾人迄今的理解,法体系始终不可能被终局完成。”〔11〕陈爱娥:《法体系的意义与功能——借镜德国法学理论而为说明》,载邓衍森、陈清秀等主编:《法理学》,元照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243 页。唯有通过体系化导向的持续法教义学作业,现实法秩序才能在排除矛盾的基础上作用于个案裁判。因此,所谓“法秩序根本不具有统一性,因而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不必拘束司法裁判”之类的主张,恰恰在根本上误解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理论初衷。因为“法秩序统一性”压根就不是对特定法秩序的现状描述。相反,“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就是现实法秩序的矛盾和碎片化等特征。
另一方面,“法秩序统一性”也不能被当成法律适用的当然前提或预设。基于法教义学的基本观念,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作业的展开,必须以特定法秩序所提供或认可的素材为论证理据。然而,这不能被理解为一国法秩序中的其他规范因素,就能当然地对目标规范的阐释产生体系影响力。“法哲学家施塔姆勒(Stammler)引证了一句话:‘一旦有人适用一部法典的一个条文,他就是在适用整个法典。’人们可以把这一观点视为不小的夸张。”〔12〕[德]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73 页。事实上,这一论点最为明显的夸张之处,就是潜在地将“法秩序统一性”当成了法律解释或续造的当然前提。正如上文所述,任何实存的法秩序皆是充斥着矛盾、赘言、缺失和非秩序性的规范集合体。假如径直将“法秩序统一性”作为法律论证的前提而不加检讨,极易诱发的问题,就是裁判说理的“循环性”和“保守主义”弊病:“循环性”弊病指的是,某项规范的证立取决于其他规范,而其他规范的证立又取决于该项规范;“保守主义”弊病则是说,新元素的证成被迫取决于先前的因素,这种保守趋势会阻止规范的修正和更新。〔13〕参见[墨西哥]阿玛利亚•阿玛亚:《藉由最优融贯的路径实现法律证成》,杭广远译,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9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113 页。以我国《民法典》在民事裁判中的体系阐释为例:应用民法概念体系须防范概念逻辑统一的过度化,应用民法规范体系不得逾越一般私法的规范界限,应用民法价值体系应避免价值秩序的不当转借,等等。〔14〕参见陈金钊、吴冬兴:《民法典阐释的“体系”依据及其限度》,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2 期,第97-101 页。
在法理上,“法秩序统一性”应被视为某种调整性理念。在司法裁判中强调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本质上是主张裁判者应尽可能在考量整体法秩序的基础上进行法律适用。因为“法律适用者寻找的不是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某个规范的答案,而是整个法律秩序的答案。无论法律秩序在外部和形式上的划分如何,必须将法律秩序作为一个价值评价的整体来适用。”〔1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121 页。由此观之,“法律适用中的‘法律秩序的统一性’只不过是一个方法上的辅助概念。”〔16〕同上注,第122 页。相应地,诉诸“法秩序统一性”理念而生成的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就是一项司法裁判的辅助性原则。该原则的具体任务,就是协助法律适用者进行法律解释、处理规范矛盾等司法作业。
作为司法裁判的辅助性原则,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具备如下特性。第一,论证上的规范指引性。这意味着,法律适用者必须在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规约下展开裁判论证。该项特性实际上诉诸这样一项基本假定:立法者不会自我矛盾。因为基于逻辑上的谬误理论(爆炸原理),从矛盾中可以推出一切,立法者的自我矛盾显然意味着规范失序。第二,实现上的动态协调性。众所周知,“法秩序绝非是系统上封闭的,它要经受不断的变迁,没有人能得窥它的全貌甚或将其展示出来。”〔17〕[德]克劳斯•阿多迈特、苏珊•汉欣:《写给学生的法理论》,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53 页。这意味着,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并非在特定个案中即可一劳永逸地予以达成。相反,每一个司法裁判都只是践行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一个环节而已。进言之,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永远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中,其始终充满着无限的开放性与可能性。
(二)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裁判辅助效益分析
裁判说理主要分为解释性说理、续造性说理和裁量性说理这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三者被统称为法律论证。作为司法裁判的辅助性原则,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辅助效益表现为,其不仅可以有效指引法律解释,也能够协助法律续造、约束自由裁量。由此,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才被称为“十九和二十世纪法理论、民法和国家法学的论证公式”。〔18〕Vgl. Manfred Baldus,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Bedeutung einer juristischen Formel in Rechtstheorie, Zivil-und Staatsrechtswissenschaft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Duncker & Humblot, 1995.
首先,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可以指引法律解释。在法解释领域,解释结论的得出,实际上取决于诸解释要素的共同作用,而法律解释的传统四要素即包括文义、体系、历史和目的。其中,文义和历史因素被当作范围性因素,被用以确定法律解释活动的最大范围,体系和目的因素则被当作内容性因素,即在范围性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19〕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334 页以下。在“价值体系化、体系价值化”的评价法学脉络中,体系要素和目的要素无疑都必须诉诸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才能得到正确运用。一方面,作为体系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的后设原则,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支撑着两者的法理正当性;另一方面,体系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又必须以准确理解“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之理论构造为前提。例如,基于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相区分的基本观念,在方法上肯定不能任意援引公法规范来解释私法或社会法规范。〔20〕以“高荣梅诉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为例,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火车到底是不是机动车”。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火车不属于机动车,因此高荣梅之女吕明英无法被认定为工伤。事实上,从裁判方法论看,白下区法院直接运用公法规范(《道路交通安全法》)解释社会法规范(《工伤保险条例》),这在方法层面会面临正当性质疑。详见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2005)白行初字第71 号行政判决书。
其次,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可以协助法律续造。在法律续造领域,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主要与“修正有缺失的法律的问题域”相关。〔21〕参见[德]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97 页。在司法裁判中,一旦出现司法评价的法秩序矛盾,法律适用者的主要任务便是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要求,尽可能消除矛盾,以维系法律评价的体系融贯性。当然,除了指引法律适用者如何消除实存的法秩序矛盾,对其他类型的漏洞填补任务,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也颇有助益。在这里,“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实际上被当作漏洞填补的正当性支点,藉此,法律适用者从现行法秩序中获取主导性的价值评价立场,进而以类推、目的性限缩等形式转用于待决案件。例如,在债权人撤销权案件中,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既然代位权和撤销权在保护债权人这一问题上具有功能等价性,那么,面对撤销权行使后规则缺位的立法现状,类推适用债权人代位权规则背后的价值序列,就应当允许撤销权人以同案起诉的方式获得优先保护。
最后,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还可以规范自由裁量。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是应对法律评价标准不一,进而促成法律统一适用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而促成法律统一适用,无疑必须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22〕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法发〔2012〕7 号)第5 条就规定:“行使自由裁量权,要处理好上位法与下位法、新法与旧法、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正确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确保适用结果符合立法原意。”事实上,“控制自由裁量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将自由裁量的行使引向‘理性化’。”〔23〕王锡锌:《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四个模型——兼论中国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模式的选择》,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311 页。作为裁判方法论上的基础性原则,建立在逻辑和目的理性基础上的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当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在裁量说理的目标层面,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明确,消除法秩序矛盾是法律适用者在个案裁判中必须处理的任务。通过这样的目标设定,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所包含的诸项法律思维规则,如上位规范优先、新法规范优先、特别规范优先、例外规范限制转介等,将会限制法律适用者的任意决策。第二,在裁量说理的论据层面,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严格限制了法律适用者在进行裁量说理时所能援引的论据。进言之,只有特定法秩序内部的规范要素及被该法秩序认可的其他规范要素,才有资格被运用于裁量说理。
(三)司法裁判必须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
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之所以必须拘束司法裁判,在法理上源于诸多规范性理由。因为一旦回到个案的语境中,就会发现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背后所潜藏的,实际上是塑造现代法治认同的诸多基础性话语。一般认为,司法参与社会治理,是通过个案积累来达成效果的。为了实现法律系统的良性运行,在以法的统治为核心诉求的现代法治中,必然要匹配司法德性、裁判义务及宪法至上等诸多现代法治的基础性命题。“人类法治演进的逻辑形态表明,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具备更为丰富的德性要素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方式。”〔24〕杨知文:《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及其制度建设》,载《法学》2021 年第4 期,第16 页。相应地,正是恪守司法德性、落实裁判义务、维护宪法价值等现代法治赖以成立的基础性命题,才衍生出司法裁判必须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这一制度化要求。
第一,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是恪守司法德性的必然要求。所谓司法德性,指称的是司法主体的个人品质(主要是职业操守和职业能力)。这是一个关乎司法伦理而非司法规则(规范)的问题。在法伦理学上,一般认为:“法官的德性不仅是关乎最低道德起点的法律规定,而更是关乎逐渐向上延伸到法官理性可能企及的最高道德境界。”〔25〕王申:《法官职业的道德义务和美德》,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4 期,第49 页。可以说,司法德性与法律适用者的个人能力是息息相关的。在能力维度上,针对法律适用者的德性评价标准,主要包含如下两个面向:其一,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其二,在可能面临不可接受的裁判后果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方法技巧,缓和规则确定性与个案妥适性的能力。众所周知,规范与事实的裂隙原本就是现代法治自身的固有缺陷。法律适用虽然在外观上表征为“涵摄模式”,但实际上几乎处处需要填入裁判主体的价值理性和技术智慧。在个案的语境中,之所以要诉诸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往往就是因为僵化地适用规则会导致裁判结论的不公正。如果法律适用者不能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要求,在司法的权限内尽可能得出较为妥善的结论,就意味着法官个人因缺乏职业能力而难以契合司法德性的内在要求。
第二,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是裁判义务的构成部分。所谓裁判义务,也被称为司法义务,是裁判者在裁判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义务。与道德义务不同,裁判义务的履行构成评价裁判质量的基本指标,对裁判主体具有法律强制性。在法理上,适度的裁判义务包括:不得拒绝裁判的义务、依法裁判的义务和裁判充分说理的义务。〔26〕参见孙海波:《司法义务理论之构造》,载《清华法学》2017 年第3 期,第165 页。基于法秩序的阶层构造,不同位阶法规范之间的效力矛盾必须排除,这无疑已经被包含在“依法裁判的义务”之中,此点无需赘言。此外,基于逻辑的理由,特别规范、新法规范等优先适用也成为排除法秩序矛盾的类型化要求。但除此以外的法秩序矛盾,是否必须在司法裁判中加以排除,却存在争议。这也是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能否构成裁判义务的关键所在。当然,本文认为,此类法秩序矛盾也属于必须排除的法秩序矛盾。因为与普遍实践论证不同,法律论证的正确性并不诉诸规范性命题绝对符合理性,而是它在现行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能够理性地加以证立。〔27〕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商务印书馆2019 年版,第352 页。质言之,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或有效性,取决于是否与现行法秩序相协调。如果裁判结论与现行法秩序产生冲突,其合法性当然就是存疑的。现行有效的法秩序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通过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来约束个案的裁判论证。在此意义上,是否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显然并非只关乎“更好的裁判”,同时也是“合法(格)的裁判”的应有之义。
第三,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是维护宪法价值和尊严的需要。“依宪治国就是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范畴,围绕宪法的基本价值构建国家体制,通过实施宪法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化、法律化保障。”〔28〕刘茂林、杨春磊:《依宪治国:法治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载《法学杂志》2013 年第7 期,第1 页。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范畴,意味着一国现行有效的法秩序,总是以宪法为核心,由位阶高低有序的法律规范所组成的有机整体。法秩序的统一性,最终必然表征为诉诸宪法的统一性。如果放任法秩序矛盾存在,显然就意味着基于宪法的整体法秩序陷入了自我混乱之中。“法秩序必须对于受规范者传达一致而清晰的命令。‘法秩序一致性’原则因此享有宪法的位阶。”〔29〕Dagmar Flelix,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1988, S. 10.转引自吴从周:《民事实务之当前论证课题》,元照出版公司2019 年版,第131 页。在此意义上,维系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实际上也就是维护宪法的价值和尊严。特别是在我国,《宪法》第5 条第2 款已经明确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在司法裁判中,坚持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当然为“维护法制统一和尊严”所包含。违反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裁判,显然构成对宪法价值和尊严的挑战。因此,从宪法的高度出发,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肯定不是一个方法上的任意理念,而是裁判论证上的必然要求。
二、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要求实现法秩序无矛盾的司法评价
自1935 年德国法学家卡尔•恩吉斯提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这一命题以来,不论是在立法、执法还是司法活动中,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30〕当然,恩吉斯并非法秩序统一性观念的首倡者,根据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巴尔都斯的考证,实际上,法秩序统一性原则,随着19 世纪的法律科学化浪潮而逐渐成为法教义学研究之核心,其在理性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概念法学派等理论学派中均存在观念原型,尤其是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国家学中,德国学者特里佩尔、海勒和西蒙特等人也从不同视角论证过这一观念。恩吉斯的贡献在于,首次从法理论的视角总结了法秩序统一性这一问题,并揭示了其对法教义学解释与建构作业的核心意义。Vgl. Manfred Baldus,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Bedeutung einer juristischen Formel in Rechtstheorie, Zivil-und Staatsrechtswissenschaft des 19. und 20.Jahrhunderts, Duncker & Humblot, 1995, S. 162-177.“统一、无矛盾、内部一致的法秩序概念,被应用于各种论证场合,特别是作为解释方法的争议部分。”〔31〕Alexander Hanebeck, Die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als Anforderung an den Gesetzgeber: Zu Verfassungsrechtlichen Anforderungen wie Systemgerechtigkeit und Widerspruchsfreiheit der Rechtsetzung als Mabstab Verfassungsgerichtlicher Kontrolle, DER Staat 41 (2002), S. 429.在司法裁判领域,因应实践场域的时空差异,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规范要求也逐渐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样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本身缺乏理论共识及实践重要性。相反,不同的理论见解,可以被视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之裁判要求的层次性表征。因此,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实践应用,恰恰需要基于现有的认知进路展开批判性整合。唯有揭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之裁判要求在结构上的多层次性,才能在司法裁判中顺利实现“排除司法评价的法秩序矛盾”这一总体要求。
(一)既有规范要求的法理检讨
从目前的理论研讨来看,对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裁判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三种理论见解。第一,以“法秩序的阶层论统一”为立论前提,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要求在司法裁判中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由于“一个法律体系的所有规范,要么系通过基本规范的应用,要么系通过直接或间接诉诸基本规范而创设之规范的应用而产生。这就是他(凯尔森)对法体系统一性问题的答案”,〔32〕See José de Sousa e Brito, Sources, Recognition and the Unity of the Legal System, Springer Nature B. V. 2019, p. 20.因此,下位规范必须符合上位规范才能被赋予法效力,进而有资格被应用于司法裁判。第二,以“法秩序的存在论统一”为立论前提,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要求在司法裁判中排除规范矛盾。在特定法秩序内,一个抽象或具体的行为,同时显得是被要求的和不被要求的,或者是被禁止的和不被禁止的,或者完全是被要求的和被禁止的,基于存在论的理由,是不可能成立的,〔33〕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200 页。故而,拟适用的法规范必须先行消除此种矛盾,才有资格成为案件的裁判依据。第三,以“法秩序的目的论统一”为立论前提,着眼于法秩序的目的论属性,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只能要求,在司法裁判中排除明显违背“目的—手段”要求的法秩序矛盾。“法秩序的统一性要求在于,将完全不认可目的合理性的手段选择和与目的实现完全相背离的手段选择全部排除出去,是将与目的重要性成反比的、明显的违反比例原则的手段选择排除出去。”〔34〕[日]京藤哲久:《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判断的相对性》,王释锋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0 年第1 期,第152 页。
很显然,在要求司法裁判应当尽可能排除法秩序矛盾这一点上,上述见解共享着相同的理论主张,但是在构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具体裁判要求时,上述见解却存在着显著差别。当然,在笔者看来,上述关于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之裁判要求的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应缺陷。
首先,“阶层论统一”对法秩序的复杂性把握不足,以致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司法裁判的规范要求失之过窄。诉诸法规范的阶层性来回答法秩序统一性之主张,实际上源于法秩序的阶层构造理论。根据法秩序的阶层构造论,法秩序在结构论上呈现为上下位规范的阶层构造,当且仅当某个规范与确定其创设的更高位阶的规范相符合时,它才具有法效力,才属于特定的法秩序。质言之,根据“阶层论统一”的观念,法秩序的统一性实际上表征为效力基础的统一性,即下位规范必须根据上位规范的授权而被创设,且法秩序内的所有规范在效力基础上最终都必须被追溯至特定的“基础规范”。〔35〕参见[奥]汉斯•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第二版),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240 页以下。但是,特定法秩序内部的矛盾,远非上下位规范矛盾所能囊括;司法裁判中棘手的法秩序矛盾,也并非上下位规范矛盾。除去上下位规范矛盾,法秩序中还存在着同位阶规范矛盾、规范目的矛盾等其他矛盾形态。由此看来,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裁判要求,肯定不只是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
其次,“存在论统一”高估了形式逻辑的功能,以致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司法裁判的规范要求可能会脱离实际。依照“法秩序统一性”的存在论理解,法秩序内部矛盾尤其是规范矛盾之所以必须被排除,不仅是出于逻辑上的考量,更是出于法规范在存在论层面的原因:“法律规范是‘当为规则’。其核心的特征是针对规范的接受对象(Normadressaten)的应然内容。”〔36〕[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69 页。这一应然内容在具体形态上又包括命令、禁止和允许;在存在论上,既然法规范以命令、禁止和允许为其存在方式,那么同一行为当然不可能在被命令的同时,又被允许或禁止。容许规范矛盾也就意味着法秩序在本体论上陷入自我矛盾。由此可知,在裁判问题上,基于“存在论统一”所主张的排除规范矛盾,主要就是排除规范适用过程中,不同规范类型(命令规范、禁止规范、允许规范)之间的逻辑矛盾。然而,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存在论理解,也不能正确推导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司法裁判的全部要求。第一,正如上文所述,法秩序矛盾还包括非规范矛盾;第二,看似具有逻辑冲突的规范矛盾,实际上也不一定为法秩序所不能容忍。例如,在刑法上,因避险行为毁坏财物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允许规范),但在民法上,因避险行为毁坏财物则可能面临损害赔偿义务(命令规范),单独看,这里似乎存在允许规范与命令规范的冲突,但实际上两者又同时为法秩序所接受。因此,单纯以形式逻辑为标准来确定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裁判要求,注定是脱离实际的。
最后,“目的论统一”忽视了规范目的的法秩序联动,以致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司法裁判的规范要求,可能会向法律评价尺度的多元性妥协。毋庸置疑,一旦触及棘手的法秩序矛盾,其必然要被还原为价值判断才能予以处理。正是紧紧抓住了法规范及整体法秩序的目的论属性,“目的论统一说”才认为,尽管法秩序中存在着论理法则矛盾、规范矛盾、价值判断矛盾、阶层矛盾和目的论矛盾,〔37〕京藤哲久,法秩序の統一性と違法性判断の相対性,平野龍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卷),有斐阁,1990 年9 月,頁196 以下。转引自王荣溥:《法秩序一致性与可罚的违法性》,载《东吴法律学报》(第20 卷)2008 年第2 期,第74 页。但法规范不过系实现规整目的之手段行为,规范矛盾在性质上并不属于逻辑矛盾,基于规范矛盾作出行为选择同样具有现实可能性。在将法秩序矛盾还原为目的论矛盾这一点上,目的论进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脱离了法秩序的目的体系化或者说价值判断融贯性要求。归根结底,由于目的论理解局限于极少数规范之间的“目的—手段”考察,故其只能要求“将完全不认可目的合理性的手段选择和与目的实现完全相背离的手段选择全部排除出去”。可是,一旦个案评价超越这一范畴,法秩序的统一性就很可能会滑向法秩序的相对性。特别是当个案评价必须超越单一法域之时,“在由不同法域所构成的法秩序中,法域间的规范目的如果欠缺体系化脉络,就很可能会因特定规范的‘溢出效应’而使规范受众无所适从,以致造成法秩序的规整失序”。〔38〕陈金钊、吴冬兴:《论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违法判断的法域协调》,载《东岳论丛》2021 年第8 期,第164-165 页。也就是说,尽管特定规范作为特定目的的实现手段具有妥当性,但一旦超越原有的目的射程,与其他规范目的产生关联,只维系极少数规范之间的目的论统一,进而主张不同法域应该根据自身的标准独自展开法律评价,却未必是妥当的。例如一旦发生跨法域的规范目的冲突,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裁判要求,就很可能会向法律评价尺度的多元性妥协。
(二)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在规范要求上具有层次性
“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可以被多种方式应用的事实,不必然被理解为其确切内容在表述上的不确定性,而仅仅是这一原则可被以多种方式接近的证明。”〔39〕Phillip Hellwege & Marta Soniewicka, Die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Annäherungen-Bestandsaufnahmen-Reflexionen, Mohr Siebeck, 2020, S. 3.以法律适用的逻辑次序为标准,本文认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司法裁判的规范要求,在结构上应当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第一,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之所以将之作为第一个层次,是因为在法律适用的逻辑次序上,首先就是对待适用的规范是否有效,即是否与上位法相冲突进行考察。第二,排除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矛盾。之所以将之作为第二个层次,是因为选择哪一个有效的规范进行适用,在操作序列上劣后于效力考察,但优先于规范背后的价值判断考察。第三,排除关联性规范的价值判断矛盾。其之所以被当作第三个层次,是因为只有在被选定的有效规范可能导致不妥的适用结论时,才需要协调具有体系关联之规范背后的价值判断。
第一个层次: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在纵向维度上,“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最高层级,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法规范整体。在整个法秩序中,上位法的规范效力优于下位法,下位法规范不得与上位法规范发生矛盾。”〔40〕马春晓:《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与行政犯的不法判断》,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2 期,第38 页。法学上的效力,既不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效力(实际效力),也不同于伦理学意义上的效力(道德效力),其核心要义在于针对规范受众的无差别拘束力。“当一条规范是由有权机关以按照规定的方式所制定,并且不抵触上位阶的法律——简单说,就是由权威所制定的,则这条规范是法律上有效的。”〔41〕[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概念与法效力》,王鹏翔译,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92 页。进言之,在司法裁判中,待适用的规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实际上取决于两点:第一,该规范是否在形式上获得上位法的授权而被创制;第二,该规范是否在内容上与授权的上位法相兼容。上下位规范之间发生冲突至少意味着,在该案件中,下位规范对被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法律拘束力。故而,在个案裁判中,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无疑构成了确定裁判依据的第一要务。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一个法律形式只有在授权另一个法律形式产生的基础上并能够单向否定被授权产生的法律形式的效力时,两者之间才能形成上下位阶关系。”〔42〕王锴:《法律位阶判断标准的反思与运用》,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2 期,第5 页。
准此而言,“法秩序统一性”的阶层论理解,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在纵向维度的裁判要求: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事实上,法律适用的首要步骤就是针对拟适用的法规范进行效力审查,只有有效的法规范才能作为适格的规范进入下一步适用程序。因此,为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就需要对该规范进行效力审查,即授权基础审查和内容审查。其中,授权基础审查主要考察待适用的规范是否存在上位法授权,只有存在上位法授权,才能进入内容审查环节;内容审查则主要考察待适用的规范是否在内容上不抵触上位法,其具体要求又包括不得作出相反规定、不得作出抵消规定、不得超越创设权限等。〔4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303 页。
第二个层次:排除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矛盾。规范适用,指的是法规范涵摄案件事实的推理过程,其在法律方法论上也被称为规范适用推理。规范适用的核心要求即据法判断,其具体路径是通过将法律规范作为规定性的大前提,使案件事实被归入构成要件以确定法律后果。即便特定法规范因满足不抵触上位法之要求而具有法效力,但其并不必然具有个案拘束力。因为在规范适用过程中,一旦出现不同规范在调整范围上的“重叠”,在规范适用层面就可能会出现“法律结果不相容、规范的可适用性互相排斥的情况”。〔44〕孔红:《规范冲突问题及其非单调逻辑研究》,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2 期,第33 页。这便是“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矛盾”。此时,需要法律适用者根据一定的规则选择恰当的规范进行适用。如果不能消除规范适用矛盾,就会形成“碰撞漏洞”,即“该矛盾所涉及到的法条便会互相把对方废止”。〔45〕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277 页。也就是说,碰撞漏洞意味着,无法处理的规范竞合将导致相关规范均不得被适用。在我国,若涉及非同一机关制定的同位阶规范、同一机关新的一般规定和旧的特别规定竞合,则需要根据《立法法》确定的法定程序报请有关机关进行裁决。
当然,“法秩序统一性”的存在论理解,已经有效证立了排除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矛盾这一裁判要求。毕竟,同一案件事实肯定不能同时对应具有内在冲突的规范,否则就可能诱发规范适用矛盾。但不同规范之间的适用矛盾判断,应以案件事实所对应之法律事实的性质为标准。只要法律事实性质不同,就不能认为规范之间存在适用矛盾。例如,若同一案件事实同时涉及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就不存在规范适用矛盾,即便不同规范于此时产生实质冲突,也只能在价值判断矛盾的范畴中处理,因为法领域本就是功能分化的产物,不同性质的法律评价肯定无法严格按照形式逻辑进行统一化处理。质言之,“以法学的科学性追求、法秩序的层级构造理论、法的安定性作为支撑的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本内涵是,在保证行为指引统一的前提下,允许不同法域根据自身目的进行相对判断。”〔46〕陈文涛:《犯罪认定中的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内涵澄清与规则构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2 期,第46 页。
具体来说,欲排除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矛盾,要求裁判主体以待适用的规范为原点,对竞合型规范进行考察,然后再行确定应适用的规范。在法律方法论上,传统的规范竞合关系主要包括“事实的法律竞合”和“时间的法律竞合”,前者表征为同一法律事实同时对应不同的构成要件或法律后果,后者则表征为同一法律事实同时受到具有差异的新规范和旧规范(旧规范未被明文废止,否则就不存在适用冲突)之调整。针对“事实的法律竞合”,一般适用特殊规范优先规则,针对“时间的法律竞合”,则一般适用新法规范优先规则。此外,就原则和规则的优先适用关系而言,基于“向一般条款逃逸之禁止”,规则相较于原则亦具有优先性;就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而言,除保留条款外,国际法规范优先于国内法被适用。但是,上述规范竞合的处理规则并非绝对,总是存在某些例外。例如,基于法律规范的“可废止性”,〔47〕法律规范的“可废止性”指的是,“如果一个规范前提可以在语义上覆盖当前案件,按照推论规则,与这个前提相关联的后果本应当被归属于这个案件,但基于其他理由(主要是规范性理由),这种归属失去了正当性。”详见宋旭光:《论法学中的可废止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 年第2 期,第135 页。当某些规范的适用会导致极端的不公正时,就可能会适用一般规范、旧法规范或法律原则等进行裁判。
第三个层次:排除关联性规范的价值判断矛盾。在本质意义上,法秩序应被视为一个价值判断的统一体。“要‘理解’法规范就必须发掘其中所包含的评价及该评价的作用范围。”〔48〕[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94 页。尽管在利益法学之前,价值判断被剥离于法之适用过程,但对概念法学和法律形式主义的理论反思,使得价值判断经由利益法学的“利益裁断”最终被重组为评价法学的核心概念。裁判大前提的形成,肯定必须遵循特定法秩序内价值判断一致性之要求。质言之,不论是经解释形成的裁判大前提,还是经由法官造法形成的个案规范,其背后所潜藏的价值判断,应当尽可能以特定法秩序内的其他价值判断为准据或与之相兼容。如果根据有效且排除了竞合的法规范所得出的裁判结论,与法秩序中其他规范所代表的价值判断存在内部龃龉,也会被认为发生了司法评价矛盾。本文将之称为“关联性规范的价值判断矛盾”。特别是在不同的法域之间,作为价值判断体系的法秩序要求,“不同法领域不得产生相冲突的评价方案”。〔49〕Dagmar Felix, Das Ehegattensplitting und die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Barbara Seel (Hrsg.), Ehegattensplitting und Familienpolitik,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08. S. 77.此时,就应以协调不同的价值判断为目标,通过修正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来化解价值判断矛盾。
应当说,“法秩序统一性”的目的论理解,已经正确地引出了价值判断在排除法秩序矛盾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只不过,法规范的“目的—手段”关系,不能被局限在极少数规范或单一部门法之内,而应被拓展至整个法秩序。因为法秩序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依赖的是所有法规范的协力,而非单个规范或单一部门法的作用。因此,欲排除特定法秩序内部关联性规范的价值判断矛盾,还需要法律适用者在进行个案裁判时,尽可能注重规范目的的彼此调和,而这个调和者,就是特定法秩序中法律价值的关系安排。
基于法律价值之间的结构论模式可知,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安排可以分为优先模式、初步优先模式和权衡模式。优先模式意味着,在特定情形下,某些价值相对于其他价值具有优先性;初步优先模式则会指向特定法秩序所处社会的价值偏好,主张此类价值的优先性一般只需承担较小的论证负担;权衡模式意味着,分量相当的法律价值需要结合个案才能逐一生成具体的价值序列。〔50〕参见雷磊:《法律体系、法律方法与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64-66 页。因此,欲澄清特定法秩序中法律价值的关系安排,必然需要诉诸法律价值的结构论模式。
首先,在价值优先模式之下,价值判断矛盾需要以同位阶规范、上位规范或宪法规范所蕴含的价值主张为处理准据。在特定法秩序中,优先关系的获取可能具有如下三个来源:在合位阶的同位规范之间,某种法律价值获得法秩序的特别支持,而其他法律价值并未获得法秩序的特别支持;上位规范对不同价值之优先序列做了特别安排;相对于其他价值,宪法上基本权所表征的价值具有优先性。其次,在价值初步优先模式之下,价值判断矛盾的处理准据,则需要参酌该法秩序所处之社会的价值性偏好。例如,弱者优先、集体利益优先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类价值偏好是不可推翻的,存在更强的理由时,就可以通过论证否定这种价值安排。例如,集体利益未必总是优先于个人利益。最后,在价值权衡模式之下,处理价值判断矛盾,一方面,需要遵循法律方法论提供的利益衡量特别是后果衡量方法,在考察相关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法律论证给出适合个案的价值序列。另一方面,更需倚重法教义学基于类案的类型化提炼,以避免司法裁判的重复处理。例如,公序良俗原则的类型化适用就包括十余种具体子类型,不同的子类型实际上代表着价值序列的分殊化安排,这种价值安排可以大大减轻后续类案裁判的论证负担。
三、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实施依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
在司法裁判中,法律评价的完整环节包括构成要件评价和法律后果评价。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在裁判中的具体落实,显然需要以“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为其实践框架。因为法律适用者总是在案件事实的构成要件评价或法律后果评价程序中,去处理可能触及的法秩序矛盾,而非对所有类型的法秩序矛盾进行抽象审查。故而,只有当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被正确地安置到“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中时,其才能真正得到有效贯彻。否则,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就很可能会沦为一个在“方法上盲目飞行”的空洞理念。由此亦可看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裁判落实,既不能被不当划约为违法性理论(诸如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违法多元论),〔51〕相关内容可参见陈金钊、吴冬兴:《论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违法判断的法域协调》,载《东岳论丛》2021 年第8 期,第162 页以下。也不能被过分缩减为法律效果的统一,〔52〕相关内容可参见陈少青:《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法律效果论”之展开》,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4 期,第73 页以下。而应透过“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是处理法秩序矛盾的实践支点
从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到一项不抵触整体法秩序的裁判,显然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毕竟,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与个案裁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逻辑推导关系。作为一项极其抽象的法理原则,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落实,必然需要诉诸司法评价的具体操作模式。如果忽略了司法裁判的具体操作模式,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就会因欠缺实践支点而沦为单纯的裁判修辞,其实践效益亦会大打折扣。本文认为,这个实践支点,就是司法裁判经常运用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
所谓“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指的是在司法裁判中,由构成要件评价和法律后果评价共同构成的个案评价体系。这一评价结构,实际上源于法律规则本身的逻辑结构。“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理论服务于法律推理的正确形式这一核心要旨,将法律规则在逻辑上构造为‘构成要件+法律后果’合乎目的。”〔53〕雷磊:《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85-86 页。由于一项完全规范在结构上必然包含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根据法律判断的形式性格,司法评价也必然是构成要件评价和法律后果评价的结合。具体来说,构成要件评价是指,“案件事实将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对比,据此我们可以作出判断,案件事实(Sachverhalt)是否属于法律所规定的构成要件(Tatbestand)。”〔54〕[德]罗兰德•史梅尔:《如何解答法律题:解题三段论、正确的表达和格式》,胡苗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7 页。例如,案件事实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契约是否满足生效要件。当然,每一构成要件,实际上又包含不同的构成要件要素,案件事实是否能被归入构成要件,需要就每一个构成要件要素逐一判断。只有当案件事实满足了每一个构成要件要素时,才能确定案件事实符合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则意谓,根据法秩序设定的法律后果条款,来决定符合构成要件之案件事实的法律处理。例如,犯罪如何处罚,契约是否合法,侵权如何赔偿。司法评价一般始于构成要件评价,终于法律后果评价,两者共同确定了法律评价的样貌。例如,在刑事裁判中,法律评价就包括犯罪构成评价和刑罚评价;在民事裁判中,法律评价就包括构成要件评价和民事后果评价。因此,只有从构成要件评价到法律后果评价的连续链条中,才能窥见法律评价的完整结构。
在裁判问题上,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核心要义正是排除司法评价的法秩序矛盾,而案件事实的司法评价模式又表征为“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故而,唯有透过“评价”这一概念,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和“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才能在司法裁判中被正确地关联到一起。一方面,只要诉诸“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就可以明确,在司法裁判中,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实践场域,就是构成要件评价领域或法律后果评价领域。此时,无论是上下位规范的效力冲突,还是同位阶规范的适用冲突、关联性规范的价值判断冲突,甚至所谓的法概念冲突,要么会作用于构成要件评价生成评价矛盾,例如,已经被民法评价为合法的行为,如果认为其符合刑法上的犯罪构成,就会被认为出现了司法评价矛盾;要么会作用于法律后果评价而生成司法评价矛盾,例如,为偿还公司到期债务,直接要求认缴资本加速到期以清偿债务,就会与法人破产制度相冲突,也会被认为出现了司法评价矛盾。此时,被拉入裁判者视野的,就是构成要件评价或法律后果评价,在法秩序整体中被割裂之状态。另一方面,在确定实践场域的基础上,借助“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还可以进一步厘清落实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思维路径。进言之,依托“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裁判者就会明白,欲实现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也就是分别在构成要件评价和法律后果评价层面,以司法的权限为边界,尽可能协调不同规范在裁判应用中可能发生的内在冲突,进而实现司法评价在整体法秩序内的无矛盾性。
(二)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在构成要件评价层面的映射
在构成要件评价层面发生的法秩序矛盾,指的是案件事实符合或不符合该构成要件,被认为与法秩序中的其他部分存在冲突。例如,根据上位规范,案件事实符合构成要件,但根据下位规范,案件事实却不符合构成要件,如果以上位规范为准,就会与下位规范产生冲突,如果以下位规范为准,又会与上位规范产生冲突。欲妥善处理在构成要件评价层面可能出现的评价矛盾,需要将法的行为规范属性作为排除矛盾的理论起点。
众所周知,法首先是作为行为规范而存在的。“行为规范的效用系在防患于法生活之弊病,故违反行为规范的行为属于不法行为。”〔55〕洪逊欣:《法理学》,自印本1984 年版,第466 页。尽管法规范同时还须负担裁判规范之功能,其行为规范属性有时亦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作出让步,以便裁判者能透过专业的眼光,调适法规范的纠纷应对能力。但是,一般国民所关注的行为在法秩序中之具体妥当性,应被给予最低程度的保障。进言之,根据法的行为规范属性,法秩序被要求为规范受众提供不包含矛盾的行为指令。这一点应当构成在司法裁判中落实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制度原点。因为在特定法秩序中,特定案件事实能否被归入特定构成要件,事实上取决于所依据的法规范。既然法规范作为行为指令不应存在相互冲突,那么,在确定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时,就必须以整体法秩序为视域,对可能发生体系关联的规范进行考察,避免相冲突的行为指令同时介入对案件事实的构成要件评价。
当然,在此之前还需要明确,为什么判断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时,需要考量同一法秩序中的其他规范。这主要源于大陆法系的抽象立法和部门立法传统。其一,在抽象立法的维度上,构成要件要素及其释义性规定,并不总是被作集中式的规定,而是基于规范之间的逻辑关联,被分置于法秩序的不同场所。“不仅不完全规范,即便所谓的完全规范,亦不过是规范意义链之一环。”〔56〕朱庆育:《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50 页。也就是说,即便面对完全法条,也需要结合非完全法条,如说明性法条、限制性法条、指示参照性法条、作为指示参引的法律拟制等,〔5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138-143 页。才能确定具体的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如果未对具有体系关联的其他规范进行考察,就可能会在构成要件评价层面诱发矛盾。其二,在部门立法的维度上,根据规范对象和规范方法之差异形成的部门法分立之格局,并不总是能够以彼此协调的方式,在构成要件评价层面达成无矛盾要求。特别是在公私法日益交融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司法评价在整体法秩序内的妥适性,对其他领域的关联性规范进行考量亦属必要。正如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所言,“在最终探求国民看来的具体妥当性这一点上,不同法域之间应不存在本质差异。”〔58〕[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4 页。因此,在确定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时,显然不能局促于单行法或单个部门法,而应以整体法秩序为视域。如果忽略了此种考量,也可能会诱发构成要件评价矛盾。
具体来说,为了尽可能避免在构成要件评价层面出现矛盾,结合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司法裁判的规范要求,必须基于如下步骤来判定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
1.在协调上下位规范的维度上,为了排除规范间的效力矛盾,应根据上位规范作出判断。在协调同位阶规范的维度上,为了排除规范间的适用矛盾,应基于特殊规范、新法规范等作出判断。若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竞合无法处理,则应根据“碰撞无效规则”,认定这些规范均不能作用于判断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对此无需赘言。兹以“新法规范优先”为例。在旧《婚姻法》的相关司法解释未被废止之前,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 年1 月18 日正式施行)第3 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 条第3 款(2017年3 月1 日正式施行)却规定:“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因诈骗行为而形成的侵权或合同之债,如果不法利益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呢?此时就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 条,而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24 条第3 款,认定这一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为前者属于新法规范,后者属于旧法规范。
2.在协调关联性规范价值判断的维度上,需要先行考察相关规范的具体“规范目的”存在何种体系关联。只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规范目的”宜作狭义理解,其“是指立法者制定法规范时所欲实现的目的,其与法秩序目的、法益、规范违反等属于不同层面的范畴”。〔59〕于改之:《法域协调视角下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2 期,第207 页。首先,若规范目的完全同一,依照法的行为规范属性,应根据“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进行处理。否则规范受众对法规范指引行为的信赖利益就会落空,法秩序的规范期待保障机能也就得不到实现。以未形成“传播源”的“深层链接行为”是否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为例。不管是在民法还是刑法上,显然都以保护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目的。因此,刑法和民法在规范目的上完全一致。但民法通说和民事裁判均认为,《著作权法》第10 条所涉及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其终极标准应为“服务器标准”(即将作品上传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服务器)而非“用户感知标准”(即用户认为作品由设链网站提供)或“实质呈现标准”(即实质性地改变作品的呈现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设链行为未形成“传播源”,其就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60〕参见王迁:《论提供“深层链接”行为的法律定性及其规制》,载《法学》2016 年第10 期,第25-26 页。那么,在刑法上,判断未形成“传播源”的“深层链接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就不应基于社会危害性,共犯正犯化,抑或是实质性改变作品呈现方式等理由,〔61〕参见欧阳本祺:《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的刑事归责——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为中心》,载《法学家》2013 年第3 期,第134 页。而应根据民法上的“服务器标准”,认定其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故而并不符合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构成。
其次,若规范目的并非完全同一,则应根据排除价值判断矛盾的基本思路进行处理,即从法律价值的优先模式、初步优先模式或权衡模式出发,审慎判定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在优先模式下,当某一规范目的受到法秩序的特别支持,就应认可此种目的对价值序列的安排,并将该目的所对应的规范,作为确定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的依据之一;在初步优先模式下,推定具有相对优先性的价值获得法律保护,进而确定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在权衡模式下,则主要依赖法官结合个案情况(案型)安排价值序列,进而得出判断结论。以“拒不返还基于不法原因的给付物”在刑法上是否构成侵占罪为例。在民法看来,“法律之所以规定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请求返还,系对本身不清白者拒予保护(clean hand principle),并具有预防不法的一般功用。”〔62〕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80 页。也就是说,为表达对行为的否定评价和预防不法,在给付人和受让人之间,法秩序排除了受让人的财产利益返还请求权。这意味着相对于公共秩序价值,给付人的财产权价值保护具有劣后性。而侵占罪只是一般性肯定给付人的财产权价值。根据法律价值的优先模式,由于民法上存在着特殊的规范目的,而刑法的规范目的又不能否认民法的规范目的。故而,在确定“不法原因给付物”是否属于“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时,就应以民法的规范目的为依据,否认“不法原因给付物”属于“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继而认定此种事实不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
(三)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在法律后果评价层面的映射
在法律后果评价层面发生的评价矛盾,是指对符合构成要件之案件事实给出的法律后果,被认为与法秩序中的其他规范相冲突。例如,当下位规范设置了比上位规范更严厉的行政处罚时:若根据上位规范进行处罚,会与下位规范相冲突;若根据下位规范进行处罚,又会与上位规范相冲突。由于法律后果直接关联着诉讼各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因而,在法律后果评价层面,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当然也包含排除司法评价的法秩序矛盾这一要求。只不过,与构成要件评价相比,即便确定了符合构成要件之案件事实的具体法律后果,在如何分配此种法律后果之问题上,仍须基于整体法秩序展开衡量,而构成要件评价只需要判断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因此,在决定如何分配特定法律后果时,法律后果评价还须尽可能尊重法律系统的内部功能分化,最大限度地协调不同规范的适用空间,避免后果评价的目的论冲突,以实现法秩序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优化。
与构成要件评价同理,之所以必须在法律后果评价层面,审查整体法秩序中具有体系关联的其他规范要素,也是基于抽象立法和部门立法的法系传统,在此不作赘述。具体来说,在特定法秩序中,为了尽可能避免在法律后果评价层面出现矛盾,结合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司法裁判的规范要求,必须基于如下思路进行处理。
第一,在确认符合构成要件之案件事实的具体法律后果这一问题上:
1.在协调上下位规范的维度上,为了排除规范间的效力矛盾,应根据上位规范确定具体的法律后果;在协调同位阶规范的维度上,为了排除规范间的适用矛盾,应根据特殊规范、新法规范等确定具体的法律后果,若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竞合无法处理,则应根据“碰撞无效规则”,认定两者均不能作用于具体法律后果的确定。上述两点作为一般法理在法律后果评价领域的应用,亦无需赘言。兹以“上位规范优先规则”为例。教育部制定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9 条第2 款规定:“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但国务院制定的《教师资格条例》第20 条却规定:“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的,其考试成绩作废,3 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在确定教师资格考试作弊行为的行政处罚时,由于《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9 条第2 款构成《教师资格条例》第20 条的下位规范,因此,法院就应认为,行政机关根据《教师资格条例》第20 条对作弊者作出行政处罚属于合法的行政行为。
2.在协调关联性规范价值判断矛盾的维度上,尽管在法律后果评价层面也可能存在矛盾,但是由于已经确认案件事实符合构成要件的调整范围,这类矛盾通常就超越了司法的权限,法律适用者一般无权通过法律方法作出调整。例如,对于同质的犯罪行为,法秩序却给出了不同的法定刑。此时,只能通过特别程序报请有关机关再行处理,或者通过立法程序修改法律,否则司法者无法消除在法律后果评价层面出现的评价矛盾。
第二,在如何分配已被确认的法律后果这一问题上,也应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使拟施加的法律后果与特定法秩序中的其他法律后果相协调。因为在特定法秩序中,所有类型的法律后果,都应当服务于法秩序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优化这一目标。故而,特定法律后果的施加,肯定不能与已经或应发生的其他法律后果产生实质性冲突。欲处理这类后果评价矛盾,首先,应根据已经法定化或类型化的规则进行处理。例如,《刑法》 第36 条第2 款就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一法律后果分配规范,实际上暗含着民事权益优先保护的理念。其次,在规则缺位之时,就需要通过法益衡量的方式,决定法律后果如何分配。以“帅英骗保案”为例,本案涉及的是已罹除斥期间之保险诈骗行为的刑法评价难题。在本案中,帅英的行为确实符合保险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关刑罚规定也是明确的,但在是否发动刑罚这一点上,则应斟酌除斥期间的风险分配功能和刑罚的特性作出决定。由于旧《保险法》第54 条第1 款已经通过除斥期间的风险分配功能,对相关的交易风险进行了分配,当除斥期间经过后,此时是否还需刑罚介入,需要在法政策上审慎考量:第一,刑法打击保险诈骗行为,肯定不应以牺牲被保险人的期限利益为代价;第二,帅英的保险诈骗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保险人怠于履行审查义务,刑法介入会在强势的保险人和弱势的被保险人之间造成法律保护失衡;第三,“法秩序的统一性要求目的和手段的协调性,相较于刑事制裁,除斥期间制度的风险分配更能配合法益保护目的实现”,〔63〕蒋太珂:《除斥期间的刑法评价》,载《政法论坛》2020 年第3 期,第148 页。当保险人通过正常的职务行为就可以预防此类不法行为时,刑罚介入就有违谦抑性和刑罚正义要求。因此,当除斥期间经过之后,为了实现法律后果评价的法秩序无矛盾,即便帅英成立保险诈骗罪,也应将保险公司“未行使撤销权之事实”当作“客观的处罚条件”,阻却刑罚的发动。
四、结语
明确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司法应用逻辑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种系统化的‘思路’注定要占据统治地位,它……逐渐地……将我们从旁路和错误的道路上带了回来;它一个接一个地准备好单个的素质和适合性,这些素质和适当性有一天被证明是实现整体性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它在对支配性的任务、‘目标(goal)’‘目的(aim)’或‘意义’给出任何线索之前,训练好所有有用的能力。”〔64〕[美]罗纳德•德沃金:《刺猬的正义》,周望、徐宗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83 页。以司法裁判的“体系正义”为导向,包括指导性案例、类案检索等在内的诸多制度性要求,实际上都离不开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参与。准此而言,法规范系统的理性统一不仅构成逻辑公设,法律系统作为“价值—目的论”统一体,也是理念性规定和具有实益的论证公式。〔65〕Vgl. Ota Weinberger, Reine oder funktionalistische Rechtsbetrachtung?, Ota Weinberger & Werner Krawietz(Hrsg.), Reine Rechtslehre im Spiegel ihrer Fortsetzer und Kritiker, Springer-Verlag, 1988, S. 245.在规范定性上,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系司法裁判必须遵循的辅助性原则,其不仅构成指引司法裁判的有益“论证公式”,也是源于维护司法德性、裁判义务和宪法价值尊严等现代法治基础命题的法理设计;在意义结构上,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对司法裁判的规范要求,实际上包含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排除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矛盾、排除关联性规范的价值判断矛盾这三个层次;在应用方案上,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必须将“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作为司法应用的逻辑支点,以法的行为规范为指引,在尽可能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矛盾和关联性规范的价值判断矛盾之基础上,审慎确定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法律后果的具体内容及其分配方式,进而实现司法评价在整体法秩序内的妥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