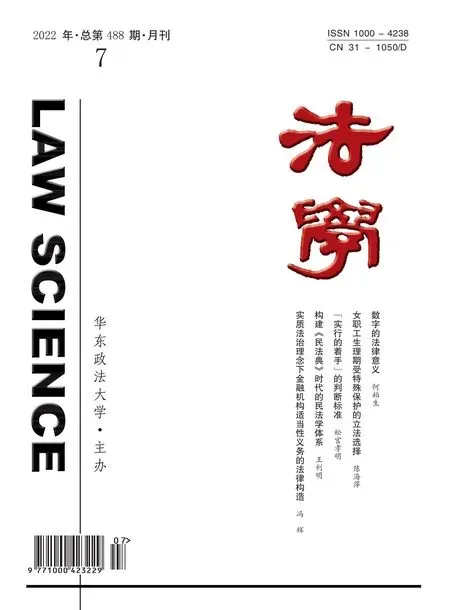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比较法考察及其启示
在当今多国的法律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是极富争议的民事救济措施。大陆法系国家多视其为法律禁忌,基本不认可,其法院也可能对普通法系国家法院作出的涉及惩罚性赔偿的判决不予执行。〔1〕See Volker Behr, Punitive Damages in American and German Law-Tendencies towards Approximation of Apparently Irreconcilable Concepts, 78 Chicago-Kent Law Review 105, 153-154 (2003).普通法系国家虽然认可惩罚性赔偿,将其作为侵权法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也认为它具有不确定性,甚至视其为法律的“异类”或“幽灵”,司法适用极为审慎。〔2〕See Rookes v. Barnard [1964] UKHL 1, p. 34;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1.惩罚性赔偿根植于普通法系国家的侵权法,普通法是其基础,也是解析惩罚性赔偿的密码,对基本属制定法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而言也是如此,忽略普通法传统就可能难以系统理解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相应地,一项法律制度的构建断非将文本经由立法固定为法律就能奏效,它需要法律体系作为支撑。如果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渊源、传统与实质不求甚解,仅知简单拿来和机械适用,就可能对其制度风险茫然无知。〔3〕参见刘银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类型化适用与风险避免——基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1 期,第183-186 页。对于基本属大陆法系的我国而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并非易事,不是将惩罚性赔偿简单纳入《民法典》和各知识产权法就能确保制度有效实施。本文将从比较法的视角解析普通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以及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与适用,希望为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性建构与实施提供借鉴。
一、普通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体系功能
(一)损害赔偿、加重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
侵权法是普通法系国家的基础法律制度,基本功能是为被侵权人提供合理救济。侵权法下的赔偿包括损害赔偿、加重赔偿、惩戒性或惩罚性赔偿等多种类型。多样性的概念体现出普通法关于侵权赔偿救济的多样性。损害赔偿(damages)即一般意义上的赔偿,也称补偿性或恢复性赔偿,基本遵循填平原则,目标是使原告的权利或利益恢复至没有被侵害的状态。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无论原告的损失是否容易界定,损害赔偿的逻辑都是如此。〔4〕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s. 153-154 (LeBel J. dissenting).损害赔偿及其目标也为大陆法系国家所认可,在国际条约层次则体现在WTO 的TRIPS 协议等文本中。〔5〕See TRIPS, Article 45.加重赔偿(aggravated damages)是指通过增加赔偿的方式赔偿原告因侵权方式或持续时间等受到的加重损害。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加重赔偿虽然可能针对与惩罚性赔偿相同的侵权行为,但其功能仍属补偿性,一般用于补偿原告因被告的可责性行为对其造成的无形伤害,目的是补偿加重的损害,且只能为此目的裁决。〔6〕See Vorvis v.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1989] 1 SCR 1085.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也认为加重赔偿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原告,而非惩罚或威慑。〔7〕See Uren v. John Fairfax & Sons Pty Limited, [1966] 117 CLR 118, p. 149.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指目的在于惩罚与威慑不法行为的赔偿。英联邦国家广泛使用惩戒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的概念,其目的也基本是惩罚与威慑(报复和谴责)不法行为。〔8〕我国研究者多将“exemplary damages”称为“示范性赔偿”,并不确切。此处“exemplary”并非“示范”之意,而是惩戒之意。参见《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5 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版,第846 页,“exemplary”条。我国研究者对两者基本不作区分,直接视为等义。本文将视其语境,分别使用惩戒性赔偿(英联邦国家)或惩罚性赔偿(美国、加拿大),并统称为惩罚性赔偿。惩罚性或惩戒性赔偿的目的不是补偿原告,而是惩罚被告,遵循与补偿性赔偿不同的逻辑。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称,惩罚性赔偿“构成旨在补偿受害者而非惩罚不法行为者的一般普通法规则的例外”,〔9〕See Vorvis v.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1989] 1 SCR 1085.并将可惩罚的行为概称为冒犯了法院正派意识(sense of decency)因而需要谴责与惩罚的行为,即“惩罚性赔偿限于如此恶意和肆无忌惮以至于其本身应受到惩罚的故意不法行为”。〔10〕See Honda Canada Inc. v. Keayes, [2008] 2 SCR 362, para. 62.
概言之,在普通法系国家的侵权法中,惩罚性赔偿针对的是被认为冒犯了法院正派意识的恶意不法行为。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与原告应获得的补偿无关。其目的不是为补偿原告,而是为惩罚被告。它是陪审团或法官对被告恶劣行为表达愤慨的方式。”〔11〕See Hill v. Church of Scientology of Toronto, [1995] 2 SCR 1130, para. 196.虽然损害赔偿或加重赔偿的基本意义在于补偿原告的损害,但也可有惩罚的涵义,甚至可构成足够的“惩罚”。例如,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曾在一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中认为,原告已获得300 万澳元的补偿性赔偿,就不再有裁决附加赔偿(惩罚性赔偿)的必要。〔12〕See Stephen Graw, Additional Damages under Australi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utes, p. 22, note 85, at https://researchonline.jcu.edu.au/53228/1/53228_Graw_2016.pdf, last visit on March 12, 2022.相应地,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和目标根本不同,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损害赔偿重视原告的损失即侵权行为的结果,而惩罚性赔偿重视侵权行为本身。“必须直接和独立地评估被告错误的严重性,并相应地评估惩罚的合适程度。其他形式的赔偿关注原告的损失,但惩罚性赔偿主要关注被告行为的过错程度。”〔13〕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s. 156-157 (LeBel J. dissenting).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陷与审慎适用
在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功能、制度缺陷等备受批评。英国最高法院于1964年审理的“Rookes v. Barnard 案”堪称其惩戒性赔偿的里程碑案件,其中戴夫林(Lord Devlin)法官对惩戒性赔偿给予了经典论述。〔14〕See Rookes v. Barnard [1964] UKHL 1, p. 34-37.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惩罚性赔偿是民事诉讼中“不受控制和不可控制的幽灵”。〔15〕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1.英国最高法院基于其判例法和制定法,认为惩戒性赔偿的大部分功能可通过加重赔偿得以实现,而其他功能则一般可作为犯罪加以惩罚。由于惩戒性赔偿有助于维护法律的效力,这可支持论证将在逻辑上应属于刑事责任的情形纳入民事责任的合理性。但有时惩戒性赔偿对被告的惩罚要比刑事处罚还严重,因此通过刑事手段使原告获利而忽视被告的刑事法律保障的做法并不合适。〔16〕See Rookes v. Barnard [1964] UKHL 1, p. 37-39.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除非受到严格控制,使(原告)个人受益的私人执法者概念令人担忧。”〔17〕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44.惩罚性赔偿将侵权法的一部分转变为私人刑法,但缺乏与刑事司法系统相关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其适用可导致不利后果,属制度缺陷。〔18〕同上注,第 158 段。侵权法的目的是补偿原告的损失,使其恢复至侵权未发生时的状态,而惩罚性赔偿却可能显著改变侵权法的正当功能。〔19〕同上注,第146-148 段。
鉴于惩罚性赔偿的制度缺陷和风险,普通法系国家对其适用较为审慎。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横跨民事法律(补偿)和刑事法律(惩罚),须针对“显著偏离平常的正当行为标准的具有高度可责性的行为”。〔20〕同上注,第36 段。英国最高法院确立了“如果,仅仅如果”(if, but only if)标准,即惩戒性赔偿作为最后的民事救济措施,仅在损害赔偿不足以惩罚被告(而非补偿原告)的情形下才予考虑:陪审团或法官如果认为损害赔偿不足以表达其对不法行为的不满,不足以惩罚和威慑被告的恶意行为,就可判决惩戒性赔偿。〔21〕See Rookes v. Barnard [1964] UKHL 1, p. 38.英国最高法院将可适用惩戒性赔偿的案件归为三类:政府公职人员实施压迫、任性或违宪的行为;被告玩世不恭地无视原告权利、为牟取利益而算计的侵权行为,使其获利远超应支付给原告的赔偿;出于制定法的规定。〔22〕同上注,第37-38 页。类型化路径对英国的惩戒性赔偿具有指导意义。但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英国将惩戒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某些类别案件的做法并不合理,加、澳、新西兰等普通法系国家均未予接受。不应将惩罚性赔偿限定于某些类别的不法行为,而是应在具体案件中决定是否需要在损害赔偿之上再施加惩罚性赔偿。〔23〕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s. 48, 67.在澳大利亚,惩罚性赔偿亦可适用于各类侵权案件,其亦被理解为法院对被告的恶意不法行为表达谴责和反对,其裁决需要考虑多种因素。〔24〕See Stephen Graw, Additional Damages under Australi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utes, p. 20-23, at https://researchonline.jcu.edu.au/53228/1/53228_Graw_2016.pdf, last visit on March 12, 2022.
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在比较英、澳、美等多个普通法系国家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基本原则。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报复)、威慑和谴责被告从事恶意不法行为。惩罚性赔偿的裁决应更多地基于法律原则。〔25〕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s. 43, 68, 70.除美国外,基本没有普通法系国家为惩罚性赔偿规定公式化的适用标准,如固定的上限、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的倍数关系等。“合适的焦点不是聚焦于原告的损失而是被告的不法行为。机械的或公式化的路径不允许充分考虑在实现公正裁决时应考虑的多种因素。”〔26〕同上注,第73 段。本文认为,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对惩罚性赔偿的公式化适用以及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简单倍数的否定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做法难以确保其合理性。
二、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标准与比例原则
(一)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标准
英国最高法院的戴夫林法官认为:“裁决惩戒性赔偿的权力是一种武器,既可以用来维护自由,也可以用来对抗自由。”〔27〕See Rookes v. Barnard [1964] UKHL 1, p. 38.该观点也为爱尔兰最高法院所引用。〔28〕See Conway v. Irish National Teachers’ Organisation, [1991] 11 I. L. R. M. 497 (S. C.), p. 512.鉴于惩罚性赔偿的两面性,须警惕其适用或滥用可能导致的非正义后果。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有两个中心原则,分别是合理性与比例原则。它在知名的“Whiten 案”中确立了合理性标准(rationality test),供法院和陪审团在裁决惩罚性赔偿及其数额时参考。“合理性的概念持续立足于侵权法的本性、历史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所发挥的功能。”〔29〕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151 (LeBel J. dissenting).这表明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传统有密切关系。惩罚性赔偿需要与不法行为的可责性相对应,不应超越惩罚与威慑的目的,其裁决应是“理性与合理性的产物”。〔30〕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108.
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的惩罚性赔偿合理性标准包括多项因素:惩罚性赔偿不是规则,而是例外;惩罚性赔偿仅针对恶意、任性或显著偏离平常的正当行为标准的高度可责性行为;惩罚性赔偿数额应与行为可责性的程度、原告的相对脆弱性和损失、被告的非法所得等成比例;需考虑被告因该不法行为受到的任何其他罚款、罚金或处罚;惩罚性赔偿一般仅在如果不裁决将使不法行为得不到惩罚或得不到充分惩罚的情形下才适用;其目的不是补偿原告,而是给予被告应得的报应,威慑被告及他人不得从事类似不法行为,表达社会对该行为的共同谴责;惩罚性赔偿仅在损害赔偿不足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情形下才适用;惩罚性赔偿不应超过合理实现其目的所必需的数额;惩罚性赔偿可能让原告获得意外之财,这与罚金等通常归国家不同;加拿大的法官和陪审团通常认为中等程度的惩罚性赔偿就已足够,它在广泛的社会环境下会不可避免地给被告带来耻辱。这些并非每个案件都需全部考虑的因素,因为各案件的具体情形不同,有些案件仅需考虑部分因素即可作出判断。在特定案件中需考虑的因素是其特定情形、惩罚性赔偿的性质以及其裁决对原被告双方公平性的“函数”。〔31〕同上注,第94-95 段。
本文认为,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给出的惩罚性赔偿合理性标准具有综合性,列举的因素涵盖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定位、规范的行为、目的、必要性、比例原则、对双方当事人的影响等方面。其一,惩罚性赔偿并非民事救济的经常性规则,仅属例外情形。其二,惩罚性赔偿所规范的行为基本是具有社会危害性或高度可责性的恶意不法行为。其三,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与威慑恶意不法行为,其必要性体现为防止行为人逃避惩罚与威慑。其四,惩罚性赔偿的裁决应与其目的相符合,数额应符合比例原则,而加拿大的司法实践表明中等水平的惩罚性赔偿即可实现其法律目标。其五,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防止对双方当事人带来不公平,既要避免对被告的过度惩罚,又要防止原告所得构成不当得利。
对惩罚性赔偿合理性的判断需以被告行为的道德可责性或社会危害性为基础。〔32〕See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517 U. S. 559, 575 (1996).具有可责性的行为不仅包括恶意侵权等不法行为本身,还包括与诉讼程序相关的不法行为,甚至较多涉及较大数额的惩罚性赔偿案件多与被告在诉讼中的不当行为有关。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既包括裁决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也包括其数额应以实现法律目的为限,否则就可能超出合理性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一旦超出合理界限,就属于任意剥夺他人合法财产的行为。〔33〕See State Farm Mut. Automobile Ins. Co. v. Campbell, 538 U. S. 408, 417 (2003).法院需审查被告行为的可责性与惩罚严厉性的关系等因素,以免出现不合比例的过度处罚。〔34〕See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517 U. S. 559, 574-575 (1996).爱尔兰最高法院认为,如果损害赔偿足以表达公众对某种不法行为的厌恶与惩罚就不用裁决惩罚性赔偿。〔35〕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s. 58-59.各普通法系国家的共识是惩罚性赔偿不应超出合理的范围。
(二)惩罚性赔偿裁决中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是实现惩罚性赔偿合理性的必要路径。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它是惩罚性赔偿的两个中心原则之一。惩罚性赔偿裁决中的比例原则是指被告需承担的侵权救济责任,其中包括损害赔偿、加重赔偿、惩罚性赔偿以及任何其他处罚或惩罚(如刑事责任),应与其恶意不法行为的可责性成比例,且与惩罚和威慑的目的合理相关。这意味着比例原则应体现为惩罚性赔偿与恶意不法行为的可责性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损害赔偿仅相当于许可费,那么法院利用惩罚性赔偿消除侵权人蛮横地无视他人权利获取的更多收益就是合理的。如果损害赔偿加上惩罚性赔偿导致赔偿过多,就可能超出惩罚所需的合理范畴。惩罚性赔偿只有在能够促进实现其目的之最低数额时才是合理的,任何更高的赔偿数额都不合理。法院应将案件事实与惩罚性赔偿的目的联系起来,考虑惩罚性赔偿的裁决如何促进实现其目的。〔36〕同上注,第71-74、110 段。
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比例原则可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与被告行为的可责性成比例。行为越具可责性,赔偿应越高。判断被告行为可责性的因素包括其行为是否被筹划和故意、行为是否持续较长时间、行为是否侵犯原告的特别个人利益或特定财产、被告的目的和动机、被告是否隐藏或试图隐藏其不法行为、被告是否意识到其错误、被告是否从不法行为中获利等。其二,与原告的经济脆弱性等成比例。与之相对的是被告可能滥用权力。但在商业纠纷中经济脆弱性问题不一定严重,因为双方都是利益追逐者。其三,与带给原告的伤害或潜在伤害成比例。潜在伤害是指尽管被告行为实际产生的伤害不大,但如果其可能给原告带来较大伤害,亦可能导致惩罚性赔偿。其四,与威慑的需求成比例。被告的财富多少只在三种情形下才可能与惩罚性赔偿有关:被告主张财务困难;被告的财富与其不法行为直接相关;较低的惩罚性赔偿对被告可能难以产生威慑效应。其五,与考虑施加或可能施加给被告的其他民事和刑事惩罚后的情形成比例。损害赔偿也有惩罚功能,甚至在很多情形下已足够。刑事责任也是一种重要因素,可导致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降低乃至消失。如果刑事处罚较轻或不足,或者刑事处罚所针对的行为范围窄于惩罚性赔偿所需覆盖的范围,就可能需要惩罚性赔偿。综合考虑被告受到的其他惩罚后,如果不足以实现惩罚与威慑的目的,才有裁决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惩罚性赔偿也仅以补足实现其目的所需数额为限。即仅在惩罚性赔偿的目标所需的惩罚与其所受惩罚之间存在差距时,才可论证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及数额。其六,与被告的不当获利成比例。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包括确保被告不将损害赔偿仅作为其不尊重原告权利的许可费,防止被告获得不法利润,但也需避免使被告面临不公正的结果。法院需防止赔偿叠加或加倍,防止过度惩罚与威慑。惩罚性赔偿仅以惩罚和威慑恶意侵权行为为目的,而非以惩罚被告为目的。〔37〕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s. 112-125.
就惩罚性赔偿的两个中心原则而言,其合理性是目标,比例原则是有助于实现目标的工具,两者的关系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38〕参见刘银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类型化适用与风险避免——基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75-176 页。“惩罚、谴责和威慑是公认的惩罚性赔偿的正当理由,其手段必须与所要达到的目标合比例。不合比例的裁决超出了其目的,变得不合理。低于比例的裁决不能实现其目的。”〔39〕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111.惩罚性赔偿的裁决仅是惩罚与威慑恶意不法行为的手段,手段须符合目的,否则就不具合理性。比例原则的正当适用能够确保惩罚性赔偿的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进而有助于实现其合理性。
(三)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不当得利的关系
惩罚性赔偿的裁决经常涉及其与损害赔偿的关系。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裁决惩戒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被告故意且傲慢地无视原告权利的行为,阻止其再次从事类似行为,因此评估惩戒性赔偿所考虑的因素与评估补偿性赔偿所考虑的因素根本不同。在这两种赔偿之间没有必要保持比例……裁决惩戒性赔偿的目的是‘教导不法行为者侵权(赔偿)所不能教的’。”〔40〕See XL Petroleum (NSW) Pty Ltd v. Caltex Oil (Australia) Pty Ltd, (1985) 155 CLR 448, paras. 9-10 (Brennan J.)这是关于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关系的经典论述。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的目的分别是惩罚被告和补偿原告,两者不具相关性,相互之间也不当然存在比例或倍数关系。
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对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的倍数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其与比例原则的关系有精彩论述。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并非与惩罚性赔偿最相关的因素,因为后者聚焦于原告的损失,前者却需关注被告的不法行为。与其关系相比,比例原则是更一般的概念。“如果要使用倍数,那么该倍数应该衡量什么?用金钱量化损害赔偿迷人地有用,但完全不够,例如在令人发指的不法行为偶然幸运地导致小额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潜在的和实际的损害是不法行为的合理衡量标准,但其他因素也是如此,如动机、计划、脆弱性、滥用支配地位、其他罚款或处罚等。这些特征都没有被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的倍数所捕获。采用倍数虽易于监督,但难以应对惩罚性赔偿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事实上它会削弱惩罚性赔偿的论证所依据的精细原则。毫无疑问,用金钱评估肆无忌惮的行为是困难和不精确的任务,但评估破裂的颅骨、失去的商业机会或破碎的声誉的价值也是如此。然而在没有借助公式或诸如倍数之类的任意规则的情形下,法院每天都在计算这些事物的损害赔偿。”〔41〕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127.
本文认为,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驳斥了借口惩罚性赔偿的不确定性而诉诸其与损害赔偿倍数关系的理由,提示该方法基本偏离了惩罚性赔偿的本质与目的。在侵权诉讼中,人格权或商业机会损害赔偿的计算同样面临类似困难,人们应正视惩罚性赔偿的复杂性,它源自制度本身,难以藉由其与损害赔偿之间的简单倍数加以克服。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亦认为惩戒性赔偿数额的裁决较为困难,其数额难以精确,本来“就不是精确的科学”。〔42〕See Facton Ltd v. Rifai Fashions Pty Ltd, [2012] FCAFC 9, para. 85.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表明,在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没有简单的对应性。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裁决需以不法行为的道德可责性或社会危害性为基础考量因素,无论是将损害赔偿作为基数,还是乘以相关倍数,均无法理依据,反而有方法论上的缺陷。
惩罚性赔偿与被告不当得利的关系是通常被忽略的问题。在TRIPS 协议以及很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下,原告可在其损害赔偿、被告侵权获利或法定赔偿之间选择一种方式获得救济。〔43〕See TRIPS, Article 45. 当然也有例外,如美国《专利法》第284 条没有规定被告的侵权获利与法定赔偿。这意味着在一般侵权救济中,尽管其法理基础不同,但原告的损害赔偿与被告的侵权获利通常具有替代性。然而在惩罚性赔偿的裁决中,二者却不再具有替代性。依据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解释,如果原告主张获得被告的侵权获利,其就不能再主张惩罚性赔偿(版权法下的附加赔偿),而只有在主张损害赔偿的基础上才有理由主张惩罚性赔偿,藉以去除被告因其不法行为而得到的多余侵权获利。法院澄清在被告返还侵权获利的路径中并无惩罚性因素,其目的仅在于阻止侵权人不公平地致富。〔44〕See Facton Ltd v. Rifai Fashions Pty Ltd, [2012] FCAFC 9, paras. 18, 31.美国《商标法》第1117 条a 款也明确规定侵权利润返还是补偿性而非惩罚性的救济。在涉及专利侵权的一则纠纷案中,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先是让被告支付侵权获利,然后又让其支付惩罚性赔偿,属于重复救济。〔45〕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125.这表明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也不认可先要求被告返还侵权获利并继而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做法。美国《专利法》第284 条规定的加重赔偿也仅是针对原告的损害赔偿而未涉及被告的侵权获利。普通法系国家关于惩罚性赔偿与被告侵权获利之间关系的认定与我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和学界认识有根本差异,值得辨析。
三、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附加赔偿解析
英国有悠久的普通法传统,也是近现代惩戒性赔偿制度的起源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英联邦国家以及美国亦有普通法传统,其中包括侵权法下的惩戒性或惩罚性赔偿。针对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英、澳、加等国,被侵权人可依据侵权法主张普通法下的救济,其中包括惩罚性赔偿。普通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与比例原则等也可适用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其中包括针对具有可责性的恶意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惩罚性赔偿裁决的比例原则等。在侵权法的基础上,各普通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又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作出具体规定。英国版权法较早规定了附加赔偿,澳大利亚等国借鉴了该制度。
(一)英国版权法下的附加赔偿
英国1956 年《版权法》首次规定了附加赔偿(additional damages),即被告在一般性的损害赔偿之上再支付给原告的赔偿。〔46〕See 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 Pty Ltd v. Palmer (No. 2), [2021] FCA 434, para. 365.该法第17 条第3 款规定,针对恶意侵犯版权的行为,法院可根据侵权行为的恶性(flagrancy)、被告因侵权而获利且原告不能获得有效救济等其认为合适的情形裁决附加赔偿。该条款其后演化为英国1988 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的第97 条第2 款,即在考虑到所有情形,特别是侵权的恶性和被告因侵权而有任何获利后,为案件公平所需,法院可裁决被告支付附加赔偿。英国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对附加赔偿是属于惩戒性赔偿还是加重赔偿有不同理解。〔47〕See Rookes v. Barnard [1964] UKHL 1, p. 37-39; 徐聪颖:《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功能认知与效用选择——从我国商标权领域的司法判赔实践说起》,载《湖北社会科学》2018 年第7 期,第150 页。本文认为,英国版权法下的附加赔偿基本属于其普通法下惩戒性赔偿原则在版权法中的固定,其中侵权行为的恶性对应恶意、肆无忌惮等侵权行为的可责性,其实施亦需侵权法作为基础。下述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下的附加赔偿亦可对此提供比较法上的支持。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可能同时涉及侵权法下的惩戒性赔偿和版权法下的附加赔偿。如在一则版权纠纷案中,被告为原告拍摄了婚礼照片,约定版权属于原告,然后被告把照片卖给两家报纸,法院判决被告构成恶意侵犯版权并支付一千英镑的惩戒性赔偿。上诉法院认为,惩戒性赔偿既可依普通法裁决,也可依英国1956 年《版权法》裁决。〔48〕See Rookes v. Barnard [1964] UKHL 1, p. 37-39.本文认为,该案虽然在表面上属于版权侵权,但被告侵犯的主要是原告的隐私权,属于侵权法范畴,所以上诉法院认为救济既可依据普通法,也可依据版权法。
英国虽然是近现代惩戒性赔偿制度的起源国,但又曾经是欧盟成员国,法律需受制于欧盟立法,而后者在总体上不支持惩罚性赔偿。欧盟《知识产权实施指令》对于具有主观过错的知识产权侵权的赔偿原则是补偿权利人的损失,而非惩罚性赔偿。〔49〕See EU Directive 2004/48/EC o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cital 26.该指令要求成员国为知识产权侵权提供有效、合比例和劝诫性的救济。被告需支付与原告实际损失相当的赔偿和诉讼成本,但不涉及任何惩罚性赔偿、惩戒性赔偿或附加赔偿。〔50〕同上注,第3.2、13.1、14 条。为实施该指令制定的英国《知识产权实施条例》(2006 年)第3 条的规定基本与此一致,未涉及附加赔偿或惩戒性赔偿,且强调该条例不影响与知识产权侵权救济相关的法律规则的适用。这可理解为英国版权法下的附加赔偿与侵权法下的惩戒性赔偿仍可适用。
欧洲《统一专利法院协议》系统规定了专利侵权赔偿规则,基本涵盖欧洲主要国家的专利侵权赔偿规则。在侵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行为侵犯他人专利权的情形下,首先,侵权人需向被侵权人支付实际的损害赔偿。其次,在可能的程度内,应使被侵权人恢复至侵权没有发生时的状态,且侵权人不应从侵权中获利,但赔偿也不应有惩罚性。最后,法院判决侵权赔偿时应考虑所有合适的因素,如侵权导致的消极经济后果,包括被侵权人失去的利润、侵权人的任何不当获利以及被侵权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作为替代方法,在合适情形下,可考虑通过假定侵权人获得许可使用该专利所需支付的许可费计算赔偿。如果侵权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其行为侵权,法院可命令其返还侵权利润或支付补偿。〔51〕See Agreement on a Unified Patent Court (2013), Article 68, paras. 1-4.因此,欧洲专利侵权赔偿的首要原则是补偿性赔偿,既不让侵权人从中获利,也不对其施加惩罚。这与美国《版权法》第504 条规定的一般侵权赔偿规则基本一致。概言之,损害赔偿和侵权获利返还是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多国所认可。
鉴于欧盟法律框架基本支持补偿性赔偿,不支持惩罚性赔偿,在英、法、德、荷兰、芬兰、丹麦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专利法中皆无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只有奥地利、波兰、立陶宛等少数国家的知识产权法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英国虽然既有侵权法下的惩戒性赔偿传统,又有版权法关于附加赔偿的规定,但其知识产权法并未全面规定惩罚性赔偿,如在英国专利法、商标法中均无关于附加赔偿或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这意味着英国虽然是近现代惩戒性赔偿及版权侵权附加赔偿制度的起源国,但其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与司法皆属保守。
(二)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下的附加赔偿
澳大利亚1968 年《版权法》第115 条第4 款借鉴英国1956 年《版权法》,引入内容基本一致的附加赔偿条款,该条款于2000 年修订时增加数字化侵权形式,于2003 年修订时再增加法院可考虑的因素。其后,澳大利亚《专利法》《商标法》《设计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和《植物育种者法》均规定了内容基本一致的附加赔偿,目的是威慑类似侵权行为的发生。〔52〕See Australian Patents Act 1990 (2018), Section 122(1A); Trade Marks Act 1995 (2015), Section 126(2); Designs Act 2003(2015), Section 75(3); Circuit Layouts Act 1989 (2012), Section 27(4); Plant Breeders Rights Act 1994 (2018), Section 56(3A).法院也明确附加赔偿具有惩罚被告的性质。〔53〕See 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 Pty Ltd v. Palmer (No. 2), [2021] FCA 434, para. 483.因此,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下的附加赔偿就是惩罚性赔偿。
澳大利亚1968 年《版权法》第115 条第2 款针对版权侵权规定的一般救济措施包括禁令、损害赔偿或被告返还侵权利润。该法第115 条第4 款规定,法院在认定侵权损害时,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形下可裁决被告支付附加赔偿。法院考虑的因素包括侵权的恶性、威慑类似侵权的需求、被告侵权或被告知侵权后的行为、侵权行为是否涉及将作品从有形载体转变为数字或其他电子机读形式、被告因侵权获得任何利益以及所有其他相关因素。这些因素(除作品数字化行为外)与上述普通法系国家的法院在裁决惩罚性赔偿时所考虑的因素基本一致。其中,侵权的恶性属于对英国版权法的借鉴,用于指示侵权行为的可责性。威慑的必要性是附加赔偿的重要目标,属于裁决附加赔偿的必要条件,而且威慑不仅包括针对本案侵权人的特别威慑,也包括针对可能从事类似行为的其他人的一般威慑。〔54〕同上注,第486 段。上述作品数字化行为仅是一种特定的侵权形式,并非判断应否给予附加赔偿的一般行为因素,而且其在澳大利亚其他知识产权法中也不存在,此处不予考虑。
第一,“侵权的恶性”是首先需考虑的因素。恶性的同义词包括“可耻、欺骗行为”“故意和算计的侵权”“对原告权利算计性的蔑视”“对利益玩世不恭地追求”等。〔55〕同上注,第482 段。可见,附加赔偿针对的是罔顾他人权利而放肆追求自己利益的恶意侵权行为,体现了道德可责性,可概称为“恶意侵权行为”。此处的侵权行为的恶性仅指该行为本身的恶性,被告威胁原告或虚假抗辩等行为属于法院需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当然,侵权行为的恶性并不必然导致附加赔偿,即前者并非后者的充分条件。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甚至认为它也并非是附加赔偿的必要条件。〔56〕同上注,第483 段。此时被告行为的可责性可能体现在其他因素中,如被告在得知其行为构成侵权后继续侵权(尤其持有蔑视态度)、威胁原告、虚假抗辩等。它们亦可指示被告行为的可责性,可被理解为侵权行为恶性的延续。
第二,“被告因侵权获得任何利益”包括被告除赔偿原告损失或返还其侵权获利后的获益。其意义在于防止被告因侵权获得任何利益,有违公平原则,属于对侵权消极后果的防止。该获益并非指一般侵权救济中的被告侵权利润。法院强调,原告如果根据澳大利亚《版权法》第115 条第2 款主张被告返还其侵权利润,就不能主张被告的侵权利润构成第115 条第4 款规定的侵权获益,并由此主张附加赔偿;相应地,原告只有在根据第115 条第2 款主张损害赔偿(而非被告返还其侵权利润)后,才可主张第115 条第4 款规定的附加赔偿。易言之,原告如果主张通过被告返还其侵权利润的方式得到补偿,就不能再主张附加赔偿。〔57〕See Facton Ltd v. Rifai Fashions Pty Ltd, [2012] FCAFC 9, paras. 31, 37.此处澄清了澳大利亚知识产权附加赔偿与损害赔偿、侵权利润返还的关系,符合侵权法下的损害赔偿须填平原告损失以及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的一般原则。
第三,“所有其他相关因素”属开放式条款,有助于法院判断相关因素是否支持附加赔偿。它们可以是侵权法下法院裁决惩戒性赔偿需考虑的因素,包括被告的侵权动机、是否试图获得许可、在诉讼中是否配合、是否曾经侵权、是否知晓其行为构成侵权、侵权持续时间以及原告保护权利的难度、是否默许侵权等。〔58〕See 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 Pty Ltd v. Palmer (No. 2), [2021] FCA 434, para. 488.这表明澳大利亚版权法下的附加赔偿与其普通法下的惩戒性赔偿实质一致。
在2021 年涉及音乐作品版权纠纷的“Palmer 案”中,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判决被告支付50 万澳元的损害赔偿以及100 万澳元的附加赔偿,使之成为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历史上惩罚性赔偿较高的案件。法院之所以判决如此高额的附加赔偿,主要是因为被告的霸道、轻视与傲慢等行为:被告在知晓原告拥有相关歌曲版权且需获得许可后,选择公然无视原告的权利;被告在被告知侵权后公开或私下攻击歌曲作者以阻止其行使权利,并威胁起诉词曲作者诽谤;被告在庭审中提供虚假证据;被告在竞选活动中通过使用作品获取了政治利益;被告公然羞辱、嘲讽乃至造谣词曲作者;被告没有履行其证据开示义务,表现出不诚实、顽抗、蔑视等行为;被告作为亿万富翁有炫富等傲慢行为;考虑到足以威慑未来侵权的需求等。〔59〕同上注,第496-505 段。因此,该案判决所针对的并非简单的版权侵权行为,而是包括版权侵权在内的多种恶意行为,最终导致法院判决高额附加赔偿。鉴于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没有必然联系,知识产权附加赔偿也无需与损害赔偿保持比例或倍数关系。在该案中,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认为附加赔偿并不必然与补偿性赔偿成比例。〔60〕同上注,第483 段。然而法院也强调,尽管附加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仍需确保附加赔偿不应超出合理界限,即原告主张的附加赔偿不能与其遭受的损害不成比例。〔61〕See Facton Ltd v. Rifai Fashions Pty Ltd, [2012] FCAFC 9, para. 45.这表明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不能过分地不成比例。
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附加赔偿是其知识产权制定法下的专门赔偿,具有惩戒性赔偿性质,它虽然在表面上借鉴自英国版权法,但也是其普通法下惩戒性赔偿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体现与立法固定。它与澳大利亚的普通法传统关系密切,侵权法下规制惩戒性赔偿的原则亦可适用于附加赔偿,并由此保障知识产权附加赔偿的有效实施。在具体案件中,法院也可能同时判决被告支付附加赔偿和惩戒性赔偿等多种赔偿。例如,在涉及外观侵权的“Paine 案”中,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判决被告支付2 万澳元的名誉赔偿、20 万澳元的惩戒性赔偿(针对仿冒行为)和一万澳元的附加赔偿(针对设计侵权)。〔62〕See Stephen Graw, Additional Damages under Australi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utes, p. 26, at https://researchonline.jcu.edu.au/53228/1/53228_Graw_2016.pdf, last visit on March 12, 2022.
除普通法传统外,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主要根据知识产权法的规定裁决知识产权附加赔偿。原告在诉讼中需明确主张附加赔偿并承担举证责任,从而给被告提供答辩或抗辩机会,如果原告没有主张,法院就不能适用附加赔偿。尽管附加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一定情形下两者仍可互相影响:损害赔偿较高或可导致附加赔偿降低,反之则可能导致附加赔偿提高。〔63〕See 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 Pty Ltd v. Palmer (No. 2), [2021] FCA 434, para. 487.这体现出法院基于普通法传统对双方当事人权益的平衡。
四、美国和加拿大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解析
(一)美国知识产权法下的加重赔偿与惩罚性赔偿
美国联邦法律与多个州的法律皆认可惩罚性赔偿制度,同时对惩罚性赔偿施加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其适用领域、最高赔偿额或比例,或要求将部分惩罚性赔偿支付给公共机构而非全部归原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等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施加必要限制,以保障被告的权益。〔64〕See Volker Behr, Punitive Damages in American and German Law-Tendencies towards Approximation of Apparently Irreconcilable Concepts, 78 Chicago-Kent Law Review 105, 157-158 (2003).其曾提出判断惩罚性赔偿合理性的三要素,分别是被告行为的可责性、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的比例(倍数)、针对可类比的不法行为所施加的民事或刑事处罚。〔65〕See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517 U. S. 559, 575-585 (1996).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普通法系国家相比,美国法院考虑的因素似乎较为简单,但也强调惩罚须首先基于被告行为的可责性。在知识产权领域,美国多个州的侵权法规定了针对侵犯注册商标或未注册商标行为的惩罚性赔偿。〔66〕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613-614 页。
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领域,美国法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现行联邦知识产权立法中。美国《专利法》第284 条针对专利侵权行为规定了最高赔偿额为3 倍的加重赔偿:法院应当判决足以补偿专利侵权损害的赔偿,使之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低于使用专利的合理许可费;法院可将其评估的或陪审团决定的数额增加至3 倍作为侵权赔偿。该规定一般被理解为惩罚性赔偿。〔67〕同上注,第139-141 页。然而本文认为,美国《专利法》规定的加重赔偿(increased damages)实质属于普通法系国家侵权法下的加重赔偿(aggravated damages),而非惩罚性赔偿。可类比的立法例是美国《商标法》第1117 条a 款,它针对商标侵权行为规定了被告利润返还、原告损害赔偿和诉讼成本等救济措施,强调它们均是基于衡平原则,并规定了举证责任。在评估原告的损害赔偿时,法院可根据案情超过原告的实际损失判决赔偿,但不能超过其3 倍。如果法院认为被告利润的返还金额不足或过多,亦可根据案情将赔偿额调整至合理。在这两种情形下确定的数额皆是补偿而非惩罚。该规定表明最高3 倍的赔偿仍是补偿性质,类似于侵权法下的加重赔偿。这反过来亦可表明美国《专利法》下的3 倍赔偿属于加重赔偿而非惩罚性赔偿。〔68〕参见徐聪颖:《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功能认知与效用选择——从我国商标权领域的司法判赔实践说起》,载《湖北社会科学》2018 年第7 期,第150 页。
美国《商标法》第1117 条b 款规定,在上述a 款规定的损害赔偿评估中,如果侵权人在知道商标属假冒的情形下仍故意使用假冒商标,或为其提供必要的商品或服务,除非发现可减轻情形,法院应当根据被告利润或原告损失之较多者的3 倍裁决赔偿,连同合理的律师费和相关利息。这是针对假冒商标侵权的制裁措施,已含有惩罚性因素。其一,针对假冒商标侵权行为,除非发现可减轻情形,法院都应当裁决3 倍的原告损失或被告利润。其二,无论是以被告利润为基数裁决3 倍赔偿,还是以原告损失为基数裁决3 倍赔偿(此时原告损失超过被告利润),对被告而言都是较重的惩罚措施,对类似侵权行为有较强威慑力。〔69〕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613 页。美国《商标法》第1117 条c 款针对假冒商标行为规定了法定赔偿。原告可在初审前选择适用法定赔偿而非根据原告损失或被告利润作出的赔偿,法定赔偿额是指在每种商品(或服务)中使用每件假冒商标须赔偿1000 美元至20 万美元,如果被告是故意使用假冒商标,则法定赔偿额最高可至200 万美元。针对故意商业性使用假冒商标行为的法定赔偿最高额是非故意的10 倍,显然已包含惩罚性因素。
美国《版权法》第504 条分别规定了传统的侵权赔偿和法定赔偿,而仅在法定赔偿部分才含有惩罚性因素。其一,侵权人须赔偿版权人的实际损失以及多出的利润(即被告侵权获利减去对原告的损害赔偿后多出的利润),这涉及填平版权人的损失和被告不当得利返还两项民事救济原则。其二,版权所有人可选择适用法定赔偿。针对每部侵权作品(包括汇编作品或演绎作品),法院可在750 美元至3 万美元之间裁决合理的赔偿。如果是故意侵权,每部侵权作品的法定赔偿上限则升至15 万美元。在故意侵权与非故意侵权之间,法定赔偿最高额可有5 倍差异,也已包含惩罚性因素。
综上,美国知识产权法规定了多种赔偿方式。美国专利法或商标法下加重赔偿的最高赔偿额基本是损害赔偿的3 倍,商标法针对假冒商标侵权行为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最高额可以是损害赔偿或被告侵权利润的3 倍。美国商标法和版权法中的法定赔偿部分还有更高倍数的惩罚性赔偿。与其他普通法系国家相比,美国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了加重赔偿,且对加重赔偿、惩罚性赔偿的上限(与损害赔偿之间的倍数或法定赔偿额)作出明确规定。针对美国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加重赔偿或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之间倍数的做法,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是在强调原告的损失而非聚焦于被告的不法行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裁决需要考虑其对惩罚性赔偿目的的影响,“简单地适用基于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倍数关系的一些公式并不合适”。〔70〕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127.本文认为该评价是合理的。
(二)加拿大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
加拿大虽然是英联邦国家,但其知识产权法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却与英国法有所不同。加拿大1985 年《商标法》(2021 年修订)第53.2 条第1 款规定,针对商标侵权行为的救济包括禁令、损害赔偿、返还利润与惩罚性赔偿等。其1985 年《专利法》(2021 年修订)第55 条第1 款规定专利侵权人应对专利权人等因侵权而遭受的所有损害承担责任。其1985 年《版权法》(2020 年修订)第34 条规定,针对侵犯版权的行为,救济措施包括禁令、损害赔偿、被告利润以及其他权利被侵犯时法律可能赋予的救济等。加拿大《版权法》第35 条第1 款规定,侵权人的法律责任是赔偿版权人因侵权遭受的损失以及法院在认为正当的情形下让侵权人在损害赔偿之上再支付其由此获得的但在计算损害赔偿时没有考虑的收益。这综合考虑了损害赔偿和侵权利润返还两种路径的差异,仍然属补偿性赔偿,也与美国《版权法》第504 条的规定实质一致。加拿大《版权法》第38.1 条第1 款规定,针对商业或非商业目的侵权,版权人可主张侵权人支付500-20000 加元或100-5000 加元的法定赔偿,该条第7 款规定,版权人选择适用法定赔偿并不影响其可能获得惩戒性或惩罚性赔偿。既然加拿大《版权法》明确规定主张法定赔偿的权利人仍可主张惩罚性赔偿,那么可推知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人亦可主张惩罚性赔偿。由于加拿大《专利法》 和《版权法》没有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所以此类赔偿应由侵权法保障。〔71〕See Nintendo of America Inc. v. King et al., 2017 FC 246, para. 170.
在加拿大的专利法司法实践中法院很少判决惩罚性赔偿,以至于多年间都几乎没有仅因专利侵权而被判决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加拿大联邦法院确认,在专利侵权救济中惩罚性赔偿的裁决极为谨慎,因为涉案专利的有效性及其权利范畴通常要等到法院判决后才能最终确定,因此即使被告故意侵犯专利权也很少被认为是恶意侵权,从而不足以支持惩罚性赔偿。在2006 年的“Dimplex North America v. CFN 案”中,加拿大联邦法院法官申明,就其所知,在联邦法院判决的涉及专利侵权的案件中,尚无仅因为被告故意侵犯专利权而被判决惩罚性赔偿的案例,而惩罚性赔偿的判决基本与诉讼中的不当行为或程序滥用相关,其中包括无视法院禁令而继续侵权的行为。〔72〕See Dimplex North America Ltd v. CFM Corp., 2006 FC 586, paras. 122-123.在该案中,加拿大联邦法院认为,虽然原告的专利属有效专利,且被告故意盗用其知识产权,但其侵权行为却并非如此霸道、冷酷或有压迫性以至于冒犯了法院的正当意识,因此没有构成恶意侵权,也没有证据表明其仅将专利侵权赔偿风险视为商业成本,损害赔偿或侵权利润返还已足可威慑此类侵权行为,因此法院决定不支持原告的加重赔偿或惩罚性赔偿诉求。〔73〕同上注,第132 段。在2017 年的“空中客车直升机案”中,加拿大联邦法院认为被告制造了原告的专利产品,须支付原告50 万加元的损害赔偿(相当于许可使用费),且因为其故意和肆无忌惮地抄袭了原告的专利产品,具有可责性,再加上威慑的需求以及被告因侵权而不当获得的利益,遂根据比例原则裁决被告支付100 万加元的惩罚性赔偿,使其成为加拿大专利法历史上的高额惩罚性赔偿案件。〔74〕See Airbus Helicopters S. A. S. v. Bell Helicopter Texteron Canada Limitée, 2017 FC 170, paras. 396-441.
虽然在加拿大版权法和商标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裁决相对较多,但其惩罚性赔偿数额一般较低。例如,在“任天堂游戏作品案”中,任天堂诉被告侵犯其游戏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且继而侵犯其585个视频游戏的版权,并为每部作品主张2 万加元的法定赔偿,总数额是1170 万加元,最终获得法院支持。法院考虑到被告对原告版权的漠视,且在诉讼后仍然继续侵权,为实现惩罚与威慑的目标,遂判决被告支付100 万加元的惩罚性赔偿。〔75〕See Nintendo of America Inc. v. King et al., 2017 FC 246, paras. 170-174.又如,在涉及版权、商标及商誉侵权的一则纠纷案中,魁北克高等法院和魁北克上诉法院均认为,被告知道或故意侵权本身并不能够证成惩罚性赔偿,因为它不能确认侵权行为具有惩罚性赔偿所需的可责性。〔76〕See Constellation Brands US Operations c. Société de vin internationale ltée, 2019 QCCS 3610; Constellation Brands US Operations Inc. c. Société de vin internationale ltée, 2021 QCCA 1664.
概言之,虽然加拿大商标法、专利法、版权法明确或隐含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其适用较为谨慎,尤其在专利法领域更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针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加拿大联邦法院仍秉持侵权法下裁决惩罚性赔偿的规则,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合理性标准和比例原则。〔77〕See Airbus Helicopters S. A. S. v. Bell Helicopter Texteron Canada Limitée, 2017 FC 170, paras. 384-437.仅在恶意侵权行为的可责性等要件得以满足的情形下才能合理裁决惩罚性赔偿,而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本身未必能够论证惩罚性赔偿。这体现了普通法传统对加拿大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制约。
五、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比较法结论与启示
普通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基本体现为侵权法下的救济和知识产权法下的救济两条路径,其惩罚性赔偿形式呈现多样性,包括英国版权法和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下的附加赔偿、美国知识产权法下的加重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加拿大知识产权法下的惩罚性赔偿等。除美国知识产权法有关于加重赔偿或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等之间最高倍数(3 倍)的限定外,英、澳、加等普通法系国家对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的倍数关系均未作任何限定,其裁决多根据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以及侵权法关于惩戒性或惩罚性赔偿的规则加以判定。这意味着普通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主要是依据知识产权制定法,但其实施仍离不开普通法的支持。
普通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的关系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除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包括附加赔偿与加重赔偿等形式)外,恶意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直接落入侵权法的范畴,受到惩戒性赔偿或惩罚性赔偿裁决规则的制约,这在英国(版权法)、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州法(商标保护)皆有体现。其二,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实施直接依赖侵权法下的惩罚性赔偿规则,如加拿大《专利法》与《版权法》仅概括规定权利救济方式,惩罚性赔偿的实施仍由侵权法保障。其三,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须依赖遵循先例、证据开示、陪审团等普通法的司法制度支撑。普通法既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运行基础,也为其适用提供了必要限制,因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须遵循普通法下的惩戒性或惩罚性赔偿判断标准,包括被惩罚的行为应是具有可责性的恶意侵权行为,惩罚性赔偿及其数额的裁决须具备合理性并受到比例原则制约等。在普通法系国家,无论是侵权法下的惩戒性赔偿或惩罚性赔偿,还是知识产权法下的附加赔偿或惩罚性赔偿,均非无源之水,皆有其普通法传统作为制度的源头与基础。这也许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排斥惩罚性赔偿的原因之一。因为法律传统不同,其中包括法律体系(如制定法与判例法)、法律解释(如是否遵循先例)与审判体系(如是否有陪审团制度)等差异,可能导致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体系在灵活性与综合性等方面有不同表现,进而导致法院在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中较难综合权衡或制约惩罚性赔偿的不确定性,从而可能损及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
普通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针对的是恶意侵权或不法行为,其中既包括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本身,也包括诉讼程序中的恶意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害已被视为在损害赔偿路径下得到合理赔偿;如果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则需考虑如何完善损害赔偿机制而非诉诸惩罚性赔偿,因为后者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因此,侵权后果严重与否虽然可能是裁决惩罚性赔偿及其数额需考虑的因素之一,但侵权后果与惩罚性赔偿及其数额的裁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或许仅在证明侵权行为恶意的维度上,考虑侵权行为的后果与惩罚性赔偿及其数额裁决的关系才有意义。否则就可能导致惩罚性赔偿超出合理的范用,侵入损害赔偿的领地,从而既混淆了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界限,也破坏了损害赔偿制度的合理性。鉴于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原因与目的根本不同,不宜将损害赔偿作为基数并以简单的倍数关系确定惩罚性赔偿,否则就属于简单而机械的立法或司法选择,将本身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惩罚性赔偿简单化处理,进而可能导致其法律目标迷失。除美国知识产权法外,上述普通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基本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与损害赔偿的简单倍数关系或惩罚性赔偿的上限,因为这既与普通法下的惩戒性或惩罚性赔偿传统不符,也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性质和目的不符。
随着我国《民法典》的出台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各知识产权专门法和《种子法》新一轮修正案的通过,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已进入实施阶段。就适用范围而言,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和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下的附加赔偿基本相当,覆盖著作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和植物新品种,且可通过《民法典》的规定延伸至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这在世界范围内亦属少见,因为除澳大利亚外,即使在普通法系国家也没有适用范围如此广泛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分别规定了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和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的计算方式包括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侵权获利(《著作权法》规定的是“违法所得”),或参照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侵权人还须赔偿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体现了全部赔偿原则。针对故意或恶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则以补偿性赔偿为基数,以其1-5 倍确定赔偿数额,此即惩罚性赔偿。〔78〕参见《民法典》第1185 条、《商标法》第63 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 条、《专利法》第71 条、《著作权法》第54 条、《种子法》第72 条。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亦须涉及合理性判断标准以及比例原则等,以上普通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或可对此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被惩罚与被威慑的行为应该是故意侵权还是恶意侵权?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须满足“故意(或恶意)侵权”和“情节严重”两个要件。在侵权人的主观过错或恶性程度方面,故意侵权与恶意侵权显然不同。我国《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保护)使用的概念是“恶意”侵权行为,《专利法》《著作权法》《种子法》和《民法典》使用的是“故意”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 4 号)认为“故意”包括“恶意”。〔7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4 号)第1 条第2 款。法释〔2021〕4 号的起草者认为在实践中很难严格区分故意或恶意,故对两者采取一致性解释,并强调不宜“误解”在商标或商业秘密领域惩罚性赔偿适用“恶意”侵权标准,而在其他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故意”侵权标准。〔80〕参见孙航:《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答记者问》,https://en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1078.html,2022 年3 月27 日访问。该解释相当于将各知识产权专门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恶意或故意侵权标准都统一在《民法典》规定的“故意”侵权标准上。因此,在我国《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框架下,“故意侵权”和“情节严重”两要件或可导致法院裁决惩罚性赔偿。然而,基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介于民刑之间的侵权救济性质,其所惩罚与威慑的行为应当是具有可责性的恶意侵权行为,这决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所以在普通法系国家,无论是其侵权法下的惩戒性或惩罚性赔偿,还是知识产权法下的附加赔偿或惩罚性赔偿,基本要求被惩罚的行为是恶意侵权行为(美国《商标法》第1117 条b 款规定的假冒商标侵权也是如此)。加拿大联邦法院强调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未必导致裁决惩罚性赔偿。〔81〕See Dimplex North America Ltd. v. CFM Corp., 2006 FC 586, paras. 122, 123, 132.就此而言,我国《专利法》《著作权法》《种子法》乃至《民法典》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之一规定为“故意侵权”就未必满足惩罚性赔偿的法理基础。法释〔2021〕4 号视“恶意”与“故意”具有一致性,则进一步消除了两者的差别及其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涵义。
关于如何认定知识产权侵权的“故意”,法释〔2021〕4 号规定法院应综合考虑知识产权客体类型、权利状态、相关产品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利害关系人)的关系等多种因素,并且具体列举了法院可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权故意的多种情形,包括被告经原告通知或警告后继续侵权、被告与原告具有法律或管理方面的关联关系、被告与原告具有业务或商业关系且接触过相关知识产权、被告实施了盗版或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等。〔8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4 号)第3 条。本文认为,鉴于知识产权的内在不确定性,除被告实施盗版或假冒注册商标等明显具有恶意的侵权行为外,上述其他各项情形都未必当然指示被告具有侵权的故意,遑论侵权的恶意。〔83〕参见刘银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类型化适用与风险避免——基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77-182 页。
无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属于“故意”还是“恶意”,其“恶性”皆需使相应的侵权行为达到需要惩罚与威慑的程度,才可论证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否则就难以支持其合理性。这意味着无论“恶意”还是“故意”,尤其是“故意”,并非裁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充分条件。
第二,“情节严重”作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要件的真正涵义是什么?
“情节严重”是我国各种法律规范中常用的表达,但如何认定却有不确定性。法释〔2021〕4 号规定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与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以及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认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并具体列举了法院可认定情节严重的多种行为。本文认为,除开放式的“其他情形”外,法释〔2021〕4 号列举的行为基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重复性的侵权行为,包括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被法院判决承担法律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的侵权行为,或者“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第二类是诉讼程序中(包括诉讼前)的不法行为,如伪造、毁坏、隐匿侵权证据或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第三类是侵权后果或潜在后果严重,包括被告侵权获利巨大或原告遭受损失巨大,或者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人身健康。〔8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4 号)第4 条。法释〔2021〕4 号的起草者认为,该要件“主要针对行为人的手段方式及其造成的后果等客观方面,一般不涉及行为人的主观状态”。〔85〕孙航:《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答记者问》,https://en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1078.html,2022 年3 月27 日访问。
本文认为,在上述第一类行为中,被告被行政处罚或被法院判决侵权后,如果再次实施相同的侵权行为,一般可被认为具有侵权的故意乃至恶意。然而,如果被告从事“类似的侵权行为”则未必构成侵权的故意,因为“类似的”行为未必构成侵权,它可能属于自由竞争乃至再创新的范畴。“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表述也具有不确定性并引发了较多争议。第二类行为基本属于诉讼程序中的不法行为,可被视为被告的侵权故意乃至恶意的延续。法释〔2021〕4 号规定的法院责令被告提供其侵权证据而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也属此类(该类行为亦可导致刑事责任)。〔8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4 号)第5 条第3 款。第三类属于对侵权后果或潜在后果的描述,可在补偿性赔偿机制下得到合理救济,并且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与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包括人身健康)未必直接相关(如假冒注册商标但同时涉及伪劣商品生产或销售才可能侵害人身健康),且此类行为应已构成犯罪,可由刑法予以规制。因此,法释〔2021〕4 号列举的“情节严重”情形主要体现为侵权人在被法院判决侵权后再次重复实施相同侵权行为以及在诉讼程序中的不法行为等。在这些情形下,被告具有侵权的故意乃至恶意,此类情形也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所支持。〔87〕See 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 Pty Ltd v. Palmer (No. 2),[2021] FCA 434, paras. 496-505; Dimplex North America Ltd. v.CFM Corp., 2006 FC 586, paras. 122-123.
根据法释〔2021〕4 号所列举的情形以及普通法系国家关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司法经验,本文认为,对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法律规范中“情节严重”的判断并非不涉及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因为其涵义恰在于证明侵权人具有侵权的故意乃至恶意,从而进一步论证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如此理解才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法理与目标。这也意味着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法律规范中的“故意(或恶意)侵权”和“情节严重”两要件的主要意义均在于证明被告的侵权故意乃至恶意,从而论证应否裁决惩罚性赔偿。而且,“故意(或恶意)侵权”和“情节严重”均非裁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充分条件。
第三,将补偿性赔偿作为基数并以相应倍数确定惩罚性赔偿是否合理?
我国知识产权法规定了多种补偿性赔偿计算方法,包括原告的实际损失、被告的侵权得利、权利许可使用费等,但在规定惩罚性赔偿时却对它们未加区分,均视之为惩罚性赔偿计算的“基数”。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法院则应当综合考虑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8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4 号)第5、6 条。可见,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计算中,基数的确定标准相对客观,而倍数的确定则须考虑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包括情节严重程度)。然而如上所述,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与目的不同。前者针对侵权结果,追求的目标是使权利人恢复至没有被侵犯的状态,属于补偿正义的救济;后者针对侵权行为本身,追求的目标是惩罚恶意侵权行为,并威慑类似行为再发生,属于报复正义的救济。因为侵权行为的恶性与其后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在两种赔偿之间亦无必然的相关性。因而既无理由支持以补偿性赔偿作为基数评估惩罚性赔偿,也无理由支持以相应倍数评估惩罚性赔偿。在上述普通法系国家中也仅有美国《专利法》与《商标法》分别规定了最高3 倍的加重赔偿或惩罚性赔偿,且被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批评为偏离了惩罚性赔偿的本质与目的。〔89〕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 127.
关于以各种方式计算的补偿性赔偿是否都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的“基数”亦需斟酌,这涉及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基础。在澳大利亚等普通法系国家,权利人仅在主张损害赔偿的基础上才可主张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附加赔偿),而不能先要求被告返还其侵权获利再主张惩罚性赔偿,否则就可能对被告不公平。〔90〕See Australian Copyright Act, Sections 115(2), 115(4)(b); Facton Ltd v. Rifai Fashions Pty Ltd, [2012] FCAFC 9, paras. 31, 37.仅有的例外是美国《商标法》第1117 条b 款关于假冒商标行为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即法院可根据被告侵权利润或原告损失之较多者的3 倍判决赔偿。我国知识产权法对权利人的损害赔偿和侵权人的侵权获利未加区分,学界也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法释〔2021〕4 号在规定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法时亦未加区分,从而可能导致对被告的过度惩罚。无论是将补偿性赔偿作为基数,还是乘以简单倍数,都属于机械的惩罚性赔偿评估或裁决方式,既忽视了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与目的,也忽略了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从而可能产生妨碍知识产权制度目标的消极后果。
第四,关于惩罚性赔偿合理性和比例原则的适用。
鉴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属于民刑之间的侵权救济措施,且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需要通过比例原则维护其合理性,使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及其数额的裁决仅以能够促进实现惩罚与威慑相关恶意侵权行为之目的为限,否则就可能超越合理的界限,导致对被告的过度惩罚以及对被告或他人的过度威慑,甚至可能损及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91〕参见刘银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类型化适用与风险避免——基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85-186 页。对此需特别预防惩罚性赔偿与侵权人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重合。根据法释〔2021〕4 号,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可以叠加,但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可加以综合考虑。〔9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2021〕4 号)第6 条第2 款。法院在此情形下需格外谨慎,注意比例原则的适用,防止过罚失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惩罚性赔偿一旦超出合理界限就可能构成任意剥夺他人合法财产,因此需要正当程序加以约束。〔93〕See State Farm Mut. Automobile Ins. Co. v. Campbell, 538 U. S. 408, 416-418 (2003).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也强调通过比例原则维护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94〕See 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 2002 SCC 18, paras. 94-95, 112-125.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一件知识产权纠纷案中曾认为,由于原告已获得较高的损害赔偿,就无需再裁决惩罚性赔偿(附加赔偿),体现出对双方权益的平衡。〔95〕See Stephen Graw, Additional Damages under Australi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utes, p. 22, note 85, at https://researchonline.jcu.edu.au/53228/1/53228_Graw_2016.pdf, last visit on March 12, 2022.在我国,法释〔2021〕4 号的起草者强调避免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滥用,提及的措施主要包括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以及通过典型案例予以指导等,但并未明确比例原则等限制规则。〔96〕参见孙航:《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答记者问》,https://en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1078.html,2022 年3 月27 日访问。这提示法院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持极为审慎的态度,藉以维持其合理性,防止消极后果。
六、结语
综合以上对普通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以及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比较分析,包括其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加上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对知识产权制度可能带来的制度风险,本文认为,难以论证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必然具有比较法上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法律体系的差别,那么更无比较法上的理由可以当然支持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移植并期待其良好实施效果。对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而言,在缺乏遵循先例制度(典型案例指导制度显然难以与其相比)基础和相应的诉讼配套机制等情形下,即使在《民法典》与各知识产权法中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能否成功移植基于普通法传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尚有不确定性。没有综合的制度基础支撑,仅有简单的立法文本,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就可能浮于表面,难以实现其既定的立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