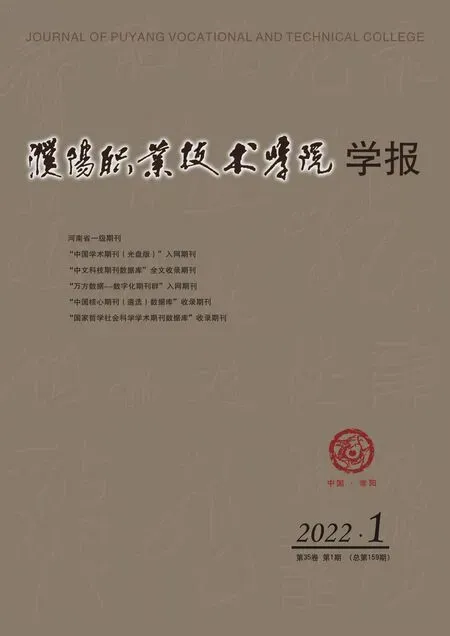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的文学创作观
郑晓婕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情采”是《文心雕龙》的关键词之一,不只存在于《情采》一篇,而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用“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来论述文学作品的创作问题,可见“情采”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因此刘勰专门创作了《情采》篇,通过论述“情”“采”来探讨文学的创作问题,其中所谈的“情采”,既涉及到作家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情感,也谈论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该如何使用文辞的问题。《情采》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抑制齐梁时期靡丽浮诡的泛滥文风,黄侃先生分析《情采》篇时这样写道:“此篇旨归,即在挽尔日之颓风,另循其本,故所讥独在采溢于情。 ”[1]112《情采》篇对有关的创作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包括“情经辞纬”说、“为情造文”说和“联辞结采”说三个方面,其中“情经辞纬”说论述的是“情”与“采”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全篇的基础;“为情造文”说论述的是“情”的创作要求,主要是“蓄愤郁陶”“述志为本”和“约而写真”;“联辞结采”说论述的是“采”的创作要求,主要是“贲象穷白”和“控引情理”。 这三个方面在《情采》篇中始终相互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刘勰独有的文学创作观。
一、“情经辞纬”说——“情采”的辩证关系
(一)“情”与“采”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关于“情”和“采”的内涵有不同的解释,原因在于一方面刘勰在论述“情”的过程中往往将其与“志、理”二字联用或通用。另一方面他也不完全反对对文章进行修饰与雕琢,《夸饰》《丽辞》等篇就专门讨论文采问题,因而造成人们理解上的不同。
“情”是《文心雕龙》中频繁出现的词,刘勰在论述“情”的时候往往将其与“志、理”二字联用或通用,《尚书·尧典》明确提出“诗言志”,这里的“志”侧重于指政治抱负。 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内涵逐渐扩大,主要指思想、情感和意愿,如《离骚》的“屈心而抑志”。 魏晋时期文学自觉越发明显,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此后“情”作为纯文学的范畴一直被重视,人们对“情”的理解也更加精细和全面,具体来说, 情包含两种意思, 一是指个人内心的情感,或称性情、性灵;二是指意志,与志的含义相同,也称意旨和沉思。至此,“言志”与“缘情”成为“情”的一体两面,魏晋时期后者逐渐超越前者,并有忽视前者的趋势,为了打破这种趋势,刘勰创作了《情采》,将言志与缘情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刘勰的“情”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感性层面的情感因素,侧重创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二是理性层面的思想因素,侧重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这两层含义将“情、志、理”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
什么是“采”?就《情采》篇而言,“采”一共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指的是文采,包括对偶、声律和辞藻等这种最普遍的含义。第二种含义是“指圣贤书辞等散行文字的文采”[2]1。 《情采》篇说到:“圣贤书辞,非采而何! ” 刘勰认为圣贤的著作文章也是有文采的。第三种含义是指作品中作家思想感情的色彩,也就是《情采》篇中所说的“情文,五性是也”的意思,第三点是《情采》篇的重点,也是“情”与“采”通用的点。
(二)“情”与“采”的关系
在了解了“情”与“采”的内涵之后,关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文中明确提到的一共有三处:第一,“文附质,质待文”,说明情与采的统一性;第二,“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说明情的根本作用与采的重要作用;第三,“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这句话则是对整个情采关系的总结。
首先,关于“情采”说与“文质”说。 刘勰《文心雕龙》文艺观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孔子的文质观。 孔子虽然提出“辞达而已矣”,但也提出“情欲信,辞欲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的最高理想是“文质彬彬”。刘勰继承了这一思想内容,直接借用孔子“文”“质”概念,并化用子贡“文犹质,质犹文”的观点进行论述,将文质关系表述为“文附质,质待文”,即文依附于质而存在,质借助文而得到更好地体现。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他所说的“情文”,前面说过,“情文”是情与采都提倡的,于是,他“很自然地就将文质关系转换为情采关系,以‘情采’说取代了传统的‘文质’说”[3]4,他将“质”这一笼统概念具体为“情”,不仅是对魏晋以来重“情”倾向的继承,也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在这里,文质关系与情采关系是一致的,因此情采关系也可表述为“采附情,情待采”,即文采必须要依附于情感, 情感的表现也必须通过一定文采的修饰,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揭示了情与采的统一性。
其次,刘勰在“情”“采”具有统一关系的前提下,提出“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情的根本作用,强调华丽的文采根源于作者的至情至性,他认为不是文采驾驭性情,而是性情驾驭文采。 第二,强调“采”的重要作用,他的重采思想在文中随处可见,开篇就用“非采而何”来赞颂圣贤的著作和文章具有文采,并举老子“不弃美”、韩非“艳乎辩说”等为例,说明文章的创作要有文采,还分别用《孝经》和《道德经》作为正反例,表明“采”的重要性。 刘勰认为写文章要用心琢磨苦心经营,努力达到文采丰富,这样最终才能光彩照人,他认为文章只有缛采,才能彪炳,而“繁采寡情”则会导致“味之必厌”。因此,刘勰的重采思想是以情为主导的。
最后,他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他认为思想感情是一篇文章的经线,辞采是文章的纬线,只有端正了经线,才能织成纬线,他用“情经辞纬”说来对情采关系进行了总结,即情采二者兼重,情是有采之情,采是有情之采,但在这个过程中情是根基,采的重视程度是由情来决定的。 文章最后进一步确定了“情经辞纬”说的意义——“此立文之本源也”。
二、“为情造文”说——“情”的创作要求
刘勰针对当时文坛上文胜质衰和繁采寡情的弊端,在本篇强调文学创作者要“为情造文”“述志为本”“约而写真”,他反对“为文造情”和“苟驰夸饰,鬻声钓世”,进一步提出了“情者文之经”的审美论,这是本篇主旨所在。 有论者指出:“‘情者文之经’这一判断,标志着中国诗学从诗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教化论到审美论的变化。”[3]4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情”的具体来源,刘勰说“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他认为诗情根源于人的“本色”,创作要求真情,归根结底是从人本真的性情中而来。但是,刘勰又充分认识到人本真的性情并不等同于作品中的诗情, 人的自然情感必须经过转化才能变为诗情, 这就要求创作者的情感必须要经过“蓄愤郁陶,述志为本”,将个人的情感转换为“约而写真”的诗的情感,然后才能进一步创作出可供人享受的文学作品。
刘勰认为文学创作必须是“为情造文”,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提倡风雅, 要求创作者必须要志思蓄愤、吟咏情性,达到“以讽其上”的目的,与此相反的则是“为文造情”,他反对这些“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的文章,认为圣贤的文章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心有情志、 心怀忧愤, 自然发而为诗,即“为情而造文”;相反,如果创作者没有经过蓄愤郁陶, 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去随意夸张虚构感情的那些伪情之作,结果只能是“淫丽而烦滥”。为情造文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刘勰提出了“蓄愤”和“郁陶”的观点。 “蓄愤”是指创作者要蓄积内心的情感,“蓄”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过程,“郁陶”与“蓄愤”是互文见义的,宋玉《九辨》中写道“岂不郁陶而思君兮”,王逸注曰“郁陶愤念蓄积盈胸臆”。 “郁”与“陶”可以互释,“郁”是郁积之意,“陶”按郑玄的注释就是“郁陶”,可见“郁陶”与“蓄愤”同义,都指的是创作者要在心中蓄积或郁积情感。 总之, 刘勰认为诗情不是一种即兴式的感情,而是要有一个蓄积和沉淀的过程,他认为情感的蓄愤和郁陶是为情造文的基础,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总结了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 是创作者的自然情感转换为诗的情感的重要一步。
经过“蓄愤”和“郁陶”的情感是一种艺术的情感,在刘勰看来,这是一种理性化的情感。 他在《情采》篇中也特别强调“理”的作用,如文中所说的“辞者理之纬”“理定而后辞畅”等,刘勰把情与理看成立文的本源,在论述“情”的过程中往往将其与“志、理”二字联用或通用,他认为在创作过程中,诗人的情感不能自然发泄,而是要经过志的充实和理的升华,从而达到情理并重和情志并重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述志为本”和“设模以位理”,来说明文学创作应该以理性的表达情志为根本。王元化先生说:“《情采》篇提出的‘为情造文’和‘述志为本’,就是企图用‘情’来拓广志的领域,用志来充实‘情’的内容,使‘情’‘志’结合为一个整体。 ”[4]184这个解释符合刘勰所讲的实际,深得刘勰思想的精髓。
总之,刘勰以“为情造文”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点,提出了“情者文之经”的审美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为情者要“约而写真”,这就要求创作者要从内心的真情实感出发,经过“蓄愤郁陶”和“述志为本”,将个人的情感转换为“约而写真”的诗的情感后,再进一步经过采的修饰, 最后创作出可供人享受的文学作品。
三、“联辞结采”说——“采”的创作要求
在经过“蓄愤郁陶、述志为本”的情感转换之后,要使其成为一部完整有意义的文学作品, 还要重视对“采”的运用,刘勰在强调“情真”的前提下,要求文章的“辞”也应该有文采的修饰。因此,“采”就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上,而对于“采”的创作要求,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有文采的文章必须是一种“情文”,对于“情文”的要求,他在文中说到“五性发而为辞章”,认为好的辞章源于创作者喜怒哀乐怨等情感的勃发,认为文采源于人的性情,即文中所说的“辩丽本于情性”,言辞的美丽来自人本来的性情,这就要求创作者要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其次,“采”的程度要适中。他认为不应该过度重视采,并引用老子所说的“美言不信”,来说明过于华丽的语言往往并不可靠,否则“采滥忽真”只会“言隐荣华”,“繁采寡情”只会导致“味之必厌”,这一点与他创作《情采》篇的背景有关, 就是为了批判当时文坛上过于重视文采的不良创作风气。 此外,他并没有完全否定“采”,而是认为适度的采对文学作品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刘勰对儒家思想的超越, 真正做到了情采并重。 最后,“贲象穷白”是运用辞采的最高境界,即文中所说的“《贲》象穷白,贵乎反本”。“贲”是《周易》六十四卦中讲文饰的第二十二卦, 它的最高境界是白贲,意思是讲求文饰的贲卦最终以白色为正,可见采饰以保持本色为贵。因此,“贲象穷白”的要求是作品中的采要保持本色,归于自然,华丽的文辞最终要归于自然,这是修辞的最高境界,好的文学作品会让人看不出其中有任何刻意雕琢的痕迹。总之,刘勰虽然主张文采,说“言以文远”,却又“恶文太章”,主张返本归素,回到真性情上来,这并非是要抛弃文饰,而是要对文辞进行自然的修饰与雕琢, 刘勰将此作为情采圆融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要“自然”,他主张要追求文章的浑然天成之美。
此外, 不能忽视的是, 上面这三点有一个大前提,即“采”是用来控引情理的,所谓“联辞结采,将欲明经”, 意思是作品运用辞采是为了讲明事理与情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设模位理,拟地置心”,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要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树立一个正确的规范, 并且要考虑适当的风格用来表达作家的心情,他认为在创作时要明确运用文思的方法,在充分表达文章思想内容的前提下做到文采华美,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
纵观《情采》全篇,刘勰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他的文学创作观, 既要求作家要有真诚的创作态度与情感,也谈论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该如何以“情”为本,做到“情”“采”并重,从而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首先,他论述了“情”“采”的辩证关系,即“采附情”与“情待采”,在这个过程中,情是根基,他用“情经辞纬”说来总结了“情”与“采”的统一关系。 其次,提出了“为情造文”说,进一步提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要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蓄愤郁陶”和“述志为本”。最后,提出“联辞结采”说,主要论述作家应该如何运用文采。总之,《情采》篇其实讲的是作家应该以“述志为本”为原则来创作出“情”“采”并茂的文学作品,即所谓“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撵藻”,只有心定了才能配合音律,思想端正了才能运用辞藻。这样以情理和情志为主,同时讲究适当的文采,再加以自然的修饰,最后才能创作出文质并重和“情”“采”兼备的优秀作品。至此,刘勰将自己关于“情”与“采”的深刻见解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其中所体现的文学创作观,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今人的写作为文有深刻的启示,值得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