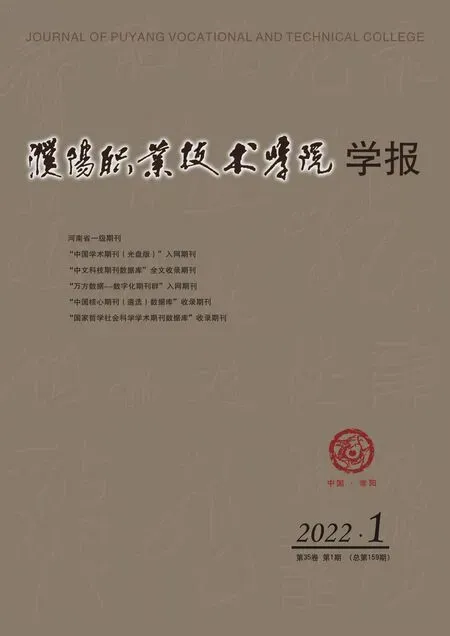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形象
杨锐祎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对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性观角色讨论, 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 由于莎翁举足轻重的地位及特殊的时代节点, 首先引起了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和文学大家的探讨。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平权运动的兴起引发新的浪潮。而国内对此话题研究时间较晚,并未足够重视。
当今时代信息的庞杂,情绪的裹挟,话语权的失衡总使得类似“女性观”“女性主义”这类话题蒙上一层暗纱。 如何寻求解决问题的法则指导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不妨回溯人文主义达到鼎盛的伊丽莎白时代,以莎翁的戏剧作品为依托,分析莎剧中的女性形象,从中窥见莎士比亚的女性观。
一、 目前学术界关于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性形象的主要观点
在对莎学的研究过程中, 戏剧所表现的女性角色一直是个热点话题。 众多的学者试图通过解读作品中暗藏的喜恶、感情倾向、时代的发展脉络来探索一个更立体的莎士比亚形象。 也正是在对其戏剧作品中体现的女性角色的探讨上, 许多人有了不同的解读,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莎翁笔下塑造了一批“完美”女性,诸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她们智慧果敢、善良美丽、不拘于世俗、不逊于男子,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德行美好,体现了超脱时代的意识和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
同样的, 莎士比亚也注意到了生活不幸的弱势女性群体,他悲悯她们的无助,同情她们的苦痛,关注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痼疾——社会环境与政治制度,因而被一些激进的研究者认定为“自由女权主义者”。
另一部分女性主义莎学研究者则秉持着完全不同的意见,在她们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本身就是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等级分明的封建君主制的产物(女王是权力象征,是“非人”的,不应放在性别问题中讨论),所面向的受众也大多是男性,迎合男性的审美。 莎翁惯用人物对照的手法揭示人物不同的命运走向, 使女主人公的不幸映照着男性的人物性格和关键抉择,如同躲在太阳背后的月亮,反射着太阳给予的光芒,本身却不夺目。这不可避免地弥漫着男权主义意识,进而升华到对整个人类生存悲欢的有偏颇的关怀,这种意识和气氛伤害了很多女读者[1]49。
女性主义莎评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固然促使更多研究者关注这个问题,提出更多自己的看法,但也造成了读者理解上的歧义和困惑。 这也就要求我们综合考量时代背景和作家的创作意图,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下回归经典文本、回到历史语境,放置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框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2]33
二、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形象
(一)喜剧中的女性形象
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中涌现出许多丰富生动的女性角色, 几乎涵盖了他所塑造的最精彩的女性形象,也是最具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的。
1.女性社会环境的理想化。 理想社会即指作家独具匠心创造的另一个平行世界, 与现实世界并行且对抗。在这个近似“桃花源”的世外之地,莎士比亚好像放下了诸多的禁锢和尘世的规矩, 尽情的表达对真善美的歌颂。
最典型的如《仲夏夜之梦》的“精灵世界”。 丹麦学者乔治·勃兰兑斯在其1896 年出版的《威廉·莎士比亚:一个批评性研究》中指出:“我们还可以从诗中看出超自然的成分……帕克、豌豆花、蜘蛛网、芥菜籽这几个小精灵, 在玫瑰花蕾里捉虫子, 逗弄蝙蝠, 追逐蜘蛛, 支使夜莺。在这出写小精灵的戏里,它们都是主角儿。 这种使人产生幸福灵感的奇迹,将此后两个多世纪英国、 德国和丹麦等国多得难计其数的浪漫作品的萌芽, 包含其中。 ”[3]20
就这样剧作由开幕时现实的冰冷, 不可违抗的父权意志,无望的逃离躲避缓缓过渡到“梦幻”世界的森林,将现实的问题拉到虚幻的情景:秩序瓦解,封建等级不再森严可怖,命运错落交织,高高在上的被戏耍,显得滑稽可笑,爱情变得简单,没有现实社会的教条礼数,没有地位阶层的阻隔,没有封建家长制的威严,没有对女性婚姻关系的“物化”。爱上一个人如此轻而易举甚至不讲逻辑,整部剧作呈现出“狂欢节”的气氛,像是蒙着一层薄雾热烈起舞,最终的结局随着仙王仙后的家庭矛盾的解决而转到现实社会的婚爱, 一切都有完美的归宿。
莎士比亚对理想社会的构建寄予着一定社会改良的设想。 无论是《仲夏夜之梦》中的“精灵世界”还是《皆大欢喜》中的亚登森林、《第十二夜》中奥莉维亚的府邸, 都是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解决的矛盾选择的逃离,核心是话语权的争夺。这些在伊丽莎白时代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婚姻、未来的女性,在这样经过净化的平行世界实现了自己的幸福, 人类社会呈现出“大美”的图景,这何尝不是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女性的同情呢? 莎士比亚的喜剧蕴含着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他着重刻画了女性的心灵美的特质,赞扬了女性追求婚恋自由的勇敢和反抗精神。 这也正是由文艺复兴时期总的时代精神所决定的, 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现世的幸福,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追求。莎士比亚凭借着对人性美的愿景,凭借着自己高超的艺术水平,描绘出一幅资产阶级新女性的独特画卷。
2.女扮男装的女性形象范式。 莎翁戏剧中女扮男装的桥段经常出现,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范式。如《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维罗纳二绅士》中的朱利娅等女性形象。
在《皆大欢喜》中,被流放的罗瑟琳女扮男装逃亡亚登森林。 戏剧中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僵化的男权世界,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罗瑟琳和西莉娅的到来, 森林里的人会继续阴沉、 腐旧的生活。 罗瑟琳的到来犹如一缕阳光, 驱散了森林里的悲观和不安。 罗瑟琳刚到的第一天就开始积极地安排自己和西莉娅的新生活, 适应陌生的环境, 努力开启新的篇章。她的积极乐观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在她的鼓励下, 森林里的人们学会表达自己的心声与情绪,更勇敢地去追求爱情,更坦诚地坦露心声。结尾,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拥有了光明的前程,坦开了心扉, 收获了幸福。 这一切改变都是围绕着女主人公——罗瑟琳展开的, 罗瑟琳也是全剧的灵魂人物和重要纽带。
尽管女主人公拥有了如此优秀美好的品质, 但作家下意识地无法磨灭掉社会风俗的偏见。 罗瑟琳的女扮男装不止改变了她的外貌, 更关键的是改变了她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 男装是她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件武器, 让她在男权社会同样拥有话语权和改造社会的能力。
当她穿上男人的衣服时, 即使她不认同自己性别上的优势,内心里觉得女儿家生来怯懦,但此时的男装让她暂时忘却了性别上的差异, 开始认可自身的价值。 在罗瑟琳看来, 女人天性就有着无法挣脱的怯弱以及生理上的劣势, 从而要依附于男性的强大, 因而女扮男装的出现是由于莎翁想让女性角色融入男权社会的折中之法, 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
在最后一幕中, 当罗瑟琳脱下男装, 许门 (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 把她和父亲及爱人奥兰多拉在一起时, 她说了这样的话:
(对父亲说)我把我自己交给您, 因为我是您的。
(对奥兰多说)我把我自己交给您, 因为我是您的。
此时, 机敏勇敢、 聪慧充满活力的罗瑟琳变得完全顺从, 她重新披上了自己女性的外衣。 她的自由重新属于了父亲和丈夫,同时社会秩序复归,隐在与世隔绝的森林背后的是冰冷尖刻的框架。 罗瑟琳踏入现世,失去了反抗不公的勇气。
女扮男装最精彩的角色是《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当爱人的朋友陷入债务纠纷时,巴萨尼奥想到用数倍于借款的金钱息事宁人,助长夏洛克的欲望;葛莱西安诺想到的是束手无策,把裁决权交给他人。法庭审判一场,是极具艺术功力的经典之作,也是全剧的高潮。莎翁为了凸现鲍西亚的主体意识,将她置于焦点地位,通过她与夏洛克几次争锋,表现她的机敏善辩、有勇有谋,全面地表现了女性的魅力,并将她推至美的巅峰,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完美女性”形象。从这些精彩的女性形象中,我们体会到女性开始追求自由平等,最典型的是婚恋自由,要求主张自己的权利, 开始渴望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重新让社会认知自己。 莎士比亚开始区别于传统的审美观念——女性的外貌美和性情的贤良温顺。 他选择把女性的智慧和美德看作是女性美的一个基本内涵。越因为这种不同于凡俗的美,越能感受到时代对女性的不公。 鲍西亚的才智能力远远胜过当时的许多寻常男子,然而只有当她穿上男装,以男人的身份出现时,才拥有了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权,才能够被时人所欣赏,成为经典。这场法庭上的争锋何尝不是莎翁的私心偏爱才使得现实中的不可能变为可能,鲍西亚的个人价值在戏剧中才能显现。
(二)悲剧中的女性形象
自1601 年始莎士比亚进入到他的悲剧创作阶段,这是他创作时期极为重要的分支。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和他个人的不幸促使他更深层次地思考人生命运。 莎士比亚的喜剧洋溢着昂扬乐观的气氛和温情脉脉,而悲剧则一遍遍地叩问人性,压抑沉重。 色调由明艳转为端庄,充斥着权利、欲望、背叛、猜忌,是现实父权社会的真实写照。
1. 女性人物性格及其悲剧命运。 悲剧中的女性人物塑造相对于喜剧而言未免显得刻板流俗。 她们的命运与男性角色的命运息息相关, 并不是戏剧想表达的灵魂人物。她们无法自救更无法渡人,最终滑入深渊,走向悲剧。 如《哈姆雷特》里的奥菲利亚,她的出场似乎只是为了剧情的展开,矛盾的激化。奥菲利亚的身份——既是哈姆雷特的爱人, 又是哈姆雷特仇敌之女, 复杂纠结的矛盾情感一遍遍地捶打着主人公的内心,迫使他做出选择。我们很少去探究她的人物性格和品质, 莎士比亚把悲剧的关注点放置在了讨论社会秩序的打碎重组、人性的跌宕、欲望的主宰等方面。在男权主导的权力角逐中,奥菲利亚没有话语权,她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的形象空洞平面化,顺从怯懦疯癫似乎是她唯一的标签。脱离了虚幻的构想,《哈姆雷特》 中奥菲利亚的处境无疑是普适的,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真实面貌。
在《奥赛罗》中出场的婚后的苔丝狄蒙娜无疑也是这样的形象,鲁莽天真,顺从孱弱。 这个女性角色一次次被裹挟在阴谋、争斗中,像浮萍一样被命运的风浪吹打得飘零无助。 悲剧中最出彩的往往是男性角色,女性是男性的衬托。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如奥菲利亚、 苔丝狄蒙娜一样沦为一个符号化的象征,激化权利的斗争,本身没有太高的艺术价值;另一类是如《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哈姆雷特》中的葛楚德,《李尔王》中的高纳里尔、里根一样对权利热衷,罔顾道德、充满欲望的人。
2. 厌女主义的氛围。 《哈姆雷特》与《李尔王》中都弥漫着浓郁的厌女主义情绪。 修·亨利在《老维克绪言——莎士比亚和演出者》一书中指出:“乔特鲁德和奥菲利娅的悲剧是,尽管按各自的方式,两人都是热心和多情的, 她们都不能给所爱的人带来安慰和帮助, 在那围绕她们激烈发生着的斗争中被抛掷一旁,几乎无人为之掉泪。 ”[4]67在哈姆雷特的眼中,他的母亲是淫荡背弃的化身, 在丈夫尸骨未寒之际就与新王通奸,踏进了乱伦的床帏。他的爱人脑袋空空,软弱天真,一味听从父兄教导,甘愿成为政敌刺探自己的工具。二人的形象都是负面的,都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赎罪。哈姆莱特仇视她们,用恶毒的语言和轻慢的态度疏远她们, 直至父亲的鬼魂的请求才唤起他对母亲的怜悯, 直至他亲眼目睹奥菲利亚的葬礼才吐露曾经的甜言蜜语。 这样的反常与矛盾的心理归根结底是由于权利的失衡, 他想通过这种贬低女性角色的方式证明女性地位低于男性, 以及他才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 负有社会秩序复位的职责,无论是在两性关系还是在权力交接中。
《李尔王》中李尔王和三个女儿的关系就是父权社会的缩影,父亲在家庭中拥有无上权威,因为考狄利亚不肯奉承逢迎, 他竟将多年服侍的爱女和忠臣一并驱逐,只在乎自己作为父亲和君主的权威。考狄利亚三姐妹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她们的身份、境遇、性格特征, 而是她们作为李尔的女儿对父亲的孝顺以及尊敬程度。 李尔也是依据此, 完成自己的王权分割, 将肥沃丰饶的土地分给对他表衷心的高纳里尔与里根。 考狄利亚尽管品行贞洁、德行完善,但只因为李尔的这一衡量标准很快遭到了他的厌弃。 这正是父权制话语的一个典型体现, 女性是不具备独立个体特征的,她的身份是通过与男人的关系界定的,居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我们在对《李尔王》后来的结局惋惜时,不应忘记审视李尔身为父权制社会代表的特征。
三、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性观的二重性:作为时代公民的局限性与作为大艺术家的超越性
(一)时代的女性观及成因
伊丽莎白时代是英国崛起的重要历史时期,航海的新发现,商业的繁盛以及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思潮辐射到英国, 使得社会风貌呈现出杂糅交汇的趋势:对物欲的追求和对自由平等的构想,旧的封建糟粕和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崛起。
宗教成为每位社会公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这是无可回避的。 要获得救赎,必须经过种种苦难的洗礼,才能达到完美的人格。 救赎, 不只是渴求一个来世的天国, 而是怀着诚挚的大爱与信仰在世界中受尽诸般痛苦。 我们在爱与信仰的感召下,才能够洗清罪恶,净化心灵,回归公义、平等、安乐祥和的“大同世界”,这个“公义的冠冕”存留的世界,在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中体现出的是理想的世外桃源。 是《皆大欢喜》中的亚登森林,《第十二夜》中奥莉维亚的府邸,《仲夏夜之梦》中的森林、小精灵、仙王仙后、神奇的“花汁”等。
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明显地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评判安东尼奥等人和夏洛克的行为。 借公爵之口说:“让你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 你虽然没有向我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 ”认为公爵等人体现仁爱宽恕,与锱铢必较、报复心强的犹太人夏洛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莎翁认为夏洛克悖逆上帝,是基督徒的对立面,得不到宽恕和心灵的平静。
基督教本身是与男权社会相适应的,《圣经》收录了许多女性被压迫,被视为不洁的事件,女性人物存在的意义都是服务于上帝,表现神的慈爱公正。从夏娃是上帝由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而来这一故事就可以体现女性对男性的依从和附属。 《圣经》中对女性肉体的忌讳、 对女性权利自由的限定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对于男权社会的维护[5]45。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儿形象即使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仍然像被豢养在手心的雀儿飞不出父权社会的框架,她们通常忠于父亲、为父亲效劳,以自己的婚恋关系为纽带, 将父亲与父权制的继承者——她们的丈夫连接, 这种连接实际上是女性权利与自由的让渡。如约耳·芬曼所言,“即使女性在戏剧中颠覆了男权, 她也不得不交出权力向男性投降”[6]124。 如《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她的陨落正是由于她在自己的父亲与爱人之间的争斗中无法自处, 她企图通过自己充沛的感情、 柔弱的劝解以及特殊的地位消解这一矛盾,最终落空,走向了死亡。 甚至在喜剧中更具“力量”,拥有众多美好品质的女儿,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她机敏善辩、勇敢有魄力,比许多男性都出色。 在父亲逝世之后她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却仍旧不是自由的。她必须经历三匣选婿的仪式, 完成将自己自主权从死去的父亲交给未来的丈夫的转变。
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力而著称,他通过塑造身份地位不同的纷繁复杂的人物,觉察到了社会存在的痼疾, 但他无力挣脱开时代的土壤。 这些不圆满是由于时代的烙印产生的自然风貌,独属于伊丽莎白时代,独属于被时光凝结的剧作本身。
(二)超越性的女性观及成因
正如查尔顿所言,莎士比亚“一方面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无可匹敌的艺术家,有着艺术家的独有天赋;他的艺术家本能可以在他的普通的‘自我’没有意识到的前提下就开启运作。 这种天赋和本能是自成一派的,是不受他的普通‘自我’所约束和控制的”。 莎士比亚通过对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诠释了他心目中的“新女性”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在他的笔下,创造出了机敏聪慧、善良勇敢、美丽独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尤其是在他的喜剧创作中,他赞扬了女性对于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 称颂了女性的美好品质和高尚德行,发现了女性的社会价值。莎士比亚被人文主义思想所打动,他热情赞扬爱与信仰,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理念,怀抱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关注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们的诉求。
由此可见, 莎翁的女性观是由作为普通伊丽莎白人的莎士比亚和作为伟大艺术家的莎士比亚共同组成的。因而具有双重性,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其女性观的复杂和矛盾。 但作为伟大艺术家的莎士比亚通过自己的艺术家本能透过时代的脉络,展现了人类社会对自由平等,对爱与美丽的无限渴望,具有超前的意识和对一切不幸的悲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艺术天赋不断冲破当时意识形态的束缚,使他的艺术作品得以自成一派。
莎翁深受人文主义思想浪潮的影响, 在他的戏剧中出现了一批生动明媚的女性人物形象, 现在读来仍能让女性读者接受欣赏,历久仍熠熠闪光。我们也将此视为一种积极的讯息。这两种互相矛盾、对立的女性观统一于莎翁丰富复杂的思想本身。 不必求全责备也不必一味称颂。对女性观的认知,女权主义的发展即便在当下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莎士比亚所能展望的已经是旁人不能及的, 尽管他无法冲破时代禁锢,无法达到人们心中的尽善尽美,留下一些纰漏和可供指摘之处。 然而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性观的探讨,我们可以体悟到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对爱与美真挚的向往;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聆听历史的脉搏,借着巨人的肩膀回溯古今,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