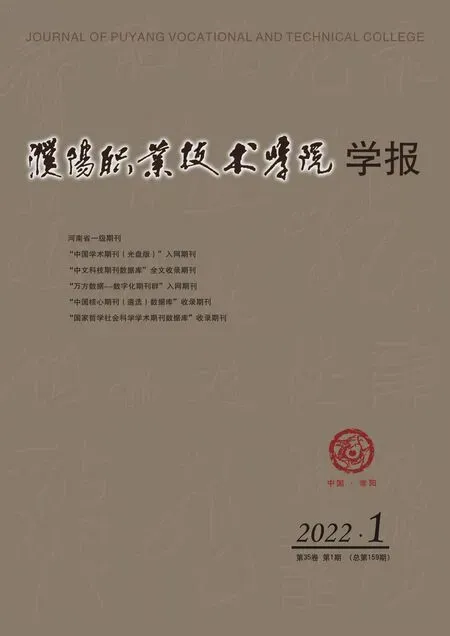从“人的主题”看魏晋名士与酒
——兼论酒与魏晋文艺之关系
马晓彤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自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魏晋名士喝酒的现象中揭示了“魏晋风度”的成因以来,关于“魏晋风度”与“酒”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 王瑶先生在《文人与酒》一文中提出了饮酒能够“增加生命的密度”[1]158这一观点。尽管王瑶先生同样认为,饮酒之于魏晋名士,有着超越现实追求层面的价值, 但饮酒之于魏晋名士最重要的理由,仍是在社会情势逼迫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后世对于酒与魏晋名士的探讨, 大多也是沿着酒是作为他们全身避祸、排遣孤寂、及时行乐的手段而存在的这条路径来展开的。 通过饮酒来提升心境以消解是非确实是魏晋名士的普遍状态。但也有学者指出,名士饮酒的最高价值在于“饮酒后焕发出形神相亲的生命元真力量,将心境提升到与道相契,由玄理神游万物, 超越一切世俗利害而以纯真纯美的心灵享受人与自然交融下的无尽美感”[2]180。
除了探讨魏晋名士饮酒之诸多意涵, 还有一些研究将魏晋风度的精神与境界与西方的“酒神精神”进行了比较,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魏晋风度与酒神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曾春海撰《竹林七贤与酒》一文,《中州学刊》2007 年第 1 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二者在精神境界上有着共同的追求, 但魏晋风度在气质上与酒神精神缺少积极有为的力量之美(臧要科、樊明光撰《魏晋风度与酒神精神》一文,《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3 年第4 期)。
关于“魏晋风度”的内涵,冯友兰、李泽厚、叶朗等前辈学者均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马良怀指出:“所谓魏晋风度, 是魏晋时代的士大夫在权威思想的崩溃与重建过程中的精神上的迷惘与困惑的外在表现。 ”[3]24笔者认为,探讨魏晋风度的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要认识到魏晋风度的出发点和核心问题是“人的主题”,而“服药”“饮酒”之行为,“放达”“任诞”之表现,是统摄在这一主题之下的具体之为。 因此,从“人的主题”切入,方能认识到饮酒之于魏晋风度的最高价值,在于魏晋名士借酒这一媒介,追步了玄学所倡的庄子“至人”的人格理想,并在酒的催化下,于文学实践中将现实人生艺术化。更高一点说,酒之于魏晋, 在于它在中国历史上士人精神家园的重建时期, 如何一步步为士阶层提供心灵与精神上的给养与安顿。 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魏晋名士的人格理想之追求和酒对于文艺创作的催化作用两方面对酒之于魏晋风度乃至整个魏晋文学艺术发展的意义展开探讨。
一、“酒正使人人自远”——醉境中的人格理想
李译厚、 刘纲纪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历来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认识美的本质的。 ”[4]93魏晋玄学的主题之一是对理想人格的建构, 何晏最开始提出以“神明”作为理想人格,王弼进一步将“神明茂”推至最高层次的圣人典范, 其二人认为 “神” 是超越了“形”而达到的“无限自由的境界”[4]132。 而在嵇康的养生观点中,则强调养“神”以亲“形”,从而使“形”“神”相亲。 概而言之,魏晋名士重视形神相和,认为“神”较之于“形”更为根本,这种以“神”作为核心的人格理想,恬淡无欲,纯任自然。
这一理想显然是受到了庄子形神观念的影响。在庄子看来,人生而饱受现实束缚,无法获得心灵自由。 他提出“重神轻形”的观点,弱化了人的形体,突出了人的精神,《庄子·达生》云: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 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 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物而不慴。 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 而况得全于天乎?[5]503
在庄子看来,醉者方可进入神全之境,在这种境界中,醉者物我两忘,不被生死所困,免受惊惧所扰。庄子的“醉者神全”强调了饮酒所至之醉境对主客观之界的超越,复归自然从而达到绝对自由,而庄子所树立的“至人”“神人”形象,就是掌握了各种摆脱世俗限制途径从而能够超越人生之困, 进入自由无待之境的理想人格。 竹林名士刘伶在《酒德颂》[6]69中描述了一个“幕天席地,纵意所如”的“大人先生”,其人“唯酒是务,焉知其余”,面对礼法之士的说教,先生“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 奋髯踑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不闻”“不睹”“不觉”,酒后的“大人先生”超越了现实纷扰,进入与万物浑然为一的澄明之境,这一形象无疑与庄子的“至人”“神人”理想相通,而醉境也与庄子描绘的神全之境相通。
《名士传》称刘伶“土木形骸,遨游一世”[6]219,《世说新语》同样记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6]530。 “土木形骸”意指身体如土木般质朴自然,而这种自然,恰是饮酒抵至神全之境所表现出的对“形”的超越,“形”归自然,方能实现更高境界上的形神合一。酒的价值,就在于让形骸随神而动,由此,生命即可随遇而安,无所束缚,从而化于大道。 身材矮小、貌甚丑陋的刘伶因醉酒迷离而入《世说新语》“容止” 门, 表明酒所激发的是一个个性张扬、自然率真的自我,这意味着超脱外在形相限制而见内蕴的“神”,方为一个人的本质,这也正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着意追求的理想人格与境界,而借由酒,逍遥境界终成一种“即刻可就的眼前之物”[7]34。
在庄子人格理想的启发下, 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士人以追求超脱境界为时尚,表现为行为上的“任诞”。而《世说新语·任诞》中对时人放旷行为的记载,多数与饮酒行为相关, 竹林名士将对庄子人格理想与精神境界的追求诉诸于饮酒这一人生体验, 这种脱略形骸、放达任诞的行为背后,流露出他们对于时代与人生痛彻的感受与不懈的思索, 尽管这一寻求精神安顿之域的努力并未真正让竹林名士获得身心的自由,但是其努力本身即具有极深沉的意义与价值,他们面对信仰的失落、时局的黑暗,不惜以前所未有的叛逆行为与此抗争,确乎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8]281。
如果说西晋竹林名士用酒追求“道”的姿态是“任诞”,饮酒是在徘徊中的探索,那么陶渊明则在酒中进入了一片“任真”之域,他不再用如竹林名士般激烈的、抵抗的方式来表达对自我价值的彰显,以及对自由的精神家园的追寻,而是将“真情”“真意”“真心”视为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陶潜诗云:“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 天岂去此哉? 任真无所先。 ”[9]125陶潜在此道出了一颗超脱一切外在现实束缚的极质朴、极真诚的本然之心。 自述“性嗜酒”“造饮辄尽”[9]502的陶渊明, 自然地将饮酒确立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他在酒中可得酒中之趣,可任一切“真实”自然流露,他的饮酒诗中呈现出一片冲淡平和、圆融自洽的和谐,肉体与精神在陶潜的生命哲学中,从容地契合于一。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6]659有学者认为,“合形神于一身的基础就是‘真’,形的‘饮酒求真’,与神的‘纵浪大化’一样,在他身上都是融进自然,也都是同归于真的”[10]2。 酒后的世界是与万物合一的世界,是听任自然,无论优先的世界,因此也是“形神相亲”的世界。 陶氏之酒融进了他的日常生活、人生追求,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返璞归真的世界。 陶渊明的“诗酒风流”将魏晋风度发展到了真正形神相亲的境界。
有论者指出:“魏晋时期, 酒参与着精神世界的建构,酒本身的价值被肯定,酒作为独立的精神势力被主题化,被自觉编织进中国精神的血脉中。”[11]34然而,当酒成为了空虚浑浊的享乐,当士人失去了名士的不甘于妥协, 失去了对精神安顿之所的探索与实践, 由痛苦的底色和积极的建构所形成的 “魏晋风度”也就随之而去。《世说新语》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孰读《离骚》,便可称名士。’”[6]660王恭此言实是对仿效风流的虚假名士的讽刺。出于对生之热恋,魏晋名士方能以极高的代价对生命与人格进行自觉的维护与探索, 而这种自觉的探索一并指向了文学艺术领域。
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醉态中的文艺创作
古人有言:“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 ”[12]907觉醒的魏晋名士开始在文学中吟咏性情,抒发着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与慨叹, 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对于生之迷恋点燃了名士的创作激情,他们将文学创作视为个体生命的另一种表达, 文学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对人自身的发现。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文”之所指不只是文学,还包含了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因此,魏晋时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更是“艺术自觉”的时代。在不断地确认自身价值、追寻精神超越的努力中,酒作为一种个性独立的标志,早已渗透在名士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们或宴饮, 或独酌,在酒的催化下,魏晋名士的“情”终于在“文”中找到了安顿之域。
文艺创作借想象而能使艺术家的个性得以张扬。《文心雕龙·神思》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13]493作为一种思维活动,想象不受时空的限制,能够遨游于古今万物、宇宙天地之间,在思绪纷飞之际,万物之“象”纷至沓来,艺术家借助“象” 将 “心理活动着和酝酿着的东西”[14]359加以表现,内在之神与外在物相“游”,从而创作出“焕然乃珍”[13]495的艺术佳作。 魏晋名士在一片酣醉中将日常的规范与逻辑打破,在“神与物游”中将一切进行重新组合,将各种在清醒状态中无法预料的、无法言说的内容在松弛自在的状态中吐露出来, 他们的个性因为酒之神助而得以张扬,终在艺术中获得了永恒。据《晋书·阮籍传》记载,“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 辞甚清壮,为时所重”[15]1360-1361。 这篇《为郑冲劝晋王笺》“辞甚清壮”,被时人誉为“神笔”,其文从上古贤哲起笔,论及司马氏成就,进而对未来功业展开想象,其文峻逸潇洒,醉境中的阮籍解放了创造力,展现了超越时空的文思。
不仅如此,伴随艺术想象而来的还有艺术灵感。随着艺术想象的展开,艺术家往往在神游外物之时,倏忽文思泉涌, 进入创作的顺利之境,“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 藏若景灭,行犹响起”[16]11。 这种“来不可遏”的状态即是灵感迸发的瞬间,灵感的产生为创作活动确立了焦点,使想象达至巅峰状态,从而显示出高度的创作力,正所谓“神动天随,寝食咸废,精凝思极,耳目都融,奇语玄言,恍惚呈露”[17]126。在灵感到来之时,艺术家对各种艺术符号的运用得以全然发挥。 然而其“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对于何以获得灵感的闪现,《文心雕龙·神思》说:“是以陶钧文思, 贵在虚静, 疏瀹五脏, 澡雪精神。 ”[18]320排除内心杂念,使精神得以净化,全然地投入创作方是唤醒灵感之途。有学者认为,饮酒是达到虚静状态的最佳方法,“即在酒精的作用下, 把自己从现实喧闹中隔离出来, 进入一个相对虚静的环境中”[19]61。 清代廖燕如是说:“酒似无与于文章,然当其搦管欲书时, 不得一物以助其气, 则笔墨亦滞而难通。”[20]67在此即指出了酒对于创作灵感的疏通。被冠以“遒媚劲健,绝代所无”的《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在“流觞曲水”的兰亭雅集中,借助酒兴,一气呵成,其笔法之丰富,字体之多变,显示出灵感到来时创作力之丰沛与无可复制性,据记载,王羲之在酒醒之后又反复多次书之, 然其艺术表现皆无法与酣醉之时的作品相比,由此可见,灵感创造了变化多端的艺术形象,而酒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激发作用。在魏晋时期,书法艺术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原先严肃齐整、气势雄健的汉代隶书一变而为“真、行、草、楷”[21]168,作为最能够表达个体情感的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所反映的依然是超逸绝伦、 风流潇洒的魏晋风度, 书法美学上的转变与魏晋名士对自由的追求是一致的, 而这种追求自然与醉境密不可分。 换言之,魏晋名士追求酒酣之后的逍遥境界,而处在逍遥境界中的个体又通过书法这一形式展示了他们个性的真诚与热烈,酒的作用,在于其显著的物质特性在创作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
不仅是书法,究其根本,一切文艺展现的都是人类内在的、独有的心灵,而文艺的价值正在于此。 诚如前文所述, 魏晋时期文艺的自觉实是名士觉醒的另一面,因此,庄子对“真”的强调和追求同样体现于魏晋名士在文艺活动中的表现。所谓“酒正自引人箸胜地”[6]657,此一“胜地”中,生命最为本真的一面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创作者与世界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他们与宇宙万物建立了深刻的联结,抵达了与清醒的逻辑思维体系并不互相通达的另一境界,“酒的酣逸乃所以帮助摆脱(忘)尘俗的能力以补平日功夫之所不足”[22]158, 酒之于创作者的意义亦应由此观之。 曹丕自述其酒酣赋诗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23]110,陶渊明亦云:“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9]235诗人们体会到了“酒中趣”,并于其中孕育出诗篇佳句。作为个体生命的延伸, 醉境中的文艺创作对现世人生的遗憾、对自然山水的热忱、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无不以真诚的姿态托出。 生命之“真”于陶诗之中得以尽情流露,渊明其诗,有“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9]144-145的朴素日常,有“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9]256的坚定抉择,更有“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9]125的哲学思索,对于陶渊明来说,饮酒就是生活,也是生命本然状态的展现,诉诸笔端,更是忠实地再现了那些生命最真诚而可贵的情感。 诗、酒自此结缘。
酒与文艺创作的结缘, 使得饮酒成为了一项文化活动,这对唐代文艺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之功,展示了不可企及的“醉态盛唐”的创造力,而诗酒相融之风虽盛极于唐,然其发端乃在魏晋。浸润在醉乡里的文艺创作, 展露出傲岸不羁的风采和自由浪漫的灵魂, 许多创作者都在醉境中找到了释放生命激情的力量。张旭作书“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 既醒,自视以为神”[24]5764;画圣吴道子“每欲挥毫,必须酣饮”[25]176;李白感叹“但得酒中趣,毋为醒者传”[26]198。 后世的诗、书、画与酒紧密地相融在一起,酒终为中国文化艺术史辟出了炽热真挚之一途。
三、结语
摆脱生之困境, 追求生命自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诗化生存理想, 也是庄子哲学与魏晋玄学共同的价值指向。牟宗三先生指出:“魏晋名士人格,外在地说,当然是由时代而逼出;内在地说,亦是生命之独特, 人之内在生命之独特的机括在某一时代之特殊情景中迸发出此一特殊之姿态。 故名士人格确有其生命之本质的意义,非可尽由外缘所能解析。”[27]60当一腔热血遭遇了外在现实的冷却, 士人转向精神世界展开探寻与挖掘,对自由与超越的追寻本身,就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名士处境之绝望和他们的“不能忘情”所构成的张力之美,正是“魏晋风度”的迷人之处,它不同于西方酒神精神的放纵与癫狂,而是具有中国古代独特的浪漫气质。我们从魏晋名士身上,看到了在混乱、黑暗、恐怖的魏晋时期,“如何追求光明,追寻美,以救济和建立他们的精神生活,化苦闷而为创造, 培养壮阔的精神人格”[8]286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生命题。无酒不成“魏晋风度”,这酒里寄托着竹林名士对庄子人格理想的追慕与想象, 浸润着陶潜平和冲淡的诗化生存。魏晋名士将人生融于酒,在最黑暗、最苦闷的时代,用酒追寻生之理想,用酒浇出中国文艺之花,其价值理应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