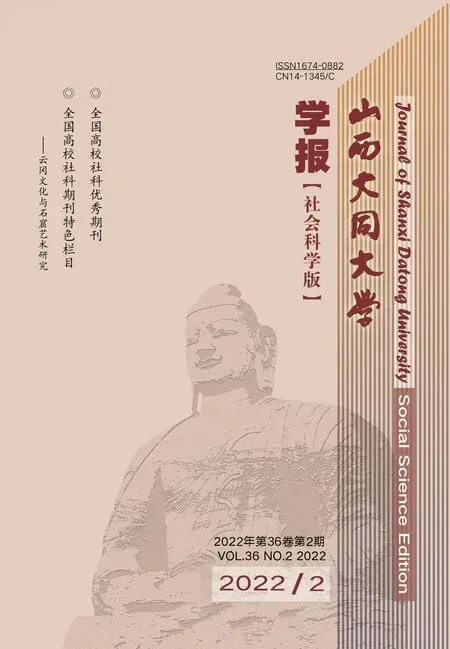南北交流下的北魏洛阳诗坛
孙惠楠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
北魏在发展前期,各方面的建设都比较凋敝,文学建树相较南朝而言,更是沉寂得多,但是经过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国力便迅速发展起来,文学的发展环境也变得更加开放。在北魏的首都洛阳诗坛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与作品。当南朝诗人大批涌入北朝且参与到北朝诗歌的建设中来,北朝诗人意识到了南朝诗歌的优越性,便开始大力学习南朝诗歌技巧,北魏的洛阳诗坛逐渐繁荣起来。
一、南北诗风融合的共同文化源流
南北朝时期虽然在地域上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在文化上却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南北之间从始至终都有着密切的交流并且相互融合,这种交融之所以能够实现,是有着相同的文化基础的,北朝地区虽然经历了五胡乱华、十六国战乱的惨况,但是一直都是以汉文化为主的,虽然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汉文化有过短暂的部分被同化的经历,但是这种被同化仅仅是作为对汉文化的影响而对汉文化灌注的新鲜血液,相较于少数民族文化,汉文化代表着先进与文明,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北朝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而少数民族的汉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南朝虽朝代更迭,但是一直延续着魏晋以来的文化传统,并以文化正统而自居,所以说,南北融合的基础是共同的汉文化。沈约曾经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阐述先秦两汉到西晋、东晋之后南方文学发展的大概状况: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馀烈,事极江右。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若夫敷衽论心,商搉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1](卷六十七,P1778—1779)
沈约认为,中国文学总的渊源从先秦开始就是“同祖风骚”,虽然在南朝宋齐之际诗风开始朝着重音律、重辞藻的方向发展,但是风骚的传统是没有改变的,只不过在风骚的渊源上实现了一些改变与超越,这就为日后南北诗风的融合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南方诗风的发展虽然背离汉魏风骚渐行渐远,但是南方文人始终没有忘记文学上的这一传统,而此时的北方文学同样在汉魏传统中找寻着点滴的线索。如魏收在史书中历数汉魏以来文学的发展踪迹:
夫文之为用,其来日久。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淳于出齐,有雕龙之目;灵均逐楚,著嘉祸之章。汉之西京,马扬为首称;东都之下,班张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络俊乂。逮高祖驭天,瑞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绝,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2](卷八十五,P1869)
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朝文学开始复苏并走上正轨,而此时,南朝正位于齐梁之际,诗歌开始转型,四声八病等声律学作诗技巧开始产生,《南史》称“齐永明中,王融、沈约、谢眺,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3](卷五十,P1247)至此,南北诗风开始分别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再加上南北双方的政治统治开始逐渐地达成和解,出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于是,不论是从政治上的需要,还是从文化上的发展,南北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都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总之,南北诗风的融合,其文化根基十分深厚,与北朝自身的汉化以及对南朝先进文化的崇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南北诗风交融的过程中,北人大力学习南朝先进的作诗技巧与审美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北朝诗歌的发展。可以说,南北诗风的融合对北朝诗歌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北朝诗歌在南北交融这一途径中实现了自身诗学艺术的完善并为最终超越南朝诗歌做了基础。
二、入北南人对北诗发展的导向作用
北魏统治者对汉族士人采取打压的态度,对文学创作不予过问,等到迁都洛阳后,洛阳诗坛的文人诗以五言为主,基本恢复了创作生机。缘于拓跋氏上层对待文学的态度开始转变,统治者开始重视诗歌创作,并且身体力行,因为诗歌艺术积累和诗人素养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两个时代的文人诗创作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一)王肃、萧综推动南北交流 北魏迁都洛阳后,经过太和十多年的强力推行汉化,拓跋氏上层的文学素养普遍提高,大批的汉族士人也受到重用,于是,一批纯文学诗人开始崭露头角。北魏洛阳诗坛最具有实力的诗人群体,是来自文学水平远超过北魏的南朝的一批诗人。主要以王肃、萧综为代表,既有厚重的诗学理论积淀,又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他们的北来,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洛阳诗坛在艺术技巧上的进步,直接影响并提携了一批本土诗人的创作。
王肃初仕南齐,本是豪门大族,因其父王奂擅权杀人而遭族灭,王肃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化成僧人奔魏,以其才学文章备受孝文帝重用,视为股肱之臣。《北史》中记载:
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帝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素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素出。[4](卷四十二,P1540)
可见,王肃在北魏颇受重视。王肃入魏后将一种叫《华山畿》的南朝民歌体式传入洛阳: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5](卷四十六,P669)
关于该诗,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古今乐录》曰:“《华山畿》者,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女子,悦之无因,遂感心疾而死。及葬,车载从华山度,比至女门,牛不肯前。女出而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入棺,乃合葬焉,号‘神女冢’。自此有《华山畿》之曲。”[5](卷四十六,P669)这种体式的三五言诗,在当时很受北人的喜爱,文坛仿作之风十分流行,如元勰的《应制赋铜鞮山松》、祖茔的《悲彭城》等,都是仿制该体的佳作,名噪一时。王肃入魏后又作《悲平城》,且融入了北地风味:
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6](北魏诗卷一,P2205)
诗歌内容简洁短小,民歌风味十足,且带有慷慨豪放之风气,南朝诗人们一入北便很快适应环境,作诗从内容到风格都北地化,与南朝传统迥异。
王肃之外,对北魏文坛影响更大、且留下作品最多的,当是稍后入魏的梁王室成员萧综。同样以成熟的南方诗体和艺术手法承载了寄寓北国、远离故土的情思,并植入了北国的独特意象,取得了南北本土诗皆无法企及的艺术效果。如其《听钟鸣》:
历历听钟鸣。当知在帝城。西树隐落月。东窗见晓星。雾露朏朏未分明。乌啼哑哑已流声。惊客思。动客情。客思郁纵横。翩翩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半夜啼。今岁行已暮。雨雪向凄凄。飞蓬旦夕起。杨柳尚翻低。气郁结。涕滂沱。愁思无所托。强作听钟歌。[6](北魏诗卷一,P2213)
萧综客居北方,深夜难寝,辗转思乡,忽闻钟声,更深感自己身在异乡,南国故土已遥不可及,作者痛恨萧梁,一意奔北,而一旦身居异国,静夜的钟声还是勾起了他无尽的思乡之情。这首诗用南朝民歌体,形式自由活泼,诗中寓情于景,又直抒胸臆,于起伏回环之间将内在的愁绪逐次展开,耐人寻味,末四句,既点题,又饱含深意,深化愁绪,指归诗旨,一气呵成。史载:“初,综既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辞……当时见者莫不悲之”,[7](卷五十五,P824)《悲落叶》同样属于悲情诗,比《听钟鸣》更为曲折:
悲落叶,联翩下重叠,重叠落且飞,从横去不归。长枝交荫昔何密,黄鸟关关动相失。夕蕊杂凝露,朝花翻乱日。乱春日,起春风,春风春日此时同,一霜两霜犹可当。五晨六旦已飒黄,乍逐惊风举,高下任飘飏。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各随灰土去,高枝难重攀。[6](北魏诗卷一,P2213)
诗歌运用暗喻的手法,以落叶自喻,叶落之悲也是自己的人生之悲,将自己的身世之悲和人生苦闷及王朝的盛衰之感,全寓喻在叶绿叶落之间,情思流宕婉转,起伏绵延,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艺术匠心。
(二)北朝诗人学南之风的兴起 作为北朝文人诗复苏的重要阶段,洛阳诗坛诗人数量多,除上述两个诗人群体外,本土汉族士人也特别多,且像郑道昭、常景、李骞、李谐、甄琛等成就颇为突出,在当时的北魏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常景是这一时期本土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是一位官场失意的文人,其诗也大多失意者的孤芳自赏或自我安慰,现存其《赞四君》,以古之先贤自喻,借赞美古代贤者彰显自我人格的完美。
长卿有艳才,直至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
王子挺秀质,逸气干青云。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
严君情沈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口,位结李强舌。素尚迈金贞,清标陵玉彻。
蜀江导清流,扬子挹馀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得闲游。[6](北魏诗卷一,P2219)
这组诗在写作手法上与南宋鲍照的《蜀四贤咏》和颜延之的《五君咏》有许多相似之处。诗人在诗句中灌注了强烈的自我主导意识,以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杨雄四位文人的不得志,自喻官场失意,凸显了诗人自己的不得志与苦闷。在艺术技巧上,四首都是五言八句,中间两联对仗整齐,首尾自由不拘,读来爽朗上口,与当时南朝的不少同体诗相似,已颇接近后来的五言律诗了。
其实,在北魏后期的洛阳时代,诗坛的学南风气十分浓厚,有相当一部分本土诗作正是通过学习、模仿南朝诗艺而走向成熟的。
客观地说,这个时期的文学融合还不算成熟,有的诗充其量只是一种简单的模拟,虽然有利于北朝诗歌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北朝诗歌的复苏与发展,但过分明显的的模拟痕迹使一些作品的艺术性会大打折扣,诗人的个人情感也会湮没在过度地模仿之中,降低了诗歌的艺术水准。如崔鸿的《咏宝剑》:
宝剑出昆吾,龟龙夹采珠。五精初献术,千户竞沦都。匣气冲牛斗,山形转辘轳。欲知天下贵,持此问风胡。[6](北魏诗卷一,P2212)
语言朴素,诗风劲健,基本不脱北诗本色,只是用典、对偶等技巧的运用超越了传统,吸纳了南诗的作法,但在诗中这些手法又略显生疏,刻意模仿的痕迹很浓。这种现象在稍后的“北地三才”中尤其明显。
从整体来看,与南朝诗歌相比,北魏的诗歌成就,仍然微不足道。当时的北魏除了温子升以及由南入北的个别文人还有些许文学素养,其他文人的成就普遍较为低下,而南朝先后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优秀诗人,如谢灵运、鲍照等,在这种巨大差异的环境下,北朝诗人大量模拟南诗,痕迹相当明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模拟之风在北朝文学极大落后的情况下是必经之路,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大量的模仿之后,北魏诗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早期南北融合程度不深,北魏古朴拙厚的四言诗没有模仿痕迹,即使到了中后期,北朝诗人也绝不是单纯模仿,而是学南之清新风气,绝无其纤秾绮艳的诗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朝诗歌中所形成的质朴清新之特色,实现了对南朝齐梁柔靡诗风的超越。北魏诗歌的独特价值在中国整个诗歌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和抹杀的。
三、北地三才的学南之举
北朝中后期在诗歌方面的创作主流是学习、模拟齐梁诗歌,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虽然史书中不乏对魏收、邢邵等人才华的褒扬之词,但实际上,这种创作方式及其产物,在当时就为人诟病。虽然整体来说魏收等人的作品水平并不算高,但将其完全否定则未免有些苛刻,这是北朝诗歌成长革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略显拙劣的阶段,到了隋朝时期,薛道衡、杨素等人无法真正成熟起来,也不会出现像隋炀帝这样融南北之长的集大成者,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初唐时的文学思潮。
(一)邢邵、魏收的“任沈之争” 在学习南诗的过程当中,“北地三才”堪称是最为努力的人,以“北地三才”为代表的学南文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北齐·魏收传》载:“除帝兄子广平王赞开府从事中郎,收不敢辞,乃为《庭竹赋》以致己意。寻兼中书舍人,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8](卷三十七,P484)由此可见,“北地三才”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声誉与地位的。《颜氏家训·文章》篇云:“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9](卷四,P273)可见,“北地三才”不仅模仿痕迹十分明显,而且往往取法于一人。
因为处于南北文风融合的初期,“北地三才”学习南朝诗风,往往停留在其表面而不得其精髓。南诗的优秀之处,在于其语言的清新婉丽、圆美流转,在于其结构的巧妙灵活、整丽严谨,声律的和谐顺畅,意境的浑融一体,而该时期的学南北人却并没有习得上述诸种优点,反而停留在南诗的表面,被其富丽华艳的描摹、精雕细琢的手法所吸引,因此写出的作品格局就不会很大,境界也不会很高,既缺乏南诗中精致的审美情趣,又丢失了北诗中崇高的气骨。
在魏收的存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满纸的宫廷诗风,魏收学习南诗取法任昉,不仅声律,就连内容都完全照搬。魏收作了大量的艳词,在他的14首存诗中,乐府诗有5首,直接描写女子的诗就有4首,其《挟琴歌》、《美女篇》(二首)、《永世乐》等作,对于闺怨香艳的描写乐此不疲,但在表现上却显得十分粗苯。其《美女篇》云:
楚襄游梦去,陈思朝洛归。参差结旌旆,掩霭顿驂騑。变化看台曲,骇散属川沂。仍令赋神女,俄闻要虙妃。照梁何足艳,升霞反奋飞。可言不可见,言是复言非。
□□□□□,我帝更朝衣。擅宠无论贱,入爱不嫌微。智琼非俗物,罗敷本自稀。居然陋西子,定可比南威。新吴何为误,旧郑果难依。甘言诚易污,得失定因机。无憎药英妒,心赏易侵违。[6](北齐诗卷一,P2268)
第一首诗重点描写楚襄王梦游之事,但同时又穿插着曹植遇宓妃之事,其中单数句描写楚王,双数句叙述曹植,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十分相似,甚至曹植的《洛神赋》也影响明显,魏收这两首诗只是简单模仿前代的赋作,并与之一一对应,汉魏文人描写楚王之事大多是将其用作典故来托物言志,而魏收此诗却是对此详细描写,敷衍成篇,缺乏诗人的情感寄托,境界不高,语言上生涩拗口,不够明白晓畅,但是遣词造句上富丽华艳,追步南风之痕迹可见一斑。
他的山水游宴诗同样充斥着满满的宫体语调,有《棹歌行》《后园宴乐》《晦日泛舟应诏诗》《七月七日登舜山诗》共四首。其《后园宴乐》云:
束马轻燕外,猎雉陋秦中。朝车转夜毂,仁旗指旦风。式宴临平圃,展卫写屠穹。积崖疑造化,导水逼神功。树静归烟合,帘疏返照通。一逢尧舜日,未假北山丛。[6](北齐诗卷一,P2269)
因作者过分雕文琢字,才气不足,所以致使整首诗语意生涩,虽然“树静归烟合”一句稍有灵气,动静结合,意境飘渺,但紧接着“帘疏返照通”却成了一大缺憾,一个“通”字显然是作者为了押韵而有意为之,但却成了煞景败笔,整首诗造作痕迹明显,格调不高。
魏收的诗,表现了北朝诗人追效南朝诗风而不及的尴尬状态,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南北诗歌之间的巨大差距。南诗之精,不在其轻艳佻巧之内容,亦不在其浮华繁缛之外在形式,而在其清幽秀丽之意境,在其明丽疏朗之格调,而魏收处于学南之前期阶段,对于南诗更深一层的优点还无法把握,只能从其华美精致的语言方面着手。所以,北人学南必然是漫长的过程。
和全面模仿南风的魏收一样,邢邵也在深入学习南朝诗风,《北史·邢邵传》载:“邵雕虫之美,独步当世,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4](卷四十三,P1589)梁朝文人也觉得“子才文辞实无所愧”,“邢子才故应是北间第一才子”。[4](卷四十三,P1591)由此可见,邢邵不仅在北方诗坛享誉很高,而且在南方诗坛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邢邵存诗现有8首,既有短制,又有长篇,内容丰富多样,邢邵诗歌原本散发着北朝诗歌浑厚古朴之风,但是,由于南北文风融合的程度逐渐加深,逐渐受到沈约、谢眺等南方诗人的影响,开始大力创作南朝齐梁诗体,使得其诗歌中逐渐透出绮丽婉转的风格特点,寓情于景、感情真挚自然,整体上形成一种悲凉感伤的风格,再加上辞藻上日趋绮丽浮艳,最初的质朴浑健之风反而越来越淡了。如其《三日华林园公宴诗》中的“新萍已冒沼,馀花尚满枝。草滋径芜没,林长山蔽亏。”[6](北齐诗卷一,P2263)诗中春意渐浓,池水涌动,浮萍荡漾,枝花怒放,一派生机的春意盎然图景;《齐韦道逊晚春宴诗》中的“日斜宾馆晚,风轻麦候初。檐喧巢幕燕,池跃戏莲鱼。”[6](北齐诗卷一,P2265)借轻风、新麦、春燕、池鱼展现了一幅清新明丽、生机勃勃的暮春景象。
学习南风者,多有描写女性之作,这是北人学南在初期阶段的必然表现,因为在刚开始意识到南北诗歌差距的时候,看不清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及差距的根源,必然会学习一些外表的东西,所以,“北地三才”在学南的初期阶段,所看到的是诗歌的遣词造句以及内容上的平庸虚无。在邢邵现存的诗歌中,有两首是描述闺阁之怨的,虽宫廷诗风十分明显,但依稀可见北诗风气的存留。其《思公子》云: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6](北齐诗卷一,P2263)
该诗一二句化用了徐干《情诗》中“绮罗失常色,金翠暗无精”两句和《古诗十九首》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两句,描写了一位女子因思念丈夫而日渐消瘦的情景,字里行间透漏着南朝齐梁之风;后两句写了该女子的心里活动,描摹了一幅想象中的未来画面,等到丈夫回来的时候大概互相都不认识了,内心的真情实感自然流露,语言简单明了,颇有北朝乐府简洁粗犷的优点,另外,邢邵将“绮罗”“桃李”作于同一首诗,前后衔接自然流畅,天衣无缝,开了二者关联使用的先河,可以说邢邵的这首诗开了一代唐诗的先风。
邢邵也写有一些应诏唱和之作,如《应诏甘露诗》《贺老人星诗》,所描写的内容无非是赞美统治者,语言华丽富贵,但毫无诗人的真情实感,总体上无甚可取之处。
虽然邢邵诗歌多为学南之作,难免带有模拟之迹,但邢邵也有几首能够体现北朝诗风的作品,而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当属《冬日伤志篇》:
昔时惰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馀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6](北齐诗卷一,P2264)
从诗中所云“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可看出,这首诗作于邢邵的晚年时期。在北齐后期,孝昭帝高演随意屠杀大臣,与邢邵交谊甚笃的好友杨愔也死在了高演的暴政之下。邢邵青壮年时期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尔朱荣之乱以及东西魏分裂等一系列战乱,在北朝大地上曾经的繁荣被战后的荒凉所取代,诗人颇有抚今思昔之感,于是感慨无穷。诗风自然变得苍凉高古。范大士评曰:“清音激越,尽洗铅华。”[10](P114)由此可见,该诗虽在写作技巧上效法南诗,但是却能够独抒胸臆,诗歌的境界变得很高,因此在某种层面上超过了南诗单调乏味、情感匮乏的诗歌格调。在诗歌结构上虽然不如南诗精致,却能够寓情于景,情感深沉,同时也说明了北诗长于气质的传统风格,质朴刚健之处,尽显魏晋风调。
邢邵学习南诗语言中的清词丽句、格式上的圆美流转,开了北人学南潮流的先锋。于是,北诗中凝重板滞、质木无文的缺点开始得到改善。
(二)温子升与北朝诗风的转变 三才之中属温子升的诗歌创作成就较高,温子升在当时统治者中颇受欢迎,当时济阴王元晖业曾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2](卷八十五,P1876)而且,温子升的作品还得到梁武帝的赞扬:“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词人,数穷百六”,[2](卷八十五,P1876)这样高的估计,现在看来未免过誉,但在当时,温子升在北方诗坛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温子升现存诗歌十一首,其中七首乐府,语言准确、简洁。大部分诗歌以反映现实为主,用乐府古题来反映北地生活,展现出了北方诗歌豪放粗犷的特点。如《白鼻驹》中的“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6](北魏诗卷二,P2220)诗中描写了一群少年侠客骑着长有白鼻子的马驹在街头寻欢作乐的逍遥情景,表现了少年们追求快活、豪情纵乐的性格特征。再如《敦煌乐》中的“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炖煌乐,不减安陵调。”[6](北魏诗卷一,P2221)描写了有远方的客人来到敦煌,一路上相伴着歌唱,此间自有敦煌的民族音乐来助兴,丝毫不比中原的音乐差,表达了诗中主人公旷达乐观的性格。温子升也写了一部分借景抒情的诗歌作品,例如《相国清河王挽歌》:“高门讵改辙,曲沼尚馀波。何言吹楼下,翻成薤露歌。”[6](北魏诗卷一,P2222)描写了清河王家家风尚严,家德流布后辈,因此清河王死去,要为他奏挽歌,情感溢于言表,表达了诗人对生命稍纵即逝的感慨。
温子升所写的诗歌,我们能够感受到从南朝诗歌中学习借鉴到不少成分,像“细草缘玉阶,高枝荫桐井。”[6](北魏诗卷一,P2221)写台阶上新生细草,桐井上的高树宛然一片新绿,展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早春景象。宛然齐梁体格,《魏书·温子升传》评价子升“文章清婉”,[2](卷八十五,P1876)把这个词用在评价温子升的诗歌创作上同样恰到好处。据《隋书·文学传序》云:“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1](卷七十六,P1729—1730)从中我们可以读出子升诗歌在“清婉”之外还能够“重乎气质”。因诗人生活于北朝浑厚的地域环境中,同时又大力模仿“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12](卷二,P67)的南朝齐梁之风,所以,能够在其诗歌当中同时看到清婉与气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征。但是,在一派学南之风中,子升诗中主要还是以词义贞刚之气为主,将南诗中细腻的艺术技巧融于开朗的格调与苍茫的画面中,读来让人浑然不觉,这方面的代表当属其《捣衣》: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6](北魏诗卷二,P2221)
诗歌用情景交融的手法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位捣衣女子对出征边塞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在《古诗源》中沈德潜将其评作“直是唐人”,[13](P339)由此可见,该诗具有相当高的境界,诗歌技巧亦相当纯熟。沈德潜将其与代表中国诗歌成就最高的唐诗相提并论,因此,其价值与成就不容后人忽视。该诗采用杂言诗体,颇有歌行意韵,诗中全篇白描,不再借助华丽的辞藻来传达旨趣,气格悠远,情感一泄而出,浑然一体,引人入胜。
温子升的诗歌创作对北朝诗歌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力,促进了北朝诗歌从沉寂的北魏前期发展到了中后期的复苏,甚至对北齐时期的诗歌繁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南诗的影响下,温子升等人带领北朝诗歌走向宣泄情感、传达心声的具有艺术性的文学体裁,促进了北朝诗风由质实到华美,逐渐使北朝诗歌发展到蔚为大观的辉煌局面。
在南北文风融合的潮流下,温子升的诗歌虽然较多的吸收接纳了南诗较为先进的诗歌技巧,但其作为北朝诗人,骨子里流淌的是存风骨、重气质的血液,因此其笔下的诗歌大多为气质贞刚、风格古朴的汉乐府诗歌,所采用的南诗精致的艺术形式只是为了表现诗人厚重深沉的情感。邢邵比温子升小一岁,但是却比温子升长寿二十多年,因此邢邵对南诗的接受程度远远要超过温子升,成为北朝学习南诗文人创作的主旋律,而作为北诗传统的乐府诗此时被大量的齐梁诗风所代替,从邢邵的诗歌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不论是遣词造句,还是风格特点,都在逐渐向南诗靠拢,而气度豪迈、语言晓畅的乐府诗仅存一首。诗歌发展到魏收所主要生活的北齐时期,诗歌中的南朝宫体烙印比比皆是,诗歌风格更加远离北诗传统,因此,在“北地三才”中,魏收的诗歌在学习南诗方面是最为彻底的,即使其诗歌中存有一定数目的乐府,但其继承的也是繁缛华丽的两晋风调,所表现出的绮靡浮艳已与南诗别无二致。在今天看来,魏收因为过分的模仿南诗而丢失了自己的风格,所创作出来的诗歌未免有些畸形,但是作为时代的主流,魏收又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并且作为落后于南诗的北诗,在前进发展的道路上,模仿学习是必经之路,为之后超越南诗做了很好的铺垫基础。
北朝文学在初期将重点放在了儒家教法上,“北地三才”出现后,逐渐注意到了南北文学的地域差异与发展距离,因此三才开始身体力行去学习模仿南诗,但是三才对于北朝文学的贡献还远不止在诗歌创作上,在文学思想上,三才同样促进了对北朝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温子升称“诗章易作,逋峭难为”,[2](卷八十五,P1877)由此可见温子升并不认同一味的盲目模仿,而是坚持在学习南诗的同时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温子升的诗歌创作也有力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在其清丽婉转的诗句中仍有北风刚健质朴的痕迹。
邢邵、魏收的文学理论要比温子升深刻得多,其文学思想颇多可圈可点之处。邢邵曾曰:“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14](北齐文卷三,P3841)邢邵看到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指出西晋时期的太康诗风迥异于建安风骨,颜延之、谢灵运通过大量创作山水诗从而取代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的独统地位。与此同时,诗人的审美情趣、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不论是从地域上看,还是从时间上看,南北之间的文风差异都是合情合理的客观存在。
四、结语
“北地三才”模仿南朝诗风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北地三才”的学南之举还属于初级阶段,显得比较笨拙,没有学到南诗中清新、绮丽的特点,反而把能够表现贞刚之气的北诗本色丢了,他们学到的只是南诗中的“宫体”恶调,对于其精髓并没有认识清楚,所以,这一点一直被后人诟病,但是,他们处于学南的开头,这在南北文风交融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他们勇敢地迈出学南的步伐,才能为北诗的发展以及超越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