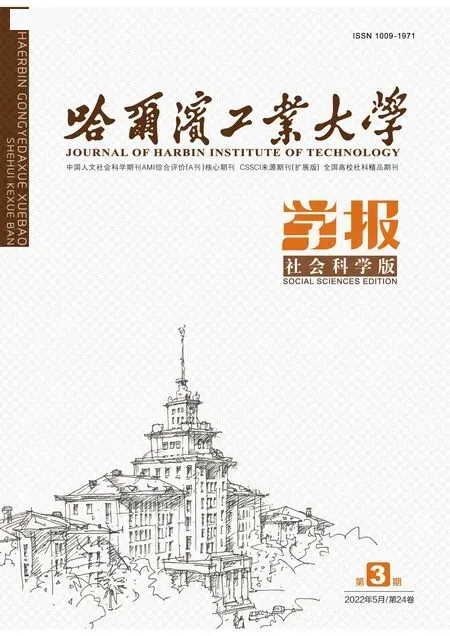茅盾的女作家论与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史塑形
曹露丹,荣光启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在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现代中国第一代女作家的登场是极具历史意义的文化事件。 在这个觉醒与迷茫、苦闷与激情相互交织的动荡年代中,这些女作家以独特的视角、鲜活的笔触为这一时代贡献了特别的篇章。 五四女作家横空出世,凭借其创作以新女性的姿态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中,迅速引起从普通读者到专业的文学批评家的广泛关注。 然而,当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成为历史的回响时,五四女作家被文学史抽象为一种具有蕴含着特定精神内涵的群体,以反封建斗士的形象呈现在世人眼前。 在这个过程中,茅盾写于20 世纪三十年代的三篇女作家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文学转型期女作家论的诞生
茅盾在1927—1934年间,先后写下了八篇作家论,开创了作家论这种新的文学批评体式。 在茅盾这一时期所写的八篇作家论中,包含三篇女作家论,分别是《庐隐论》《女作家丁玲》和《冰心论》。 茅盾最初写作作家论是应叶圣陶的邀请,据茅盾回忆,当他正在构思小说《动摇》时,叶圣陶向他约稿写评论文章,叶圣陶建议茅盾写鲁迅,但是评论界对鲁迅的作品众说纷纭,各执己见,难以统一,需要深思熟虑方能下笔,所以先写了《王鲁彦论》[1]。 如此看来,茅盾的作家论的写作似乎源于偶然,然而,叶圣陶的邀约只是一个契机,茅盾应约写作,并在后来的几年中持续创作作家论,有其深层的动因。
20 世纪20年代末,随着五四的落潮,新兴的革命文学替代了尚未发展成熟的文学革命,成为新的时代偶像。 创造社与太阳社中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受到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启发,以及“左倾”思潮的影响,在文学批评方面,片面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而否定文学的艺术性,并且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建立的新文学传统。 在“革命文学”的旗帜下,五四时期的文学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文学或小资产阶级文学,甚至鲁迅、叶圣陶、茅盾等重要作家的作品,也被看作是透露着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落伍文学。 茅盾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一方面,他支持“革命文学”的建立,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五四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不能抛弃。茅盾认为“革命文学”应该继承和发展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不是割断与五四的联系、彻底抛弃新文学传统。
“革命文学”的论争,是驱使茅盾开始创作作家论的深层原因,创作作家论的目的是要总结新文学十年的功过得失,梳理五四新文学传统,纠正时下“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在理论上的偏颇,也希望借此引导新文学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茅盾写下了三篇女作家论。
这三篇作家论都写于20 世纪30年代前期,正是左翼文学兴盛的时期。 茅盾作为左翼文学的重要人物,他的批评意识也从五四时期的朦胧状态转向了一个清晰的理论范畴。 他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自觉地不断地接近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念。 因此,在对几位女作家的具体分析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运用了阶级分析法。 茅盾认为,从本质上来讲,文学作品是作家特定的阶级意识与阶级情感的映射,因此,不能单从文学审美的层面去谈论作品,必须充分考虑到作家的阶级出生和政治态度。
茅盾在介绍作家的生平经历时,特别关注作家思想意识的转变,着重考察这种思想意识的变化如何展现在作品当中。 茅盾将庐隐的创作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全盛时代,这一时期庐隐的创作是朝着客观的写实主义的方向走的。《一个著作家》反映了包办婚姻的问题,《灵魂可以卖吗》描写纱厂女工的生活,《月下的回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同胞的毒害。 庐隐的作品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矛盾,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茅盾认为庐隐是这一时期女作家中注意社会题材的第一人。 庐隐创作的第二阶段是五四落潮之后,随着五四的落潮,庐隐的创作也改变了方向。 茅盾用一句话来概括她这一阶段的创作:“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2]评价说她这一时期创作虽然不少,作品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仍旧囿于《海滨故人》的模式,穿着用幻想编织出来的sentimental 的衣衫。叙述完这两个阶段之后,茅盾单独讲了《曼丽》一集,虽然对《曼丽》集中的作品评价不高,但是却从其中看到了庐隐转变的可能性。 在《曼丽》中,庐隐没有单将婚姻问题和男女问题当作爱情问题来处理,而是当作社会问题来处理,虽然观察并不深刻,但也是她创作中的一点波澜。 茅盾认为引起这一转变的原因是时代的暴风骤雨在庐隐心中引起了震荡。
茅盾对于冰心和丁玲的分析与上述模式相同,从传记材料中分析作家思想立场的变化,将作品与作家思想立场的变化相对应,最后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对作家的思想意识作出价值判断,以此为根据评判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 茅盾明确指出庐隐是“资产阶级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产儿”,庐隐早期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尽管幼稚,但是值得肯定。 如果庐隐在现实主义的路向上坚持创作,肯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是,庐隐的创作随着五四的落潮而停滞在某一阶段,后期的作品没有太大的社会价值。 冰心在五四时期写下的“问题小说”因为关注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被茅盾所肯定,而那些在“爱的哲学”的驱动下写就的作品,则是“混着神秘主义的色彩”,“完全是唯心论的立场”,“用以解释社会人生却一无是处”[3]的。 对于冰心在《分》《冬儿姑娘》中表现出来的回归现实问题的倾向,茅盾予以肯定,也表达了自己的期待。 同样的,与《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塑造了有叛逆性的个人主义者的作品相比,丁玲那些在普罗革命文学运动影响之下创作的作品,如《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水》获得了更高的评价。
正如温儒敏所说:“茅盾这些‘作家论’总是有一个无形的坐标,坐标轴的一边标明时代社会的变迁,另一边标明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而作品及其所体现的创作道路则由两轴之间的起伏曲线来表明。 情况似乎就变得如此简单,你在时代、作家、作品三方面确定任何一方面的其中一点,都可以从固定的坐标中找到其他两方面相应的‘点’。”[4]在这样的批评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茅盾脑袋中的“本质”“意义”“规律”等基本概念,通过这些将复杂的文艺现象简单地化约为社会现象,再以阶级分析的眼光作出价值判断。这是一种极其理性化的批评方式,任何可能影响到理性判断的因素都被排除在外,这其中就包含了性别因素。
事实上,无论是庐隐、冰心还是丁玲,她们的作品中都蕴含着女性特殊的生命体验,庐隐的彷徨,冰心的温婉,丁玲的执拗,都在作品中有生动的体现,这是女性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独特的生命体验。 然而,当茅盾从纯粹理性判断的角度出发,侧重于对文学文本做社会学分析时,这些独特而宝贵的女性书写却成为了应当修正的异端。
二、女作家论价值导向下的五四女作家
茅盾的三篇女作家论,在主题批评上采取了定性的操作方式,将作家的创作历程与社会思想的变迁直接对应起来,按照意识形态的需求,对作品做出富有权威的终极性的价值判断。 茅盾始终怀着强烈的热情关注着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社会使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茅盾提炼出了三位女作家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圈定了她们的无价值和无意义。
茅盾三篇女作家论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他总结了三位五四女作家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更在于这三篇女作家论形成了一种价值评判的导向。即在思想上遵从时代精神反映论和历史进步趋向论,以切合意识形态和时代需求的观念为标准,对作品作权威性的价值判断,也正是因为看重文学反映社会历史潮流的功能,茅盾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如此一来,除后期加入“左联”,在创作上有重大转变的丁玲外,对其他两位女作家既有作品的评价,表现为以“问题小说”为首的价值递减的差异序列。 而“问题小说”是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当时启蒙主义的思潮孕育出文学要触及现实人生,并且如实反映社会问题的主张。启蒙主义催生了问题小说,问题小说切合启蒙主义思潮,同时,启蒙主义思潮也借着问题小说的潮流得以传播得更加广泛。 “问题小说”的产生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需要,也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的“问题小说”被认定为最能体现“五四精神”的正典。茅盾通过对“问题小说”的肯定,实际上肯定了“五四精神”,只不过他强调的是“五四精神”中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 后来的文学史就是在这套价值体系中对五四女作家进行评价,它对五四女作家文学史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这部文学史诞生在一个弥漫着集体意识的时代中。 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史的要求,在于以国家话语的方式重建现代文学的经典序列,而评判作家与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阶级论。 在政治的强力压迫中,王瑶正是借用茅盾的权威观点,在文学史中为五位五四女作家争得一席之地。 《中国新文学史稿》总共记录了冰心、庐隐、冯沅君、袁昌英、濮舜卿五位五四女作家,王瑶借用茅盾的观点诠释了冰心、庐隐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五四精神”,对于其他几位女作家,也是在茅盾女作家论建立的价值体系中给予评价。 例如,在谈到濮舜钦时,仅仅提到了她有剧作《人间的乐园》,这部作品之所以被重视,也是因为其内容体现了诸多社会问题,有反封建家长专制、揭露婚姻不自由等内容。 再如,王瑶对于袁昌英的总体评价是消极的,认为她的作品只是使人得以消遣和安慰的东西,唯独《孔雀东南飞》获得了正面评价,因为这部戏反映了五四时期的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
茅盾女作家论所产生的影响,在新时期的文学史书写中表现得更加清晰。 新时期文学史的书写旨在破除单一阶级论的捆绑,挣脱意识形态加诸文学的沉重枷锁。 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现并还原“五四精神”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案。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曾经被驱逐于文学史之外的五四女作家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也是得益于“五四精神”的复归。 然而,当我们深入到文学史的具体书写中,茅盾女作家论中形成的价值体系,继续影响着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史塑形。
首先,在新时期文学史重写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文学史,都是在“问题小说”的架构中来评定五四女作家体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作者论及冰心的创作时,仍然首先肯定了她的“问题小说”,认为冰心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也肯定了冰心这些“问题小说”的价值。 对庐隐的评价也是如此,《海滨故人》系列中有许多的作品侧重于表达个人情感,不能称之为“问题小说”,却也被吸收到“问题小说”的框架之中,理由是这些作品探究的是“人生”是什么的问题。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评论陈衡哲与冰心时,也是说到“陈衡哲、谢冰心出现在‘五四’前后启蒙思潮的高峰和转折时期,她们写的多是启蒙主义的‘问题小说’。她们思考着人生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少有日后出现的妇女作家作品中那种自叙传色彩”[5]222。 还有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也都是在这样的架构中谈论冰心、庐隐的作品。
其次,以“五四精神”为武器反抗政治对文学的压迫,是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手段。 这里所提到的“五四精神”包含“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等启蒙理念,但是在对“五四女作家”的阐释中,“五四精神”则成为“反抗精神”的同义语,这与茅盾的女作家论所建立的价值导向是一致的。 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论及五四女作家冯沅君时,这部文学史认为她“确实代表了‘五四’时期觉醒了的女性的呼声,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6]。 这里所指的女性的呼声,就是她们反抗旧式家庭、争取婚恋自由的诉求。 在其他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中,对于冰心、庐隐和冯沅君等作家都采用了相似的价值判语。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所论述的女作家分为三类:“她们的艺术个性大致可以分作三组加以讨论:出现于新文学运动前期的陈衡哲、谢冰心为一组,出现于流派盛行时期的庐隐、石评梅、冯沅君为一组,凌叔华、苏雪林为一组。”[5]222虽然杨义强调是以艺术个性为依据对几位作家进行分组,实际上却不然。 将陈衡哲与冰心划为一组,是因为“陈衡哲、谢冰心出现在‘五四’前后启蒙思潮的高峰和转折时期,她们写的多是启蒙主义的‘问题小说’。 她们思考着人生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少有日后出现的妇女作家作品中那种自叙传色彩”[5]222。 庐隐、石评梅与冯沅君在一组,“她们的小说表现出来浓郁的自叙传的和主观抒情的色彩,她们多由自己本身或身边人物的悲惨遭遇,看出旧社会、旧礼教的冷酷和黑暗,从而产生感伤的和社会反抗的情绪。 总的来说,这组女作家的小说比冰心、陈衡哲的‘问题小说’更富有叛逆性”[5]224。 对于凌叔华和苏雪林的评价则是:“同时出现的另一组作家凌叔华、苏雪林的小说,情调较为温顺,缺乏上列作家小说中的叛逆性,缺乏庐隐那种刻骨铭心的悲哀,缺乏冯沅君那种无所顾忌的大胆描写,缺乏石评梅《匹马嘶风录》中那种气宇轩昂的豪情。 她们较多地描写温饱而微愁的家庭生活”[5]226-227。不难看出,杨义为女作家分类的标准并不是艺术性的差异,而是在“问题小说”这一论述框架内,以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叛逆性为依据对作家进行分类。
最后,新时期的文学史对五四女作家的评价,仍然遵从着茅盾在女作家论中强调的时代精神反映论。 茅盾在《冰心论》中,将冰心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并且肯定了“问题小说”时期的创作,因为这一时期的创作切实反映了五四时期的现实问题。 对于第二阶段的创作,茅盾则给予了批评,原因是冰心逐渐脱离了现实,而转向了充满着神秘主义的“爱的哲学”。 面对小说《分》展现出来的创作新质则感到欣喜,这时的冰心似乎有意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上来。 新时期文学史对冰心的论述大都直接使用了这个论断。 仍然以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例,在评价冰心的作品时,杨义认为相比于《超人》时期的创作,“问题小说”与《分》以后的创作更有价值,给出的原因仍然是后者更加清晰、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现实。 时代精神反映论同样用于衡量别的女作家,在评价冯沅君时,也是肯定了《卷施》所表现出来的风貌,因为“这些小说,充满着‘五四’青年的生机勃勃的青春活力,充满着反抗封建礼教的坚贞不屈的精神”[5]287。 对冯沅君《春痕》及《劫灰》的评价则远远低于第一时期的创作,也是因为其后期的创作在反映现实社会的力度上不如之前。 此外,新时期的文学史在总结庐隐的创作时,不断地提及“创作停滞论”,也是在强调庐隐后期的作品未能跟随时代的潮流,反映新的社会历史现实,而仍然躲在五四的“海滨小屋”中。 新时期的主流文学史,比如《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也都有着类似的观点。
三、女作家论影响之探因
茅盾这三篇女作家论诞生依托于具体的时代语境,与其他作家论一样,茅盾透过作家的创作,挖掘作品中时代性、社会性的内涵,对于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指明新文学接下来的发展方向都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为什么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语境,茅盾的作家论仍然如此具有生命力,甚至直接影响到文学史中五四女作家形象的塑造呢? 除了茅盾本身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家论与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动因有着深层的一致性。
“新时期”的历史叙事是以“文化大革命”为逻辑起点的,十年梦醒,过往种种仍是历历在目,满含沉重与伤害的记忆,很容易使人将这段时期视为黑暗矇昧的时代。 因此,人们对于“新时期”的想象和叙述,自然都是与“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的新中国史相对立的。 “新时期”无疑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术语,同时也饱含着国人对于新历史时期的热切期盼,正是这样的社会心理,使“新时期”这一术语被迅速运用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在思想文化领域,面对“文化大革命”梦魇终结之后的“新时期”,人们亟需一种新的支撑性话语解释历史和指导实践,在这样一个结局和开端叠合的历史时代,曾经推动了中国历史向现代转变的“五四”,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20 世纪70年代末,一场以回归“五四”为目标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80年代与“文化热”的浪潮结合,形成了一股席卷中国大地的时代潮流,进入90年代后,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被命名为“新启蒙”。
不难看出,正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语境,造就并赋予了“新启蒙”运动的精神指向。 这场“新启蒙”运动初期的理论来源并不是欧洲的启蒙思想,而是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理论,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新启蒙”运动缘起于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的自我批判,而自左翼时期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这种自我批判不可忽视的精神资源。 吊诡的是,这场自我批判运动,在形式上表现为强调个人自由、反思集体生活,具体的操作方式则是征用和重启“五四”,也就是在“新启蒙”运动自身的暧昧性中,五四精神与三十年代的叙述经验,都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资源。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新时期现代文学史的重新编写,是为了清除文学史中唯阶级论的僵化思想,打破一体化思想下政治加诸文学的沉重枷锁,实现文学史的去政治化,从而响应解放思想的启蒙主义号召。 虽然新时期的文学史表现出对政治的反抗姿态,但实际上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原动力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只是政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从正向的压迫转为驱动文学史做逆向的反抗。 与20 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中极端化的阶级分析相比,新时期以思想解放、启蒙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的价值评判体系,无形中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以“五四”之名,对现代作家的内涵作精神提纯。 换言之,新时期文学史的肌理仍旧是政治性的。 而正如温儒敏在评价茅盾的作家论时所说的:“他的犀利的主题意义的分析,从意识形态角度切入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确有一种鞭辟入里的作风。 在以政治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里,茅盾这种作家论比较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7]。 茅盾的作家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与以政治为底色的新时期文学史的需求是相符合的。 具体到五四女作家在文学史中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五四女作家回归文学史得益于“五四精神”的重新释义,而茅盾在三篇女作家论中,通过对“问题小说”的积极评价,肯定了“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面向,那就是反封建的进步性,这一点也符合新时期文学史复归“五四精神”的要求。 因此,新时期文学史对于五四女作家的评价,基本上沿用了茅盾女作家论搭建起的价值体系。
结语
茅盾女作家论中性别视角的缺失,使得她们创作中真正打动人心且极具艺术价值的东西没有被正视。 新时期的文学史对于五四女作家的描述不仅没有有力地修正这些缺陷,还进一步将五四女作家的价值固定在以“五四精神”为价值准心的评价体系中。 如此一来,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反抗精神为表征的“五四精神”逐渐成为确证五四女作家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支点,而“觉醒”“反叛”的斗士的形象也就成为五四女作家的本质性特征,甚至成为五四女性文学的本质性特征。
诚然,新启蒙语境影响下的文学史,为五四女作家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提供了空间,但是在“五四精神”的绝对标准下,也造成了女作家文学史形象的单一化。 那么,当下的文学史又应该如何安置五四女作家呢? 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曾对文学史写作提出质疑。 他认为大多数的文学史或是社会变革史,或是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的思想史。 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否真的存在呢? 当人们谈论文学史时,自然会认为这首先是一部历史,然后它才是作家与作品的排列组合,因此,文学史的书写首先要遵守历史设定的原则[8]。 许多文学史的分期都与政治历史的发展具有同构性,这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国家社会革命和政治的发展,决定了文学转变的取向,这其中所蕴含的是一种政治性而非审美性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韦勒克所提出的问题彰显出文学史的宿命,完全独立于时代发展语境的文学史并不存在,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在于,如何降低其他因素在文学史书写中产生的影响,并聚焦于作家与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就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史塑形而言,应当把“五四”及“启蒙精神”对其创作的影响视为一种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左右她们创作发展的主要力量。 如果没有五四,就不会有她们彻底的个性觉醒,也没有促使她们登上文坛的契机,然而启蒙带给她们的不仅仅是“人的觉醒”,也有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 这些基于性别特性的真实书写,造成五四女作家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之间的疏离,这种疏离也透露着她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不懈的探索与思考。
比起寻找那些失踪在历史尘埃之中的作家,文学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家和作品,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再焕新颜,并且为当下的创作提供可以借鉴的传统,引导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创作源泉和活力。 当我们抛弃启蒙视角所带来的盲视,以更宽广更多元的视角去检视五四女作家的创作,尤其是尊重其性别特性为作品带来的别样风姿,五四女作家则会在文学史中呈现出更加多元与鲜活的形象。如此,既使我们看到五四文学更加多元的面向,也能为当代女性主义写作提供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