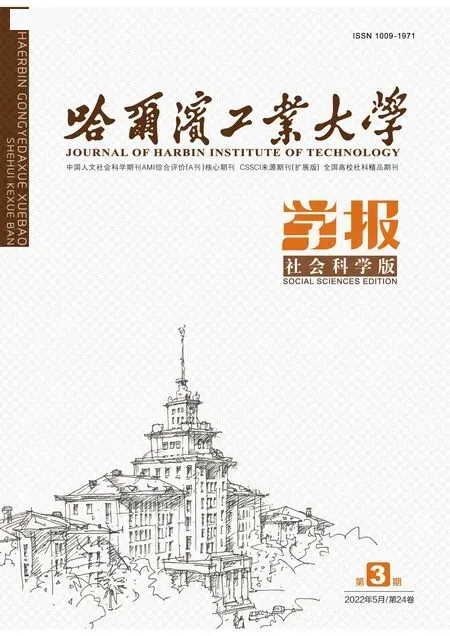萧红的疾病体验与书写
孙 琦
(1.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2.黑龙江东方学院 人文学院,哈尔滨 150066)
萧红生平与作品的紧密缠绕为人们阅读萧红提供了某种路径。 萧红短暂的一生被各类疾病困扰,与萧军的情感纠葛让她一度感到绝望,特殊情况下的两次生产极大损伤了她的身体。而动荡时局中,萧红辗转流途使得包括肺结核病在内的各类疾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 在香港住院期间,萧红喉部肿瘤的误诊仿佛宿命般加速了她的生命进程。 漂泊与病痛中的萧红在写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大量生殖、疾病、死亡等意象。 这些意象指涉的女性身体、生存困境等主题无不显示着萧红对“阶级和民族斗争的大框架”的突破。
一、疾病体验:萧红的异常性格与行为
病迹学(pathography) 一词源于希腊语pathos (病)和graphein (书写记录),直译为病情记录。 它的另一含义是一门对杰出的历史人物从其精神状态方面用精神医学的传记方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1]。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曾极大推动精神医学的发展,“潜意识”“俄狄浦斯情节”等概念对文学有着深刻影响,这一学说也成为探究作家创作意图、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理论依据。病迹学在此基础上确立并逐步发展,旨在“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分析探究他们的异常性格、错综的内心纠葛、疾病史及其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揭示这种关联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及创作活动和作品中的作用和意义”[2]。 这为人们解读作家生平及作品提供了跨学科式的视野。 研究者们在考察歌德、尼采、梵高、夏目漱石等作家时发现,其精神状况与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透过写作进行自我排解,或是借助“狂气”创作出经典之作,但无一例外都会在其创作中留下“病迹”。 就此把握作家的精神结构与心理特征,并对作品出现的象征与隐喻进行挖掘,病迹学理论因科学“诊断”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文学研究中主观臆断的局限。
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郁达夫、萧红、张爱玲等都具有强烈的个人写作风格,疾病也是这些作家的重要写作意象。 在以往的分析中,研究者大多通过“疾病的隐喻”分析其疾病书写,进而探讨作品思想内涵。 实际上,透过病迹学理论,可在此基础上厘清作家精神状态、创作心理与其作品的关系,这为文学、传记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萧红生平因其身后大量的传记书写显得有据可考。 萧红一生中许多选择令人感到困惑、惊异甚至唏嘘不已,而这些选择极大影响了她的人生际遇及作品。 萧红的婚恋、生育、疾病极大缩减了她的生命长度,这必然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但萧红的非理性已然不能仅用性格叛逆加以解释。 由此,病迹学理论提供了一种解读萧红的路径。 笔者认为,多年的漂泊与疾病极大影响着萧红,使她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行为、性格,甚至被某些精神与心理疾病长期困扰。
首先,萧红对他人有依赖心理,她渴望并轻易进入亲密关系且不计后果。 萧红与家人决裂后流落哈尔滨,为了“极力避免真正的或想象出来的被遗弃”[3],与汪恩甲在哈尔滨东兴顺宾馆同居并怀孕,其后汪恩甲的突然消失,再次被“遗弃”的萧红面临着400 块大洋的债务与被卖到妓院的困境。 于是当“拯救者”出现时,萧红与仅见过几次面的萧军发生了关系。 此时萧红已有孕在身,这种带有自我损伤的冲动性行为及其后果萧红不会不知道,《生死场》中王婆对痛苦待产的金枝说“危险,昨晚你们必是不安着的”[4],而萧红选择用身体解救自己,避免再次被抛弃。 在与萧军分手后,萧红在明知怀孕的情况下选择嫁给端木蕻良,这是萧红第二次在怀孕的情况下与另一位男性进入亲密关系,萧红的选择让很多朋友费解,甚至胡风发出“但何必这样快? 你冷静一下不好吗?”[5]的感慨。 而萧红在病重卧床之际遭遇了第三次“遗弃”。 在香港遭遇轰炸之际,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突然离开,并委托骆宾基照顾萧红。据端木蕻良妻子回忆,“回酒店时发现了骆宾基与萧红的私情愤而离开”[6]。 曾有论者对萧红私生活多加指责,笔者认为这与她的精神状况有关。
其次,萧红存在情感不稳定的情况,她常常感到空虚、寂寞,其中包含自我损伤的冲动性与自残行为。 萧红在其作品与书信中不止一次地感叹过她的寂寞。 在给萧军、白朗的信中,萧红时常提及“如今我只感到寂寞”“强烈的哀愁”“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与此相对的是萧红情绪的多变易怒,尤其对关系亲密的人更是如此。 萧红曾与萧军发生激烈争吵,对关照她生产的好友白朗及白朗母亲发泄怒火。 寂寞的心境驱动下,萧红的种种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她的自我损伤行为令人费解。 萧红抽烟与饮酒情况严重,与汪恩甲在哈尔滨东兴顺宾馆同居并怀孕期间,萧红也“烟不离手”。 1932年萧红在哈尔滨诞下一个女婴,萧红产后出现剧烈头痛、高烧,极其虚弱,孩子旋即送人。 如果说第一次生产萧红遭遇的痛苦更多归咎于客观原因,那么第二次生产则更多包含着萧红的自我损伤。 萧红大着肚子露宿走廊,独自一人赶赴重庆,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花钱却大手大脚。 萧红曾向朋友梅志表露心态,孩子虽然夭折,但当下“自己一个人实在拖不起一个孩子”,而令人不解的是种种行为发生在萧红已经与端木蕻良结婚之后。 在香港期间,萧红因肺结核加重而不得不住院治疗,医生建议她手术治疗喉部的肿瘤。 肺结核病带来的虚弱与亢奋相互交织,消耗着萧红最后的理智,她在众人一致反对声中极为轻率地签下了手术同意书。后来肿瘤被证明是误诊,这也直接导致了萧红的死亡。 除去战乱、时局等因素,这些鲁莽且不顾个人安危的行为让人不能不怀疑萧红的精神与心理健康状况。
二、妇女即疾病:女性身体的隐喻
刘禾认为男性批评家在解读萧红的《生死场》时存在某种盲区,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指出“《生死场》中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7]477才是《生死场》的核心思想。 笔者认为,这是鲁迅、茅盾、胡风等男性批评家对女性身体本能的轻视与排斥。 他们较为轻率地将其视为民族国家衰弱的某种隐喻,而不能或不愿看到宏大叙事话语背后的女性身体,一如他们无法理解萧红对于婚恋与人生道路的选择。 而萧红对女性身体、疾病、死亡的直观书写反而超越了民族主义文学的藩篱,成为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极具生命力的部分。
关于身体与疾病的书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疾病书写某种程度上承担了社会文化的隐喻功能。 鲁迅挖掘人的灵魂的深处,从内向型的视角窥视国民的麻木与愚昧;郁达夫自喻“零余者”,在异国他乡怀着病态敏感的心理寻求生理需求与精神上的安慰;新感觉派写作更是身体景观的集中展现;沈从文在城乡二元对峙的结构中书写乡土文明与边地人民的纯粹、英武,以此对照都市文明中孱弱、病态的都市人;解放区作家将对身体与精神的改造纳入革命叙事之中。桑塔格认为:“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既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为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情。”[8]为中国“诊病”,寻求启蒙与救亡是五四知识分子们肩负的时代责任,疾病叙事为他们找到了某种写作路径。
幸运的是,男性作家始终能找到关乎启蒙、现代性、知识分子心态的言说方式。 相比之下,女作家和她们笔下的人物虽然一直疾呼“我是我自己的”,却无法找到确切的言说方式,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的失语者。 这其中蕴含着一层较为复杂的政治编码转换,即女性与疾病的关系。 中国进入21 世纪以来,一些思想家、改革家们便试图将积贫积弱的民族同女性与疾病建立起某种联系。 他们认定中华民族虽然腐朽,但其男性主体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只是病入膏肓,而在寻找病因的过程中,女性则成为承载“疾病”的客体之一。 于是他们从“放小脚”“改造娼妓”等问题入手进行变革,并称“皆因女子缠足,天下男子的聪明慢慢就会闭塞起来,德行就会慢慢丧坏起来,国家慢慢也就闭塞丧坏起来”[9]。 既然如此,在“疾病的隐喻”视域下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改造与拯救女性身体便成为极好的方式。 “对造成国家积弊的女体问题进行改造,就此女性身体作为客体被政治编码为极弱民族的疾病隐喻。”[10]这一传统并非近代社会才出现,从《离骚》到《红楼梦》,都存在着男性性别错指、以女性身份自居的现象。 这看似奇怪,实际上如同君臣、父子、夫妻等纲常伦理等级序列中,总固定着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于是“无论是寄托芳草还是寄托女性,都表现了作者们作为客体价值、待他人取也值得他人取的‘物’的地位的认同,特别是对夫妇、男女两项关系中从属角色的认同,这角色自然是女性角色”[11]。 男权社会的运转不断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以期达成救亡与启蒙的作用。
从“问题小说”到“解放区文学”,作家们思考女性的出路、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并将其抽象为影响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积弊加以讨论,并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将女性的自身问题置换为现代性问题,女性这一符号逐渐成为“空洞的能指”。 而在对女性他者化的过程中,女性身体与心理问题,诸如生殖、成为母亲、女性一生的周期性被隐蔽在国家民族的宏大话语之中。巴金小说《家》中的钱梅芬是肺病患者,她的肺病被视为对封建大家族的控诉;《骆驼祥子》中虎妞的难产而死加速了祥子的堕落进程;《雷雨》中繁漪的“歇斯底里”源自情欲的压抑。 女性的身体成为某种载体,附和着沉重的男性话语前行。 在郭沫若的《残春》、穆时英的《公墓》等作品中,受肺病困扰的女性面容较好,体态柔弱,苍白的脸上带着淡淡红晕,散发着“病态美”,这同样是男性对女性身体与疾病的某种主观想象。 她们或是成为承载文化道德的容器,或是成为男性欲望凝视的对象。
如果说民族积弊被隐喻为疾病,女性除了成为疾病的载体外,还将被编码、隐喻为何? 如果说男性作家可以以女性、疾病自喻以此达成对自身的写照,完成其政治话语的表述,那么除了启蒙主义视域下的宏大主题,留给女性作家言说的空间还剩下多少? 被挤压话语空间的女作家们似乎只剩下女性的自身的经验了,而这与时代主题无关,与现代性话语无涉,只得隐藏于“地表之下”。 于是,女性既然无法如穆桂英、花木兰一样化妆为男性,那么便如莎菲、陈白露一样,将身体悬浮于时代洪流中,或是在男性的帮助下成长为梅行素或林道静,由此进入男权规定的秩序与规范之中。 庐隐、冯沅君呼喊的声音仅盘旋在五四时期;冰心、丁玲无不站在男性启蒙者的视角书写女性;张爱玲、苏青、梅娘关于女性的书写长久以来仅被纳入通俗文学加以考察。 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书写中,萧红被视为左翼作家中并不算成功的一个。 她的《呼兰河传》被选择性遗忘,对《生死场》的评价大多指涉“国土沦丧的愤懑和生活颠沛的痛苦迫使他们写出了反日的作品”[12],萧红关于女性身体经验的书写更是被无限遮蔽。
三、“生”“死”“场”:乡村“恶托邦”图景
如果说女性写作空间已经被男性话语无限挤兑,女性作家无法逃离“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写作,那么萧红则探索了一条独特的女性写作路径。萧红出生在东北一隅的呼兰河畔,地理的边缘性让她极度渴望外面的世界,上学、读书构成了萧红渴望逃离家庭甚至家乡的重要原因。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疾病让她笼罩在巨大的寂寞之中,她极度渴望并轻易进入亲密关系,但对待怀孕、生产、成为母亲却极为冷漠,这并非传统女性价值的观念。作为作家,她与一众左翼作家关系密切,却又主动疏离左翼文学圈。 萧红似乎始终逆潮流而动,包括试图在男性话语挤兑中的狭窄空间建立女性写作,而不断挣扎与沉浮的女性身体成为她的言说途径,基于此,萧红也构建出承载着“生”与“死”的乡村恶托邦场域。 美国学者萨金特对“恶托邦”(dystopia)下过这样的定义:“一个与读者处于平行时空的虚构社会,作者意在通过细致的描写,展现一个比现实社会更加险恶的世界”[13]。 在萨金特看来,“恶托邦”是消极的乌托邦。 从鲁迅开始,乡村一直是五四新文学作家关注的焦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使得诸多作家笔下的乡村呈现某种奇观色彩,他们书写乡村时大量使用血腥、疾病、死亡等意象,这使中国传统的“桃花源”式乡村消隐,乡村荒野景象凸显。 而性别身份使萧红笔下的乡村呈现出异质性特征。 如同许多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一样,命运的安排让萧红经受疾病的考验,也让萧红将身体、精神病痛与时代之“病”产生共鸣。 而萧红的意义不止于此,其作品将民族—国家、阶级、性别等多重矛盾融注于文本之中,并通过自身的疾病体验书写女性经验,由此铺展乡村恶托邦图景。
在萧红笔下,女性身体成为指涉生死意义的场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诸如生殖叙事长久以来被视为隐秘的文化禁忌,这同上文“妇女即疾病”的表述并无二致,它在男性作家笔下转化为爱情或婚姻的宏大话语,而生殖、生育等指涉女性身体的表述成为藏污纳垢的部分被有意遮蔽。 萧红撕破了笼罩在其身上的权力话语面纱,借以书写女性的生存、生殖、疾病与死亡探讨女性身体的意义。 如果说诸多现代作家的写作主题是生活,那么萧红描写的则是生存的故事,并借助书写乡村思考生命的意义。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明确表示:“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 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萧红在写作对象中融入了她对人生悲剧的理解,同时融入了萧红自己的个人感受,萧红带着某种冷漠甚至略带调侃地看待“生”与“死”,将自身的宿命感投射于作品与人物中,这使得萧红的作品深度远超同时期作家。 刘禾认为,“对于萧红来说,生命并非要进入国家、民族、人类的大意义圈才获得价值。 在女人的世界里,身体也许就是生命意义的起点和归宿”[7]480。 在抗战文学这一宏大主题外,萧红对女性经验的书写隐秘曲折地表达出女性遭受的男权社会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生殖同样是萧红写作的重要主题。 萧红在《生死场》第六章写到五姑姑的姐姐、二里半的婆子、金枝、李二婶子四位女性的痛苦的生产经历,而“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 在十三章,萧红用整整一章书写女性和动物一般的生殖,并将其命名“生产的刑罚”。 《王阿嫂之死》中,“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萧红在小说《弃儿》中同样写到过自己经历的刑罚:“芹听不清谁在说话,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像被抽断一样。 她流着汗,也流着泪。”[14]她自述自己“像龃龉的包袱或是一个垃圾箱”。 女性身体,尤其是下体的裸露,在“身体写作”中常作为被窥视的审美对象,但萧红将其视作生命困境的表征。 两次非正常生育让萧红感受到女性不能节制生育和被迫生养的痛苦,因此萧红将惯常的女性生殖、生产称之为“病”。经历痛苦与遭受漠视让她倍感孤独,也促使萧红和她笔下的女性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也由此揭示出乡村女性独自面对此种体验时孤立无援的生命自处状态。
除了生存与生殖,在这片土地上还有疾病与随之而来的死亡。 福科在《规训与惩罚》中谈到“从运动、姿势、态度、速度等各个环节对身体施加‘微妙的强制’,不断征服身体的各种四处乱串的力量”[15],作为“裹小脚”的延续,权力对女性身体实行着方方面面的控制。 在乡村,作为受压迫最深的女性,小团圆媳妇被惩罚的原因在于“没有团圆媳妇的样子”,爱说笑被视为道德的放荡,进而被指认为疾病。 婆婆花了大钱为小团圆媳妇治病,希望将健康的女性身体转化为驯顺而萎靡的女性身体。 “美丽的月英下身慢慢腐烂,成为载满蛆虫的躯体,仿佛美丽的女性注定遭受某种诅咒,其美丽而空洞的肉体不再具备生殖的属性与功能只能慢慢枯萎。”金枝说:“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实际上,萧红在借金枝之口思考乡村底层女性的生命价值。 在萧红笔下,女性的特征、欲望慢慢萎缩、枯竭,进而被压抑、遗忘终将成为“空洞的能指”。 对女性身体的规范是对身体、道德的双重约束以此达到启蒙与强国之功效。月英与小团圆媳妇的意义绝非仅对乡村百姓命运的观照,女性身体功能的退化和腐烂既是对权力社会的反抗与颠覆,更是对救赎的祈求与召唤。萧红拒绝将女性身体看作承载民族积贫积弱的容器,意在将其真实还原。 这与其说这是对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悯,不如说这是对女性工具性作用的体认。 这与其说是对启蒙话语的呼应,不如说萧红依托自身经验构建了独特的女性写作空间。
上文论及男性将启蒙与兴亡问题隐喻为疾病,以此完成其性别政治话语表述。 祥林嫂、春宝娘等一系列乡村妇女在启蒙知识分子笔下成为国民麻木与愚昧的受害者,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李七嫂遭受的凌辱成为抗日宣传的表述,女性身体遭遇的迫害被编码转喻成国家被暴力入侵。 于是,女性声音如果不想被遮蔽只能另寻话语的构建方式。 萧红在被无限挤兑的话语空间中敏锐地用动物隐喻女性的生存状态。 “作为人之拟态对象的那些动物,同样没有等级差序,除了马、牛、猪、狗之类的乡村日常动物外,频繁出现的还有鱼。 而且鱼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专属于女性的拟态对象。”“不仅止于鱼与妇女在‘态’性上的相似,或许,在萧红的潜意识里,还不自觉流露出了动物等级的差序。”[16]也基于此,萧红笔下的故土呈现出“恶托邦”特质。 在这片土地上,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人退行成某种动物成为荒野景观中的“前存在状态”,乡村中女性身体则成为“生”与“死”意义生长的场所。 萧红有意将女性“拟态”为低等生物,与原始生殖崇拜建立联系,揭示乡村女性的生存困境。 她拒绝了桃花源式的乡村乌托邦想象,着力于乡村“恶托帮”书写,让人看到一种始终比当下更为恶劣的乡村图景和人性状态。
结语
萧红将自身的疾病体验投射在中国乡村女性这一整体上,并借助女性身体完成对自我的观照。就此,“生”与“死”不仅意指民族兴亡,更指向个人尤其是女人,而其意义生长的场域也不仅在于土地、家园,更加指向女性身体本身。 从自身经验出发,萧红和她笔下女性的身体不是抽象的“人之躯体”,而是负载和感应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女性之躯体。 萧红透过个人的“疾病”体验之“痛”抵达文本之“痛”,使人们由这些女性的身体疼痛感受到中国乡村的“疼痛”。 萧红的乡村书写,经由特殊时期乡村女性的生存与斗争经验,图解整个中国乡村的苦难历程,最终抵达近代社会进程中中国农人的生存境遇。 这不仅是作者悲悯情绪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乡土世界的终极关怀。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