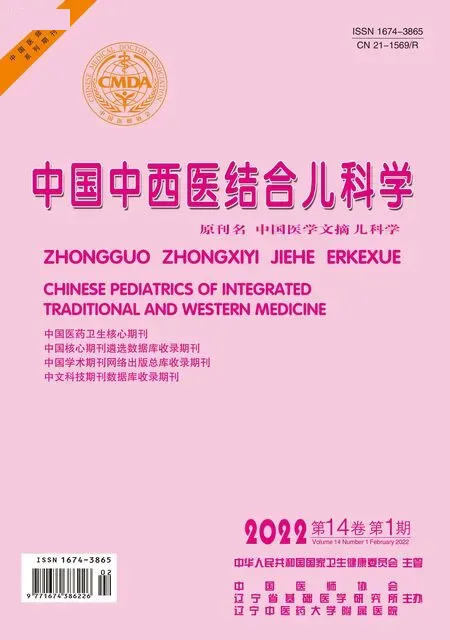贾六金教授治疗儿科脾胃病常用对药举隅
曹霞, 张焱, 贾六金
对药又称为药对,始见于《内经》,首创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临床常用的相对固定的一种特殊药物配伍形式,是中医传统经验证明了的优化组合,也是“中药配伍中的最小单位,其组成简单,但具备中药配伍的基本特点”[1-2]。全国首届名中医贾六金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悬壶三晋六十余载,强调辨证,提倡组合思维,临床善用组方对药,疗效良好。笔者有幸作为继承人伺诊学习,受益颇多,现将其儿科脾胃病部分常用对药整理浅析如下,以见一斑。
1 常见对药
1.1 枳实、白术 《金匮要略》载有枳术汤,《内外伤辨惑论》录有枳术丸。仲景用做汤剂,枳实为君,辅以白术为臣。东垣用做丸剂,白术为君,辅以枳实为臣。前者为汤剂,主消散,用治近心处坚硬胀满,形如边缘平整之圆盘;后者用丸剂,主补益,主要治痞,消食,强胃。
贾教授结合小儿“脏腑娇嫩”“脾常不足”的生理特点,临床取张元素“养正积自除”之意,用白术倍于枳实组成对药,达健脾行气除痞之功。脾胃虚弱甚者,枳壳易枳实,既下气宽中,又和缓不伐脾气。此药对多用于脾胃系疾病厌食、积滞、腹痛、疳证等辨证为脾虚兼有气滞食积者。白术苦甘温,归脾、胃经,可补益脾胃、和中、燥湿消滞,《医学启源》称其“去脾胃中湿,除胃热,强脾胃,进饮食,和胃。”《本草通玄》谓:“补脾胃之药,更无出其右者。”枳实辛苦寒,归脾、胃、大肠经,可消胀满、导滞消痞、消化胃中所伤,《汤液本草》有载“非枳实不能除痞”。两药相辅相成,补消结合,寓消于补,守中有走,相互为用。费伯雄《医方论》赞其“一补脾,一去实,简当有法,勿以其平易而忽之。”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表明,单味枳实与白术均有助于调节胃肠的运动,但是两药配伍之后效果更佳[3]。
枳实、白术配伍精当,疗效卓越,且在临证中衍生出众多方剂。如加木香、橘皮等理气药治疗气滞、痞满胀痛较甚者;加神曲、麦芽等消食药治疗脾虚气滞兼食积内停者;加大黄、黄芩、黄连之三黄枳术丸,主治湿热积滞壅塞于肠腑,有消积导滞、清利湿热之功。此外,还可在辨证基础上加温中化痰药、泻下药、活血药等治疗对应疾病,扩大了应用范围,是儿科脾胃系疾病中常见对药。
1.2 苍术、白术 《张氏医通》二术二陈汤,首载苍术、白术配伍,主治脾不运湿、痰湿不化,功以运脾除湿。白术味甘长于健脾和中,通过振奋脾气而除内湿,但燥湿之力不及苍术。李杲曰“白术味苦而甘,性温,味厚气薄,阳中阴也,可升可降。”苍术苦温,气味苦烈,擅燥湿除水,水湿去则脾气得健、太阴得安。李时珍认为“苍术阴中阳也,可升可降,入手太阴、阳明、太阳之经,足太阴、阳明。”张隐庵《本草崇原》云:“凡欲补脾,则用白术;凡欲运脾,则用苍术。”黄元御也云:“白术守而不走,苍术走而不守,故白术善补,苍术善行。其消食纳谷,止呕住泄亦同白术,而泄水开郁,苍术独长。”故苍术为运脾燥湿止泻之首选,白术为补气健脾第一要药。
尊钱乙“脾主困”的学术思想,结合小儿脾胃病证“脾常不足”“胃小且脆”的生理特点,发病容易、传变迅速的病理特点,虚实夹杂、寒热错杂的临床特点,贾教授重视小儿脾气易困遏之特质,治疗以恢复脾胃纳运、升降功能为要。补脾同时尤重运脾,益气之余不忘行气理气,常苍术、白术同用,主治厌食、积滞、呕吐、泄泻等属脾胃虚弱、脾虚夹滞者。取补运兼施之意,目的在于除脾困、展脾气、复脾运,现今儿科临床已得到广泛应用。贾教授还强调,苍术属辛苦刚燥之品,久用恐有劫阴之弊,故脾失健运已有阴伤表现者,不宜继续使用。
现代药理研究也发现,白术和苍术都有调节消化、心血管、神经系统及抗炎抗菌的能力,这与健脾和胃、温中安神的中医疗效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白术中所独有的多糖及氨基酸类化合物成分,是其补脾增益效力更强的原因[4]。
1.3 砂仁、白豆蔻 砂仁辛温,归脾、胃、肾经,有化湿行气、温脾止泻之功,《中华本草》赞曰“和中之品,莫如砂仁,冲和调达,不伤正气,调醒脾胃之上品也[5]。”白蔻仁是姜科植物白豆蔻的果实,辛温,入肺脾胃经,亦有化湿行气、温中止呕的功效。砂仁尚能理气安胎、固精止泄,气滞明显者用之,其气浊,专于中、下焦。白豆蔻芳香而气清,专于中、上焦,湿重者多用。
脾为后天之本,小儿生长发育过程中对水谷精微的需求旺盛,与小儿脾胃形质、功能产生矛盾会影响脾升胃降、脾运胃纳。湿邪最易困阻脾胃,脾虚生湿,脾虚湿困,湿浊重者,可弥漫三焦。贾教授临证首重脾胃的治疗,认为脾胃健则五脏安、后天和则百病愈,以养中、和中、调中之法,使升降相合,燥湿相宜,纳运相济。砂仁、白豆蔻皆为芳香之品,贾教授强调二者相伍使用,功效倍增,三焦并治,适用于脾胃虚寒、气滞湿阻中焦者,以腹痛泄泻、腹胀食少、恶心呕吐、胸脘痞闷为主要表现。合用既能宣通三焦气机、芳香化湿,又可醒脾开胃、行气止痛。
临证尤要注意,砂仁还有消除痰浊之功,可用于痰气互结、胸膈胀闷。正如张介宾《景岳全书》所述,可以:“快胸膈开痰,平气逆咳嗽。”清代汪绂《医林纂要·药性》提及砂仁“润肾、补肝、补命门,和脾胃、开郁结”,故补肾药中酌加砂仁,可引诸药归肾。现代研究表明砂仁具有胃肠保护(抗溃疡、促进胃排空促进胃蠕动、对胃肠细胞生物电活动的影响)、镇痛、抗炎、止泻、调节菌群、降血糖、抗氧化等药理作用[6]。
二者煎煮时壳和种子须破碎后入药,白豆蔻后下煎煮数沸即可但不宜超过2 min,《古今医统大全》和《炮炙大法》“数沸则起”观点可取;砂仁后下宜煎煮3~6 min但不宜超过8 min,此时汤液中相关有效成分的溶出总量相对较高,可最大发挥相关汤剂的疗效[7]。
1.4 焦三仙、炒莱菔子 焦山楂、焦神曲、焦麦芽,三药皆入脾、胃经,合称焦三仙,能增加消食导滞能力,可化谷、面、肉诸积。山楂为消油腻肉食积滞的要药,2015版《中国药典》载有“焦山楂消食导滞作用强”。神曲消食和胃,化水谷宿食,《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认为“麸炒六神曲健胃理脾作用强,焦神曲消食化积作用强”[8]。麦芽最早收录于梁《名医别录》:“味咸,温,微寒,无毒。主治消渴”[9],明《本草纲目》记载:“麦芽,皆能消导米面、诸果食积[10]。”莱菔子归肺、脾、胃经,辛、甘、平。能消食化积、除胀行滞,面食积滞必用,且有降气化痰之功。贾教授用两句话概括:伤谷二芽宿神曲,肉滞山楂面莱菔。
小儿伤乳伤食,停滞不化,出现不欲乳食、腹部胀满、大便不调,导致积滞。其表现如《医宗金鉴·幼科·积滞门》所载:“小儿食积任意餐,头温腹热便脓酸,嗳气恶食烦作渴,大安承气审宜先”,故小儿乳食壅积或有积滞化热者,可用此对药消食导滞,消者散其积,导者行其气。诸药相须为用,损其谷,消其滞,攻其积,运脾气,生胃气,舒肝气,使纳运升降功能恢复正常。临床要注意,脾胃虚弱无积者慎用,即使有积滞,亦不能多服、久服,以防伐脾胃生发之气。
实验研究发现,焦三仙炒焦后产生的焦香物质(包括焦香气味物质在内的美拉德反应产物)有促进消化的作用,其与其他化学成分(如有机酸等)协同作用,通过促进胃肠平滑肌收缩、促进消化液分泌、中枢神经刺激及“脑肠关联”机制等,增强“消食导滞”的功效[11]。
1.5 草果、干姜 草果性温味辛,专入脾胃两经,乃中焦之专药,功能燥湿散寒、除痰截疟、消食化积。李东垣《医学入门·本草》曰:“温脾胃而止呕吐,治脾寒湿、寒痰之剂也。益真气,又消一切冷气膨胀,化疟母,消宿食,解酒毒、果积,乃其主也,兼辟瘴解瘟”[12],其中特别提到消果积。临证应用本品,多宗前贤之经验,亦多有发挥。根据报导,本品单用对于腹胀的治疗效果十分显著[12]。
干姜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认为其“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湿痹,肠澼,下利。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气,通神明[13]。”《得配本草》也载其“辛,热。入手少阴、足太阴经气分。生则逐寒邪而发散,熟则除胃冷而守中。开脏腑,通肢节,逐沉寒,散结气[14]。”药理研究证明该药含芳香性挥发油,对消化道有轻度刺激作用,可使肠张力、节律及蠕动增强,从而促进胃肠的消化功能[15]。
贾教授临证常用此对药治疗癖积,癖积多因恣食生冷瓜果,损伤胃气,阴寒之邪得以乘之,脾不及化,余滞不消,并胃内汁沫搏聚不散,渐成癖积。主要表现为上腹不适,饱胀,隐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口臭等症状,结块较大者可在上腹部扪及移动性块状物。程度严重者,通过胃镜活检钳将结块捣碎,然后洗胃或用泻药将其排出;或腹壁外用手按摩挤压使结块破碎。程度轻微者可中医辨证治疗,贾教授主张消积导滞,渐消缓散,使结块溶解变小,自然排出。在四君子汤运其脾、消积丸攻其积的基础上,必加草果、干姜,两药合用,散其滞,温其寒,消其积,行其气,达消积除癖之功。贾教授强调,中医辨证论治多据病因病机而制定治法,而药对的组成又是治则治法的具体体现,本组药即体现温消相伍,行散相配,温法、消法并用的用药特点,随病情变化组方对药选择得当,疗效非凡。
2 经典医案
患儿女,5岁2个月,2020年6月10日初诊。主诉:纳差3月余。患儿自幼脾胃虚弱,纳食一般。3月前过食糖果糕饼后症状加重,食欲不佳,食量较前减少约一半。睡眠可,小便调,大便稍干,2~3日一行。舌质淡红,舌苔白,脉细。查体:体质量15 kg,身高107 cm。精神一般,面色欠华,腹软,肝脾未及肿大,叩之呈鼓音。中医诊断:厌食(脾胃不和)。治以燥湿健脾、行气和胃,药物组成:炒苍术、厚朴、陈皮、砂仁、木香、枳实、白术、白蔻仁、莱菔子、鸡内金、连翘、炒三仙各10 g,甘草6 g。12剂,水煎服,日1剂,分早晚2次空腹温服。
2020年7月13日二诊。患儿食欲改善明显,未再服药,体质量增长2 kg,原方继服1个月。半年后随访,家长告知患儿目前食欲佳,生长发育良好,各项指标均已达标。
按:脾胃纳运功能失常为厌食的发病机制,轻症患儿体质量、身高等生长发育指标多正常或稍低,其他症状较少,虚象不明显。本案患儿初诊时除食欲不振、大便稍干外无明显不适,体质量、身高略低于标准值,符合厌食的诊断标准,治以运脾开胃,予贾教授常用对药加减获效。方中有枳实与白术、苍术与白术、砂仁与白豆蔻、焦三仙与莱菔子等对药,体现消补并用,补运结合,温散相伍的特点,终使脾胃纳运相和,升降相宜,燥湿相合而收功。
3 讨论
贾教授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结合小儿脾胃生理病理特点,深入体会中药配伍规律,使用对药扩大治疗范围,通权灵变,临证常获奇效。临床强调对药使用得当,不仅能发挥药物自身功用,还可使药物之间相互制约、减轻毒性;相互协同、相辅相成。在脾胃病辨治中,尤多用对药,标本同治,消补并用,补运结合,温散相伍,使脾胃纳运、升降、燥湿功能恢复正常。病证契合,药随法出,见效亦著。本文数则对药既是对先贤经典之继承,又是贾教授临证经验所悟之创新,提示我辈要深入体会中药配伍规律,及时总结名老中医药专家的验方对药,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特色,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