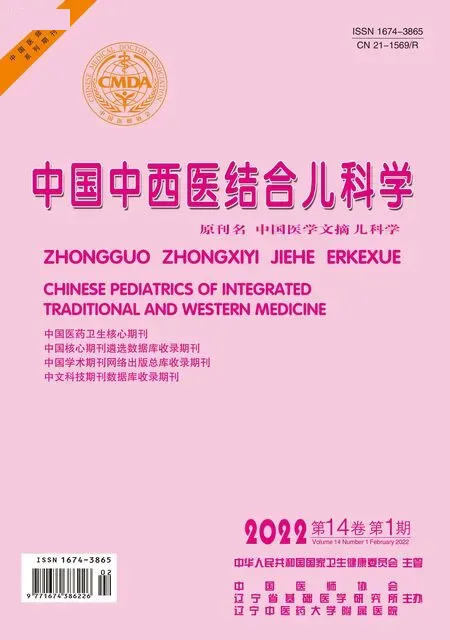从“肝生血气”论治儿童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张亚茹, 张蒙蒙, 邢露露, 翟文生
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是一种因免疫功能异常介导的骨髓造血干/祖细胞缺陷而引起的外周血全血细胞减少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症[1-2],发病率高,治疗缓解率及10年生存率均较低[3],其主要表现为贫血、出血和感染综合征。依据其起病缓急,儿童再障可分为急性再障和慢性再障[4],慢性再障发病缓慢,病程长,病情反复,是难治性血液疾病[5],其感染、出血症状较轻,以贫血为主要表现。现代医学主要采用免疫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及对症处理措施,其中免疫抑制治疗是再障最重要的药物治疗方法,但目前疗效欠佳[6],长期用药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发生率高,易复发[7],且对患儿身心发展尤为不利。中医治疗在提高疗效、减轻并发症、降低西药不良反应、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显著[8-9]。
中医古籍没有关于慢性再障的记载,现代中医根据患者贫血、出血、易感染的临床表现将其归属于“虚劳”“髓劳”“血虚”“内伤发热”等范畴[10],《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载:虚劳“面色白,时目暝,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责之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兼或不兼外感邪毒,多以“虚劳血虚”概括诊断[11]。
肝生血气理论出自《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以生血气。”虽言儿童慢性再障为“虚劳血虚”,然血与气者,相因相成,荣损一体。治疗再障,不仅要补血虚,还要益气虚,血虚者,补其脾肾,气虚者,益其肺脾肾,而肝同时与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密切相关,又有小儿肺脾肾不足,心肝有余,且虚则补母,温肝即养心,故曰,小儿再障之气血生化,脾肾为之本,心肺为之主,肝为之动、为之因、为之机。现遵其经义并后世医家观点,结合儿童慢性再障之病因病机,探析肝生血之作用机制。
1 应春而生血
《素问·五常政大论》言:“敷和之纪,木德周行,阳舒阴布……其政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脏肝……其应春。”即肝生血气是因为肝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春气生发,万物俱荣,人体感应春气,肝气得春之启迪正常升发而后启迪诸脏[12],诸脏之气生生有由,生机不息,气血顺其生发之性而旺盛;且儿童为稚阴稚阳之体,生长发育迅速,合春之机,药物得当,随拨即应。
肝应春之机,生理上生血气、性升发,其病理当分太过不及,于儿童慢性再障而言,太过者,“上”则可能出现齿衄、鼻衄等血气逆证,“下”则皮下出血、便血等;不及者,气虚、气郁也,气虚则血虚,则懈怠乏力、面色苍白、头晕目眩等,气郁则血滞,则忧闷、烦躁、发热等。
2 藏血且生血
肝藏血是指肝具有贮藏血液、调节血液运行和防治出血的功能[13],出自《素问·调经论》:“夫心藏神……肝藏血……而此成形。”肝藏血,涵养肝气,濡养形体官窍,且根据机体活动量的增减、情绪及外界气候变化等因素调节人体各部分血量的分配。李念莪在《内经知要》中认为“肝为血海,自应生血,肝主春升,亦应生气。”此处则把肝生血理论和肝藏血理论相联系,表明肝为合成补充和代谢交换血液营养物质的重要场所之一[14],以充足的血量以及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保证血液营养物质的合成储存和代谢交换[15]。
3 疏泄以生血
脾肾为先后天之本,主人体一切虚弱劳损,治虚必不离脾肾。然则肝主升主动,脾主运主化,脾困不健,肝木疏达脾土,助后天气血生化之源[16];肝肾同居下焦、同寄相火、同根同源,肝疏助肾藏,助先天精血生成之本,脾肾生气生血之功,肝之力不可或缺。且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主于肺,即气血化生,必不离心肺,心肺生血气,必不离肝。《灵素节注类编·阴阳脏腑总论》有言:“是故不足,则以相生者助之,如补肝助心之类”,即肝的生发助心火化赤为血;“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肝升助肺降,气机可调匀[17];“呼出乃心肺也,吸入乃肾肝”,肝肾的摄纳助肺主气,形成宗气,促血的化生。故气血化生,以肝为先导,脾肾为基石,心肺为辅翼。
可知,肝应春之机促气血生化,肝藏血助化生血气,肝助他脏以生血,其促生、生发及催生之功,为临床从肝论治再障提供了理论基础。
4 调肝生血,养肝藏血,五脏和合,以治再障
儿童慢性再障以贫血为主要临床表现,兼见出血。血虚者,气血化生不及,气不煦血,血不濡气;出血者,气血功能失调,气不摄血,血不随气。治疗必不限于肝,不拘于脾肾,不离于心肺,故以肝为先,和调五脏。
4.1 调肝之气,舒肝之性,促气血生化之机 肝应春,为血液的产生提供了一个促生之机、之时,肝功失调,必失其时机,治则从其气为补,逆其气为泻,故以辛补之,以辛散之,柴胡是也。柴胡最先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录为“茈胡”,归为上品药[18],“味苦,平、微寒,无毒。主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本草图经》云:“二月生,其苗香,茎青紫,叶似竹叶稍紧……”;叶天士指出“柴胡轻清……春气一至,万物俱新。”柴胡得天地春升之性,入少阳以生气血,主推陈致新,其于表里、内外、上下、气血,凡气机所在之处莫不透达。故曰,调肝气,疏肝性者,柴胡也。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柴胡有调节血液凝固、调节免疫系统功能、改善肝功能、保肝降脂、利胆等功能,醋制柴胡可保护黏膜,抑制黏膜出血,加速损伤黏膜修复[19]。
4.2 柔肝之体,理肝之用,养血气化生之所 肝藏血,以血为体,以气为用,其体柔润,其用阳刚,即云肝“体阴而用阳”。肝气得血以充,肝血赖气以生;一身之血气又需肝之血气为疏。肝脏具有曲直刚柔的双重性,柔有冲和濡润之旨,不拘风木刚强疏达之能,不背肝木春生万物发荣之性。柔肝者,归、芍也;理肝者,柴、芎也。当归,甘辛温质润,入肝、心、脾经,味甘而重,功专补血,气轻而辛,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又兼补,为血中气药;白芍以其酸甘之性养肝阴、柔肝体、缓肝急,使肝气条畅,肝体柔和。二者均生血以养肝,养肝助生血。肝者,风木之脏,藏有形之血,疏无形之气。柴胡、川芎者,风药也,其性入肝,二者相须,既能畅达无形之气,又能藏泄有形之血,气顺血行,周身气机畅达,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疏其血气,令其条达”也。当归对血液系统亦具有双向性调节作用,既促凝又抗凝,其主要效用成分当归多糖可有效改善造血微环境,改善造血干细胞数量及功能,又能对缺血损伤组织起保护作用[20-22];白芍的主要有效成分是白芍总苷,体内实验发现其具有降低血液黏度、抗血小板聚集、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免疫调节、保肝等多种生物学效应,并且毒副作用较小[23-24];川芎能改善微循环和抑制血小板聚集[25],川芎嗪可迅速透过血脑屏障,有利于在脑部发挥作用[26-27]。
4.3 以肝为先,和调五脏,达血荣气充之境 补血益气,不离肺之助、心之主、脾之源、肾之根,前述柴胡、当归、白芍入肝调肝,此为以肝为先,另佐陈皮理肺、肉桂温心、白术健脾、熟地附子补肾益精,则为和调五脏,论治如下:
以柴胡添一味陈皮,平金逆升木陷:清代赵其光的《本草求原》:“陈皮辛温更胜,故升而浮,能使肝引下焦之阳气以宣肺气”,柴胡、陈皮相使,疏宣有序,升降相因,顺肝升肺降之性,且陈皮又入脾胃,斡旋于中土之枢,升其升者,降气降者,因势而为,理周身气机之变。
以当归加一味肉桂,温肝木助心火:唐容川《本草问答·卷二上》“心火生血尤赖肝木生火,此是虚则补其母之义,故温肝即是温心。”又云“肉桂大辛,则大温,虽得金味,而实成为木火之性,故主入心肝血分,以助血之化源。”当归、肉桂二药,均为入肝助心生血之品。
以白芍伍一味白术,土中泻木,成脾土之化:《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土得木而达之”。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因于脾之运化及肝之疏达。白术,味甘苦,性温,归经脾胃,一则甘缓苦燥,能健脾胃、运精微、补气血、养心神,二则质润气香,能温运脾胃,益气燥湿。白芍柔肝之性,防肝疏泄之变,术芍同用,疏肝理脾,另有黄芪、党参相佐,助气血生化之源。
再有熟地配上附子,乙癸双生,全肾精之治:熟地黄,味甘,性微温,归肝、肾经,可补血养阴,填精益髓,“专补肾中元气,兼疗藏血之经”;淡附片,辛热助阳化气,温肾阳,化寒水,且“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追散失之元阳;引补血药入血分,以养不足之真阴”;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大量熟地配少量附子,蒸精髓以化血气,补一身阴阳之根,理精髓血气之本。
亢害承制,制则生化,盛损虚养,养则全形,诸药共举,肝升则肺降,肝温则心旺,肝达则脾畅,肝泄则肾藏,木得曲直,五脏皆和,血气乃安。此外,现代研究表明,再障常合并肝功能损害,或互为因果,应酌情选用护肝药物[28]。
儿童慢性再障亦可见发热,发热有外感内伤之分,其在表者,汗而发之,治其卒病,顾其痼疾,在此不予赘述;其内伤者,当责五脏血气阴阳之不足,随证用药,简述如下。气虚发热者甘温除之,柴、术之属酌加参、芪,血虚发热者,宜补气生血,黄芪、当归之用。病久及肾,则有肾阳不温,肾水不化,肾火上炎,虚而发热,且用熟地滋阴育肾水,附子温阳蒸肾阴,凭一味肉桂,挟裹肾水上行,引虚火之归元。研究表明,附子酸性多糖能增强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显著提高白细胞数量,具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且对环磷酰胺所致骨髓抑制有较好的抵抗作用[29];熟地黄醇提液有抗衰老和促进红细胞新生的作用,多糖能增强机体造血功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5-羟甲基糠醛能增强红细胞变形性[30];党参白术黄芪均可改善造血功能,提高免疫力,预防感染[31-33]。
综上,儿童慢性再障以“贫血”为主要症状,纠正贫血是治疗关键,出血为儿童再障气虚虚损及变生他病的重要原因,内伤发热亦可以气血失和一言蔽之,是故调肝藏血防出血,养肝生血治贫血,设生发之机推陈致新,调五脏之和化生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