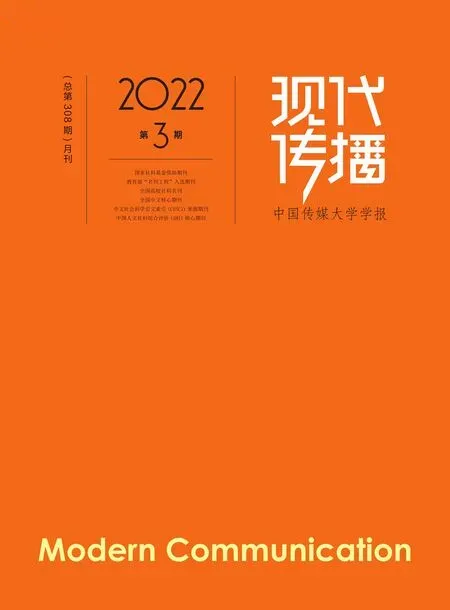拟像的“星丛”:短视频二次创作的批判性解读
王学成 杨浩晨
一、拟像:媒介历史维度下的一种批判性视角
拟像一词源于拉丁语单词“semulacre”,16世纪末期被纳入到英文语言体系之中,主要用于描述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对现实存在的事物的描摹和再现。当“拟像”进入社会研究的范畴后,具有了脱离事物原有面貌、自身不存在的特质和深度的影像的寓意。它主要包括两层涵义:其一是事物的影像;其二则是指假装的或是具有欺骗性的替代物。①在传播学的视域下,拟像是对媒介现象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人们媒介观的一种映射。拟像表现形式的嬗变反映着媒介形态的变迁,而其意义层面上的迁移则如同一面“媒介之镜”,折射出人们对媒介的认知与理解。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以“eidolon”指代物的形象和对某物进行的表征,它也被广泛认为是拟像一词的希腊文词源。②柏拉图(Plato)视现实事物为理念世界的摹本,而这一摹本还可以通过艺术品,即拟像的形态再一次表现出来。柏拉图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拟像的批判和否定态度,他将拟像视为具有偏离性因素的不完美的摹本,认为“它只是运用拟像而形成了相似性的外部的、无效用的结果”③,基于模仿而形成的拟像“既不可能拥有真知,也不可能拥有正确的意见”④。因此,在柏拉图的笔下,拟像成为对艺术作品这一试图以写实手法反映现实的媒介的批判工具。在宗教秩序主导下的中世纪社会,基督教文化不仅将画像、雕塑视为拟像,还认为人(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产物)的存在也是一种拟像。这种“只保留了外在影像却丢失了内在相似性”的拟像与柏拉图的拟像观一脉相承。因此,尼采将整个中世纪基督教视为柏拉图主义的变种。基于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他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拟像观,认为“距真实存在者越远,它就越纯、越美、越好”⑤。由此,拟像的地位发生了倒置,从柏拉图笔下的虚假影像转换为具有自身实在性的存在。不仅如此,拟像地位的提升代表着真实与虚假之间的藩篱被打破,差异性主导的运动与变化的世界取代了同一性主导的静止的理念世界。
随着广播、电视等一系列电子媒介的兴起,影像成为了图像传播的重要形态。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将拟像视为媒介操纵、控制大众的一种表现,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其媒介批评理论:“电视广播传媒提供的、被无意识地深深解码了并‘消费了’的真正信息,并不是通过音像展示出来的内容,而是与这些传媒的技术实质本身联系着的、使事物与现实相脱节而变成互相承接的等同符号的那种强制模式。”⑥由此,拟像折射出的是符号对真实的抽离和重塑,而拟像本身既是媒介权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同时也成为了鲍德里亚建构社会批判思想的载体。
当鲍德里亚借对拟像的批判而哀叹真实的消亡时,人类社会正处于广播电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而随着媒介技术不断进步,影像生产技术与互联网的融合营造了现实与虚拟相互交融的世界。其中,短视频的兴起更是为媒介格局带来了解构和重塑。短视频二次创作是基于对既有的内容素材进行剪辑、配字幕、配乐等手段,形成新作品的一种影像创作手法。它短平快的传播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叙事结构,不断强化着碎片化的传播环境,其强互动性和传播力掀起了一场全民参与式的影像盛宴。在此背景下,短视频何以生产符号?如何作用于人们的认知并影响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这些问题使影像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再度成为一个重大的议题,而对这一议题的探讨又应合了拟像所具有的符号表征以及社会再建构意义。因此,拟像的视域为剖析短视频时代之下的新媒介现象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
二、拟像的“星丛”:基于短视频二次创作形成的新媒介现象
拟像以符号的抽象性特质抽取、消解进而重构真实,将人们带入到一个高度仿真却又独立于现实之外的超真实之中。而图像作为“重组”社会现实的符号经历了由绘画等艺术作品到数字化影像的进路,短视频即是数字化图像创作工艺与大众审美需求相碰撞、融合的新兴媒介形态。同时,短视频二次创作也揭示了拟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呈现出的新形态:一种“星丛”式的发展格局。
“星丛”是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在《德意志的悲剧起源》中提出的概念,他以夜空中松散而同时具有相互连接的群星为喻体,指涉一种去中心、非同一性的状态。⑦而这种比喻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社会思想中亦有所体现。在《恶的透明性》中,鲍德里亚展望了符号价值的最终走向,他以微观物理学意义上的粒子运动为隐喻,指出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符号的价值最终走向一种分形阶段:在媒介编码原则主导下,拟像物的生产呈病毒扩散式发展,“在模拟的天空中闪耀片刻,画出一条折线”⑧。由此可见,“星丛”是一种基本状态、一种内部构造,同时也是一种运动轨迹。基于短视频二次创作而生成的新“拟像世界”同样具有星体运动开放性、发散性等特征,这种“星丛”式的发展格局具体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拟像生产体系的“星丛”式开放状态。就物理层面的宇宙系统而言,星丛并非是闭合空间内的单一物质的集合,而是由繁杂庞大的各类星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开放系统。“星丛”自宇宙中漂流的混沌物质之中产生,并不断吸纳着外来的新物质。同样,互联网的开源性消解了媒体机构对传统影像生产的垄断,短视频平台的井喷式涌现、视频制作剪辑工具的普及抹平了影像生产的门槛,使短视频二次创作成为开放式的创作广场。由此,拟像不再囿于媒介机构的固定圈层,而成为在一个开放状态下不断扩散的“星丛”。
二是短视频参与者的星体式的去集中化分布。在传统影像传播环境下,媒介机构是影像的生产与传播者,图像、影像的大规模生产“压制、弱化并最终消解了大众”⑨。与之相对,短视频二次创作颠覆了这一传受关系。短视频作品的传播高度依存于社交媒体平台,而这些平台上海量用户的生产与传播能力使“拟像世界”的基本秩序完成了由集体观看的垂直链条到集体参与的去中心化格局的范式转变。正如星丛内部并不存在“中心控制”的力量,各类星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而形成星丛系统一样,短视频二次创作将拟像的生产结构由鲍德里亚笔下符号的“强制性整合”转化为大众的“主动参与”,使人以具有主体性的姿态生存于拟像的“星丛”之中。
三是拟像世界的“星丛”式运动,即非单向的发展轨迹。对于“星丛”而言,其内部的各星体和物质时刻处于不间断的运行状态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鲍德里亚笔下基于图像的仿真而形成的拟像世界即是作为整体而不断运动发展的“星丛”,但这一进路之下的拟像世界因媒介组织单向虚化进程导致了真实的消亡。而短视频二次创作中用户的广泛参与形成了影像生产与现实的交相辉映,这种符号生产的技术属性与用户的生产与传播的融合使得拟像世界的运行呈现出一种非单向度运动的“星丛”式轨迹。
三、“星丛”的生成:拟像视域下短视频二次创作的内在逻辑
对“星丛”而言,从吸收转化物质到星体间的排列布局再到形成在宇宙中的运行轨迹是其运动发展的进路,而拟像视域下图像如何摹仿现实、主体如何参与其中、拟像世界如何发展也同样是其生产中最为核心的三个命题,下文将由此对短视频二次创作中的拟像生产展开具体分析。
(一)个性化戏仿:双重内爆开辟“星丛”空间
对于拟像生产而言,媒介机构依据特定的编码逻辑将社会历史、事件整合为符号,并在不断复制之后以图层、影像的形态呈现在大众面前,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这种符号的无限复制及其结果称为“内爆”。“内爆”在物理学意义上指事物内部发生聚爆,进而消除了事物之间界限的进程。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世界的内爆使媒介与信息之间的边界被模糊,以至于媒介本身就是讯息。鲍德里亚在此基础上对“内爆”作出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内爆是对原因模式、决定的差异模式及其肯定和否定的控制的吸收。”⑩
在短视频二次创作中,个性化戏仿通过借用、延伸与发挥的方式取代了传统媒体时代的集中式采编。戏仿使原作的内涵被消解和重构,对原作、戏仿的重复与扩张形成内爆,进而开辟出了拟像“星丛”的空间。
其一是拟像之于原作的内爆。当原作中的内容以片段的形式被置于短视频的框架中时,其原有的内涵也同时得到了重构。短视频二次创作以剪辑、删减和拼接的方式对原作或现实事物进行抽取、剥离与再现。除内容的大幅缩减之外,原作、原事件中的线索、铺垫以及情境的完整性也随之被打破,原有的逻辑整体性为一个个孤立的、互不统属的“精彩片段”所取代。与星丛初诞生之时对物质的吸入和重组相类似,二次创作使原内容的主题、逻辑和结构被消解,这正是影像内涵的第一重内爆。
其二是拟像在不断外延之中的再内爆。模仿性是根植于拟像生产的内在逻辑,图像、影像对现实的摹仿性生产决定了它一直以来处于“赝像”的地位。当拟像以艺术品为载体时,手工劳动为创作者在拟像生产中提供了一定的主观性空间,而机械复制和数字化生产则通过高精度的复刻完全抹除了差异性存在的空间。对于短视频二次创作而言,融入创作者自身社会背景、认知框架和观念的戏仿行为不仅重新在摹仿中打开了创意的空间,更通过大众对摹仿品的再摹仿和再创新使“摹本”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反转:当戏仿被置于更具个性化、多元化主题背景的短视频二次创作框架中时,摹本亦成为了拟像生产的一个基点,进而发生了拟像生产的第二重内爆——摹本的一切内涵也在不断经历着重组,更为重要的是不再附着于原作,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创作和传播体系。
(二)弹幕互动:虚拟式共在营造非中心化“星丛”布局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曾言,“我无法构想一个我自身不在那里出现的可感的地方”。在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移动设备的屏幕打破了空间的界限,使真实和拟像纠葛在一起。在二次创作题材的短视频作品之中,具有强互动性的弹幕在影像作品中的嵌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沉浸式体验,并突破了现实与拟像世界的区隔。
弹幕作为观众参与影像传播的文字见证,实质上是一种虚拟的身份标志,短视频参与者发送的弹幕融入到影像之中,成为了短视频内容的一部分,在弹幕的刷屏式互动背后,二次创作指涉的对象甚至短视频内容本身不再牢牢占据人们的关注焦点,取而代之的是由弹幕互动创造出的、现实社会身份差异被剔除的“星丛”空间。
弹幕在连接身体与影像的同时也是观众情感的具象化载体,弹幕的嵌入使观众实现了情感的共在。短视频二次创作以现实事件或影视作品作为凭依,所有的弹幕互动均围绕着与之相关的话题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弹幕形式和内容上的共同性。同时,短视频中吸引受众注意力的节点的埋设使弹幕往往能够在同一时间刷屏式显示,由此实现了观看者、创作者相互之间全时空的虚拟共在。这种虚拟的情感交流、社会互动与短视频的主题有机结合,成为凝聚星体的重要作用力。
(三)“梗”的制造与传播:新社会语言助推“星丛”外向延展
星丛的发展不仅是由外向内的吸入,亦意味着由内向外的扩张,而助推其不断扩展、膨胀的因素是它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次创作生成的短视频作品通过网络媒介的广泛传播塑造了一个虚拟的拟像空间,而语言的辐射力量使它的影响力突破次元边界。在短视频扩张过程中,经由二次创作形成的“梗”构成了外向延展的动力。
“梗”最早是对喜剧节目中的“哏”,即娱乐性铺垫台词的误用,而随着它成为一种网络用语,“梗”已经成为了网络流行事物中的笑点的代名词。这些二创“梗”多源于为人所熟知的影视作品。如在电视和网络媒介上均广为传播的经典战争剧《亮剑》和拥有近30年历史、为各年龄段人群所熟知的日本动漫作品《名侦探柯南》等都成为了“梗”的出处。
二创“梗”经历了由影视作品对现实的原创式表现到短视频的改编再到广大受众的多元化理解的不断演变,这一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对社会现实不断剥离的单向外延,但人们对二创“梗”的创作和传播往往会融入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自己的亲身体会,从而使它的现实性不断强化。
二创“梗”以语言的形态扎根于人们的认知与思维之中,以其鲜明的大众化色彩而融入到短视频、互联网乃至社会娱乐文化中。由此,不仅是短视频作品的观看者,现实社会中的公众也如同被引力牵引的物质一样,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拟像的“星丛”,并使短视频二次创作以文化的形态根植在现实社会中。
四、意义的“热寂”:短视频二次创作带来的社会隐忧
本雅明以“星丛”为喻,畅想了一幅开放性、非控制性的社会关系图景,然而它并非是对稳定、和谐的“乌托邦”的绝对保证。“星丛”自身的运动深刻地嵌于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之中,在表象上的包容和多元背面,“星丛”的发展同样蕴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在鲍德里亚看来,星丛的运动与微观意义上的细胞运动类似,它往往“从稳定走向不稳定,这种发展过程充满随意性”,其结果可能会“导致与系统预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在物理意义上,星丛的不断扩张蔓延伴随着宇宙中“熵”的不断增加,当它达到临界值时,宇宙的运行亦由有序走向无序,最终使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运动或生命的能量存在。这一被称为“热寂”(heat death)的风险最终会导致宇宙的终结。从社会层面而言,“热寂”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作为社会产物的艺术创作、批判反思、文化语言等均陷于意义的虚无。
因此,在耀眼的星光——短视频二次创作空前流行的背面是社会意义层面的悖论:在空前广泛的参与者、空前丰富的表象之下,娱乐至上的内核、单向度的思维模式和渗透式的媒介暴力却导致了影像的意义危机。因此,在星丛的灿烂背后,是宇宙的“热寂”;在拟像的黎明背后,则是意义的“黄昏”。
(一)灵光消逝:“星丛”内核的庸俗化趋向
在本雅明看来,原创艺术品具有“灵光”,赝品或者仿造品反而烘托出了原作的价值。鲍德里亚则表明了拟像世界中“灵光”的消灭:“它(艺术)服膺于纯粹的图像的循环和陈腐的超美学。”在短视频二次创作所建构的拟像“星丛”中,“灵光”的消逝主要表现为影像内核的同质化趋向。在对一切事物进行二次创作并融入创作者乃至受众观念所营造出的题材多样化、内涵多元化的表象之下,对娱乐性的追求是它最本质甚至是唯一的内核。
娱乐至上的追求不仅取代了原作中的艺术性,也同时消解了创作者、观众的参与所注入的新内涵,进而使它沦为鲍德里亚所谓“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越来越少的世界”的缩影。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是二次创作的重要载体,这些平台在为短视频二次创作的兴起提供便捷条件的同时也形成了以流量为导向的创作环境,点击量带来的丰厚回报和粉丝量的不断提升营造出了一种“身处万众瞩目的中心”的体验。在这一目标的刺激之下,娱乐性作为受众接受度高、创作门槛低的一种元素,成为了迅速获取关注度的“捷径”。在娱乐主导下,具有整体性的原作被肢解为迎合受众笑点的欢愉片段,艺术作品应有的思想深度也为创作者的恶搞吐槽、观众们的纵情宣泄所取代。这一趋向使得短视频二次创作完成了由“创作”向“制造”的转变。拟像的“星丛”未能完成意义层面上对拟像的超越,反而消解了由创作者和受众共同营造新的“灵光”的可能性。
(二)泯然众人:情感共同体表象下的单向度陷阱
由观看者所发送的刷屏式弹幕根植于图像的呈现和传播中,弹幕围绕着影视作品这一共同的主题将不同时空下的人们凝聚起来,形成了一个突破时空限制的“情感共同体”。但是在这一“情感共同体”的表象之下,短视频二次创作却可能使人们的认知迷失在这一介于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赝像”之中,并逐渐丧失主体性,最终沦为“单向度的人”。
无论是原作还是对其进行二次创作的摹本,其最终意义都与现实社会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基于社会现实进行创作进而引导人们思考现实问题。短视频二次创作融合了原作、二次创作者、观看者的弹幕创作三重元素,形成了一个既独立于现实之外也不同于影像世界的“乌托邦”。虽然它具有现实与虚拟交融的性质,但当参与者通过弹幕深度参与到拟像的构建时,他们所关注、在意的既非现实也非与之相关的影像,而是由此构建出的“情感共同体”体验。这一“共同体”难以包容,甚至排斥个体性的思想。而弹幕互动构建“情感共同体”的功能意味着它更倾向于求同而非存异,在弹幕这一刷屏式的语言洪流之下,被裹挟在其中的人们难以表达不同的声音,也难以辨别何为本体和延伸,何为真实和非真实。由此,“拟像”之星丛的形成真正达到了鲍德里亚笔下媒介“再建构”现实的顶点:“它不再存在于外观的秩序中,而是存在于模拟秩序中。”同样地,人们的思考也被禁锢在这一乌托邦式的“赝像”之中,成为了原子式的存在。
(三)天下滔滔:话语绑架背后的媒介暴力
凯尔纳(Douglas Keller)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由符号所主导和支配的后现代社会中。在这一社会中,符号的生成、传递和演绎是拟像对现实再建构的前提,媒介对符号的垄断和控制消解了社会中“人”的意义,“形成了原子化的、核子化的、分子化的大众”。而在互联网环境中,短视频二次创作所建构的“拟像”之星丛使符号对社会公众的支配作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延伸。这一过程中,二创“梗”在网络和现实中的流行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将人们纳入到一个新的社会话语体系中。二创题材短视频拥有庞大的受众人群,但相比于整体网民群体和社会公众而言仍然只是小众群体。然而,随着网络媒介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人被纳入到“星丛”的引力范围,这些“梗”逐渐取代了社会话语体系中固有的表达方式,将社会中不与短视频作品直接接触的“大多数人”裹挟到由短视频二次创作建构的话语体系中。由此,二创“梗”以其病毒式传播、高频度表达实施了难以抵挡的话语绑架,完成了对现实的媒介暴力。伴随着这一媒介暴力以及相应的话语绑架,作为人文精神载体的语言也随之被重构。短视频娱乐化的本质为这些“梗”注入了恶搞性质的基调,这些恶搞性质的“梗”所具有的隐喻往往带有娱乐性甚至低俗性的内涵,不断解构着语言本应具有的艺术性、严肃性意义,进而使得语言的人文价值不断被消解。
注释:
① [英]DORLING KINDERSLEY:《牛津英语图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773页。
② 张劲松:《拟像概念的历史渊源与当代阐释》,《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37页。
③ Gilles Deleuze.LogicofSens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258.
④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3页。
⑤ [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9页。
⑥ Jean Baudrillard.SymbolicExchangeandDeath(Trans Hamilton Grant).London:SAGE.1993.p.75.
⑦ 潘可礼:《社会空间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⑧ [法]让·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王晴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