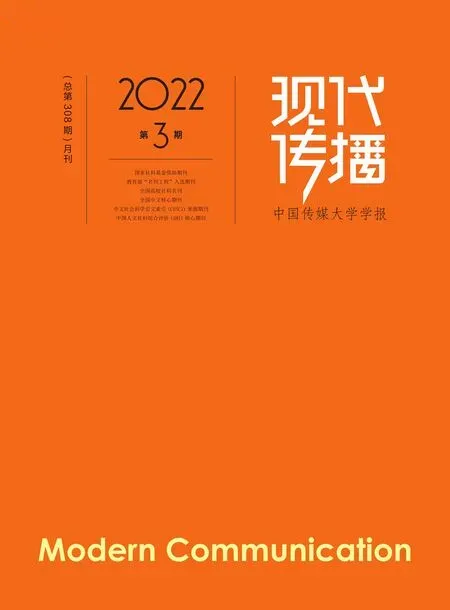后电视时代的媒介空间:建构、特性及反思*
顾博涵
新冠疫情期间,信息的作用变得格外突出,大众需要大量信息来加强对突发事件的了解,填补信息空窗带来的恐慌与焦虑。因此,手机、电脑、电视等媒介成为大众与外界沟通、了解信息、增强认知的重要渠道。其中,电视收视回升格外明显。根据国家广电总局节目收视大数据系统(CVB)统计,2020年“1月25日至2月9日,全国有线电视和IPTV较去年12月份日均收看用户数上涨23.5%,收视总时长上涨41.7%,电视机前每日户均观看时长近7小时”①。电视收视回升,观看人数与收视时间增长明显,电视重新迎来了高光时刻。基于此,本文从技术逻辑与空间逻辑的双重路径对电视回归现象进行分析,从不同的逻辑视角探讨电视媒介的新发展,并对媒介与空间合力形成的新媒介空间进行深入思考。
一、技术逻辑下的媒介演进——后电视时代的到来
媒介环境学派指出,技术的发展关系着媒介的进化。对于电视媒介而言,媒介现象的出现、媒介形态的演进、媒介融合的加深都离不开技术的更新发展。疫情期间电视能够回归高光时刻也得益于技术的助力。
(一)“后电视时代”的到来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电视媒介进行了全面革新,在样态、形式与内容方面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等新趋势,媒介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电视媒介的概念已无法全面且准确地定义当今电视媒介发展的新局面。因此,阿曼达·D.洛茨(Amanda D.Lotz)对新技术发展下的美国电视进行分析,重新界定了电视发展阶段,提出用后电视网时代(the post-network era)来形容当今这个“有线电视频道为观众创造更多选择的时代”②。洛茨认为“在后电视网时代,观众对于观看的内容、时间和地点有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③“后电视网时代”的提出迅速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的讨论,在概念本土化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电视发展情况,谭天等学者认为使用“后电视时代”的概念来定位中国电视发展现状更加恰当。
“后电视时代”的内涵十分丰富。从发展动力角度分析,信息技术的综合发展是后电视时代能够到来并不断前进发展的核心动力。无论是信号传输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各项终端设备的演进提升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因此,对于后电视时代而言,技术是核心驱动力之一。从媒介功能角度分析,后电视时代不仅满足大众在信息获取、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需求,同时满足了大众的社会交往需求。借助交互技术的应用,电视媒介不断开拓社交功能,从传统线性播放的信息获取逐步扩展为参与式传播下的社会关系互动。从媒介产品形态分析,后电视时代对应的媒介产品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与形态。在传统电视产品的基础上,后电视时代聚合多种网络视频形态,提供广泛意义上的多元视频产品。从终端类型分析,后电视时代的接收终端不局限于多元的电视设备,同时包括部分手机、电脑等移动接收设备。接收终端种类的多元化也是媒介融合发展趋势下,传统电视媒介寻找新出路的重要体现。从媒介参与角度分析,传统电视媒介给予大众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等媒介活动的空间较小,而后电视时代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展大众参与的空间,提升参与主动性,优化大众的媒介参与体验。总之,伴随着技术发展,传统电视行业不断革新,融合多重技术,以更加丰富的视频形态,更前沿的信息技术,提供更具交互性的媒介产品,最终迎来了后电视时代。
(二)后电视媒介的“基因特征”分析
在网络兴起前,电视稳坐“国民媒介”的位置,逐渐发展出自身独特的“媒介基因”。在进化过程中,后电视媒介传承了传统电视媒介的内核,保留并发扬了电视媒介的优势基因。
首先,电视象征着权威与主流,体现了媒介专业主义。即便技术变革带来了去中心化的生产模式,后电视媒介仍然保持着一种相对专业化的生产模式,信源具有权威性与公信力。
在新冠疫情期间,信息的准确性、客观性、科学性关乎个人生命健康。因此,后电视媒介在疫情期间充分发挥了信源可靠的优势,加之信号传输技术不断升级,传播的时效性极大提升,让大众能够迅速获取权威信息,消除信息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
其次,电视媒介与家庭文化关系密切。电视媒介凭借自身的独特性,成功进入并占据着家庭空间,“电视成了千百万个重新建立的‘家’的文化标志,没有一种文化载体,能像电视那样富有社会的同情心和家庭的凝聚力”④。中国电视发展初期,电视数量较少,经常在公共空间中以集体观看的方式进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与电视技术的发展,家庭电视拥有量迅速提升,电视走进客厅、走进卧室,观看电视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家庭活动。在后电视时代,电视更是凭借接收终端数量充足、种类多元、可移动性较高等优势,深度融入家庭生活中,传承家庭文化,维系家庭情感。
最后,电视媒介一直以来具有较强的仪式化色彩,电视的节目内容设计与呈现形式承载着建构集体记忆的重任。在后电视时代,配合空间整体氛围与节目呈现,电视媒介带来的沉浸感与仪式感更为强烈。
在传统基因基础上,后电视媒介衍生出新的媒介基因与媒介特色以适应技术的变革,更好地满足大众的媒介需求。一是随着交互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屏互动成为新特色。在传统电视时代,互动的流程繁琐且具有延迟性,多媒介同屏互动与即时互动较难实现。随着交互技术的发展,后电视时代逐渐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实时跨屏交流。多屏互动促进了内容分享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构建社会关系的需求。
二是打破了传统线性播放模式。传统的电视节目播放严格遵循线性播放模式,大众的选择空间较少。在后电视时代,随着网络记录、存储、点播等技术的完善,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被打破,大众可以随时选择网络电视进行观看。非线性的模式扩大了大众观看的可选择范围,让大众可以依据自身需求去安排媒介活动。非线性模式也带来了碎片化的观看与传播方式,更快地适应了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模式,满足多场景观看的需求,让大众能够便捷地使用后电视媒介充实缝隙时间。
三是终端多元,平台互建,融合发展。在终端多元与媒介融合的共同推动下,后电视时代在传统平台的基础上,开拓多平台渠道,实现聚合发力,扩大媒介覆盖广度,最终汇聚为媒介合力,提升后电视媒介的影响力,充分激发后电视媒介的发展潜力。
综上,在技术推动下,电视媒介的发展迎来新的时代篇章,后电视时代能够实现的媒介功能越来越多,对于大众需求的满足度越来越高。因此,在疫情期间,后电视媒介展露优势,找准大众媒介需求,提供多元媒介服务,让电视重新迎来发展高光。
二、空间逻辑下的后电视时代——媒介与空间深度融合
在技术助力的同时,疫情期间特殊的空间环境也是电视媒介回归的另一关键因素。换言之,疫情期间电视收视增长与特定的空间情境息息相关。针对这种媒介研究中的空间考量,有学者提出了“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的转变”⑤。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实践逻辑进一步细化为空间逻辑,主要针对媒介与空间的关系,“把传播活动与其所嵌入的以及所生产的特定空间情境结合起来”⑥,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桎梏中。
(一)空间逻辑的核心:媒介与空间的关联
长久以来,空间研究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尤其在时间与空间的争论中,空间往往被污名化。在早期的研究中,“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⑦。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研究中呈现“空间转向”的趋势,空间研究得到重视,相关理论得以深入发展。
媒介研究中的“空间意识”在媒介环境学中得以开端,从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媒介偏倚”理论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理论再到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场景地理”理论,从不同角度将空间的视角带入媒介研究中。特别是梅罗维茨对电子媒介的关注,探讨电视对场景及空间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讲,媒介环境学开启了媒介研究中的空间视角,重塑了大众对于空间与媒介关系的认知。随后,媒介地理学的出现将媒介空间研究带入新的发展阶段,以跨学科的视角将空间引入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探讨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地理呈现与不同地理空间中的媒介发展。
因此,空间逻辑的核心在于关注与探讨媒介、空间以及二者的关系。对于后电视时代而言,媒介与空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二者的勾连愈加深入。为了更好地理解大众在疫情期间居于家庭空间中的媒介选择与媒介活动,需要明确家庭空间与后电视媒介的独特性与关联性。
第一,家庭具有鲜明的空间性,其空间建构离不开媒介助力。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家庭作为一种地理空间,具有实在的发生场所,我们的日常生活便是开展在具体的家庭空间中。从空间关系建构的角度出发,家庭中充斥着各种连接与关系,并借助媒介手段注入权力、情感、文化等意义要素,在不断交织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家庭空间关系网。因此“不仅在地理学的意义上,而且用客体关系理论来说,家都是一个潜在的空间(potential space)。”⑧针对家庭空间这一特定空间对象,后电视媒介作为家庭空间与外部空间联系的桥梁,直接关系着家庭空间自身的建构以及空间关系的维系。
第二,媒介发展与选择依赖于空间环境。正所谓“媒介总是存在于空间中的,不同的空间造就不同的媒介。”⑨电视媒介作为“日常生活的伴生物”,是“对住所依赖度最高的媒介”,这也是电视的媒介基因决定的。即使在后电视时代,依旧无法割裂电视媒介与家庭空间、家庭文化之间的依赖关系与伴随关系。
而大众的媒介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空间环境的影响。大众的媒介接触与使用会随着空间场景的改变而有所区别。因此,同在家庭空间中,后电视媒介发挥其伴生优势,成为大众的媒介选择。特别在此次疫情期间,更加凸显了后电视媒介在家庭空间中的优势,为电视迎来收视回流奠定了基础。
(二)媒介与空间的双向驯化: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
后电视媒介与家庭空间关联密切,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双向的“驯化”过程,这个过程并非简单地把电视摆进家庭空间中,而是将电视媒介融入家庭空间,使其参与日常家庭生活,同时也将家庭空间打上媒介的烙印,使空间具有媒介的功能与意义。这种驯化的建构过程就是“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的过程。
媒介空间化是通过媒介技术的升级、媒介形式的丰富、媒介功能的扩展,实现并增强媒介的空间性。既包含了媒介对虚拟空间的生产与连通,也包含了对实在空间的建构与融合。空间媒介化是指空间在技术发展的支持下,在自身需求的推动下具有了媒介的属性与功能,空间既具有生产信息的能力,又能够完成传播信息的任务。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并非两个割裂的过程,而是共同交融作用的过程。
参考温弗里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总结的媒介化过程,即“延伸(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ation)和适应(accommodation)”,结合空间化的过程,可以将后电视媒介空间化与家庭空间媒介化的具体过程总结为压缩、延伸、替代、对抗、适应与融合。
第一,压缩。压缩的过程体现在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马克思提出资本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空间,开拓更大的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所谓时间消灭空间并非意味着空间彻底消失,而是指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商品与资本在空间中的流通时间,弱化了距离感,空间相对被压缩。在此基础上,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将其发展并总结为“时空压缩”。时空压缩既是过程也是感受,关键在于它“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压缩的背后是加速,尤其在后电视时代,传播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大众的时空感受。传播加速使得时空压缩现象更加明显。后电视媒介打破地域隔阂,重构大众的时空认知,将不同的空间压缩汇集在媒介接受空间中。
第二,延伸。延伸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后电视媒介在全方位地延伸进入家庭空间,参与信息传递、情感维系、家庭关系互动等日常活动,在情感、认知、行动等多重意义上进入家庭空间中。其次,家庭空间延伸出媒介的功能,进行媒介生产实践活动。最后,后电视媒介延伸了大众的感知系统,将媒介发展成人的一部分,扩大了大众的空间感知范围。
第三,替代。后电视媒介在逐渐替代一些家庭物品与组织机构。电视的打开关闭与家庭活动安排紧密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电视成为了钟表、日历的替代品。电视媒介传递信息,打开大众了解社会的窗口,提供大量交谈话题,成为了话题制造工具的替代品。电视媒介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与仪式感的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是专业的社会机构与组织的替代符号。在替代过程中,媒介与空间逐渐互相嵌入,原本的空间活动与媒介属性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第四,对抗。媒介与空间相互作用势必会解构原本的空间秩序与媒介格局,冲击既有的社会关系与权力体系,这也意味着对抗的过程是无法避免的,无论是压缩、延伸还是替代、融合的过程,都会伴随着对抗的存在。
第五,适应与融合。适应与融合既是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的过程,也是一种状态与结果的呈现。对于后电视媒介与家庭空间而言,适应与融合是双方具有了对方的属性且内化为自身特性的过程与状态。当然,压缩、延伸、替代、对抗、适应与融合并非单向线性流程,而是在相互驯化的过程中交替或同时发挥作用,最终完成媒介与空间的双向建构。
三、后电视媒介空间:双重建构下的第三空间
基于技术逻辑与空间逻辑,后电视媒介与空间借助技术高速通道得以相互建构、相互影响,最终形成“后电视媒介空间”。对于后电视媒介空间的界定主要从媒介空间属性与媒介空间形成两方面展开。
首先,需要明确空间与媒介空间的属性。空间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其内涵具有复杂性。早期,艺术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对空间的重视不足,界定模糊含混。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现代空间理论奠基者的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开启了空间理论的新视角,强调“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在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二元划分基础上,加入“社会空间”的分析,形成三元一体的空间构成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划分一方面打破了空间流于表面的物化现象,避免陷入“模糊的幻想”(illusion of opaqueness);另一方面避免了空间跌入纯精神化的陷阱,以防困于“透明的幻想”(illusion of transparency)中。
在此基础上,爱德华·W.苏贾(Edward W. Soja)将空间划分为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第一空间强调空间的物质性、实践性;第二空间偏向于主观性、精神性;第三空间则是在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的基础上,以更加综合的视角将物质性与精神性归纳在新的空间中。当然,第三空间不是机械的第一空间加第二空间,第三空间的关键是融合,是将实在物质与抽象想象融合,不断解构并重构形成的综合性空间。
第三空间理论给媒介空间属性的界定带来了新启发。信息的生产与流动、社会关系的维系与建构等都在媒介空间中得以完成,纯粹的一元空间、二元空间都无法全面体现媒介空间的属性。因此,媒介空间不是纯粹的物质空间或精神空间,而是一种杂糅交融的混合型空间,将实在空间与虚拟空间、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进行了融合延伸,形成了一个开放、融合、多元的独特空间,体现了第三空间的属性。
后电视媒介空间亦是如此。一方面后电视媒介空间不断融入实在的物质空间中。不仅是家庭空间,后电视媒介空间的形成也会依托于电梯、车辆、地铁等一系列实在物质空间。因此,后电视媒介空间具有天然的物质属性。另一方面,后电视媒介空间也具有虚拟空间的特点。后电视媒介打破了地域的局限,为大众构筑了一个认识世界、感知世界、与世界建构关系的全新途径,创造了一种逻辑意义上的抽象空间。在此基础上,后电视媒介空间聚合了两种空间形态,将虚拟性与实在性、物质性与精神性进行了深层次的贯通融合,最终形成第三空间。而且相对于传统的电视媒介空间,后电视媒介空间凭借技术优势,对虚拟空间的开发度与利用度更高,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程度更深,第三空间的属性更为突出。
其次,从媒介空间形成角度分析,后电视媒介空间的产生经历了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的双重作用,经过了压缩、延伸、替代、对抗、适应与融合的建构过程。媒介空间既包括媒介生产打造的空间,也包括激发媒介属性后的既有空间。一方面肯定媒介具有生产性,媒介能够建构空间;另一方面强调随着空间的深入开发,空间的媒介功能显现,其多元属性得以激发。媒介空间作为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涵盖了双重建构的过程与结果。
综上,在技术的催化与生产实践的推动下,后电视媒介空间的内涵与外延得以丰富,无论是实在的、物理的空间属性,还是信息的、文化的、精神的虚拟空间属性,都在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的双重作用下统筹融合,最终成为一个不断更新发展的第三空间。
四、后电视媒介空间的特性分析
(一)后电视媒介空间的层次流动性
空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流动性。尤其在后电视时代,空间的流动性更加明显。“流动空间”(the space of flows)由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即“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在肯定空间具有物质性的基础上,卡斯特强调了空间的流动性,指出流动空间是通过社会中各种元素(信息、人员、资本等)的流动而产生的。而且为了避免抽象地理解流动空间,卡斯特将流动空间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的第一个层次、“由其节点(node)与核心(hub)所构成”的第二个层次与“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构成的第三个层次。
对于后电视媒介空间而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不断改进,空间中信息、技术、关系、资本的流动性更加突出,空间流动的层次性也更加明显。后电视媒介空间的第一个流动层次体现在其信息传输装置、接收装置、显示装置与互动装置上。配合高清转播等传输设备、数字电视等丰富多元的接收设备、VR眼镜等观看设备、电子运动感应等互动设备的使用,后电视媒介空间不断完善生产、传播、接收、互动等环节的物质基础与电子回路。
第二个流动层次中的节点与核心在后电视媒介空间中得到了全面发展。传统的电视媒介空间中,节点的数量、位置分布、聚合连接力远远不如当今互联网技术加持下的后电视媒介空间。后电视媒介空间能够实现节点与核心之间、节点与节点之间、核心与核心之间较为顺畅的连接,在交互中实现文化、信息、技术与资本的流动,并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社会资本的累积。
第三个流动层次体现为后电视媒介空间中占支配地位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电视媒介的特殊性与公共性,后电视媒介空间中的生产主体主要为专业媒介组织或机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官方性。但技术发展带来的去中心化趋势还是对传统的支配主体造成冲击,参与生产传播的主体逐渐多元,信息接收者的能动性得到提升,其态度与行动不断挑战传统生产主体的支配地位。因此,后电视媒介空间中的支配主体呈现多元博弈的态势。综合来看,后电视媒介空间具有流动性,且是一种富有层次化的流动性。
(二)后电视媒介空间的多元融合性
后电视媒介空间与其他空间的多元融合一方面是媒介融合发展下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空间的特性使然。空间具有叠加性、融合性与渗透性,不同空间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可以共融共生,不仅能够实现不同地理空间的联结,也能够实现不同媒介空间的叠加与融合。
首先,不同的地理空间以视觉影像的形式汇集呈现在后电视媒介空间中。在高清影像技术、沉浸式技术与场景搭建技术的辅助下,后电视媒介空间能够提供更加逼真的在场感与情境感,将不同的地理空间在媒介空间中复制、压缩、转换并关联,建构起媒介空间与不同地理空间的联系。大众在后电视媒介空间中,可以得到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信息,借助视频内容的转化完成不同地理空间的连接,实现了不同地理空间的切换与虚拟在场。
其次,多元媒介集合使不同类型的媒介空间在后电视媒介空间中叠加、融合。随着移动媒介的发展,媒介融合不断加深,跨屏互动技术日趋成熟,不同媒介空间的界限不再判若鸿沟,最常与电视媒介空间交融叠加的便是手机等新媒体形成的媒介空间。电视媒介空间与新媒体媒介空间的交叉融合,是后电视媒介空间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点与必然趋势。
(三)后电视媒介空间的情感性
后电视媒介空间的情感性不仅包括长久积淀形成的情感氛围,也包含短时间内聚集的各种情绪,同时涵盖了情绪与情感之间的转化。后电视媒介空间的情感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后电视媒介空间共享了地理空间中的情感氛围。后电视媒介空间具有较强的情感张力,擅于进行情感的转移与内化,将地理空间中长久积累的情感转变为媒介空间的情感。以家庭空间为例,后电视媒介空间依托家庭空间,通过制造情境、渲染氛围、加强互动的方式,将家庭带给个体的归属感、陪伴感与安全感等情感进行转移,赋予后电视媒介空间同样的情感氛围。而且在后电视时代,媒介空间与家庭空间的融合程度加深,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媒介空间,其情感持久性更强、稳定性较高。
第二,后电视媒介空间借助媒介的情绪传播功能与搅拌功能,将社会情绪转化为情感合意。后电视媒介通过不同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传递不同的社会情绪,配合传播过程中的仪式化特点,放大情绪的影响力,以大众的媒介互动活动为桥梁,不断将情绪汇集在后电视媒介空间中。在此基础上,后电视媒介继续发挥搅拌功能,“在人们之间充蕴共通的气氛和感情,并增加其密度”。通过媒介搅拌过程,“人们的感受能力得到调动,心理上的相互作用,就会使人们凝聚为一个情绪的集合体”。当情绪共振达到一定程度后,情绪转变为大众的情感共鸣,形成一种共同体式的关联感与归属感,群体意识得到强化,形成情感合意。
五、割裂与入侵:对后电视媒介空间的反思
对于后电视媒介空间而言,空间的流动性越强,大众对空间的依赖性越高,空间问题便越棘手。伴随着后电视媒介空间的深入发展,“割裂”与“入侵”的空间问题不断暴露。
(一)割裂:后电视媒介空间等级问题加剧
后电视媒介空间的等级问题与空间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边缘”结构关联甚密。核心与边缘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它的划定取决于对比范围的选择。随着对比范围的变化,核心对象与边缘对象处于动态转变的过程。虽然核心与边缘的界定不是绝对固定的,但“核心—边缘”结构的存在,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对比与割裂的状态,反映了空间中的等级差异。后电视媒介空间中的“核心—边缘”结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地理空间发展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则是空间中不同群体的等级差异。
首先,地理空间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导致媒介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能力存在差异,由此带来后电视媒介空间的等级分化。不同地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媒介发展状况、资金支持情况、文化历史背景等均有差异。其中经济发展好、媒介技术升级速度快、资金支持到位、文化底蕴丰厚的地区,即处于核心区域的后电视媒介空间,其生产力与扩大再生产能力相对较高。相反,边缘媒介空间由于各项条件不到位,媒介空间生产能力有限,有些甚至未能进入后电视时代,仍旧处于电视媒介空间欠发展状态,由此,后电视媒介空间产生了等级区分。
其次,后电视媒介空间中的生产实践与大众的受教育水平、媒介素养等密切相关。后电视媒介功能性越来越强的同时也对使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较于按下开关就能观看的传统电视媒介,如今的后电视媒介需要大众持续关注与学习,需要掌握一定的操作技巧才能获得更好的媒介体验。因此,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媒介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众在后电视媒介空间中对新技术使用的灵活度、对信息接收与理解的深度、对信息再生产与再传播的积极性,无形中设置了后电视媒介空间的准入门槛。大众能否进入后电视媒介空间、进入后的参与度与使用度都会带来后电视媒介空间中的群体分化与等级割裂问题。后电视媒介空间中的数字鸿沟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所加深,媒介空间中的等级割裂问题不断加剧。
(二)入侵:后电视媒介空间界限的模糊
一方面, 媒介空间代表着公共空间,负责传递公共信息,营造情感氛围,另一方面,媒介空间连接着私人空间,通过信息生产、传播、解读与再生产的过程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建立联系。但随着后电视媒介的发展,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侵占程度逐渐加深,二者的空间界限不断模糊。
首先,大众使用后电视媒介获得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媒介也在获取、记录与分析相关的位置信息、浏览偏好等私人信息,将个人的直接媒介活动与间接生活活动转变为数字化记录,私人空间被迫暴露在公共空间中。这个过程冲击了大众对私人空间的主导权,丧失了个人空间的私密性,直接影响个人隐私安全,让大众陷入一种名为社会监视的焦虑中。
其次,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杂糅混乱,破坏了原本的空间功能与劳动秩序。定位并分割不同的空间是为了能够最大化地发挥空间作用并合理规划劳动安排。公共劳动空间与私人生活空间的分离是现代劳动制度确立的基础之一,但私人空间被公共空间过度入侵,不仅让私人空间无形中成为媒介公共空间扩张的免费资源,也导致大众在空间中的生产活动界限不再明晰,空间劳动的合理合法性受到蒙蔽,产生劳动异化等问题。
后电视媒介空间中的割裂与入侵问题是对空间公平与正义的挑战,不仅不利于当下的空间建构与个人权利保护,也对长远的空间生产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在面对媒介空间转向趋势时,我们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思考媒介与空间的关系、挖掘后电视媒介空间的更多特性,同时也要注意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困境,助力后电视媒介空间长久发展。
注释:
①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节目收视逆势爆发 为疫情防控 强信心 鼓士气》,http://www.nrta.gov.cn/art/2020/2/13/art_114_49972.html,2020年2月13日。
②③ Amanda D.Lotz.TheTelevisionWillBeRevolutionized(Second Edit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4.pp.27-28,p.28.
④ 汪天云等:《电视社会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⑤⑥ 王斌:《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媒介演化的空间历程与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第64页。
⑦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⑧ [英]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1页。
⑨ 邵培仁、杨丽萍:《转向空间:媒介地理中的空间与景观研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3页。
⑩ 胡智锋、周建新:《电视节目编排三论》,《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