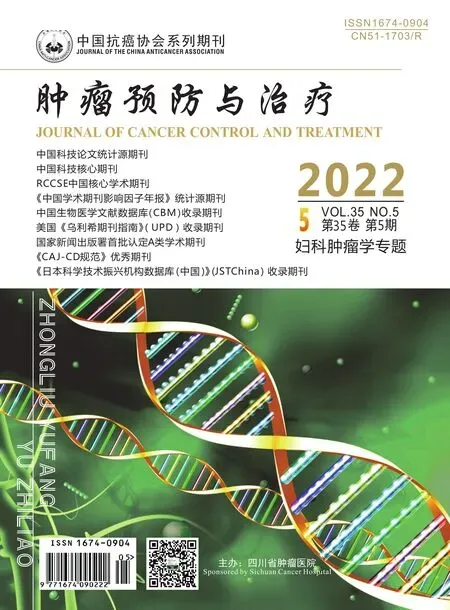基于肿瘤免疫微环境联合免疫治疗卵巢癌的研究进展*
马金燕,冯炜炜
200025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妇产科
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死亡率最高的肿瘤[1],目前卵巢癌的一线治疗仍然是手术和以铂为主的化疗,超过80%的患者最初会对治疗产生反应,但大多数会复发,并最终发展为对化疗耐药[2]。然而,尽管采用多模式治疗以及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 (poly adenosine diphosphate 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应用于维持治疗,晚期患者预后仍然很差,生存率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微弱的改善[3]。近二十年来,免疫疗法迅速发展,使各种癌症的治疗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包括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lymphocyte 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及其配体(B7/CD80)和程序性死亡受体1 (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PD-1)及其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的抑制剂,它们逆转来自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信号,其作为癌症治疗的新方法被广泛研究。过继细胞治疗(adoptive cell therapy,ACT)、溶瘤病毒、癌症疫苗的应用也正在不断更新发展。
肿瘤免疫微环境(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TIME)作为调控肿瘤发展、浸润及转移的重要环境,主要由浸润的免疫细胞及其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组成。在TIME和肿瘤驱动基因的共同刺激下,肿瘤细胞可以通过重新编程宿主的正常细胞,使其获得更适合肿瘤生长的表型和功能[4]。本文围绕卵巢癌免疫微环境的变化,概述了近几年免疫治疗联合化疗、联合靶向治疗及过继细胞治疗等新型治疗方式的发展和进步,为卵巢癌个性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1 卵巢癌的TIME
1.1 免疫细胞
在TME中,CD8+T细胞浸润肿瘤,即CD8+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是免疫识别的象征,Sato等[5]证明高密度的CD8+TILs提示上皮性卵巢癌(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EOC)患者预后较好。CD8+T细胞通过分泌颗粒酶B、肿瘤坏死因子和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来清除肿瘤细胞,因此CD8+T细胞的调节在卵巢TME中至关重要[6]。在抗原暴露持续存在的癌症内环境中,T细胞逐渐丧失效应功能,上调包括PD-1在内的抑制性受体的表达,并表现出较差的记忆能力。而这种耗竭型T细胞的耗尽,可被PD-1抗体等通过抑制性受体阻滞而重新激活[7]。
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和来源于肿瘤的抑制性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也能抑制T细胞的抗肿瘤反应[8]。Tregs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负向调节抗肿瘤反应,这表明Tregs 介导肿瘤免疫逃避[9]。Curiel 等[10]发现CD4+CD25+FOXP3+Tregs在体内特异性抑制抗肿瘤T细胞,促进肿瘤生长。此外,它们的存在与卵巢癌不良预后相关。在一项探讨减瘤术对原发性和复发性EOC免疫系统的影响的研究中,CD4/CD8在原发性肿瘤中升高,而在复发性肿瘤中不升高。初次减瘤增加了循环效应细胞CD4+和CD8+T细胞,循环CD4+Tregs和IL-10血清水平下降,而TGF-β和IL-6水平没有下降,CD4+Tregs在新辅助化疗后也有所下降,表明手术会引起全身及TME中免疫抑制的减少,导致CD8+T细胞对回忆抗原反应的能力增强,而在化疗或复发性EOC的患者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11]。此外,凋亡的Tregs细胞甚至获得更优越的抑制能力。TME中的氧化应激导致肿瘤浸润性Tregs细胞的高凋亡,这是由于细胞内核转录因子E2相关因子的抗氧化系统较弱[12]。凋亡的Tregs细胞通过CD39和CD73将大量ATP转化为腺苷,然后通过腺苷受体亚型A2A途径维持和放大抑制活性并介导PD-L1抑制剂耐药。
此外,骨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具有显著的抑制T细胞反应的能力[13],其在卵巢癌患者中增加,并在疾病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被认为是EOC组织和腹水中最丰富的浸润性免疫细胞,它们具有免疫抑制M2表型,其特征是表达CD163、CD204、CD206和IL-10[14],并且与肿瘤进展相关[15]。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包括产生IFN-γ和对癌细胞的直接细胞毒性。在卵巢癌患者腹水中发现完全成熟的人类NK细胞亚群过表达PD-1[16]。以上数据可能有助于设计新的治疗方法,以提高 NK 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
这些先天和后天形成的免疫细胞,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卵巢癌独特的TME,充分了解肿瘤细胞与卵巢固有免疫系统不同细胞亚群之间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才能进一步寻找免疫治疗的靶点和联合免疫治疗的契机。
1.2 免疫抑制网络及特点
卵巢癌免疫抑制网络冗杂,是免疫治疗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即便患者通过免疫治疗产生了大量肿瘤特异性T细胞,这些T细胞在体内可能也不会那么容易破坏肿瘤细胞。总的来说,卵巢癌免疫抑制网络的机制包括如前所述Tregs抑制CD8+效应T细胞;其次为免疫调节酶吲哚胺-2,3-双氧酶(indoleamine-2,3-dioxygenase,IDO)通过局部消耗色氨酸并产生有毒色氨酸代谢物(如kynurenine)来诱导免疫耐受性,导致TME中效应T细胞或NK细胞的生长受到阻碍,并抑制其杀伤功能,IDO抑制剂可以提高当前化疗或免疫治疗的抗肿瘤疗效[17];还有最经典的抑制途径为抑制性免疫检查点CTLA4和PD-1与配体PD-L1的结合;此外,MDSCs以及抑制因子如TGF-β等也参与调控卵巢癌免疫抑制网络[18]。
1.3 免疫治疗策略
目前对肿瘤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认识已经为患者合理分层管理和制定治疗策略奠定了基础。2009年,Camus等[19]首次在结直肠癌中基于免疫浸润观察到三个主要免疫协调谱(热肿瘤、可变肿瘤、冷肿瘤),这使得临床工作者能够根据肿瘤逃逸和免疫协调之间的平衡进行以免疫为基础的肿瘤分类,这三类肿瘤的2年复发风险分别为10%、50%和80%。这一概念导致了免疫评分的开发和实施,即通过对肿瘤中心和边缘浸润的两种淋巴细胞群体(CD3和CD8)的量化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从I0(表示两个区域两种细胞类型密度都很低)到I4(两个区域的免疫细胞密度都很高)。免疫评分已在全球范围内在结肠癌中得到验证,具有很大的预后价值。除了TILs的存在外,其他特征,如PD-L1的表达、可能的基因组不稳定性以及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存在,已被描述为免疫热肿瘤的特征。相反,冷肿瘤也被描述为免疫无知(几乎不表达PD-L1),其特点是高增殖、低突变负荷和抗原提呈标记物低表达,如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I类低表达[20]。另外对于“可变肿瘤”,其特征是TIME的改变和抑制性细胞的存在,这些细胞阻止存在于间质中的CD8+T细胞进入肿瘤细胞。这类患者可通过T细胞转运调节剂、表观遗传调节剂、TME重塑分子、放射治疗等增加免疫效应细胞在肿瘤中的浸润[21]。在卵巢癌中,免疫治疗的初步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令人满意,目前利用TME诱导抗肿瘤T细胞效应是免疫治疗有效的重要因素,许多方法正在研究实现这一目标,包括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疫苗、自体肿瘤疫苗和其他联合疗法。成功的卵巢癌免疫治疗依赖于抗原提呈细胞的刺激,减弱免疫抑制微环境,以及增强效应T细胞的活性。
2 联合免疫治疗
2.1 化疗联合ICIs治疗
化疗是卵巢癌一线标准治疗,可以导致癌细胞的破坏和免疫原性分子的释放[22]。铂类化疗可以通过下调DC和肿瘤细胞上PD-L2的表达,提高肿瘤T细胞识别能力,从而干扰信号转导子和转录激活因子6介导的TME免疫抑制[23]。紫杉醇治疗也可能有利于卵巢癌的免疫治疗,因为已有研究证明紫杉醇治疗提高了CD8+T细胞浸润水平,上调了PD-L1的表达,并且发现紫杉醇联合抗PD-L1/PD-1抗体治疗的荷瘤小鼠比单用紫杉醇治疗的小鼠存活时间更长[24]。Mkrtichyan等[25]发现,环磷酰胺和PD-L1抑制剂(CT-011)的联合,减少Tregs的渗透,并显著增强CD8+TILs的数量。吉西他滨联合CTLA-4阻断剂可诱导CD4+和CD8+T细胞依赖性抗肿瘤免疫反应[26]。
2.2 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ICIs治疗
根据III期临床研究数据,抗血管生成药物贝伐单抗已作为晚期卵巢癌的一线治疗药物,与卡铂和紫杉醇联合使用[27]。肿瘤血管在结构和功能上往往异常,由于淋巴引流功能的障碍,肿瘤血管倾向于缺氧、低pH值和高组织间压力的免疫抑制环境。异常TME促进免疫抑制性Tregs细胞的激活和扩增,促进TAMs的招募,促进异常内皮细胞的扩增,抑制DC的成熟,从而导致抗原呈递受损和肿瘤特异性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的激活。PD-1/PD-L1通路经常使肿瘤细胞和肿瘤浸润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上调,标记它们为功能失调或“耗尽”,并限制其细胞毒性潜能[28]。此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TME中可促进MDSCs的扩增,增强其免疫抑制功能[29]。因此,可将抗血管新生疗法和ICIs相结合,许多III期临床试验目前正在进行中。抗血管生成药物可能通过使异常的肿瘤血管正常化、对免疫细胞和内皮细胞的直接抑制作用、增加免疫效应细胞向肿瘤的浸润以及将免疫抑制性TME转化为免疫支持性TME从而部分提高免疫治疗的有效性[30]。
Liu等[31]2018年在ESMO上发表了令人鼓舞的初步结果,II期试验评估了抗PD-1抑制剂和贝伐单抗联合用于38例EOC患者,包括18例铂耐药患者。组合治疗显示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为28.9%,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8.1个月并且无意外的不良反应。在一项II期非随机临床试验中,pembrolizumab(抗PD-1抗体)与贝伐单抗和口服环磷酰胺的组合耐受性良好,并在25.0%的复发性卵巢癌患者中显示出95.0%的临床获益和>12个月的持久治疗反应。这种组合可能代表了未来复发性卵巢癌的治疗策略[32]。
2.3 PARP抑制剂联合ICIs治疗
PARP是一个由17个核蛋白组成的家族,其特征是有一个共同的催化位点参与DNA损伤修复[33]。PARP-1显示出广泛的免疫调节作用:调节单核细胞来源的DC成熟;减少CD86和CD83以及IL-12和IL-10的表达;调节T细胞功能中必不可少的活化T细胞核因子(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ed T cell,NFAT)的激活过程[34]。具有乳腺癌易感基因蛋白1和2(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l/2,BRCA1/2)突变的EOC已被确定为免疫治疗和PARP抑制剂联合治疗的理想候选者[35]。在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igh-grade serous ovarian cancer,HGSOC)中,含有同源重组缺陷(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HRD)且BRCA1/2突变的肿瘤表现出更高的新抗原负荷和更多的CD3+和CD8+TILs,与同源重组完备的肿瘤相比,PD-1和PD-L1表达水平升高,提示BRCA1/2突变的HGSOC对PD-1/PD-L1抑制剂的敏感性增高[36]。PARP抑制剂增强肿瘤抗原性,使肿瘤对检查点阻断疗法敏感。PARP抑制剂还能通过产生更高的突变负担,提高新抗原表达水平,从而改善HRD卵巢癌对免疫治疗的反应。同时,阻断PD-L1可恢复免疫活性,以增强PAPP抑制剂的抗肿瘤作用[37],在复发性卵巢癌中表现出适度的临床疗效[38]。因此,评估免疫检查点阻断联合PARP抑制剂在卵巢癌临床试验中的疗效是一种潜在的治疗策略。在I/II期TOPACIO试验中,评估了PARP抑制剂尼拉帕利和抗PD-1抗体派姆单抗联合治疗铂类耐药卵巢癌的疗效,在具有BRCA1/2突变的队列中,ORR和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分别为45%和73%[39]。I/II期篮式MEDIOLA试验表明,联合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和抗PD-L1抗体durvalumab治疗铂敏感复发并且BRCA突变的EOC,12周时,DCR为81%,ORR为63%[40]。上述结果表明,PARP抑制剂和PD-1/PD-L1抑制剂联合应用可以增加抗肿瘤效果,在EOC的临床应用方面亟待进一步探索。
2.4 抗CTLA-4抗体
单一的抗CTLA-4单克隆抗体(ipilimumab或tremelimumab)在晚期或复发性EOC中的疗效并不理想,与PARP抑制剂的联合治疗处于早期阶段,但似乎可以耐受并诱导抗肿瘤反应。研究发现PD-1/CTLA-4表达水平的升高可减弱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表达。顺铂联合PD-L1抗体和CTLA-4抗体治疗大大增强了BRCA1缺陷小鼠的抗肿瘤免疫,产生系统性免疫反应。这种反应包括增强DC的活化和减少Tregs的数量,并在CD8+和CD4+TILs的活化中增强[41]。Higuchi等[42]证实,CTLA-4抗体和PARP抑制剂联合应用可以增强T细胞功能,增加新型淋巴细胞克隆量,从而产生持久的抗肿瘤效果。在NCT02485990 II期试验中,24例晚期或复发性患者tremelimumab单用或联合奥拉帕利合用,其中1例部分缓解,9例疾病稳定,没有报道4级不良反应[43]。在NCT02571725 I期临床试验中,同样的组合用于3个BRCA突变的EOC患者,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并且在3个周期后肿瘤体积有所减小[44]。
3 ACT
ACT是在体外选择抗原特异性T细胞,并将其扩增到一定水平,从而获得靶向性免疫应答。用于ACT的T细胞可以来自外周血淋巴细胞或TILs。在体外修饰培养和扩增后,激活的T细胞被重新注入到宿主体内,这些工程细胞通过识别MHC中的抗原而启动[45]。T细胞可以通过基因修饰表达肿瘤抗原特异T细胞受体(T-cell receptor,TCR),或者编码跨膜蛋白的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两种类型。首次证明ACT在EOC中可能具有活性的证据来自于一项非随机I期研究,13例EOC患者,在首次手术并结束含铂的化疗后,接受TILs过继转移治疗(TIL组),与11例对照组(仅化疗)比较3年总生存率与3年无病生存率有显著性差异。结果表明,在所有化疗完成后,TILs的过继转移可能是实现完全治愈晚期EOC的一种有希望的方法[46]。间皮素是一个有潜力的靶点,且在约70%的EOC中表达。有证据表明第二代抗间皮素CAR-T在卵巢癌治疗中的初步结果是令人鼓舞的:6名EOC受试者接受抗间皮素CAR-T静脉输注治疗,这些T细胞在受试者的血液中扩增,并转运到肿瘤部位,治疗1个月后,1名患者恶性胸腔积液清除,所有患者病情稳定,表明该疗法是可行并且安全的[47]。
随着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产生更强大的TCR或CAR修饰T细胞。然而,与目前处于III期临床试验(NCT022788887)的恶性黑色素瘤的ACT研究相比,卵巢癌的ACT治疗仍处于起步阶段,最近一项小规模的研究提出,ACT和ICIs联合应用卵巢癌是可行并且安全的[48],因此联合免疫疗法可以为ACT治疗的完善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4 其他免疫治疗方法
基于肿瘤生物学、免疫治疗与TME的关系以及免疫抑制网络,许多学者正在研究针对卵巢癌新的更有效的免疫治疗方法。特异性抗原如NY-ESO-1、FR-alpha、MSLN、MUC16和p53是有吸引力的免疫治疗靶标,因为它们在EOC中频繁表达;还有主动免疫如癌症疫苗、溶瘤病毒等。另外,靶向其他免疫抑制途径可能是一种增强免疫治疗反应的方法。其中IDO通过消耗色氨酸使T细胞增殖停滞是影响TILs抗肿瘤作用的关键靶向途径之一,最近研究表明卵巢癌中IDO1的表达通过芳香烃受体(aromatic hydrocarbon receptor,AHR)激活诱导T细胞PD-1表达[49],为设计针对IDO1和AHR通路的策略以增强卵巢癌的抗肿瘤免疫提供了依据。
然而,像其他癌症治疗一样,在卵巢癌患者中使用免疫治疗也有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ICIs治疗后肿瘤生长出现反常的加速称为高进行性疾病(hyperprogressive disease,HPD),据报道发病率在4%到29%之间[50]。因此,未来确定HPD的生物学基础和机制以预测哪些患者易感HPD是非常重要的。
5 总结与展望
TIME是免疫抑制和免疫耐受的重要调节器,可以破坏TILs的数量和活性。更好地理解卵巢癌细胞和间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确定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可靠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至关重要。在设计新的治疗策略时,尤其是针对“可变肿瘤”或“冷肿瘤”的治疗策略时,应考虑TME的所有组成部分。这些策略可能包括启动T细胞反应的策略;针对肿瘤细胞新抗原的疫苗和ACT;在原位接种策略中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以及同时靶向负责T细胞无能或衰竭的检查点抑制剂。
尽管单一免疫治疗在卵巢癌中疗效有限,联合治疗似乎是最大化达到治疗益处的乐观选择,仍需要进一步分析疗效和风险,确定理想的反应标志物,从而制定个性化的免疫治疗方法应用于临床实践。
作者声明:本文全部作者对于研究和撰写的论文出现的不端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并承诺论文中涉及的原始图片、数据资料等已按照有关规定保存,可接受核查。
学术不端:本文在初审、返修及出版前均通过中国知网(CNKI)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学术不端检测。
同行评议:经同行专家双盲外审,达到刊发要求。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文章版权:本文出版前已与全体作者签署了论文授权书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