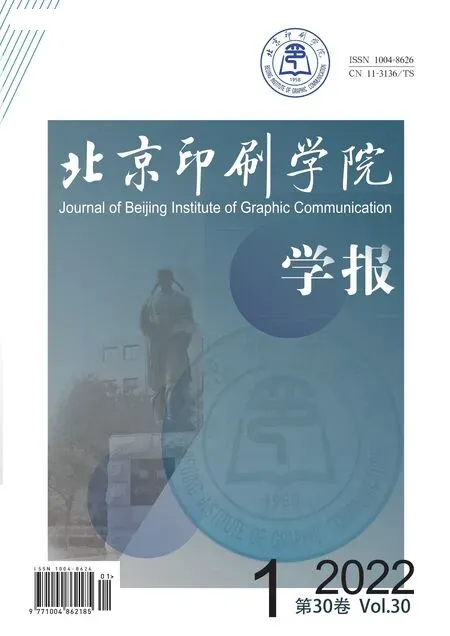论启蒙的进步或倒退
——以《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为中心的考察
覃 丹
(贵州大学,贵阳 550025)
启蒙究竟是人类的福音还是人类的灾难?启蒙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开起了倒车?《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这篇附录(以下简称“附录”)通过引用《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历险的故事,对此进行了分析。不可否认的是,启蒙使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树立起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并从以前愚昧无知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启蒙运动也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二战时期流亡美国期间,深切地体验到了二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灾难与破坏、法西斯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杀戮,他们认为这都是在人类经过充分启蒙的基础上所犯下的罪行。启蒙使自然和神灵的奴仆翻身成为世界的主人,但它却使人类走向了另一个神话:理性的神话。如何正确地看待启蒙,成为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启蒙的进步:理性战胜了神话
一场壮大且空前的崇拜理性的启蒙运动虽然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但其带来的影响一直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它用理性的光辉驱散了人们处于蒙昧状态下的黑暗,以科学为帆,以真理为船,载着人们驶向通往文化进步的康庄大道。启蒙造就了人的主体性意识,让人们不再是通过上帝去理解这个世界,相反地,我们学会了理性地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将所有的事情都装进统一的科学理性思考的体系内,加工改造后形成固定不变的唯一正确答案,是我们现代人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
随着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理性不可避免地将神话的虚幻面纱揭开,并用启蒙这把钥匙开启人类走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魔盒。《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是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他的智慧、谋略、狡猾等此类理性启蒙因素在荷马史诗中被放大并加以歌颂和赞扬,这既是一个理性启蒙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故事也是一个练就自我主体的故事,其核心概念是“牺牲与放弃”。在附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奥德修斯作为一个敢于冒险的英雄,将自身展现为一种资产阶级个体的原型,一种源自于自始自终自我确认的观念[1]36。这种观念即自我对于价值的取舍,确认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自我确认的过程是启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也是人树立主体性意识的过程。自我确认之后,为之努力战胜一切困难与挑战,这也是启蒙的出发点。在荷马史诗中,对于神话所提供的说明,以及用许多杂乱的故事企图构建起来的统一性,都无不彰显着主体摆脱了神话力量[1]39,其无处不在蕴藏着资产阶级启蒙要素。对于附录中所引用的奥德修斯的故事而言,它的展开显然同样也是以围绕理性战胜神话这一主题而进行的。启蒙语言赋予了史诗中的所有地方以确切的名字,使得历险者能够把握地理方位而准确地到达目的地。指南针的使用也避免了史诗中海难事件的发生。指南针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对人类的科学进步和文明的发展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为我们打开了世界市场,将人类从畏惧自然的迷雾中解放了出来,不再盲目迷信天神与海神,而是运用指南针等科学仪器开辟前进的道路。
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的十年间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但他通过运用自身的智慧与谋略,躲过了女妖塞壬的迷惑人的歌声,逃过怪物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战胜了波吕斐摩斯……最终安全地返回到自己的家乡与妻儿团聚。他的海上战胜重重困难的壮举,彰显了人类在征服自然和面对险阻时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与豪迈精神。荷马史诗所建构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了“规范理性”的成就,这种“规范理性”凭借其自身具有的合理秩序粉碎了神话。
二、启蒙走向自我的对立面:理性异化成新的神话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始终。对于启蒙而言,也同样如此。霍克海默指出,没有任何作品能够比荷马史诗更能够有力地揭示出启蒙和神话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1]38,并在附录中,根据奥德修斯的故事,探讨了神话与启蒙之间的辩证法,即:神话就是启蒙,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与世界的历史进程是相等的,启蒙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祛魅化的历史,同时也是追求进步、歌颂理性的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启蒙却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理性成为了非理性,进步成为了退步。这其实就是一个否定—肯定—否定的循环的辩证过程。
奥德修斯在自我持存的原则下,每一次的冒险活动中都以抗拒自然、背弃自然来达到战胜各种困难的目的。奥德修斯为了不陷入塞壬歌声的诱惑之中,将自己捆绑起来,并用蜡封住了水手们的耳朵,他们竭力抗拒塞壬的歌声如同抗拒死亡一样。[1]49不可否认,奥德修斯的这个看似理性的行为使得他们一行逃脱了塞壬歌声的迷惑,免于陷入航船触礁沉没的灾难之中,因此得以安然渡过。但是这却无形之中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这与人类的本性——享受和欣赏大自然美的权利是相违背的。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附录中所指出的:“人类对其自身的支配,恰恰是以自我本身为依据的,它几乎总是会使其得以发挥作用的主体遭到毁灭;因为自我持存所支配、压迫和破坏的实体,不是别的,只是生命,是生命的各种各样的功能”[1]45。奥德修斯为了实现自我持存,以牺牲自我生命的亲近大自然的功能,同时放弃了自我欣赏和享受大自然的权利,从而对客体(自然对象)进行控制,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相分离,并陷入了自我毁灭的状态。奥德修斯引以为傲的理性始终支配着他,以此使得他战胜一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当他在与巨人波吕斐摩斯的交战中,通过耍弄改名换姓的诡计(宣称自己的名字叫“无人”,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存在)实现了藏在羊的肚子里而安全逃走的计划时,他再一次否定了自我,压制了自我。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说:欺骗就是理性的标志,在欺骗面前,理性则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1]51如果将他的这种利用语言在事实和表达上的不同一性掩盖自己真实身份的欺骗行为称之为对个体的个性、特殊性进行宰制,我想也不为过。语言中的词句与范畴因为其含义的明确性会使得人们将对于事实的表达限定在某个既有的框架之内。[2]事实与对事实的表达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间隙,表达不可能完整地呈现事实,因此这个间隙最终导致了启蒙的异化。[2]也就是说,表达和事实之间,既存在着差别性又存在着同一性,这既受制于语言表达者的目的也取决于表达者本人的特性。如此种种,就是《启蒙辩证法》一书探讨的主旨所在:合理性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启蒙的核心在于追求真理,祛除幻想和假象,原本是为了达到祛魅化的状态,却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异化状态。奥德修斯看似在理性的支配下战胜了大自然,实现了自我持存,赢得了胜利。但“实际上,奥德修斯从未占有一切;他总是要等待和忍耐,总是要不断地放弃。他从来没有尝到过莲子的滋味,也没有吃过太阳神许珀里翁的牛,甚至在他穿越海峡的时候,还必须得计算被斯库拉从战船上掠走的船员数目。奥德修斯披荆斩棘,奋勇直前,战斗就是他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他的伙伴所获得的荣誉,他们只有通过贬低和祛除他们对完整而普遍的幸福的追求,才能够最终赢得英雄的头衔”[1]47。“牺牲与放弃”在奥德修斯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奥德修斯的理性包含牺牲、狡诈、工具性,也就是不仅对神明、自然力量,而且对他人也是工具性的利用态度。他没有时时刻刻都尊敬所有的神明,更不会敬畏自然力量”。[3]奥德修斯为了成就自己的主体地位,练就自我,不惜牺牲和破坏生命的各种功能,并割裂自我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压制自然,控制自然。看似取得了一番成就的奥德修斯,实际上却走向了自我的异化。如果说奥德修斯作为启蒙理性的代表,通过理性破除了神话在大众心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人们从崇拜神明转向崇拜理性,那么在理性的背后潜藏着的无疑是另一个神话——神话原本的地位被理性所取代,它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成为了新的神话。
三、对启蒙的反思
《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这篇附录对于启蒙理性的批判,以及对神话与启蒙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的探讨,其目的并不是进行纯粹的理论批判,而是指出启蒙发展路径的困境所在并寄希望于启蒙能够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4]虽然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最悲观的著作[5],但在《启蒙辩证法》的前言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指出:“并不是像文明批判者(如赫胥黎、雅斯贝尔斯、伽塞特等)所说的那样,关键在于作为价值的文化;而是在于,如果人冥顽不化,启蒙就必须在自己身上做文章。关键并不在于维持过去,而在于让美梦成真。然而,今天,过去依旧在维持,而且是以破坏过去为代价。直到19世纪,教育一直都是一种特权,牺牲的是未受教育者的幸福。到了20世纪,工厂像铁幕一样,消解了一切文化。文化捍卫者认为,如果出卖文化没有破坏经济成就,代价或许就不会如此昂贵”。笔者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于启蒙运动并不完全是否定的态度,其中不乏持有对启蒙的本身肯定的态度,更带有一种对启蒙在今后的发展的期待,期待它能够向着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而对于启蒙在当时的发展情况而言,他们对启蒙运动带有着恨铁不成钢的失望的态度。由此可见,二者对于启蒙运动本身的初衷是带有肯定和期待的感情色彩的,但却对它后来逐渐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趋势而感到失望与不安。“启蒙以普遍真理自居(激进地)否定一切他者,不能容忍任何“特殊的真理”,这才是《启蒙辩证法》的反思批判所在”。他们希望启蒙能够从另一个神话的统治中解脱出来,以便能够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正如他们在《启蒙辩证法》的前言里所说:“其中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想准备好一种实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与盲目统治的纠结之中解脱出来”。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毫无疑问,对于启蒙的批判目的是在于能使被笼罩在理性神话里的世界有所改变。在理性神话充斥着的资本世界里,原本的进步都逐渐走向了退步。现代社会在资本逻辑的指引下,使得大众将自己对于幸福、美好、成功等概念的理解都整齐划一地装进了千篇一律的框架内,个体被社会所同化,逐渐丧失掉了自己的特殊性。启蒙神话笼罩着的世界使得人们不断地趋向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断地以破坏自我、破坏大自然、丧失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总之为了使理性的主体获得更多的利益,不惜牺牲任何代价,人们就这样无形之中被理性的神话统治和支配着。社会的进步逐渐走向了对立面,如何使启蒙走出神话的笼罩而走向合理化?
“合理的启蒙勇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是走向极端与偏执,而是力主和解;彻底的启蒙仅仅是对极少数未来哲学家而言的,合理的启蒙才是针对所有人的。”[7]激进地质疑一切启蒙是不可取的,盲目地崇拜理性更是不可取的。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做到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否则只会走向自我毁灭。反观我们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有时会不顾具体历史条件、不顾有无消极后果一概强行推行着“极致的启蒙”。因此,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生产力发展的脚步似乎一刻也停不下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但是当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不难发现,外卖方便了人们就餐的同时,是否有可能滋长部分人的惰性?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在极大增加容积率的同时,与老式的住宅相比,人与人之间的热情被冷漠所代替,邻居之间的熟悉被陌生所代替、一次性用品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的污染、人类肆无忌惮地对自然资源无止境开采最终导致的环境恶化……所以,对于启蒙的反思不应该局限于启蒙本身,同时也应当从人类自身来进行反思。这是因为启蒙的初衷是为人类带来福音,只不过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资本逻辑的驱使逐渐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走向了极端与偏执,越出了自我的合理边界。笔者认为,倘若启蒙能够脱离极致化发展的轨道,向着合理化发展,符合人类社会长久发展的价值尺度,那么它一定还潜藏着无限的发展前景,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