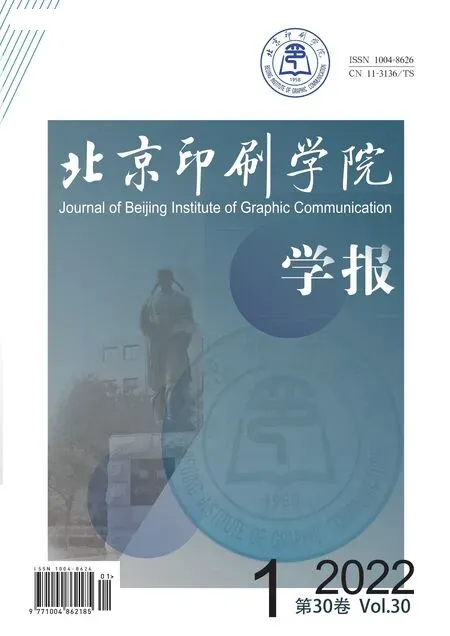王重民与季羡林交往交流考
王京山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王重民先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和敦煌学家,而季羡林先生是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二人同为北京大学教授,共同经历了若干时代风雨,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场景交往交流,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众所周知,季羡林有记日记的习惯。季羡林的日记从他大学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耄耋之年。但是,季羡林的日记没有全部出版。目前整理出版的主要包括他大学时代的日记《清华园日记》、德国留学日记《留德岁月》,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在北大任教初期的日记。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日记尚未整理出版。王重民也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迄今为止王重民的日记均没有公开发表。笔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重民全集》编纂”也没有整理出版王重民日记的计划。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王重民和季羡林的日记均付诸阙如,而他们二人的交往交流大多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目前只能从公开出版的文献中搜寻蛛丝马迹,来还原他们交往交流的若干场景。
一、王重民季羡林的浅交往——共同参会
从1946年季羡林回国任北大教授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此时王重民虽然也是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但他的本职是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曾任代馆长,而季羡林是北大新晋教授,属于学术界的后起之秀。他们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往往会共同参加一些会议或学术活动。在这些会议上,他们互相见面、互闻其名但没有更深层次的交往,因为参会人数众多,他们交流不多。目前所见,有以下两条记录:
其一,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宋云彬在其《北游日记》中记录了一次王重民和季羡林共同参加的宴会。
1949年年初,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宋云彬与一批著名人士来到解放不久的北平,参与了一系列社会活动,后来又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在1949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王重民和季羡林共同参加的一次宴会:
上午赴北京饭店,出席学协理事会。中午偕圣陶夫妇暨振铎、彬然同赴北大俞平伯等之宴。列名具柬邀请者凡十七人:俞平伯、王重民、朱光潜、金克木、郑天挺、林庚、吴晓玲、季羡林、沈从文、顾颉刚、向达、孙楷弟、黄文弼、魏建功、杨人楩、韩寿堂、赵万里。地点为孑民纪念堂。[1]
这里的学协,是当时“学术工作者协会”的简称。这里的“圣陶”,即后来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这里的“彬然”,即教育家、出版家傅彬然。宋云彬是和叶圣陶、傅彬然一同由香港赴北平的,所以他们也常常一起活动。这次宴会是俞平伯等人主办的,出席者都是一时俊彦,王重民和季羡林都受邀出席,可见他们当时在北平学术界的地位。
其二,王重民、季羡林共同参加在北平图书馆举行的《赵城金藏》座谈会。
1933年,秘藏八百年的国宝《赵城金藏》在山西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重见天日。经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赵城金藏》安然无恙。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4月30日,4000多卷的《赵城金藏》最终入藏北平图书馆,成为北平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北平图书馆接收《赵城金藏》后,经过初步整理,挑选部分经卷展出,并在1949年5月14日邀请各界人士举行展览座谈会,为这部国宝“会诊”,商讨如何修复和保藏办法。王重民和赵万里代表北平图书馆出席座谈会,季羡林作为知名学者也参加了该座谈会。[2]
在会上,王重民作为北平图书馆副馆长首先发言:
“此经为国宝,经八年抗战,跋涉千里而入本馆。荣负保藏之责,将努力修整,以便与本馆原存192卷并为一体,望各为报道,每位赐以宝贵意见。”[3]
这是季羡林第一次出席保护和抢救《赵城金藏》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季羡林是否发言不得而知。但就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决定修复《赵城金藏》,到1965年《赵城金藏》修复完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任继愈主持下,以《赵城金藏》为底本重编的《中华大藏经》完成,其中就蕴涵着季羡林的贡献。[4]
当然,王重民和季羡林共同参会的情况肯定不止以上两次。总体上,这些共同参会的经历虽不足以深入交流,但是共同参会使他们彼此逐渐认识熟悉,为进一步交往交流打下了基础。
二、王重民季羡林的深度交往交流——合作研究
王重民和季羡林入职北大的时间前后相继。季羡林1935-1946年留学德国,1946年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而王重民1934-1947年在法、英、德、意、美等国著名图书馆考察并搜求流散国外的中国珍贵文献,1947年回国,在北平图书馆任职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创办图书馆学专修科,直至1952年王重民辞去北京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即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职务,在北京大学专事教学科研。
王重民、季羡林二人的深度交往交流具有深厚的基础。他们从事的学科专业相近,学术研究交叉融合度也很高。他们交流互动的第一个学科领域是图书馆文献领域。王重民长期担任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副馆长、代馆长。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是国内文献资料收藏和学术研究的重镇,与北京大学互动频繁;而季羡林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同时担任北平图书馆评议会成员。[5]在二人的交往中,王重民丰富的文献学、图书馆学知识为季羡林回国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支持。他们交流互动的第二个领域是史学。王重民和季羡林都擅长历史研究,都是当时国内史学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王重民自不必说,他的史学成就有目共睹。而季羡林归国后,研究中印、中外文化交流史成果斐然,很快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新星。[6]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时,季羡林就名列18位学者组成的第一届编委名单。[7]1956年,季羡林以其历史研究的成就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共同的学科背景为他们的交流交往提供了基础。他们交流互动的第三个领域是敦煌学。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等一批人远赴英法,寻访、抄录、整理敦煌卷子,编辑敦煌劫余文献目录,其对敦煌变文、曲辞等方面的研究,不但使敦煌学研究别开生面,也以其巨大成就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代表人物。[8]
季羡林的敦煌学研究也成就斐然。后来季羡林成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敦煌吐鲁番研究》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自1983年起直到2009年去世,季羡林一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一职。这期间正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突飞猛进的时期,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诸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时期。[9]王重民、季羡林二人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共同兴趣,为他们的深入交流乃至合作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
新中国成立前后,王重民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教育教学上来,但到1952年之前王重民在北大还是处于“客卿”的位置,他的本职岗位还是在北京图书馆[10],此时他利用自己图书馆学文献学的专长为季羡林提供了若干研究资料。而季羡林留学归国后,因资料缺乏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限制,无奈放弃了原先的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把精力用在与印度有关、国内资料相对较多的印度史、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上来,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敦煌学方面的研究。在季羡林这个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王重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11]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学研究中,王重民季羡林有了更多的交流互动乃至合作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也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之与印度研究相结合。1950年,季羡林和曹葆华合作翻译了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就是二者结合的结晶。后来,王重民又告诉季羡林马克思还写有《印度大事年表》,季羡林听后既感觉自己“孤陋寡闻”,同时又有点“半信半疑”,问了周边的朋友,都说不知道此事。[12]王重民就借来该书的俄文版给季羡林,季羡林看后十分高兴,遂决定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供研究印度史的朋友们参考。该书翻译完毕后,季羡林对马克思实事求是的好学精神极为感佩,在《介绍马克思的〈印度大事年表〉》一文中写道,“马克思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当然更不是专门研究印度史的,但他竟能对印度史下这样大的功夫,做这样彻底的工作,可见他的实事求是的好学的精神是如何伟大。”[13]这事实上成为季羡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在这个过程中,王重民及时提供了文献资料,对季羡林的研究起到了支持和指引导航作用。[14]
王重民和季羡林对于敦煌学和西域研究注力颇多,也曾合作研究,主要表现在他们二人共同为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写本影印本作跋。回鹘文是我国维吾尔族先民在公元9~15世纪使用的一种文字,目前留存文献较多。《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写本是一部有代表性的回鹘文文献,是汉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回鹘文译本,也简称为《玄奘传》。该文献大约在1930年出土于我国新疆。该文献被发现后,很快被文物商人分割出售。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派其弟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赴新疆购得240叶,入藏北平图书馆;另外8叶由法国考古学家海金(Joseph Hackin)所得,后交予德国学者葛玛丽(Annemarie VonGabain,1901—1993,又译冯·加班),123叶被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97叶流向俄国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5]这样,世界孤本回鹘文《玄奘传》星散分藏世界各处。1932年葛玛丽女士从北平图书馆借走收藏的240叶《玄奘传》写本进行研究,数年不还,几经催要未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北平图书馆感觉索要更加无望。孰料二战结束后葛玛丽女士不但将《玄奘传》原本完璧归赵,还把原属海金的8叶也一并送给北平图书馆,至此北平图书馆藏有回鹘文《玄奘传》共248叶。[16]
1951年,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民族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的赛福鼎先生在北京大学东语系看到几种回鹘文古籍,他大为兴奋,认为这些书对研究维吾尔古代语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久,国家民委即派员前去联系复制这些回鹘文古籍。王重民、季羡林与向达等认为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玄奘传》更为重要,于是请冯家昇先生进行整理,并于1951年影印出版4册影印本。[17]在影印本出版前,王重民、季羡林两位先生合写了一篇跋文,详细介绍了回鹘文《玄奘传》的曲折经历及其影印出版的重要意义。
这篇跋文末署名为“王重民、季羡林谨记于北京大学”,落款时间为1951年6月18日,应该是在回鹘文《玄奘传》写本影印出版之前写就的。这是王重民季羡林二位合作研究的明证。该篇跋文没有收入刘修业的《王重民教授著述目录》,也没有收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媛的《〈王重民教授著述目录〉补遗》,故此北京大学王锦贵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重民全集》编纂”的编纂目录亦未收此文。此文被收入《季羡林全集(第30卷):附编》,由国内季羡林研究专家叶新教授发现,告知笔者,经重大项目管理组认定补充编入《王重民全集》,为笔者从事《王重民全集》编纂开展王重民先生著述资料收集整理以来的一个重要收获。
三、王重民季羡林的特殊交流——余音袅袅
1956年,北大图书馆学专科改为图书馆学系,王重民任系主任。此后他们二人的交往不多。1960年初,王重民、季羡林等共同参加了北大向达教授发起的“敦煌学六十年”专题讲座。[18]王重民和季羡林一起共同为推动敦煌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文革”结束后,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季羡林担任首任主席,他在学会任务中提出要“在王重民先生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基础上重编《敦煌吐鲁番遗书总目》”[19]。从这个意义上说,季羡林是在完成王重民先生未竟的事业,并将之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1978年5月王重民获得平反,而季羡林也重新恢复名誉,还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新的春天,大作频出。约略统计,从1978年至2002年,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季羡林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20]按说,王重民和季羡林的交往交流因为阴阳两隔,已经无法延续了。但斯人已去,余音宛在。在此略述一下王重民去世后季羡林为王重民及夫人刘修业女士所做的贡献及展现的情谊。
王重民逝世后,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将主要精力放在王重民遗著的整理上,先后整理出版王重民著作7种,整理发表王重民论文16篇,以个人之力推动、组织了20世纪80年代的王重民研究。[21]1992年,王重民最后一本遗著《冷庐文薮》终于出版,刘修业夙愿得偿,次年仙逝。季羡林和其他著名学者周一良、宿白、周绍良、陈岱孙等一起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贵宾室举行的刘修业先生追思会,高度赞誉她晚年对王重民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22]
业师王锦贵教授还对笔者讲述了一件小事,从中可以看出季羡林对王重民的挚友深情。2008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台湾胡适纪念馆牵头编纂《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由王锦贵任主编。书稿编竣,需要找一位名人题写书名,王锦贵便想到了季羡林先生。当时季羡林身体抱恙长住三〇一医院,王锦贵通过北大校办找到季羡林的助手,季羡林的助手问王锦贵:“季老因身体原因轻易不给人题字,除非是亲朋故旧。请问王重民先生跟季老熟悉吗?”王锦贵成竹在胸,对季羡林助手说:“您只要跟季老说,是给《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题字,这两位都是季老极为熟识的,他一听就会明白。”果然,很快季羡林题字就送到了王锦贵手上。一年以后,季羡林驾鹤西游,这件事为王重民和季羡林的交往交流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王重民和季羡林的交往交流写下了一段朋友交谊的佳话。昔人有言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又言“君子喻于义”,回看王重民与季羡林几十年的交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他们之间的切磋交流、惺惺相惜,为我们留下了极可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