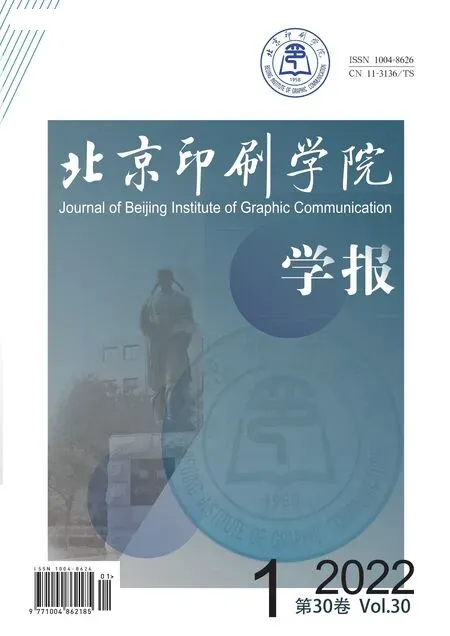20世纪以来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研究体系与方法论
张 佩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北京 102600)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下文简称《分类》)二十五卷,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这是现存最早的李白作品注本,非常珍贵。其流传时间长,传播范围广,引起普遍关注,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与不可低估的地位。
笔者长期致力于李白古注本研究,于此重点谈一下20世纪以来的《分类》研究,对其学术动态、学术史进行梳理,进而对李白诗古注本研究的体系与方法论建构展开讨论。
一、关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注本文本
(一)关于古注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考证
1.从宏观、中观视角对古注本整体展开全幅研究,侧重建立起框架,择出具有探索价值的阐释点
詹锳、杨庆华首先确认了《分类》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研究李白诗,这部书还是不能忽略的”[1],初步整理出诸版款行、注释特征,为后续研究开山之本。芳村弘道、刘崇德进一步指出,“(《分类》)在为数不多的李白集注本中,不仅最为古老而被珍视,而且有‘详赡’之誉”[2]。作者考证出成书时间,“大致当完成于《序例》所署至元二十八年(1291)”,介绍了原本系统各版本的收藏处所与版式特点、删节本删注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原文问题。芳村弘道、詹福瑞在进一步厘清删节本体系郭本与玉本的基础上,对注释内容、注家及其动机等展开讨论。[3]71-73以上三篇,为《分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振龙《李白诗古注本研究》比较全面地梳理了白诗主要古注本,对诸家注释方法、思想形成系统性研究[4]。他对《分类》用功尤深,沿着原著章节脉络,增补材料予以专论[5],使注本体系呈现更为明晰。
2.从微观视角切入,对于杨萧注进行考辨,侧重于细读文本中发现问题,同时虑及接受中发生的新变
胡振龙复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明代林兆珂《李诗钞述注》的解说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以不误为误,二是未能指出它存在严重抄袭。他指出:“其书篇幅长达十六卷,但基本上是抄袭他人的见解,主要抄自宋代杨齐贤注和元代萧士赟的补注,也有的抄自明朝人的著述,如郭云鹏本所收徐祯卿评语以及唐汝询《唐诗解》中的见解”[6]。这种做法理应受到指责,四库馆臣却于此不置一辞,实不应当。
这一研究的价值有三:除杨萧注与太白诗的匹配程度之外,将侧重点置于注释本身的传播与接受;予四库馆臣对林著的解题进行有效批评,端正注释本源所在;在不同注本的比对中展现杨萧注的价值。
(二)运用杨萧注对相关作品、注释或人物进行考证
1.乐府诗类
(1)关于李白乐府诗古题、具体篇目等展开研究
聂石樵将北宋人见闻与记载作为信史资料,来考证《蜀道难》本事,支持其“讽章仇兼琼”的观点[7]。其中,萧注提供了一则掌故,被用作辅证。
李从军旨在辨析《梁甫吟》产生的确切年代与特定环境,故于论证前将萧氏观点,即“主有事实”作为对本诗解读中形成的重要观点之一[8]。
康怀远将萧注作为乐府解题的重要观点来征引。萧注:“此诗其为明皇宠武妃废王皇后而作乎……唐诗人多引《春秋》为鲁讳之义,以汉武比明皇,中间比义引事,读者自见。”作者认为,“明皇宠武妃废王皇后,”事在开元十二年,当时李白尚在蜀中,严习格律、辞赋,“均无意于朝廷宫闱之废立”,因此推知“《白头吟》之不作于蜀中昭然明矣”[9]。
王立增指出,由唐至清对李白乐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注解与探讨比兴寄托之意等方面,较零散,重感悟。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研究成果不多。解放后前三十年,出现了专门的著作。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研究趋于细致化和科学化。作者强调,元代李白乐府诗研究较有成就的是萧士赟和范椁。萧氏《分类》中于乐府诗之笺注,多能阐发其中的比兴寄托之意,对后世的影响颇大[10]。
(2)从注释征引文献中汲取信息,去整理、研究其他乐府类作品或典籍
喻意志认为,清人王谟所辑《歌录》“有遗漏及考据失实者”,故对其全部佚文加以分析,以资提供一份可信的音乐文献辑佚成果。其中就包括对杨萧注中所引三处《歌录》内容(依次为《阳春歌》《白马篇》《怨歌行》三篇题下注)进行仔细辨析,强调“第一条《歌录》乃《乐录》之误。第二、三条《乐府诗集》未引,而李善注引之。故萧氏所引《歌录》亦出自《文选》李善注,而非其原书”[11]。
2.李白研究类
这一类型发挥了注释最基本的义疏功能,重点在于研究者对“旧材料”“旧证据”版本的选择、整体熟悉程度以及运用的方法。
牛宝彤探索李白文思想时首先指出,传世的杨齐贤、萧士赟、胡震亨三家注仅注李白诗,置李白文于不顾;至王琦,方将诗、文合注,较为完备[12]。
郁贤皓全面总结了二十世纪初关于李白生平方面研究的情况。作者指出,“李白的研究除各种诗话有零星的评说外,宋、元、明、清注释李诗的仅有杨齐贤、萧士赞、胡震亨、王琦四家;对李白的生平历代几乎都未深人研究。”[13]全文侧重点不在古注本研究,却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思路,即注意在分散的材料中整理、挖掘太白生平蛛丝马迹,以寻求新的突破。
杨海健从注本角度考证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来源与纂集过程,对于注本的特色、彼此间关联有着简洁清晰的描述;尤重杨萧注的影响力、分类依据、流传与接受情况等,为接下来的论证张本[14]。
朱易安站在李白接受史立场,从诗文本细读角度去审视《分类》,认为以此为端“李白的诗歌文本开始受到重视”,萧氏是在杨注基础上展开这项工作。这不仅意味着完整的、成体系的李白诗文本阅读,同时受“千家注杜”接受环境影响,李白诗歌文本阅读的回归在“李杜比较”中展开;提倡李杜并重,才有可能激发起李白诗歌文本阅读的回归[15]。
3.明代文学研究类
此类研究多是基于古注的文献保藏功能。明代在诗文别集刊刻翻刻、编纂方面相当活跃,出版业发展态势甚好。明政府曾下令严禁篡改旧版文字、行格,这就为后世提供了稳定可靠、富有文学文献学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而作为典籍重要构成的注释自然也日渐得到重视,与明代文学研究的关联度日渐增高,成为后人研究有明文学的重要依据。
(1)关于明代文学家及其作品
耿传友以实证研究方法,对明末作家王次回的家世、生平、著作、交游等进行考辨。论证中对李白注文进行辨析,并以此作为钩沉史料的依据[16]。
黄艳芬论述了许自昌的家世生平、园林家乐、戏曲交游活动等,进而剖析其思想发展与戏曲创作情况。认为许自昌的戏曲创作明显地带有戏曲文人化的特点;崇尚侠义,使其戏曲具有个性化;晚期思想受到佛道影响,作品呈现神仙道化的倾向[17]。
文中没有太多借鉴许自昌刻书、藏书情况所提供的信息来增加分析的广深程度,却给我们进行注本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即在分析《分类》许自昌刻本时对刊刻者同时期的交游、创作倾向、审美变化等加以考虑,有助于理解他对杨萧注兼及太白诗文的接受、变改及传播情况。
(2)关于明代刻本及其流布
杨军厘清了明代翻刻宋本的历代著录与现存状况。研究中涉及对李白古注本编纂、刊刻的辨析[18]50。作者特重从明代整体出版环境切入,使注本研究延伸至出版史、出版思想史领域。
徐学考证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哈尔滨师范大学所藏七部入选古籍,其中包括明嘉靖刻玉几山人曹道本《分类》二十五卷。作者详录该本版式,特别言及“版心下刻工有‘马’‘仁’‘天赐’‘信’‘陆敖’,查‘陆敖’或‘陆鏊’,明嘉靖间刻字工人,刻过《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曹道本等书”[19]。笔者点校《分类》时,遍查国图古籍馆藏玉几山人本,并未看到。哈师大藏本,正补此缺。
林柳、孔庆茂则对建阳书坊刻本进行“小命题”研究,将范围缩至明代中期;注重以刻书世家研究为基础,多角度分析此期坊刻本特点。这有助于我们从明代书坊格局、传播生态方面去理解杨萧注本及其删节本系统在明代的流布[20]。
4.整体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
殷春梅强调,宋人开始“真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开展李白诗文搜集、整理、编纂、刻印,并对李集进行分类、编年、注释及考证”。此外,“出现了第一个对李白诗集进行注释的人,这就是杨齐贤的《李太白集注》”[21]。与前人诟病杨注“博而不约”有别,作者尤重其开山意义。
孙语林以国图藏善本初盛唐别集序文为基础,对唐宋两代文人所撰初盛唐别集序文进行比较,探寻其发展流变之本因[22]。此类研究于注本探研亦有所益,其视野不再蜷局于单个诗人别集,是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理念、编选纂集思路等。从文学研究别集与从文献角度入手尚有差别,前者混融、线索性强,后者侧重于条分缕析中发现隐藏的信息。
5.与其他李白集注本进行比对
詹锳《我们是怎样整理〈李白全集〉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前言》[23]开宗明义,“本书的编写目的,是要写成一个新注本,超越王注取代王注”。因此,詹先生从李白集整理实践角度出发,对于过往注本的情况及彼此间的关联予以系统回顾与评议。他在论证“新注何以超越王本”的过程中,本于具体实践需要与经验,对诸本的分析比对显得更为精细,对于后来者研究杨萧注乃至整个古注本系统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姚璐对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进行探研。由于学缘关系,作者成功运用一手访谈资料,使今人注研究深入全面,呈现出活跃的学术气氛。她将研究“置于李白研究史的进程中来观照,并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分析”[24]。对今人注本予以重视有助于换位审视古注,有所发明。
宋星雨对《汉语大词典》中征引李白作品书证进行归纳统计。做了“文献校对”与“体例辨析”,前者考察作品内容在用字上的差别,后者考察立目失误、书证失误、书证纰漏等等[25]。研究具有语料还原性质。
方旭娟以李白诗异文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诗文对校各版本,归纳出李诗异文的特点、成因及研究价值[26]。这种将“异文”单独提炼出来作为核心考察对象的思路,于李集诸本探研有益。
谭尧尧分析了明代李白集序跋分类、形成原因、内部关联及影响。在梳理明以前序跋时,强调“元代萧士赟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影响巨大,为后世大量翻刻”[27]。
6.李白集版本叙录或相关刻本研究
吴则虞介绍了元代家刻本的整体情况,特别言及建阳、建安刊刻之盛,整理出书坊所刻宋代传本,其中就有至正元年万玉堂刊刻《分类》二十五卷[28]。
詹锳综合分析了宋本、仿宋本李白诗文集,指出“一种题作《李太白文集》,一种题作《李翰林集》。前一种是蜀刻本,元人所刻杨齐贤、萧士赟注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及明郭云鹏删节杨萧注加上散文的《分类补注李太白集》,都是从这个板本系统来的”[29]。先生认同杨桦的观点,即“宋甲本宋乙本俱为南宋高宗时刊本”[30],并结合文献、传播现象等对版本情况予以进一步考证[31]。
申风《李集书录》[32],是李白研究中一篇重要资料论。以现存李集为线索,简述其编纂付梓年代及有关书录记载;按版本源流体系分类编排;后附近世研究专著,极便检索。
叶树声讨论明代苏常私人刻书。文中言及《分类》版本系统中的郭云鹏刻本,侧重讨论书坊本身的特色,即摹刻逼真,堪称绝妙[33]。受此篇启发,或可对郭氏“摹刻精美”传统下大肆删减杨萧注,增补徐祯卿注的行为,从坊刻角度予以深入讨论。
李坚详录郑州大学图书馆藏《分类》的版本信息。标注卷端题:“春陵杨齐贤子见集注,章贡萧士粹可补注,明长洲许自昌玄甫校。”[34]
王永波认为明代编纂、评注、刊刻李集多达六十余种,编刻参与者人数多、素质普遍较高,不少版本得到了修订刊刻,对白诗传播、接受产生深远影响。此期,《分类》被多次翻刻,多达二十种,“成为李白诗流传史上单部著述翻刻最多的书”[35]。
陈君忆比较宋本系统和元本系统的李诗集,指出《李诗选》的选源为元本系统的《分类》,而杨慎亦用宋本系统之乐史本对《李诗选》进行校勘[36]。
二、关于注者及其注释
(一)关于注者生平与交游的考证
关于杨齐贤、萧士赟个人生平、交游方面的研究一直无法与《分类》注本本身相比。作为李白诗经典化过程中重要的构成,《分类》在历史时期便占据着不容忽视的位置,也被今人广为征引,作为研究白诗的可靠文献资料。与之不相符的是,两位注家没有得到特别的关注,除却其生平资料稀缺,还在于研究者对探索角度的选取不同——许多看似关联度不高的文献都提供了注家生活年代的语境线索;同时,稍稍摆脱“注释者”的身份,将二人置于新的学术视域他们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在这方面,胡振龙、张佩做了一些较为集中的研究:
胡振龙认为“南宋注李白诗的杨齐贤生卒年月虽不可考,但其登进士第的时间为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其生活年代显然晚于“天会二年(1124)进士”[37]王绘。他在探索萧氏注释思想及源流时自然融入对其生平、交游,以及注释李诗动因的探索,为后续研究注者提供了清晰的图式。
张佩考证表明,杨齐贤于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前后担任过夔路运司帐干。颇有“挂职”意味,且久居闲职,故极便宜观察蜀地风土人情,收集李白散佚诗文及轶闻事迹。他看到过当世所存太白诗篇较萧氏更多,其“记览极详博”的特点是研究《分类》时必须高度重视的,不宜因后人议论导向而轻易否定[38]21。此外,她将萧士赟个人研究从“注家”体系、李白“接受者”群体中单独列出,转为对萧氏一门“家族文学史”的考察。研究以生平、诗文资料较为丰富的萧立等作为核心考证对象,次之以萧澥,推而及诸作为子辈的萧士资、萧士赟,最后整理出萧氏族谱与诗学风尚[39]。文章能稍补以往注家生平资料单薄之缺。
(二)对于杨萧注释进行考辨
注释具有保存文献,保藏信息的重要功能。这些信息中,由注家经眼,记录当时所见所闻的类型则显得尤为珍贵,可作为考辨对象,于本位中提供观点与态度等,也可作为考证依据,从“旁观”视角偕同厘清问题。研究者对于此进行考辨,往往将其置于不同的序列中进行。
1.置诸李白诗古注本体系中进行比对
杨注因借萧氏补注以存,故而一直表现出“独立性”较弱的状态,研究者往往二者并举,再与白集其他注本比较。
李春光指出“《四部备要》取便研读,多用注释之本”,且注本往往较《四部丛刊》本精详。如《李太白诗集》,《丛刊》用宋人杨齐贤集注本,“尚有疵谬,不够精赅”;而《备要》用王琦集注本,此本在杨、萧、胡三家注释基础上,“专精研磨,探幽索隐,又有所增益,并订正了许多讹误”[40]。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的侧重点在于比较《备要》与《丛刊》,李集注本于此仅作为例证,并非作者考证对象。换一种角度,《丛刊》本选择收录现存最早的李集注本杨萧注,其文献保藏、传播意义则更为突出。
徐小洁研究明朱谏《李诗选注辩疑》,探讨了朱注与杨萧注的关系,指出“士赟的笺释与辨伪对朱谏影响更深,而朱谏对之保持理性的批判态度,有借鉴,也有纠正;有赞同,也有异议,反映了朱谏独立的批评意识”[41]。这就从其他注家的视角对杨萧注进行讨论,颇具“旁观者清”的意味。
蒋晓光认为,王琦“创造性地以‘情景交融’思维和文学性的‘讽谕’观照诗学,这是他取得巨大成就、突出前人的原因”,此外,其说诗理论、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42]。与徐小洁论朱谏一样,作者同样注重将王注与杨萧注进行比较。
孙易君探索王琦注“后出转精”的深层原因。她将王注与杨萧注进行了溯源式比较,认为注李诗的广博倾向自杨萧便已开启,这与太白本人丰厚的知识储备,传奇的人生经历亦相匹配[43]。文章对作者、注者风格的体认有别于前人“不协”之论,注意到诗风潇洒飘逸与诗人渊博广深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不可兼容的关系。
2.置诸《分类》版本系统中展开研究
汪桂海记录了国家图书馆藏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分类》的版本信息。文中言及“萧氏虽对杨氏集注之不足有所纠补,此书卷帙浩博,犹不能无失,唐觐《延州笔记》即曾予指摘。然所注多征引故实,兼及意义,大致详赡,足资考镜”[44]。
张佩认为明郭云鹏校刻本《分类》引用了徐祯卿若干评注。考证徐注时,作者将其与杨萧注进行比较、辨析,指出徐注弥补了《谈艺录》“较少针对某一诗人作品进行专门地、集中地点评”这一不足,也为解读李诗保存了珍贵的资料[45]。此外,王琦在借鉴萧注时做了以下工作:大胆质疑,细致辨析;批判继承笺注成果;纠正刻意比附之处。综合而观,王琦对萧注的吸收经过深思熟虑,既不全盘接纳亦不轻率否定[46]。作者还指出,杨萧两位注家在解读中倾注了大量心血:率先指明解诗焦点、难点所在;对李诗进行全面校读。当然,注中仍存在明显的讹误、疏漏,甚至刻意比附,今人运用古注时当详加甄别[47]。
(三)运用杨萧注对相关作品、注释或人物进行考证
运用杨萧注对相关作品、注释或人物进行考证,由来已久。可以说,这一类始终伴随着古注本研究,起步早,对注本使用频率高,挖掘探索亦较深刻。
1.在太白乐府诗研究中,大量运用杨萧注
乔长阜探讨《蜀道难》主题,开篇述说了五种观点,其中便有“元人萧士赟的讽玄宗幸蜀说”。因此说“业经前人证诸史实”已被推倒,作者未特别展开讨论[48]。
安旗指出萧氏谓《公无渡河》“讽止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虽无确证以证诗,却点明“此诗必有所指”。诚因如此,后世如陈沆等解此诗,都会注意到与史实关联去发掘深意[49]。
补拙对萧氏所言“水精帘以水精为之”产生质疑,考索后认为《辞源》注“形容质地精细而色泽莹澈之帘”,是正确的[50]。对诗歌中单个语汇实指的研究看似细微,实则于作品、诗人影响甚巨,有必要对旧注进行仔细斟酌。
李从军指出诸家于《梁甫吟》主旨歧议有七,萧士赟、沈德潜等“主有实事所指”。作者认为这“未能准确地指出此诗的产生年代、未能准确地指出产生此诗的特定条件和具体的环境”[51]。
杨明采用“诗史互证”来论证李白对李林甫、杨国忠持有不同的政治态度。他指出萧氏论《远别离》主旨为“无借人国柄”,实属有见地;只是将创作时间定于天宝末,“也还不够准确”[52]。
郑文论《梁甫吟》诗旨,注意梳理出从古注至今注的逻辑轨迹[53]。与其他文章一样,萧注被视作解读的“原点”,辨析诗意的“首发”参考。
丁毅、逢春《论李白〈蜀道难〉》检讨诸家观点,其中“元萧士赟说《蜀道难》是讽玄宗天宝之乱幸蜀而作。”[54]作者强调学者们从多角度讨论《蜀道难》主题,大有裨益,可启发后学去理解名篇。
康怀远考论《白头吟》系年,对萧注、胡注予以细辨,认为萧氏言“此诗其为明皇宠武见废王皇后而作”颇有代表性,不过“事在开元十二年”,白尚在蜀中,登览、求学,“均无意于朝廷宮闱之废立”,故“《白头吟》之不作于蜀中昭然明矣”[55]。
张瑞君认为,太白乐府中一些关键语词的深层内涵并未得到有效解读。比如“雉子班”的“班”与“斑”,萧注作“雉子班”;杨注征引梁吴均《雉子班》开篇,亦作“可怜雉子班”,皆为“班”字。据此,作者指出“杨齐贤时代早于郭茂倩,可见《乐府诗集》成书以前,就写作‘雉子班’,意为一群雉子或演群雉的戏班”[56]。
2.在太白生卒年、入仕等问题的讨论中,将杨萧注作为“史料”引证
舒大刚对李白纪年史料、纪年诗文、相关注释等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诸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占有史料不充分、擅疑古书、误解古人的毛病”[57]。此中,杨萧注亦被用作史料、考辩的对象。
郭建伟参乎“阳冰序”“魏序”、李诗、碑传、诏敕等,推定李白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春。至于广德年间诗文则“大部分当已被萧士赟误作赝品删汰了”。“萧士赟固守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故而大加删削杨注所引“广德以后事”,“无形中增加了对李白实际卒年考证的难度,直接导致了李白卒年的长期被误说”[58]。
3.在唐诗学研究、李杜比较研究、具体作品解读中,从杨萧注中汲取相关信息,以增加理论探索的广深程度
黄志辉研究表明杨齐贤已注意到“赤壁”的同名异地问题。所谓“今江汉间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完好保留了宋时关于赤壁的情况,为今人考察地名指称提供一据[59]。
杨玉忠比对萧注与元人杨维祯《西湖竹枝歌》,认为“赧郎”就是“吴音也,歌者助语之词”。王琦指萧注“强解”,反使诗意解读不通[60]。作者重视旧注价值,注意与同时期其他诗人作品、注释展开横向比对,使考证更为严密。同样考察“赧郎”,杨琳则将以杨注为据,认为此词“是由李白创造的,后世的个别用例应该是李诗词语的因袭,因为元代以前找不到‘赧郎’的第二个用例”[61]。
孙春青全面探讨了明代唐诗学的内容、特质,指出“明嘉靖至万历中期,出现了唐诗选本热。李白、杜甫和初盛唐诗人的别集、合集后来居上,成为唐诗刊刻的新热点”[62]。研究涉及萧注,从中观、宏观两个维度去审视注本的编纂、刊刻情况,对注本在整个诗学中位置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
陈建森评论《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神思”贵在“穿越”,“李白的‘神思’在宇宙大化中穿越飞扬而‘无敌’于天下。”[63]文中征引萧注侧重其诗文赏鉴方面,是作者挖掘太白古风诗歌“穿越”线索与“一体变易”的重要依据。
4.借助杨萧注对太白诗异文、太白集文本多歧状态进行考辩,细化对文本经典化历程的探索
经典化过程往往曲折,未必越变越好。有时可能是技术处理,有时也只是选择更流行的版本。孙桂平对李诗的自改、他改、受众选择等情况进行辨析,对杨萧注等古注也予以考辨[64]。作者重视古注本中异文、古注与正文之间的关系,为解决诗歌文本问题提供一种思考途径,即注意正文文本的形成、衍生过程,以及从注释中梳理出诗人的诗思、比较隐微的版本信息等。
陈尚君指出李白诗集中有定稿、有初稿,许多诗歌经诗人反复修改方得完成。作者开篇即言李白“天才纵逸的另一面,是极度勤奋的学习与修改”[65],这不惟对研究李诗文本多歧状态有利,对于脱出固有成见去研究古注本,亦大有裨益。
5.从宏观角度来探讨文学典籍注释的特点,将杨萧注作为重要的例证与文本依据
丁俊苗强调典籍注释因时间性、时代性造成的“空间”落差,是新注不断被催生的重要因素。他着重以李白集的结集历程、古注本及彼此关联为例证,认为“李白的诗文,杨、萧、胡、王四家注,就是研究李白诗文思想艺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集中的注释连续统文献,大诗人李白的历史形象也会是断裂的、平面的”[66]。
(四)作为考证、辨析其他典籍的资料
将杨萧注作为考证、辨析其他典籍的资料,属于发挥“辅翼”功能,去助力其他典籍的振起“翻飞”。从文献学、编辑出版史视角来看,这是提供给后人一观稀见文献资料、一窥当时图书出版市场的珍贵机会。
王红霞、任利荣对域外典籍中所存李白诗文资料进行辨析,归纳出车天辂《五山说林》中解李白诗文材料九则。其中,解《侠客行》:“车氏言曾见一本亦作‘纵死’”,而元刻本系统中的萧本、玉本、郭本俱作“纵使”,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则作“纵死”。这就从域外典籍诗文保藏角度进一步说明,《侠客行》传播过程中“二者混用情况颇多”[67]。
吕冠南“就旧辑本有涉《(韩诗)内传》之文者,循其来源,逐加按察,剔其伪者,订其讹者,存其疑者,补其阙者”。这“涉《内传》之文者”便有萧注《惜余春赋》的语段,被作者评为“萧士赟统诸善注,详备而不失其真”[68]。
(五)乐府一类
与之前“在太白乐府诗研究中,大量运用杨萧注”一类不同,此处将视野延及整个乐府学研究。明镜不烦君照,这样便于更加通透明晰地观察杨萧注的位置与功能(以萧注为主)。当然,这里的注释无法完全独立而观,须与太白乐府融合。
1.融入宏观乐府学,兼及文体学理论研究
向回论著中探讨了李白“古乐府之学”的确切含义问题。他认为李白对汉魏乐府古题理解深刻,曲调熟悉,创作中擅长融入主题、题名相类的史事、故事,长于化用古题曲辞[69]。作者于研究中大量运用杨萧注,注意对其进行比对、辨析。
申东城在比对李杜乐府时指出,萧氏认为李白乐府多有讽喻,是实有真知灼见。尽管遭到王琦、赵翼等人批评,作为较早对李诗进行全面注释的注家,这种认知的主体方向于解诗意义重大,有助观者理解“李白乐府秉承《风》《骚》旨意,多兴讽当时君臣国事”[70]。
王辉斌认为《乐府诗集》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由其“以音乐为分类”的划分标准引起。他对集中所收李白乐府细致甄别,以期充分认知其收诗之误[71]。这就从侧面体现了旧注的价值,即通过整体注释太白诗,太白旧题乐府的篇目、性质更加显明,有助于后人理解白诗,理解乐府整体发展情况。
2.融入具体乐府古题,兼及古风类作品探讨
刘长东考察太白《胡无人》是否具有本事,考证出“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的天象。据此确定其创作于“李白初入幕府时期,即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次年正月之间”[72]。文中对萧注观点、材料等予以借鉴、考辨。
张佩认为,李白对《将进酒》古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翻新。考证中以元版杨萧注为底本,比对异文、注释,以探索《将进酒》古题的传播历程,以及太白对其接受的方式、方法与翻创细节[73]。
冷卫国探索李白《蜀道难》与左思《蜀都赋》之间的关系,及其“以赋为诗”的创作特征。作者强调“讽玄宗入蜀说”来自元人萧士赟《分类》的笺释[74]。
孙尚勇综合前贤所论,尝试清理《〈大雅〉久不作》所涉各种问题。文中以杨、萧见解作为讨论的起点,即二者“以为此诗反映了李白的文学复古思想,其着眼点在诗骚赋等韵文”。作者指出这种较早形成的观点,在后世流传度广、接受度高,使观者视角始终囿于纯文学范围,以致湮没了诗中隐含的太白政治思想核心内容[75]。
(六)明代诗学,尤其是李白诗接受研究
有明一代在李白诗文接受与传播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而对于明代诗学的研究中会涉及太白诗文集、注家及其注释活动、理念等。具体至杨萧注,虽未处于核心位置,却也不容忽视。
胡江山指出,胡震亨有目的地辑录前人诗论,精心规划安排,于其中加入自己意见,建构出《唐音癸签》特有的诗学理论体系[76]。研究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去把握胡震亨的解诗理念、知识架构以及对杨萧注的接受与批判。
苏焘指出“明初对李白的理论评价,呈现出比元代更为明显的理学与文学相融通的特征以及艺术审美趋向”。其中,高棅对萧注中因“不合雅正”而批评、删减白诗的情况,用小字注予以说明、保留,反映出他从文学角度对李诗遴选的审慎态度[77]。这种从诗文采选角度去考辨杨萧注的方法,接近从编纂思想、文本集结一维去考察注本价值与传播,相当于“以外观内,全幅呈现”。
付才武从明诗话入手,讨论李白“生平事迹”“从永王璘”“李杜高下”等焦点问题。论证注重吸纳“散见于作家文集或随笔中有关诗人诗歌的记载”,其中就包括对旧注进行采集、选取与分类[78]。研究虽不以杨萧注为核心,却从文体辨析角度予旧注以特殊梳理,突出其保藏史事、掌故方面的“独立”特质。
三、注本研究的体系与方法论
综合以上,以《分类》为原点,以之所触及的领域为延伸,我们可以将注本研究的体系自内而外逐环展开,来探讨现阶段注本研究的情况与方法。
(一)关于注释
历时最长的,便是借助杨萧注去研究李白及其诗文。此类发挥注释最基本功能,自然生发,绵延不绝。研究者多从中汲取材料、观点、态度,去考证具体“阐释点”。无论是作为定点批驳的对象,还是有力的同道支撑,杨萧注因产生较早都保持着较高的利用率。至于全面得到重视还是在詹锳、芳村弘道等详述其版本源流之后。
另一种,则是借助其他材料对杨萧注进行考辩,真正开始关注注释内容。此类型往往侧重选取单个注释进行辨析,累积到一定程度方才顾及“规律”。实质上,此中逻辑关系不甚严密,得出的结论也难以达到较高理论水准。自胡振龙开始,整体性研究全面展开,不过单条注释与注家浑融阐释思路之间的逻辑缝隙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弥缝。
此外,将注释作为语料库进行语言学研究是近些年新兴的类型。比如编纂辞典中征引太白诗句作为例证,其运用是否恰当,对词语的阐释是否准确,可以通过古注进行训释、考证。这与纯粹的李集注本研究存在天然联系,如从现代语用角度去考虑古诗文及其注释的功用。
还有一种情况,便是探索诗词格律、古汉语语法的研究中也会大量征引李诗及注释。其对注释的使用颇具规模,一开始便默认所选择语料意义的“内涵”与“外延”,关注点不在注释本身。不过,对古注的深入探研,当有益于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资料。
(二)关于注本
在《分类》研究中,注本可分为元版本与删节本系统。重在考察源流关系、删改情况;旨在提升注本的有效利用率,避免那种将删节本视为元版,源流混淆的情况。笔者在专著《〈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版本系统研究》《日本尊经阁藏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研究》中对“删节本系统”进行考证,包括:郭云鹏本、玉几山人本、许自昌本、霏玉斋本、四库全书本。研究仍重文献考证,还未延及批评话语、理论体系、时代特征等。其后,笔者尝试在单篇论文中予以融入、提升,仍觉十分不足。
另外,近两年李集注本研究的学位论文不多,却呈现出一种“横向关联”的趋势。即从此前的独立版本、版本体系等“纵轴”探索,逐渐转移至注重文本构成拆解的“横轴”类型化研究(比如分析异文、序跋、副文本中其他部分)。
(三)关于李白研究
此类研究往往与杨萧注研究重合。研究李诗运用古注,研究古注则必须参照李诗。近些年李白研究产生不少新的“生长点”,但细读文本是共通的诉求。由于《分类》编纂中,注家于文体辨析有着特殊的感悟,研究者也普遍注意到这个问题,故而常在对李诗某一类型、某一组诗进行分析时高频征引杨萧注。此外,探索李白接受,注本所呈现出的文本多歧状态是重要的分析对象与因素。还有一种趋势,便是重论“旧题”(如李白生卒年、具体作品创作时间与主题等)时,回归注释、以注释为讨论起点。这种相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学者首选。
(四)关于注家
在注本研究中,从研究逻辑与篇章撰写的设计结构来说,注释者的生平与交游都是首先要交代清楚的。搞清楚了注家,关于注释的其他研究方能稳步推进。不过,对于杨齐贤、萧士赟的研究似乎并未严格遵循这条规律,比起注释本身,注家得到的关注度一直不高。笔者于此体会甚深:首先,注释者的知名度与注释对象相差悬殊。莫说与李白相比,即使与后世注家朱谏、王琦等相论,亦存在一定距离。这就使研究者更倾向于从李白接受、李白集编纂流布等以“李白”为关键词的角度着手,使范畴稳稳落在“李白研究”之内。
(五)关于其他“核心典籍”
这里所谓“核心典籍”主要是指:第一,注释中征引频次高的几类重要典籍;第二,各类典籍内容、接受与传播中涉及到李诗及其注释,后者可作为前者的重要文献来源或辅证。而目前在《分类》研究中,具备两种属性或其一,成为研究核心的主要是《乐府诗集》(包括其他乐府类典籍)、《文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乐府类研究中古注的利用率尤高,虑其原因如下:
首先,杨萧注撰成年代与郭茂倩编定《乐府诗集》相近,保留了同期可以互参互证的语料、典故、本事等信息。
其次,乐府诗文本构成相对复杂。一首乐府题便可梳理出一套文本、声韵体系,跨年代的创作者们又各有所好所长,不断翻新创造。个中精品又渐在原体系外别开一路,复壮大至新的门庭,比如李白乐府作品。这就意味着研究传统乐府或李白诗,都需要从古注中汲取能量。
再次,注释与一般评点或散论不同。注释会比较集中地围绕诗人作品展开,表面散若星尘,内在团如蚁聚。注家对单个作品的见解浸润于浑融解读之中,无论正确与否都可存一种态度、思路,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杨萧注虽被诟病“驳杂繁复”,却很适合乐府诗“阡陌纵横”的存在状态,提供大量信息,几可梳理出一篇微型“诗史”,极便后人研习。
(六)关于明代文学与刊刻出版
此类以断代别出。如上文所言,明代在诗文别集刊刻翻刻、编纂成集方面相当活跃,出版业发展态势良好。与杨萧注本融合的明代文学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关于明代文学家及其作品,关于明代刻本及其流布。前者注重从《分类》中采择文献、勾陈史料去研究明代作家,比如王次回、许自昌。
以往有一种观点,即研究“非一流”文士,学术价值不大,研究意义有限。窃以为其思考原点与重心在于文学本身,以文学作品、作家的经典化程度为重要考察依据,难免有所不及。文学史中许多聚讼纷纷却悬而未决的问题,所缺失的可能恰是作家团队的完整、梯队的层次分明,故而研究“小家”或可补文思理路,使源流清明通畅。《分类》在明代流传甚广,其传播接受过程中与不少士人结下渊源。因此,无论以明代文学还是太白古注作为研究对象,都会予对方以增益。比如许自昌研究,若囿于“晚明戏曲家”定位或“刊刻李白集”一事,则研究自是难以展开,二者兼及,却真可别开气象。
至于明代刻本及其流布方面的研究,现阶段要比作家研究更扎实。举凡涉及杨萧注本,研究者都会注意将其融入明代整体出版环境中,尤其突出典籍传递中的“物质承载”意义,这是单纯探讨“版本信息”所无法涵盖的。当下对明代朱谏《李诗辩疑》《李诗选注》探索的不断深入,从太白诗接受、后出古注视角为《分类》研究提供了有力撑持。
(七)关于整体文学史与文学理论
如果说注本与“李白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合力讨论“文学史、文论中的李白”;那么,注本与整体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便是“注本如何影响李白所在的文学史与文论”。近些年,学者们格外注意探勘李白及其诗文经典化的路径,表现出两种自觉:从“史”中着力挖掘“学术”意义,从“学术”中理出“史”的线索。前者对注本研究的视野、理论高度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后者则侧重思维方式转换,需要更加广深的整体性思维。二者的共同诉求则是,不受注本“文字散点,思维弥散”格局的影响,逐步提炼、整合,使注本研究的成果能自然融入文学史的书写、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不惟仅存于文献学资料库中。具体至各个融合方向,则主要有唐诗学、宋代文学史、文化史、唐宋别集序整理等。
(八)关于文学鉴赏
在文学史、文学理论、文献学中,无论治何种细目,都脱离不了对具体作家、人物进行解读。方法不一而足,或隐或显,“鉴赏”成分都是有的。着眼方法论意义,鉴赏最能引领观者触摸文学的艺术本质。不过近些年文学研究偏重“文—史”“文—论”,“文”与“艺”的互动明显不足。包括笔者在内,学者们对太白古注的研究集中于文献考证、注释思想提炼方面,鉴赏仅作为分析工具,甚少作为研究目标。而鉴赏所需的滋味、意境、寄托、博采四大要素(袁行霈《中国文学的鉴赏》),恰是注家属意、“注释点”密集之处,于解读李诗大有裨益,是我们在后续研究中必须予以重视的。
(九)关于文本形态
文本形态,是主体文本经过空间传播、时间累积之后呈现出来的状态,所涉甚广,所涵甚丰。于此,笔者不单独用“版本”“注本”等来分论文献方面的研究趋势,整合为“文本形态”来观,重点谈研究中涉及的几项比较:
首先,《分类》两大版本系统之间。现阶段主要是对异文、删减增补、底本源流等情况进行比较。虽已虑及注家、家族、断代及同时期诗文语境与风尚,但皆未完成理论构建,也未能充分参与进文学史的书写。
其次,《分类》与其他古注之间。最初这种比较的结果,并没有突破四库馆臣对诸本的评价,仍以王琦注为集大成之“正宗”去衡量各家。近些年,各注本皆得到重视,研究不断细化,稍脱以往成见。今人注本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如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
再次,李白诗(包括注本)在不同文本之间。比如,具有代表性的善本、各种选本、各类总集、别集,甚至各种类型涉及到太白诗、注的文体。
第四,传统的李白、杜甫比较研究。已从诗文优劣、结集先后、数量、质量等“存异”式研究,逐步走向彼此辉映参照、文本交相阅读的“融通”式研究。
第五,跨时空、跨文体比较。注重充分挖掘注本内涵,调动其所保藏资源来探讨不同诗学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各种文体。
这一系列不断向外环演漾的比较圈层,使位于中心的古注研究变得立体而丰富,有助于突破固有格局限制。
(十)关于古籍注释及文学“元概念”探讨
此类研究的目标并不在于(或不直接在于)“某个”注本,而是讨论典籍注释的整体情况,关乎文学中部分“元概念”的认知与再讨论。
不少学者探索古籍注释理论与方法时,会自觉借鉴西方阐释学,以期从哲学维度来审视我国注释的技术、方法、功能、价值等。两者自有共通之处,比如立论基础都在于解释文本,研究目标皆包含在“意义”与“会义”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架构。当然,无论古今中外的注释者、阐释者还是将二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后来者”,都不可避免去追求文本意义的“稳定”。这就造成,我们在注本研究中对许多问题讨论未果,本质上是“元概念”体系构建不稳,需要从中国文学典籍注释的深层次研究中寻求支撑。此中存在两个要点:第一,突出我国注释的独特性,形成相对独立、匹配度高的理论体系;第二,突出集部注释的特殊性,同时注意其与经部注释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主体思想之间的关联。
(十一)关于出版史与出版思想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第一:“叙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79]已道尽古籍编纂、出版的真谛,特别强调了编辑出版活动中的思想意义与学术价值。不过随着现代学科的细分,与出版史密切相关的传统学科文字学、训诂学、注释学、校雠学、版本学、目录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往往自扫门径,各有厅堂。即如近些年研究格外注意交叉融合,纯粹从某一学科来看对方,既不能免却“边缘”感,也无法免俗强调自己宗正门户的本位自觉。
通观太白集古注研究,甚少重视其“图书”性质,自然也就较少将注本的形成、发展、增删、融合等,比较深入地与编辑、出版、传播、阅读这类注重图书生产与受众迁移的行为挂钩。相比较而言,现阶段关于宋元别集、古籍整理、断代出版史等的研究融合甚广,征引或论及白集古注时会注意到与当时整个出版环境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