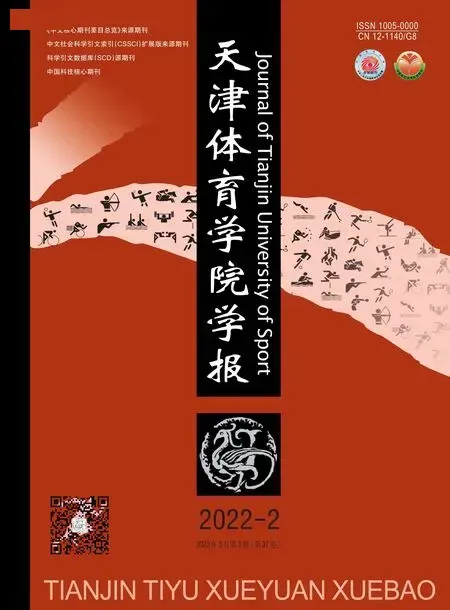体育遮蔽与解蔽的技术认识
——基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体育哲学考察
刘欣然,占雅男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预示着进步的无限可能;另一方面,隐含着灾祸的重组机制。“技术”的发展与变革,对体育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类参与体育的实践形式,随着“技术”变革而发生着相应改变。体育指向人的生存,是生命存活的能力保障和本原力量。可是在“技术”时代中,“技术”优劣成为提高运动成绩与赢得奖牌的主要因素,人的体力、体质、体能因素却退居次要位置,体育本原意义在“技术”变革中,反而遭到无情的肢解与否定。在现代文明中,“体育无法避免与排除技术的影响”[1],这就需要思考“体育”与“技术”的哲学关系,在这一问题中,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技术观”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深刻剖析技术现象中的体育本质问题,以技术“解蔽”[2](有所揭示的展开状态)为思维钥匙,揭示体育领域中的“技术”现象,直面体育“遮蔽”与“解蔽”的存在疑难。现代文明生活致使“科技导致身体活动的长期减少”[3],大规模身体主动运动被制止,体育反倒成为一种努力契机,成为身体静态的反面。在“技术”时代中,人类肉体或被过度开发与运用,或被无情遗忘与弃置,寻求回归生命本原的技术“解蔽”之径,是体育哲学的时代责任与使命。
1 “存在”之思——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体育思维引入
对“存在”(Sein)的追问,是海德格尔毕生的求索,思及“存在”人才能从中寻获意义。海德格尔[4]认为:“问之所问是‘存在’,‘存在’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的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恰就是‘存在者’本身”。“存在者”是世间“存在着”的东西(动物、植物、器物甚至人类),通过对“存在着”的追问,将世间万物按照“属”进行划分,最终根源又将回到“存在”之中。“海德格尔说,整体性的存在,其原意指的就是从自身中所绽放的东西”[5]。他揭示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是来自于事物自身的“展现”与“绽放”,并在此过程中保持自身的属性不变。对人类而言,“存在”的展现根本上就是“存在者”实现了它的用途并被感知,这样它便通达了“存在”,也实现了“存在者”的“在场”。海德格尔认为通过“存在者”可以通达“存在”。在探讨“人的存在”时,“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6]。世间之物的“展现”与“解蔽”并不是自发的进行过程,而是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或媒介向“存在者”进行“发问”,在“发问”(审视、凝思、抉择、领悟等)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并揭示“存在者”何以“存在”的根基。能够“发问”与“领会”的“存在者”,除“人”以外便无其他,致使海德格尔开始思考“人的存在”,为避免词义混淆,他将其称之为“此在”(Dasein)。“人作为一种存在者,在对‘存在’的思考中,被放置到优先的位置”[7]。
从自然生物属性看,人类本身就具有动物性的肉身,健硕的肌肉、发达的四肢、魁梧的身躯就是面向“存在”的述说,是“存在着”的最好证明。人类强健身形的拥有,勇毅精神的凝聚,就需要在体育实践运用中获取,“本原技术”就充当着“牵引者”的角色,成为保持这一自然属性的有效途径。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人的存在”样态发生着迁移,“静态的身体”受到褒奖,“动态的身体”遭到荼毒,身体运动被排斥在真实生活之外,“本原技术”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人的物欲贪婪“遮蔽”了身体的真实需求,就需要寻求“解蔽”之途,让人在“无蔽”之态中回归自然,用以实现人“存在之为存在”的原始样貌,体育借以“本原技术”的形式向文明病态展开宣战。在身体静态的文明面前,体育“对身体器官的整合增强身体延展的张力,弥补文明进程中身体自由的缺席”[8],“本原技术”让身体在文明中“去蔽”,人以“无蔽”的姿态通达了“存在”。
“此在”是指“人的存在”,而“存在”又是“‘存在者’的存在”,它表现为“存在着”,是一个在时间上的延续过程。人作为特殊的“存在者”,在其生命“向死而生”的延展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就是面向自然的索求,并以此而进行的“技术”革新与创造。在世界之中,“体育被看成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9],它让人产生位移,也使得“移动的人”成为一种标签,“技术”与“体育”在这种位移中也产生着关联。体育借“本原技术”的工具性,对人类肉体进行“野化”与“驯化”,使得“人的存在”凸显出来。体育再运用“现代技术”的创造性,让身体的自然属性适应社会文明的发展,“存在着”也就成为人“此在”的现在进行时,使人在体育中真正通达“存在”之途。
2 “技术”之问——海德格尔“技术观”的体育意义凝合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探索,始终建立在对“存在的意义”[10]的追问之上,从而建立起对“技术”的“解蔽”之思。“技术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涉及人类存在的真理”[11]。“技术”在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中,扮演着让“存在”回归自身的主体角色,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先导切入并思及“存在”,将技术的“解蔽”缘由灌输其中,并以此通达“人之存在”的本真原貌。探及“存在”被遗忘的根本,“技术”的异化行径触及时代的恐惧(人与技术的主客体置换),这种“恐惧”将“技术”引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代交互的反思中,并开启“技术”触碰并探及“存在”问题新的可能性。
何为技术(Technology)?“技术首先是一种才能”[12]。早期“技术”是一种生产才能,即将一种物质转化为新形式的技艺。海德格尔把“原材料”转化为“新材料”的生产技艺,对物质进行改造并以新的面貌及用途呈现出来,看作是“技术”的本原能力。如此看来,“本原技术”乃是一种“解蔽”的方式,让“存在”显现的过程,就是让物质进入“无蔽”状态,并以新形式呈现出事物的“本原力量”。“技术”借以科学之名在工具、机械、电子信息的帮衬下,在本原自然中圈划领域攻城略地。“什么是现代技术?它提供一种‘解蔽’的可能,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开采与储存的能量”[13]。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技术”过度“解蔽”所造成的“促逼”,可能成为大自然反叛与惩罚的起因。“现代技术”对本原自然的过度“解蔽”,反而是对“存在”的“遮蔽”,甚至会造成某种对“存在的遗忘”。
思考“技术”一定会触及“人”与“技术”的存在关系,“技术”具有生成与毁灭的双重性。“海德格尔反对技术无节制的滥用”[14],技术需要用以价值规范,以便维护人类的存在利益。“技术”既是人类自我摧毁的力量,亦是人类自我救赎的途径。在体育之中,“本原技术”是以“解蔽”状态进入到人类实践活动之中,它是肉体的改造、潜能的挖掘、素质的调遣,人类在“技术”中感受到来自身体的强蛮、野性与活力。而在“现代技术”中,由于功利价值的驱使,体育中充斥着“物欲”迷恋,“技术”将人当成“非人”来改造,从而造成对人“存在的遗忘”。“现代技术”的自我膨胀,人被当作移动的躯壳,将人类本真的行动力禁锢起来,人“存在的意义”也就迁移为“技术”统治的权力,人从此成为“技术”的奴隶。为了获得生命的救赎,体育依旧保持着“本原技术”的不变初心,为了寻求人的“解蔽”,为了社会的适应,为了身体的强蛮,体育用“技术”的合理性,勾连起人与自然最为本真的“存在姿态”。
3 观念的纷争——“技术”双重本质的体育阐明
“技术”的“古今之分”,在“时间之矢”中所表现出来的双重属性,形成了不同的“技术”力量,创建与毁灭、遮蔽与解蔽、遗忘与忆起等,都随着“技术”变革交替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海德格尔对技术理性批判具有历史统一性”[15],需要在“本原技术”与“现代技术”之间,进行连续性与差异性的分析。在体育领域中,“本原技术”的“亲和”与“现代技术”的“促逼”,使得体育兼具“技术”的双重属性,共同应对人类精神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理性与非理性等等,对立统一观念中所遇到的矛盾问题。“技术”在文明的创建中,逐渐搭建着机械永动装置,在“技术座架”的天平两端,构成体育不同的价值取向,需要通过体育的哲思起意,在其中刻画“人之存在”的不同场景。
3.1 时间的刻度:“技术”在历史中的思维显现
“技术”在时间中该如何理解呢?“技术”与“人”已经紧密结合为生命共同体。“本原技术”是人类生存实践中的行为投射,“技术是人的行为”[16],是基于对大自然的改造而获得的本原能力,是劳动、生产、改造等实践活动的累积,是对第一性自然的利用。在海德格尔看来,“本原技术”在对自然的运作中,还蕴含着极其深刻的道理,其本质上是“去蔽”与“展现”的过程。“本原技术”是符合自然规律而出现的“技术”形式,它引导事物以某种途径去“展现”自身,但却始终在保护万物的自然本性。“本原技术”不是功利性的创建,而是人依靠原始力量的生存选择,是生命本真样态的展现,真正使得“让人成为人”在体育中获得实现。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颠覆了以经验为主导“本原技术”的存在根基。“现代技术的显著特点是使来源于科学的理论知识得以体现”[17]。科学技术与理论知识的结合,使得“现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与“应用科学”相等同,“手工技术和以动力机械为特征的现代技术”[18],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角。机器、设备、制剂、化工、电子、信息等,由新材料、新工艺形成的“现代技术”占据着绝对主导。“现代技术”不再像“本原技术”那般“温柔”,它“是区别于技艺对自然的延展,试图将世界格局化、同质化与数学化”[19]的可怕力量。“现代技术”与“本原技术”,二者本质皆为“去蔽”,但“现代技术”的“去蔽”,却是对原始“存在者”施以的“挑战”,其中蕴含着对于大自然过分的苛求。在时间的浸溺下,“现代技术”为“去蔽”而来,反倒成为“异化”的根源,大自然被非自然力量所“遮蔽”,罪魁祸首只能从“技术”自身中找寻。
3.2 古今的对话:“技术”在思想中的体育交谈
人类以身体为载体,在体育中创造出顺应自然规律的生存形式,通过身体运动与实践,用生命本原能力实现对自身的改造。体育是一种身体性的运动,“是针对体能实践的技艺行为”[20],并从中展现出生命原始的强蛮状态。“体育是人动物性行为的投射”[21]。体育既来源于生命行为,又是生存活动的投射与升华,它是以身体为载体的“技艺性运动行为”[22],从中体现出人的素质与能力。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历史潮流已经让“科学”与“技术”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工业、机器、电子、信息等“技术”革命形式层出不穷,体育领域同样感受到来自“技术”变革的冲击。体育是针对人本身的改造,是依靠本原能力进行的身体练习、运动与实践,是体现“本原技术”的最佳载体。可是,在“现代技术”中,“人类增强技术已经产生严重的伦理问题”[23]。人们已经被物质、权力与欲望迷离,体育不为生命着想,不思身体勇力,却成为“现代技术”所宰制的奴隶。
在体育领域中,两种“技术”的现实对抗下,“本原技术”日渐式微示弱,“现代技术”逐渐争胜逞强,因此,两种“技术”观念在体育中产生了差异。第一,就体育目的而言,“本原技术”以生命实现为目的,展现出人的主体地位;“现代技术”以科技至上为目的,人被挪移于客体的位置。第二,就体育手段而言,“本原技术”是挖掘人潜能与素质的手段,人是实践活动的中心;“现代技术”是彰显科技权力与欲望的手段,知识是技术变革的中心。第三,就体育价值而言,“本原技术”中体现出人的生命价值,生命是最为高鹄的意义;“现代技术”中呈现着身体的工具价值,身体只是科技的实验产品。第四,就体育思想而言,“本原技术”以身体为载体,展现生命完美的身体姿态,用以解释“让人成为人”的现实意义;“现代技术”以身体为对象,扭曲生命完满的存在意义,用以证实“技术即权力”的功利主义。体育领域的两种“技术观”,“本原技术”作为“解蔽”是对“存在者”的“带出”与“调遣”,是身体基础性与本原性的展现;“现代技术”用以“解蔽”(却可能导致“遮蔽”)则是对“存在者”的“促逼”与“挑战”,是身体工具性与对象性的挖掘。
4 “现代技术”何以“挑战”——“人”本质异化的体育揭示
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中的“技术观”,是由现时代人类生存境况所引发的思考,“技术”在时代交互、更替与变换中发生了转向,需要在“存在论”层面上领悟“技术”本质,并诠释“技术”通往“存在”的哲学途径。“技术与社会的二元性与分离性”[24],都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末世主义”与“享乐主义”都必须进行反思与批判。在“技术座架”的织网面前,“本原技术”时常遭到“遗忘”,而“现代技术”却发生着“异化”,体育置于“本原”与“现代”两种“技术观”之间,体育现象该如何揭示?“技术座架”中体育将展现怎样的现实图景,是当下所面临的思想挑战,需要得到思想揭示、文化警醒与哲学反思。
4.1 现实的迷惘:技术“异化”中的体育“遮蔽”
人类过度依赖于“技术”实现自我价值时,“人的本质”就会逐渐转向于“物的本质”[25],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反倒成为了主角,主导着社会历史的进程,进而在生产力发展中体现着“技术”的本质。在这一思维模式中,体育也受到“技术异化”思想的侵袭,将“人”与“体育”割裂开来,从而形成某种价值思维上的对立,体育的存在意义遭到肢解与否定。
在“技术异化”的现实中,体育随着“技术”变革一同更新,并因此愈加依赖于“技术”的发展。这将带来一些现实的问题,在竞技运动中“以数字化的指标来控制训练过程,以生物技术监控训练效果,运动员的人性化被数字化所取代,把运动员推向了物化的边缘”[26]。在运算思维与数字建模中,体育运动的各种形式与内容,都被转换成数字方程而进行“筹划”,人被设计为“0”与“1”的计算游戏中,“人的存在”也就变得无有生机、了无生趣。
在功利主义侵蚀面前,“现代技术”急速奔涌前行,体育也在巨大利益诱惑下,尝试在器械装备、化学制剂、生物改造、基因编码等方面,以“物”的视角来审视并占据“人”的体育。这一切都是在“现代技术”发展中,所导致地体育“遮蔽”与“掩藏”,身体教养与培育、运动素质与能力、竞赛成绩与名次,都在功利主义面前变得急躁起来,进而对“人”进行“促逼”。体育需要保持时刻的清醒,以便获得生命自救与“解蔽”的途径。
4.2 目的的筹划:技术“订造”中的体育“安置”
人与“体育”无法分离,人与“技术”亲密无间,三者可以是互为依赖的存在关系。“技术”是人类文明形成并发展的起因,“技术”对存在着事物的“解蔽”,可以看成是文明演进的动力。论及体育之于人的产生根源,同样是为了人的自我“解蔽”,是面向人本原能力的运作与调遣。可是,在“现代技术”的世界里,对事物的“解蔽”反倒造成了“促逼”与“压制”,一种蛮横的威逼与至上的权力,使得“人本身”没有停歇与喘息的时机。“人的存在”在“现代技术”的膨胀与自满中,发生着目的性的迁移,原本用于对自然“解蔽”的途径,逐渐转向于人类目的性的“订造”(Bestellen),“技术”开展加工并制造带有“人为”意志的产品。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人在自然不足以应付人的表象之处,就订造自然”[27],并使“订造”之物能够符合“存在者”的心意。
在“现代技术”中,人时常失去主体的位置,成为“技术”操控的对象,被随意摆布与宰制,功利性的“订造”反倒获得一种“神性”权力,并按照“技术”设计的世界将人安置其间,人可能置换为“技术”的螺钉。体育在“现代技术”中,也被“安置”于“订造”所设计的程式中,身体能力、素养与意识;运动项目、形式与过程;竞赛胜败、成绩与名次;金钱、荣誉与地位,都可能成为“订造”的目的因。体育被“安置”于“现代技术”的机械工程中,体育爱好者、健身指导员、体育教师、学生、教练员、裁判员与运动员,都可以成为“现代技术”所“订造”的对象,从而形成一系列利益锁链。“技术”为“解蔽”而来,在现代社会中反倒造成了某种“遮蔽”,“技术订造”最终目的并未指向“人”。“体育之于人”的真实目的被“遮蔽”,需要在本质意义上寻求“解蔽”。
4.3 合理的魅惑:技术“座架”中的体育“集置”
在“现代技术”中,“存在者”的“持存”与目的性的“订造”何以成为可能?海德格尔在“技术观”中以“座架”这一概念建立起了“持存”与“订造”的合理性。“座架”(Ge-stell)一词,在德文中,“Ge-”的字根有“聚集”之意,“stell”则具有“摆置”的意思,海德格尔用“座架”来诠释“技术”高效地“集置”能力。所谓“座架”,就是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之下,自然界所有的物质(包括人在内)都被“聚集”在一个巨大的网格系统中,所有“存在物”的有用性都被预先“摆置”其中,而这种有用性的东西则被称为“持存物”,人与“存在者”的“持存”便成为可能。“因此,作为技术本质的座架是这样一种要求:把人‘会集’待技术展现中,唤起他的限定的方式全部的思想、追求和努力”[28]。人类因现实发展需要,因功利目的唤醒自身的“本原能力”,而不得不去利用“技术”时,反倒会掉入到技术“座架”的陷阱之中,真假难辨、虚实不分。
在体育中,“现代技术”本义是发现“人自身”,可是,为了寻求极限的挑战、潜能的端点、卓越的起因,对肉体的实践运用与素质展演,反倒变成为“技术”实现自身目的的绝佳时机。“现代技术”借助机械装置、穿戴设备、生物药剂、基因工程、电子信息等工具手段,用以发现人的体质、体力、体能、体格的最大峰值与绝佳表现,进而造成对人本原自然的“促逼”,体育成为“技术”用以“集置”的对象。
5 “本原技术”何以“展现”——“人”本质复归的体育救赎
依循着“海德格尔反思技术的尝试”[29],使我们能够更多地思考自然、人、技术、体育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人应该居于中心的位置。体育应该更多地依赖于“本原技术”的展现,从而实现对人“本原能力”的“解蔽”与“开显”,并尽量远离“现代技术”的蒙蔽与欺骗,运用“本原技术”保持对生命养护、身体培育与体能锻造的始终如一。海德格尔在“技术”思想中,用“解蔽”、“促逼”、“订造”、“集置”等词汇,隐射出“技术异化”的现实状况,“本原技术”与“现代技术”何以为继,值得深思。在体育领域中,朝向“本原技术”本真的实践回归,是克服“现代技术”异化的有利手段,反抗“现代技术”过度化的侵袭,只能回溯到“本原技术”中进行哲学寻觅。
5.1 本质的还原:技术“四因”中的体育“解蔽”
体育在“本原技术”中展现出身体的实践技艺,是由生存而引发的身体技艺与行为。在体育之中,“技艺实现了本体论维度上的延伸,使‘体育技艺’成为体育的本质”[30],这还需要对体育进行本质还原,以便充分认识体育在“本原技术”中如何展现自身。对体育而言,正是人类运用“技术”手段,将世间各种因素加以统筹、限制与利用,进而使得体育以身体实践技艺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在此中寻觅通达“存在”的方式。“天”的审视,遵循“天道”以应“人事”,天命有为、时序更替、世运涨落,都应该成为体育运用“本原技术”参与实践活动的“存在”义理,“人”才能从“天道”中鼎立;“地”的纳怀,顺应“地利”以显“人情”,天行刚健、地势坤舆、厚德载物,才能便于体育与“本原技术”的融合,人才能在“地势”中增益无穷;“人”的实践,契合“人文”以达“人为”,人文化成、品行育人、人之为人,都包蕴着体育植入“本原技术”中的人文精神,人才能从中诠释着“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哲学起因。
在“本原技术”中,体育怎样才能获得“解蔽”的途径,追溯“本原技术”的有用性,使“存在者”得以呈现出来,亚里士多德在“四因”学说给予了启示。“本原技术”对于体育“解蔽”是通过身体实现的,是“人的存在”最为基础的呈现方式。第一,在质料因中,人的身体是体育活动的载体,“本原技术”所运作的对象也是人本身,体育中体现出人生命活动的本原状态。第二,在形式因中,生命活动所呈现出的体育动作与行为,走跑跳投、挪转腾移、攀爬牵拉、推握挺举等,都可以是“本原技术”所关注的对象,从而使“人的存在”变得丰富起来。第三,在动力因中,“本原技术”是体育发展的推动力,使体育将人的素质提升、潜能挖掘、技艺获取而运作与锻造,面向人的主体存在与全面发展,体育“是发展与完善的力量”[31]。第四,在目的因中,体育是面向“人的存在”的实践行为,而“本原技术”则是体育实践运作的工具与途径,最终都将回归到“让人成为人”的哲思起意。在面向人的本质探索中,体育能够在“本原技术”中获得“解蔽”,从而彰显出“人之存在”的本性,使人实现自然“本原能力”的身体还原,“人的存在”才能在生存中获得“人学”意义。
5.2 身体的自然:技术“澄明”中的体育“在场”
“本原技术”是人进入“此在”世界的打开方式,“身体作为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32],技术总是以身体作为实践基点,并在“人的存在”基础之上,建立世界活动的意义中心,体育也在其中寻找到“身体存在”的意义联系。在体育之中,寻找“存在者”的本真状况,是“一种进入到真实存在的过程,一种促成显现和光明的过程”[33],这就需要人向自然“敞开”与“澄明”,以身体为运作中心从而实现一种真实的“在场”。在体育之中,身体面向“本原技术”的“澄明”之境展现自身,标志着“存在者”实现“解蔽”,从而进入到自然的场域中,使得人“在场”存在变得清晰起来。“在场是在外观中就有从无蔽状态中站出来这回事”[34]。体育为“人的存在”提供着场域,在“本原技术”中呈现自身的同时,使得“存在者”的显身与隐匿交替上演,人的潜在能力时而“在场”或“缺席”,进而引发出某种身体的自然神秘,体育通过“本原技术”成为制造神秘的起因。
“人的存在”是一个生命动态的存在体,从内在尺度与外在表现中都透露出“存在者”的真实。“人的存在”根本是建立在身体之上,当“存在者”得以在“本原技术”中展现自身时,生存也就透过体育活动展现出来,以实现人与身体的同时“在场”。“存在仅作为生活中凝固、硬化了的一个部分,这种生活把人的生存抛入客体性”[35],从而表达出“存在着”作为生存的“在场性”,“本原技术”直接导向人的生存意义,体育在其中虏获“在场”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将“此在”作为“人之生存”的“存在”,就是融入生活本身的自由诠释,体育用“本原技术”的行动表现,彰显出“生存”作为“人之为人存在”的意义缩影。“现代技术隐藏了体育和运动员”[36],人被放置在技术的背后,这就需要体育在“本原技术”中实现“去蔽”。体育借助“本原技术”实现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无蔽”,顺应自然规律从而锻造身体,符合社会期许追求公平正义,在身体行为与意志品质的双重塑造中,实现人面向生存的“解蔽”。人类保持“澄明”之思去通达“存在”,是“本原技术”的本真姿态,在体育实践中强健身体、纯化心灵,实现肉体与精神的统一,从而使得人在体育中以“无蔽”实现“在场”状态。
5.3 回返的途径:技术“理性”中的体育“呈现”
“技术”需要“理性”思维的浸染与植入,才不至于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以致“人”被技术所驾驭与奴役,而“成为技术社会所设计的部件而已”[37]。在知识社会的高速运转中,人们追逐“技术”进步,而忘记身体的“本原能力”,对“理性”的疯狂欲求,致使机器与人、物欲与人、金钱与人之间都形成了某种错觉与错乱,“技术”的本性压制着“人性”。
哈贝马斯、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学者,提出“技术理性”的思维,希望弱化“技术”自身的目的性,而用“技术”规则的“理性”思维去凸显“人的存在”价值。体育在合乎“理性”的否定、怀疑与批判中,“现代技术”所形成的“促逼”与“遮蔽”,需要回返“本原技术”中以“敞开”与“解蔽”,摆脱“技术”对人的奴役,以凸显“技术”的工具价值,“为人所用”而不是“为物所役”。在体育领域运用“技术”的过程中,需要摒弃一种功利性的机械主义,一种数字化的计算思维,一种程序化的信息编排,人要成为“技术”的主导,就需要彰显出“人的存在”,“以朝向身体的回归”为主旨,体现出人此刻“在场”的当下性,与“此在”的生存意义。“这个关于人类生存的解释学问题被海德格尔称为Dasein,即‘此在’,这是能够向一般存在敞开的唯一的生存方式”[38]。体育正是深入“此在”的生存境况之中,是“生存论”获得意义彰显的重要形式,也是人证明此刻“在场”的行为语言。体育之于“人的存在”价值,来自于对“人生命意义的养护”[39]与“人生命行为的磨砺”[40],在“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对存在的遗忘”,就是对“此在”生存性的否定,需要在“本原技术”的“理性”思维中,对体育进行价值还原与意义呈现。
6 结 语
当技术时代来临后,我们需要思考“科技时代体育哲学的作用”[41],针对“技术之思”是最好的开始。“通过技术实现人类解放可能吗?”[42]人是世间的实践主体,“体育”与“技术”都因实践而被“人”所利用、关涉与提及,对“人的存在”的思考,自然也就成为“体育”与“技术”的实践主因。在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中,“体育”初心不变始终以人的“本原能力”为实践对象,保持人的体力、肌力、气力、勇力、毅力与活力的完满,体育成为人“生命存在”的重要维护力量。而“技术”却逐渐分化为“本原技术”与“现代技术”,本义为了事物的“开显”与“解蔽”,反而造成了“存在者”某种“促逼”与“遮蔽”,并在“技术异化”的现实面前凌驾于“人”之上,技术目的性占据着社会主导,“人”与“技术”发生着本质置换。体育是对生命“本原能力”的行为实践,任何运用“现代技术”所促成“身体动态”都是虚假的掩饰,唯有回归生命的自然本性,在体育中导向“本原技术”的“解蔽”,才是生命力涌现的选择途径。在现代社会的“技术”张狂中,为了寻求人的生命力的价值呈现,有必要在“人的存在”意涵中,思考“体育”与“技术”的哲学关系,从“存在论”的语境中使“人”获得价值“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