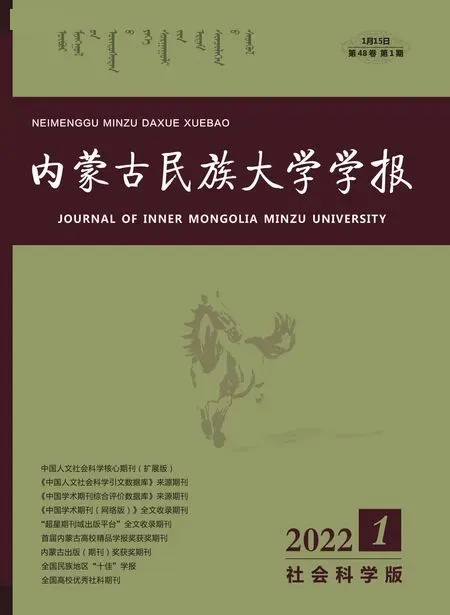中唐骈文批评中的功利派与折中派
于景祥,张力仁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中唐时期的骈文批评虽然门派很多,但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看,主要有两派:第一个是功利派,其特点是着眼于政治教化,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大倡散体古文,反对骈体,这一派以古文家为主要代表;第二个是折中派,其特点是从折中的角度出发,对骈散两持其平,当时以皎然与裴度为代表。
一、功利派的骈文批评
客观地说,中唐骈文批评的主力是古文家,但是其骈文批评中功利化色彩特别浓重。从历史顺序上看,中唐前期的古文先躯箫颖士、独孤及已开中唐功利派骈文批评的先声。萧颖士在其《江有归舟三首·序》中说:“我之所以诲,学乎?文乎?学也者,非云徵辨说,摭文字,以扇夫谈端,輮厥词意,其于识也,必鄙而近矣,所务乎宪章典法,膏腴德义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1]从文与学两个方面入手,认为学之要务在于“宪章典法,膏腴德义”,显然是宗经的观念,以儒家经典为务;而文之要在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风雅之传统,为政治教化服务。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思想,所以他批评骈体,一方面批评骈体行文局束与崇尚形似的华靡之风;另一方面,也是更要紧的是批评其内容浅俗而背离儒道,尤其是背离为文应有益于政治教化的宗旨。独孤及在这方面与萧颖士同出一辙,他在《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中指出:“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辨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2]3945—3946他以儒家传统的言志之说为准则,认为志、言、文三者相互为用,但关键是要本乎王道,源于五经,“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辨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不但对先文学、后比兴提出批评,尤其对骈偶与四声八病的规则更为不满,认为是文之“大坏”。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是典型的儒家重视政治教化作用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学观。
韩愈上承儒家重视政治教化作用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学观,又进一步明确为“文以明道”的文学创作准则,把文章当成明道的工具,道为本,文为末,而其道就是儒家之道:“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仓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18,所以他大倡古文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儒家之道,恢复儒家之道统:“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3]18
正是基于这样的功利目的,特别是复兴儒道,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目的,所以韩愈在文学批评方面大力倡导古文,反对骈文,认为骈文不仅拘于偶对,更不便承载儒家之指归。《旧唐书·韩愈传》中说得明白:“(愈)尝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4],也正是基于此点,他反对在科举考试之时以这样的文体取士:“而方闻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2]5583韩愈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骈体文之弊:“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四举而后有成。……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凡二试于吏部。……人或谓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于今之世,其道虽不显于天下,其自负何如哉?肯与夫斗筲者决得失于一夫之目而为之忧乐哉!”[2]5583认为以骈体文取士,不利于人才选拔,并且对骈文非常蔑视,认为它“类于俳优者之辞”,为自己不得已而作此类文章而不好意思,“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所以,韩愈的骈文批评,虽然在改革华而不实的骈体文风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也因为多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有时不免有些偏颇。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韩愈上面这些言论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从创作实践上考察,他不但没有彻底抛弃骈体,而且还吸收其长处,写出相当多的骈散结合的佳作,如其《为裴度让官表》《进学解》等就是典型代表。问题在于韩愈本人在骈文批评方面理论与实践并不统一,有时自相矛盾。
柳宗元也是一位古文大家,在文学主张上,也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强调文学的明道功能:“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5]550当然,他所要明之道在内容上与韩愈有些差别:“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5]542—543其所谓“道”不仅包括儒道,而且取诸家之长:老庄与子、史都在其中,其重点在于“辅时济物”,“益于时政:“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5]508正是在这种讲究功利和实用的思想基础之上,他在《乞巧文》中批评过于重视形式技巧之美,而缺乏实用功能的骈体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5]316应该说,他对骈体文的批判抓住了这种文体的主要特征,击中了要害,是古文家中批判骈体最有力的人物之一。当然,在创作实践中,柳宗元也不是一概排斥骈体,不仅在其散文中时常加进骈语,而且也有骈文传世,如其《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宗元启:伏以周汉二宣中兴之业,歌于大雅,载于史官。然而申甫作辅,方召专淮夷之功;魏邴谋谟,辛赵致罕羌之绩。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圣贤克合。谋协一德,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赵之事。东取淮右,北服恒阳。略不代出,功无与让。故天下文士,皆愿秉笔牍,勤思虑;以赞述洪烈,阐扬大勋。宗元虽败辱斥逐,守在蛮裔,犹欲振发枯槁,决疏潢污;罄效蚩鄙,少佐毫发;谨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惧不敢进献,私愿彻声闻于下执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战交绩。无任踊跃屏营之至。不宣,宗元谨启。”[2]5822虽然是歌功颂德之作,但却没有阿谀之态。全文多是整齐的骈词俪语,中间夹杂一些奇句单行文字,并适当地使用一些典故,因此文章一方面典丽宏赡,从容闲雅;一方面又文气通脱,自然流转,毫无拘束和堆垛之感,这是骈散结合的结果。柳宗元骈散兼善,所以他在两者的结合上成就自然突出。因此,我们在考察其骈文批评时,不能单纯研究其言论,还要考察其创作实际,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
李翱是中唐古文方面的又一大家,在文学观上一本于儒家传统观念,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认为文章应该以仁义为本,以文为末。其《杂说》上中有曰:“志气不能塞天地,言语不能根教化,是人文之纰缪也。……人文纰缪,无久立乎天地之间,故文不可以不慎也”[2]6427—6428,这是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其《寄从弟正辞书》中又说:“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子殁千馀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2]6422强调文章要以“仁义”为本,而“文”则是一艺,是末。当然,他虽然也主张文以明道,但是其所明之“道”与韩愈等人也有所区别,即在崇儒的同时,主张吸收诸家之长。在《答朱载言书》中,他说:“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矣。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子、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2]6411—6412可以看出,他的“道”比韩愈之“道”的内涵丰富得多,除了儒家之“道”外,诸子百家都囊括其中,显示出广泛的包容性,不像韩愈之“道”那样狭窄。
另外,李翱既强调文学的明道功能,也重视词章,提出义、理、文三者兼善的观点:“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志》,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此之谓也。”[2]6412虽然其为文的终极目标仍然在于教劝的功利目的,但是因为并重,比那些单纯强调道统、轻视文之作用的古文家进步多了。也正因为这样,他在骈文批评上便不同于其他古文家,而有持平之论。他在《答朱载言书》中指出:“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2]6411既反对尚异好奇,追求险怪,又反对好理而轻文;既反对单纯追求对偶,又反对彻底否定骈偶;既反对好难,又反对好易;总体上是折中与兼容的态度,尤其对待骈文和散文能够这样不偏不倚,确实难能可贵。所以,在中唐古文家的骈文批评中,我们不能不说李翱的见识更为深刻。
上述几家之外,中唐时期还有一位特殊人物权德舆,他与古文家关系较密切,但是又对杰出骈文家陆贽特别推崇,其骈文批评也值得注意,大体上说,其理论主张同古文家相近。
权德舆同古文家一样,也特别强调文章有益于政治或教化的实用功能,对骈体文在这方面的弊端有所揭示。在《答柳福州书》一文中,他说得明白:“两汉设科,本于射策,故公孙弘、董仲舒之伦,痛言理道。近者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2]4994由科举而及于文体文风,强调的是文的实用功能,特别有助于“理道”,即发挥经国济世的作用,从而批评骈体文和律诗雕琢绮靡的不良风气。同时,他又从教育目的上切入,认为培养人才为立国之本,由此出发,批评当时把重点引向讲究对偶声病的做法,对科举中使用骈体和律诗提出疑问。其《进士策问五道》第五问中说:“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修辞待问,贤者能之,岂促速于俪偶,牵制于声病之为耶?”[2]4935显然,他认为育才造士是关键,而讲究骈偶和声病是本末倒置。不过,从总体上说,权德舆的这种强调经世致用的骈文批评观念,在他有关骈文大家陆贽其人其文的评价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陆贽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骈文家,其骈文作品既流利畅达,又切中时弊,有为而作,是地道的经世致用之文。在唐代,对陆贽其人其文的评价,以权德舆最为客观与中肯。首先,在《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中,权德舆把政治家兼骈文家的陆贽与汉代的贾谊相提并论:“尝读贾谊书,观其经制人文,铺陈帝业,术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后时,遇亦深矣!然竟不能达四聪而尽其善,排群议而试厥谋,道之难行,亦已久矣!东阳、绛、灌,何代无之?噫!一熏一莸,善齐不能同其器,方凿圆枘,良工无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乱日多,大雅衰而正声寝。汉道未融,既失之于贾傅;吾唐不幸,复摈弃于陆公。”[2]5032没有因为他是骈文家而在其人其文上有所歧视,说明他批评当时的骈体,是就其雕琢绮靡的不良风气而言,如果是不拘于俪偶,牵于声病,内容上又益于政治教化的骈体,他并不否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又着重从经世致用的功效上对陆贽骈文进行分门别类的总结与分析,并且由文及人,人文并评:其一曰:“公之秉笔内署也,搉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俾剽狡向风,懦夫增气,则有《制诰集》一十卷;览公之作,则知公之为文也。”[2]5033言其制诰类骈文突出的经世作用;其二曰:“润色之余,论思献纳,军国利害,巨细必陈,则有《奏草》七卷;览公之奏,则知公之为臣也。”[2]5033由陆贽奏草一类骈文而及其人,极言其忠恳;其三曰:“其在相位也,推贤与能,举直错枉,将斡璇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阶;敷其道也,与伊、说争衡;考其文也,与《典》《谟》接轸,则有《中书奏议》七卷;览公之奏议,则知公之事君也。”[2]5033人文并评:认为其人可与古贤伊尹、傅悦比肩,其奏议类骈文与儒家经典一脉相承;接下来,又总评其人:“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时、命也。仲尼有才而无位,其道不行;贾生有时而无命,终于一恸,惟公才不谓不长,位不谓不达,逢时而不尽其道,非命欤?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说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时遇主,克致清平。陆君亦获幸时君,而不能与房、魏争列,盖道未至也。应之曰:道虽自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农、稷不能善稼;奔车覆辙,孔、孟亦废规行。若使四君与公易时而相,则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贞观、开元者,盖时不幸也,岂公不幸哉!以为其道未至,不亦诬乎?公之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为别集,十五卷。其关于时政,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惟制诰奏议乎!”[2]5033—5034这里,权德舆先是采取比较之法,又知人论世,突出陆贽经国济世之才,驳斥有些人对他不公正的评价;然后又对其骈文进行总的概括与评价,其中最推崇的是陆贽“关于时政”的“制诰奏议”类骈文,认为这类骈文“昭昭然与金石不朽”。可见,其批评的着重点还是在政治方面。
二、折中派的骈文批评
中唐时期,受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影响,否定骈文、倡导古文之风盛极一时,但也有人不从流俗,以折中的态度看待骈文与散文,进行较为客观、较为中肯的骈文批评,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诗僧皎然与裴度。
皎然是中唐时期有名的诗僧,既擅长诗歌创作,又有诗论专著,即《诗式》与《诗议》,其中也涉及骈偶问题,具有骈文批评的价值。同其他骈文批评家相比,皎然的骈文批评很少带有政治教化色彩,主要从骈文本身特别是创作上入手。当然,他也卷入到唐代的骈散之争的旋涡中去了。首先,皎然以经典为证据,否定复古派对骈文的诟病,其《诗议·论文意》中说:“或云: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于俪辞。予曰:不然。《六经》时有俪辞,扬、马、张、蔡之徒始盛。‘云从龙,风从虎’,非俪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非俪耶?”[6]207—208立论坚实,证据充分,揭示出复古派的偏颇。同时,他在《诗议·论文意》中对今文不及古文的原因,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古人后于语,先于意。因意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斧斤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此古手也。”[6]208显然,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语与意的地位:古人所以超过今人,关键是以意为先,即“因意成语,语不使意”,所以用骈用散都得心应手,“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如果以语为先,刻意用骈或者刻意用散都不合适,都不可避免地“见斧斤之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皎然在骈散两种文体创作上的基本主张:就骈文而言,他认为关键是要达到“浑成”,也即自然的境界,所以他在《诗式》卷一“对句不对句条”中又指出:“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7],很明显是以自然为准则。就散文而言,他认为关键是不能“造作”,其实也是讲究自然的原则,即不能不顾实际需要而刻意作散,总的方针是该骈则骈、该散则散;既不刻意为骈,也不苦心作散,用骈用散顺其自然,在骈散地位上两持其平。当然,皎然的这种骈文批评观念明显受到了《文心雕龙》的影响。第一,文中批驳复古派把今文不及古人的罪责强加于骈偶的偏见时指出:“《六经》时有俪辞,扬、马、张、蔡之徒始盛。”[6]207又举经书中“云从龙,风从虎”[8]为证,其意、其辞明显源于《文心雕龙·丽辞》:“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9]314特别是“扬、马、张、蔡之徒始盛”一句,讲自觉追求骈俪之始,更是直接取自《文心雕龙·丽辞》中“自扬、马、张、蔡崇盛俪辞”之句。第二,论述骈散关系之语如“因意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斧斤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6]208,也正是从《文心雕龙·丽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9]314化来,意思是作骈作散都要讲究自然与浑成。由此可见,皎然受《文心雕龙》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裴度主要生活在中唐时期,是朝廷重臣,参与文学活动有限,但是对当时文体文风改革中所涉及的骈散问题也有所论列。大体说来,他的骈文批评虽然也以着眼政治教化为主,以儒家经典为法式,但是不像古文家那样激进,而是有所折中。其一,他以儒家经典为范式,批评古文家单纯追求怪奇的不良风气,其《寄李翱书》中指出:“董仲舒、刘向之文,通儒之文也,发明经术,究极天人。其实擅美一时,流誉千载者多矣,不足为弟道焉。然皆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谟、训、诰、《文言》《系辞》、国风、雅颂,经圣人之笔削者,则又至易也,至直也。虽大弥天地,细入无间,而奇言怪语,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此所谓文可文,非常文也。”[2]5461—5462就中唐古文创作思潮而言,这样的批评是很中肯的,切中要害,因为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古文家在作文之时刻意追求怪奇,缺乏平易之气,走入极端。其二,他又以儒家“辞达”说为理论依据,直接批评李翱等古文家对待骈文的偏激行为,指出:“……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志,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则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逾,又何必远关经术,然后骋其材力哉?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2]5462在他看来,为文之要在于达意,在“气格”与“思致”,而不在骈散,所以便以非常形象的语言批评李翱刻意作散、强与骈文分疆划界的错误做法。从中可以看出裴度在骈散二体上没有壁垒和成见,也比较折中。
从实而论,中唐时期上述两派骈文批评的出现,不是文学批评的退步,而是巨大的进步,反映出当时骈文批评的深入,说明中唐文学批评家在文体意识上明显超过初盛唐的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