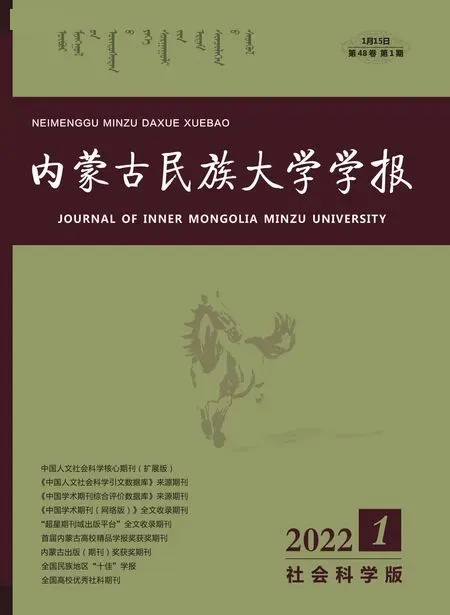阿夫沙尔王朝对伊朗民族国家的影响探析
冀开运,申瑛瑛
(1.西南大学 伊朗研究中心;2.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18世纪初期,得益于周边伊斯兰各国开始普遍衰落及西方殖民体系尚未健全,阿夫沙尔王朝①大规模向外扩张并在50年代达到顶峰。作为伊朗②历史上最后一个大规模对外扩张且范围超过伊朗高原的王朝,阿夫沙尔王朝这个动荡不安的“彗星”,曾有过四位统治者。阿夫沙尔王朝开国皇帝纳迪尔·沙赫③于1736年在穆甘平原被贵族会议拥立为王,建立阿夫沙尔王朝,1747年6月在其侄子阿里·戈利(Ali Quli)的授意下被侍卫刺杀。第二任统治者阿里·戈利(Ali Quli)1747年被拥立为王,称阿迪勒沙(意为公正的沙赫),不到一年时间被其亲兄弟逼迫退位并挖去双目,后被纳迪尔·沙赫的寡妻下令处死。沙哈鲁(Shahrukh)1748年10月被拥立为王,不久被废黜,此后赛义德·穆罕默德(Said Mohammed)短暂掌权,称苏莱曼二世。在苏莱曼二世被废黜后,沙哈鲁于1750年再次被拥立为王,此次统治直至1796年。后沙哈鲁为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开国君主阿迦·穆罕默德(Agha mobammad)折磨致死,这也标志着阿夫沙尔王朝的终结。
阿夫沙尔王朝的建立者纳迪尔·沙赫17世纪末④出生于波斯东北边境呼罗珊省北部土库曼人基尔克卢分支阿夫沙尔的一个普通牧民家庭。童年受父亲宠爱,是一名天资聪慧的优秀猎手,后因其父亲早逝,成长环境艰苦,早年生活贫困。大约15岁已经效忠于呼罗珊部落首领巴巴·阿里·贝格(Baba Ali Berg),成为颇得总督赏识的得力助手,得到巴巴·阿里的公开提携后声名鹊起,不久就掌握了呼罗珊的实权。
1722年是伊朗近代的重要时间节点,通常将阿富汗人攻占伊斯法罕、苏丹·侯赛因(Sultan Husayn)出城投降看作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统治的大体终结。这也是纳迪尔·沙赫跌宕起伏的一生的重要转折点,直接影响其未来职业生涯的走向,从公开对抗阿富汗首领马哈茂德,到加入塔赫马斯普二世麾下恢复萨法维王朝的统治,纳迪尔·沙赫仅用短短三年便完成将波斯从阿富汗人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艰巨任务。接着驱逐本土奥斯曼人甚至入侵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后将扩张的雄心投向当时逐渐衰败的莫卧儿帝国,袭击印度占领德里,但德里一战后纳迪尔·沙赫遭遇身体疾病与心理折磨的双重压力,变得反复无常,其统治的十年以冲突、混乱和压迫为主要标志。1747年,纳迪尔·沙赫被其侍卫暗杀,他的帝国迅速崩溃,此后伊朗分裂成几个独立的领域,混战一直持续到几十年后恺加王朝的崛起。
目前国内尚未发表研究阿夫沙尔王朝及纳迪尔·沙赫本人的专著,仅在一些有关伊朗的通史性著作中略有提及。对阿夫沙尔王朝的研究论文成果有龙沛《伊朗阿夫沙尔王朝的崛起机遇、扩张困境及历史遗产》一文[1],主要是在近代早期伊斯兰帝国体系瓦解的大背景下,分析阿夫沙尔王朝的崛起、扩张和再解体的原因、困境及历史遗产。文章指出阿夫沙尔王朝的崛起和扩张更多受益于18世纪西方尚未健全的殖民体系和周边帝国势力的相对下沉,在近代伊朗历史上作为连接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的历史节点,对伊朗近代历史进程和走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解体后伊朗地区的长期动荡削弱了恺加王朝时期伊朗抗衡英俄殖民帝国渗透的能力。
国外研究,除了以《剑桥伊朗史》第七卷[2]为代表的通史性著作外,对阿夫沙尔王朝的研究成果突出集中于对纳迪尔·沙赫本人全方位的研究上。对于纳迪尔·沙赫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经过了劳伦斯·路克哈特(Laurence Lockhart)、迈克尔·阿克斯沃西(Michael Axworthy)及欧内斯特·S·塔克(Ernest s Tucker)三位学者的接续努力。劳伦斯·路克哈特的《纳迪尔沙:基于同时代史料的批判研究》[3]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纳迪尔·沙赫生平的著作,系统探讨其出身、生平以及征战经历。迈克尔·阿克斯沃西的《波斯之剑:纳迪尔沙与现代伊朗的崛起》[4]以及欧内斯特·S·塔克的《后萨法维时代纳迪尔沙对伊朗正统性权力的追求》[5]均为21世纪新作,迈克尔·阿克斯沃西更关注纳迪尔·沙赫军事领域的研究,欧内斯特·S·塔克主要着重于纳迪尔·沙赫取得伊朗王位并建立阿夫沙尔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过程,著作出版前二人均有研究重点更为集中的相关论文发表。建国者纳迪尔·沙赫通过对阿富汗人的反侵略战争、对奥斯曼帝国的争霸战争以及对莫卧儿帝国的侵略战争等三阶段三种性质的对外作战,迅速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大帝国。阿夫沙尔王朝连接了萨法维王朝与恺加王朝,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伊朗国家统一产生了宽领域、深层次的影响。通过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在连接萨法维王朝与恺加王朝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分析伊朗民族国家构建长时段的内外逻辑,从而对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作出连贯准确的整体把握。
一、重建疆域
近代早期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三大帝国的鼎立,以实力对比势均力敌为基础,长期维持着伊斯兰世界相对稳定的状态。18世纪初期,伊斯兰各国开始普遍衰落,阿富汗吉尔扎伊部落攻陷萨法维王朝首都伊斯法罕,打破了三大帝国的均势。此后纳迪尔·沙赫发起的一系列对外作战,建立起阿夫沙尔王朝,为现代伊朗的领土认同与边界划分打好基础。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伊朗被当时的强国沙皇俄国及奥斯曼帝国瓜分,一定意义上有限地延续了伊朗作为当时伊斯兰世界三大帝国的大国影响。
纳迪尔·沙赫重建统治疆域与提高个人威望的过程基本同步,分为以下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对阿富汗人的作战。1722年10月,经过几个月围困,阿富汗军队征服了伊斯法罕,推翻苏丹·侯赛因统治。四年后,纳迪尔·沙赫开始效力于萨法维遗孤塔赫马斯普二世,这标志着他从一名地方军阀变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1729年5月,纳迪尔·沙赫在反侵略战役中于阿什拉夫(Ashraf)击败了吉尔扎伊(Ghalzay)阿富汗人,这一事件标志着阿富汗人在伊朗的权力的终结。第二阶段是对奥斯曼人的作战。1730年,纳迪尔·沙赫首次在阿塞拜疆与奥斯曼人作战,1732年,他回到了伊斯法罕,在那里废黜塔赫马斯普二世(TahmaspII),并立其八个月大的儿子为沙阿,称阿巴斯三世(Shah Abbas III)。1733至1734年,纳迪尔·沙赫于伊拉克及阿塞拜疆第二次对奥斯曼人作战,1735年底,完全收复波斯西部及西北部地区,次年,于穆甘平原举行了忽里勒台⑤,在这里与代表们签订了执政协议并举行了加冕典礼,至此纳迪尔·沙赫的国内威望进一步提升。第三阶段是对莫卧儿帝国的作战。1738年,纳迪尔·沙赫在征服汉达基王朝(Hotak dynasty)[6]最后的据点坎大哈(Kandahar)后,将扩张的雄心投向当时逐渐衰败的莫卧儿帝国,1739年2月,在卡尔纳尔战役中击败了莫卧儿帝国的主要军队后进驻德里。伴随着卡尔纳尔的胜利以及对德里的征服,纳迪尔·沙赫成为名扬世界的人物,其成就与威望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
他能够实现这三阶段作战胜利,得益于一支战斗力出众、数目庞大、装备新式火器、拥有现代作战方式的军队。在纳迪尔·沙赫的指导下,波斯完全接受了火药武器,这引发了波斯军队的技术、演习、纪律以及系统等多方面的变革,若非纳迪尔·沙赫的英年早逝,这些改进还将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这支庞大的军队纪律严明、积极进取、补给充足且拥有纳迪尔·沙赫定期支付军费和提供补给,以杰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为代表的学者们甚至将其与欧洲的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 in Europe)[7]636相媲美。纳迪尔·沙赫建立起的这支新式军队不断进化,在其带领下相继打败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等劲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力量,而且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虽然由于纳迪尔·沙赫登上王位的十一年间对外扩张战乱频仍,更多地被定义为更稳定的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之间短暂的过渡时期,但这一时期纳迪尔·沙赫在伊朗高原的迅速崛起和卓越功绩早已成为传奇,甚至一个世纪以后的伊朗依然致力于恢复纳迪尔·沙赫时代的版图[8]138。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阿夫沙尔王朝与中国康乾盛世乾隆执政时间基本同期,纳迪尔·沙赫的阿夫沙尔王朝与乾隆执政时期的大清帝国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领域有一定可比性⑥。伴随着纳迪尔·沙赫的对外征服,阿夫沙尔王朝从西亚到南亚地区连年战火,中亚地区曾经由三大帝国构成的近代早期伊斯兰世界帝国秩序不复存在。
二、国家构建
早在18 世纪初期,外有强敌内有忧患,萨法维王朝衰落的迹象就已经显现。1722年伊斯法罕被攻陷后,萨法维王朝面临着来自阿富汗、帝俄和奥斯曼的三重威胁,纳迪尔·沙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萨法维王朝的守护者进入了伊朗历史的主流,几乎没有使用政治暴力就崛起掌权[9],建立了阿夫沙尔王朝。
伊朗民族国家在萨法维王朝两百多年间通过划定疆域、确定什叶派信仰等措施得以初步确立,在阿夫沙尔王朝时期其民族国家的构建得以进一步强化。
第一,阿夫沙尔王朝的国家机构的运转高度依赖纳迪尔·沙赫本人,其统治期间国家频繁的对外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证纳迪尔·沙赫的个人威望,这也是其建立国家认同转移国内统治危机的重要手段。纳迪尔·沙赫是一个高度波斯化的土库曼人,掌握并在日常活动中使用波斯语。纳迪尔·沙赫建立王朝后,沿袭伊朗历史上以族名冠以王朝的惯例,伊朗本土精英并没有认为纳迪尔·沙赫取代萨法维是“蛮族入侵”或者“以夷易夏”,其本人也在1736年登基后采用沙赫这一典型伊朗领导人的称号。其王朝本身带有土库曼政权与伊朗政权的二重性,体现出纳迪尔·沙赫本人的土库曼人与伊朗人双重认同的特性,究其本质,阿夫沙尔王朝及其建立者的土库曼属性服从服务于其波斯属性。
第二,波斯民众对于伊朗阿夫沙尔王朝也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1742年10月,纳迪尔·沙赫与其子礼萨·戈利(Riza Quli)爆发冲突,因为猜疑礼萨·戈利参与刺杀沙赫的阴谋活动且多次与其沟通无果,纳迪尔·沙赫一气之下下令挖掉礼萨·戈利的双眼并呈给他过目。礼萨·戈利曾是沙赫引以为傲的接班人,更是有能力将阿夫沙尔王朝的统治延续下去的不二人选,在其失明后,帝国的运势急转直下,垂垂老矣,气数将尽,由于纳迪尔·沙赫的冲动暴虐造成了一个家族、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悲剧。纳迪尔·沙赫的前半生,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但其统治末期,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伊朗后人常将礼萨·戈利受刑后的话改为:“你挖出的不是我的眼睛,而是波斯的眼睛”[4]335,以体现纳迪尔·沙赫遇刺后其统治区域的混乱与悲剧。从世俗的角度来说,纳迪尔·沙赫居功至伟,对阿富汗人作战的胜利洗去了波斯人被外族入侵的耻辱,完成了复仇,也因此使得礼萨·戈利个人的悲惨遭遇更像是全体波斯人民的遭遇。
第三,纳迪尔·沙赫统治期间曾经多次进行人口迁移,随着时间推移,迁居政策成为其统治时期的一个主题,这客观上加强了伊朗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纳迪尔·沙赫在统治期间多次在多地进行过人口迁移,向北迁移的人口规模数以万计,如1730年11月抵达马什哈德时,纳迪尔·沙赫要求检阅之前应按照他的要求迁居呼罗珊的部落人口[4]137,移民包括五六万库尔德人、阿夫沙尔人和最近从哈马丹和阿塞拜疆迁到东部的人口。18世纪30年代初,国内叛乱被平定后,六万多名阿卜达里人被分派到呼罗珊的不同地区定居[4]141。此外,纳迪尔·沙赫军队中有一些警卫部队的成员,是从纳迪尔·沙赫要求在呼罗珊重新定居的叛乱部落首领的家庭中招募的[7]634。移民政策是其统治时期的重要支柱,尽管在不同的文献中他对待移民的态度相去甚远,但就促进民族融合、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角度下,其治下迁居政策的贯彻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纳迪尔·沙赫的多种生活习俗、政治法令中均体现出其强烈的波斯属性以及独属于伊朗高原的归属感。在纳迪尔·沙赫多年的征战生涯中,坚持在每年的3月21日庆祝诺鲁孜节⑦。纳迪尔·沙赫十分重视诺鲁孜节,其发迹后几乎从没有长时间间断诺鲁孜节的庆祝活动,当结婚生子等时间正好在诺鲁孜节日附近,还会延长庆祝活动。1727年的诺鲁孜节就因纳迪尔·沙赫迎娶一位库尔德首领之女而延长至两周。诺鲁孜节在纳迪尔·沙赫眼中,还有着战前祈福纳吉的作用,每次准备发动战争前的诺鲁孜节都会被悉心准备。除了关于诺鲁孜节的庆祝活动,纳迪尔·沙赫还在1739年洗劫德里后颁布过一条重要法令,宣布波斯地区免除3年的赋税。这足以证明这一时期的纳迪尔·沙赫是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全体波斯人民的领导者,而非局限于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他是全体波斯人的“沙赫”,而非仅仅是土库曼部落的“汗王”。
第五,纳迪尔·沙赫自诩为波斯帝国正当的继承者,其国家认同主要分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方面,纳迪尔·沙赫具有波斯民众惯有的雅利安人认同,1736年其登基以后篆刻的新式王家印章上,刻有“自国家与宗教之宝消失于原处,真主以雅利安人纳迪尔之名将其归还”[4]208的铭文,这应是经其默许或者根本就是其授意下的政治行为。在新式王家印章上的重要铭文中,纳迪尔·沙赫在诸多身份中选定了伊朗语支诸民族共同的祖先“雅利安人”的称呼,其意义不言自明。伊朗高原对外的雅利安认同的自豪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纳迪尔·沙赫作为土生土长的土库曼人,一是借以证明伊朗高原土著居民的血统高贵性,二是重在强调自身与伊朗高原各个族群之间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另一方面,纳迪尔·沙赫具有波斯族裔的伊朗认同。纳迪尔·沙赫在加冕典礼上的宣誓词中称自己为“伊朗人纳迪尔”,尽管有些学者认为纳迪尔·沙赫末期对域内人民施行残酷统治是由于其土库曼人的族裔身份,但总体来看,其统治下未发现有打压波斯人等土库曼部落之外的民族歧视政策,阿夫沙尔王朝未针对波斯人与其他族裔制定特殊身份限定政策,因而他算是完全伊朗化的统治者,其统治下的严苛,只能算是统治者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而绝非是土库曼人对波斯人的迫害。1722年后伊朗高原土库曼人与其他族裔的民族意识及民族边界模糊,具有超越民族的地域认同及国家认同,其治下的波斯民众也认可阿夫沙尔王朝的正统性。
三、宗教主张
纳迪尔·沙赫建立帝国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打天下的任务就已经完成,治天下被提上日程,随着1736年纳迪尔·沙赫在穆甘平原登上王位后,构建阿夫沙尔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刻不容缓。在萨法维王朝统治两个世纪之后,纳迪尔·沙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废除萨法维统治的旧有制度巩固新王朝,其中挑战伊朗的十二什叶派身份,建立伊斯兰教贾法里教派并将其作为逊尼派第五教派的决定[10]尤为引人注目。
萨法维王朝统治的两百年多年间,伊朗确立了什叶派主教地位,逐渐成为伊朗民族认同的核心。纳迪尔·沙赫早年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坚定信徒,在登基前,明确公开宣布了什叶派信仰。纳迪尔·沙赫为他的前两个孩子取了典型的什叶派名字:礼萨·戈利(Riza Quli)和穆尔塔扎·戈利(Murtaza Quli)。纳迪尔·沙赫曾为纪念战胜阿卜达里人而建立过一个宗教基金,它的契约日期为1732年6月,并印有纳迪尔·沙赫的个人印章,包括了什叶派的座右铭:“没有比阿里更具有骑士精神的青年了……我是这个时代罕见地得到了上帝恩典的人,是十二名伊玛目的仆人。”[5]34纳迪尔·沙赫还给赫拉特的帖木儿·沙鲁克(Timurid Shahrukh)清真寺的圆顶镀金,并认为这样“十二伊玛目信仰”的光芒每天都会增加。[5]35因此,纳迪尔·沙赫早期反对阿富汗人的运动充满了为保护什叶派和萨法维人而斗争的色彩。他将萨法维王朝遗臣团结在什叶派旗帜之下,以恢复旧王朝正统为口号四处征战,伴随着纳迪尔·沙赫军事能力增强,国家地位提升的同时,什叶派十二伊玛目的信仰在广大伊朗穆斯林的心中根深蒂固。
1735年底,纳迪尔·沙赫完全恢复了伊朗的西部及西北部地区的统治,收复除坎大哈外所有阿富汗人入侵之前的边境地区,次年在穆甘平原召开忽里勒台,在与忽里勒台代表们签订的协议中提出了“波斯人必须停止诅咒欧麦尔(Umaribn al-Khattab)和奥斯曼(UthmanibnAffan)……波斯人理应接受逊尼派教义,将伊玛目贾法尔(Jafar)奉为自己教派的领袖⑧”等宗教条件,并在随后通过的条款中重申对奥斯曼人的和平协议:“(1)波斯人已经摒弃了之前的信仰,转而选择逊尼派,他们理应被公认为第五学派贾法里派;(2)既然现有四大教法学派的伊玛目在克尔白均享有自己的立柱,那么伊玛目贾法尔也理应拥有一根立柱……”[4]195—198通过以上条例,纳迪尔·沙赫向奥斯曼帝国提议,将十二什叶派视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第五个流派,贾法里派应享有前四大教法学派(沙斐仪派、哈乃斐派、马利基派和罕百里派等伊斯兰逊尼派已经承认的教法学派)的所有特权,并在麦加的克尔白拥有立柱。相应地,伊朗什叶派将放弃各项反逊尼派的基本活动皈依逊尼派。
有关这一时期的著作均绕不开纳迪尔·沙赫形式上改信逊尼派贾法里教派的法令,关于宗教改制,最早研究见于劳伦斯·路克哈特著作之中,众多学者对纳迪尔·沙赫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的解析无出其右。路克哈特在提到其宗教政策时指出这一政策完全与萨法维王朝背道而驰,“在许多方面,他试图尽可能让新王朝脱离萨法维时期的方式和习俗。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用逊尼派取代什叶派……”[3]270同时他认为,纳迪尔·沙赫并非宗教狂热分子,“他确实迫害什叶派,但他这样做纯粹是出于世俗原因”[3]278。
此外,欧内斯特·S·塔克指出纳迪尔·沙赫的贾法里教派提案的国内外版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11],在国外,纳迪尔·沙赫将此政策阐述为彻底皈依逊尼派,称贾法里教派是消除所有什叶派仪式的逊尼派,已经取缔了如诅咒前三位哈里发等反逊尼派的活动,并在官方信中向奥斯曼人解释说,在萨法维王朝的弊政被消除后,贾法里教派与四个正统的逊尼教派没有什么不同,为伊朗什叶派被完全接受为逊尼派扫清道路。与提交给奥斯曼人的内容不同,国内版本的贾法里教派被描述为尽管重新划定了公共和私人信仰表现之间的界限,却保留了什叶派的基本方面。用迈克尔·阿克斯沃西的话来说:“……波斯人也并未向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被简单地要求立即改宗逊尼派: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独立的宗教身份。”[4]200纳迪尔·沙赫提出什叶派仪式不可强烈反对逊尼派,其国内宗教政策将这些仪式重新定义为什叶派的基本外在表达,尽管他禁止民众像萨法维王朝时期那样公开举行攻击逊尼教的仪式,但在伊朗执行宗教政策的具体过程中发出信号,宽恕什叶派的伪装,民众得以内心保持对某些教义的信仰。
纳迪尔·沙赫充分理解什叶派在联结波斯各民族方面所发挥的纽带作用的本质,他的宗教政策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首先,贾法里教派是一种为“逊尼派的药丸加糖”[3]279的做法,其本质是以便其能更容易地被伊朗原什叶派穆斯林及奥斯曼帝国所接受,一旦改信逊尼派为民族所接受,对内将割裂新王朝与萨法维王朝的法统联系,对外可以有效缓和长期以来与周边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紧张关系;其次,对外则为建立统一的穆斯林世界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创造有力的政治宗教环境。纳迪尔·沙赫的视野已经不局限于国家,而是国际性的,其统治梦想远远超出了萨法维帝国的范围,他构思的是囊括统一的穆斯林世界的宏伟蓝图。再次,萨法维王朝末期,大力提倡部分极端什叶派思想及宗教仪式,一度促使王朝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冲突升级,使伊朗在18世纪初面临的国际局势极度恶化,新王朝建立之初宣扬放弃前王朝什叶派某些狭隘的做法,意在纠正萨法维王朝末期什叶派极端主义。最后,关于设立贾法里教派的协议,在阿夫沙尔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展开的数年谈判拉扯中,奥斯曼帝国对待贾法里教派的拒绝态度昭然若揭且从一而终,而纳迪尔·沙赫一开始接受搁置争议,不久后又重开谈判,在协商失败后再度诉诸战争,通过其态度的前后转变不难推测改信逊尼派的宗教政策本就是他拖延时间备战与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政治策略,在阿夫沙尔王朝已经作出部分妥协却仍未被奥斯曼帝国等主流伊斯兰教逊尼派国家接受的情况下,对奥作战便成为顺理成章的圣战。
1736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波斯人与奥斯曼人签订协议,协议中搁置宗教议题,1738年5月,伊斯坦布尔派大使向纳迪尔·沙赫表示苏丹不接受贾法里教派以及第五根立柱的建议,沙赫派波斯大使继续进行谈判,最终于1742年1月,奥斯曼再次拒绝接受和平协议,纳迪尔·沙赫随即准备对奥作战。一系列谈判中,宗教议题始终是双方争论的焦点,长达六年的拉扯最终以战争的方式画上了句点。
1747年6月纳迪尔·沙赫的死标志着阿夫沙尔王朝最终放弃贾法里教法学派的概念。他的孙子沙哈鲁成为他的继任者后,明确地将自己塑造为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正统的坚定捍卫者。
不论纳迪尔·沙赫早年作为一位坚定的什叶派信仰者还是在其加冕后对旧王朝宗教改制及失败,均促进什叶派信仰发展。纳迪尔·沙赫的宗教政策与萨法维王朝时期的差异十分明显,可以说是其借宗教改革的方式来废除萨法维统治的旧有制度。他的提议未能吸引奥斯曼帝国或伊朗臣民的支持,在其遇害后,宗教政策便随着阿夫沙尔王朝的瓦解分崩离析,这恰恰证明了伊朗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正统在萨法维王朝末期发展起来的巨大力量。纳迪尔·沙赫建立贾法里教派概念的尝试是短暂的,它与历史悠久的什叶派传统背道而驰,放弃什叶派的传统仪式,意味着将放弃在12—18世纪已成为什叶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阿夫沙尔王朝宗教政策的强烈冲击下,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反而更加稳固,什叶派最终成为伊朗不可逆转的潮流。
四、物质财富
纳迪尔·沙赫摆脱了萨法维政权垮台后的无政府状态,恢复波斯的所有旧边界,并通过谈判和反奥斯曼联盟确保北部的俄罗斯人的撤离[7]639。新式军队是纳迪尔·沙赫维护广阔疆域的重要工具和基础保障,正因为如此,他在征战过程中重视财富掠夺,财富得到了积累,用以付清或提前支付士兵薪资、购买火器战马及建造战船等维持军队日常运作的多项活动。伊朗阿夫沙尔王朝的财富积累主要得益于纳迪尔·沙赫统治时期,其统治下财富来源的主要方式并非常规的生产积累及经济贸易,而是18世纪常见的对内横征暴敛以及对战败或归降区域的收缴掠夺,如1736年10月在伊斯法罕收缴军费及1746年12月再度对伊斯法罕进行洗劫[4]215,1739年与莫卧儿帝国著名的卡尔纳尔战役后在德里的掠夺,1740年2月征服信德获得巨额战利品及信德总督的供奉[8]21,5月沿着印度河追击胡达亚尔汗后获得原属于苏丹·侯赛因的部分财物[4]257等。这诸多财富积累活动中,有详细记载且数目最庞大的当属1739年在德里的洗劫。
格尔纳尔的胜利以及对德里的征服,使纳迪尔·沙赫成为名扬世界的人物,莫卧儿帝国上百年间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被伊朗阿夫沙尔王朝收入囊中,对此印度一位历史学家记录道:“348年积累的财富一转眼就倒手了”[12]35。1739年3月20日至5月16日纳迪尔·沙赫仅在德里停留不到两个月,这期间收缴黄金白银珠宝及其他珍贵财宝共计7亿卢比,约合8750万英镑,其中包括最负盛名的孔雀王座以及光之山和光之海两大顶级珠宝。
这些财富在纳迪尔·沙赫遇害后,辗转赞德人之手,后成为恺加王朝的财富得以保留下来。恺加王朝建立者阿迦·穆罕默德沙1794年在克尔曼获得“光之海”“月亮王冠”“伟大的国王”等三颗原本由纳迪尔·沙赫从印度带回的著名宝石[8]90,后于1796年攻破马什哈德从沙哈鲁治下获得了阿夫沙尔王朝的其余财富。同年,阿迦·穆罕默德沙建立恺加王朝,定都德黑兰,领有除现阿富汗以外萨法维王朝时期的大部分疆域。
虽然阿迦·穆罕默德沙建国次年便被刺身亡,但其战争掠夺的金银珠宝得以以国家财富的方式流传,直到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时期还存在国家银行的保管库里,其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纳迪尔带着俘虏向德里进军……依据战争财产的规定,夺得的珠宝将成为波斯王国的财富……用来支撑我们的货币。”[12]35“……以黄金和王室的珠宝作为后盾发行了新钞票,这些最珍贵的珠宝是纳迪尔王在印度打仗时的战利品。”[12]46这笔国家财富的来龙去脉清晰可见,而礼萨·沙阿·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时期借由威权政治推行的包括币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层面的改革措施,直接推动了近代伊朗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礼萨·汗时期的统治之所以“构成了推动伊朗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有力杠杆”[13],纳迪尔·沙赫时期巨额的国家财富积累功不可没。纳迪尔·沙赫对外扩张过程中积累的财富短期内减轻了现代伊朗的财政压力,对其国家再统一以及国内统一局势的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国家记忆
纳迪尔·沙赫本人凭借丰功伟绩成为伊朗的民族英雄和伊朗爱国主义的精神源头之一。纳迪尔·沙赫从默默无闻中崛起,在与众多强大对手作战的过程中,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熟练的军事指挥官,对抗外来侵略并收复失地,使得伊朗边界不断延伸。作为伊朗的文化名片,纳迪尔·沙赫的存在本身就是伊朗爱国主义的物质寄托,其强大的军事及政治行动建立了与波斯文化影响范围基本吻合的地理范围的大伊朗,阿夫沙尔帝国鼎盛时期的统治范围,有助于波斯文化在大伊朗范围内影响的延续,形成并巩固了大伊朗文化圈。
纳迪尔·沙赫被伊朗人民尊称为“波斯拿破仑”,以体现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所取得的傲人战绩。更有甚者,认为单论军事能力纳迪尔·沙赫要更优于拿破仑,毕竟“拿破仑最后被联军击败,纳迪尔·沙赫却一直战无不胜”。[12]36作为伊朗历史上最后一个大规模对外扩张的王朝阿夫沙尔王朝的建立者,纳迪尔·沙赫除被称为“波斯拿破仑”外,还享有“亚洲最后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波斯之剑”等多项头衔,这些称号无一不在彰显纳迪尔·沙赫享誉波斯的军事神话。
脱去上衣,在明亮的光线下,面对镜子做双侧乳房视诊。双臂下垂,观察两边乳房的弧形轮廓有无改变、是否在同一高度,乳房、乳头、乳晕皮肤有无脱皮或糜烂,乳头是否提高或回缩。然后双手叉腰,身体做左右旋转状继续观察以上变化。
伊朗人民对纳迪尔·沙赫的崇拜由来已久,在纳迪尔·沙赫遇刺身亡后,在其生前曾担任阿夫沙尔王朝财务官的穆罕默德·卡齐姆·马尔维(Muhammad Kazim Marvi)就在其著作中表示纳迪尔·沙赫是一位能回击中亚侵略者的领袖[14],由于穆罕默德·卡齐姆·马尔维的著作成书于纳迪尔·沙赫死后,所以这本纳迪尔·沙赫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波斯散文编年史,并非完全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政治产物。在相对写作自由的条件下,这本著作仍然像米尔扎·马赫迪汗·阿斯特拉巴迪(Mirza Mahdi Khan Astarabadi)为纳迪尔·沙赫撰写的传记⑨一样,赞美和颂扬了纳迪尔·沙赫的胜利和勇敢的行为。
恺加王朝时期,致力于恢复纳迪尔·沙赫时代的统治疆域,由此在伊俄战争结束后,又再度东征,与赫拉特作战并尝试收复阿富汗。纳迪尔·沙赫统治时期对外征战恢复了伊朗的帝国版图,在18世纪西方殖民体系尚未健全及周边地区帝国体系相对下沉的空档期[1]90,他树立的大伊朗观念深入人心,伊朗恺加王朝将对外作战收复原本由纳迪尔·沙赫夺回却又失去的地区看作一种民族责任和民族尊严。
到了巴列维王朝时期,纳迪尔·沙赫反击阿富汗人入侵,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再次巩固伊朗统一的历史地位更加突出。纳迪尔·沙赫在德里掠夺的财富成为国库资金,巴列维王朝时期曾用以作为后盾发行新货币。著名珠宝“光之海”,是由纳迪尔·沙赫打败莫卧儿帝国后作为战利品带回呼罗珊,后作为伊朗的国家遗产留存,礼萨·汗时期曾储存于伊朗国库,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回忆录中以无比自豪的口吻提到英王拥有“光之山”,伊朗拥有“或许是颗更加美丽的宝石”[15]——光之海。这颗顶级的钻石至今仍得以在德黑兰展出,它是伊朗的国家财产的一部分,更是伊朗人民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承载着伊朗厚重的民族自豪感,闪耀着纳迪尔·沙赫时代以来的光辉。
此外,在伊朗马什哈德城,伊玛目礼萨圣陵的西北方向,至今仍坐落着伊朗阿夫沙尔王朝开国君主纳迪尔·沙赫的陵墓博物馆(Mausoleum of Nader Shah),为20世纪50年代在原址修建,博物馆内展出众多高质量军事文物,陵墓外还有伊朗人民为纪念纳迪尔·沙赫而建造的雕像。纳迪尔·沙赫的陵墓及博物馆作为景点对外开放后,每年都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了解其南征北战的英雄事迹。作为伊朗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者,纳迪尔·沙赫俨然已经成为现代伊朗人民的历史记忆、民族记忆和爱国主义精神、文化的重要源泉。
六、结语
阿夫沙尔王朝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其兴衰进程始终影响着中东地区王朝更替和同时期西方国际形势,对近代中东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夫沙尔王朝的溃败,标志着伊朗高原的帝国时代的终结以及近代早期伊斯兰世界依靠三大帝国的均势长期维持的伊斯兰世界相对稳定的状态被打破。纳迪尔·沙赫被公认为波斯帝国正当的继承者,在阿夫沙尔王朝时期,超越族群的地域认同更加强烈,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远远高于族群认同。当时的伊朗人没有清晰的族群与边界意识,更多的是对伊朗高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且这种族群边界的相对模糊性和灵活性延续至今。直至近代,伊朗的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依然只是一种民间社会行为,而非国家政治行为,不带有法律性,但客观上来讲,在伊朗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过程中,单从族群而言,波斯文化主导下的非波斯族裔人民居功至伟。阿夫沙尔王朝的建立,对近代伊朗的版图、族群结构产生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充分体现了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历程中非波斯因素的重要性,这也充分体现近五百年来,伊朗高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创立与巩固离不开伊朗高原的各个族群,今天伊朗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今天伊朗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纳迪尔·沙赫多年南征北战,推动伊朗军事近代化,建立起地域广阔的大伊朗,加强了伊朗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强化了伊朗在萨法维时期初步建立起的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历程。纳迪尔·沙赫对外扩张过程中积累的财富,不少直到巴列维时期仍是国家资金的重要担保及国族荣耀的重要来源,崇拜他已经成为伊朗人民爱国主义的具象的外在表现。作为一名杰出军事家,纳迪尔·沙赫建立的王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伟大征服者的个人权威,在他被刺杀后,由其后继者统治的阿夫沙尔王朝领土相对收缩,国力也更加孱弱。尽管阿夫沙尔王朝留有诸多遗憾,但纳迪尔·沙赫这位白手起家的“波斯拿破仑”,用自己手中的剑,在重建伊朗大一统的同时,为后世留下了精神与物质的多重财富,不论其所勾勒的建立统一穆斯林世界的蓝图完成了多少,纳迪尔·沙赫都曾为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交上过一份差强人意的答卷。阿夫沙尔王朝实现的国家统一,在巩固强化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历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建设性作用。
[注 释]
①Afsharids,1736—1796年,共六十年。相对于恺加王朝末期的大幅收缩而言,其全盛时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具体领土包括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及巴基斯坦部分地区。
②国外主流文献一般将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具有共性的政治体、文化体,在1935年以前称波斯,之后称伊朗,为了便于理解本文统一称为伊朗,只在涉及语言族群等具体内容时称为波斯。
③纳迪尔·沙赫(Nader Shah,1688—1747):1736—1747年在位,阿夫沙尔王朝建立者,“纳迪尔”,意为“罕有的”或“奇迹”,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称号,为便于理解本文全文采用纳迪尔·沙赫。本名为“纳迪尔·古里”(Nader Qoli),成为土库曼部落首领后称“纳迪尔·汗”(Nader Khan)。曾被萨法维王朝旧部统治者塔赫马斯普二世(Tahmasp II,1722—1732)赐名“塔赫马斯普·古里·汗”(Tahmasp Qoli Khan),意为“塔赫马斯普的奴仆”,但此处非传统意义上的奴隶,在当时以沙赫的名字做自己的名字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沙赫”部分汉语文献也译作“沙阿”或简称“沙”,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相当于“皇帝”或“天子”。结合中国语境“沙”类似俄国沙皇头衔,“赫”意味赫赫有名,指全伊朗境内唯一最高的合法统治者。
④出生于1688或1698年,尚无统一定论。欧内斯特·S·塔克(Ernest S Tucker)在其著作中指出纳迪尔·沙赫出生在1688年;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认为可靠的时间为1698年8月6日。
⑤忽里勒台即qoroltai,也可译作库里尔台。在突厥语中意为聚集,而在蒙古语中意为会议。它是古代蒙古的一个负责推举部落的首长及可汗的政治军事议会,这里类似于成吉思汗曾经召开的意在向贵族大臣展示实力、接受其效忠的会议,与会人没有实质的议政权及参与决策权。
⑥阿夫沙尔王朝存在于1736年至1796年,前后共六十年。乾隆,作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前后也共六十年,起止时间为1736年2月12日至1796年2月8日。不仅如此,纳迪尔曾被赐名“塔赫马斯普·里·汗”(Tahmasp Qoli Khan),其含义为“塔赫马斯普的奴仆”,也非常类似清王朝时期称“奴才”,意为服从、尊重、忠诚以及作为统治者认可的“圈内人”身份,在清朝时期只有满洲大臣和抬旗入满籍的汉人大臣才可称“奴才”,普通汉人大臣只可称“臣”。
⑦每年3月21日的春分日,是源自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的新年诺鲁孜节。波斯人自萨珊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起便开始在诺鲁孜节举行庆祝活动,至今仍是伊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⑧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他的最初四个继任者“四大哈里发”中的两名,欧麦尔·伊本·哈塔卜(Umaribn al-Khattab,634—644在位)与奥斯曼·伊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644—656 在位)。贾法尔·本·穆罕默德·本·阿里(Jafar bin Mohammed bin Ali),伊斯兰教什叶派主流派别十二伊玛目派尊奉的十二位伊玛目中的第六任伊玛目,创立了贾法里教法学派及十二伊玛目派神学。
⑨穆罕默德·卡齐姆·马尔维(Muhammad Kazim Marvi)的著作Tdrikh-i’dlam-ard-yiNddiri 英译为The World-Illuminating History of Nader,汉语译作《照亮世界历史的纳迪尔》;纳迪尔·沙赫的宫廷编年史家米尔扎·马赫迪汗·阿斯特拉巴迪(Mirza Mahdi KhanAstarabadi)著《纳迪尔沙史》(Histoire de Nader-Chah),二书均为记载纳迪尔时代的原始史料。其他当代编年史没有讨论纳迪尔的整个职业生涯,或者不是由为他工作过的人所著,故未纳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