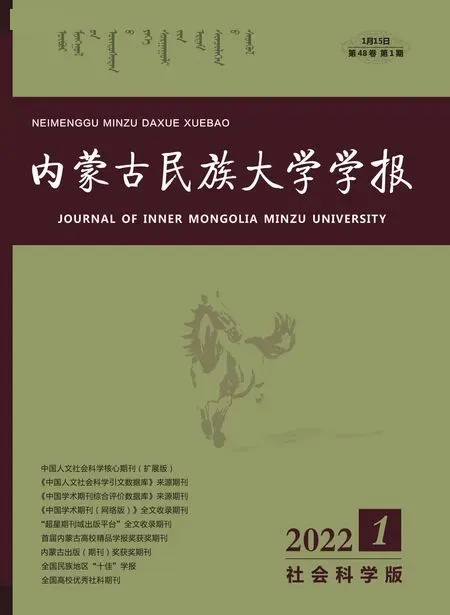辽代通辽地区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外交流
崔 宁,王 宬
(1.内蒙古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2.科尔沁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教学部,内蒙古 通辽 028000)
引言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它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意义是诠释着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交流和发展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心愿,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类永恒的信念。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他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darauf geründete Studien)的第一卷中提出:“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存在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1]。该观点被学术界和大众认可,继而被广泛使用。20世纪初,随着文物考古资料不断丰富,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Herrmann)在著作《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中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通道[2]。至此,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被明确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地区。
作为丝绸之路北线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中有一条始于内蒙古东部,越过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向西北穿过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一直到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3]。主要途经地区为地势平坦、没有阻隔的欧亚草原,再加上游牧民族天生的机动性,保证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的通畅,继而成为东西方文明相互学习、融合,彼此升华的重要通道。
内蒙古通辽位于西辽河中下游、科尔沁草原腹地,北纬42°15′—45°41′、东经119°15′—123°43′。通辽东靠吉林省四平市,西接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南依辽宁省沈阳市、阜新市、铁岭市,北边与兴安盟以及吉林省白城、松原市相邻。西辽河流域连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蒙古高原,是中原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的分界处。通辽位于欧亚草原南部的东端,历史上成为沟通中国南北和世界东西方的交通要道,通辽是其中东西交通路线的节点地区。2004年,科技部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西辽河文明首次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被确定为中华文明之源。通辽地处西辽河流域文化区的核心位置,旧石器晚期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10000年。中古时期,契丹在西辽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北方草原政权,最初的活动范围在西辽河流域的“松漠”地区。李鹏在《松漠访古——辽上京道历史地理新考》一书认为“松漠”是“北魏时期对科尔沁沙地的泛称”,即“大体分布在通辽市的扎鲁特旗南部、科左中旗、开鲁、科尔沁区、科左后旗和奈曼旗的中北部等地”[4],归辽代上京道管辖。明代嘉靖年间,蒙古族科尔沁部从嫩江流域来到西辽河流域,开启“科尔沁草原”的历史。1913年,“通辽”作为地名首次出现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卓里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因债务欲出放祖传的卓里克图亲王牧场事件的叙述中:“……去年十二月,会同卓里克图亲王暨在事汉蒙各员履勘。查得巴林他拉西北地方平甸一区,南临大道,西枕辽河,东倚平冈,北凭广野,地势高爽,永无水患,而水陆交通之便利,尤为他处所不及。拟即设立镇基,定名通辽……”①生动的语言形象地描绘了通辽当时的地理风貌、水文、交通特点。卓亲王色旺端鲁布在给黄仕福的书信中加以具体说明:“……巴林爱新荒段照章应设镇基一处,前经本亲王会同贵总办择定地点,派员丈量完竣,命名曰通辽镇,并呈报省署出示招领在案……”②经过镇基的勘察和丈量,通辽镇于1914年建成。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通辽镇历经由镇到县再到县级市的变化。1999年,哲里木盟撤盟设市,成立地级通辽市至今。
本文以辽代通辽地区为视角,旨在呈现通辽历史上作为辽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在辽王朝主导的草原丝绸之路东端奏响的文化交流的恢宏乐章。同时,辽代契丹民族在与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交流中表现的勃勃生机和创造力,对今天通辽的新丝绸之路建设也有现实意义。
一、辽代契丹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
公元10世纪初,兴起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契丹在草原丝绸之路东端建立了强大的辽帝国,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5]438,既是第一个统一整个中国东北的草原政权,又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契丹民族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游牧民族,在经济生活方面更多地展示出兼容并蓄的特点,四时捺钵、农耕渔猎,精美的辽三彩和马鞍让辽王朝的手工业闻名于世。一个具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民族注定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契丹民族自建立辽王朝起就十分重视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一方面奉行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5]923的武力征服政策,一方面频频采取和亲、使臣交往手段同周边建立友好关系,最终通过设立榷场同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交往。契丹民族在东北亚通过战争、和亲的方式,使阻卜(鞑靼)、高丽成为属国,贯通并且保持了东北亚北部和南部的丝绸之路的稳定。契丹民族向西通过和亲的方式同大食(伽色尼王朝)、波斯(萨曼王朝)、回鹘、西夏、吐蕃建立友好关系,使丝绸之路的西半部畅通无阻。《辽史》记载,辽太祖天赞二年(923年),波斯与辽通使;天赞三年(924年),阿拉伯帝国与辽通使,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遣使到辽国为王子请婚;太平元年(1021年),辽乃以可老为公主嫁之[5]189。据此,辽代的榷场分布在万里草原丝绸之路各个站点,并且第一次设立在阿拉伯地区。契丹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不间断地东征西拓,频繁地通婚和联姻,使草原丝绸之路成为大通道,推动了东西方沿线的贸易发展。史料记载,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燕京留守耶律隆庆遣副留守秘书大监张肃设宴招待北宋使臣路振,所用“醆盏斝皆颇璃黄金扣器”[6]14。我国古代陶瓷技术发达,北宋时期实用器皿包括饮食器皿均为陶瓷材质,国产玻璃多用于制作艺术观赏品和佛塔塔基的舍利瓶。这里提到的玻璃饮食器皿应当是从玻璃制造工艺成熟的伊斯兰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来到辽国的。此时,经由伊斯兰商人的转手贸易,辽代的对外贸易间接达到欧洲和非洲国家。唐朝晚期“安史之乱”导致传统丝绸之路被吐蕃阻断,契丹握住了历史的接力棒,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草原丝绸之路也在辽朝再次进入繁盛时期。
契丹以草原游牧民族崛起于长城以北,南取幽燕,建立了辽朝,历九主二百余载。迨天祚播迁,大石又延辽国于远方异地,遂使契丹一词渐从族名演变为中国的指称,此时的契丹发挥着沟通内地同西欧、阿拉伯诸国的通道作用。一方面,契丹将中国农耕文化中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儒家思想、生产方式、手工业、建筑传播到中亚地区,成为中华文化展演的窗口;另一方面,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契丹自身的经济、文化等已经十分发达,在向外传输自身文化的同时,也影响着外界对中国的印象,一些国家甚至认为契丹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把契丹作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俄文至今称中国为КИТАЙ,即“契丹”一词的斯拉夫语译音;穆斯林和西欧人用Qita(Khita)或者Qata(Khata)来指称中国北部,例如《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和《史集》(Jami‘al—Tarikh),皆从契丹而起。契丹虽然久已与其他民族同化而今难以辨析,但是契丹在历史上的功绩永载史册[7]。从世界文化格局角度来说,契丹民族开拓草原丝绸之路,使东西方各民族实现文明交流互鉴,意义远远超过丝绸贸易本身。
二、辽代通辽地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
通辽地区的辽代遗存众多,有四十多座大型城址[8],二十一座贵族墓[9]。陆续出土的考古文物呈现出草原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这种繁盛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
(一)经济交往频繁
1.玻璃器皿。草原丝绸之路频繁的商贸活动,丰富了通辽地区契丹人的生活。许多带有异域色彩的西方商品进入辽国,为习惯使用陶瓷器皿的东方文明带来新的实用器皿,在通辽地区主要以玻璃器皿为主,包括杯、瓶、盘三种。
玻璃器皿不仅在辽代属于奢侈品,而且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这个时期的玻璃器皿总数量也不过百件。通辽地区辽墓出土八件辽代玻璃器皿,这些玻璃器皿体型大、品种全、工艺精湛。陈国公主墓出土七件辽代玻璃器皿:两只棕色玻璃把杯,与伊朗高原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玻璃把杯拥有相同的独特造型;一只典型伊斯兰刻花高颈玻璃瓶;一只乳丁纹高颈玻璃瓶;两只具有中亚风情的高颈玻璃瓶;一只乳丁纹玻璃盘[10]。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了一只令世人惊叹的蓝色透明高脚玻璃杯。9世纪至10世纪时期,阿拉伯贸易非常发达,玻璃器皿是阿拉伯重要的商品之一。大食帝国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将玻璃器皿带入辽朝,而后作为契丹贵族豪华贵重的随葬品。伊斯兰玻璃器皿通过贸易交往输入辽国的同时,辽代契丹的大批商队也将中国的土特产品和瓷器输出到伊斯兰地区。埃及的福斯塔特出土了辽代的白瓷盘口瓶,伊朗的波斯湾港口席拉夫出土了辽代白瓷碗,伊拉克萨马拉、地中海东岸出土了辽三彩[11]148。
物质的交流是地区之间交往的最初动力,最终实现互惠互利、文明互鉴,契丹再次开拓的草原丝绸之路打开了沿线各民族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大门,来往于草原丝绸之路的大批商人、使节、僧侣、学者,都成为友好交流的使者。
2.外来物产。伴随着频繁的中西交流,大量奇珍异宝在辽境出现。契丹人追求美好生活,可以概括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由此产生的中西贸易交流盛况从通辽地区辽墓大量出土的琥珀饰品中可以窥见一二。
《旧唐书》记载:“大秦……多金银奇宝……有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12]近年来,学者们更倾向于“琥珀产地在波罗的海”说。例如,许晓东在《辽代琥珀来源的探讨》中提出琥珀来源于北欧的波罗的海,探讨了琥珀传入中国的路线。琥珀产自欧洲,辗转西域各国,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来到辽国。《契丹国志》记载:“诸小国贡进物件: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怕里呵、门得丝、碙砂、褐里丝……契丹国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13]这样人数多、品种丰富、数额大的“贡献”和“回赐”实际是官方贸易,琥珀成为其中的重要物产。除固定的大宗官方贸易外,中亚、西亚一带的阿萨兰回鹘、波斯、大食等国历来富有商业传统,各种形式的私人转手贸易将琥珀等物品直接或者间接从西域各国带入辽境。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和陈国公主墓都大量出土琥珀制品,其中陈国公主墓琥珀种类丰富,达2100余件[11]202,包括琥珀珍珠头饰、琥珀珍珠耳坠、琥珀珍珠项链(含704件琥珀)、4组琥珀璎珞(第1组含257颗琥珀珠、5件琥珀浮雕饰件和两件素面琥珀料;第2组含60颗琥珀珠、9件琥珀圆雕、浮雕琥珀饰件;第3组含416颗琥珀珠、5件琥珀饰件;第4组含64颗圆球形琥珀珠、9件琥珀饰件),精美绝伦[11]203。这些琥珀色彩艳丽,以橘红、橙黄、褐红、暗红色为主,被雕刻为鱼、鸿雁、鸳鸯、双鸟、蚕蛹、龙、蝴蝶、莲花等形象,赋予各种吉祥寓意,体现着契丹人的习俗和审美情趣。一只橘红色鸳鸯形琥珀[10]19,正面有浮雕莲花一朵,中央刻鸳鸯一对,交颈卧伏。鸳鸯交颈是中原汉文化民俗,意为夫妻和谐恩爱。这一文化元素由辽国工匠雕刻在由草原丝绸之路而来的琥珀之上,完美阐释了东西方物产和文化艺术的交融。同样,契丹商人也远行到中亚进行贸易活动,阿拉伯诗人优素福·哈斯·哈吉甫(Yusup Xas Hajip)在他的长诗《福乐智慧》(Qutadghu bilik,成书于1069年)中称赞:“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14]和平、交流、繁荣,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主旋律。这种繁盛景象,同辽代积极与草原丝绸之路沿线政权建立密切联系是分不开的,可以说直接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与融合。
3.农作物和水果。草原丝绸之路上密切的东方与西方交往将西域的一些农作物和水果带入辽境,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奉使辽金行程录》中《胡峤陷虏记》一文记载了西瓜如何来到通辽地区及种植西瓜的方法:“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③,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④,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又东行,至袅潭⑤,始有柳,而水草丰美。”[6]9这里的平川即今天通辽的扎鲁特旗。水草丰美的山地草原,因为回纥西瓜的到来,出现了一片片瓜地,成为中国大陆最早引种西瓜的地区之一。时至今日,福巨古城(辽龙化州)⑥所在的莫力庙苏木依旧种植大面积沙地西瓜、葡萄,成为民俗旅游采摘园。
契丹还经由草原丝绸之路从西域引种黄瓜、豆角、大蒜、葱、韭菜等,也栽培了桃、杏、李、梨、栗子等,也能做到将水果制成蜜饯保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对后世影响深远。辽代契丹民族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不断向域外探索,不仅丰富了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密切了沿线国家和民族的友好关系,发展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
(二)文化交流密切
辽代契丹的军事征战与“和亲”等怀柔政策,使草原丝绸之路成为通途,在经济交往频繁的同时,辽朝与西域各国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西域手工艺制作技术、佛教、西域驯兽文化沿草原丝绸之路传入通辽地区。
1.金银器中的西方元素。契丹民族自古就有崇尚金银的习俗,这同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关,金银易于保存和携带,同时也是最好的身份象征。辽朝工匠沿袭唐朝技艺,又受到来自波斯和地中海等地文化的影响,创造了大量具有中西合璧特点的金银器皿。开鲁金宝屯辽墓随葬的金腰带、金耳环、管状器等,装饰有联珠纹、忍冬纹等纹样[15],技法高超,饱满圆润。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人物纹八棱金杯,足底边缘和杯身八面的凸棱上錾刻整齐的连珠纹作为分隔装饰。连珠纹是波斯和中亚地区流行的一种纹样,常常出现在织物、建筑浮雕以及青铜、陶等器物上。丝绸之路开通后,连珠纹传入中国,流行于隋朝,兴盛于唐朝。辽代诸多器物上采用的连珠纹,多数受到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影响;忍冬纹则是希腊民族传统的装饰纹样。同样出土于吐尔基山辽墓的鎏金凤纹银壶,高颈,鼓腹,肩部折出一棱。折棱处向上斜出一指垫,下面连接圆环把手。手持壶时,拇指按在指垫上既舒适又能够保持壶的稳定,设计实用巧妙,是典型的中亚粟特式装饰风格[16]。这种折肩壶的使用贯穿整个辽代,契丹人对它的喜爱可见一斑。
这些金银器制作中的萨珊风格、粟特风格、希腊纹样都出自西方,契丹传统的金银器制作呈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点,反映出辽朝与西方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贸易、文化往来密切的事实。
2.佛教的传播。辽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重要的内容是精神文化交流,佛教的传播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辽太祖在龙化州建开教寺,是佛教在辽朝传播的初始,但是佛教的繁盛离不开回鹘和西夏的推动。《辽史》记载:“甲申,回鹘进梵僧名医”[5]170,“冬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5]303这些来到辽朝的印度、回鹘僧人以及他们带来的经书促进了佛教的传播。终辽一代,上至帝王官僚,下至平民百姓,无论男女,皆以崇佛为尚,因此辽代佛塔和佛像数量众多,辽朝人最初信奉的萨满教日渐式微。
通辽地区辽代遗存中佛教元素屡见不鲜。福巨古城有两座佛塔基址遗存出土刻有“佛”“□□切生死苦□□造一切地狱□□得不忘”等字的残损石块,专家根据形状判断石块所刻应当为殿前庭院中经幢上宣扬救拔幽显、往生净土诸功德的经文。2016年,开鲁县金宝屯发现了辽代贵族耶律蒲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弟苏四世孙)的琉璃砖墓葬。琉璃也称“瑠璃”,折光率高、流光溢彩。人们把琉璃奉为“佛教七宝”之一,认为它有消灾辟邪的功能。琉璃晶莹剔透,暗合佛教不染凡尘的修行要求。辽贵族墓葬用琉璃明志,一心向佛,潜心修行,希望来世达到佛家的最高境界。
此外,一些佛教文化图案在辽代大型墓葬中也被广泛使用。开鲁县金宝屯M2墓室四面墙壁上部绘有红色和黑色的莲花图案。辽代寂善大师佛学造诣高深,石棺之上亦绘有各种“莲花”纹饰。莲花是佛教“八吉祥”之一,与法轮、宝瓶、胜利幢、双鱼、宝伞、白海螺、吉祥结都被赋予深刻的内涵和吉祥寓意[17]。莲花品性圣洁,寓意修行超脱尘世;莲花年年生发,也象征灵魂不死,世世轮回。墓室主人选择莲花图案,希望自己的灵魂回归佛国净土。在辽代中西文化交流繁盛的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显然更自由、更多元化。佛教的兴盛,繁荣了契丹人的精神世界。
3.驯兽文化的流行。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中西交往越来越广泛,异域文化随着物产的交换来到辽境并且为契丹人喜爱,其中就有独特的西域驯兽文化。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一件胡人驯狮浮雕琥珀配饰,将这一异域文化生动再现。长方形的琥珀面上,左侧刻一胡人形象,头戴西域胡人常见的三角形尖顶帽,袒胸露背,腰系长带,身着短裙,双目圆睁注视左手牵着的雄狮。雄狮被刻画成温顺的模样,眉眼低垂。原产自西域的狮子出现在辽境,应当为商贸或者朝贡而来。陈国公主墓中的驯狮琥珀配饰,说明西域的驯兽文化已经被皇室贵族接受并且在上层社会盛行。
狮子在佛教中是文殊菩萨坐骑,勇猛而精进,由此衍生出象征权威和具有镇宅化煞的民俗寓意。契丹人因此将狮子视为祥瑞之兽,狮子也成为重要的装饰纹样。通辽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了一件鎏金双狮纹银盒(妆奁盒,也可以用作食盒),盒子顶部模压一对相互追逐嬉闹的狮子,四周装饰云纹、缠枝花纹、双鸟蝶花纹、花瓣纹等,一派吉祥喜乐的氛围。狮子产于西域,与它相关的驯兽文化从唐朝流行到辽朝,被贵族阶层喜爱,同时,狮子因吉祥寓意而成为中国民俗文化中最受大众欢迎的动物之一。草原丝绸之路加速了中西文化由物质交流到精神交流的进程,东西方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
三、结语
草原丝绸之路在辽代再次兴盛,通辽地区作为契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汇聚点,辽代的通辽也因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而商贾贸易发达、人们文化生活丰富。通辽地区辽文化遗产丰富,直观、形象地再现了当时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将草原丝绸之路的繁华和中西方交流的盛况更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带一路”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借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彰显中华民族在新时代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担当和思考: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文明的交流、社会的进步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我国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历史的传承,而且是在适应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这终将奏响新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流的宏大乐章。“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节点城市意义凸显,它们曾经辉耀于丝绸之路的昨天,也将闪亮于丝绸之路的未来。
[注 释]
①见通辽市科尔沁区档案局存档《民国全宗》,黄仕福《为开放镇基掣签招领请备案给奉天都督的呈文》。
②见通辽市科尔沁区档案局存档《民国全宗》,《卓亲王色旺端鲁布为自留镇基之事致黄仕福的信》。
③平地松林:约自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巴林右旗起,西经克什克腾旗、扎鲁特旗、东乌珠穆沁旗,到达多伦诺尔南北之地,纵深数百里。
④川:《契丹国志》作“州”。
⑤袅潭:贾敬颜《疏证稿》谓,今开鲁县西北之塔拉干泡子。
⑥2018年8月,中国辽金史学会第十四届年会对“福巨古城即辽龙化州”的论断给予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