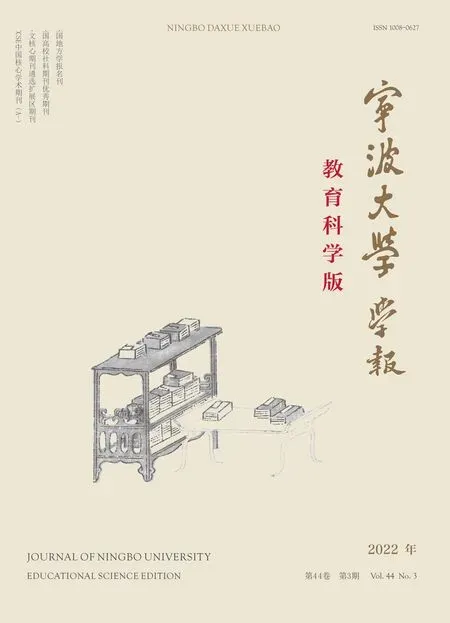“生活·实践”教育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
申国昌,李 楠
“生活·实践”教育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
申国昌,李 楠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生活·实践”教育在继承杜威“教育即生活”、美欧新教育运动以及中国近现代教育理论本土化探索成果精髓的基础上,充分汲取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论精华,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实践育人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对当下落实“双减”政策,推进劳动教育,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培养符合未来社会所需人才以及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具有深刻意义。
生活·实践教育;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实践价值
“生活·实践”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实践为方式的教育,是以生活为内容、实践为路径的教育,是源于生活与实践、通过生活与实践、为了生活与实践的教育。[1]该理念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规律与人才培养规律,既有国际视野又扎根中国大地,既具战略高度又有人文关怀,在全国教育界具有重大影响。
探究“生活·实践”教育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有利于精准把握其育人思路,推动“教育通过生活与实践创造美好人生”落地生花,全面提升素质教育质量与水平,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生活·实践”教育的历史渊源
“生活·实践”教育传承了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优秀基因,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美欧新教育运动以及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对美欧先进教育理论的借鉴与本土化探索。
(一)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论
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是无数教育家孜孜以求的重要课题。如,卢梭的“问题不在于防他死去,而在于教他如何生活”[2],裴斯泰洛齐的“生活具有教育的作用”[3]“所有的教育艺术,必须服务于每个孩子的实际生活”[4],斯宾塞的“为我们的完美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5]等。杜威正是在批判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二者关系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教育即生活”是杜威的基本教育主张,“以生活来诠释教育是他一生坚持的理论取向”[6]。杜威所处的年代, 美国社会自由资本主义衰落、垄断资本主义兴起,社会变革要求对原本脱离社会实际生活、远离儿童年龄特点的传统教育进行改造。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杜威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7]28他充分思考教育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提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7]4“教育在它最广的意义上就是这种生活的社会延续”[8],强调教育要回归生活世界,关注儿童现实生活,从而达到人们所期盼的教育应有之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开放性。从当时来看,它熏染了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等数量巨大的教育家群体。这些教育家们或著文或演讲宣传其教育思想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中国化阐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理论。如,陶行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期间,深受杜威、克伯屈、孟禄等诸多教育大家影响,其中尤以杜威为最。回国后,他投身于教育领域,成为杜威思想的有力宣传者与杜威访华的主要策划者。更为重要的是,陶行知把杜威教育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主张跳出鸟笼子,提出既源于杜威,又不同于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并由此发展出民主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乡村教育思想、教育实验思想、终身教育思想和创造教育思想等,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杜威教育学说对儿童生活的关注促使教育发生了前古未有的变化,其理论本身以及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转型,而且为当下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生活·实践”教育继承了杜威“教育即生活”论对儿童生活的重视与强调,主张教育以生活为中心、为内容、为目的,与生活融为一体。生活是教育的基本要义。
(二)美欧新教育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剧烈变革,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要求教育能够培养个体的合作意识与责任感,让学生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科学的思维方法。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被动、机械学习已不再适应时代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新运动。新学校、新方法是这场教育运动的显著标志,如欧洲教育界公认的第一所新学校——阿博茨霍尔姆学校、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均产生于此。儿童中心,关注儿童兴趣与需要,重视活动与经验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这场运动的精神实质,这些成果精髓为“生活·实践”教育所吸收。“生活·实践”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以儿童为本的教育。从滥觞之时到如今,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是其矢志不渝的追求,始终体现出对人的极大关切,充满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重申的教育的人文主义方法精神内核高度一致。“生活·实践”教育主张教育“源于生活与实践,通过生活与实践”[1]。一方面,它关注学生真实的学习与生活情境,让儿童所见、所闻、所感皆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养成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习惯。另一方面,“生活·实践”教育强调学生的主动探索与活动经验,主张让孩子在参与中、体验中、互动中学习知识,增长本领,充分保证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三)中国近现代教育理论本土化探索
近现代以来一大批仁人志士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了丰富见解,其既是受到国际教育思潮与运动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内生需要。他们吸收世界先进教育文化,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本土化的教育理论,如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晏阳初“四大教育”“三大方式”、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等。这些理论闪烁着中国近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心系国家命运、思索民族未来的勇敢担当与强烈社会责任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统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一笔永恒财富,成为当下教育理论的营养之源。“生活·实践”教育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吸收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宝贵经验,在前辈教育家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行的。
其一,“舶来品”是中国教育学的最初形态,从效仿日本到师从欧美再到中国化、本土化,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探求适合中国的教育之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们将西方先进教育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根植于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最终产生了蔡元培改革北大、陶行知晓庄师范学校、陈鹤琴南京鼓楼幼稚园等一批成功案例。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本土化探索表明,只有正确处理中西矛盾,立足中国实际,博采众长,探索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教育制度与理念,才能产生民族的、世界的教育。基于此,生活·实践教育十分强调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同时秉持开阔胸襟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其二,惟创新者进,中国近现代史上先进教育家群体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功绩启示我们,教育理论创新是时代提出的根本要求,也是教育繁荣发展的必然途径。“生活·实践”教育正是周洪宇教授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在深刻把握时代脉搏和审视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基础上首创的教育理念,其崭新的视角与逻辑为当下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遵循。其三,老一辈教育家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奉献精神为当下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提供巨大鼓舞,激励着教育工作者们肩负起时代使命,大胆探索教育模式与教育方法,为提高教育质量与水平、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二、“生活·实践”教育的理论基础
“生活·实践”教育聚焦生活与教育、实践与教育的关系。其“生活”来源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实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并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践育人的重要论述。理论基础兼具历史性、哲学性与时代性。
(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转化
“生活·实践”教育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作为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汉森在其《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家,陶行知是唯一被列入的中国教育家,与杜威、蒙台梭利等人并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灾难深重,危机四伏,旧教育旧学校完全脱离社会实际与人民需要,亟需变革。陶行知在深刻把握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立足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基本国情和晓庄试验乡村示范学校的探索成果,对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理念进行改造与创新,提出生活教育理论的三大原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陶行知认为,“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9]634在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体系中,“生活”的涵义极为广泛,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9]180,而“教育”也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学校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这样,“生活即教育”即意味着“社会是一座无形的大学校”[10],教育是以广阔的社会为学习对象。
除此之外,陶行知特别强调“做”在“教”与“学”中的中心地位,“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不然“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为学”[11],这是陶行知提出的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生活教育之路。一方面,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具有深刻性、前瞻性以及战略性,另一方面,当下中国教育仍然面临着陶行知时代生活与教育、学校与社会、教学与实践的脱节。这使得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成为“生活·实践”教育最核心的理论来源。“生活·实践”教育充分汲取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精髓与营养,综合考虑时代变迁、社会需要以及教育变革,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生活教育三大原理创新性地发展为“生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存即共进、世界即课堂、实践即教学、创造即未来”六大原理,将陶行知的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三力”发展为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新力“六力”,将生活教育六大特质“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历史的”发展为“生活的、实践的、人民的、民族的、科学的、开放的”,将陶行知“创造出真善美的活人”发展为“培养真善美的时代新人”,是当代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再生性创造。[12]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指导
马克思的实践论是生活·实践教育的另一重要理论基础。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3]56“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61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根本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对实践有巨大的反作用。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科学真理也必须在实践中探寻,反之,教育理论也可以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旗帜鲜明地强调实践是“生活·实践”教育的题中之义与显著底色。
首先,“生活·实践”教育根植于实践。“生活·实践”教育理论本身是基于近二十年的基层改革实践逐步形成的。世纪之初,周洪宇敏锐地洞察到教育领域存在的“灰色教育症”,构建起“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面向学生发展的整个过程”[14]的“阳光教育”理论体系作为解决之策。与此同时在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率先开展“阳光教育”实验,这是“生活·实践”教育的最初形态。此后“阳光教育”发展演化为主张“全体、全面、全程、全盘、全球”的“新全人教育”、[15]再到强调以人为本、个性发展、师生平等、求同存异、开放创新的“新人文教育”,最终积累与沉淀为“生活·实践”教育。
其次,“生活·实践”教育以实践为对象和路径。“生活·实践”教育研究全人类的教育实践,实证、实验、实践是其主要研究方法与具体实施路径。[16]最后,“生活·实践”教育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它既在指导当下教育变革、推动教育发展中实现自己的使命,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生活·实践”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理论不断适应具体实践的形势与变化,实践过程中坚决破除妨碍发展的理论观念,实现一次又一次理论与实践统一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践育人重要论述的引领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17]实践在帮助学生增长知识、练就本领、锤炼意志、修炼情操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践育人问题做出了系统、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理念和新观点,既阐明了实践育人的重要作用,又为实践育人的落实路径指明方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时代意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践在促进青年成长成才方面的重要性,“实践是提高本领的途径”[18]“广大青年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炼、增长本领”[19]“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才,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20]。他谈到,“社会实践、社会活动以及校内各类学生社团活动是学生的第二课堂”[20],鼓励广大青年参加学生支教、志愿活动、从军报国等各类社会实践,求索真知,奋勇争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依靠勤劳和汗水开辟人生和事业前程”[19],把个人实践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联系起来,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当中,让实干成为人生的鲜亮底色。习近平总书记的实践育人理念对于推动当下育人模式转型,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生活·实践”教育充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践育人的重要论述,主张“实践即教学”, 让实践与教学相互促进,发挥实践在学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生活·实践”教育的实践价值
(一)推进“双减”政策落实的新路径
首先,在“生活·实践”教育中,“生活是教育的内容,实践是教育的方式”,[21]413教育“源自生活、融于生活、创造生活”[21]412,因而一切与生活实践情境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成为儿童的作业,从而以主动地、实践地增长学识、探求真理的过程代替传统的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回应了“双减”政策强调作业布置要尊重教育规律,鼓励分层化、弹性化与个性化作业的要求,有利于真正缓解学生作业过重、过难、过偏负担。其次,有减必有增,减的是“负”,增的是学校教育质量。“生活·实践”教育认为,学校担负校内教育中心、家教辅导中心、特长培训中心、托管中心和社会实践中心六重角色。[16]多重角色的统一有助于构建高质量的课程体系,整合各类学习资源,营造好学求知的校园氛围,从而更好发挥学校育人主导作用,达到学生在校内“吃饱”“吃好”的效果。最后,课后服务是“双减”政策的重要一环,在“生活·实践”教育中,生活与实践蕴含的丰富学习资源有助于缓解地区差异带来的资源不均,避免课后服务空洞、单一,保证课后服务质量,从而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促进学生差异化、个性化发展。
(二)中小学实施劳动教育的新抓手
马克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个体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中的重大意义,多次在重要讲话、政策文件中重申、强调劳动教育,表明了党中央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培养体系的坚强意志与坚定决心。尤其是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基本方略与实施路径予以明确,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提供了具体遵循。《意见》强调,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多方面多渠道保证劳动教育切实落地,补齐劳动教育短板,同时发挥家庭基础作用、学校主导作用和社会支持作用,根据学生年龄特点与实际情况,广泛开展各类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在劳动中知行合一,全面发展。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劳动教育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生活·实践”教育强调生命、生活与实践,为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与有力抓手。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22],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劳动教育能够助力学生成‘人’,帮助他们确证、体验作为‘人’的意义与价值。”[23]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劳动教育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更易于激发学生劳动兴趣,体验劳动乐趣。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学生切实参与实际劳动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有助于在劳动实践中厚植劳动光荣、热爱劳动情怀。“生活·实践”教育通过关注生命、生活与实践实现“以劳育人”,旨在让学生会劳动,想劳动,爱劳动,不仅具备必需的劳动能力、拥有正确的劳动观念,树立热爱劳动的精神,而且勇于担当历史重任,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作用。
(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策略
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西周官学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就已折射出文理兼备、智能兼求的人才培养思路,而如今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附着在人力资源之上的智力资源取代物质资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国之栋梁成为当下教育的必然使命。“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24],建立人才优势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应试教育”“考试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基础教育被纳入升学教育的狭窄轨道,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死读书,读死书”的传统状态,不利于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更无益于个体能力、个性以及社会关系等综合全面发展,育人模式亟需转型,“生活·实践”教育回应了这一诉求。一方面,“生活·实践”教育关注所有学生,关注学生发展的每个方面。它主张融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培养具有世界观、中国心、现代化的时代新人,具体包括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思维、健康的身心、艺术的爱好、手脑并用的能力、合作的意识、负责的精神,让个体更加适应现实生活,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生活·实践”教育关注每个学生,关注学生个性差异。个体之间生活背景、个性差异的千差万别决定了千篇一律的教育难以让每个学生闪耀光彩,“生活·实践”教育将每个学生视为独特的生命个体,力求给予适宜个体发展的独特“养料”,从而促进每个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和持续性进步。
(四)培养未来社会所需人才的新举措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白皮书指出,“在贫富分化加剧、传统就业机会逐步消失的背景下,中小学教育在培养世界公民和未来社会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模式应该帮助儿童具备能力,使其能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谐、高效的世界。”[25]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教育先行”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从教育后行到教育并行,再到教育先行,这不仅是教育培养人才的长期性带来的理念的变化,更是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即教育应着眼于为未来社会,积极革新,谋求远虑,培养未来社会所需人才,引领社会变革与进步。澳大利亚原未来委员会主席埃利亚德曾指出,未来并不具有明确的道路与目的地,通向未来的道路需要我们去创造,与此同时,创造者们也在创造着自己。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面向预设的确定性的未来,还要注重培养学生一种创造未来的素质,培养出新人去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未来,并去应对这种未来,最终创造美好未来。“生活·实践”教育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单一对高分的追求,它所主张的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六力”,能让学生拥有更强烈的好奇心、更丰富的想象力、更理性的批判性思维,从而迅速适应未来社会的各种变化、应对纷繁复杂的挑战、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将有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五)中国特色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的新声音
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繁荣中国教育理论的内在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具有开创精神的教育家担当起引领教育改革的重任,他们在探索中国特色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形成了诸如“主体教育”“情境教育”“生命·实践教育”“新教育”等一系列把握时代脉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育理论,为丰富中国特色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从阳光教育的提出到新全人教育的构想,再到新人文教育的产生,最终到“生活·实践”教育,它们无一不是适应时代变革,扎根中国大地,对当下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的新解答与新回应。尤其是2017年周洪宇立足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需要,深刻把握教育变革规律,将阳光教育、新全人教育、新人文教育汇聚成更有时代精神的“生活·实践”教育,内涵丰富,现实性强,是中国特色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的新声音。与此同时,它绘制的一幅幅以生活和实践为核心的教育生态蓝图在中国大地迅速铺开,又成为中国特色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的源泉与动力。
[1] 周洪宇. “生活·实践”教育:创新性发展“生活教育学”[N]. 中国教师报, 2021-12-01(06).
[2] 卢梭. 卢梭全集 第6卷 爱弥儿 上 论教育[M]. 李沤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0.
[3] 裴斯泰洛齐. 天鹅之歌[M]//张焕庭.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208.
[4] 阿图尔·布律迈尔. 裴斯泰洛齐选集 第2卷[M]. 戴行福等,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364.
[5] 赫·斯宾塞. 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 胡毅,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58.
[6] 唐斌, 朱永新. 杜威“教育即生活”本真意义及当代启示[J]. 中国教育学刊, 2011(10): 84-87.
[7] 杜威. 杜威教育论著选[M]. 赵祥麟, 王承绪, 编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8]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7.
[9]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 第2卷[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10]顾红亮. 杜威“教育即生活”观念的中国化诠释[J]. 教育研究, 2019, 40(4): 22-27.
[11]董宝良.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217.
[12]周洪宇. 继承与发展:从生活教育到“生活·实践”教育[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1, 43(03): 2-9.
[13]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4]周洪宇. 教育的信念与追求[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8: 6.
[15]周洪宇. 让教育充满阳光[N]. 光明日报, 2013-02-06(14).
[16]刘来兵, 赵美君, 鲍成中. “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下的学校变革——访天有集团副总裁、总校长鲍成中[J]. 生活教育, 2020(8): 5-9.
[17]向宗鲁. 说苑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58.
[18]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102-103.
[19]习近平. 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4-30(02).
[20]张烁.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垒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01).
[21]申国昌. 新理念、新领域与新范式: 周洪宇与教育文化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22]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6.
[23]赵蒙成.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本体价值与实践进路[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2): 38-47.
[24]白居易. 十四辨兴亡之由[M]//丁如明, 聂世美. 白居易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854.
[25]未来学校: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J]. 教育智库, 2020(4): 4.
Historical Origi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Life-Practice” Education
SHEN Guo-chang, LI Nan
( 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Life-practice” education fully absorbs the essence of John Dewey’s “education in life”, the new educational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 localize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odern educators, as well as Tao Xingzhi’s theory on life education and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 This research, combined with CPC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practical education, examined its profound historical origin and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eveal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o advance labor educ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cultivate talent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future society, and construct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of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fe-practice” edu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valu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BOA200050)
申国昌(1967-),男,山西山阴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教育史、教育政策。E-mail:hzsdsgc@163.com
G40-052.2
A
1008-0627(2022)03-0016-07
(责任编辑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