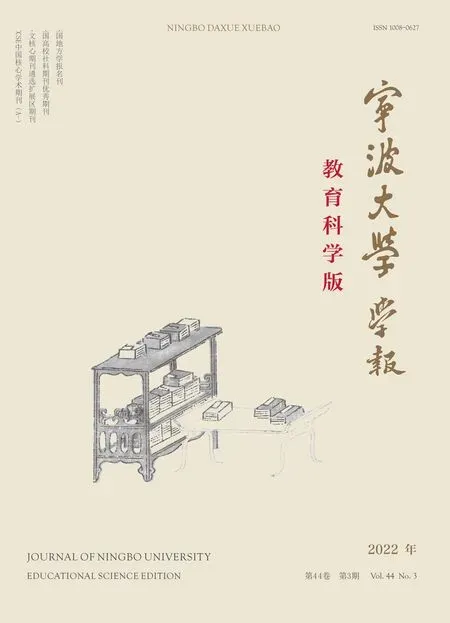杨贤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贡献及启示
向 勇
杨贤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贡献及启示
向 勇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300)
杨贤江(1895-1931)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大众化。杨贤江与各种教育思潮展开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持《学生杂志》等刊物,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推动广大青年追求进步,投身革命;撰写《教育学ABC》和《新教育学大纲》等教育学著作,积极向青年宣传唯物史观;译介苏俄教育学著作,为先进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提供了途径。通过研究杨贤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贡献,从中得出若干启示,以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青年
近代中国处于急剧动荡时期,国人对国内形势普遍不满,纷纷提出各种教育救国方案。西方教育思潮的大量涌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传入中国,给苦苦寻求出路的中国教育界指明了方向。杨贤江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帮助进步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大众化,回应了时代的需要。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杨贤江的教育思想,对于其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方面缺乏关注,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对杨贤江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贡献进行梳理,并从中总结经验,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提供借鉴。
一、杨贤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主要贡献
(一)与各种教育思潮进行论战,扩大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力
杨贤江所处的20世纪20、30年代,各种教育思潮交织激荡,它们虽都以救国救民为号召,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杨贤江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与各种教育思潮展开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争取了更多的人参加革命斗争。
1. 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
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是由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张尚龄、周太玄、曾琦等人于1918年发起组织的团体组织。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李达、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等都曾是其会员。1919年10月,杨贤江加入少中。同年11月1日,少中南京分会成立,其被推选为分会书记;1920年,杨贤江被选为少中第二届评议部评议员,负责监督会务进行、选举职员、审查会员资格。[1]262少中成立初期抱着谋求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革的初衷,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对于少中是否应该采取一种主义作为学会指导思想时,成员之间开始产生分歧。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以《醒狮周报》为中心组成国家主义派,他们积极宣扬国家主义,敌视马克思主义,诋毁苏联和社会主义。《醒狮周报》出版后,“不到一年,不但畅销至二万份以上,而且南北各大都市的青年大学生纷纷响应”。[2]
在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中,杨贤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家主义派的教育思想进行驳斥。他指出,国家主义派持超阶级的国家观,认为教育要以国家为中心,但在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背景下,国家主义派却反对民众革命,其主张没有触及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为封建军阀张目;由于国家主义派的主张抽掉了反帝、反封建内容,因此,不但不能救国,实足以亡国。中国要有出路,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国家是阶级的,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就必须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3]通过论战,杨贤江批驳了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廓清了事实,阐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把不少被国家主义派迷惑的爱国青年争取过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
2. 批判“三论”“四说”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界思想比较活跃,提出了各种教育主张,其中“三论”(“教育万能”“教育救国”“先教育后革命”),“四说”(“教育清高”“教育中正”“教育神圣”“教育独立”)最为广泛传播。针对这些观点,杨贤江在《教育杂志》《中国青年》《学生杂志》等刊物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予以分析与批判,通过科学阐释教育的本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教育界的影响。
“三论”中“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是人的身心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改造社会的最重要手段,是一种片面地夸大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的教育观点。“教育救国论”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教育的不普及,主张通过创办学校、普及职业教育等方式来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教育救国论”对教育在救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不恰当的夸大,实质上是“教育万能论”的衍变。而“先教育后革命”论认为中国人大部分是不懂革命的“阿斗”,只有先抓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然后再进行革命。[4]98对于“三论”,杨贤江认为,教育在阶级社会中作为革命的一种补充手段为争取劳动者境况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尖锐对立的时代背景下,主张用教育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无疑是超越了当时的时代与环境,因此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教育有非凡的本领,有超越一切而独立特行的存在,不是梦呓,也准是夸大狂”。[5]323“四说”认为教育是超凡脱俗的事业,不应为政治所左右,被金钱所迷惑,而应保持其独立性,这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对此,杨贤江认为,“四说”所持观点有其合理的成分,应该予以肯定,但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受到经济与政治的制约,并不会超越时代与环境而独立存在,仅靠教育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救亡图存的目的。因此,“四说”是世人的迷信,都是掩蔽教育的本来面目,而具欺蒙麻醉作用的。[6]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作为阶级支配的工具,它只会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现“四说”的 “神圣”,我将换言以“凡俗”;其“清高”,我将换言以 “平庸”;其“中正”我将视以 “阶级的”;其“独立”我将视以“隶属的”。[5]221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还出现了一些贬低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观点。1929年,舒新城在《教育杂志》发表《致青年教育家》一文,在文中,他认为,“教育并不是清高的,教育界的钻营奔竞,倾轧排挤的种种污浊行为、卑贱勾当,并不亚于其他各界”。舒还提出“天才改途论”,认为“教师只是庸人的佣工之一种,你们自审是庸人,愿过虚伪的平常生活,从事教育也无妨;若自问是天才,想改造社会国家,建立不世之勋,我劝你们早早改途,努力从应走的路上走去,不要再在这中庸之道的十字街上徘徊踯躅”。[1]231-232舒文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对于舒新城的观点,杨贤江表示反对。1929年7月20日,杨贤江在《教育杂志》发表《读舒新城君的〈致青年教育家〉》 一文。在文中,他指出,“舒君未尝说出的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迁,因而他虽然揭破了教育的‘黑暗方面’,却不能指出一条教育者‘应该的路’。不特未指出而已,好像还留下了些不太好的印象与不大负责任的言论。”[5]156“天才改途论”的主张是错误的,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忘记了教育毕竟还是“改造国家社会”的“工具”。杨贤江认为,这样蔑视教育,轻视教育,听任教育终于留在“婢妾下厮”的地位而认为“也无妨”的主张,除使教育事业益发糟糕,益发乌烟瘴气而外,似乎不会再有别种好处。[1]233
杨贤江认为,对于教育在救亡图存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中国教育界为什么会出现看法迥异的情况,究其根本,都是与对教育的本质认识不清有关。杨贤江认为,“教育的本质,不过是帮助人营生活的一种手段。”[5]156-157教育作为起源于人类生活实际需要的,到了阶级社会以后,教育也就带上了阶级的色彩,成为剥削阶级支配无产阶级的工具,而与劳动人民脱离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只有起来进行革命,从剥削阶级手中夺取政权,才可能使教育恢复本来的面目。如果不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就算“三论”“四说”所主张的“教育救国”成功了,也还只是一个“强凌弱、富劫贫”的世界。因此,要变革中国社会,就必须投身于革命。杨贤江的教育观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研究教育问题、开展教育工作的,同时又主张通过教育来促进社会变革,这样就恰当地摆正了教育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7]192-193
3. 批判国故派
1923年,上海澄衷中学在举行策问式国文会考时,其考题内容主要来自《四书五经》等古代典籍,校长曹慕管还将考题在报纸上予以发布,企图将教育拉回到封建复古的轨道上。对此,杨贤江认为,这不仅是澄衷中学一所中学的问题,而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复古逆流有关。而教育界的复古是最可怕的一种不好现象,“其影响足以麻痹青年学生的神经,使他们感觉不灵,竟会对于有灭国亡种的祸患熟视而无睹”。[1]102-103为了肃清这股复古逆流对于教育界的影响,杨贤江在1924年2月的《学生杂志》上,以《国故毒》为题发表了一篇短评,发动对国故派的批判。3月25日,在《时事新报》上他又发表《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的信——讨论国故》一文。5月5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今年的五四和第三期复古运动》,继续批判国故派。针对青年学生的一些疑问,杨贤江还专门撰写《研究国学问题》《中学生读书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去救国》等文章予以回复。杨贤江在批判国故派的过程中,利用与青年通讯联系的机会,向他们推荐《新青年》《中国青年》《前锋》《新建设》《向导》等革命刊物,在其主持《学生杂志》上积极指导广大青年学习社会科学,介绍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宣传党的纲领与路线方针。
1924年由杨贤江发动的这场反对国故派复辟活动的斗争,围绕着中学生要不要读古文,应不应保存国故的问题展开。论战中,陈望道、肖楚女、恽代英、沈雁冰等共产党员也撰文支持杨贤江,一起共同纠正了人们浑浊的头脑,是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影响遍及全国,有助于广大青年冲破封建旧势力的阻拦,推动了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契机。
(二)改造《学生杂志》,向青年宣传革命道理
“五四运动”之后,原来追求进步的青年却普遍出现了烦闷、萎靡的精神状态。为了唤醒青年一代的使命意识和革命精神,摆脱萎靡状态,从1921年到1927年,杨贤江利用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刊物《学生杂志》的机会,向青年宣传革命道理,教育青年追求进步。他采取在《学生杂志》发表社论、短评、通讯、答问等方式,研究青年问题,指导青年运动。1927年,杨贤江离开《学生杂志》时,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达到230多篇,通讯达100多例,答问青年学生问题1650多条。[1]71在他的努力下,一份“极不堪的、守旧的、市侩记的、脑袋混沌”的《学生杂志》被改造成为一个对青年进行指导与推动青年运动的阵地。[7]182
通过在《学生杂志》撰文,杨贤江号召青年根据时代需要,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职责。“可敬可爱的青年学生!我希望你不要闭着眼瞎读书呀!现在是什么时代,中国是什么国家,你该看看明白、做青年该要做个活的进步的青年不要做个死的陈腐的青年。”“你可以醒了!你应该醒了!你若还有热血,你若还有余力,我劝你就用这血和为去杀敌!青年!别再做梦,快起来吧!”[1]91对于只顾埋头升学,不闻窗外事的学生,杨贤江进行劝导:“你们如果升入大学,各选习专门课程,务请你们兼顾社会环境,千万不要变成书痴,不要把大学生当作一种特殊的高贵阶级,而把劳苦民众的利益、失学青年的痛苦完全忽视不顾。你们要知道一面是学生,一面还是个国民;一面须有专门研究,一面还该留意和人类生活最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及一般社会生活。若求学而不重视社会的根据,不想促进社会的进化,单以个人的荣耀与福利为目的,便是时代落后的遗少,而非现代中国的青年。”[1]93
为了改造社会,杨贤江积极鼓励学生与教育工作者参与政治,参加革命。1923年5月,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学生与政治》一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主张学生应该与闻政治的。”[1]90-91两个月后,他又连续发表《再论学生与政治》《中国的学生运动与青年运动》《做今日底青年该怎样》《中国青年之敌》《青年求学问题》《怎样叫做觉悟的青年》等文章,进一步号召青年学生参与政治。此外,他还在《学生杂志》写了“关于学生干政问题”“关于学生救国问题”“学生政治运动问题”等大量通讯和答问,号召青年学生参与政治。1923年暑假,杨贤江应邀在上海景贤女中作了《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报告,集中阐明了他的观点,他说:“自五四运动以来,学生界的一个深刻的教训,知道非加入政治运动不可。因为军阀的坏已到了极点,所以公开地加入政治运动而推翻军阀统治是很对的。”“政治不弄好,教育事业也不会办好的,因为这是先决的问题。”[1]87同时他还撰文批评那些趋炎附势、不问政治,脑筋里则充满着功名利禄的学生。指出“他们只是埋首读书,只望文凭到手,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私行为。”杨贤江还号召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政治,努力铸造革命人才。“不管教育最好的目的怎样,但就目前讲,只有革命的教育,才是中国需要的教育;只有革命的教育者,才是中国需要的教育者。做教育者的人不但应该指导学生去革命,还应当指导群众去革命”。[1]94
在主持《学生杂志》期间,杨贤江意识到,对于青年人的指导,不能只限于讲革命的道理,还必须全面关心青年的生活。1925年,杨贤江在《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全人生指导”的思想,为解决当时的青年问题提供理论指南。“全人生指导”涵义较为广泛,既指德、智、体、知、情、意的全面教育,也指对青年求学、择业、交友、恋爱、家庭以及为人处世、兴趣爱好的全面关心与指导。[8]3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借鉴了国内外教育思想的精华,主张从社会环境和青年的身心发展特征来解决青年问题,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与大众化。
《学生杂志》在当时中国发行数量较大,流传范围较广,对广大青年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杨贤江通过主持《学生杂志》,教育了大批青年,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重要的贡献。《学生杂志》被广大青年看成是“生活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杨贤江被称赞为“青年一代最好的指导者”。[1]71叶圣陶回忆,在1923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以前,紧密联系青年的刊物,就只有《学生杂志》。李一氓回忆,当时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大多受《学生杂志》的影响,受杨贤江的影响。[7]13《学生杂志》对邹韬奋也产生了影响,邹曾说过,他很喜欢杨贤江的文章,他在《生活杂志》中设通讯栏,就是仿效了杨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夏衍看了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的文章目录后说,有些文章对现在还是有用的。[7]222
(三)撰写教育著作,面向进步知识分子宣传唯物史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贤江流亡日本,为了廓清民众的认识,建构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杨贤江撰写了《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两本著作。《教育史ABC》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教育史,并根据社会发展形态理论来叙述教育发展史的著作,而《新教育大纲》是中国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阐述教育学原理的专著。
1929年5月,《教育史ABC》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教育史ABC》主要“供给一般人以教育史的常识和供给初学者以正确的研究教育史的门径”,使中学生、大学生得到一部系统的、优良的教科书或参考书,改变了以往教育史著作艰深难读的弊病。[5]54《教育史ABC》性质、内容乃至体裁都与一般教育史教科书者相异,“作者视教育事业自有其根据的历史背景(经济关系及政治关系),本书于说明教育事业之变迁发达,常要述及当时代的社会环境者即为此故。”[5]54并且打破以往教育史将朝代更迭作为分期的标准,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对教育史进行分期。该书贯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的分析方法,揭露和批判了剥削阶级教育的弊端及其阶级本质。[9]1930年2月,《新教育大纲》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杨贤江以有志于教育事业的青年为阅读目标,希望能够借此书来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在书中,杨贤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述了教育的起源和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批判“三论”“四说”等教育思潮;揭露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为少数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本质,明确教师、学生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只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教育才有出路。
许多知识分子正是通过阅读《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涤除了自己过去对教育问题的种种错误认识,开始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7]108《新教育大纲》被苏区师范学校采用为教本,武装了大批的苏区教师,对苏区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郭化若等回忆,延安图书馆藏书《新教育大纲》对他帮助最大。[7]112《新教育大纲》对国统区的青年也产生了影响。据潘懋元回忆,是《新教育大纲》让他第一次懂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懂得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教育的实质,懂得教育和革命的关系,认清了形形色色教育理论的错误所在。[7]108-109
(四)翻译苏俄教育著作,介绍苏俄教育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苏联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积极成就。杨贤江认为,苏俄教育的依据正是马克思主义原则,“苏联的一切教育理论的根据,乃是马克思、恩格斯、达尔文和第特兹根的教训,以及列宁的演绎和发展一由经验及行动中实证过来的伟大贡献”。[5]229杨贤江除了翻译《新兴俄国教育》等著作之外,还大量译介有关苏俄教育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
二、启示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根本动力
杨贤江所处的时代,既是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是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斗争的年代。杨贤江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他的理想信念:“改造旧社会,建设一个人民群众能自由幸福地生活的新社会成为其终生奋斗的目标”“什么叫 ‘救国’?就是为了保护在这块国土内人民的福利。”[7]192当革命处于高潮时,他通过与“国家主义派”论战、批判“三论”“四说”、批判国故派以及改造《学生杂志》,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广大青年走向革命道路;当革命进入低潮时,他继续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撰写《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翻译苏俄教育著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向杨贤江学习,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夯实理想信念,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
(二)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客观要求
要做好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大众化工作,需要扎实的教育学理论基础。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除学业需要阅读的书籍之外,杨贤江还认真阅读了许多有关教育学、哲学、历史、体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著作。即使在编辑任务和革命活动十分紧张的1923年,他还抽出时间到复旦大学新开设的心理系当了两年特别生。[7]193杨贤江的研究视野非常广阔,他译介的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包括俄、美、英、日、法、德、瑞典、意大利、朝鲜等国,篇目(包括译著)达到131种以上,字数达到100万以上。[4]97杨贤江对于苏俄教育著作的译介,增进了中国教育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了解,让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正是由于杨贤江学识渊博、见识宽广,他才能将时代的需要和青年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并吸收借鉴古德国康德的“完人教育思想”和日本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思想的有益成分,创造性提出了“全人生指导”思想。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不但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了,也把国外的其他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化了,从而形成一个既扎根于中国大地又吸取了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的思想体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向杨贤江学习,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从关心青年生活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基本前提
杨贤江在教育工作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解决青年的切身利益。“我们不能像空想的革命论者,突然狂喊现代教育的破产,却提不出实际意见和实际方法”。[8]3例如杨贤江在主持《学生杂志》时,除了刊载宣传革命道理的文章外,对于青年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学业、恋爱、婚姻、家庭、就业、体育锻炼、生理现象方面,都占了相当的篇幅。青年学生苦恼的生活小事,如妻子不育、强迫结婚、讲话口吃、手淫遗精等,杨贤江都在刊物上予以一一解答。据统计,他任职《学生杂志》期间,与全国大中小学生通信、答问达3000多次。[1]71杨贤江通过摒弃“第一不从学生本身着想,第二不从社会环境着想”的旧式教育方法,深入广大青年的日常生活,使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获得了源头活水。[7]5-6另外,杨贤江的文章说理透彻,文风活泼,就像与友人促膝谈心,无空洞说教而富真情实感,不是以势压人,而是把自己摆进去,就事论理,以理服人,为广大青年所喜爱。[7]140-141因此,我们要向杨贤江学习,努力聆听人民心声,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
三、结语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杨贤江是重要的开拓者和先行者。夏衍说,杨贤江是最早从共产党的角度研究教育问题的。[7]222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当时教育理论思想非常混乱时刻,毅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科学阐明教育起源、教育本质、教育经济论和教育目的论,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教育观,写出《教育ABC》《新教育大纲》等不朽的教育学著作。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全人生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广大青年的实际相结合,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大众化。在杨贤江等的不懈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教育领域得到迅速的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念,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新的教育模式开始奠定。通过梳理杨贤江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主要贡献,可以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1] 金立人, 贺世友. 杨贤江传记[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2] 李义彬. 中国青年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113.
[3] 吴洪成. 不朽的革命人生, 辉煌的教育成就——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23.
[4] 潘懋元, 宋恩荣, 喻立森.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5] 任钟印. 杨贤江全集第三卷[M].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5.
[6] 杜学元, 吴吉慧, 范琐哲, 等. 杨贤江年谱长编[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396.
[7] 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 杨贤江纪念集[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8] 钱忠源. 杨贤江论“全人生指导”文选[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9] 孙培青, 郑登云. 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299-301.
Yang Xianjiang’s Contribution and Enlightenment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Early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
XIANG Yong
(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300, China )
Yang Xianjiang (1895-1931), an early Marxist educato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founder of proletarian education in China, combin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Early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he staged heated debates to argue for the publicity of Marxism; as chief editor of journals like, he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educ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lling on the youths to join the revolution; in his pedagogical works such as, he actively publiciz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e youth; as translator of the pedagogical works of the pre-Soviet Union, he was devoted to introduction of a way for the advanced Chinese to understand Marxist pedagogy. The study of Yang Xianjiang’s popularization of early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s contribute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Yang Xianjiang;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 youth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运用浙东红色文化资源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研究”(2021SCG088)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研项目课题“运用浙东红色文化资源提升高校思政课育人效果研究”(xyjy2020030)
向勇(1975-),男,湖南沅陵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史。E-mail:1416380114@qq.com
G40-09
A
1008-0627(2022)03-0100-07
(责任编辑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