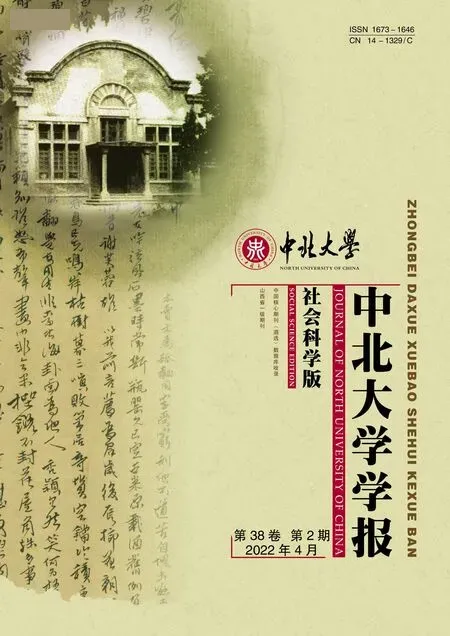从文学地理空间角度看陶渊明诗文中的田园路
方立娟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陶渊明作品中存有大量与地理相关的意象, 这些意象大多不是单独存在于文本中, 亦可形成值得探寻的文学地理空间, 比如田园、 山林等, 关于这点, 本人在《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书写》一文已有相关阐述。(1)拙文《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书写》于2021年发表在《地域文化研究》第2期。 《从文学地理空间角度看陶渊明诗文中的田园路》一文在2020年历经数次投稿, 后在2020年12月30号投稿至《中北大学学报》, 特在另一篇文《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书写》发表后补上相关信息。陶渊明在论及田园生活时, 有时还会延伸到通往田园之路, 如“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1]“扬楫越平湖, 泛随清壑回”[1]等, 这些路既可看作田园的延伸, 也可分别看作独立单元。 若以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 这些路还可看成重要的文学地理空间。 关于文学地理空间的概念, 有不少学者述及, 如曾大兴认为:“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是指存在于文本中的以地理物象、 地理意象、 地理景观 (地景) 为基础的空间形态, 如山地空间、 平原空间、 海洋空间、 草原空间、 乡村空间、 都市空间等等, 这种空间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艺术空间, 是作家艺术创造的产物, 但也不是凭空虚构, 而是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间有重要的关系。”[2]杜华平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的论文《论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与深进》中指出:“文学地理空间的深进, 就是指写出‘地方灵魂’, 其实质是作家与地理空间的深度契合。”[3]10田园路作为陶渊明作品中的一个地理空间, 融入了陶渊明的情感, 具有一定的探究价值。
1 陶渊明诗文中的田园路特点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 与其现实接触的田园有着重要联系。 《宋书》记载:“亲老家贫, 起为州祭酒, 不堪吏职, 少日, 自解归。 州召主簿, 不就。 躬耕自资, 遂抱羸疾, 复为镇军、 建威参军……”[4]2511陶渊明与田园有着真正的密切接触, 他笔下的田园, 也有着不一般的现实意义。 首先, 在历史上, 陶渊明家本来就有田庄, 钱志熙认为:“渊明的田庄, 似乎不止园田居、 南村两处, 还有西田、 下潠田两处。”[5]85陶渊明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和《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分别指出了他在西田和下潠田的劳作与收获。 其次, 陶渊明在自己一些作品中展示了不同时期田园的一些景象, 如在《归园田居》中, 诗人以“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1]展示了他初归田园时的景象; 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 他以“果菜始复生, 惊鸟尚未还”(2)“果菜始复生”句“菜”字下, 宋本注:“一作药。”[1]展示了遭遇火灾后田园的一些状况; 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以“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3)“炎火屡焚如”句“如”字下,宋本注:“一作和。”[1]描绘他在气候反常时遭遇的田园困境。 陶渊明笔下之田园具有现实意义, 是陶渊明归田生活的部分记录。
关于陶渊明笔下的田园, 目前, 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 蔡瑜在《陶渊明的人境诗学》中对陶渊明笔下的“园田” “田园”进行了论述。 她说:“‘田园’指涉一片静态的产业, 往往是大范围的田地园圃, 有时甚至即是‘苑囿’ ‘园舍’ ‘田庄’。 田、 园本各有其意, 树谷曰田, 树果曰园, ‘园’的意义在‘田园’连词中或是指大范围具有经济效益的果园而与田庄并列, 或是只作为一种休憩区域的意涵。 然而, 陶渊明采用‘园田’连词时, 则园、 田两者并重, 同时有从园到田、 由近而远的推展, 形成很具体的生活化空间”[6]68。 陶渊明家的田园, 大概有远有近, 其中不乏离家近的园圃, 如在《时运》中, 陶渊明言:“斯晨斯夕, 言息其庐。 花药分列, 林竹翳如。”[1]“花药分列”之花,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注:“一作‘华’”[1],“华”亦有花之意, 此庐外即有类似于园圃的存在; 又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果菜始复生”之“菜”,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注:“一作‘药’”[1], 但不管陶渊明此处原文作“药”还是“菜”, 都可以说明陶渊明家附近有一个园圃, 在戊申岁陶渊明某处宅子失火后, 附近的园圃也受到了影响。 当然, 也有一些田地和园圃离家远, 有时劳动需要经过一段远路, 陶渊明在作品中也记载了这一类通往田园的偏远路途。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中言:“地为罕人远”[1];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云:“扬楫越平湖, 泛随清壑回。 郁郁荒山里, 猿声闲且哀。”(4)“郁郁荒山里”句“郁郁”后,宋本注:“一作皭皭。”[1]去田园劳作, 先要划船渡湖, 再随溪流进去, 所到田园乃处在一荒山中, 还能听到猿声。 这一类路途偏远, 跟陶渊明去往田园劳作的现实生活也密切相关。
《归去来兮辞》中有“农人告余以春及, 将有事于西畴。 或命巾车, 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寻壑, 亦崎岖而经丘。 木欣欣以向荣, 泉涓涓而始流”(5)“农人告余以春及”句“及”字下, 宋本注:“一无及字,一作暮春,又作仲春。”“经丘”之“经”, 宋本注:“一作寻。”[1]等句, 此处所涉及去往田园之路, 大概出于作者根据以前生活经验的想象。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曾引周振甫之言来阐明观点:“周君振甫曰:‘《序》称《辞》作于十一月, 尚在仲冬; 倘为‘追录’ ‘直述’, 岂有‘木欣欣以向荣’ ‘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 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 将有事于西畴’ ‘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 不言而可喻矣。 ’本文自‘舟遥遥以轻飏’至‘亦崎岖而经丘’一节, 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 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7]20虽说有想象成分, 但前往西畴之路也比较偏远, 有时要驾车, 有时需划船, 还需经过沟壑和山丘。 这样的路途跟陶渊明去往偏远田园耕种的现实路途是相似的。
有些通往田园之路不易行走。 偏远之路, 行走起来容易有诸多不便。 在《归去来兮辞》中, 陶渊明展示了归去的放松与愉悦, 可在涉及通往田园之路时, 他并没有避讳路途之偏远难行, 还用了“崎岖”等词来形容。 在《归园田居》其三中, 他说:“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6)“衣沾不足惜”句“沾”字下,宋本注:“一作我衣。”“但使愿无违”句“无”字下,宋本注:“一作莫。”[1]道路狭窄, 草木茂盛, 露水还沾湿了诗人的衣服, 可他这时想到的却是不违心愿。 这样的路是一种田园实录, 实际上也融入了作者的内心情感, 更加突出了诗人归去心志之坚。
2 陶渊明诗文中田园路与行役路的情感意蕴
陶渊明的一些田庄确实处于偏远之地, 不易行走, 在陶渊明一些诗文中也有反映。 但如果把通往田园之路与行役路途中呈现出的景象对比可以发现, 陶渊明对于二者有着明显的情感区别。
陶渊明在行役诗中描绘行役之路时流露过厌倦的情绪。 钱志熙认为:“陶渊明的行旅诗, 多写留恋山泽、 厌倦途旅之情, 实为古老的行役诗传统, 与稍后兴起的壮赏山川之美的纪游诗有所不同。”[5]237《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言:“眇眇孤舟逝, 绵绵归思纡。 我行岂不遥, 登陟千里余。 目倦川涂异, 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 临水愧游鱼。”(7)“登陟千里余”句“陟”字下,宋本注:“一作降。”“目倦川涂异”句“异”字下, 宋本注:“一作修涂永。”[1]路虽远, 舟可行, 然而, 诗人却流露出一种归念以及疲惫感。 笔者在《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书写》一文中也已阐明:“园田、 山泽居、 班生庐与‘眇眇孤舟逝’之现实景象相照应, 在虚实交替中, 诗人的仕隐矛盾也进一步凸显, 然而在这首诗中, 现实地理空间反而涉及较少, 加之诗人自言‘绵绵归思纡’, 可知在此诗中其归隐之意要盛于出仕之意。”[8]
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8)此诗题又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里, 诗人有“凉风起将夕, 夜景湛虚明, 昭昭天宇阔, 皛皛川上平”[1]之语, 正初秋, 风微凉, 月澄明, 天宇阔, 川上平, 这般壮阔夜景并没能安定诗人的内心, 他因惦记行役事难眠, 又言“商歌非吾事, 依依在耦耕”[1], 行役途中仍牵挂着田园之事。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则是陶渊明于返程途中所作。 “鼓棹路崎曲, 指景限西隅。 江山岂不险, 归子念前涂。”(9)“指景限西隅”句“西”字下, 宋本注:“一作‘四’”。[1]路途崎岖, 还恰逢夕阳落山, 甚至途中还显现出险意。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的“山川一何旷, 巽坎难与期。 崩浪聒天响, 长风无息时”[1]再一次强调了行役之险。 反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路途虽偏远不易行, 诗人却言“日入相与归, 壶浆劳近邻”[1], 有一种安宁之意。
陶渊明笔下所呈现的地理空间很多, 田园路、 行役路其实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学地理空间, 其中呈现的景象也不一样。 行役路上往往具有开阔之景, 交通也似更为便捷, 至少有舟可通, 而通往田园之路, 有时可乘车或乘船, 有时还需携带农耕用具步行, 这两者在陶渊明笔下都有着艰辛的意味。 不过, 对于通往田园之路的艰辛, 诗人不仅可以坦然接受, 还能衍生出更为诗意的画面。
陶渊明对通往田园路和行役路态度之不同,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 田园路跟陶渊明的自然思想相契合。 老子有“道法自然”[9]79之言, 偏远的田园路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不管是杂草还是荒山, 都保存了一定的自然性质, 而行走于田园之路上的陶渊明, 他是一个“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1]之人, 在他辞官后, 通往田园之路崎岖也好, 偏僻也罢, 都契合了他的本性。 与之相反, 行役路跟陶渊明本性有相违处, 行役时任务在身, 难免有身不由己之感, 更何况陶渊明当时所处的大环境较为动荡, 很难实现志向。 陶渊明不止一次任职于军幕中, 其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均可为证。 以“使都”看, 陶渊明在军幕中还承担过某种任务, 古直先生认为:“则渊明三月使都, 殆即为敬宣奉表辞职也。”[10]102同年, 陶为彭泽令, “仲秋至冬, 在官八十余日, 因事顺心, 命篇曰《归去来兮》; 乙巳岁十一月也”。 乙巳岁即义熙元年, 据《宋书》, 义熙三年闰月, “凡桓玄余党, 至是皆诛夷”[4]14, 此时距陶渊明辞官不到两年。 关于陶渊明是否曾仕桓玄, 学术界目前还有争议。 但不论陶渊明是否曾仕于桓玄, 都可看出陶离开的官场, 非盛世之普通官场, 而是历经飘摇动乱后充满倾轧与血腥、 机谋与暗算之地。 理解了这些, 便可更好地理解陶渊明行役路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担忧。
钱志熙认为:“在天地自然方面, 陶渊明的隐逸行为, 已经明显地表现了他在庙堂与山水之间是选择了后一场合的。”[5]152陶渊明的选择契合了他的自然思想, 不管是不为五斗米折腰, 还是逃离充满倾轧的官场, 或是遵从内心的选择, 这种种都跟他的自然思想有关。 这般充满自然性的、 偏远的通往田园之路, 可以安放他的自然思想, 虽艰辛却也给了他一份安宁与诗意。
通往田园之路, 相对于住宅或田园来说更具备自然性的空间。 住宅与田园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类规划影响, 虽说植物生长有一定的自然规律, 但园里植物的存在又很难摆脱人为性, 即使野生植物留在园中, 也可能符合了园子主人的规划意识。 但通往田园之路不一样, 有些即便是人为规划的, 但也具自然性, 陶渊明自称:“见树木交荫, 时鸟变声, 亦复欢然(10)“然”, 宋本注:“一作尔。”有喜。”[1]在通往田园之路上, 应不乏这般景象, 从家到田园的路, 也可以有很多种, 农人对劳作路途的自由选择度也更高。 而那种偏远少人行之处, 远离尘世喧嚣, 也适合爱闲静的陶渊明行走, 通往田园之路也是他精神栖居地之一。
其次, 田园路可以是通往家之路。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说:“创造家或故乡的感觉是写作中一个纯地理的构建, 这样一个‘基地’对于帝国时代和当代世界的地理是很重要的。 一篇文章中标准的地理, 就像游记一样, 是家的创建, 不论是失去的家还是回归的家。”[11]48在中国古代诗歌中, 可见很多诗人的家园情怀。 通往田园之路, 属于田园-家或家-田园的路途, 相比行役路而言, 距离家乡更近, 而行役路虽也可连接故乡, 却是诗人远离家乡, 漂泊异乡的见证。
最后, 通往田园之路也可以是通往理想之路。 如《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郁郁荒山里, 猿声闲且哀。” 这跟现实田园周边环境有关, 而诗歌末两句“遥谢荷蓧翁, 聊得从君栖”[1]亦含理想寄托。 通往田园之路, 也可以象征着通往理想之路。 这种理想之路跟《桃花源记》中的桃源路又相互映衬。 桃源路是“渔人”进入桃花源的路径, 也比较偏远。 这是无意中发现的路:“缘溪行, 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1]后来, 渔人看到桃花林, 走了数百步, 也看到了两岸的风光。 “林尽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1], 之后, 渔人从这小口进入, 一开始里面很是狭窄, 走了几十步才至阔朗之处, 看到了村庄。 不过, 相比田园路而言, 陶渊明对桃源路有着神秘且浪漫的书写, 缘溪行的随意, 桃花林的浪漫, 从山的洞口通过又见阔朗天地的惊喜, 通过桃源路, 还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村庄。 这条路神秘出现, 后又不见,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 寻向所志, 遂迷不复得路”[1]。 《桃花源记》中的田园生活很是美好安定, 这仿佛是处于太平时代的景象, 而陶渊明身处乱世, 他内心自然需要一个太平时代去安放他的理想。
3 陶渊明诗文中田园路的传播接受及独特性质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路是重要且特殊的文学地理空间, 其融入了作者的内心情感, 也在后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具有独特性质。
李志艳认为:“文学文本的传播也是异域空间的文化旅行。”[12]陶渊明的田园曾一再引人关注和热议, 也不乏关于陶渊明田园的唱和之作。 通往田园之路方面,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 曾被误收入陶集的《归园田居》其六(“种苗在东皋”)中就有对通往田园之路的简单描绘。 文本的传播自然也会影响读者的判断。 这首诗又被认为是江淹所作, 江淹《陶征君潜田居》言:“种苗在东皋, 苗生满阡陌。 虽有荷锄倦, 浊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车, 路暗光已夕。 归人望烟火, 稚子候檐隙。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 但愿桑麻成, 蚕月得纺绩。 素心正如此, 开径望三益。”[13]1577此诗曾被苏轼当成陶渊明所作,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韩子苍云:‘《田园》六首, 末篇乃序行役, 与前五首不类。 今俗本乃取江淹‘种苗在东皋’为末篇, 东坡亦因其误和之, 陈述古本止有五首, 予以为皆非也。 当如张相国本题为《杂诗》六首。 江淹《杂拟诗》亦颇似之, 但《拟渊明诗》‘开径望三益’, 此一句为不类。 故人张子西向余如此说, 余亦以为不然。 淹之比渊明情致, 徒效其语, 乃取《归去来》句以充入之, 固应不类……”[14]25-26《陶征君潜田居》一诗在本质上确实不类渊明所作, 也确实取了《归去来兮辞》中的句子, “日暮巾柴车”便是对《归去来兮辞》中“或命巾车”的接受, “日暮巾柴车, 路暗光已夕”也是对陶渊明通往田园之路的接受。
《归去来兮辞》中的“农人告余以春及, 将有事于西畴。 或命巾车, 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寻壑, 亦崎岖而经丘”, 在后世其实有不少接受者, 比如, 苏轼的“北山怨鹤休惊夜, 南亩巾车欲及春”[15]513; 杨万里的“柴桑卧病一茅庐, 或棹孤舟或命车”[16]; 范成大的“寻壑经丘到此堂, 官闲聊作送春忙”[17]等, 陶渊明通往田园道路的一些描写, 成了一种文化典故, 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与接受, 然而, 他们跟陶渊明笔下那种真实的通往田园的道路书写尚有区别。
“文学地理学认为, 正是通过文学接受者这个途径, 文学实现了对地理环境的某些影响, 尤其是对人文环境的影响。”[18]陶渊明通往田园之路在后世得到了一定的关注, 但得到的回应其实有限, 唐初王绩的《田家》也有对陶渊明田园的接受, 却少了通往田园之路的描述, 他的《春日山庄言志》虽有对偏僻之处的描写, 却多跟其住处有关, “入谷开斜道, 横溪渡小船”[19]46虽有“扬楫越平湖, 泛随清壑回”之意味, 也有陶渊明所描述入桃花源的意味, 但也没有连接到具体的田园生活。 储光羲《田家杂兴》八首也有学陶之处, 但也不见对通往田园之路的描绘。 宋代吴芾的《和陶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与《和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亦不见对通往田园之路的描述。
后世很多和陶慕陶者, 他们笔下的田园跟陶渊明田园本就不同, 更何谈通往田园之路。 这样的路途, 为陶渊明的田园增添了个性化特征, 尽管慕陶拟陶和陶者众多, 但有些通往田园之路, 却是属于陶渊明的, 很难模仿。 诚如钟惺所言:“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 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 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 所以为真旷达。”[20]陶渊明真正从这样一条路走过, 历尽艰辛, 也享受着自由。
4 结 语
以前的研究者也有对陶渊明行役时情感的关注, 不过关于陶渊明笔下田园路与行役路之区别, 田园路与桃源路的相互映衬等问题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陶渊明在行役途中易流露出厌倦、 担忧等情绪, 他笔下的一些田园路虽偏远不易行, 诗人却写出了一种诗意与安宁, 主要是因为通往田园之路契合作者的自然思想, 行役路与其本性有相违之处。 田园路更具自然性, 农人去劳作时对路途的选择相对更为自由。 通往田园之路又可跟通往桃源之路相互映衬, 田园路有着现实基础, 又不乏理想与希望, 桃源路随意浪漫, 却也有着一定的现实因子。 陶公笔下的田园路在后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也有其独特性质。 通往田园之路, 赋予了陶公田园诗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