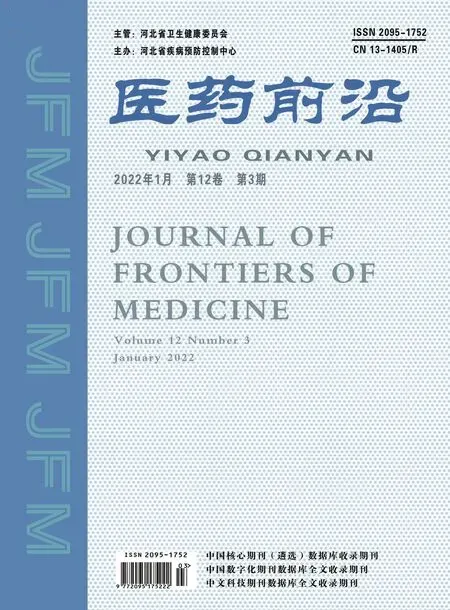溃疡性结肠炎的流行病学与NLRP3炎症小体关系的研究现状
何 云,李运泽(通信作者),赵华莹,张 佩,伍文红
(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广西 柳州 545000)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最早于1903年由Willks和Boas提出,在临床中又称为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以大肠黏膜和黏膜下层为主要病变部位[1]。近年来,UC的遗传学和免疫机制研究是临床研究的一重要课题。自开展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后,逐渐发现了UC的一系列易感基因和ECMI基因,其中NOD样受体家族3(NOD-like receptors, NLRP3)基因参与了人类众多疾病的发生发展,NLRP3炎症小体由三个结构域所组成,包括NLRP3、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及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1(caspase-1),均参与了UC的发生过程。其中靶向NLRP3炎症小体与UC关系已成为临床研究重点,本文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流行病学与NLRP3炎症小体关系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溃疡性结肠炎流行病学及病因
1.1 流行病学特点
溃疡性结肠炎属炎性肠病中的一种,为消化系统常见病。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该病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以北美和欧洲地区较为高发,年发病率为0.6~20.0/10万,而中东和亚洲地区年发病率为0.1~6.3/10万,而我国UC年发病率为26.5/10万,且发病率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而呈上升趋势[2]。本病好发于20~50岁人群,其中男性较为多发。UC以慢性炎症及形成溃疡为主要病理特点,病变范围主要为直肠、乙状结肠甚至整个盲肠,可侵犯大肠黏膜及黏膜下层。患者发病后临床症状可分为消化道症状及肠外症状,其中消化道症状以腹泻、腹痛及便血等为主要表现,肠外症状表现为发热、身体消瘦、虹膜炎等,且该病在临床中具有慢性持续、急性发作、病情反复及并发症多等特点,若未及时采取有效治疗措施,可致下消化道出血、结肠穿孔及癌变。据赵梅花等[3]研究报道,与正常人相比,UC患者发展为大肠癌的概率要高数倍。
1.2 病因
目前,临床对本病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多数研究者认为与以下因素有关[4-5]:肠道感染是诱发UC的一重要因素,而迄今未发现存在特异性病原体。当前,肠腔内菌群的改变受到了临床重视。通常肠道菌群紊乱与黏膜屏障通透性增加、抗原刺激及肠上皮细胞受损有关,在长期影响肠黏膜的免疫系统的情况下可引发肠道持续性炎症;UC患者多存在免疫调节紊乱,病灶黏膜中体液免疫细胞数提高,经临床实验室检测可见少数患者血清中有抗中粒细胞质抗体、抗结肠上皮抗体及特异性自身抗体。UC为一种多基因遗传性疾病,近年来炎症性肠炎的遗传学已作为消化系统疾病研究的一重要课题,自开展全基因关联研究后,易感UC的一系列基因逐渐被发现,如NKX2-3、ECM1、IL12B、IL23R及NLRP3等,当前发现UC易感性位点共47个,共中UC特有的位点共19个[6]。有研究发现,NLRP3炎症小体为UC的发病机制研究提供了有效依据[7]。
2.NLRP3炎症小体的生理作用
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是在炎症小体激活剂的作用下,而NF-kB促进NLRP3炎症小体各分子转录和翻译是其激活过程。能激活NLRP3炎症小体的分子较多,包括微生物、尿酸单钠(MSU)及ATP等分子[8]。无活性的procaspase-1可通过NLRP3炎症小体转化为有活性的caspase-1,而IL-18前体和IL-1β可通过活性caspase-1分子转化为能发挥生物学作用活性的il-18和IL-1β,导致机体发生炎症反应,对多种炎性反应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3.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与调节因子
3.1 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
长期以来,在寻找UC潜在药物治疗靶点中一直将NLRP3炎症小体活化机制作为一重要研究课题,其活化机制有以下几种模式:①线粒体产生及损伤的活性氧与NLRP3的激活有密切关系,据相关研究表明,抑制活性氧产生或线粒体蛋白VDCA的表达对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可产生抑制作用[9]。同时,Zhai等[10]研究表明,在NLRP3激活过程中活性氧的释放与线粒体损伤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细胞内caspase-1表达和IL-1β的释放可在活性氧抑制剂乙酰半胱氨酸的作用下降低。②细胞内K+外流为激活NLRP3的必要信号之一,ATP的释放可激活细胞膜上的P2×7受体,开启P2×7门控离子通道,可形成膜孔,可造成细胞内K+外流。③巨噬细胞吞噬SIO2、胆固醇晶体等颗粒状物质后可造成溶酶体破碎或损伤,所释放的cathepsin B等蛋白酶对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有促进作用。
3.2 NLRP3炎症小体激活的调节因子
3.2.1 调节因子—Nek7 Nek7为NIMA相关激酶家族,可激活NLRP3炎症小体,对DNA损伤反应和有丝分裂过程具有调节作用。Tanmura等[11]研究表明,小鼠胚胎发育中存在Nek7缺陷,而在胚胎发育晚期生长受到阻滞甚至死亡,提示在胚胎生长和存活过程中Nek7具有重要作用;Perera等[12]研究报道,在体内模型中,Nek7对NLRP3激活的作用得到了证实:将有Nek7缺陷的小鼠与野生型小鼠相比较,前者IL-1β分泌减少,并降低了免疫细胞的聚集和疾病严重度,提示在NLRP3炎症小体激活中Nek7为正向调节因子。
3.2.2 调节因子—蛋白激酶PKR PKR可调节AIM2、NLRP1和NLRP3等炎症小体的激活。杨连雷等[13]在PKR缺陷型和野生型小鼠中分别提取巨噬细胞的实验中发现,PKR缺陷型小鼠IL-18、IL-1β的分泌和caspase-1的激活与野生型小鼠相比明显受到抑制;将野生型小鼠提取的巨噬细胞用PKR的抑制剂2-氨基嘌呤后,IL-1β的分泌和caspase-1的激活减少。而给予尼日利亚菌素、ATP和二氧化硅等NLRP3的激动剂时,PKR-/-来源和PKR+/-来源的巨噬细胞内,IL-18、IL-1β的分泌水平和caspase-1的活化与未给予时比较无明显变化;来源于野生型小鼠的巨噬细胞内,IL-18、IL-1β的分泌水平和caspase-1的活化与PKR-/-来源的巨噬细胞也无显著差异,可见PKR对IL-18和IL-1β的分泌、caspase-1的活化及炎症小体的激活不是必须条件。
4.UC与NLRP3炎症小体的关系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维持肠道内环境稳定、调节肠道炎性反应等方面NLRP3炎症小体发挥着重要作用,NLRP3的失调对引发炎症性肠病(CD)和UC具有一定作用[14]。肠道固有免疫系统为机体面对各种细菌抗原的第一道防线,UC患者固有免疫系统减弱使得不断累积细菌抗原,从而诱发了获得性免疫系统瀑布式炎性反应。在肠道细菌和免疫系统之间NLRP3炎症小体发挥了重要作用,NLRP3炎症小体可确保肠道内维持稳定状态,有利于保护结肠炎,而NLRP3缺陷可导致对炎症性肠病易感。
在UC发病中,NLRP3炎症小体有促炎性反应作用,对试验小鼠使用NLRP3依赖的IL-18、IL-1β治疗,能缓解急性结肠炎[15]。此外,有研究表明,NLRP3炎症小体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干扰素诱导蛋白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肠道菌群等。NLRP3参与UC的机制较复杂,通过caspase-1拮抗剂pralnacasan对于DSS诱导的结肠炎可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16]。在UC、急/慢性结肠炎的结肠组织中,NLRP3炎症小体表达水平呈上升趋势,提示NLRP3炎症小体在UC在发生发展中有促进作用。
5.结论与展望
NLRP3炎症小体参与了UC的发生发展过程。但对于NLRP3炎症小体表达水平对UC的影响仍有部分研究者存在争议,NLRP3基因缺陷会降低小鼠对口服2%DSS所诱导的结肠炎的易感性,而对TNBS灌肠和口服2.5%或3%DSS所诱导结肠炎的易感性会增加。后续有待进一步研究UC患者体内NLRP3炎症小体的表达状态,明确NLRP3炎症小体与UC相关炎性因子的相互作用,以期成为UC治疗的新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