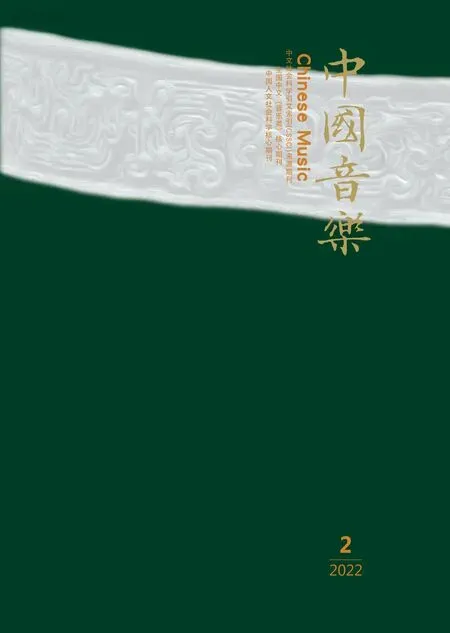互鉴共赢 殊途同归
——从“学术史”视角看中国音乐史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关系
○ 胡 斌 孙 焱
在中国当下高校的音乐学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中,中国音乐史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Ethnomusicology①该术语最早由孔斯特于1950年提出,从关注“他者”音乐起源逐渐延伸至关注“人类一切音乐文化”的音乐学下属学科,其研究方法强调音乐本体分析和文化阐释的结合。自1980年该西方学科正式引入中国并开启了学科本文化的过程,至今涌现了大量成果,成为音乐类高校尤其是硕博培养中的重要专业之一。由于国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中文译名持有不同意见,因此本文采用“Ethnomusicology”称之。虽然均属于音乐学下属分支学科,在研究领域与研究理念上各有区别,但在学术研究及各层级音乐理论人才培养的现实过程中,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这三个专业领域逐渐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现象,不少中国音乐史学家同时又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专家或Ethnomusicologist。那么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音乐史学和中国传统音乐及Ethnomusicology的研究对象有过怎样的交叉和分离?三者的研究目标又有何区别?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三者既有重叠又相对独立的关系?其实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在学界日常已有的各类学术成果中均有显现,当下学人也越来越倾向应当从整体的、关联的以及学科史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全面理解。本文将以“中国音乐史”为出发点,从学术史的视角,就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及Ethnomusicology之间的学科关系进行讨论。
一、中国音乐史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虽然诸多音乐学科均来自于西方,但是对于中国音乐史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而言,两者应该是最为“本土”的传统学科了,一古一今,彼此关系密切。从当下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诗经》《楚辞》《成相篇》等,即是民间音乐相关内容以史学文本的方式呈现,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戏曲与民间音乐部分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本就迥然一体,不可分割。
20世纪初至1949年是中国音乐学的酝酿和起步阶段,整体以个人或小众会社的研究方式为主,研究对象以中国音乐史学和传统音乐为代表。同时,这一阶段也是中国音乐史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初创时期,两者最初的奠定似乎都可追溯自相同的一些学者和成果,不论是代表学者、研究成果、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两者都有着密切的交叉,呈现出在交叉互嵌中前进的历史样态。
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史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在部分地相互结合过程中得以确立和发展的。王光祈、童斐、刘天华、郑觐文等人共同的特点都是立足本土,且领域广博,既是中国音乐史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代表人物,但这并非意指当时的学者具有鲜明的中国音乐史学家与中国传统音乐学家的双重身份,实际上这些学人可能并不需要从“分专业”或“割裂”的角度来“严格”看待他们的研究对象。虽然在研究成果的学科归属上各有倾向,但内容的交叉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中,有数量不少的重要著述集中在传统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中也包括有大量的音乐史学学术资源。参考陈永在《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②陈永:《中国音乐史学之近代转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的整理统计,在1920年至1936年间的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中,涉及的音乐史学学术资源主要包括有国乐研究、外族音乐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等方面。
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继承了史学研究注重文献为主的方法,与此同时,亦开始看重“传统音乐的实践和采集”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尤以杨荫浏先生为代表。他的《中国音乐史纲》对史料力求辨伪求真,特别注意史料与活态音乐之间的联系,并且指出,全部的中国音乐史,是一部以民间音乐为主体、吸收融化外来音乐和创作改编相结合的发展史。这一结论明确而直接地阐明了中国音乐史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关系,同时在研究内容、范畴及方法上给予了相当的开放性。他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和采集是一种自觉性的学术行为,是一种学科建设意义的活动,他于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被学界认为当时最具学术价值的有关中国传统器乐艺术研究的论文《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其中明确表现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基础:“须从古今一脉中间,去接近它(国乐)基础的深度……国乐却待认清了来路,才可以有合理的去路。”③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6-7页。这也是他于1942年在重庆青木关教授“国乐概论”和“中国音乐史”的理论思想基础。他怀着对“今之乐,犹古之乐也”的坚信,意识到每种传统器乐和声乐品种,都储存了程度不等的古代音乐信息,都跳动着中国音乐历史的脉点。乔建中在对杨荫浏学术思想的总结中提及,“音乐史学家的最重要的任务,应该首先通过实践去感受这些活态音乐的活的灵魂。然后才能谈得上努力追溯其产生、形成的踪迹,尽可能恢复其历史真貌”④乔建中:《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一个里程碑—新解杨荫浏先生“实践—采集”的学术思想》,《人民音乐》,1999年,第11期,第6页。。杨荫浏先生的“实践—采集”研究方法,一方面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初创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一时期仍然是以个人化的探索为主,但中国音乐史学已经彰显出自身资源厚重、起步较高、注重实践、对象特殊的学术特色,也暗示了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音乐史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之间依然会继续交叉前行。
如果说1949年前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实践—采集”行为更多是一种个人性的行为,那么1949年至1966年间中国音乐史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大规模的对民间音乐的采集、记录、整理工作则是国家在场下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一部分,与三四十年代相比,无论涉猎的范围、品类和深度都有新的扩展。以杨荫浏、廖辅叔、沈知白、李纯一为代表的研究队伍,成果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特别是由文化部牵头,以原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为重镇,汇集了杨荫浏等全国致力于音乐史学的学者和高校教师,定位研究理念和方法,从传统音乐活态中追寻回溯,依朝代将不同阶段的音乐机构和承载的音乐形态系统化梳理,终将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脉络相对清晰地展现于学界⑤项阳:《在艺术与文化的有机整合中推动中国音乐史学转型》,《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9期,第4-13页。。再如李纯一等学者深入考古学领域,以出土的实物来检验史籍中关于音乐的记载,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等⑥田可文:《中国音乐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20年,第61页。。这一时期,音乐史研究成果逐渐丰满起来,其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继续交叉前行,并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将“共时”视角应用于“历时”研究的思路与观点,在后来诸多音乐史学家的言论中渐有体现。音乐实践中存留至今的、活的历史材料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上与前两者相比虽然并非主流,但是已经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与认可。用“逆向考察”来描述“历时与共时”相结合并作用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逐渐在实践中显示了其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具有特殊重要性,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与北宋鼓吹教坊及其乐器的关联、西安鼓乐与唐燕乐的关联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这种学术体会是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根据中国音乐史学的内在特点逐渐萌生和总结而来的,也为后来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方法应用于中国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前期理论基础。
自1980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研讨会及之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成立至今,中国音乐史与中国传统音乐相融合的研究方式在各自领域中都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新的理论思考与个案研究逐一问世,传统音乐研究中的史学思维也好,音乐史研究中的传统音乐对象也罢,在诸多学者的学术实践中,不但延续着由学科交叉带来的理论思考,而且在个案研究中形成了“历时”与“共时”共同构建的问题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学科界限的突破。其中较为突出的学术成果,如项阳进行的关于山西乐户的系列研究,该专题研究一方面分析了山西现存民间礼俗同音乐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以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承机制进行了整体认知,其长达二十余年的学术关注本身即已构成了横向田野的纵向审视,并在中国音乐历史研究中结合文献总结出了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从而实现了从田野到文献、从现象研究到机制研究、从当下到历史的“接通”,以双向观察和体验促成了新的学术认知。其《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一文就传统田野考察与历史研究相“接通”的概念再次进行了强调,文章“思考音乐学界音乐史学与传统音乐相结合‘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实践意义,强调音乐史学走出书斋,传统音乐接通历史,在各有侧重的视角下进行综合、立体的研究,从而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⑦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第9页。。诸如此类的成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过去的学科边界历经交叉后成为新的学科焦点,“古”与“今”之间除了习惯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也逐渐通过学术个案及反思的穿针引线,形成了越发明晰的“整体观”思维,尤其是在中国“本土”音乐学科的整体框架下,丰厚的学科传统与积淀为今天出现的学术转变提供了土壤和空间,使我们看到了中国音乐史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之间在研究内容、范畴、方法、理念上进行关联的各种无限可能。
由上可见,中国音乐史与中国传统音乐之间实际上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我们对历史上民间音乐相关内容的了解,正是源于音乐历史文献,今天的传统音乐研究仍然是在中国音乐的历史传承与发展脉络的语境中进行的。从音乐史学资料来说,其范畴主要包括音乐文献资料、音乐考古资料、当下现存的音乐民俗资料,这一点早为学界共识。出于现代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音乐史与传统音乐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方向,这一点与中国的历史学与民俗学研究有着相当的一致,但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社会存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⑧白寿彝:《民俗学和历史学》,《思想战线》,1985年,第1期,第17页。。从今天“微观史”“生活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还能够给以往“正史”“官史”语境下的中国音乐史研究提供来自底层、民间的学术话语与资源,从而真正形成“立体”“复数”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国音乐史研究可以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提供历史背景与历史事实,并进行历史脉络阐释,使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更加具有深度和厚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材料和观念可以充实并扩大音乐史料的范围,提供细节参考与横向语境,使中国音乐史研究更加饱满,更加立体。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借鉴,不但在研究内容、研究范畴方面彼此拓展,更在研究方法、学术观念上起到了相互补足与互为反思的作用。
二、中国音乐史学与Ethnomusicology
中国音乐史学与Ethnomusicology之所以能够相互关联并成为当下音乐学研究中的热点,主要基于如下共识:1.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需要“共时”视角的参与,需要与音乐的当下田野相互关照,而Ethnomusicology需要“历时”视角的参与,需要在音乐的历史田野中追溯渊源与脉络;2.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不仅需要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也需要对现代史学方法的借鉴,而Ethnomusicology进入中国,需要在中国的音乐历史田野中实现“中国话语”和“中国表述”的凝练与创新。
王光祈兼具中国音乐史学家和比较音乐学家,其《东方民族之音乐》和《东西乐制之研究》等是Ethnomusicology在中国最早的代表成果,这一点已是学界公认。至于王光祈之后至1980年之间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阶段是否可以纳入Ethnomusicology在中国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该问题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中国音乐史学与Ethnomusicology之间的学术关联,则主要见于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
如果说前辈学人对将“共时”视角引入“历时”研究是一种源自学术积累的敏感,将当下遗存作为历史描述的切入点是基于客观存在的论据,那么明确将Ethnomusicology学科理论与方法用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并且致力于在历史文献中有意识地展开横向田野,重理历史叙事方式,则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大胆尝试。与之前学者提出的由今及古的逆向考察不同,洛秦与修海林的关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反思⑨洛秦:《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34-46页;修海林:《在历史中展开共时—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音乐》,2000年,第2期,第17-18页。,则站在学科的高度,主动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在理论与观念上进行融合,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的理论思维得以形成,并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提出了越发清晰的革新主张,即实现另一种历史的叙事方式,以实现更为全面的历史呈现。之后,齐琨结合自己的田野探讨了在历史过程中阐释音乐文化现象的观点,认为“口述历史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今音乐文化的存在状态和延续原因,亦可将现今音乐研究中似乎已成为常识的概念放置在历史过程中重新加以反思”⑩齐琨:《历史地阐释:民族音乐学之历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83页。。经过多年的学术实践,Ethnomusicology相关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成果渐渐有所积累:2009年汉唐音乐史国际研讨会上,洛秦从“新史学”的视野对能够反映唐代长安音乐社会生活的各种音乐史料进行了新的解读,探讨了从文献构建历史社会音乐生活空间的可能性。⑪该文为洛秦在2009年汉唐音乐史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朱国伟于2010年提出“民族音乐学的逆向考察、历时与共时研究法、宏观与微观的地域观念、比较研究方法、音乐解释法、乐器学方法和实地考察法等研究方法,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能起到借鉴的作用。”⑫朱国伟:《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借鉴作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8页。至2014年,洛秦更进一步,通过对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旗帜鲜明地提出重写音乐史的意义在于研究范式上的突破。作者分析了音乐属性的多重性与音乐历史的“被发现”“被书写”和“被阐释”的特点,并通过四个不同历史空间的“历史田野”,论述了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核心,即注重叙事而非描述,强调阐释而非证实。⑬洛秦:《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写》,《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第6-26页。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新的材料得以挖掘使用、新的视角与解读方法得以归纳总结、新的研究目标得以确立、新的历史表述为音乐史学带来了新的写作范式。
此后,随着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意识下的中国音乐史研究越发深入,专题化、规模化的情况开始显现,其中,成果最为凸显的则是“新史学”理念下的宋代音乐史学研究。2009年、2013年、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先后举办了三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成立“宋代音乐国际学术研究中心”;2012年以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推出“宋代音乐文化阐释与研究文丛(第一辑)”……宋代音乐研究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洛秦、康瑞军撰文就当时宋代音乐史学理问题的相关讨论进行了归纳总结,主张充分借鉴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成熟人文学科丰富的学术成果和学理资源,实现“新史学”理念对宋代音乐研究的范式与思维的拓展,以此丰富宋代音乐研究的学术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建立断代音乐史研究创新学术体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⑭洛秦、康瑞军:《国际化视野下宋代音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思考(2009—2013)》,《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69-74页。此外,李方元以《宋史·乐志》等文献为例,提出在历史叙事中实际存在这“历史时间”与“叙事时间”两种意义的时间概念,且“历史时间”由“叙事时间”提供,叙事比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历史编纂体裁的不同,指明可以通过历史叙事来考察历史文本编纂的目的性,将“新史学”意识带入了对史学元理论问题的思考⑮李方元:《音乐史中的叙事与分析—对音乐历史研究的思考》,该文系李方元在2010年“唐宋音乐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言内容介绍见杨成秀:《“唐宋音乐史学研讨会”综述》,载《音乐艺术》,2011年,第2期,第143页。。立足当代,通过历史文本的编纂(而不仅仅依赖历史考据,并试图让文本“说话”)来表达史学观念的撰史方式,在今天的宋代音乐史学及其学术环境里,已逐步引起了学界的共鸣。这一趋势还体现在《宋代音乐研究的社会史取向—以音乐制度为例》⑯康瑞军:《宋代音乐研究的社会史取向—以音乐制度为例》,《音乐艺术》,2011年,第2期,第93-98页。《“新史学”与宋代音乐研究的学科语境—写在“第二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⑰康瑞军:《“新史学”与宋代音乐研究的学科语境—写在“第二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音乐艺术》,2014年,第2期,第121-131页。等诸多论文之中,尽管这些论文的具体立论对象是音乐制度、文本、思想、音乐实践和体裁,大致未出传统范畴,但是,这些论文往往在研究理念上呈现出鲜明的语境意识和论证逻辑,尝试以点及面、经由案例考证抽象到一般学理的方式来揭示研究对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在部分学者看来,在研究中去尝试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必要的,即以“叙事”和“阐释”为历史书写的核心。历史材料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特定的史学观念,所发现和整理的文献依然仅仅是素材,而历史研究的重点则是书写。
中国音乐史与Ethnomusicology思维相融合的学术成果虽然初具规模,并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但是毫无疑问,两者之间能够摩擦出的火花并不止于此。考虑到Ethnomusicology在中国的音乐学术发展中仍然面临尚待解决的“本土化”问题,且主要集中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而中国的音乐历史田野又实在浩瀚而广博,能够发掘的学术富矿和能够给Ethnomusicology提供的历史经验远未显露完全,加之两者的往来不仅仅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互鉴,更加是东西方不同学术思维、不同表达语境和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往来碰撞,因此中国音乐史学与Ethnomusicology之间的未来仍有待展现。实际上,受Ethnomusicology以及人类学的影响,政治史、经济史、生活史、身体史、环境史等诸多新视角都给中国音乐史研究带来了对象、范畴及史观方面的更新与突破,正如齐琨在其《书写历史—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范式与范畴之中国经验》一文中所说:“目前的历史民族音乐学更是一个领域,召唤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盟,共同思考关于历史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具体到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这两个学科,目前展现的是在知识结构与叙事模式上的互补,这也是目前历史民族音乐学存在的意义。”⑱齐琨:《书写历史—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范式与范畴之中国经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58页。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音乐史研究越发呈现出“复数”的趋势,尤其在史观变化的情况下,以往的“信史”可能成为“非信史”,以往的“野史”可能也成为音乐史编撰的重要依据,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对“他者”“普通社会”的关注,以及对“历史田野”的结构与阐释,并与学界“重写音乐史”的论争相结合,为中国音乐史提供了新的叙事对象与方式。同样,受到中国音乐史的影响,Ethnomusicology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也从静态转向了动态,当下的田野资源与文化想象都成为一种历史的生成变化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结合中国数千年的音乐文化历史发展过程,能够给Ethnomusicology带来的理论更新与完善无疑是来日可期的。
三、中国音乐史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Ethnomusicology的殊途同归
任何学术理论的发展都有其脉络化的渐进过程,如同西方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是建立在学者对Ethnomusicology过于强调“共时”研究的反思一样,中国语境下“历时与共时”的接通也有着自己的学术缘起和独特的领域范围。中国音乐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区域音乐文化种类繁多,各自相应的本土研究视角与方法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特色与传统。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在中国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土壤,首先触及的就是对“本土历史”与“本土田野”的关注,与中国传统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相结合,也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新思考与新局面。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结合各自研究对此进行了思考,如洛秦《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⑲洛秦:《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34-46页。、赵志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述见》⑳赵志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述见》,《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3期,第137-144页。、李延红《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㉑李延红:《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音乐艺术》,2006年,第3期,第113-122页。、方建军《民族音乐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相互关系及作用》㉒方建军:《民族音乐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3期,第62-70页。以及项阳《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㉓项阳:《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第1-7页。等文,这些理论思考无一不是建立在各自长期的中国音乐历史与田野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并表达了对中国音乐文化“新的叙事方式”的要求与主张。但是,与其说这种“新的叙事方式”是中国音乐史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Ethnomusicology彼此之间的视角互补,不如说是各自领域在当代学术理论更新背景下自我突破的内在需要。
任何一种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学术见解,都是要建立在勤奋的田野工作和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的,学界诸多Ethnomusicology思维下的传统音乐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均是如此。无论是通过亲身体验还是学科反思,田野调查与历史分析逐渐成为诸多音乐研究中必备的双重学术能力,研究传统既要把握当下,又要回到历史。通过学术研究中的实践经验及理论经验的逐步积累,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中国音乐史与中国传统音乐在历史文化上不可分割的一体性,以及西方“历史人类学”及“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整体研究的方法论思考,都共同强调了学术研究中多种学科“接通”和知识结构拓展的意义。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无论是以Ethnomusicology的研究视野来审视与考量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发展与变迁,或是以中国历史田野来促进中国语境下Ethnomusicology学科的理论更新,都显示出了学术内涵及目标的基本一致性。
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为例,该领域虽然长期以来都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呼吁,但是在实际学术操作上又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关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史料文献的极度匮乏,至于一些无文字的民族,文献史料则更是无从谈起,从口述史的角度对当下遗存进行记述往往成为主要的手段之一。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少数民族音乐史写作已经是中国音乐史学科自身完善的短板所在,如何在极具困难的条件下完成数十种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写作,如何有效纳入中国音乐史的整体框架,这仍然是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传统音乐研究的角度来说,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属于小众化学术对象,同样面临需要纳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整体框架的学科需要,并且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巨大的文化差异和陌生的文化叙事方式都是学术研究中不得不面对和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多种学科视角的相互协作显然是必要且必须的;从Ethnomusicology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对于外国学者或者大部分的中国学者,无论是做田野调查还是进行史学写作与叙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无疑都是Ethnomusicology学科语境下最为典型的音乐个案之一。但在传统田野工作方式与文本叙事已经难以满足现实学术研究所需的情况下,如何从三者结合的创新思维出发进而步入学术实践?这显然是需要通过集体的学术智慧经过长期的学术实践来逐步思考和解决的。至21世纪初,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与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Ethnomusicology相互结合得越发紧密,如何从“活态”音乐中挖掘与历史资料的联系,如何挖掘和利用在实地考察中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发掘藏匿在纸堆史料中与现实生活中音乐事象之间的某种联系,让封存的历史文献资料与当下活态音乐“描述”达成“一致”,从而互相支撑、互相验证,已经成为当下学者们正在思考的共同话题。杨民康于2017年发文《历史民族音乐学:把音乐史还原到上下文语境中进行研究—兼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书写的难题与对策》,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同音乐文化史及历史民族音乐学在方法论上均有较大关联,后两类方法主张将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志的思维观念和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史研究领域,将已被“提纯”的音乐事象还原为音乐表演和音乐文化活动过程,把音乐作品、音乐事件和音乐人物还原到其具体生存的上下文语境中进行整体描写,也即将音乐史还原为音乐文化史。㉔杨民康:《历史民族音乐学:把音乐史还原到上下文语境中进行研究—兼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书写的难题与对策》,《黄钟》,2017年,第1期,第119页。该学术观点既是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Ethnomusicology三者共同作用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理性总结,也是以案例方式对三者学科之间关系的实证。
无论是学科发展的偶然,还是信息时代思想传播的必然,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在延续自身传统学术脉络的同时,都面临着在全球化与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共存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处理自身学术发展与世界学术话语的沟通与交流问题,这既需要对自身传统的坚持,也需要对外来学术理论的借鉴。从前述可见,中国音乐史研究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对“在历时中展开共时”“在共时中追溯历时”的总结与认可,同西方Ethnomusicology及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中对现实田野的强调及对历史田野的反思,这两者在超出国界、地域概念的文化认知意义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基于差异性极强的个案研究与理论反思上又具有积极的相互借鉴意义。此外,中国音乐史研究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因为数千年的音乐文化延续和极具差异的音乐文化个案,使其在面对基于世界多元民族音乐研究而形成的Ethnomusicology时,显示出了极强的适应性。虽然在三者碰撞之初出现了质疑与争议,但是就当下而言,显然已经初步实现了平稳过渡与借鉴反思,三个学科如何共同跳出自身局限以达到从单一学科目标到整体的学术目标的升华,这仍是当下学者正在积极关注的问题。
中国音乐史学和传统音乐研究及Ethnomusicology的交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对口述史研究方法的注重、民族音乐史和区域音乐史成果的涌现,以及新史学研究范式的突破和整合,都超越了过去学科交叉平面化的情况,而朝纵深化、多元化、学理化的层面深入发展。纵观近四十年来,中国音乐史学对原有史学观念进行了突破,发掘了很多新史料,采用了很多新方法,形成了很多新视角,涌现了大量成果,尤其是受新史学的巨大影响,使得中国音乐史学和传统音乐研究及Ethnomusicology之间在“整体性”学术思维之下形成了交叉互补。历时和共时、文献和田野、精英和草根、小文化和大历史的相互接通开启了中国音乐史学更为完整的学术品格,共同推动了中国音乐学术的前进方向。中国音乐史研究音乐历史,无疑也要关注传统音乐;中国音乐史侧重历时研究,无疑也要关注共时阐释;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不仅适用于“本我”,也可以成为“他者”的参照。因此,三者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包容的。
就现实来看,自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以及国内Ethnomusicology相关学术机构相继成立,从学会及学术机构的参加人员往往身居多个学术领域,即可看出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既精于中国音乐史,又专于传统音乐的学者不在少数,国内Ethnomusicology相关领域的学者,也与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大多有着切实的关联。回顾以往,中国音乐史学和传统音乐研究及Ethnomusicology彼此之间的界限和分野已经逐渐打破,研究对象的重叠、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研究学者的多重身份等特征渐渐贯穿三个学科的发展,并在当下进行了深入、升华,不仅在研究范式上形成了新的交叉整合,而且共同提升了中国音乐学更多完整的学术品格,可以说,中国音乐史学和传统音乐研究及Ethnomusicology在最终的研究道路上实现了殊途同归。
——评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