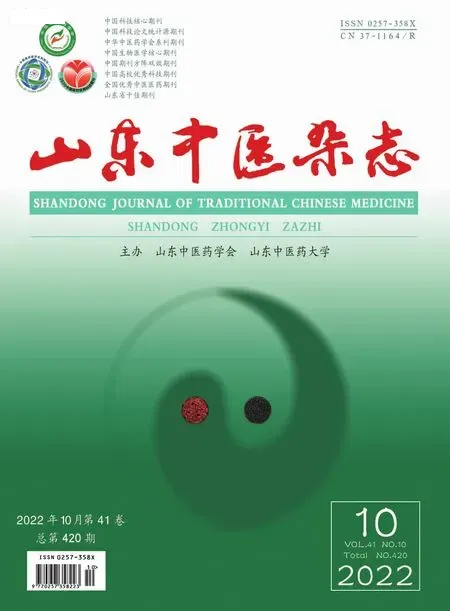补肾活血法为基础治疗灾难性抗磷脂综合征验案
姜洪叶,刘世巍,李昕潼,邓秀敏,王佳喆,袁丽莎
(1.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2.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肾病内分泌科,北京 100102)
1 病历资料
患者男,59岁,因“意识模糊10 d伴无尿3 d”于2018年8月20日就诊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肾病科。刻下症见:神志不清,躁动不安,乏力气短,双下肢水肿,无尿,三日未行大便,便干色黑。舌淡暗,边有瘀点,苔白厚,脉沉涩。
8月10日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意识模糊,伴言语不利在外院就诊,头颅CT示:右侧颞枕交界斑片状低密度影,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外院予疏血通、桂哌齐特静脉滴注,以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脑供血和脑代谢;并用头孢呋辛、拉氧头孢抗感染等。治疗后患者病情未好转,肾功能迅速恶化,为求进一步治疗转入望京医院。既往房颤病史8年,间断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治疗;血小板减少病史5年,最低至50×109/L,口服醋酸泼尼松片2个月后自行停药;2013年脑梗死病史,遗留左下肢活动不利。入院化验检查:白细胞4.48×109/L,红细胞2.28×1012/L,血小板48×109/L,血红蛋白78 g/L,白细胞介素-6 79.94 pg/mL,降钙素原30.51 ng/L,C-反应蛋白50.86 mg/L,D-二聚体10.83 g/L,纤维蛋白原1.51 g/L,血肌酐865.0 μmol/L,血尿素氮36.8 mmol/L,总蛋白54.89 g/L,白蛋白28.44 g/L,肌酸激酶409 U/L,肌红蛋白680 ng/mL,B型钠酸肽(BNP)1680 ng/mL,乳酸脱氢酶431 U/L。类风湿因子、肿瘤标志物、甲状腺功能均未见异常。血管超声示:右上肢浅静脉血栓形成、双侧股静脉血栓形成。查体:意识模糊,精神差,言语不清,平车推入病房。全身皮肤及黏膜未见黄染及出血点。桶状胸,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心界扩大,心率132次/分,节律绝对不齐,未闻及心脏杂音。腹部膨隆,质软,叩诊呈鼓音,肝脾无明显压痛及叩击痛。左上肢肌力3级,左下肢肌力2级,右侧肢体肌力正常,肌张力及腱反射均减退,双下肢呈中重度凹陷性水肿。请风湿科会诊:该老年患者系急性多系统损害,存在急性肾衰竭、脑梗死、细菌性肺炎、多处血栓形成、血小板减少等。考虑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可能性较大,建议完善抗核抗体谱、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CA)、抗磷脂抗体(APL)、血小板抗体(PAIgG)检查。患者短期内尿量急剧减少,肾功能迅速衰竭,病情危急,立即进行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超滤量2000 mL,隔日1次,密切观察基本生命体征。同时予达肝素钠10 000 IU每日1次皮下注射抗凝,左氧氟沙星抗感染等治疗。
8月21日实验室报告:抗核抗体谱、ANCA、PAIgG均阴性,抗心磷脂抗体(ACA)IgM 129 U/mL,抗β2糖蛋白ⅠIgM 95.1 U/mL。结合高滴度APL抗体及相关临床表现,可初步诊断为灾难性抗磷脂综合征(CAPS)。立即予甲基强的松龙1 g(日1次×3 d)及免疫球蛋白400 mg/kg(3 d)静脉滴注治疗,后予醋酸泼尼松片每日50 mg维持治疗。中医诊断为水肿,辨证属肾阳亏虚、瘀结水留证。治以温肾暖脾、破血泄浊。处方:制附子(先煎)20 g,肉桂20 g,肉苁蓉15 g,茯苓30 g,白芍20 g,白术20 g,泽泻30 g,桃仁15 g,红花15 g,水蛭10 g,虻虫5 g,酒大黄(后下)15 g,芒硝(冲服)15 g。14剂,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分服。
9月5日二诊:服药后,每日泻下大量暗黑色大便,便后神志好转,呼之能应,躁动不安减轻,双下肢水肿减退,尿量逐渐增多,乏力气短。舌质暗,但较前浅,边有瘀点,苔白腻,脉沉涩。处方:前方加鸡血藤20 g、丹参20 g、熟地黄30 g、当归20 g。14剂,煎服法如前。复查血管超声示右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血小板降至36×109/L,但未见明显出血征象。停用达肝素钠,改用华法林钠片每日1.5 mg口服抗凝。
9月20日三诊:服药后患者神志清醒,交流可言语回应,双下肢水肿明显消退,大小便可,但后背与双臂皮肤出现多处紫癜,大小不等,乏力气短明显。舌质浅暗,舌边瘀点少许,苔白腻,脉沉涩。处方:前方去水蛭、虻虫,加人参20 g、生黄芪30 g、三七粉(冲)5 g、虎杖15 g、仙鹤草15 g。14剂,煎服法如前。复查血管超声示右侧头静脉血栓形成,急查血小板16×109/L。停用华法林钠片抗凝,立即输注血小板1单位。
10月5日四诊:服药后患者精神明显好转,无明显乏力气短,皮肤紫癜逐渐消退,大小便正常。患者诉时有口干舌燥,饮水多。舌质浅暗,舌边瘀点少许,苔白少津,脉沉细涩。处方:上方加生地黄30 g、麦冬20 g、山茱萸15 g、五味子10 g。14剂,煎服法如前。复查血管超声示左侧股浅静脉及右上肢浅静脉血流信号较前通畅,复查血小板稳定在60×109/L以上,继续予华法林钠片口服,使凝血功能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在2~3之间。
患者整体情况明显改善,药证相符,临证加减用药。继续服药3个月后,患者神志清楚,精神正常,口干舌燥好转,大小便正常,生活基本自理。复查血管超声血栓全部再通,血流信号良好,抗心磷脂抗体IgM从129 U/mL降至18 U/mL,抗β2糖蛋白ⅠIgM从95.1 U/mL下降至11 U/mL,血小板稳定在100×109/L以上,血肌酐由入院时865.0 μmol/L降至125 μmol/L,遂未再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好转出院后,规律门诊服药1年余,病情稳定,未有复发情况,激素也逐渐减量至停服。
2 分析与讨论
2.1 灾难性抗磷脂综合征(CAPS)临床现状
CAPS是Asherson[1]在1993年 首次 提出,实验室检查存在高滴度抗磷脂抗体,临床表现为短期内多处血栓形成,且多为静脉血栓,并迅速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CAPS极为罕见,患病率大约为1/20万,病情急骤,来势凶险,经过积极治疗后死亡率仍可达到37%[2]。由于临床上误诊率和误治率较高,此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常常会被低估。本病在任何年龄都可发病,但中青年患者所占比例较多,集中在30~50岁[3-4]。
CAPS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还未完全明确,目前认为感染、外科手术术后、抗凝药物的中断或不足、药物使用不当等都可能会诱发本病[5]。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是因为全身多处血栓形成引起各个器官缺血及缺氧,损害程度与血栓形成的大小数量和范围等有关,常常累及的器官主要包括肾脏、肺脏、心脑血管、皮肤等,少数累及胃肠道、脾脏及肾上腺等[3]。治疗方面,普遍应用抗凝治疗、激素治疗、血浆置换和/或丙种球蛋白三联治疗,此类疗法存活率最高[6]。此外,还有利用利妥昔单抗、依库珠单抗、羟氯喹、去纤苷等治疗,但确切疗效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7]。
2.2 对CAPS的中医认识
中医文献中并未有类似CAPS的病名,根据其发病特点和临床表现可将其进行相关证候分类。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多发血栓贯穿始终,其与中医血瘀证及络病有共通之处,可将其归属于血瘀证或络病范畴。因瘀血停于身体各部可引起不同的病证,故该病临床始发症状复杂多样。瘀滞血脉之中,表现为肢体疼痛、麻木,皮肤苍白或青紫甚至皮肤溃烂,可归于中医学脉痹范畴,正如《素问·痹论》所云:“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瘀血停滞于肾,影响气血运行,日久损耗阳气则肾阳不足,蒸腾气化失司,气不化水,是以“无阳则阴无以化”,故水液不能从小便而去,而停聚于周身,表现为水肿,尿少甚至无尿等,可将其归于中医学水肿范畴,如《血证论》所说:“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瘀血阻滞脑络,血行受阻而溢于脉外,气血不能濡养脑络与经脉,表现为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不利,偏身麻木等,可归于中医学中风范畴,如《灵枢·刺节真邪论》所云:“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枯槁”;此外,当瘀阻心脉、肝胆等时,可归属于中医学心悸、癫狂、黄疸等范畴,邪气侵扰日久,正气亏虚,五脏俱损,可按虚劳治之。
中医学认为本病临床表现复杂多变,极易误诊误治,导致病情迁延不愈,久病及肾,邪气入络,最终演变成肾虚血瘀之证。肾虚主要与肾之精、气、阴、阳亏损有关,这些与血瘀形成有密切的联系。《素问·上古真天论》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藏精,精化气,气可分阴阳,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肾虚,从而引起血瘀。肾精不足,精亏则血少,血行迟缓而成血瘀。肾气亏虚,无力鼓动血行,血滞脉中而成血瘀,正如《医林改错》所说:“元气即虚,必不能达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肾阴亏虚,阴虚阳亢,虚热内生,阴液损耗,血液黏滞而血行不畅成瘀,王清任也说:“血受热则煎熬成块”。《素问·调经论》曰:“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肾阳亏损,阳气无力温煦血脉,寒凝血滞则血瘀。反过来瘀血也会阻滞气血运行,五脏得不到气血濡养,导致五脏亏损,病久及肾以致肾虚。因此,病至后期,肾虚与血瘀往往互相影响,共同存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说:“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可见血瘀与络脉关系十分密切。在以中医理论指导治疗此病时,多以补肾活血通络法为基础辨证加减用药。
2.3 病案分析
此例患者年近花甲,年老体弱,肾精不足,精不化气,气虚无力行血,加之基础疾病较多,邪气易侵扰五脏,影响脏腑功能,而生痰瘀浊毒之邪。《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临证指南医案》亦指出:“肾藏精,精血相生,精虚则不能灌溉诸末,血虚则不能营养筋骨。”肾精亏损,无以化气血,气血不足以致脏腑失养,邪气易侵袭人体而引发疾病。《灵枢·营卫生会》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血证论》又言:“瘀血不行,则新血断无生理……盖瘀血去则新血易生,新血生而瘀血自去”。老年人气血亏虚,推动无力,血行不畅致瘀,瘀血阻滞体内反过来影响气血运行,脏腑失于濡养,功能失常,生机受阻则影响新血的形成。《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肾主藏精,精以化气血,气分阴阳,肾阴为一身阴气之本,“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本,“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8]。肾之精气充足,气血化生有源,气行则血行,而无血瘀之弊。因此,此病的关键病机是肾虚血瘀,治疗上应以补肾活血法为基础辨证加减用药。
初诊以溯本探因,明辨病机为原则,根据其临床表现,辨为肾阳亏虚、瘀结水留之证,予真武汤合抵当汤加减温肾暖脾、破血泄浊。方中重用附子,以其辛温之性壮肾之元阳,则水勿妄行;配伍肉桂、肉苁蓉,辛甘温热以助振奋肾阳,阳气充而津可化也;白术之温燥以培脾土,则水有所制;茯苓之淡渗,佐白术培土之力,制水而兼有利水之妙也;泽泻甘寒以制诸药温燥之性,淡渗以助利水渗湿之功;白芍酸收苦降,以亟收散漫之阳气而归根;大黄苦寒以泄下逐瘀,佐芒硝增强其泻下之效,使邪气从下焦而去;桃仁、红花相须为用,水蛭、虻虫咸苦相合,以助活血化瘀通络、消癥破积之功。方中施药补泻并用,补不留邪,泻不伤正,共助温补脾肾、破血泄浊之功效。
二诊邪毒从二便分消,诸症减轻,说明药符其证。以“离经既瘀,疏通为要”为原则,兼以养血,治病求本,防血复动。予鸡血藤、丹参增强活血通络之力,加熟地黄、当归滋阴养血。消瘀以散旧血,养血以生新血,取“旧血不去,则新血断然不生,而新血不生,则旧血亦不能自去也”之意。血小板持续下降,但并未有出血征象,评估患者高凝与出血风险后,改用华法林口服抗凝。华法林主要通过抑制维生素K依赖的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的生成和活化阻断凝血过程,从而发挥抗凝作用,临床上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心脏瓣膜病、心房颤动等疾病,主要与内源性凝血机制有关,对血小板影响不大[9]。
三诊患者症状明显好转,但出现皮下出血,乏力气短,此乃邪郁日久,损耗正气,气不摄血,血溢脉络而渗于皮下。以既已出血,塞流为先,益气同治为原则。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脏气,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神农本草经》中说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重用生黄芪甘温以补气行血,气旺则血行,并有利水之效,补中有动,走而不守,内外皆达。研究发现,黄芪对血流动力学有改善作用,并且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10]。人参之补迅而虚,黄芪之补重而实,二者配伍,补气之力相得益彰。去水蛭、虻虫以防其峻猛破血加重出血风险,取三七粉既能化瘀,又可止血,辅以虎杖活血散瘀,仙鹤草收敛止血,一敛一散,增强其止血而不留瘀、活血而不伤正之效。《灵枢·本藏》曰:“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脉中气血充足,阴营阳卫,血行其道,无妄行之虞。患者血小板严重下降,出血风险增加,故停用华法林抗凝,输注血小板以快速提高血清中血小板含量,防止重要脏器出血而加重病情。
四诊皮下紫癜消退,乏力气短好转,治疗过程反复出血,或服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攻伐峻猛的药物,日久必会耗伤阴血津液,应以扶正补虚,培元固本,以善其后为原则。予生地黄、麦冬取增液汤之意,二者合用,增加其滋阴增液、生津止渴之力。山茱萸、五味子益气生津,收涩外散之阳,所谓“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患者多处血栓再通,血小板也稳定上升,继续予华法林抗凝,根据INR调整用量。后又调方多次,均在前方基础上辨证加减灵活用药,诸药合用,益肾滋阴温阳以固其本,活血化瘀通络以治其标,扶正而不壅滞,祛邪而不伤正。
此例患者病变在血,血瘀贯穿于病程始终,在治疗过程中因血小板减少发生出血,出血过多过久必定会损耗阴血。因此,此例患者出现血瘀→出血→血虚的中医病机演变过程,故病在血以调血为主,分析血瘀、出血、血虚的侧重点,进而以活血、止血、养血之法论治。在调血的同时,重视温养肾元,扶助正气,此也是调节免疫力的体现,从而减少激素的用量以及使用时间。对于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的相似疾病时,抓准病机是关键,切不可局限于某一症状,应遵循“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原则,调其虚实,澄之源,清其流,使脏腑气血和调,则病安从来。
3 小结
CAPS发病率极低,病势急骤,病情复杂,临床上早期极易误诊为某一脏器的损伤。因此,早期发现血小板减少伴有血栓形成时,应尽快完善对APL抗体的检查以明确诊断。西医治疗过程中长期使用大剂量激素,会给病情带来极大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这也是引起患者病情加重的常见原因。早期联合中医药治疗此病尤为必要,中医注重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发挥了其方证结合、因人施治等独特优势,不但可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还能调节机体免疫力以减少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用量,从而减少不良反应。但是,此病的临床表现复杂多变,如何正确把握疾病的病情发展变化,了解不同阶段下证候变化规律,从而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分析、归纳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