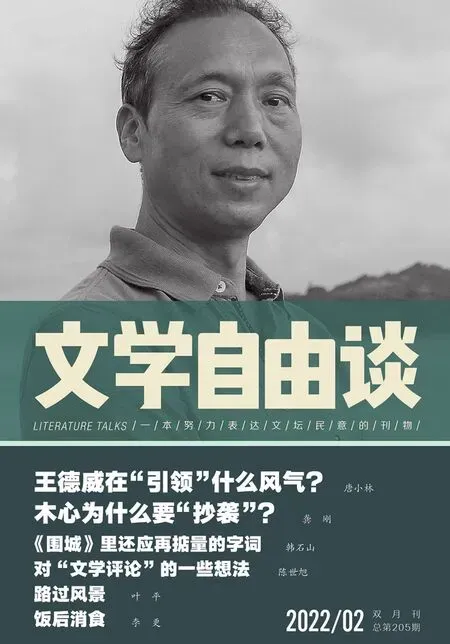巴别尔的敖德萨保罗·策兰的乌克兰
□狄 青
一
伊萨克·巴别尔的身份“复杂”,他是苏联作家,却出生并成长于乌克兰的敖德萨;他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大师之一,却因了犹太人的身份从降生那日起便受尽屈辱和煎熬,这种命运一直与他如影随形到1940年,那一年他被当局秘密处死。他是学霸,有阅读各种文学书籍过目不忘的本领,却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被心仪的学校拒之门外;1911年,同样是因为犹太人身份而未被家乡的敖德萨大学所录取。他十几岁就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各个文学期刊投稿,却屡遭退稿,他的犹太人身份依旧是被频繁退稿的一个因素,直到他遇到了作家高尔基。高尔基实在是太欣赏巴别尔的文学才华了,不仅在自己主编的《编年史》杂志1916年11月号上发表了巴别尔的两篇短篇小说,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关系为这个小伙子提供文学机会。正是因为高尔基以及爱伦堡这些作家不遗余力提携与扶掖,1936年6月,巴别尔成为苏联作家协会首席作家之一,与另一位同样身为犹太裔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同样获赠了一幢别墅,巴别尔似乎也迎来了自己短暂的“人生巅峰”?
事实证明,那的确是巴别尔一生中短暂的“辉煌”。更多的时候,他都在与命运拼死较劲儿。为了糊口也为了理想,他在酒馆做帮佣,在罗马尼亚作战,在契卡做外事翻译,在征粮队做征粮员,在通讯社做记者。1920年,巴别尔化名柳托夫(因为巴别尔太像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了),随哥萨克第一骑兵军参加了苏波战争。他根据在此期间的所见所闻陆续写出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品,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骑兵军》。
许多人知道巴别尔都源于《骑兵军》,不知为什么,我从《骑兵军》中似乎找到了雷蒙德·卡佛作品风格的真正源头。但我更喜欢的还是巴别尔的另一部代表作——《敖德萨故事》,并由此认识了敖德萨这座城市。这部以黑海岸边的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萨为背景的小说,严格意义上来讲似乎并不是一部长篇小说(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部散文作品),而是一本系列故事集,当然,说它是短篇小说集也许更恰当一些。在众多的故事里,人物是互相穿插和纠缠的,但却让读者得以更直观地了解到敖德萨这座城市所发生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故事。我一直以为是这本《敖德萨故事》启发了欧美某些作家以及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中各式各样的以城市命名的小说“故事集”的泛滥。
巴别尔是苏联人,也是乌克兰人,但无论是作为苏联人的身份还是乌克兰人的背景,都不能真正“说明”他,他永远都有另外一个抹不去的身份——犹太人。在《我的鸽子窝的故事》中,巴别尔讲述了自己童年为了得到一个鸽子窝所经历的悲惨故事。巴别尔九岁那年,父亲告诉他,如果他能考入当地的中学预备班,就送他三对鸽子;而巴别尔的堂祖父还为他做了一个鸽子窝。可是敖德萨的学校把对犹太孩子的录取率定得很低——一个四十个名额的班,犹太孩子的名额仅能给两个。虽然巴别尔的考试成绩很优异(没错,他的成绩总是很优异),但另一个富商因向学校“捐赠”了五百卢布,便让他的儿子顶替了巴别尔的名额。巴别尔没办法,只能直接报考中学一年级。在一年之内,他背熟了三本书,直接考上了中学一年级,可当他兴高采烈地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的脸色却难看如死灰,巴别尔写道:“她痛苦而怜惜地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残疾人,因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我们家有多么不顺。”这一幕生动地告诉读者,犹太人当年在欧洲所遭受的侮辱、迫害与歧视。
灾难果然随之而来,给巴别尔做鸽子窝的堂祖父被打死了。巴别尔写到:“绍伊尔卧在锯木屑中,胸脯被打烂了……他两腿岔开,很脏,肤色发紫,而且已经僵硬。”
当然,巴别尔所讲述的敖德萨故事并不是只有上述沉重的底色。与生下来就离开敖德萨的阿赫马托娃,以及曾在敖德萨短暂生活过的普希金、契科夫、蒲宁、高尔基等人不同,巴别尔与敖德萨是撕扯不开的关系。在他死后五十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伊萨克·巴别尔名列第一。
爱伦堡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因为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在写自己的东西。”海明威认为巴别尔的作品比自己的更凝炼。而博尔赫斯则认为巴别尔的每段文字都如诗歌一样优美。约翰·厄普代克对巴别尔的评价则简短而有力:“他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敖德萨始建于1794年5月,是当时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后重新建造的,她是想在乌克兰大草原南端再造一座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德国人,敖德萨的前两任总督分别是身经百战的法国军人黎塞留和兰热龙,这令敖德萨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城市”,敖德萨从一开始就沾染了“混血”的气息。这在《敖德萨故事》一书中有所呈现。
说实话,我不觉得巴别尔的小说(故事)好读,一个个短篇之间的组合,读来也并非十分顺畅。许多时候其结构甚至是矛盾和“匪夷所思”的,但却又是被作家所精心设计的。以《金蔷薇》一书而成名的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读到巴别尔的作品后,就认为“一位俄语的魔术师诞生了”。这个评价是中肯和专业的,面对巴别尔这个文学“魔术师”,读者的阅读智力,其实是需要经受一番考验的。
敖德萨人在2010年,也即作家辞世七十周年之际,在敖德萨为伊萨克·巴别尔竖立了一尊雕像。雕像就位于离巴别尔故居不远的地方,虽然看上去并不雄伟,但巴别尔终于与他热爱和描摹的这座城市融为了一体。也是在2010年,敖德萨又特别设立了“伊萨克·巴别尔文学奖”。
1990年,克格勃档案解禁。有关巴别尔的审讯和死亡细节被曝光。1939年5月13日,巴别尔被诬为西方间谍被捕。在最后的陈述中,他说:“我完全无罪,从没做过间谍,也从没进行过任何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在审问时我做的证词是诽谤我自己。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二
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保罗·策兰是德国人,抑或说他是德国的犹太人。这当然是因为他一生都在用德语创作,并且他的诗歌在德语国家内受到热烈追捧。其成名作《死亡赋格》曾震撼整个德国,令他先后获得了德国不莱梅文学奖以及德语国家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当然,保罗·策兰被认作是德国人也与其作品始终受到德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们的一致推崇有关,这些人中就包括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堪称世界级的德国文化巨匠。而在保罗·策兰之前,受到如此推崇的德语文人大约也只有卡夫卡、里尔克以及托马斯·曼了。
但是,保罗·策兰却并没有在德国真正生活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代表过德国参与过任何文学活动。而保罗·策兰的父亲以及他无比深爱的母亲却都是死于德国人之手。他的母亲是在乌克兰的米哈伊洛夫集中营被纳粹军官开枪打穿了脖子,他自己也曾在二战中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流离失所。
于是,又有许多人把保罗·策兰的“国籍”划归到了乌克兰,尤其是在乌克兰被全世界目光所聚焦的当下。保罗·策兰这个名字已然被大量线上线下的媒体纳入到了乌克兰著名作家诗人行列,我想这当然与他的那首著名的诗作《冬》有关——
下雪了,妈妈,雪落在乌克兰:
救世主的光环是万千颗粒的愁苦。
在这里,我的泪水够不到你。
往日的招手只留下那默默傲世的一别……
我们就要死去:棚屋你何不眠?
这风,也像被驱赶着那样逃散……
是他们吗,那些在炉渣中冰凉的人——
心旌飘飘,臂是烛台?
我在黑暗中依然故我:
柔能解愁,刚则断肠?
我的星辰中有一架洪亮的竖琴,
琴弦生风,直到根根扯断……
弦上偶尔悬着一朵时光玫瑰。
正在熄灭。一朵。永远的一朵……
那会是什么呢,妈妈:成长还是创伤——
是否我也陷进了乌克兰的积雪?
是的,保罗·策兰在他的作品里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乌克兰,但是,就像他没有在德国真正生活过一样,他实际上也并没有在他笔下的乌克兰真正生活过,抑或说保罗·策兰并没有在作为国家概念的乌克兰生活过。严格来说,保罗·策兰的“祖国”是罗马尼亚——这倒很像是另一位用德语写作的罗马尼亚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赫塔·米勒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的蒂米什瓦拉,而保罗·策兰则出生于原属罗马尼亚北部的切尔诺维茨。切尔诺维茨作为地名最早是出现在奥匈帝国的版图之上的,1918年,奥匈帝国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土崩瓦解,切尔诺维茨遂成为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两年后,也就是1920年,保罗·策兰出生,换句话说,保罗·策兰出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尼亚。1938年,保罗·策兰离开家乡前往法国巴黎上医学院预科,又是在两年后的1940年,苏联军队占领了他的家乡切尔诺维茨;1941年,纳粹德国又攻占了切尔诺维茨;再之后,切尔诺维茨便被划归到了乌克兰,一直到今天。
1938年,当保罗·策兰乘火车途径柏林时,正赶上纳粹德国开始对犹太人进行第一轮大屠杀。后来他承认,那次的经历令他终生难忘。作为一名犹太裔诗人,他的文字从此就再没有脱离过苦难与死亡。
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裔哲学家阿多诺认为:“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保罗·策兰1945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死亡赋格》一诗,以对纳粹邪恶本质的强力控诉和深刻独创的艺术感染力震动了战后西方文坛,《死亡赋格》在二战后的德语国家可谓家喻户晓,成为德语“废墟文学”中的重要代表作品。阿多诺因此收回了他的那句话,又说了另外一段著名的话:“长期受苦的人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
人们普遍认为是在1970年4月20日的那一天,保罗·策兰从巴黎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上投河自尽的,直到十天后的5月1日,一名垂钓者才在塞纳河下游七英里处发现了保罗·策兰的尸体。
据说最后摆放在保罗·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传记。他在其中的一段上面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段余下的部分则未画线,余下的部分是:“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
二战之后,保罗·策兰与乌克兰变得再也撕扯不开。因为他的父母、亲人,包括他童年少年时候的朋友,都死在了纳粹在乌克兰建造的集中营里。
乌克兰在《冬》这首诗的第一行里出现,负载了保罗·策兰复杂的情绪,既有对其父母惨死于乌克兰的剜心之痛,亦有对冬季雪落在故乡的向往与怅惘。他最后问他心爱妈妈的那句话——是否我也陷进了乌克兰的积雪?令无数读者动容;而这句话,在我看来,恰是保罗·策兰对于自身破碎命运的比附,因为他的命运就像不断见证着这世间苦难的乌克兰冬天的积雪一般。
保罗·策兰的后期作品多半阴暗晦涩,表现了对世事百态的极度失望和厌倦。母亲的死是他的诗歌起点,也是他的诗歌终点。离世前,保罗·策兰已患上精神分裂症,而他喜欢的诗人荷尔德林,同样也患有精神分裂症。
如今,在我们周遭,有那么多大学里的博导硕导、研究院里的这家那家,文坛上的大腕二腕,活得花团锦簇风生水起,却是张嘴保罗·策兰,闭嘴伊萨克·巴别尔。他们因为“研究”抑或消费着保罗·策兰们而赚得盆满钵满,而享受着各种无比优厚的待遇和高不可攀的名分,却既不愿经受保罗·策兰悲痛生活之万一,更不愿感受保罗·策兰内心痛苦之一厘。
保罗·策兰当初其实是诗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名字,说是他的笔名似乎也未尝不可,“策兰”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隐藏或保密了什么”的意思,保罗·策兰要隐藏抑或保密的事情是什么呢?或许它们就埋藏在乌克兰冬季厚厚的积雪之下。